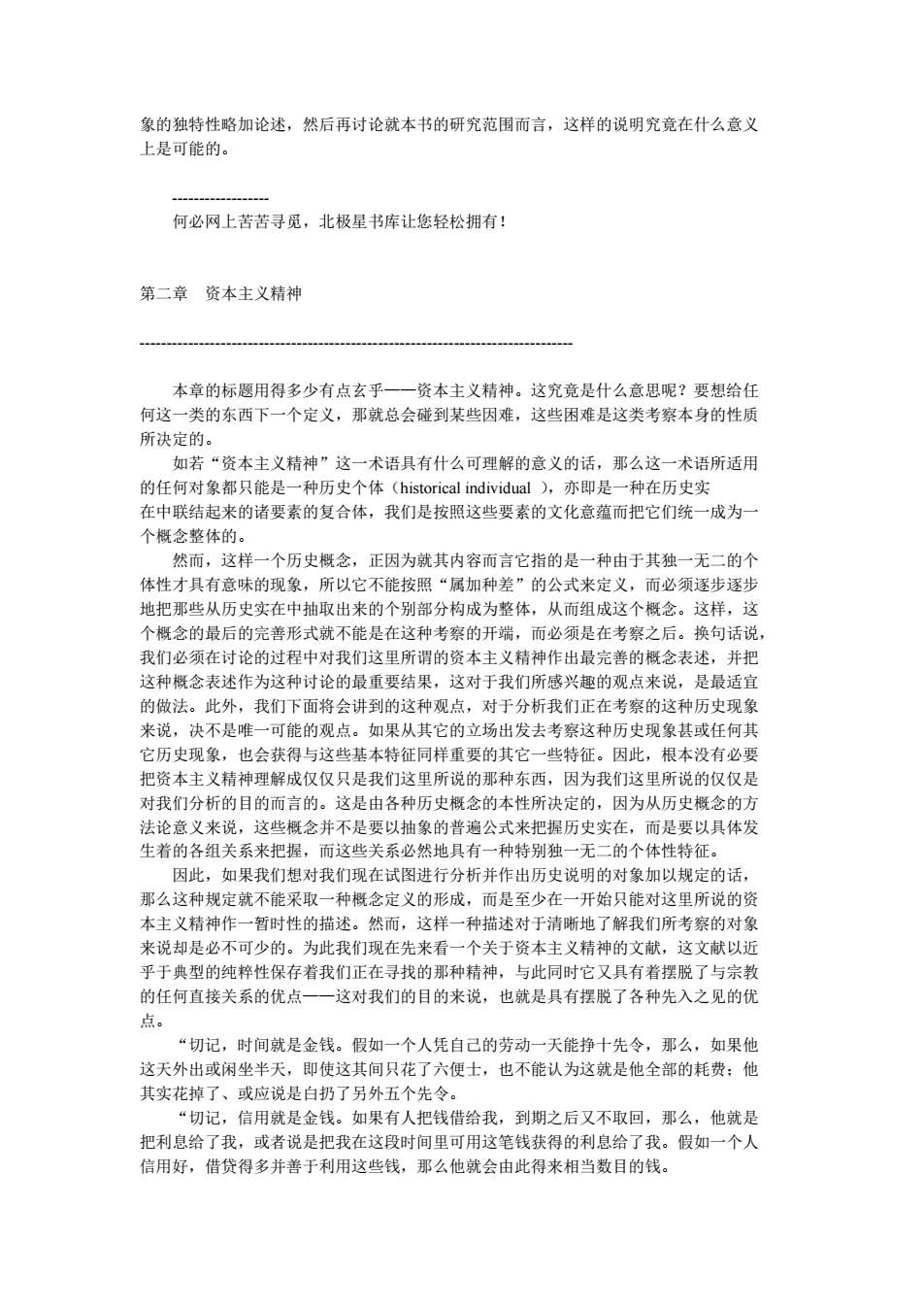
象的独特性略加论述,然后再讨论就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这样的说明究竞在什么意义 上是可能的。 何必网上苦苦寻觅,北极星书库让您轻松拥有! 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 本章的标题用得多少有点玄乎一一资本主义精神。这究竞是什么意思呢?要想给任 何这一类的东西下一个定义,那就总会碰到某些因难,这些困难是这类考察本身的性质 所决定的。 如若“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具有什么可理解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一术语所适用 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historical individual),亦即是一种在历史实 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 个概念整体的。 然而,这样一个历史概念,正因为就其内容而言它指的是一种由于其独一无二的个 体性才具有意味的现象,所以它不能按照“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而必须逐步逐步 地把那些从历史实在中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这样,这 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在讨论的过程中对我们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作出最完善的概念表述,并把 这种概念表述作为这种讨论的最重要结果,这对于我们所感兴趣的观点来说,是最适宜 的做法。此外,我们下面将会讲到的这种观点,对于分析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种历史现象 来说,决不是唯一可能的观点。如果从其它的立场出发去考察这种历史现象甚或任何其 它历史现象,也会获得与这些基本特征同样重要的其它一些特征。因此,根本没有必要 把资本主义精神理解成仅仅只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东西,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仅仅是 对我们分析的目的而言的。这是由各种历史概念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从历史概念的方 法论意义来说,这些概念并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历史实在,而是要以具体发 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而这些关系必然地具有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 因此,如果我们想对我们现在试图进行分析并作出历史说明的对象加以规定的话, 那么这种规定就不能采取一种概念定义的形成,而是至少在一开始只能对这里所说的资 本主义精神作一暂时性的描述。然而,这样一种描述对于清晰地了解我们所考察的对象 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献,这文献以近 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精神,与此同时它又具有着摆脱了与宗教 的任何直接关系的优点一一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也就是具有摆脱了各种先入之见的优 点。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 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 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 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 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
象的独特性略加论述,然后再讨论就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这样的说明究竟在什么意义 上是可能的。 ------------------ 何必网上苦苦寻觅,北极星书库让您轻松拥有!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 本章的标题用得多少有点玄乎——资本主义精神。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想给任 何这一类的东西下一个定义,那就总会碰到某些因难,这些困难是这类考察本身的性质 所决定的。 如若“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具有什么可理解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一术语所适用 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historical individual ),亦即是一种在历史实 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 个概念整体的。 然而,这样一个历史概念,正因为就其内容而言它指的是一种由于其独一无二的个 体性才具有意味的现象,所以它不能按照“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而必须逐步逐步 地把那些从历史实在中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这样,这 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在讨论的过程中对我们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作出最完善的概念表述,并把 这种概念表述作为这种讨论的最重要结果,这对于我们所感兴趣的观点来说,是最适宜 的做法。此外,我们下面将会讲到的这种观点,对于分析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种历史现象 来说,决不是唯一可能的观点。如果从其它的立场出发去考察这种历史现象甚或任何其 它历史现象,也会获得与这些基本特征同样重要的其它一些特征。因此,根本没有必要 把资本主义精神理解成仅仅只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东西,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仅仅是 对我们分析的目的而言的。这是由各种历史概念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从历史概念的方 法论意义来说,这些概念并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历史实在,而是要以具体发 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而这些关系必然地具有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 因此,如果我们想对我们现在试图进行分析并作出历史说明的对象加以规定的话, 那么这种规定就不能采取一种概念定义的形成,而是至少在一开始只能对这里所说的资 本主义精神作一暂时性的描述。然而,这样一种描述对于清晰地了解我们所考察的对象 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献,这文献以近 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精神,与此同时它又具有着摆脱了与宗教 的任何直接关系的优点——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也就是具有摆脱了各种先入之见的优 点。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 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 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 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 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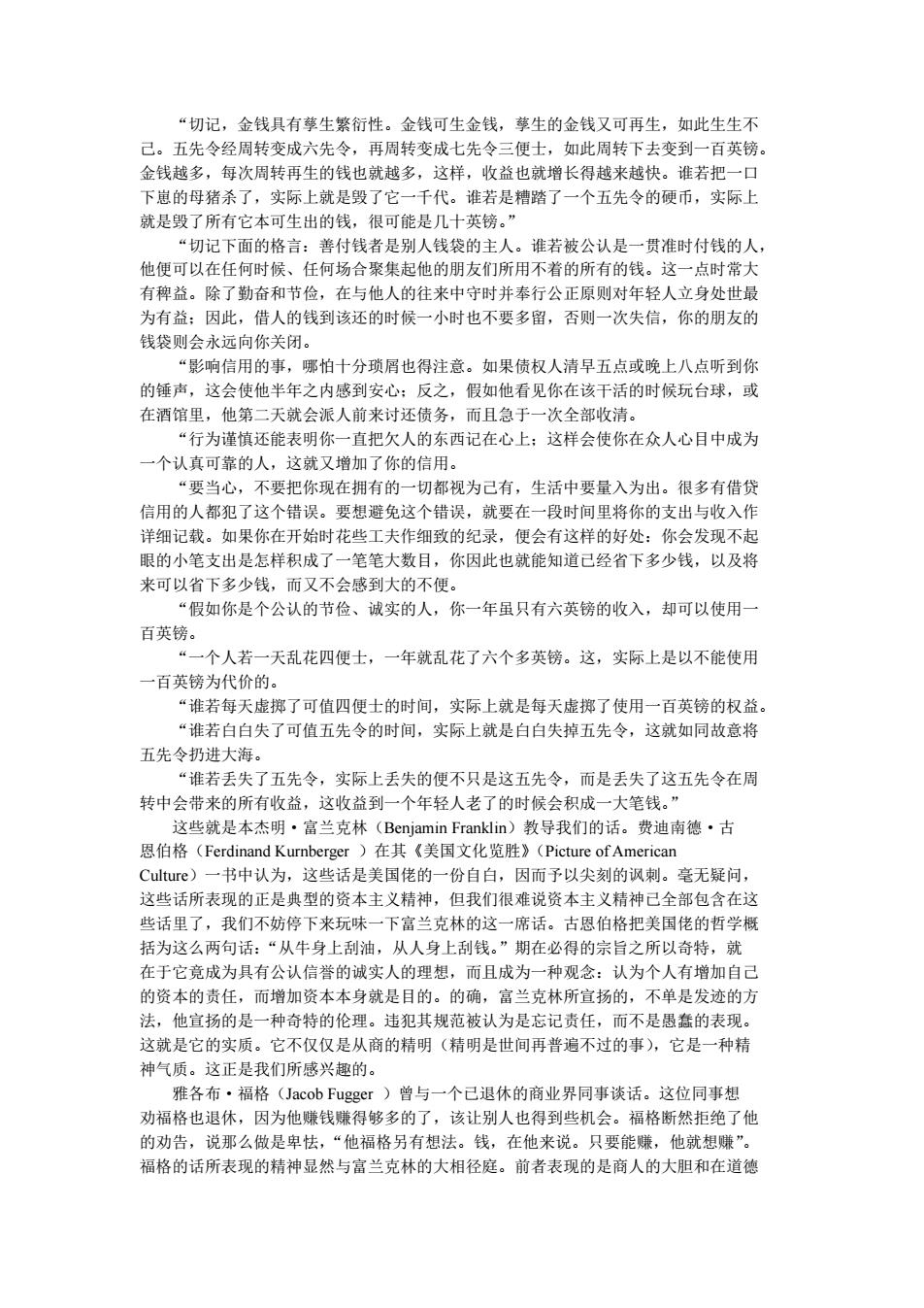
“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 己。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 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谁若把一口 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谁若是糟踏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 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 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 有稗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 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 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 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 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 “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 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很多有借贷 信用的人都犯了这个错误。要想避免这个错误,就要在一段时间里将你的支出与收入作 详细记载。如果你在开始时花些工夫作细致的纪录,便会有这样的好处:你会发现不起 眼的小笔支出是怎样积成了一笔笔大数目,你因此也就能知道已经省下多少钱,以及将 来可以省下多少钱,而又不会感到大的不便。 “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 百英镑。 “一个人若一天乱花四便士,一年就乱花了六个多英镑。这,实际上是以不能使用 一百英镑为代价的。 “谁若每天虚掷了可值四便士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每天虚掷了使用一百英镑的权益。 “谁若白白失了可值五先令的时间,实际上就是白白失掉五先令,这就如同故意将 五先令扔进大海。 “谁若丢失了五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便不只是这五先令,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 转中会带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 这些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教导我们的话。费迪南德·古 恩伯格(Ferdinand Kurnberger)在其《美国文化览胜》(Picture of American Culture)一书中认为,这些话是美国佬的一份自白,因而予以尖刻的讽刺。毫无疑问, 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我们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己全部包含在这 些话里了,我们不妨停下来玩味一下富兰克林的这一席话。古恩伯格把美国佬的哲学概 括为这么两句话:“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期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 在于它竞成为具有公认信誉的诚实人的理想,而且成为一种观念: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 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的确,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迹的方 法,他宣扬的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 这就是它的实质。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间再普遍不过的事),它是一种精 神气质。这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雅各布·福格(Jacob Fugger)曾与一个己退休的商业界同事谈话。这位同事想 劝福格也退休,因为他赚钱赚得够多的了,该让别人也得到些机会。福格断然拒绝了他 的劝告,说那么做是卑怯,“他福格另有想法。钱,在他来说。只要能赚,他就想赚”。 福格的话所表现的精神显然与富兰克林的大相径庭。前者表现的是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
“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 己。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 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谁若把一口 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谁若是糟踏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 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 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 有稗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 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 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 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 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 “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 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很多有借贷 信用的人都犯了这个错误。要想避免这个错误,就要在一段时间里将你的支出与收入作 详细记载。如果你在开始时花些工夫作细致的纪录,便会有这样的好处:你会发现不起 眼的小笔支出是怎样积成了一笔笔大数目,你因此也就能知道已经省下多少钱,以及将 来可以省下多少钱,而又不会感到大的不便。 “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 百英镑。 “一个人若一天乱花四便士,一年就乱花了六个多英镑。这,实际上是以不能使用 一百英镑为代价的。 “谁若每天虚掷了可值四便士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每天虚掷了使用一百英镑的权益。 “谁若白白失了可值五先令的时间,实际上就是白白失掉五先令,这就如同故意将 五先令扔进大海。 “谁若丢失了五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便不只是这五先令,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 转中会带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 这些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教导我们的话。费迪南德·古 恩伯格(Ferdinand Kurnberger )在其《美国文化览胜》(Picture of American Culture)一书中认为,这些话是美国佬的一份自白,因而予以尖刻的讽刺。毫无疑问, 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我们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这 些话里了,我们不妨停下来玩味一下富兰克林的这一席话。古恩伯格把美国佬的哲学概 括为这么两句话:“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期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 在于它竟成为具有公认信誉的诚实人的理想,而且成为一种观念: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 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的确,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迹的方 法,他宣扬的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 这就是它的实质。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间再普遍不过的事),它是一种精 神气质。这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雅各布·福格(Jacob Fugger )曾与一个已退休的商业界同事谈话。这位同事想 劝福格也退休,因为他赚钱赚得够多的了,该让别人也得到些机会。福格断然拒绝了他 的劝告,说那么做是卑怯,“他福格另有想法。钱,在他来说。只要能赚,他就想赚”。 福格的话所表现的精神显然与富兰克林的大相径庭。前者表现的是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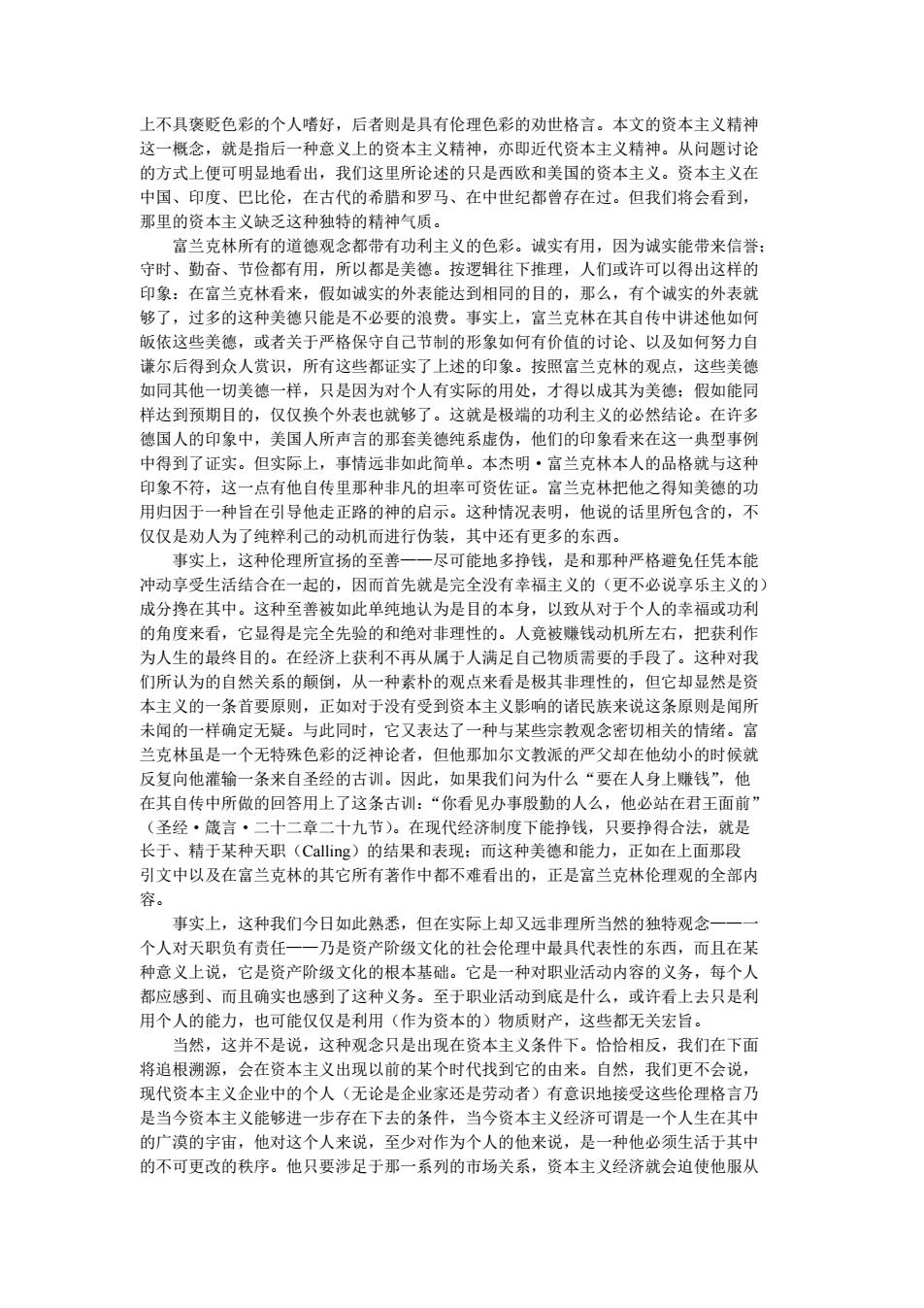
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后者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本文的资本主义精神 这一概念,就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亦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从问题讨论 的方式上便可明显地看出,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只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 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 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 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按逻辑往下推理,人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 印象:在富兰克林看来,假如诚实的外表能达到相同的目的,那么,有个诚实的外表就 够了,过多的这种美德只能是不必要的浪费。事实上,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讲述他如何 皈依这些美德,或者关于严格保守自己节制的形象如何有价值的讨论、以及如何努力自 谦尔后得到众人赏识,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上述的印象。按照富兰克林的观点,这些美德 如同其他一切美德一样,只是因为对个人有实际的用处,才得以成其为美德:假如能同 样达到预期目的,仅仅换个外表也就够了。这就是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必然结论。在许多 德国人的印象中,美国人所声言的那套美德纯系虚伪,他们的印象看来在这一典型事例 中得到了证实。但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的品格就与这种 印象不符,这一点有他自传里那种非凡的坦率可资佐证。富兰克林把他之得知美德的功 用归因于一种旨在引导他走正路的神的启示。这种情况表明,他说的话里所包含的,不 仅仅是劝人为了纯粹利己的动机而进行伪装,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一一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 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 成分搀在其中。这种至善被如此单纯地认为是目的本身,以致从对于个人的幸福或功利 的角度来看,它显得是完全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人竞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 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 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 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正如对于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诸民族来说这条原则是闻所 未闻的一样确定无疑。与此同时,它又表达了一种与某些宗教观念密切相关的情绪。富 兰克林虽是一个无特殊色彩的泛神论者,但他那加尔文教派的严父却在他幼小的时候就 反复向他灌输一条来自圣经的古训。因此,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要在人身上赚钱”,他 在其自传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这条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圣经·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 长于、精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结果和表现:而这种美德和能力,正如在上面那段 引文中以及在富兰克林的其它所有著作中都不难看出的,正是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内 容。 事实上,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 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一一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 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 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至于职业活动到底是什么,或许看上去只是利 用个人的能力,也可能仅仅是利用(作为资本的)物质财产,这些都无关宏旨。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观念只是出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恰恰相反,我们在下面 将追根溯源,会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某个时代找到它的由来。自然,我们更不会说, 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个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劳动者)有意识地接受这些伦理格言乃 是当今资本主义能够进一步存在下去的条件,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一个人生在其中 的广漠的宇宙,他对这个人来说,至少对作为个人的他来说,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 的不可更改的秩序。他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
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后者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本文的资本主义精神 这一概念,就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亦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从问题讨论 的方式上便可明显地看出,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只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 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 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 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按逻辑往下推理,人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 印象:在富兰克林看来,假如诚实的外表能达到相同的目的,那么,有个诚实的外表就 够了,过多的这种美德只能是不必要的浪费。事实上,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讲述他如何 皈依这些美德,或者关于严格保守自己节制的形象如何有价值的讨论、以及如何努力自 谦尔后得到众人赏识,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上述的印象。按照富兰克林的观点,这些美德 如同其他一切美德一样,只是因为对个人有实际的用处,才得以成其为美德;假如能同 样达到预期目的,仅仅换个外表也就够了。这就是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必然结论。在许多 德国人的印象中,美国人所声言的那套美德纯系虚伪,他们的印象看来在这一典型事例 中得到了证实。但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的品格就与这种 印象不符,这一点有他自传里那种非凡的坦率可资佐证。富兰克林把他之得知美德的功 用归因于一种旨在引导他走正路的神的启示。这种情况表明,他说的话里所包含的,不 仅仅是劝人为了纯粹利己的动机而进行伪装,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 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 成分搀在其中。这种至善被如此单纯地认为是目的本身,以致从对于个人的幸福或功利 的角度来看,它显得是完全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 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 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 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正如对于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诸民族来说这条原则是闻所 未闻的一样确定无疑。与此同时,它又表达了一种与某些宗教观念密切相关的情绪。富 兰克林虽是一个无特殊色彩的泛神论者,但他那加尔文教派的严父却在他幼小的时候就 反复向他灌输一条来自圣经的古训。因此,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要在人身上赚钱”,他 在其自传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这条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圣经·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 长于、精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结果和表现;而这种美德和能力,正如在上面那段 引文中以及在富兰克林的其它所有著作中都不难看出的,正是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内 容。 事实上,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 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 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 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至于职业活动到底是什么,或许看上去只是利 用个人的能力,也可能仅仅是利用(作为资本的)物质财产,这些都无关宏旨。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观念只是出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恰恰相反,我们在下面 将追根溯源,会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某个时代找到它的由来。自然,我们更不会说, 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个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劳动者)有意识地接受这些伦理格言乃 是当今资本主义能够进一步存在下去的条件,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一个人生在其中 的广漠的宇宙,他对这个人来说,至少对作为个人的他来说,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 的不可更改的秩序。他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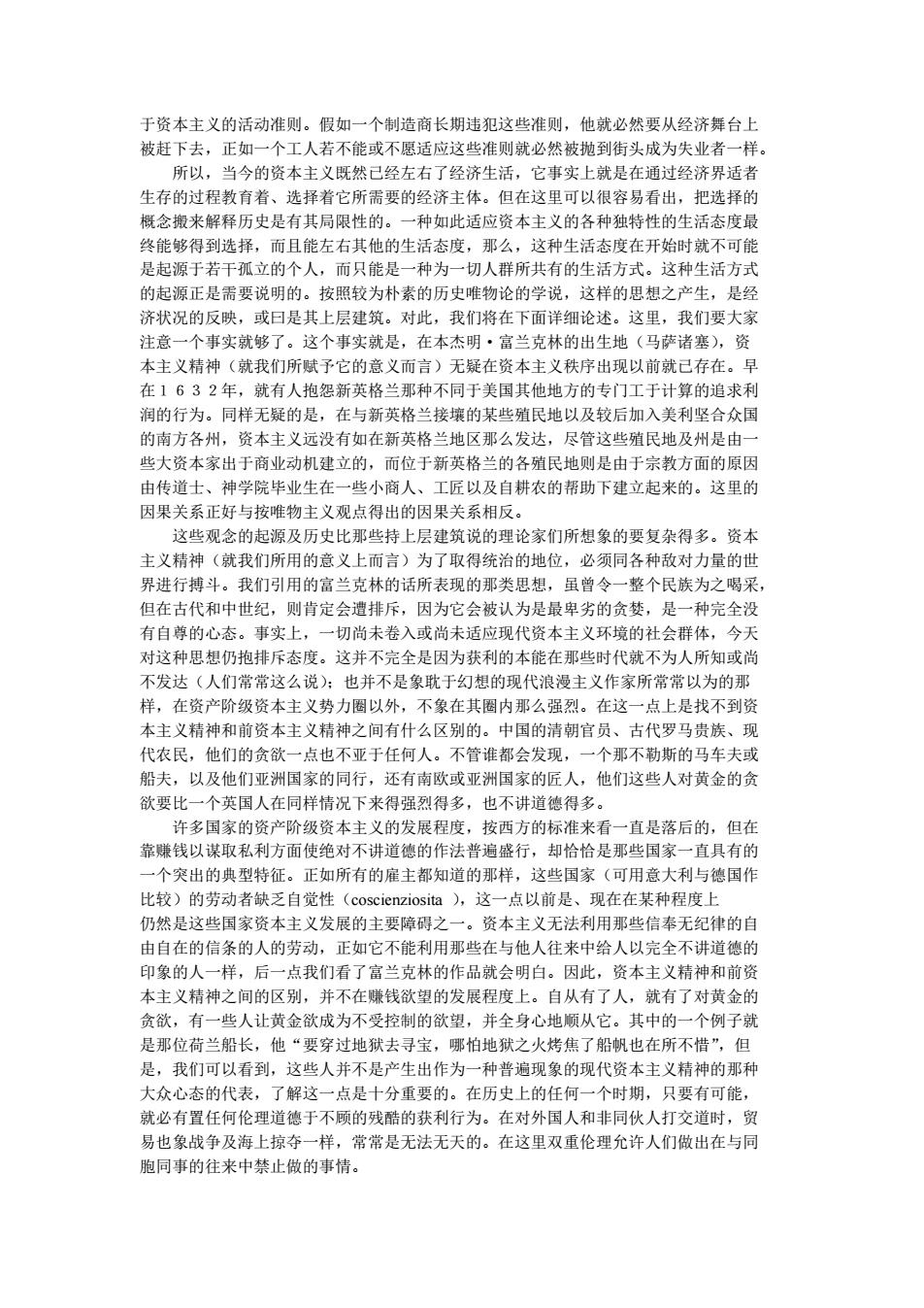
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假如一个制造商长期违犯这些准则,他就必然要从经济舞台上 被赶下去,正如一个工人若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被抛到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 所以,当今的资本主义既然己经左右了经济生活,它事实上就是在通过经济界适者 生存的过程教育着、选择着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但在这里可以很容易看出,把选择的 概念搬来解释历史是有其局限性的。一种如此适应资本主义的各种独特性的生活态度最 终能够得到选择,而且能左右其他的生活态度,那么,这种生活态度在开始时就不可能 是起源于若干孤立的个人,而只能是一种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 的起源正是需要说明的。按照较为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学说,这样的思想之产生,是经 济状况的反映,或曰是其上层建筑。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论述。这里,我们要大家 注意一个事实就够了。这个事实就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资 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言)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早 在1632年,就有人抱怨新英格兰那种不同于美国其他地方的专门工于计算的追求利 润的行为。同样无疑的是,在与新英格兰接壤的某些殖民地以及较后加入美利坚合众国 的南方各州,资本主义远没有如在新英格兰地区那么发达,尽管这些殖民地及州是由一 些大资本家出于商业动机建立的,而位于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则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 由传道士、神学院毕业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里的 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 这些观念的起源及历史比那些持上层建筑说的理论家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资本 主义精神(就我们所用的意义上而言)为了取得统治的地位,必须同各种敌对力量的世 界进行搏斗。我们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话所表现的那类思想,虽曾令一整个民族为之喝采, 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则肯定会遭排斥,因为它会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是一种完全没 有自尊的心态。事实上,一切尚未卷入或尚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社会群体,今天 对这种思想仍抱排斥态度。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获利的本能在那些时代就不为人所知或尚 不发达(人们常常这么说):也并不是象耽于幻想的现代浪漫主义作家所常常以为的那 样,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势力圈以外,不象在其圈内那么强烈。在这一点上是找不到资 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什么区别的。中国的清朝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 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不管谁都会发现,一个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 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对黄金的贪 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 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一直是落后的,但在 靠赚钱以谋取私利方面使绝对不讲道德的作法普遍盛行,却恰恰是那些国家一直具有的 一个突出的典型特征。正如所有的雇主都知道的那样,这些国家(可用意大利与德国作 比较)的劳动者缺乏自觉性(coscienziosita),这一点以前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 仍然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 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正如它不能利用那些在与他人往来中给人以完全不讲道德的 印象的人一样,后一点我们看了富兰克林的作品就会明白。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 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 贪欲,有一些人让黄金欲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地顺从它。其中的一个例子就 是那位荷兰船长,他“要穿过地狱去寻宝,哪怕地狱之火烤焦了船帆也在所不惜”,但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并不是产生出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 大众心态的代表,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 就必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在对外国人和非同伙人打交道时,贸 易也象战争及海上掠夺一样,常常是无法无天的。在这里双重伦理允许人们做出在与同 胞同事的往来中禁止做的事情
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假如一个制造商长期违犯这些准则,他就必然要从经济舞台上 被赶下去,正如一个工人若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被抛到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 所以,当今的资本主义既然已经左右了经济生活,它事实上就是在通过经济界适者 生存的过程教育着、选择着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但在这里可以很容易看出,把选择的 概念搬来解释历史是有其局限性的。一种如此适应资本主义的各种独特性的生活态度最 终能够得到选择,而且能左右其他的生活态度,那么,这种生活态度在开始时就不可能 是起源于若干孤立的个人,而只能是一种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 的起源正是需要说明的。按照较为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学说,这样的思想之产生,是经 济状况的反映,或曰是其上层建筑。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论述。这里,我们要大家 注意一个事实就够了。这个事实就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资 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言)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早 在1632年,就有人抱怨新英格兰那种不同于美国其他地方的专门工于计算的追求利 润的行为。同样无疑的是,在与新英格兰接壤的某些殖民地以及较后加入美利坚合众国 的南方各州,资本主义远没有如在新英格兰地区那么发达,尽管这些殖民地及州是由一 些大资本家出于商业动机建立的,而位于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则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 由传道士、神学院毕业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里的 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 这些观念的起源及历史比那些持上层建筑说的理论家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资本 主义精神(就我们所用的意义上而言)为了取得统治的地位,必须同各种敌对力量的世 界进行搏斗。我们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话所表现的那类思想,虽曾令一整个民族为之喝采, 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则肯定会遭排斥,因为它会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是一种完全没 有自尊的心态。事实上,一切尚未卷入或尚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社会群体,今天 对这种思想仍抱排斥态度。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获利的本能在那些时代就不为人所知或尚 不发达(人们常常这么说);也并不是象耽于幻想的现代浪漫主义作家所常常以为的那 样,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势力圈以外,不象在其圈内那么强烈。在这一点上是找不到资 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什么区别的。中国的清朝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 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不管谁都会发现,一个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 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对黄金的贪 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 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一直是落后的,但在 靠赚钱以谋取私利方面使绝对不讲道德的作法普遍盛行,却恰恰是那些国家一直具有的 一个突出的典型特征。正如所有的雇主都知道的那样,这些国家(可用意大利与德国作 比较)的劳动者缺乏自觉性(coscienziosita ),这一点以前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 仍然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 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正如它不能利用那些在与他人往来中给人以完全不讲道德的 印象的人一样,后一点我们看了富兰克林的作品就会明白。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 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 贪欲,有一些人让黄金欲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地顺从它。其中的一个例子就 是那位荷兰船长,他“要穿过地狱去寻宝,哪怕地狱之火烤焦了船帆也在所不惜”,但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并不是产生出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 大众心态的代表,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 就必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在对外国人和非同伙人打交道时,贸 易也象战争及海上掠夺一样,常常是无法无天的。在这里双重伦理允许人们做出在与同 胞同事的往来中禁止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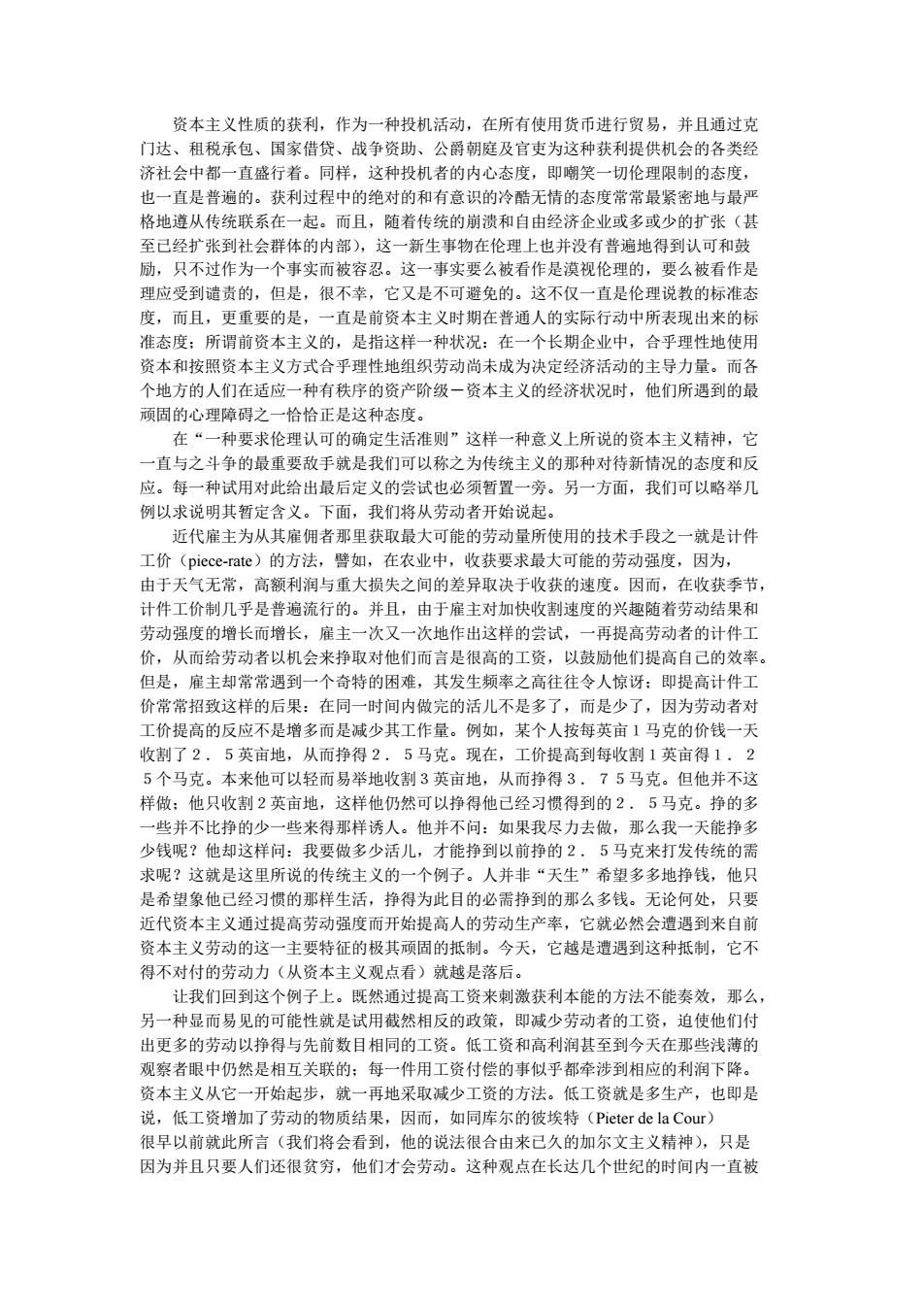
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作为一种投机活动,在所有使用货币进行贸易,并且通过克 门达、租税承包、国家借贷、战争资助、公爵朝庭及官吏为这种获利提供机会的各类经 济社会中都一直盛行着。同样,这种投机者的内心态度,即嘲笑一切伦理限制的态度, 也一直是普遍的。获利过程中的绝对的和有意识的冷酷无情的态度常常最紧密地与最严 格地遵从传统联系在一起。而且,随着传统的崩溃和自由经济企业或多或少的扩张(甚 至已经扩张到社会群体的内部),这一新生事物在伦理上也并没有普遍地得到认可和鼓 励,只不过作为一个事实而被容忍。这一事实要么被看作是漠视伦理的,要么被看作是 理应受到谴责的,但是,很不幸,它又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一直是伦理说教的标准态 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直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在普通人的实际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标 准态度:所谓前资本主义的,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 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而各 个地方的人们在适应一种有秩序的资产阶级一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时,他们所遇到的最 顾固的心理障碍之一恰恰正是这种态度。 在“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这样一种意义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 一直与之斗争的最重要敌手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对待新情况的态度和反 应。每一种试用对此给出最后定义的尝试也必须暂置一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略举几 例以求说明其暂定含义。下面,我们将从劳动者开始说起。 近代雇主为从其雇佣者那里获取最大可能的劳动量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之一就是计件 工价(piece-rate)的方法,譬如,在农业中,收获要求最大可能的劳动强度,因为, 由于天气无常,高额利润与重大损失之间的差异取决于收获的速度。因而,在收获季节, 计件工价制几乎是普遍流行的。并且,由于雇主对加快收割速度的兴趣随着劳动结果和 劳动强度的增长而增长,雇主一次又一次地作出这样的尝试,一再提高劳动者的计件工 价,从而给劳动者以机会来挣取对他们而言是很高的工资,以鼓励他们提高自己的效率。 但是,雇主却常常遇到一个奇特的困难,其发生频率之高往往令人惊讶:即提高计件工 价常常招致这样的后果:在同一时间内做完的活儿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劳动者对 工价提高的反应不是增多而是减少其工作量。例如,某个人按每英亩1马克的价钱一天 收割了2,5英亩地,从而挣得2,5马克。现在,工价提高到每收割1英亩得1,2 5个马克。本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割3英亩地,从而挣得3.75马克。但他并不这 样做:他只收割2英亩地,这样他仍然可以挣得他己经习惯得到的2.5马克。挣的多 一些并不比挣的少一些来得那样诱人。他并不问:如果我尽力去做,那么我一天能挣多 少钱呢?他却这样问:我要做多少活儿,才能挣到以前挣的2,5马克来打发传统的需 求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传统主义的一个例子。人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挣钱,他只 是希望象他己经习惯的那样生活,挣得为此目的必需挣到的那么多钱。无论何处,只要 近代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开始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它就必然会遭遇到来自前 资本主义劳动的这一主要特征的极其顽固的抵制。今天,它越是遭遇到这种抵制,它不 得不对付的劳动力(从资本主义观点看)就越是落后。 让我们回到这个例子上。既然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获利本能的方法不能奏效,那么, 另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就是试用截然相反的政策,即减少劳动者的工资,迫使他们付 出更多的劳动以挣得与先前数目相同的工资。低工资和高利润甚至到今天在那些浅薄的 观察者眼中仍然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件用工资付偿的事似乎都牵涉到相应的利润下降。 资本主义从它一开始起步,就一再地采取减少工资的方法。低工资就是多生产,也即是 说,低工资增加了劳动的物质结果,因而,如同库尔的彼埃特(Pieter de la Cour) 很早以前就此所言(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说法很合由来已久的加尔文主义精神),只是 因为并且只要人们还很贫穷,他们才会劳动。这种观点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被
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作为一种投机活动,在所有使用货币进行贸易,并且通过克 门达、租税承包、国家借贷、战争资助、公爵朝庭及官吏为这种获利提供机会的各类经 济社会中都一直盛行着。同样,这种投机者的内心态度,即嘲笑一切伦理限制的态度, 也一直是普遍的。获利过程中的绝对的和有意识的冷酷无情的态度常常最紧密地与最严 格地遵从传统联系在一起。而且,随着传统的崩溃和自由经济企业或多或少的扩张(甚 至已经扩张到社会群体的内部),这一新生事物在伦理上也并没有普遍地得到认可和鼓 励,只不过作为一个事实而被容忍。这一事实要么被看作是漠视伦理的,要么被看作是 理应受到谴责的,但是,很不幸,它又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一直是伦理说教的标准态 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直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在普通人的实际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标 准态度;所谓前资本主义的,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 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而各 个地方的人们在适应一种有秩序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时,他们所遇到的最 顽固的心理障碍之一恰恰正是这种态度。 在“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这样一种意义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 一直与之斗争的最重要敌手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对待新情况的态度和反 应。每一种试用对此给出最后定义的尝试也必须暂置一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略举几 例以求说明其暂定含义。下面,我们将从劳动者开始说起。 近代雇主为从其雇佣者那里获取最大可能的劳动量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之一就是计件 工价(piece-rate)的方法,譬如,在农业中,收获要求最大可能的劳动强度,因为, 由于天气无常,高额利润与重大损失之间的差异取决于收获的速度。因而,在收获季节, 计件工价制几乎是普遍流行的。并且,由于雇主对加快收割速度的兴趣随着劳动结果和 劳动强度的增长而增长,雇主一次又一次地作出这样的尝试,一再提高劳动者的计件工 价,从而给劳动者以机会来挣取对他们而言是很高的工资,以鼓励他们提高自己的效率。 但是,雇主却常常遇到一个奇特的困难,其发生频率之高往往令人惊讶;即提高计件工 价常常招致这样的后果:在同一时间内做完的活儿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劳动者对 工价提高的反应不是增多而是减少其工作量。例如,某个人按每英亩1马克的价钱一天 收割了2.5英亩地,从而挣得2.5马克。现在,工价提高到每收割1英亩得1.2 5个马克。本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割3英亩地,从而挣得3.75马克。但他并不这 样做;他只收割2英亩地,这样他仍然可以挣得他已经习惯得到的2.5马克。挣的多 一些并不比挣的少一些来得那样诱人。他并不问:如果我尽力去做,那么我一天能挣多 少钱呢?他却这样问:我要做多少活儿,才能挣到以前挣的2.5马克来打发传统的需 求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传统主义的一个例子。人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挣钱,他只 是希望象他已经习惯的那样生活,挣得为此目的必需挣到的那么多钱。无论何处,只要 近代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开始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它就必然会遭遇到来自前 资本主义劳动的这一主要特征的极其顽固的抵制。今天,它越是遭遇到这种抵制,它不 得不对付的劳动力(从资本主义观点看)就越是落后。 让我们回到这个例子上。既然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获利本能的方法不能奏效,那么, 另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就是试用截然相反的政策,即减少劳动者的工资,迫使他们付 出更多的劳动以挣得与先前数目相同的工资。低工资和高利润甚至到今天在那些浅薄的 观察者眼中仍然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件用工资付偿的事似乎都牵涉到相应的利润下降。 资本主义从它一开始起步,就一再地采取减少工资的方法。低工资就是多生产,也即是 说,低工资增加了劳动的物质结果,因而,如同库尔的彼埃特(Pieter de la Cour) 很早以前就此所言(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说法很合由来已久的加尔文主义精神),只是 因为并且只要人们还很贫穷,他们才会劳动。这种观点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