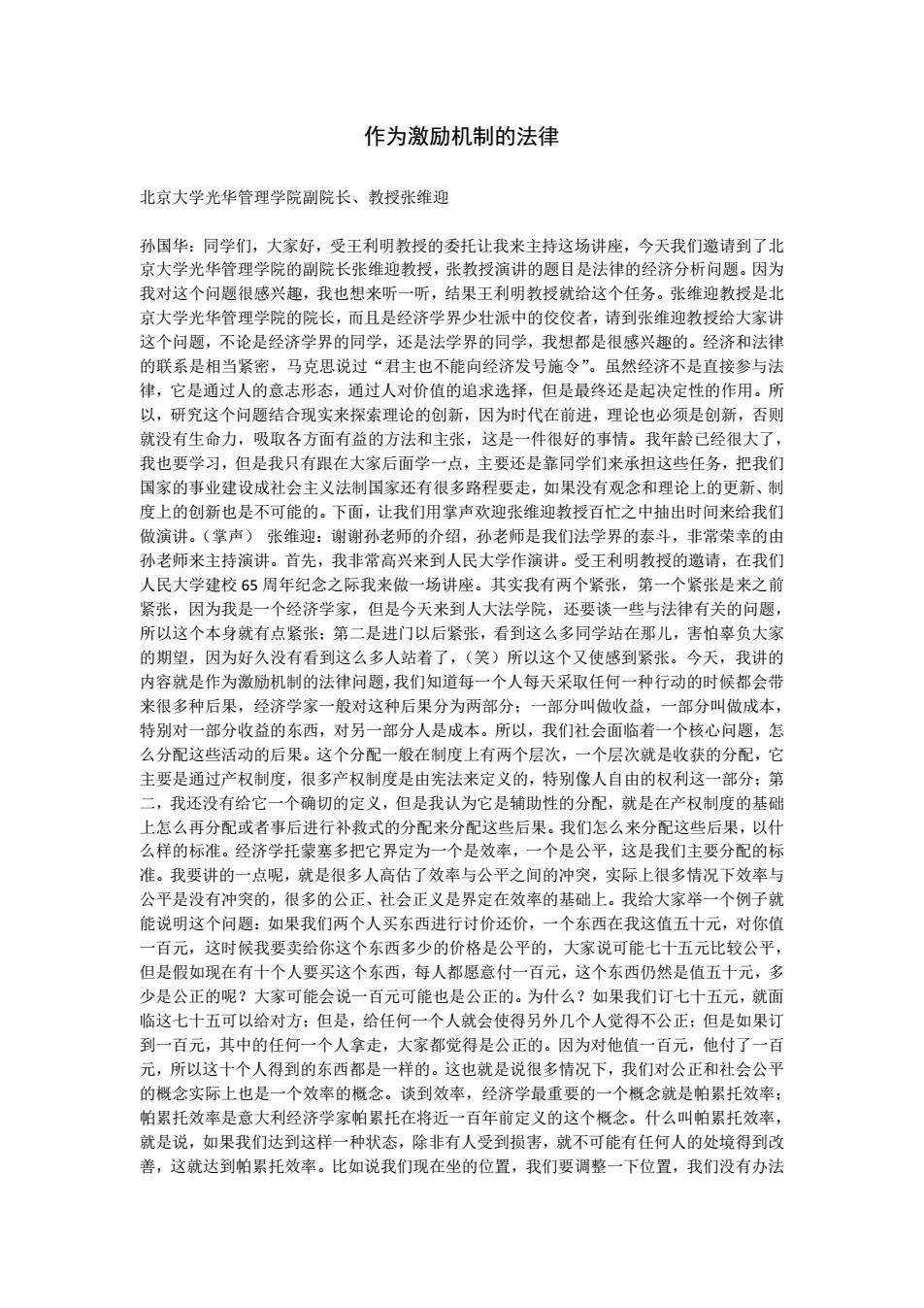
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张维迎 孙国华:同学们,大家好,受王利明教授的委托让我来主持这场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张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法律的经济分析问题。因为 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也想来听一听,结果王利明教授就给这个任务。张维迎教授是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而且是经济学界少壮派中的佼佼者,请到张维迎教授给大家讲 这个问题,不论是经济学界的同学,还是法学界的同学,我想都是很感兴趣的。经济和法律 的联系是相当紧密,马克思说过“君主也不能向经济发号施令”。虽然经济不是直接参与法 律,它是通过人的意志形态,通过人对价值的追求选择,但是最终还是起决定性的作用。所 以,研究这个问题结合现实来探索理论的创新,因为时代在前进,理论也必须是创新,否则 就没有生命力,吸取各方面有益的方法和主张,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年龄己经很大了, 我也要学习,但是我只有跟在大家后面学一点,主要还是靠同学们来承担这些任务,把我们 国家的事业建设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还有很多路程要走,如果没有观念和理论上的更新、制 度上的创新也是不可能的。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张维迎教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给我们 做演讲。(掌声)张维迎:谢谢孙老师的介绍,孙老师是我们法学界的泰斗,非常荣幸的由 孙老师来主持演讲。首先,我非常高兴来到人民大学作演讲。受王利明教授的邀请,在我们 人民大学建校65周年纪念之际我来做一场讲座。其实我有两个紧张,第一个紧张是来之前 紧张,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今天来到人大法学院,还要谈一些与法律有关的问题, 所以这个本身就有点紧张:第二是进门以后紧张,看到这么多同学站在那儿,害怕辜负大家 的期望,因为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站着了,(笑)所以这个又使感到紧张。今天,我讲的 内容就是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问题,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天采取任何一种行动的时候都会带 来很多种后果,经济学家一般对这种后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做收益,一部分叫做成本, 特别对一部分收益的东西,对另一部分人是成本。所以,我们社会面临着一个核心问题,怎 么分配这些活动的后果。这个分配一般在制度上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收获的分配,它 主要是通过产权制度,很多产权制度是由宪法来定义的,特别像人自由的权利这一部分:第 二,我还没有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我认为它是辅助性的分配,就是在产权制度的基础 上怎么再分配或者事后进行补救式的分配来分配这些后果。我们怎么来分配这些后果,以什 么样的标准。经济学托蒙塞多把它界定为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公平,这是我们主要分配的标 准。我要讲的一点呢,就是很多人高估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效率与 公平是没有冲突的,很多的公正、社会正义是界定在效率的基础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 能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两个人买东西进行讨价还价,一个东西在我这值五十元,对你值 一百元,这时候我要卖给你这个东西多少的价格是公平的,大家说可能七十五元比较公平, 但是假如现在有十个人要买这个东西,每人都愿意付一百元,这个东西仍然是值五十元,多 少是公正的呢?大家可能会说一百元可能也是公正的。为什么?如果我们订七十五元,就面 临这七十五可以给对方:但是,给任何一个人就会使得另外几个人觉得不公正:但是如果订 到一百元,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拿走,大家都觉得是公正的。因为对他值一百元,他付了一百 元,所以这十个人得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我们对公正和社会公平 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个效率的概念。谈到效率,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帕累托效率: 帕累托效率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将近一百年前定义的这个概念。什么叫帕累托效率, 就是说,如果我们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除非有人受到损害,就不可能有任何人的处境得到改 善,这就达到帕累托效率。比如说我们现在坐的位置,我们要调整一下位置,我们没有办法
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张维迎 孙国华:同学们,大家好,受王利明教授的委托让我来主持这场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张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法律的经济分析问题。因为 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也想来听一听,结果王利明教授就给这个任务。张维迎教授是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而且是经济学界少壮派中的佼佼者,请到张维迎教授给大家讲 这个问题,不论是经济学界的同学,还是法学界的同学,我想都是很感兴趣的。经济和法律 的联系是相当紧密,马克思说过“君主也不能向经济发号施令”。虽然经济不是直接参与法 律,它是通过人的意志形态,通过人对价值的追求选择,但是最终还是起决定性的作用。所 以,研究这个问题结合现实来探索理论的创新,因为时代在前进,理论也必须是创新,否则 就没有生命力,吸取各方面有益的方法和主张,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年龄已经很大了, 我也要学习,但是我只有跟在大家后面学一点,主要还是靠同学们来承担这些任务,把我们 国家的事业建设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还有很多路程要走,如果没有观念和理论上的更新、制 度上的创新也是不可能的。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张维迎教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给我们 做演讲。(掌声) 张维迎:谢谢孙老师的介绍,孙老师是我们法学界的泰斗,非常荣幸的由 孙老师来主持演讲。首先,我非常高兴来到人民大学作演讲。受王利明教授的邀请,在我们 人民大学建校 65 周年纪念之际我来做一场讲座。其实我有两个紧张,第一个紧张是来之前 紧张,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今天来到人大法学院,还要谈一些与法律有关的问题, 所以这个本身就有点紧张;第二是进门以后紧张,看到这么多同学站在那儿,害怕辜负大家 的期望,因为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站着了,(笑)所以这个又使感到紧张。今天,我讲的 内容就是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问题,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天采取任何一种行动的时候都会带 来很多种后果,经济学家一般对这种后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做收益,一部分叫做成本, 特别对一部分收益的东西,对另一部分人是成本。所以,我们社会面临着一个核心问题,怎 么分配这些活动的后果。这个分配一般在制度上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收获的分配,它 主要是通过产权制度,很多产权制度是由宪法来定义的,特别像人自由的权利这一部分;第 二,我还没有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我认为它是辅助性的分配,就是在产权制度的基础 上怎么再分配或者事后进行补救式的分配来分配这些后果。我们怎么来分配这些后果,以什 么样的标准。经济学托蒙塞多把它界定为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公平,这是我们主要分配的标 准。我要讲的一点呢,就是很多人高估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效率与 公平是没有冲突的,很多的公正、社会正义是界定在效率的基础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 能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两个人买东西进行讨价还价,一个东西在我这值五十元,对你值 一百元,这时候我要卖给你这个东西多少的价格是公平的,大家说可能七十五元比较公平, 但是假如现在有十个人要买这个东西,每人都愿意付一百元,这个东西仍然是值五十元,多 少是公正的呢?大家可能会说一百元可能也是公正的。为什么?如果我们订七十五元,就面 临这七十五可以给对方;但是,给任何一个人就会使得另外几个人觉得不公正;但是如果订 到一百元,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拿走,大家都觉得是公正的。因为对他值一百元,他付了一百 元,所以这十个人得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我们对公正和社会公平 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个效率的概念。谈到效率,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帕累托效率; 帕累托效率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将近一百年前定义的这个概念。什么叫帕累托效率, 就是说,如果我们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除非有人受到损害,就不可能有任何人的处境得到改 善,这就达到帕累托效率。比如说我们现在坐的位置,我们要调整一下位置,我们没有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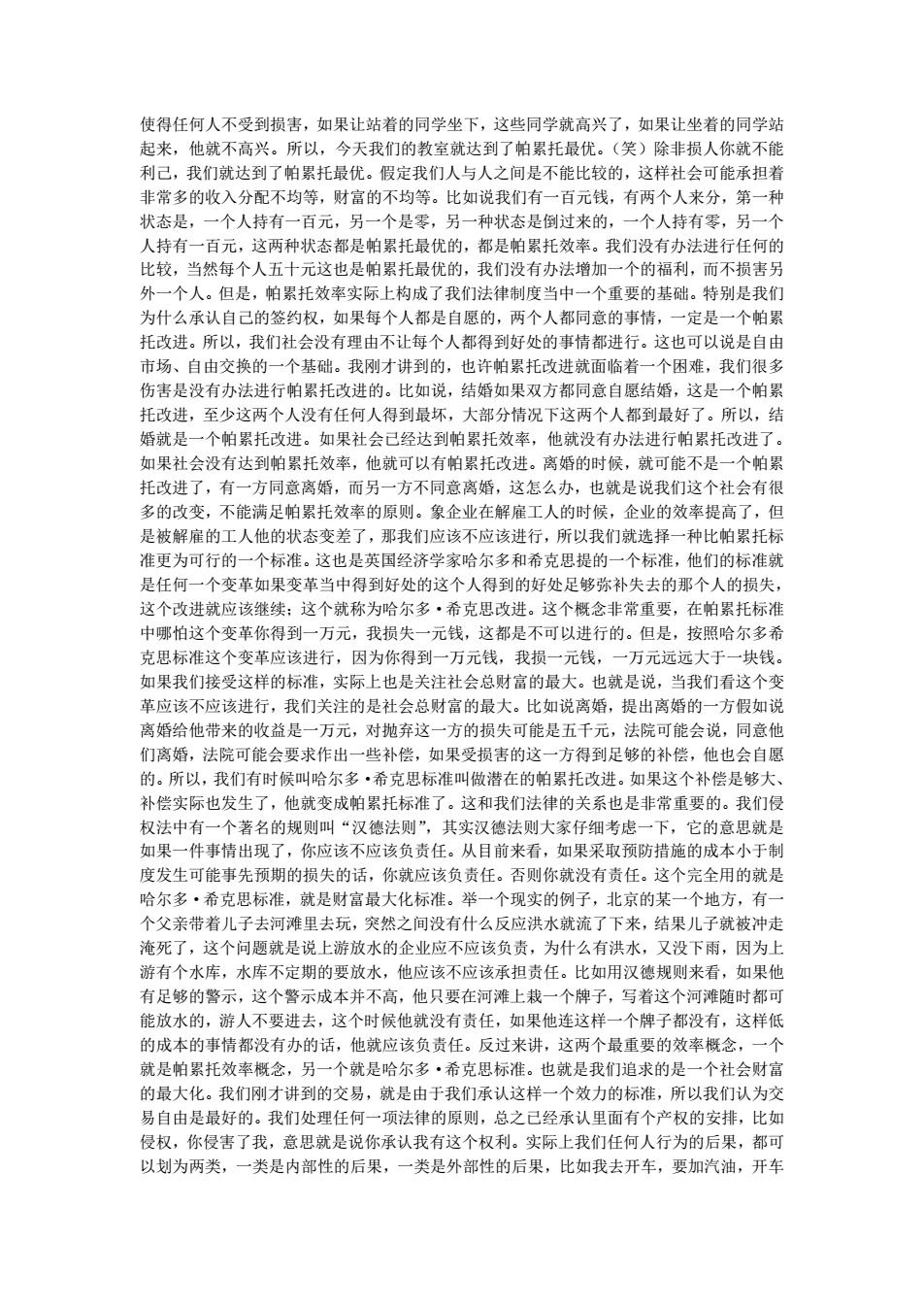
使得任何人不受到损害,如果让站着的同学坐下,这些同学就高兴了,如果让坐着的同学站 起来,他就不高兴。所以,今天我们的教室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笑)除非损人你就不能 利己,我们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假定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能比较的,这样社会可能承担着 非常多的收入分配不均等,财富的不均等。比如说我们有一百元钱,有两个人来分,第一种 状态是,一个人持有一百元,另一个是零,另一种状态是倒过来的,一个人持有零,另一个 人持有一百元,这两种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的,都是帕累托效率。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 比较,当然每个人五十元这也是帕累托最优的,我们没有办法增加一个的福利,而不损害另 外一个人。但是,帕累托效率实际上构成了我们法律制度当中一个重要的基础。特别是我们 为什么承认自己的签约权,如果每个人都是自愿的,两个人都同意的事情,一定是一个帕累 托改进。所以,我们社会没有理由不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的事情都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自由 市场、自由交换的一个基础。我刚才讲到的,也许帕累托改进就面临着一个困难,我们很多 伤害是没有办法进行帕累托改进的。比如说,结婚如果双方都同意自愿结婚,这是一个帕累 托改进,至少这两个人没有任何人得到最坏,大部分情况下这两个人都到最好了。所以,结 婚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如果社会已经达到帕累托效率,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帕累托改进了。 如果社会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他就可以有帕累托改进。离婚的时候,就可能不是一个帕累 托改进了,有一方同意离婚,而另一方不同意离婚,这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有很 多的改变,不能满足帕累托效率的原则。象企业在解雇工人的时候,企业的效率提高了,但 是被解雇的工人他的状态变差了,那我们应该不应该进行,所以我们就选择一种比帕累托标 准更为可行的一个标准。这也是英国经济学家哈尔多和希克思提的一个标准,他们的标准就 是任何一个变革如果变革当中得到好处的这个人得到的好处足够弥补失去的那个人的损失, 这个改进就应该继续:这个就称为哈尔多·希克思改进。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在帕累托标准 中哪怕这个变革你得到一万元,我损失一元钱,这都是不可以进行的。但是,按照哈尔多希 克思标准这个变革应该进行,因为你得到一万元钱,我损一元钱,一万元远远大于一块钱。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标准,实际上也是关注社会总财富的最大。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这个变 革应该不应该进行,我们关注的是社会总财富的最大。比如说离婚,提出离婚的一方假如说 离婚给他带来的收益是一万元,对抛弃这一方的损失可能是五千元,法院可能会说,同意他 们离婚,法院可能会要求作出一些补偿,如果受损害的这一方得到足够的补偿,他也会自愿 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哈尔多·希克思标准叫做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如果这个补偿是够大、 补偿实际也发生了,他就变成帕累托标准了。这和我们法律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侵 权法中有一个著名的规则叫“汉德法则”,其实汉德法则大家仔细考虑一下,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一件事情出现了,你应该不应该负责任。从目前来看,如果采取预防措施的成本小于制 度发生可能事先预期的损失的话,你就应该负贵任。否则你就没有责任。这个完全用的就是 哈尔多·希克思标准,就是财富最大化标准。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北京的某一个地方,有一 个父亲带着儿子去河滩里去玩,突然之间没有什么反应洪水就流了下来,结果儿子就被冲走 淹死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上游放水的企业应不应该负责,为什么有洪水,又没下雨,因为上 游有个水库,水库不定期的要放水,他应该不应该承担责任。比如用汉德规则来看,如果他 有足够的警示,这个警示成本并不高,他只要在河滩上栽一个牌子,写着这个河滩随时都可 能放水的,游人不要进去,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责任,如果他连这样一个牌子都没有,这样低 的成本的事情都没有办的话,他就应该负责任。反过来讲,这两个最重要的效率概念,一个 就是帕累托效率概念,另一个就是哈尔多·希克思标准。也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社会财富 的最大化。我们刚才讲到的交易,就是由于我们承认这样一个效力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交 易自由是最好的。我们处理任何一项法律的原则,总之已经承认里面有个产权的安排,比如 侵权,你侵害了我,意思就是说你承认我有这个权利。实际上我们任何人行为的后果,都可 以划为两类,一类是内部性的后果,一类是外部性的后果,比如我去开车,要加汽油,开车
使得任何人不受到损害,如果让站着的同学坐下,这些同学就高兴了,如果让坐着的同学站 起来,他就不高兴。所以,今天我们的教室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笑)除非损人你就不能 利己,我们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假定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能比较的,这样社会可能承担着 非常多的收入分配不均等,财富的不均等。比如说我们有一百元钱,有两个人来分,第一种 状态是,一个人持有一百元,另一个是零,另一种状态是倒过来的,一个人持有零,另一个 人持有一百元,这两种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的,都是帕累托效率。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 比较,当然每个人五十元这也是帕累托最优的,我们没有办法增加一个的福利,而不损害另 外一个人。但是,帕累托效率实际上构成了我们法律制度当中一个重要的基础。特别是我们 为什么承认自己的签约权,如果每个人都是自愿的,两个人都同意的事情,一定是一个帕累 托改进。所以,我们社会没有理由不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的事情都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自由 市场、自由交换的一个基础。我刚才讲到的,也许帕累托改进就面临着一个困难,我们很多 伤害是没有办法进行帕累托改进的。比如说,结婚如果双方都同意自愿结婚,这是一个帕累 托改进,至少这两个人没有任何人得到最坏,大部分情况下这两个人都到最好了。所以,结 婚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如果社会已经达到帕累托效率,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帕累托改进了。 如果社会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他就可以有帕累托改进。离婚的时候,就可能不是一个帕累 托改进了,有一方同意离婚,而另一方不同意离婚,这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有很 多的改变,不能满足帕累托效率的原则。象企业在解雇工人的时候,企业的效率提高了,但 是被解雇的工人他的状态变差了,那我们应该不应该进行,所以我们就选择一种比帕累托标 准更为可行的一个标准。这也是英国经济学家哈尔多和希克思提的一个标准,他们的标准就 是任何一个变革如果变革当中得到好处的这个人得到的好处足够弥补失去的那个人的损失, 这个改进就应该继续;这个就称为哈尔多·希克思改进。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在帕累托标准 中哪怕这个变革你得到一万元,我损失一元钱,这都是不可以进行的。但是,按照哈尔多希 克思标准这个变革应该进行,因为你得到一万元钱,我损一元钱,一万元远远大于一块钱。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标准,实际上也是关注社会总财富的最大。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这个变 革应该不应该进行,我们关注的是社会总财富的最大。比如说离婚,提出离婚的一方假如说 离婚给他带来的收益是一万元,对抛弃这一方的损失可能是五千元,法院可能会说,同意他 们离婚,法院可能会要求作出一些补偿,如果受损害的这一方得到足够的补偿,他也会自愿 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哈尔多·希克思标准叫做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如果这个补偿是够大、 补偿实际也发生了,他就变成帕累托标准了。这和我们法律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侵 权法中有一个著名的规则叫“汉德法则”,其实汉德法则大家仔细考虑一下,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一件事情出现了,你应该不应该负责任。从目前来看,如果采取预防措施的成本小于制 度发生可能事先预期的损失的话,你就应该负责任。否则你就没有责任。这个完全用的就是 哈尔多·希克思标准,就是财富最大化标准。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北京的某一个地方,有一 个父亲带着儿子去河滩里去玩,突然之间没有什么反应洪水就流了下来,结果儿子就被冲走 淹死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上游放水的企业应不应该负责,为什么有洪水,又没下雨,因为上 游有个水库,水库不定期的要放水,他应该不应该承担责任。比如用汉德规则来看,如果他 有足够的警示,这个警示成本并不高,他只要在河滩上栽一个牌子,写着这个河滩随时都可 能放水的,游人不要进去,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责任,如果他连这样一个牌子都没有,这样低 的成本的事情都没有办的话,他就应该负责任。反过来讲,这两个最重要的效率概念,一个 就是帕累托效率概念,另一个就是哈尔多·希克思标准。也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社会财富 的最大化。我们刚才讲到的交易,就是由于我们承认这样一个效力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交 易自由是最好的。我们处理任何一项法律的原则,总之已经承认里面有个产权的安排,比如 侵权,你侵害了我,意思就是说你承认我有这个权利。实际上我们任何人行为的后果,都可 以划为两类,一类是内部性的后果,一类是外部性的后果,比如我去开车,要加汽油,开车

的时候还不能看书,这也是一定的成本:好处是开车以后我可以享受,可以达到我的目的地, 但是外部性的后果是你开车不能撞人或者交通堵塞,你自己只承担一部分成本,其他成本有 别人承担,你要排放污染或下雨的时候车从水中穿去,给行人身上溅了好多水。这就是说我 们任何一种行为带来的后果分成两部分,内部性的和外部性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决策只考虑 对自己的、给自己带有什么:这就是说个人的最优行为和社会最优的行为是不一样的。社会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个人能够对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任。如果他对所有的行为负责任, 个人最好的东西也是对社会最好的东西,我们怎么样让他外部性的东西都内部化,这就是激 励机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对一个行为的外部后果内部化,这就是我理解的法律作为激励 机制的核心观点。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科思定理,科思定理讲的意思就是如 果产权权利分配是清楚的,没有交易成本,所有的外部性都可以通过当事人自由的谈判可以 解决问题。如果科思定理的条件满足,比如说没有交易成本,我们只需要一个法律,那就是 合同法,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夜晚喜欢唱歌,特别喜欢 三点钟唱歌,这时候我的邻居就会不高兴,给他带来了影响,我们两个人可以谈判,比如唱 歌对我来讲值一百元,给他带来的噪音成本可能是五十元钱,我们两个就可以谈判,而且谈 判结果与谁有产权没有关系,假定他有产权他可以阻止我唱歌,享受安静的权利是宪法赋予 他的,那也没关系,我现在唱歌得到一百元的好处,他得到五十元,我会敲他的门,说我给 你七十五块钱,你让我唱一首歌吧?他肯定会同意,因为对他的成本是五十元,拿到七十五 元,还多了二十五元,我也同意因为我享受一百元,但是我才付出七十五元。第二,如果权 利是我的,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我爱唱歌,他没有权利阻止我,不论这个产权是谁的,只要 唱歌带来的价值大于他带来的成本,这个歌就一定会唱。这就是哈尔多·希克思标准。反过 来说,唱歌给我带来五十元的享受,他也带来是一百元的成本,那也没有关系,这歌肯定不 会唱,为什么呢?如果说产权他的,但是他就不会让唱了,我就没法唱,如果产权是我的, 我就有权利唱歌,但是对他遭受痛苦是一百元,他就会敲我的门说,我给你七十五元钱你别 唱了。那我呢,也就同意了,因为我拿到了七十五元,唱歌对我的享受是五十元,我还赚了 二十五元钱。当然这个中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配,权利界定给谁,谁就可以得到好处。这个 时候就会引起分配问题,但是与效率没有关系,无论哪一种情况下,效率都是一样的。如果 这个交易成本为“零”,我们只需要一个法律,就是合同法,而且我们也不需要侵权法,因 为我知道开车可能撞人,所以我给每一个可能被我撞的人可以签订一个合同,撞了你,我付 多少钱就可以了。我们甚至不需要刑法,我要去杀谁,我自己跟他去商量,杀你给你多少钱。 (大笑)但是,由于交易成本不是为“零”,很多情况下他非常高。这个时候谈判就没法解 决问题,我们就要创造出合同法之外的其它的法律。比如说,一种可能为什么我们谈判达不 成协议,由于信息不对称,好比唱歌对我值一百元,对他值五十元,我送给他七十五元,但 是问题呢?他会假装成本不是五十元,可能是一百元,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愿意付多少钱。所 以我们俩可能就达不成这个协议。这个时候交易成本会很高,本来我可以唱的歌,由于他不 让我唱,要唱的就得给我二百元钱,实际上给他五十元钱他就满足了。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很 多的讨价还价,比如说你要买一件衣服,上面标明的价格是五百元,你就会说太贵了吧,对 方就会说,你给多少钱吧,你就会说二百怎么样,他说行拿走,但是你心里仍然觉得难受, 肯定吃亏了,也许一百元就可以买到,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可以带来很多的成本。另外,谈判 的成本也与人的多少有关系,假如说我给每一个都可能被我开车撞的人去谈判,成本会非常 的高:如果我要办一个企业,施放出一些污染来,这是受损失的外部成本,我要和所有的居 民每一个都谈判,这个成本就会非常高,每一个居民都可能要的钱很多,最后这个企业本来 应该办,但是到了最后也没法办了。这就是交易成本和谈判的人数以及信息的不对称,谈判 成本就会非常高。所以我们不能只依靠合同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了交易成本,只靠自 由市场的谈判不能解决,这样我们需要更多的法律的规则。关于激励机制,经济学家在过去
的时候还不能看书,这也是一定的成本;好处是开车以后我可以享受,可以达到我的目的地, 但是外部性的后果是你开车不能撞人或者交通堵塞,你自己只承担一部分成本,其他成本有 别人承担,你要排放污染或下雨的时候车从水中穿去,给行人身上溅了好多水。这就是说我 们任何一种行为带来的后果分成两部分,内部性的和外部性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决策只考虑 对自己的、给自己带有什么;这就是说个人的最优行为和社会最优的行为是不一样的。社会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个人能够对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任。如果他对所有的行为负责任, 个人最好的东西也是对社会最好的东西,我们怎么样让他外部性的东西都内部化,这就是激 励机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对一个行为的外部后果内部化,这就是我理解的法律作为激励 机制的核心观点。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科思定理,科思定理讲的意思就是如 果产权权利分配是清楚的,没有交易成本,所有的外部性都可以通过当事人自由的谈判可以 解决问题。如果科思定理的条件满足,比如说没有交易成本,我们只需要一个法律,那就是 合同法,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夜晚喜欢唱歌,特别喜欢 三点钟唱歌,这时候我的邻居就会不高兴,给他带来了影响,我们两个人可以谈判,比如唱 歌对我来讲值一百元,给他带来的噪音成本可能是五十元钱,我们两个就可以谈判,而且谈 判结果与谁有产权没有关系,假定他有产权他可以阻止我唱歌,享受安静的权利是宪法赋予 他的,那也没关系,我现在唱歌得到一百元的好处,他得到五十元,我会敲他的门,说我给 你七十五块钱,你让我唱一首歌吧?他肯定会同意,因为对他的成本是五十元,拿到七十五 元,还多了二十五元,我也同意因为我享受一百元,但是我才付出七十五元。第二,如果权 利是我的,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我爱唱歌,他没有权利阻止我,不论这个产权是谁的,只要 唱歌带来的价值大于他带来的成本,这个歌就一定会唱。这就是哈尔多·希克思标准。反过 来说,唱歌给我带来五十元的享受,他也带来是一百元的成本,那也没有关系,这歌肯定不 会唱,为什么呢?如果说产权他的,但是他就不会让唱了,我就没法唱,如果产权是我的, 我就有权利唱歌,但是对他遭受痛苦是一百元,他就会敲我的门说,我给你七十五元钱你别 唱了。那我呢,也就同意了,因为我拿到了七十五元,唱歌对我的享受是五十元,我还赚了 二十五元钱。当然这个中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配,权利界定给谁,谁就可以得到好处。这个 时候就会引起分配问题,但是与效率没有关系,无论哪一种情况下,效率都是一样的。如果 这个交易成本为“零”,我们只需要一个法律,就是合同法,而且我们也不需要侵权法,因 为我知道开车可能撞人,所以我给每一个可能被我撞的人可以签订一个合同,撞了你,我付 多少钱就可以了。我们甚至不需要刑法,我要去杀谁,我自己跟他去商量,杀你给你多少钱。 (大笑)但是,由于交易成本不是为“零”,很多情况下他非常高。这个时候谈判就没法解 决问题,我们就要创造出合同法之外的其它的法律。比如说,一种可能为什么我们谈判达不 成协议,由于信息不对称,好比唱歌对我值一百元,对他值五十元,我送给他七十五元,但 是问题呢?他会假装成本不是五十元,可能是一百元,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愿意付多少钱。所 以我们俩可能就达不成这个协议。这个时候交易成本会很高,本来我可以唱的歌,由于他不 让我唱,要唱的就得给我二百元钱,实际上给他五十元钱他就满足了。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很 多的讨价还价,比如说你要买一件衣服,上面标明的价格是五百元,你就会说太贵了吧,对 方就会说,你给多少钱吧,你就会说二百怎么样,他说行拿走,但是你心里仍然觉得难受, 肯定吃亏了,也许一百元就可以买到,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可以带来很多的成本。另外,谈判 的成本也与人的多少有关系,假如说我给每一个都可能被我开车撞的人去谈判,成本会非常 的高;如果我要办一个企业,施放出一些污染来,这是受损失的外部成本,我要和所有的居 民每一个都谈判,这个成本就会非常高,每一个居民都可能要的钱很多,最后这个企业本来 应该办,但是到了最后也没法办了。这就是交易成本和谈判的人数以及信息的不对称,谈判 成本就会非常高。所以我们不能只依靠合同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了交易成本,只靠自 由市场的谈判不能解决,这样我们需要更多的法律的规则。关于激励机制,经济学家在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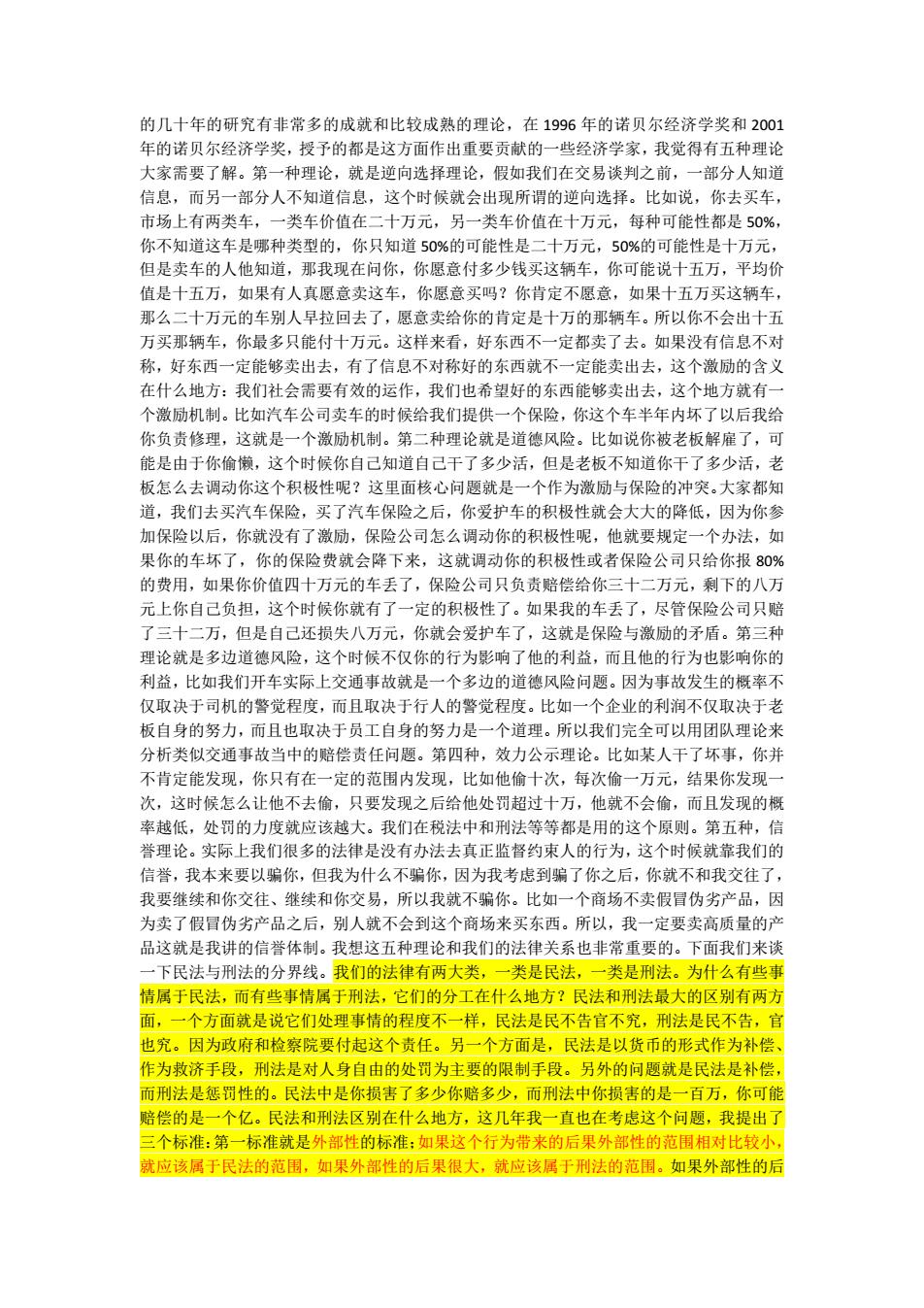
的几十年的研究有非常多的成就和比较成熟的理论,在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2001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的都是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些经济学家,我觉得有五种理论 大家需要了解。第一种理论,就是逆向选择理论,假如我们在交易谈判之前,一部分人知道 信息,而另一部分人不知道信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逆向选择。比如说,你去买车, 市场上有两类车,一类车价值在二十万元,另一类车价值在十万元,每种可能性都是50%, 你不知道这车是哪种类型的,你只知道50%的可能性是二十万元,50%的可能性是十万元, 但是卖车的人他知道,那我现在问你,你愿意付多少钱买这辆车,你可能说十五万,平均价 值是十五万,如果有人真愿意卖这车,你愿意买吗?你肯定不愿意,如果十五万买这辆车, 那么二十万元的车别人早拉回去了,愿意卖给你的肯定是十万的那辆车。所以你不会出十五 万买那辆车,你最多只能付十万元。这样来看,好东西不一定都卖了去。如果没有信息不对 称,好东西一定能够卖出去,有了信息不对称好的东西就不一定能卖出去,这个激励的含义 在什么地方:我们社会需要有效的运作,我们也希望好的东西能够卖出去,这个地方就有一 个激励机制。比如汽车公司卖车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个保险,你这个车半年内坏了以后我给 你负责修理,这就是一个激励机制。第二种理论就是道德风险。比如说你被老板解雇了,可 能是由于你偷懒,这个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干了多少活,但是老板不知道你干了多少活,老 板怎么去调动你这个积极性呢?这里面核心问题就是一个作为激励与保险的冲突。大家都知 道,我们去买汽车保险,买了汽车保险之后,你爱护车的积极性就会大大的降低,因为你参 加保险以后,你就没有了激励,保险公司怎么调动你的积极性呢,他就要规定一个办法,如 果你的车坏了,你的保险费就会降下来,这就调动你的积极性或者保险公司只给你报80% 的费用,如果你价值四十万元的车丢了,保险公司只负责赔偿给你三十二万元,剩下的八万 元上你自己负担,这个时候你就有了一定的积极性了。如果我的车丢了,尽管保险公司只赔 了三十二万,但是自己还损失八万元,你就会爱护车了,这就是保险与激励的矛盾。第三种 理论就是多边道德风险,这个时候不仅你的行为影响了他的利益,而且他的行为也影响你的 利益,比如我们开车实际上交通事故就是一个多边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事故发生的概率不 仅取决于司机的警觉程度,而且取决于行人的警觉程度。比如一个企业的利润不仅取决于老 板自身的努力,而且也取决于员工自身的努力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团队理论来 分析类似交通事故当中的赔偿责任问题。第四种,效力公示理论。比如某人干了坏事,你并 不肯定能发现,你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现,比如他偷十次,每次偷一万元,结果你发现一 次,这时候怎么让他不去偷,只要发现之后给他处罚超过十万,他就不会偷,而且发现的概 率越低,处罚的力度就应该越大。我们在税法中和刑法等等都是用的这个原则。第五种,信 誉理论。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法律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监督约束人的行为,这个时候就靠我们的 信誉,我本来要以骗你,但我为什么不骗你,因为我考虑到骗了你之后,你就不和我交往了, 我要继续和你交往、继续和你交易,所以我就不骗你。比如一个商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因 为卖了假冒伪劣产品之后,别人就不会到这个商场来买东西。所以,我一定要卖高质量的产 品这就是我讲的信誉体制。我想这五种理论和我们的法律关系也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来谈 一下民法与刑法的分界线。我们的法律有两大类,一类是民法,一类是刑法。为什么有些事 情属于民法,而有些事情属于刑法,它们的分工在什么地方?民法和刑法最大的区别有两方 面,一个方面就是说它们处理事情的程度不一样,民法是民不告官不究,刑法是民不告,官 也究。因为政府和检察院要付起这个责任。另一个方面是,民法是以货币的形式作为补偿、 作为救济手段,刑法是对人身自由的处罚为主要的限制手段。另外的问题就是民法是补偿, 而刑法是惩罚性的。民法中是你损害了多少你赔多少,而刑法中你损害的是一百万,你可能 赔偿的是一个亿。民法和刑法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几年我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提出了 三个标准:第一标准就是外部性的标准:如果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外部性的范围相对比较小, 就应该属于民法的范围,如果外部性的后果很大,就应该属于刑法的范围。如果外部性的后
的几十年的研究有非常多的成就和比较成熟的理论,在 1996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 2001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的都是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些经济学家,我觉得有五种理论 大家需要了解。第一种理论,就是逆向选择理论,假如我们在交易谈判之前,一部分人知道 信息,而另一部分人不知道信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逆向选择。比如说,你去买车, 市场上有两类车,一类车价值在二十万元,另一类车价值在十万元,每种可能性都是 50%, 你不知道这车是哪种类型的,你只知道 50%的可能性是二十万元,50%的可能性是十万元, 但是卖车的人他知道,那我现在问你,你愿意付多少钱买这辆车,你可能说十五万,平均价 值是十五万,如果有人真愿意卖这车,你愿意买吗?你肯定不愿意,如果十五万买这辆车, 那么二十万元的车别人早拉回去了,愿意卖给你的肯定是十万的那辆车。所以你不会出十五 万买那辆车,你最多只能付十万元。这样来看,好东西不一定都卖了去。如果没有信息不对 称,好东西一定能够卖出去,有了信息不对称好的东西就不一定能卖出去,这个激励的含义 在什么地方:我们社会需要有效的运作,我们也希望好的东西能够卖出去,这个地方就有一 个激励机制。比如汽车公司卖车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个保险,你这个车半年内坏了以后我给 你负责修理,这就是一个激励机制。第二种理论就是道德风险。比如说你被老板解雇了,可 能是由于你偷懒,这个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干了多少活,但是老板不知道你干了多少活,老 板怎么去调动你这个积极性呢?这里面核心问题就是一个作为激励与保险的冲突。大家都知 道,我们去买汽车保险,买了汽车保险之后,你爱护车的积极性就会大大的降低,因为你参 加保险以后,你就没有了激励,保险公司怎么调动你的积极性呢,他就要规定一个办法,如 果你的车坏了,你的保险费就会降下来,这就调动你的积极性或者保险公司只给你报 80% 的费用,如果你价值四十万元的车丢了,保险公司只负责赔偿给你三十二万元,剩下的八万 元上你自己负担,这个时候你就有了一定的积极性了。如果我的车丢了,尽管保险公司只赔 了三十二万,但是自己还损失八万元,你就会爱护车了,这就是保险与激励的矛盾。第三种 理论就是多边道德风险,这个时候不仅你的行为影响了他的利益,而且他的行为也影响你的 利益,比如我们开车实际上交通事故就是一个多边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事故发生的概率不 仅取决于司机的警觉程度,而且取决于行人的警觉程度。比如一个企业的利润不仅取决于老 板自身的努力,而且也取决于员工自身的努力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团队理论来 分析类似交通事故当中的赔偿责任问题。第四种,效力公示理论。比如某人干了坏事,你并 不肯定能发现,你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现,比如他偷十次,每次偷一万元,结果你发现一 次,这时候怎么让他不去偷,只要发现之后给他处罚超过十万,他就不会偷,而且发现的概 率越低,处罚的力度就应该越大。我们在税法中和刑法等等都是用的这个原则。第五种,信 誉理论。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法律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监督约束人的行为,这个时候就靠我们的 信誉,我本来要以骗你,但我为什么不骗你,因为我考虑到骗了你之后,你就不和我交往了, 我要继续和你交往、继续和你交易,所以我就不骗你。比如一个商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因 为卖了假冒伪劣产品之后,别人就不会到这个商场来买东西。所以,我一定要卖高质量的产 品这就是我讲的信誉体制。我想这五种理论和我们的法律关系也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来谈 一下民法与刑法的分界线。我们的法律有两大类,一类是民法,一类是刑法。为什么有些事 情属于民法,而有些事情属于刑法,它们的分工在什么地方?民法和刑法最大的区别有两方 面,一个方面就是说它们处理事情的程度不一样,民法是民不告官不究,刑法是民不告,官 也究。因为政府和检察院要付起这个责任。另一个方面是,民法是以货币的形式作为补偿、 作为救济手段,刑法是对人身自由的处罚为主要的限制手段。另外的问题就是民法是补偿, 而刑法是惩罚性的。民法中是你损害了多少你赔多少,而刑法中你损害的是一百万,你可能 赔偿的是一个亿。民法和刑法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几年我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提出了 三个标准:第一标准就是外部性的标准;如果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外部性的范围相对比较小, 就应该属于民法的范围,如果外部性的后果很大,就应该属于刑法的范围。如果外部性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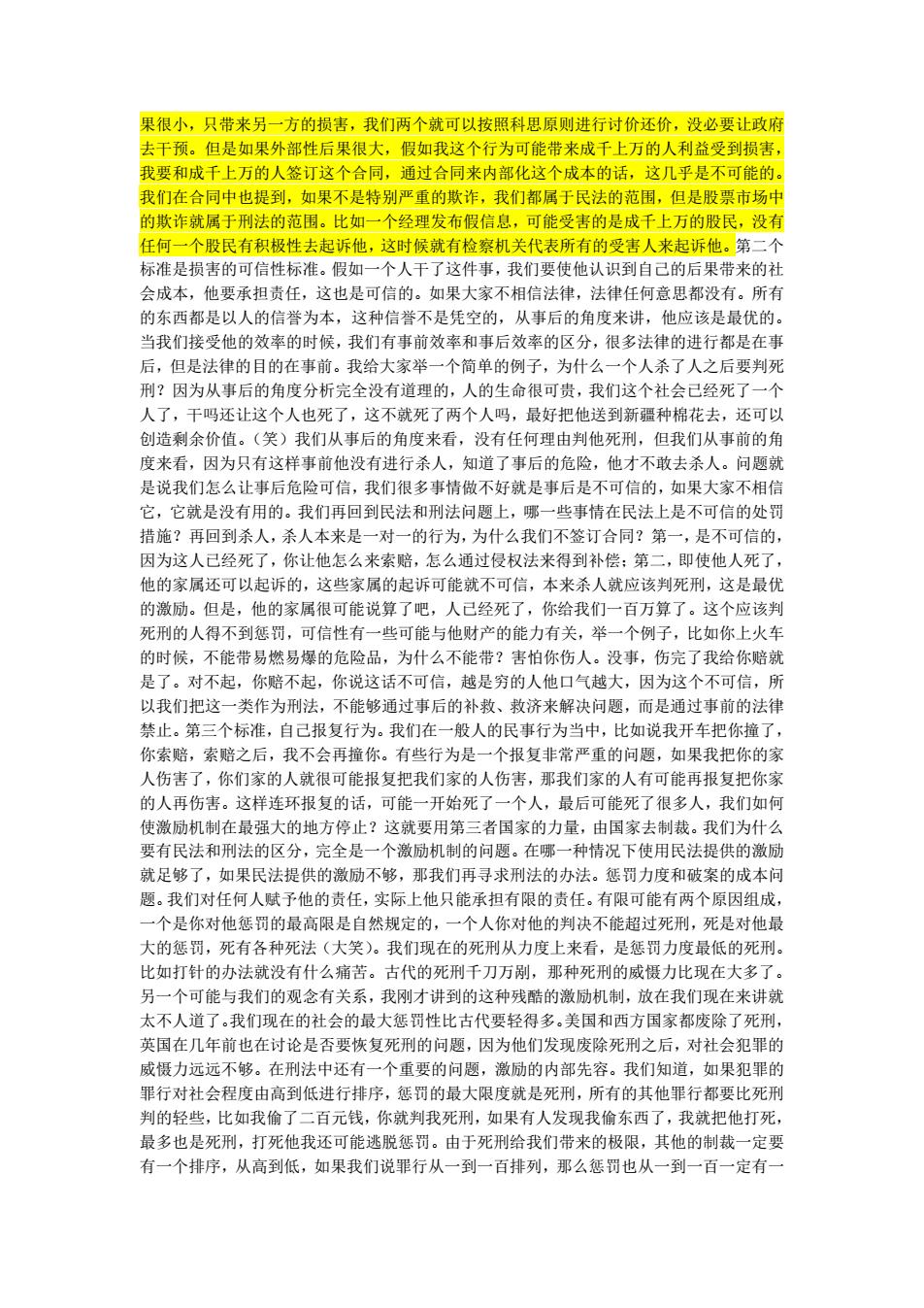
果很小,只带来另一方的损害,我们两个就可以按照科思原则进行讨价还价,没必要让政府 去干预。但是如果外部性后果很大,假如我这个行为可能带来成千上万的人利益受到损害, 我要和成千上万的人签订这个合同,通过合同来内部化这个成本的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合同中也提到,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欺诈,我们都属于民法的范围,但是股票市场中 的欺诈就属于刑法的范围。比如一个经理发布假信息,可能受害的是成千上万的股民,没有 任何一个股民有积极性去起诉他,这时候就有检察机关代表所有的受害人来起诉他。第二个 标准是损害的可信性标准。假如一个人干了这件事,我们要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后果带来的社 会成本,他要承担责任,这也是可信的。如果大家不相信法律,法律任何意思都没有。所有 的东西都是以人的信誉为本,这种信誉不是凭空的,从事后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最优的。 当我们接受他的效率的时候,我们有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的区分,很多法律的进行都是在事 后,但是法律的目的在事前。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一个人杀了人之后要判死 刑?因为从事后的角度分析完全没有道理的,人的生命很可贵,我们这个社会己经死了一个 人了,干吗还让这个人也死了,这不就死了两个人吗,最好把他送到新疆种棉花去,还可以 创造剩余价值。(笑)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判他死刑,但我们从事前的角 度来看,因为只有这样事前他没有进行杀人,知道了事后的危险,他才不敢去杀人。问题就 是说我们怎么让事后危险可信,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好就是事后是不可信的,如果大家不相信 它,它就是没有用的。我们再回到民法和刑法问题上,哪一些事情在民法上是不可信的处罚 措施?再回到杀人,杀人本来是一对一的行为,为什么我们不签订合同?第一,是不可信的, 因为这人已经死了,你让他怎么来索赔,怎么通过侵权法来得到补偿:第二,即使他人死了, 他的家属还可以起诉的,这些家属的起诉可能就不可信,本来杀人就应该判死刑,这是最优 的激励。但是,他的家属很可能说算了吧,人己经死了,你给我们一百万算了。这个应该判 死刑的人得不到惩罚,可信性有一些可能与他财产的能力有关,举一个例子,比如你上火车 的时候,不能带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为什么不能带?害怕你伤人。没事,伤完了我给你赔就 是了。对不起,你赔不起,你说这话不可信,越是穷的人他口气越大,因为这个不可信,所 以我们把这一类作为刑法,不能够通过事后的补救、救济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事前的法律 禁止。第三个标准,自己报复行为。我们在一般人的民事行为当中,比如说我开车把你撞了, 你索赔,索赔之后,我不会再撞你。有些行为是一个报复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我把你的家 人伤害了,你们家的人就很可能报复把我们家的人伤害,那我们家的人有可能再报复把你家 的人再伤害。这样连环报复的话,可能一开始死了一个人,最后可能死了很多人,我们如何 使激励机制在最强大的地方停止?这就要用第三者国家的力量,由国家去制裁。我们为什么 要有民法和刑法的区分,完全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在哪一种情况下使用民法提供的激励 就足够了,如果民法提供的激励不够,那我们再寻求刑法的办法。惩罚力度和破案的成本问 题。我们对任何人赋予他的责任,实际上他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有限可能有两个原因组成, 一个是你对他惩罚的最高限是自然规定的,一个人你对他的判决不能超过死刑,死是对他最 大的惩罚,死有各种死法(大笑)。我们现在的死刑从力度上来看,是惩罚力度最低的死刑。 比如打针的办法就没有什么痛苦。古代的死刑千刀万刷,那种死刑的威慑力比现在大多了。 另一个可能与我们的观念有关系,我刚才讲到的这种残酷的激励机制,放在我们现在来讲就 太不人道了,我们现在的社会的最大惩罚性比古代要轻得多。美国和西方国家都废除了死刑, 英国在几年前也在讨论是否要恢复死刑的问题,因为他们发现废除死刑之后,对社会犯罪的 威慑力远远不够。在刑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激励的内部先容。我们知道,如果犯罪的 罪行对社会程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惩罚的最大限度就是死刑,所有的其他罪行都要比死刑 判的轻些,比如我偷了二百元钱,你就判我死刑,如果有人发现我偷东西了,我就把他打死, 最多也是死刑,打死他我还可能逃脱惩罚。由于死刑给我们带来的极限,其他的制裁一定要 有一个排序,从高到低,如果我们说罪行从一到一百排列,那么惩罚也从一到一百一定有一
果很小,只带来另一方的损害,我们两个就可以按照科思原则进行讨价还价,没必要让政府 去干预。但是如果外部性后果很大,假如我这个行为可能带来成千上万的人利益受到损害, 我要和成千上万的人签订这个合同,通过合同来内部化这个成本的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合同中也提到,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欺诈,我们都属于民法的范围,但是股票市场中 的欺诈就属于刑法的范围。比如一个经理发布假信息,可能受害的是成千上万的股民,没有 任何一个股民有积极性去起诉他,这时候就有检察机关代表所有的受害人来起诉他。第二个 标准是损害的可信性标准。假如一个人干了这件事,我们要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后果带来的社 会成本,他要承担责任,这也是可信的。如果大家不相信法律,法律任何意思都没有。所有 的东西都是以人的信誉为本,这种信誉不是凭空的,从事后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最优的。 当我们接受他的效率的时候,我们有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的区分,很多法律的进行都是在事 后,但是法律的目的在事前。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一个人杀了人之后要判死 刑?因为从事后的角度分析完全没有道理的,人的生命很可贵,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死了一个 人了,干吗还让这个人也死了,这不就死了两个人吗,最好把他送到新疆种棉花去,还可以 创造剩余价值。(笑)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判他死刑,但我们从事前的角 度来看,因为只有这样事前他没有进行杀人,知道了事后的危险,他才不敢去杀人。问题就 是说我们怎么让事后危险可信,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好就是事后是不可信的,如果大家不相信 它,它就是没有用的。我们再回到民法和刑法问题上,哪一些事情在民法上是不可信的处罚 措施?再回到杀人,杀人本来是一对一的行为,为什么我们不签订合同?第一,是不可信的, 因为这人已经死了,你让他怎么来索赔,怎么通过侵权法来得到补偿;第二,即使他人死了, 他的家属还可以起诉的,这些家属的起诉可能就不可信,本来杀人就应该判死刑,这是最优 的激励。但是,他的家属很可能说算了吧,人已经死了,你给我们一百万算了。这个应该判 死刑的人得不到惩罚,可信性有一些可能与他财产的能力有关,举一个例子,比如你上火车 的时候,不能带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为什么不能带?害怕你伤人。没事,伤完了我给你赔就 是了。对不起,你赔不起,你说这话不可信,越是穷的人他口气越大,因为这个不可信,所 以我们把这一类作为刑法,不能够通过事后的补救、救济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事前的法律 禁止。第三个标准,自己报复行为。我们在一般人的民事行为当中,比如说我开车把你撞了, 你索赔,索赔之后,我不会再撞你。有些行为是一个报复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我把你的家 人伤害了,你们家的人就很可能报复把我们家的人伤害,那我们家的人有可能再报复把你家 的人再伤害。这样连环报复的话,可能一开始死了一个人,最后可能死了很多人,我们如何 使激励机制在最强大的地方停止?这就要用第三者国家的力量,由国家去制裁。我们为什么 要有民法和刑法的区分,完全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在哪一种情况下使用民法提供的激励 就足够了,如果民法提供的激励不够,那我们再寻求刑法的办法。惩罚力度和破案的成本问 题。我们对任何人赋予他的责任,实际上他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有限可能有两个原因组成, 一个是你对他惩罚的最高限是自然规定的,一个人你对他的判决不能超过死刑,死是对他最 大的惩罚,死有各种死法(大笑)。我们现在的死刑从力度上来看,是惩罚力度最低的死刑。 比如打针的办法就没有什么痛苦。古代的死刑千刀万剐,那种死刑的威慑力比现在大多了。 另一个可能与我们的观念有关系,我刚才讲到的这种残酷的激励机制,放在我们现在来讲就 太不人道了。我们现在的社会的最大惩罚性比古代要轻得多。美国和西方国家都废除了死刑, 英国在几年前也在讨论是否要恢复死刑的问题,因为他们发现废除死刑之后,对社会犯罪的 威慑力远远不够。在刑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激励的内部先容。我们知道,如果犯罪的 罪行对社会程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惩罚的最大限度就是死刑,所有的其他罪行都要比死刑 判的轻些,比如我偷了二百元钱,你就判我死刑,如果有人发现我偷东西了,我就把他打死, 最多也是死刑,打死他我还可能逃脱惩罚。由于死刑给我们带来的极限,其他的制裁一定要 有一个排序,从高到低,如果我们说罪行从一到一百排列,那么惩罚也从一到一百一定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