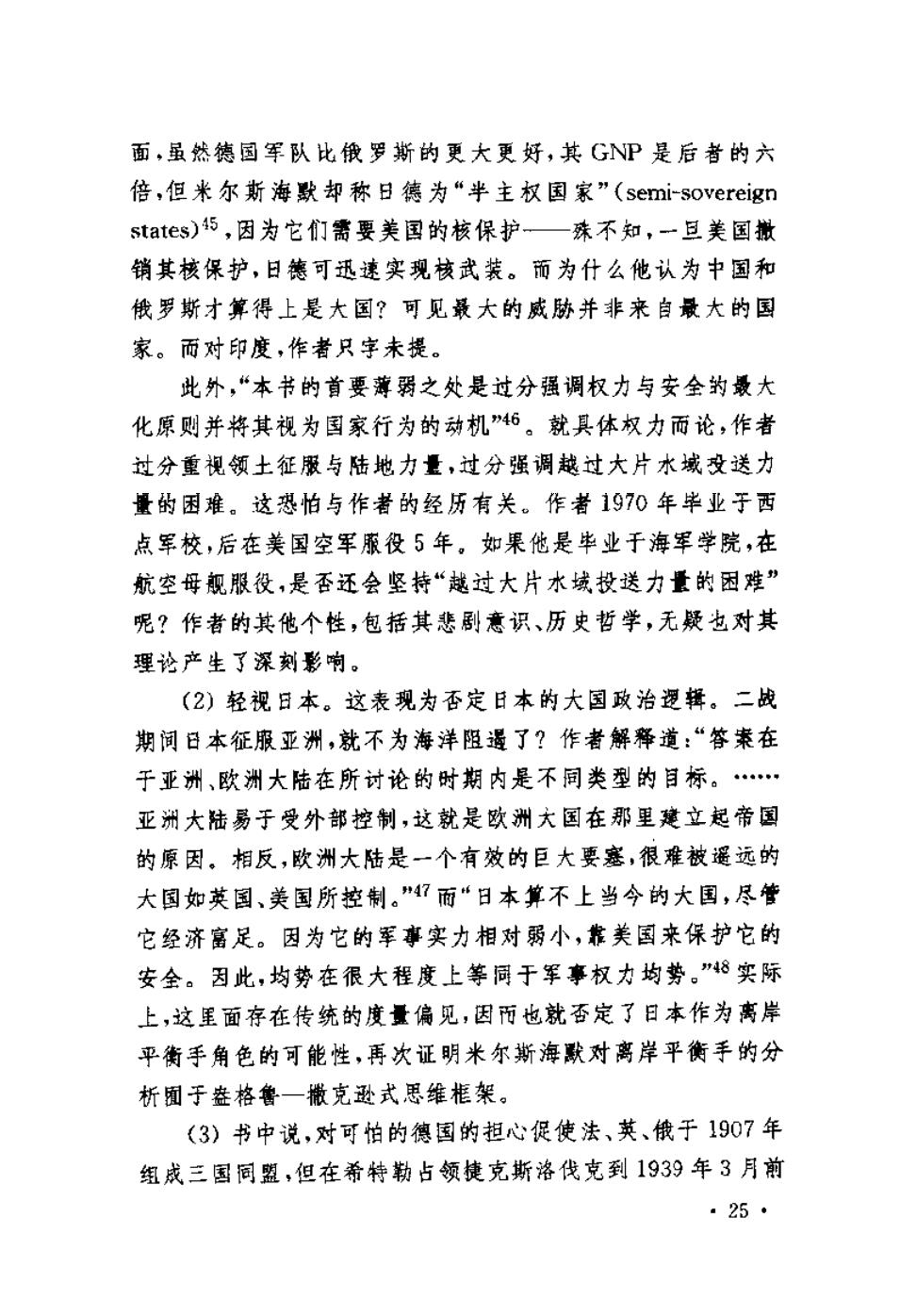
面,虽然德国军队比俄罗斯的更大更好,其GNP是后者的六 倍,但米尔斯海默却称日德为“半主权国家”(semi-sovereign state$)5,因为它们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一殊不知,一旦美国撒 销其核保护,日熊可迅速实现核武装。而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和 俄罗斯才算得上是大国?可见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最大的国 家。而对印度,作者只宇未提。 此外,“本书的首要薄弱之处是过分强调权力与安全的最大 化原则并将其视为国家行为的动机”46。就具体权力而论,作者 过分重视领土征服与陆地力量,过分强调越过大片水域设送力 量的困推。这恐怕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作者1970年毕业于西 点军校,后在美国空军服役5年。如果他是毕业于海军学院,在 航空母舰服役,是否还会坚持“越过大片水域投送力量的困难” 呢?作者的其他个性,包括其悲剧意识、历史哲学,无疑也对其 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2)轻视日本。这表现为否定日本的大国政治逻辑。二战 期间任本征服亚洲,就不为海洋阻遥了?作者解释道:“答案在 于亚洲、欧洲大陆在所讨论的时期内是不同类型的自标。… 亚洲大陆易于受外部控制,这就是欧洲大国在那里建立起帝国 的原因。相反,欧洲大陆是一个有效的巨大要塞,很难被遥远的 大国如英国、美国所控制。”47而“日本算不上当今的大国,尽管 它经济富足。因为它的军事实力相对弱小,靠美国来保护它的 安全。因此,均势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军事权力均势。”48实际 上,这里面存在传统的度量偏见,因而也就否定了日本作为离岸 平衡手角色的可能性,再次证明米尔斯海默对离岸平衡手的分 析囿于盎格鲁一撒克逊式思维柜架。 (3)书中说,对可怕的德国的担心促使法、英、俄于1907年 组成三国同盟,但在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到1939年3月前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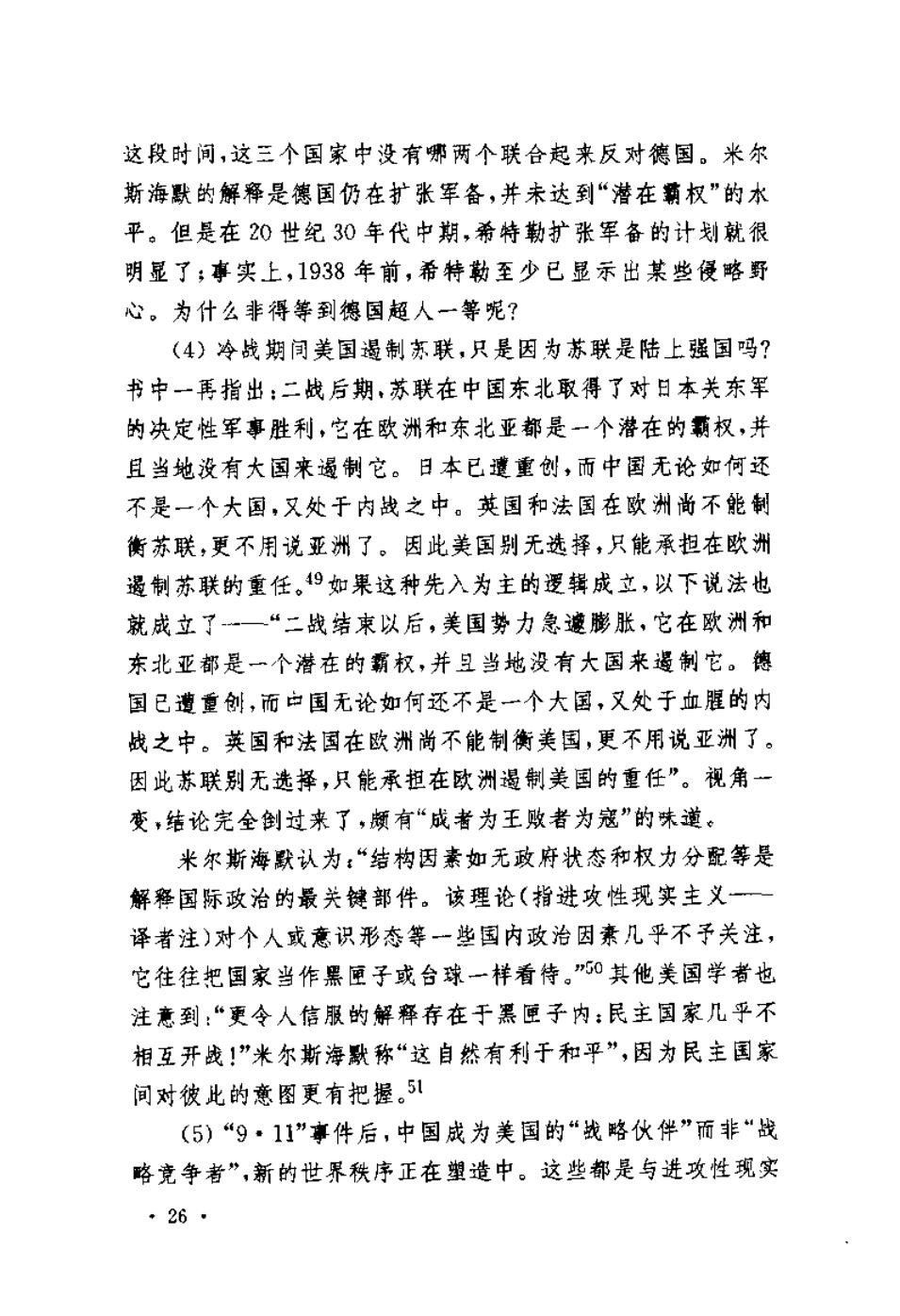
这段时间,这三个国家中没有哪两个联合起来反对德国。米尔 斯海默的解释是德国仍在扩张军备,并未达到“潜在霸权”的水 平。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希特勒扩张军备的计划就很 明显了;事实上,1938年前,希特勒至少已显示出某些侵略野 心。为什么非得等到德国超人一等呢? (4)冷战期间美国遏制苏联,只是因为苏联是陆上强国吗? 书中一再指出:二战后期,苏联在中国东北取得了对日本关东军 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它在欧洲和东北亚都是一个潜在的霸权,并 且当地设有大国来遏制它。日本已遣重创,而中国无论如何还 不是一个大国,又处于内战之中。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尚不能制 衡苏联,更不用说亚洲了。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担在欧洲 遏制苏联的重任。9如果这种先入为主的逻辑成立,以下说法也 就成立了一“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势力急遵膨胀,它在欧洲和 东北亚都是一个潜在的霸权,并且当地没有大国来遏制它。德 国已遭重创,而白国无论如何还不是一个大国,又处于血腥的内 战之中。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尚不能制衡美国,更不用说亚洲了。 因此苏联别无选择,只能承担在欧洲遏制美国的重任”。视角一 变,结论完全倒过来了,颇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味谨。 米尔斯海默认为:“结构因素如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分配等是 解释国际政治的最关键部件。该理论(指进攻性现实主义一 泽者注)对个人或意识形态等一些国内政治因素几乎不予关注, 它往往把国家当作黑匣子或台球一样看待。”0其他美国学者也 注意到:“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存在于黑匣子内:民主国家几乎不 相互开战!”米尔斯海默称“这自然有利于和平”,因为民主国家 间对彼此的意图更有把握。51 (5)“9·11”事件后,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而非“战 略竟争者”,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塑造中。这些都是与进攻性现实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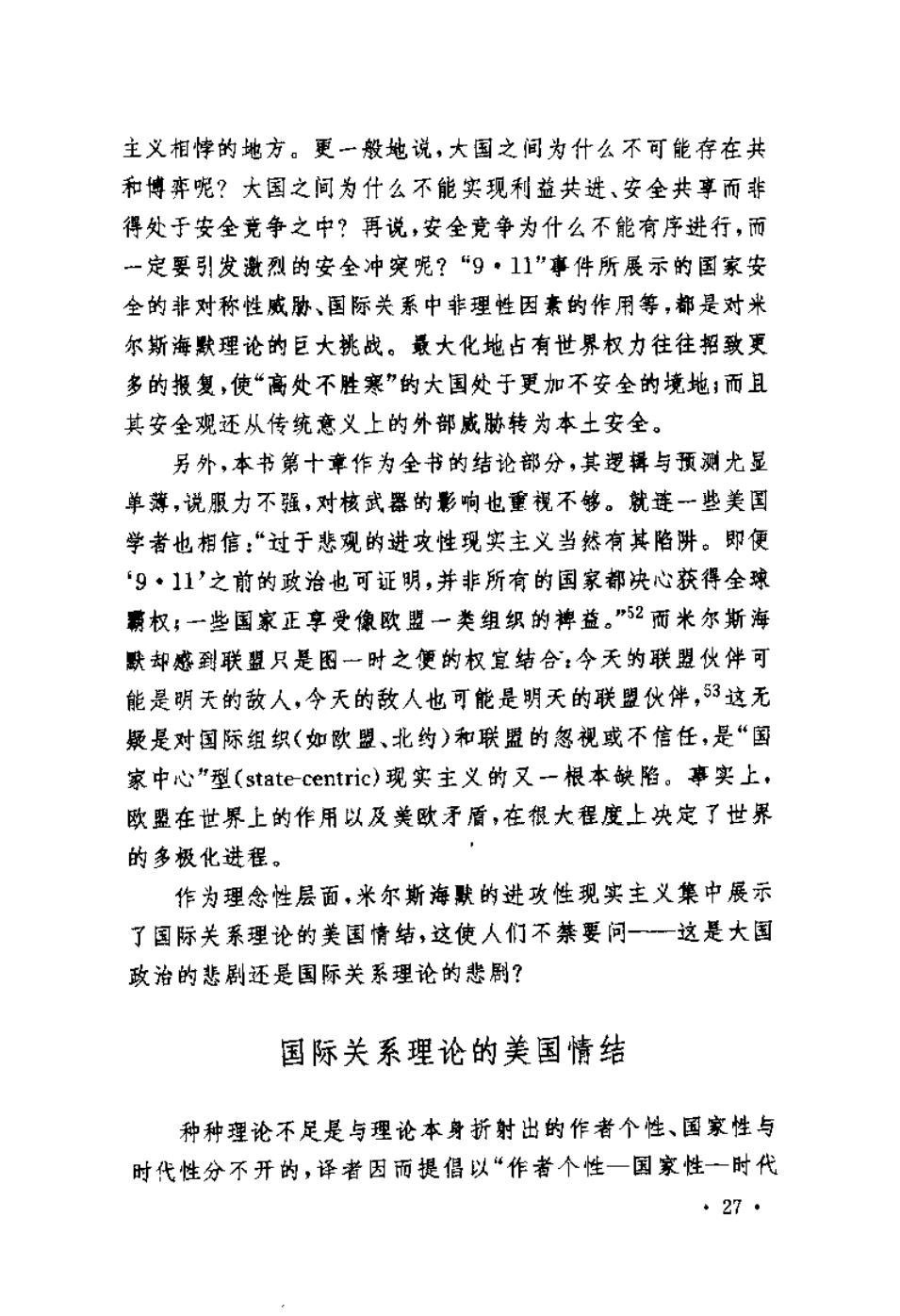
主义相悖的地方。更一般地说,大国之间为什么不可能存在共 和博弈呢?大国之间为什么不能实现利益共进、安全共享而非 得处于安全竞争之中?再说,安全竞争为什么不能有序进行,而 一定要引发激烈的安全冲突呢?“9·11”事件所展示的国家安 全的非对称性威胁、国际关系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等,都是对米 尔斯海默理论的巨大挑战。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往往招致更 多的报复,使“高处不胜寒”的大国处于更加不安全的境地:而且 其安全观还从传统意义上的外部威胁转为本土安全。 另外,本书第十章作为全书的结论部分,其逻辑与预测尤显 单薄,说服力不强,对核武器的影响也重视不够。就连一些美国 学者也相信:“过于悲观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当然有其陷阱。即便 ‘9·11’之前的政治也可证明,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决心获得全球 精权;一些国家正享受像欧盟一类组织的裨益。52而米尔斯海 默却感到联盟只是图一时之便的权宜结合:今天的联盟伙伴可 能是明天的敌人,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明天的联盟伙伴,53这无 疑是对国际组织(如欧盟、北约)和联盟的怒视或不信任,是“国 家中心”型(state-centric)现实主义的又一根本缺陷。事实上, 欧盟在世界上的作用以及美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央定了世界 的多极化进程。 作为理念性层面,米尔斯海联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集中展示 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情结,这使人们不禁要问一这是大国 政治的悲剧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 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情结 种种理论不足是与理论本身折射出的作者个性、国家性与 时代性分不开的,译者因而提倡以“作者个性一国家性一时代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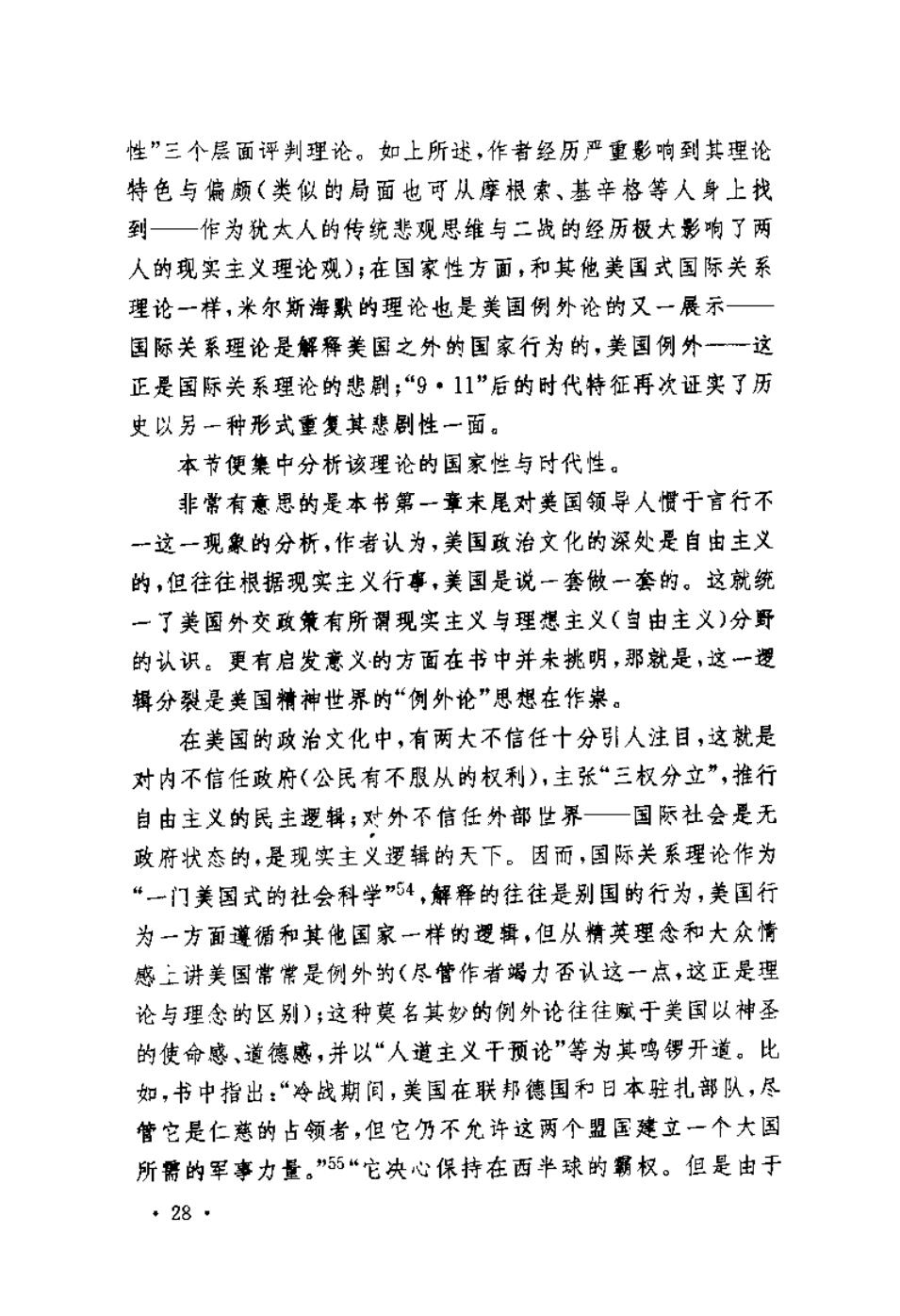
性”三个层面评判理论。如上所述,作者经历严重影响到其理论 特色与偏颇(类似的局面也可从摩根索、基辛格等人身上找 到一作为犹太人的传统悲观思维与二战的经历极大影响了两 人的现实主义理论观);在国家性方面,和其他美国式国际关系 理论一样,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也是美国例外论的又一展示一 国际关系理论是解释美国之外的国家行为的,美国例外一这 正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别;“9·11”后的时代特征再次证实了历 史以另一种形式重复其悲剧性一面。 本节便集中分桥该理论的国家性与时代性。 非常有意思的是本书第一章末尾对美国领导人惯于言行不 一这一现象的分析,作者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处是自由主义 的,但往往根据现实主义行事,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这就统 一了美国外交政缣有所谓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分野 的认识。更有启发意义的方面在书中并未挑明,那就是,这一逻 辑分裂是美国精神世界的“例外论”思想在作崇。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有两大不信任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 对内不信任政府(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主张“三权分立”,推行 自由主义的民主逻辑;对外不信任外部世界—国际社会是无 政府状态的,是现实主义逻辑的天下。因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 “一门美国式的社会科学54,解释的往往是别国的行为,美国行 为一方面遵循和其他国家一样的逻辑,但从精英理念和大众情 感上讲美国常常是例外的(尽管作者竭力否认这一点,这正是理 论与理念的区别);这种莫名其炒的例外论往往赋于美国以神圣 的使命感、道德感,并以“人道主义干预论”等为其鸣锣开道。比 知,书中指出:“冷战期间,美国在联邦德国和日本驻扎部队,尽 管它是仁慈的占领者,但它仍不允许这两个盟国建立一个大国 所需的军事力量。55“它决心保持在西半球的霸权。但是由于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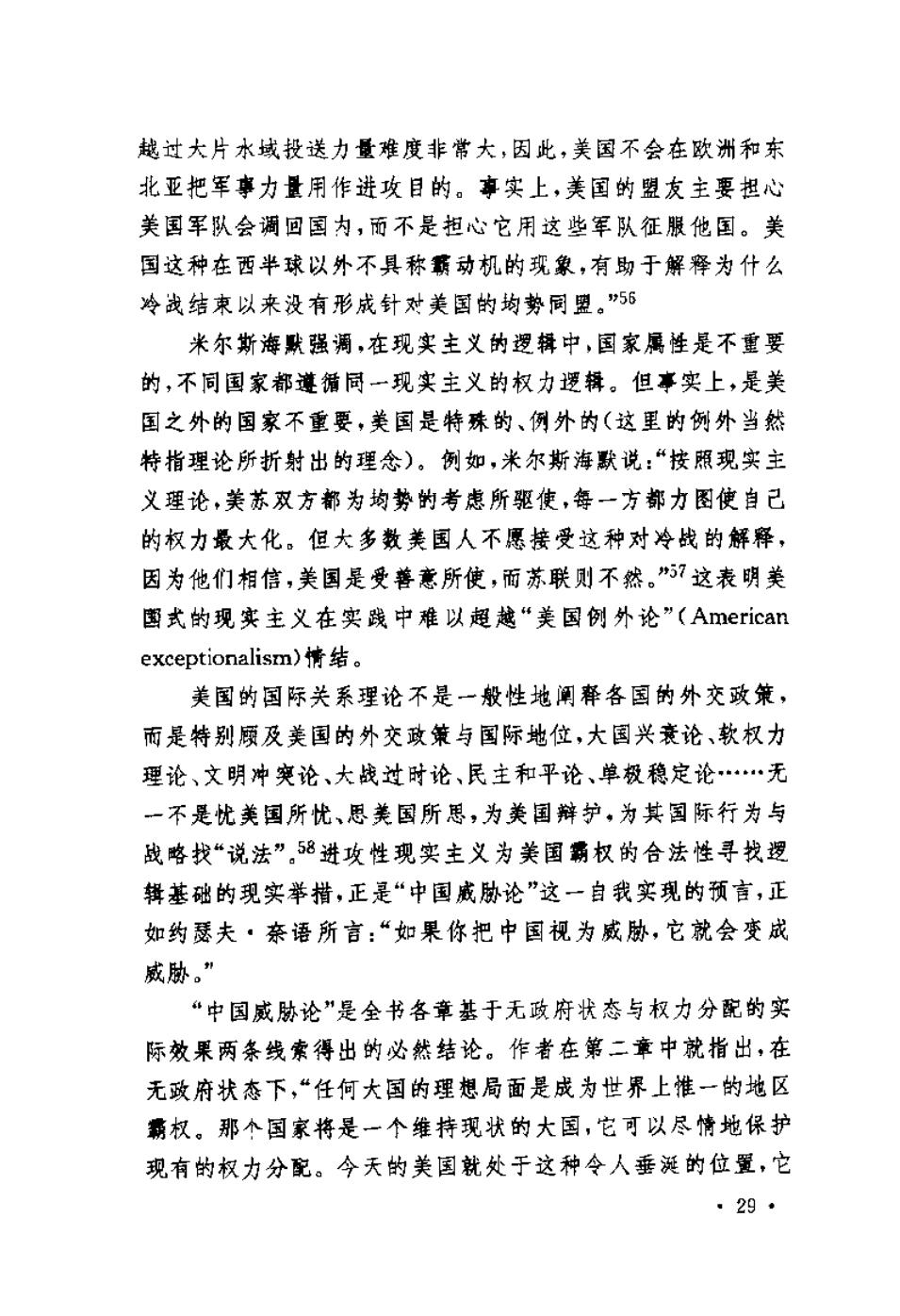
越过大片水域投送力量难度非常大,因此,美国不会在欧洲和东 北亚把军事力量用作进攻目的。事实上,美国的盟友主要担心 美国军队会调回国为,而不是担心它用这些军队征服他国。美 国这种在西半球以外不具称病动机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冷浅结束以来没有形成针对美国的均势同盟。56 米尔斯海默强调,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国家属性是不重要 的,不同国家都遵循同一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但事实上,是美 国之外的国家不重要,美国是特殊的、例外的(这里的例外当然 特指理论所折射出的理念)。例如,米尔斯海默说:“按照现实主 义理论,美苏效方都为均势的考虑所驱使,每一方都力图使自己 的权力最大化。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接受这种对冷战的解释, 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受善意所使,面苏联则不然。5?这表明美 图式的现实主义在实践中雅以超越“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情结。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般性地阐释各国的外交政策, 而是特别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大国兴衰论、软权力 理论、文明冲突论、大战过时论、民主和平论、单极稳定论…无 一不是忧美国所忧、思美国所思,为美国辩护,为其国际行为与 战略找“说法”,58进攻性现实主义为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寻找逻 辑基础的现实举措,正是“中国威胁论”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正 如约瑟夫·奈语所言:“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 威胁。” “中国威胁论”是全书各章基于无政府状态与权力分配的实 际效果两条线索得出的必然结论。作者在第二章中就指出,在 无政府状态下,“任何大国的理想局面是成为世界上推一的地区 薄权。那个国家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它可以尽情地保护 现有的权力分配。今天的美国就处于这种令人垂诞的位置,它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