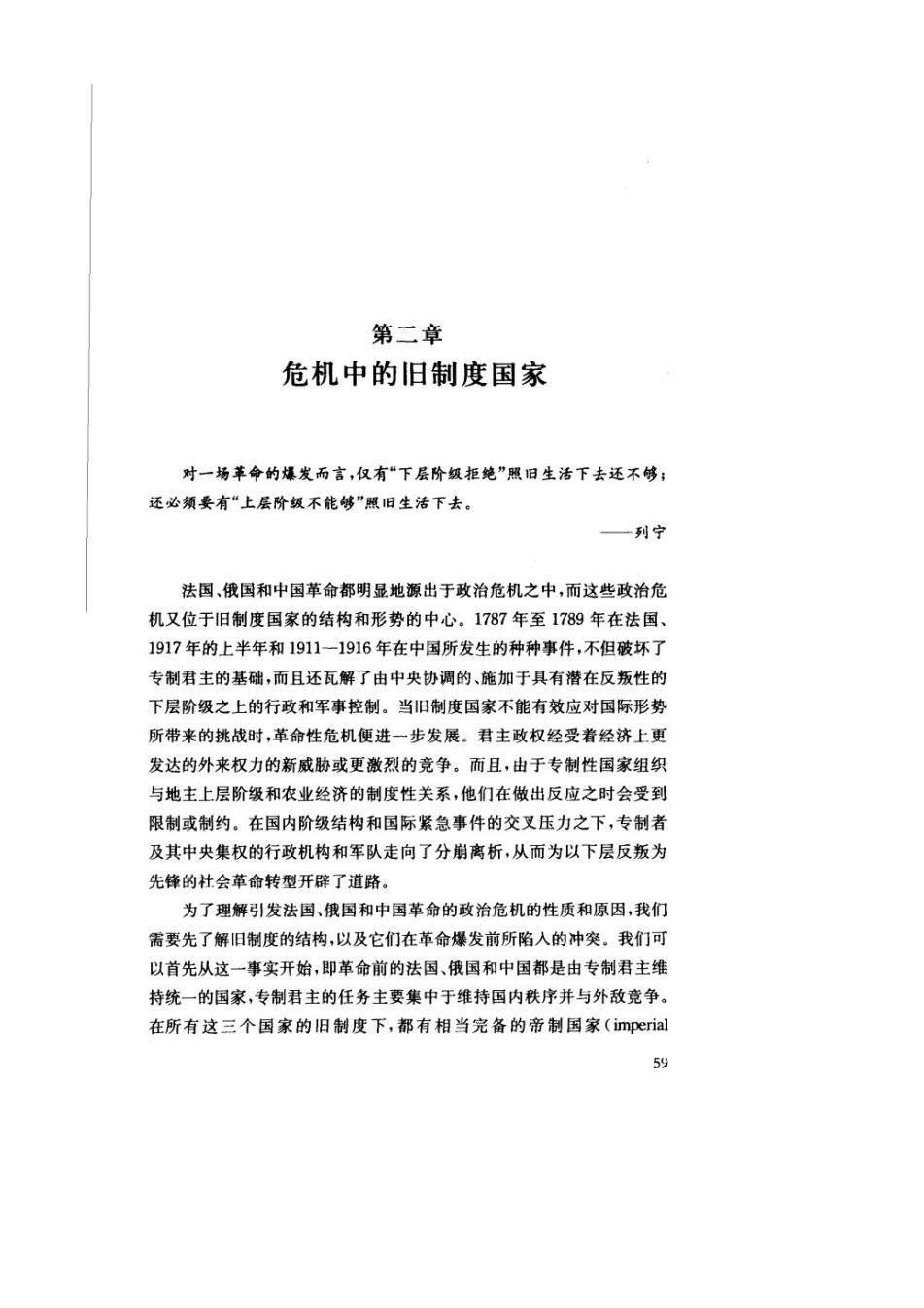
第二章 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对一场革命的爆发而言,仅有“下层阶级拒绝”照旧生活下去还不够: 还必须要有“上层阶级不能够”照旧生活下去。 一列宁 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明显地源出于政治危机之中,而这些政治危 机又位于旧制度国家的结构和形势的中心。1787年至1789年在法国、 1917年的上半年和1911一1916年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不但破坏了 专制君主的基础,而且还瓦解了由中央协调的、施加于具有潜在反叛性的 下层阶级之上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当旧制度国家不能有效应对国际形势 所带来的挑战时,革命性危机便进一步发展。君主政权经受着经济上更 发达的外来权力的新威胁或更激烈的竞争。而且,由于专制性国家组织 与地主上层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性关系,他们在做出反应之时会受到 限制或制约。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之下,专制者 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以下层反叛为 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 为了理解引发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政治危机的性质和原因,我们 需要先了解旧制度的结构,以及它们在革命爆发前所陷入的冲突。我们可 以首先从这一事实开始,即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中国都是由专制君主维 持统一的国家,专制君主的任务主要集中于维持国内秩序并与外敌竞争。 在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旧制度下,都有相当完备的帝制国家(imperial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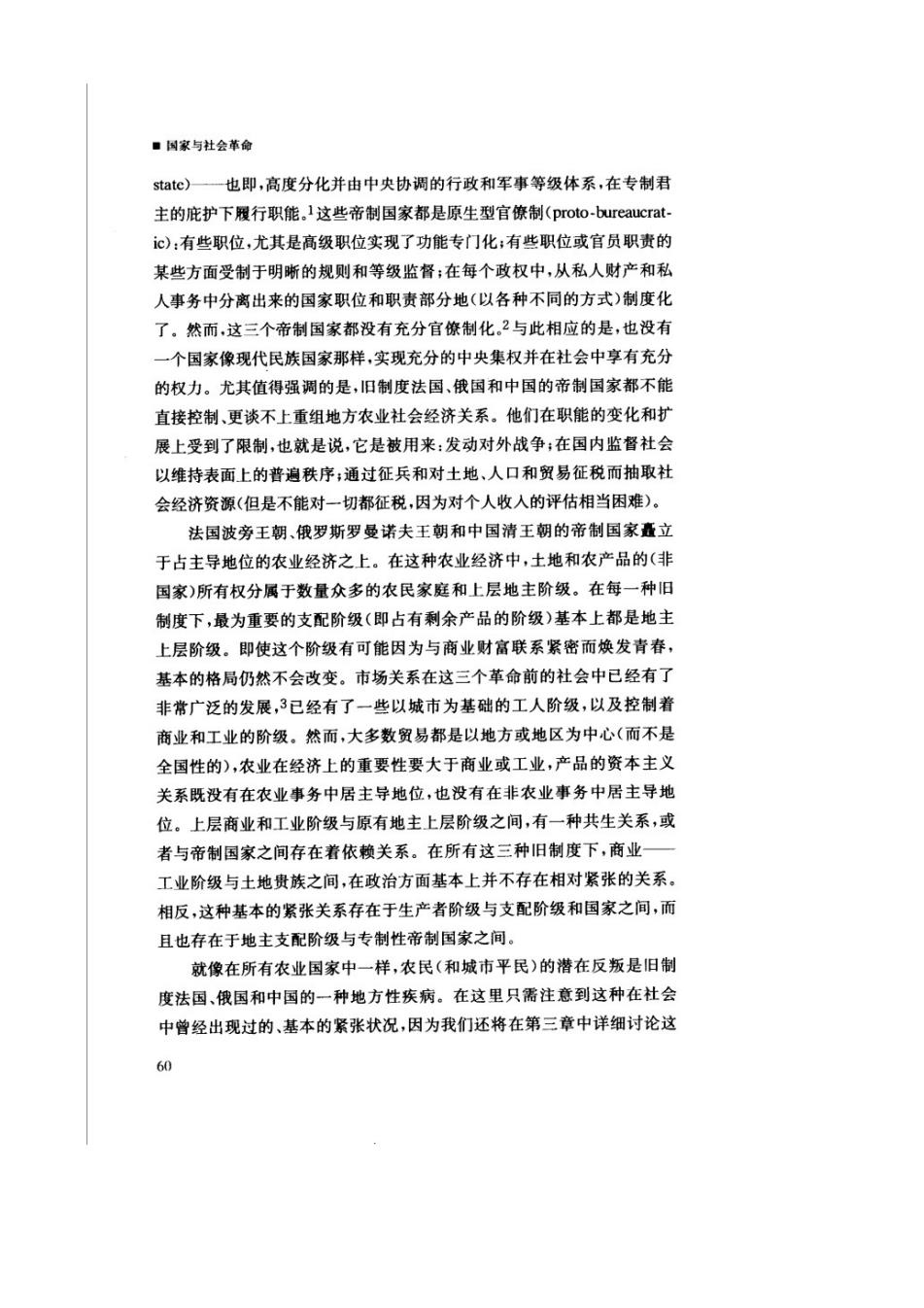
■国家与社会革偷 state)一也即,高度分化并由中央协调的行政和军事等级体系,在专制君 主的庇护下履行职能,l这些帝制国家都是原生型官僚制(proto-bureaucrat-- i©):有些职位,尤其是高级职位实现了功能专门化;有些职位或官员职责的 某些方面受制于明晰的规则和等级监督;在每个政权中,从私人财产和私 人事务中分离出来的国家职位和职责部分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制度化 了。然而,这三个帝制国家都没有充分官僚制化。2与此相应的是,也没有 一个国家像现代民族国家那样,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并在社会中享有充分 的权力。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旧制度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帝制国家都不能 直接控制、更谈不上重组地方农业社会经济关系。他们在职能的变化和扩 展上受到了限制,也就是说,它是被用来:发动对外战争:在国内监督社会 以维持表面上的普遍秩序;通过征兵和对土地、人口和贸易征税而抽取社 会经济资源(但是不能对一切都征税,因为对个人收人的评估相当困难)。 法国波旁王朝、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和中国清王朝的帝制国家矗立 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之上。在这种农业经济中,土地和农产品的(非 国家)所有权分属于数量众多的农民家庭和上层地主阶级。在每一种旧 制度下,最为重要的支配阶级(即占有剩余产品的阶级)基本上都是地主 上层阶级。即使这个阶级有可能因为与商业财富联系紧密而焕发青春, 基本的格局仍然不会改变。市场关系在这三个革命前的社会中已经有了 非常广泛的发展,3已经有了一些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以及控制着 商业和工业的阶级。然而,大多数贸易都是以地方或地区为中心(而不是 全国性的),农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要大于商业或工业,产品的资本主义 关系既没有在农业事务中居主导地位,也没有在非农业事务中居主导地 位。上层商业和工业阶级与原有地主上层阶级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或 者与帝制国家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在所有这三种旧制度下,商业 工业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在政治方面基本上并不存在相对紧张的关系。 相反,这种基本的紧张关系存在于生产者阶级与支配阶级和国家之间,而 且也存在于地主支配阶级与专制性帝制国家之间。 就像在所有农业国家中一样,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潜在反叛是旧制 度法国、俄国和中国的一种地方性疾病。在这里只需注意到这种在社会 中曾经出现过的、基本的紧张状况,因为我们还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这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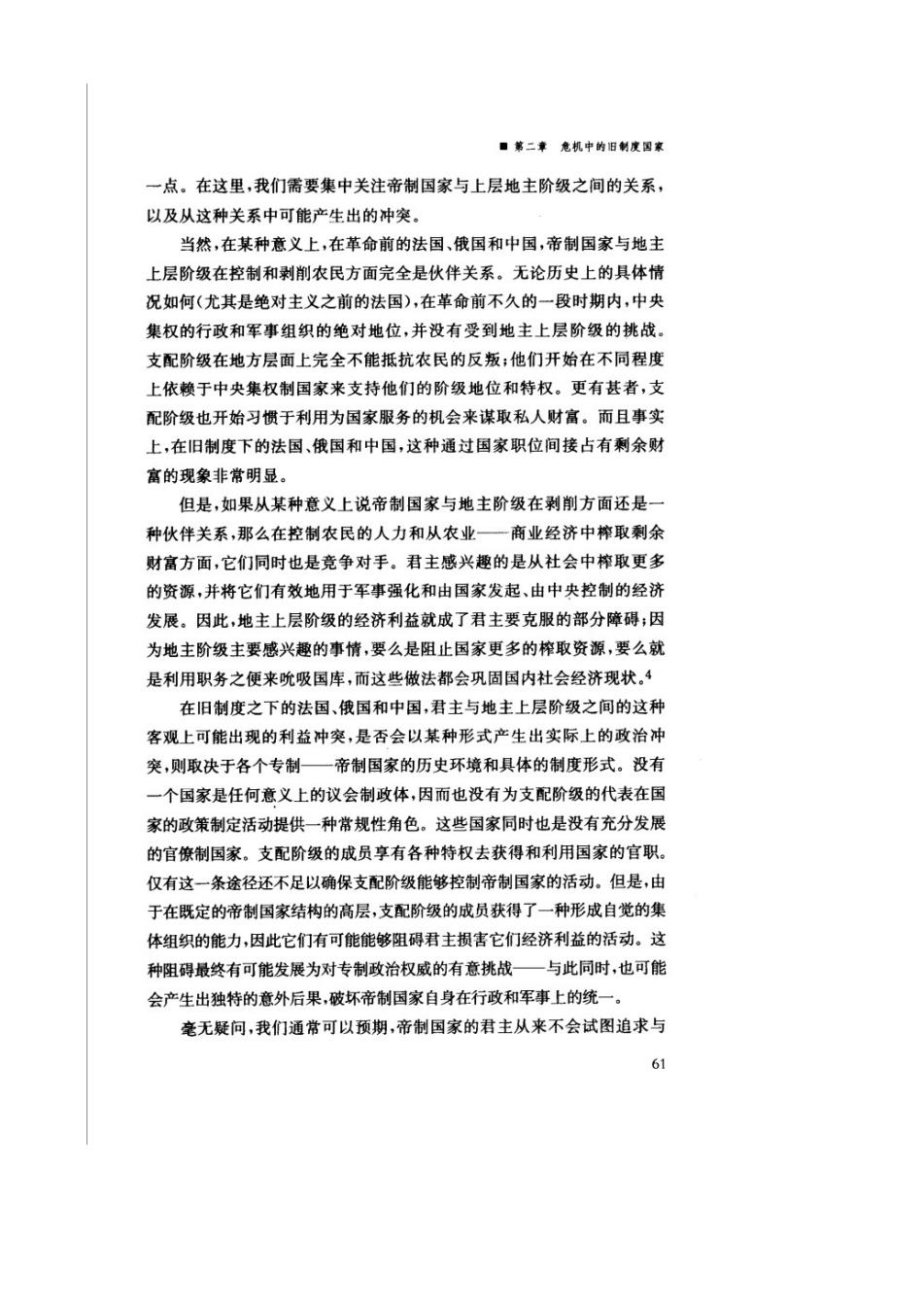
■第二章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一点。在这里,我们需要集中关注帝制国家与上层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 以及从这种关系中可能产生出的冲突。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在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中国,帝制国家与地主 上层阶级在控制和剥削农民方面完全是伙伴关系。无论历史上的具体情 况如何(尤其是绝对主义之前的法国),在革命前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中央 集权的行政和军事组织的绝对地位,并没有受到地主上层阶级的挑战。 支配阶级在地方层面上完全不能抵抗农民的反叛:他们开始在不同程度 上依赖于中央集权制国家来支持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特权。更有甚者,支 配阶级也开始习惯于利用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来谋取私人财富。而且事实 上,在旧制度下的法国、俄国和中国,这种通过国家职位间接占有剩余财 富的现象非常明显。 但是,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制国家与地主阶级在剥削方面还是一 种伙伴关系,那么在控制农民的人力和从农业一商业经济中榨取剩余 财富方面,它们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君主感兴趣的是从社会中榨取更多 的资源,并将它们有效地用于军事强化和由国家发起、由中央控制的经济 发展。因此,地主上层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成了君主要克服的部分障碍;因 为地主阶级主要感兴趣的事情,要么是阻止国家更多的榨取资源,要么就 是利用职务之便来吮吸国库,而这些做法都会巩固国内杜会经济现状。4 在旧制度之下的法国、俄国和中国,君主与地主上层阶级之间的这种 客观上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是否会以某种形式产生出实际上的政治冲 突,则取决于各个专制一帝制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具体的制度形式。没有 一个国家是任何意义上的议会制政体,因而也没有为支配阶级的代表在国 家的政策制定活动提供一种常规性角色。这些国家同时也是没有充分发展 的官僚制国家。支配阶级的成员享有各种特权去获得和利用国家的官职。 仅有这一条途径还不足以确保支配阶级能够控制帝制国家的活动。但是,由 于在既定的帝制国家结构的高层,支配阶级的成员获得了一种形成自觉的集 体组织的能力,因此它们有可能能够阻碍君主损害它们经济利益的活动。这 种阻碍最终有可能发展为对专制政治权威的有意挑战一与此同时,也可能 会产生出独特的意外后果,破坏帝制国家自身在行政和军事上的统一。 毫无疑问,我们通常可以预期,帝制国家的君主从来不会试图追求与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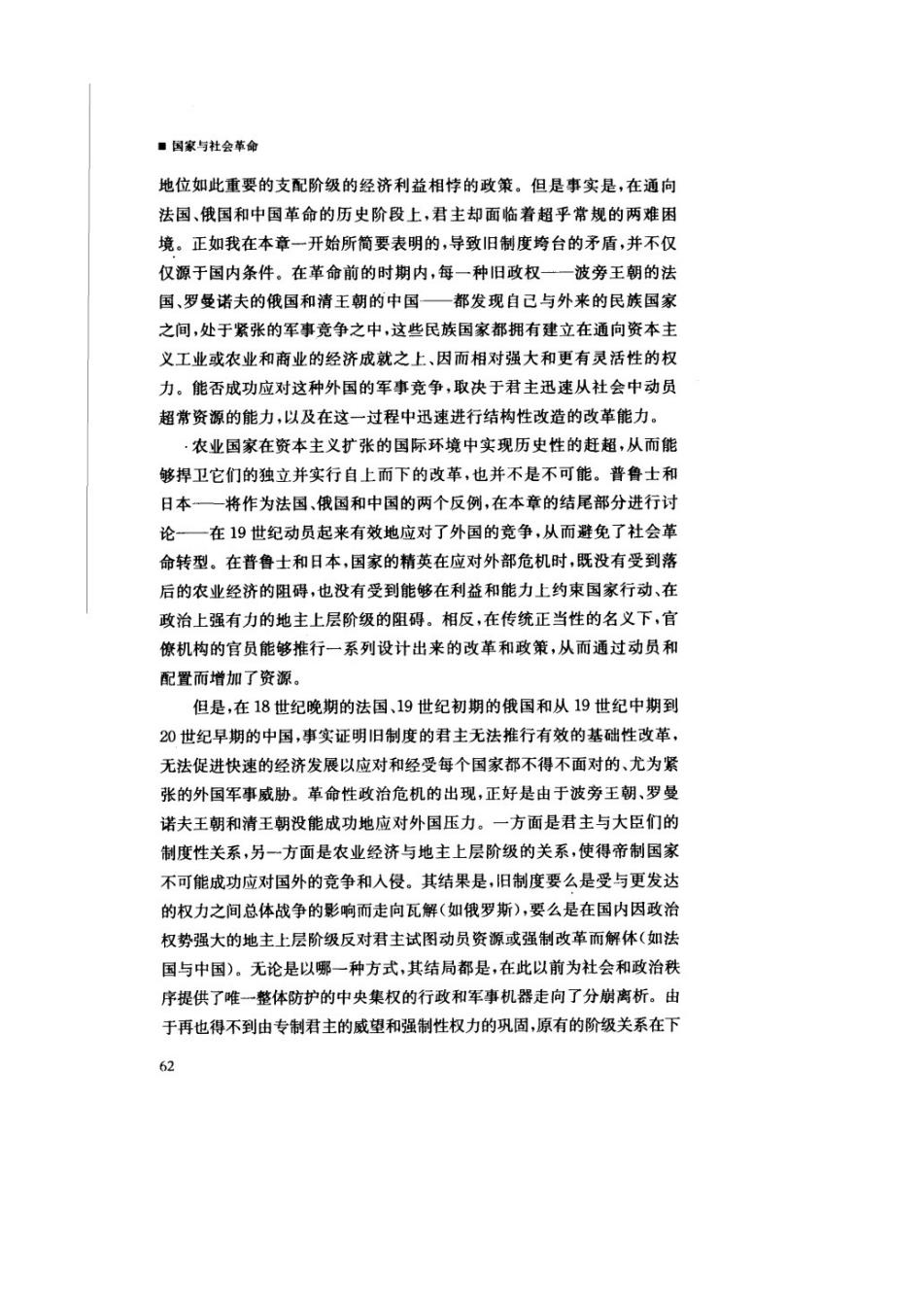
■国家与杜会革命 地位如此重要的支配阶级的经济利益相悖的政策。但是事实是,在通向 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上,君主却面临着超乎常规的两难困 境。正如我在本章一开始所简要表明的,导致旧制度垮台的矛盾,并不仅 仅源于国内条件。在革命前的时期内,每一种旧政权一一波旁王朝的法 国、罗曼诺夫的俄国和清王朝的中国一都发现自己与外来的民族国家 之间,处于紧张的军事竞争之中,这些民族国家都拥有建立在通向资本主 义工业或农业和商业的经济成就之上、因而相对强大和更有灵活性的权 力。能否成功应对这种外国的军事竞争,取决于君主迅速从社会中动员 超常资源的能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迅速进行结构性改造的改革能力。 ·农业国家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历史性的赶超,从而能 够捍卫它们的独立并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并不是不可能。普鲁士和 日本一—将作为法国、俄国和中国的两个反例,在本章的结尾部分进行讨 论一在19世纪动员起来有效地应对了外国的竞争,从而避免了社会革 命转型。在普鲁士和日本,国家的精英在应对外部危机时,既没有受到落 后的农业经济的阻碍,也没有受到能够在利益和能力上约束国家行动、在 政治上强有力的地主上层阶级的阻碍。相反,在传统正当性的名义下,官 僚机构的官员能够推行一系列设计出来的改革和政策,从而通过动员和 配置而增加了资源。 但是,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19世纪初期的俄国和从19世纪中期到 20世纪早期的中国,事实证明旧制度的君主无法推行有效的基础性改革, 无法促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应对和经受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尤为紧 张的外国军事威胁。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正好是由于波旁王朝、罗曼 诺夫王朝和清王朝没能成功地应对外国压力。一方面是君主与大臣们的 制度性关系,另一方面是农业经济与地主上层阶级的关系,使得帝制国家 不可能成功应对国外的竞争和入侵。其结果是,旧制度要么是受与更发达 的权力之间总体战争的影响而走向瓦解(如俄罗斯),要么是在国内因政治 权势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反对君主试图动员资源或强制改革而解体(如法 国与中国)。无论是以哪一种方式,其结局都是,在此以前为社会和政治秩 序提供了唯一整体防护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机器走向了分崩离析。由 于再也得不到由专制君主的威望和强制性权力的巩固,原有的阶级关系在下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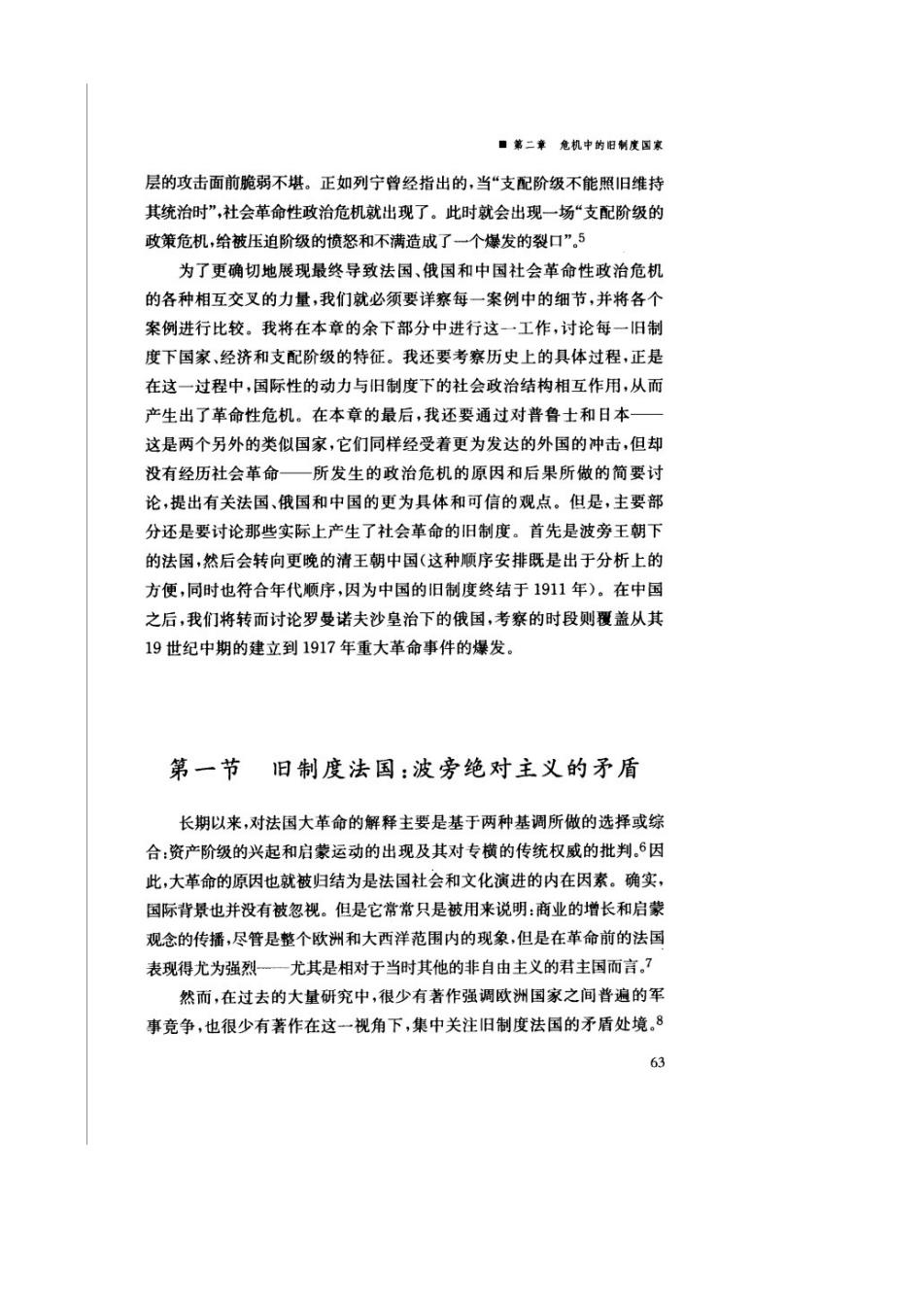
■第二章危机中的阳制度国家 层的攻击面前脆弱不堪。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当“支配阶级不能照旧维持 其统治时”,社会革命性政治危机就出现了。此时就会出现一场“支配阶级的 政策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了一个爆发的裂口”。5 为了更确切地展现最终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性政治危机 的各种相互交叉的力量,我们就必须要详察每一案例中的细节,并将各个 案例进行比较。我将在本章的余下部分中进行这一工作,讨论每一旧制 度下国家、经济和支配阶级的特征。我还要考察历史上的具体过程,正是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性的动力与旧制度下的社会政治结构相互作用,从而 产生出了革命性危机。在本章的最后,我还要通过对普鲁士和日本一 这是两个另外的类似国家,它们同样经受着更为发达的外国的冲击,但却 没有经历社会革命—所发生的政治危机的原因和后果所做的简要讨 论,提出有关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更为具体和可信的观点。但是,主要部 分还是要讨论那些实际上产生了社会革命的旧制度。首先是波旁王朝下 的法国,然后会转向更晚的清王朝中国(这种顺序安排既是出于分析上的 方便,同时也符合年代顺序,因为中国的旧制度终结于1911年)。在中国 之后,我们将转而讨论罗曼诺夫沙皇治下的俄国,考察的时段则覆盖从其 19世纪中期的建立到1917年重大革命事件的爆发。 第一节旧制度法国:波旁绝对主义的矛盾 长期以来,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主要是基于两种基调所做的选择或综 合: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出现及其对专横的传统权威的批判.6因 此,大革命的原因也就被归结为是法国社会和文化演进的内在因素。确实, 国际背景也并没有被忽视。但是它常常只是被用来说明:商业的增长和启蒙 观念的传播,尽管是整个欧洲和大西洋范围内的现象,但是在革命前的法国 表现得尤为强烈一尤其是相对于当时其他的非自由主义的君主国而言。? 然而,在过去的大量研究中,很少有著作强调欧洲国家之间普遍的军 事竞争,也很少有著作在这一视角下,集中关注旧制度法国的矛盾处境。8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