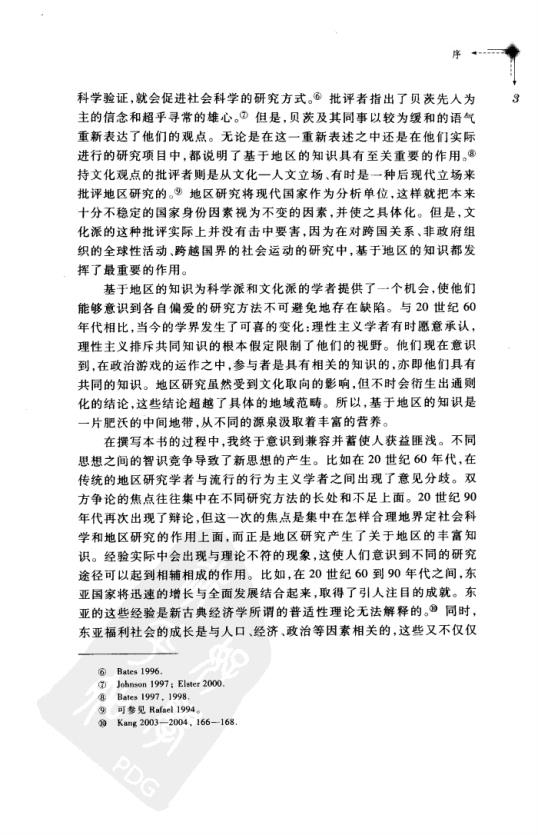
序 科学验证,就会促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批评者指出了贝茨先人为 3 主的信念和超平寻常的雄心。①但是,贝茨及其同事以较为缓和的语气 重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无论是在这一重新表述之中还是在他们实际 进行的研究项目中,都说明了基于地区的知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⑧ 持文化观点的批评者则是从文化一人文立场、有时是一种后现代立场来 批评地区研究的。地区研究将现代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这样就把本来 十分不稳定的国家身份因素视为不变的因素,并使之具体化。但是,文 化派的这种批评实际上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在对跨国关系、非政府组 织的全球性活动、跨越国界的杜会运动的研究中,基于地区的知识都发 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基于地区的知识为科学派和文化派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 能够意识到各自偏爱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与20世纪60 年代相比,当今的学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理性主义学者有时愿意承认, 理性主义排斥共同知识的根本假定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现在意识 到,在政治游戏的运作之中,参与者是具有相关的知识的,亦即他们具有 共同的知识。地区研究虽然受到文化取向的影响,但不时会衍生出通则 化的结论,这些结论超越了具体的地域范畴。所以,基于地区的知识是 一片肥沃的中间地带,从不同的源泉汲取着丰富的营养。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终于意识到兼容并蓄使人获益匪浅。不同 思想之间的智识竞争导致了新思想的产生。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在 传统的地区研究学者与流行的行为主义学者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双 方争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不同研究方法的长处和不足上面。20世纪90 年代再次出现了辩论,但这一次的焦点是集中在怎样合理地界定社会科 学和地区研究的作用上面,而正是地区研究产生了关于地区的丰富知 识。经验实际中会出现与理论不符的现象,这使人们意识到不同的研究 途径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比如,在20世纪60到90年代之间,东 亚国家将迅速的增长与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东 亚的这些经验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普适性理论无法解释的。》同时, 东亚福利社会的成长是与人口、经济,政治等因素相关的,这些又不仅仅 Bates 1996. Johnson 1997:Elster 2000. 年Ba1e31997.1998. 9可参见Rafacl1994。 Kng2003一2004,166一168 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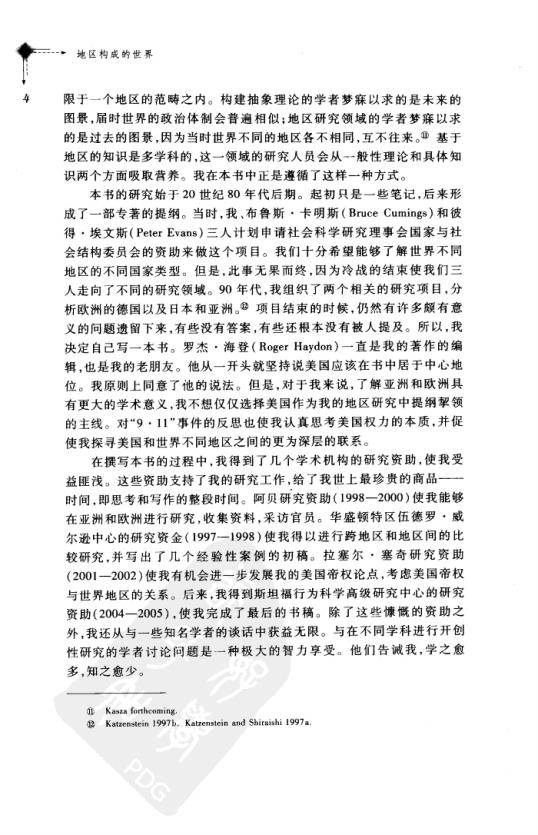
地区构战的世界 限于一个地区的范畴之内。构建抽象理论的学者梦寐以求的是未来的 图景,届时世界的政治体制会普遍相似:地区研究领域的学者梦寐以求 的是过去的图景,因为当时世界不同的地区各不相同,互不往来。基于 地区的知识是多学科的,这一领城的研究人员会从一般性理论和具体知 识两个方面吸取背养。我在本书中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方式。 本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初只是一些笔记,后来形 成了一部专著的提纲。当时,我,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和彼 得·埃文斯(Peter Evans)三人计划申请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国家与社 会结构委员会的资助来做这个项目。我们十分希望能够了解世界不同 地区的不同国家类型。但是,此事无果而终,因为冷战的结束使我们三 人走向了不同的研究领域。90年代,我组织了两个相关的研究项目,分 析欧洲的德国以及日本和亚洲。®项目结束的时候,仍然有许多颜有意 义的问题遗留下来,有些没有答案,有些还根本设有被人提及。所以,我 决定自己写一本书。罗杰·海登(Roger Haydon)一直是我的著作的编 辑,也是我的老朋友。他从一开头就坚持说美国应该在书中居于中心地 位。我原则上同意了池的说法。但是,对于我来说,了解亚洲和欧洲具 有更大的学术意义,我不想仅仅选择美国作为我的地区研究中提纲挈领 的主线。对“9·11"事件的反思也使我认真思考美国权力的本质,并促 使我探寻美国和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更为深层的联系。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几个学术机构的研究资助,使我受 益匪浅。这些资助支持了我的研究工作,给了我世上最珍贵的商品一一 时间,即思考和写作的整段时间。阿贝研究资助(1998一2000)使我能够 在亚洲和欧洲进行研究,收集资料,采访官员。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 尔逊中心的研究资金(1997一1998)使我得以进行跨地区和地区间的比 较研究,并写出了几个经验性案例的初稿。拉塞尔·塞奇研究资助 (2001一2002)使我有机会进一步发展我的美国帝权论点,考虑美国帝权 与世界地区的关系。后来,我得到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 资助(2004一2005),使我完成了最后的书稿。除了这些慷慨的资助之 外,我还从与一些知名学者的谈话中获益无限。与在不同学科进行开创 性研究的学者讨论问题是一种极大的智力享受。他们告诫我,学之愈 多,知之愈少。 Katzenstein 1997b.Katrenstein and Shiraishi 1997a. 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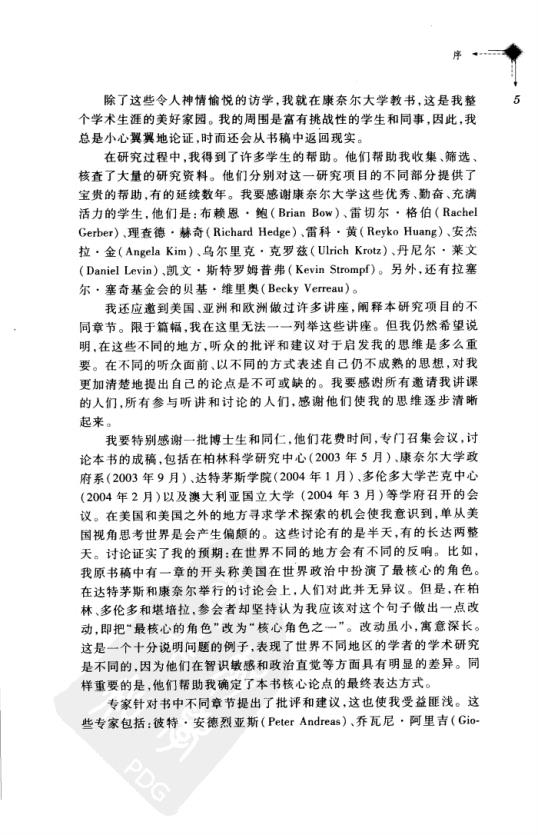
序 除了这些令人神情愉悦的访学,我就在康奈尔大学教书,这是我整 5 个学术生涯的美好家园。我的周围是富有挑战性的学生和同事,因此,我 总是小心翼翼地论证,时而还会从书稿中返回现实。 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学生的帮助。他们帮助我收集、筛选、 核查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他们分别对这一研究项目的不同部分提供了 宝贵的帮助,有的延续数年。我要感谢康奈尔大学这些优秀、勒奋、充满 活力的学生,他们是:布赖恩·饱(Brian Bow)、雷切尔·格伯(Rachel Gerber),理查德·赫奇(Richard Hedge),雷科·黄(Reyko Huang)、安杰 拉·金(Angela Kim)、乌尔里克·克罗兹(Ulrich Krotz)、丹尼尔·莱文 (Daniel Levin),凯文·斯特罗姆普弗(Kevin Strompf)。另外,还有拉塞 尔·塞奇基金会的贝基·维里奥(Becky Verreau)。 我还应邀到美国、亚洲和欧洲做过许多讲座,阐释本研究项目的不 同章节。限于篇幅,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这些讲座。但我仍然希望说 明,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听众的批评和建议对于启发我的思维是多么重 要。在不同的听众面前、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自己仍不成熟的思想,对我 更加清楚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是不可或缺的。我要感谢所有邀请我讲课 的人们,所有参与听讲和讨论的人门,感谢他们使我的思维逐步清晰 起来。 我要特别感谢一批博士生和同仁,他们花费时间,专门召集会议,讨 论本书的成稿,包括在柏林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5月).康奈尔大学政 府系(2003年9月)、达特茅斯学院(2004年1月)、多伦多大学芒克中心 (2004年2月)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4年3月)等学府召开的会 议。在美国和美国之外的地方寻求学术探索的机会使我意识到,单从美 国视角思考世界是会产生偏颇的。这些讨论有的是半天,有的长达两整 天。讨论证实了我的预期: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反响。比如, 我原书稿中有一章的开头称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 在达特茅斯和康奈尔举行的讨论会上,人们对此并无异议。但是,在柏 林、多伦多和堪培拉,参会者却坚持认为我应该对这个句子做出一点改 动,即把“最核心的角色”改为“核心角色之一”。改动虽小,寓意深长。 这是一个十分说明问题的例子,表现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学者的学术研究 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在智识敏感和政治直觉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同 样重要的是,他们帮助我确定了本书核心论点的最终表达方式。 专家针对书中不同章节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这也使我受益匪浅。这 些专家包括:彼特·安德烈亚斯(Peter Andreas))、乔瓦尼·阿里吉(G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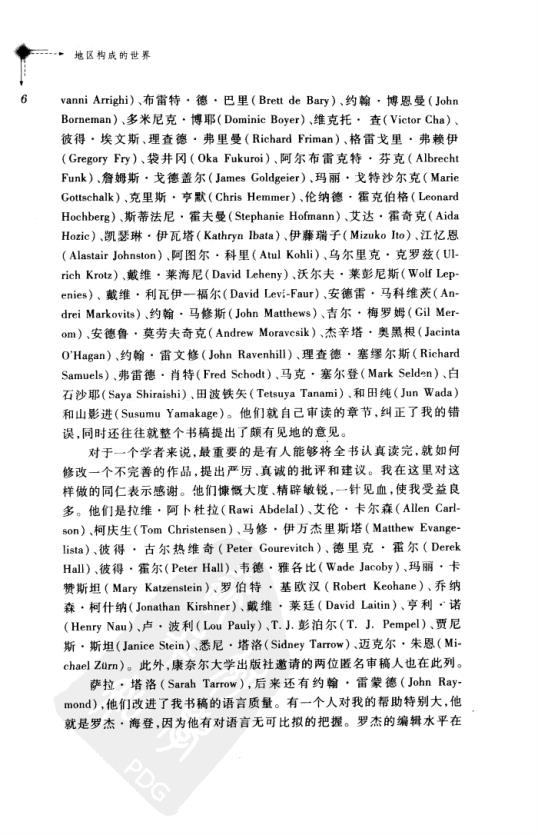
地区构成的世界 vanni Arrighi)、布雷特·德·巴里(Brett de Bary)、约翰·博恩曼(John Borneman)、多米尼克·博耶(Dominic Boyer),维克托·查(Victor Cha)、 彼得·埃文斯、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iman)、格雷戈里·弗赖伊 (Gregory Fry)、袋井冈(Oka Fukuroi)、阿尔布雷克特·芬克(Albrecht Funk),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玛丽·戈特沙尔克(Marie Gottschalk),克里斯·亨默(Chris Hemmer),f伦纳德·霍克伯格(Leonard Hochberg)、斯蒂法尼·霍夫曼(Stephanie Hofmann)、艾达·霜奇克(Aida Hozie),凯瑟琳·伊瓦塔(Kathryn Ibata)、伊臻瑞子(Mizuko Ito)、江忆恩 (Alastair Johnston)、阿图尔·科里(Atul Kohli),乌尔里克·克罗兹(Ul rich Krotz),戴维·莱海尼(David Leheny)、沃尔夫·莱彭尼斯(Wolf Lep enies)、戴维·利瓦伊一福尔(David Levi-Faur),安德雷·马科维茨(An- drei Markovits)、约翰·马絛斯(John Matthews)、吉尔·梅罗姆(Gil Mer- om),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esik)、杰辛塔·奥黑根(Jacinta O'Hagan)、约翰·雷文修(John Ravenhill)、理查德·塞摆尔斯(Richard Samuels)、弗雷德·肖特(Fred Schodt),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白 石沙耶(Saya Shiraishi),田波铁矢(Tetsuya Tanami)、和田纯(Jun Wada) 和山影进(Susumu Yamakage)。他们就自己审读的章节,纠正了我的错 误,同时还往往就整个书稿提出了颠有见地的意见。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人能够将全书认真读完,就如何 修改一个不完善的作品,提出严厉,真诚的批评和建议。我在这里对这 样做的同仁表示感谢。他们慷概大度,精辟敏锐,一针见血,使我受益良 多。他们是拉维·阿卜杜拉(Rawi Abdelal)、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 son)、柯庆生(Tom Christensen)、马修·伊万杰里斯塔(Matthew Evange- lista)、彼得·古尔热维奇(Peter Gourevitch),德里克·霍尔(Derek Hall)、彼得·霜尔(Peter Hall)、韦德·雅各比(Wade Jacoby),玛丽·卡 赞斯坦(Mary Katzenstei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乔纳 森·柯什纳(Jonathan Kirshner)、戴维·莱廷(David Laitin),亨利·诺 (Henry Nau)、卢·波利(Lou Pauly)、T.J.彭泊尔(T.J.Pempel)、贾尼 斯·斯坦(Janice Stein)、悉尼·塔洛(Sidney Tarrow)、迈克尔·朱恩(Mi- chael Zurn)。此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邀请的两位置名审稿人也在此列。 萨拉·塔洛(Sarah Tarrow),后来还有约翰·雷蒙德(John Ray- mod),他们改进了我书稿的语言质量。有一个人对我的帮助特别大,他 就是罗杰·海登,因为他有对语言无可比拟的把握。罗杰的编辑水平在

序 学术图子里有口皆碑。他认真编辑了此书,我对此深怀感激。 我将此书献给玛丽(Mary),泰(Tai)和苏珊螺(Suzanne)一一我生活 中至高无上的三位一体。 彼得·卡赞斯坦 纽约伊萨卡 君A别 ④驱多 P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