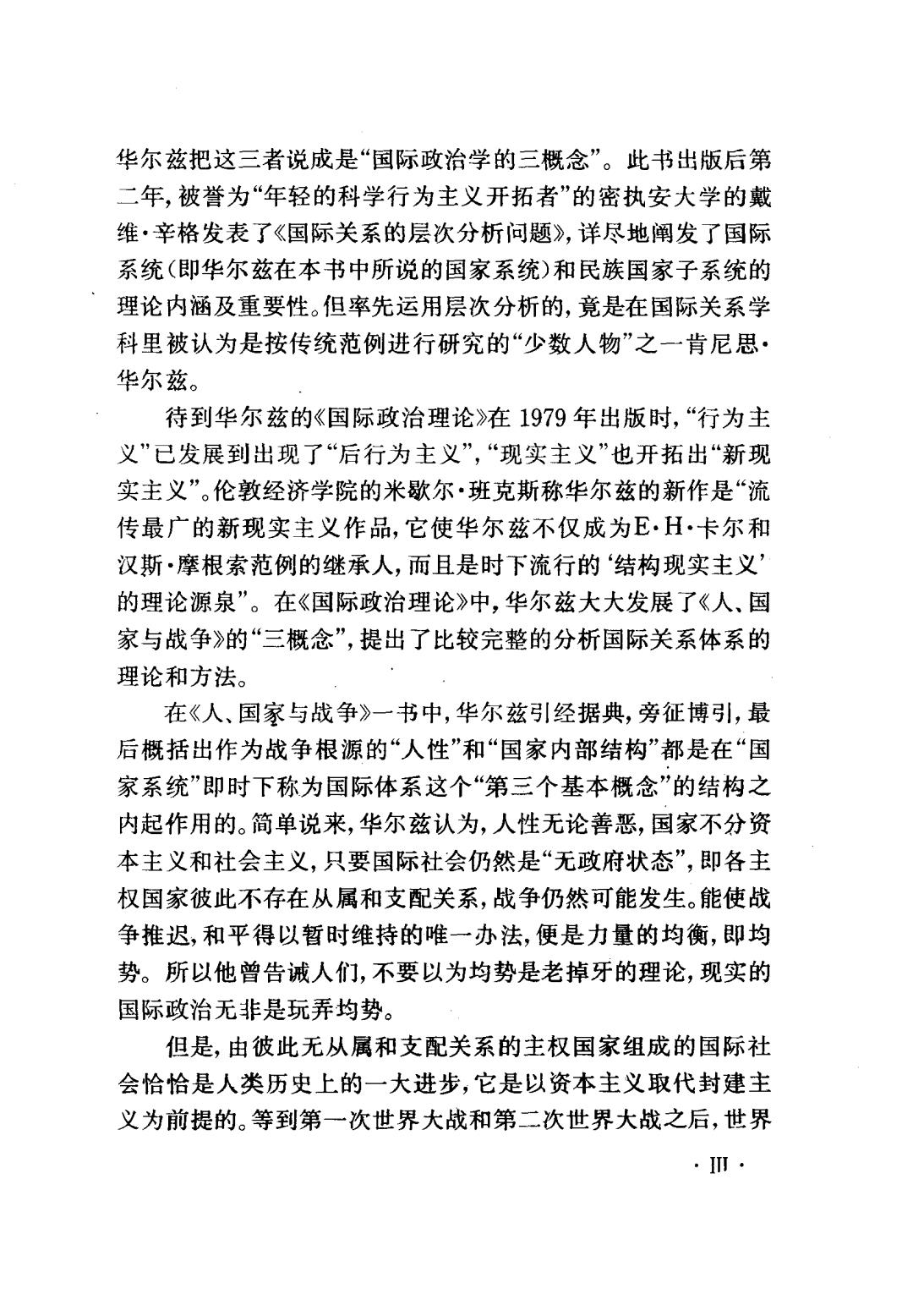
华尔兹把这三者说成是“国际政治学的三概念”。此书出版后第 二年,被誉为“年轻的科学行为主义开拓者”的密执安大学的戴 维·辛格发表了《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问题》,详尽地阐发了国际 系统(即华尔兹在本书中所说的国家系统)和民族国家子系统的 理论内涵及重要性。但率先运用层次分析的,竟是在国际关系学 科里被认为是按传统范例进行研究的“少数人物”之一肯尼思· 华尔兹。 待到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在1979年出版时,“行为主 义”已发展到出现了“后行为主义”,“现实主义”也开拓出“新现 实主义”。伦敦经济学院的米歇尔·班克斯称华尔兹的新作是“流 传最广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它使华尔兹不仅成为E·H·卡尔和 汉斯·摩根索范例的继承人,而且是时下流行的‘结构现实主义’ 的理论源泉”。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华尔兹大大发展了《人、国 家与战争》的“三概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分析国际关系体系的 理论和方法。 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华尔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 后概括出作为战争根源的“人性”和“国家内部结构”都是在“国 家系统”即时下称为国际体系这个“第三个基本概念”的结构之 内起作用的。简单说来,华尔兹认为,人性无论善恶,国家不分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要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即各主 权国家彼此不存在从属和支配关系,战争仍然可能发生。能使战 争推迟,和平得以暂时维持的唯一办法,便是力量的均衡,即均 势。所以他曾告诫人们,不要以为均势是老掉牙的理论,现实的 国际政治无非是玩弄均势。 但是,由彼此无从属和支配关系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 会恰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是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 义为前提的。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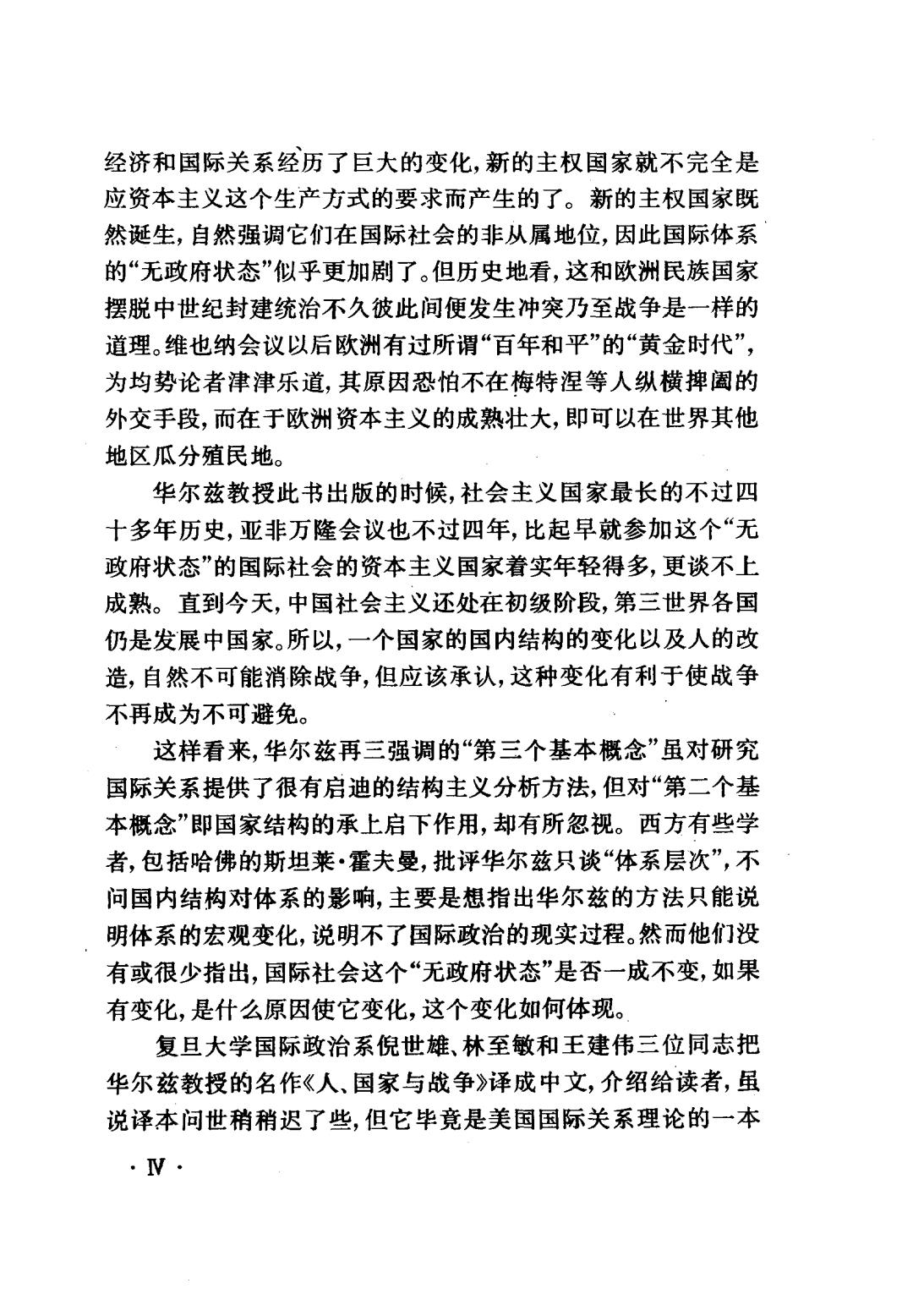
经济和国际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新的主权国家就不完全是 应资本主义这个生产方式的要求而产生的了。新的主权国家既 然诞生,自然强调它们在国际社会的非从属地位,因此国际体系 的“无政府状态”似乎更加剧了。但历史地看,这和欧洲民族国家 摆脱中世纪封建统治不久彼此间便发生冲突乃至战争是一样的 道理。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有过所谓“百年和平”的“黄金时代”, 为均势论者津津乐道,其原因恐怕不在梅特涅等人纵横捭阖的 外交手段,而在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熟壮大,即可以在世界其他 地区瓜分殖民地。 华尔兹教授此书出版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最长的不过四 十多年历史,亚非万隆会议也不过四年,比起早就参加这个“无 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着实年轻得多,更谈不上 成熟。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第三世界各国 仍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一个国家的国内结构的变化以及人的改 造,自然不可能消除战争,但应该承认,这种变化有利于使战争 不再成为不可避免。 这样看来,华尔兹再三强调的“第三个基本概念”虽对研究 国际关系提供了很有启迪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但对“第二个基 本概念”即国家结构的承上启下作用,却有所忽视。西方有些学 者,包括哈佛的斯坦莱·霍夫曼,批评华尔兹只谈“体系层次”,不 问国内结构对体系的影响,主要是想指出华尔兹的方法只能说 明体系的宏观变化,说明不了国际政治的现实过程。然而他们没 有或很少指出,国际社会这个“无政府状态”是否一成不变,如果 有变化,是什么原因使它变化,这个变化如何体现。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倪世雄、林至敏和王建伟三位同志把 华尔兹教授的名作《人、国家与战争》译成中文,介绍给读者,虽 说译本问世稍稍迟了些,但它毕竟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本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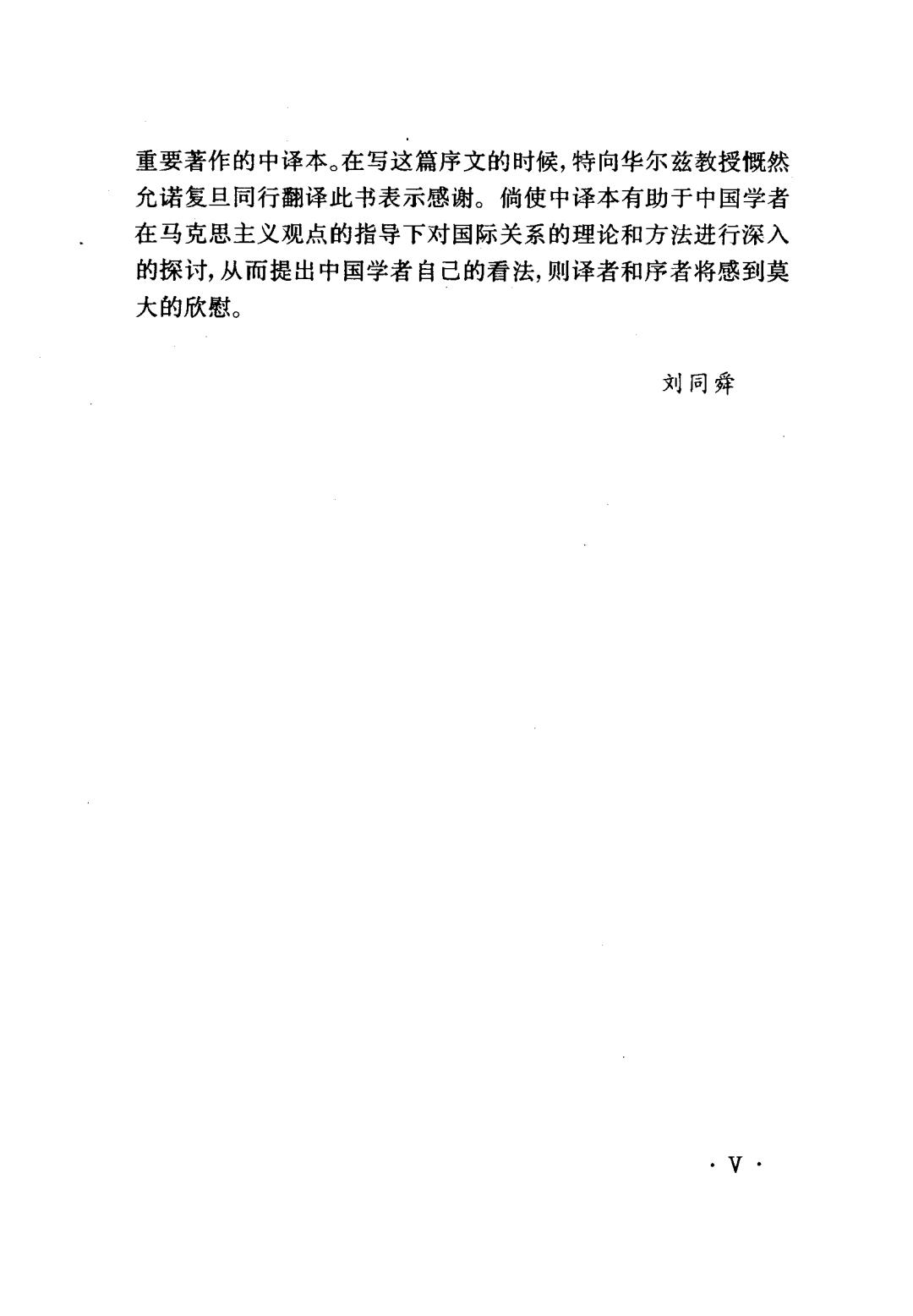
重要著作的中译本。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特向华尔兹教授慨然 允诺复旦同行翻译此书表示感谢。倘使中译本有助于中国学者 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指导下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 的探讨,从而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看法,则译者和序者将感到莫 大的欣慰。 刘同舜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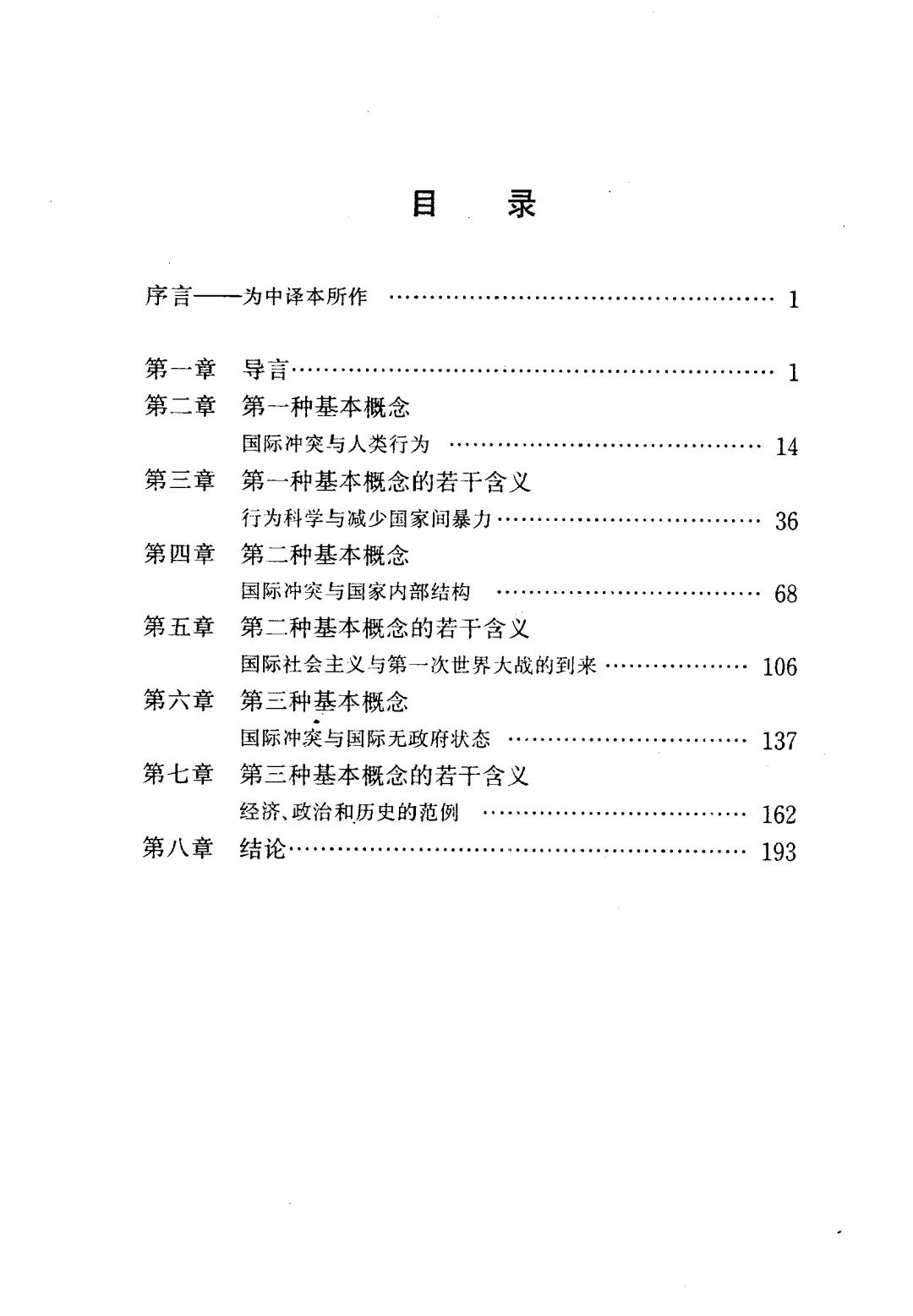
录 目 序言——为中译本所作 第一章导言… 1 第二章第一种基本概念 国际冲突与人类行为 14 第三章第一种基本概念的若干含义 行为科学与减少国家间暴力… 36 第四章第二种基本概念 国际冲突与国家内部结构 68 第五章第二种基本概念的若干含义 国际社会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106 第六章 第三种基本概念 国际冲突与国际无政府状态 137 第七章第三种基本概念的若干含义 经济、政治和历史的范例 162 第八章结论… 193

第一章导言 有人曾说,要问谁赢得了某场战争等于问谁战胜了旧金山 地震。在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战争中没 有胜利可言,只有程度不同的失败。但战争是否也像地震那样, 成了人类智力所无法控制、无法消除的自然现象呢?很少有人 会这样认为。然而,不管人们怀着多么崇高的愿望,以及不管怎 样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消除战争,换来的只不过是国家之间短暂 的和平。努力与收获、愿望与结果之间的不相称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听说,俄国人民怀有强烈深切的和平愿望:我们相信美国人 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从这些说法中得到某种宽慰。但从历史和 现状来看,很难相信愿望能够创造所企求的条件。 社会科学家们从他们的研究中认识到,现在和过去是紧紧 相联的;一个体系的各个部分是密切地相互依赖的。因此,在估 计建立一个完全美好的世界的可能性时,他们持谨慎态度。如果 有人问现在能否在曾是战火连天之地实现和平,回答多半是悲 观的。也许这个问题问错了。实际上,如果人们提出的是以下问 题,那末,回答就不至于那样令人祖丧了:有没有减少战事、增加 和平机会的途径?我们能否在将来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和平? 和平是人们同时追求的众多目标之一。寻求和平的途径很 多。人们是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追求目的和使用方法的。纵然 人们很难相信还存在着政治家所没有尝试过或国际法专家所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