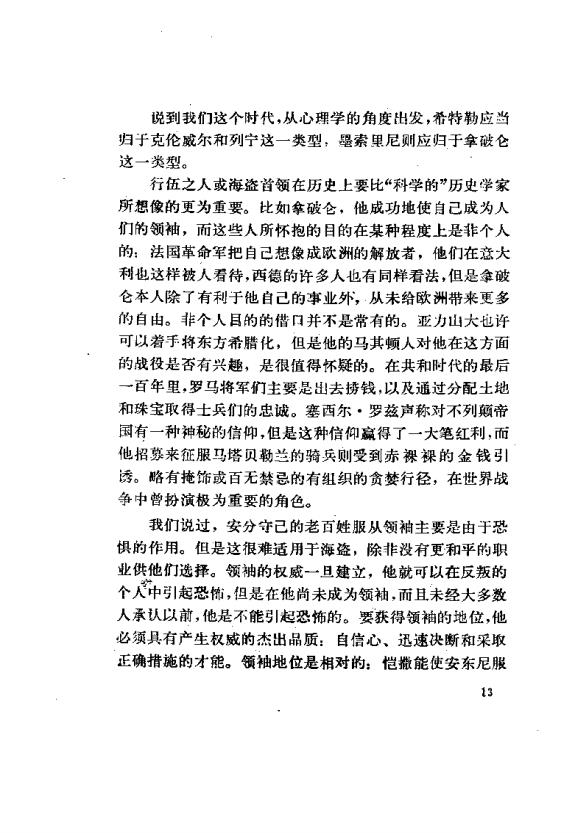
说到我们这个时代,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希特勒应当 归于克伦威尔和列宁这一类型,壁索里尼则应归于拿破仑 这一类型。 行伍之人或海盗首领在历史上要比“科学的”历史学家 所想像的更为重要。比如拿破仑,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人 们的领袖,而这些人所怀抱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个人 的:法国革命军把自己想像成欧洲的解放者,他们在意大 利也这样被人看待,西德的许多人也有同样看法,但是金破 仑本人除了有利于他自己的事业外,·从未给欧洲带来更多 的自由。非个人目的的楷口并不是常有的。亚力山大也许 可以着手将东方希腊化,但是他的马其顿人对他在这方面 的战役是否有兴趣,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共和时代的最后 一百年里,罗马将军们主要是出去捞钱,以及通过分配土地 和珠宝取得士兵们的忠诚。塞西尔·罗兹声称对不列颠帝 国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但是这种信仰赢得了一大笔红利,而 他招墓来征服马塔贝勒兰的骑兵则受到赤裸裸的金钱引 诱。略有掩饰或百无禁忌的有组织的贪婪行径,在世界战 争中曾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我们说过,安分守已的老百姓服从领袖主要是由于恐 惧的作用。但是这很难适用于海盗,除非没有更和平的职 业供他们选择。领袖的权威一旦建立,他就可以在反叛的 个人中引起恐惭,担是在他尚未成为领袖,而且未经大多数 人承认以前,他是不能引起恐怖的。要获得领袖的地位,他 必须具有产生权威的杰出品质:自信心、迅速决断和采取 正确措施的才能。领袖地位是相对的:恺撒能使安东尼服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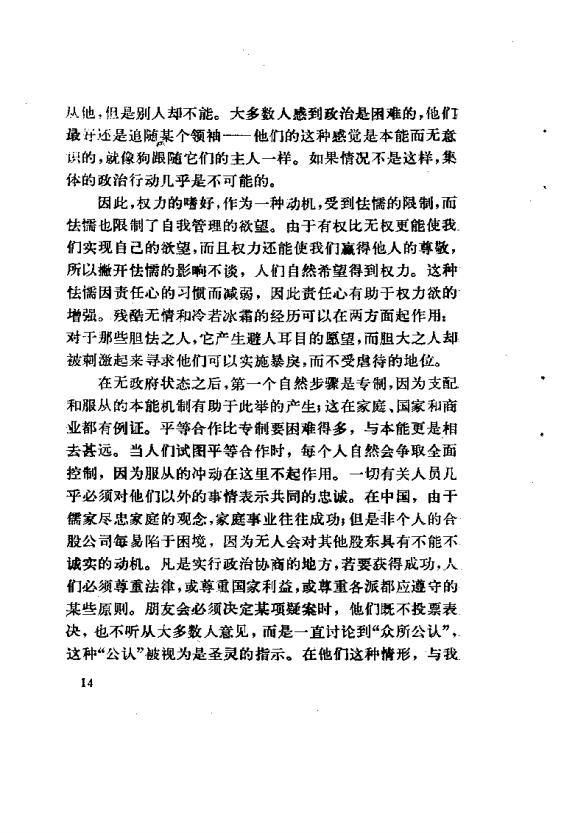
从他,组是别人却不能。大多数人感到政治是困难的,他工 最好还是追随某个领袖一一他们的这种盛觉是本能面无意 识的,就像狗跟随它们的主人一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集 体的政治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权力的嗜好,作为一种动机,受到怯懦的限制,而 法播也限制了自我管理的欲望。由于有权比无权更能使我 们实现自己的欲望,而且权力还能使我们赢得他人的尊数, 所以撇开怯懦的影响不谈,人们自然希望得到权力。这种 怯需因责任心的习惯而减弱,因此责任心有助于权力欲的 增强。残酷无情和冷若冰霜的经历可以在两方面起作用: 对于那些胆法之人,它产生避人耳目的照望,而胆大之人却 被刺做起来寻求他们可以实施暴戾,而不受虐待的地位。 在无政府伏态之后,第一个自然步骤是专制,因为支配 和服从的本能机制有助于此举的产生;这在家庭、国家和商 业都有例证。平等合作比专制要困难得多,与本能更是相 去甚远。当人们试图平等合作时,每个人自然会争取全面 控制,因为服从的冲动在这里不起作用。一切有关人员几 乎必须对他们以外的事情表示共同的忠诚。在中国,由于 儒家尽忠家庭的观念,家庭事业往往成功;但是非个人的合 股公司每易陷于困境,因为无人会对其他股东具有不能不 诚实的动机。凡是实行政治协商的地方,若要获得成功,人 们必须尊重法律,或尊重国家利益,或尊重各派都应遵守的 某些原则。朋友会必须决定某项疑案时,他们既不投票表 决,也不听从大多数人意见,而是一直讨论到“众所公认”, 这种“公认”被视为是圣灵的指示。在他们这种情形,与我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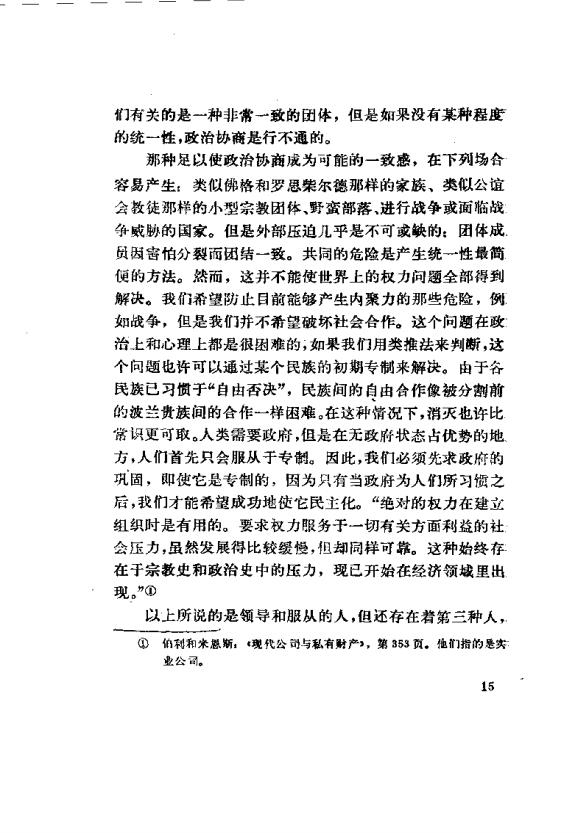
们有关的是一种非常一致的团体,但是如果没有某种程度 的统一性,政治协商是行不通的。 那种足以使政治协商成为可能的一致感,在下列场合 容易产生:类似佛格和罗总柴尔德那样的家族、类似公谊 会教徒那样的小型宗教团体、野蛮部落、进行战争或面临战 年威胁的国家。但是外部压迫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团体成 员因密怕分裂而团结一致。共同的危险是产生统一性最简 恒的方法。然而,这并不能使世界上的权力问题全部得到 解决。我们希望防止目前能够产生内聚力的那些危险,例 如战争,但是我们并不希望破坏社会合作。这个问题在政 治上和心理上都是很困雄的,如果我们用类推法来判断,这 个问题也许可以通过某个民族的初期专制来解快。由于谷 民族已习惯于“自由否决”,民族间的自由合作像被分割前 的波兰贵族间的合作一样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消灭也许比 常识更可取。人类需要政府,但是在无政府状态占优势的地 方,人们首先只会服从于专制。因此,我们必须先求政府的 巩固,即使它是专制的,因为只有当政府为人们所习领之 后,我们才能希望成功地使它民主化。“绝对的权力在建立 组织时是有用的。要求权力服务于一切有关方面利益的社 会压力,虽然发展得比较缓模,但却同样可靠。这种始终存 在于宗数史和政治史中的压力,现已开始在经济领域里出 现。”① 以上所说的是领导和服从的人,但还存在着第三种人, ④伯利和米新:现代公司与私有尉产,第353页。他们指的是实 业公面。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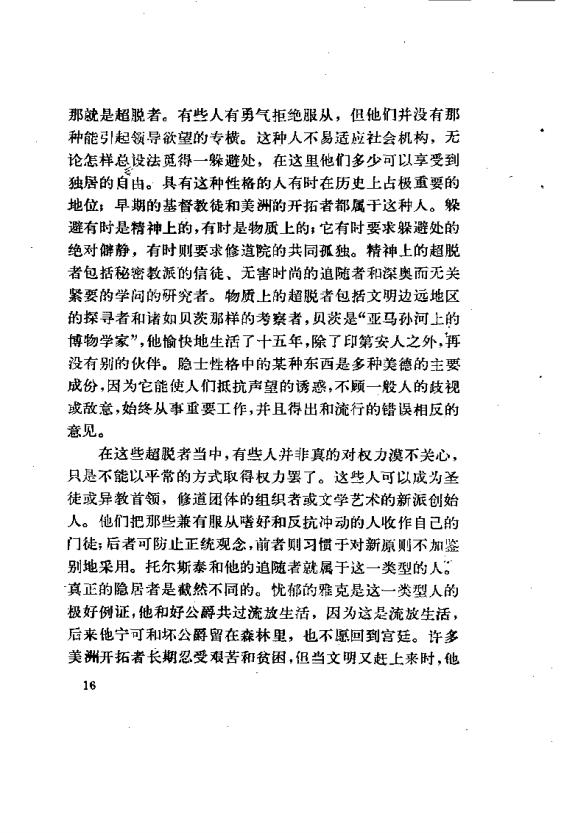
那就是超脱者。有些人有勇气拒绝服从,但他们并没有那 种能引起领导欲望的专横。这种人不易适应社会机构,无 论怎样总设法觅得一躲避处,在这里他们多少可以享受到 独居的自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有时在历史上占极重要的 地位:早期的基督教徒和美洲的开拓者都属于这种人。躲 避有时是精神上的,有时是物质上的:它有时要求躲避处的 绝对僻静,有时则要求修道院的共同孤独。精神上的超脱 者包括秘密教蕨的信徒、无害时尚的追随者和葆奥而无关 紧要的学问的研究者。物质上的超脱者包括文明边远地区 的探寻者和诸如贝茨那样的考察者,贝茨是“亚马孙河上的 博物学家”,他愉快地生括了十五年,除了印第安人之外,弭 没有别的伙伴。隐士性格中的某种东西是多种美德的主要 成份,因为它能使人们抵抗声望的诱惑,不顾一般人的歧视 或敌意,始终从事重要工作,并且得出和流行的错误相反的 意见。 在这些超脱者当中,有些人并非真的对权力漠不关心, 只是不能以平常的方式取得权力罢了。这些人可以成为圣 徒或异教首领,修道团体的组织者或文学艺术的新派创始 人。他们把那些兼有眼从嗜好和反抗冲动的人收作自己的 门徒:后者可防止正统观念,前者则习惯于对新原则不加鉴 别地采用。托尔斯泰和他的追随者就属于这一类型的人。 真正的隐居者是截然不同的。忧郁的雅克是这一类型人的 极好例证,他和好公爵共过流放生活,因为这是流放生活, 后来他宁可和坏公爵留在森林里,也不愿回到宫廷。许多 美洲开拓者长期忍受艰苦和贫困,但当文明又赶上来时,他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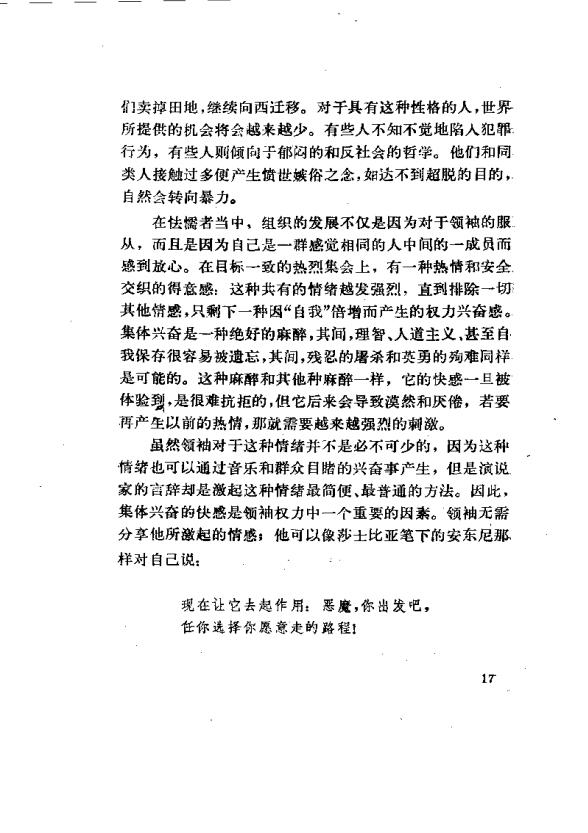
]卖掉田地,继续向西迁移。对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世界 所提供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有些人不知不觉地陷人犯罪 行为,有些人则倾向于郁闷的和反社会的哲学。他们和同 类人接触过多便产生愤世嫉俗之念,如达不到超脱的目的, 自然会转向暴力。 在怯橘者当中,组织的发展不仪是因为对于领袖的服 从,而且是因为自己是一群感觉相同的人中间的一成员而 惑到放心。在目标一致的热烈集会上,有一种热情和安全 交织的得意感:这种共有的情绪越发强烈,直到排除一切 其他错惑,只剩下一种因“自我”倍增而产生的权力兴奋感。 集体兴奋是一种绝好的麻醉,其间,理智、人道主义,甚至自 我保存很容易被遗忘,其间,残忍的屠杀和英勇的狗难同样 是可能的。这种麻醉和其他种麻醉一样,它的快惑一且被 体验到,是很难抗拒的,但它后来会导致漠然和厌倦,若要 再产生以前的热情,那就希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澈。 虽然领袖对于这种情绪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种 情绪也可以通过音乐和群众目睹的兴奋事产生,但是汶说 家的言辞却是激起这种情绪最简便、最普通的方法。因此, 集体兴奋的快感是领袖权力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领袖无需 分享他所激起的情感;他可以像都士比亚笔下的安东尼那 样对自己说: 现在让它去起作用:恶魔,你出发吧, 任你选择你愿意走的路程!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