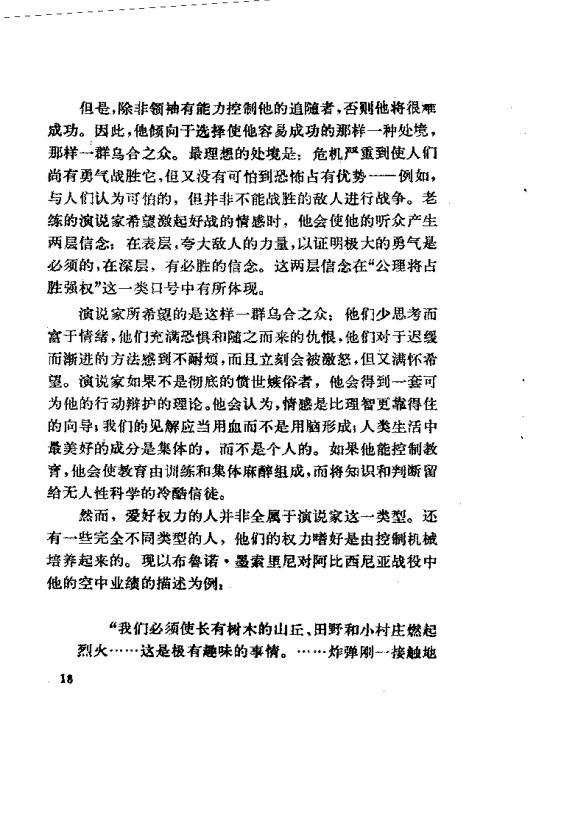
但是,除非领轴有能力控制他的追随者,否则他将很 成功。因此,他倾向于选择使他容易成功的那样一种处境, 那样一群乌合之众。最理想的处境是:危机严垂到使人们 尚有勇气战胜它,但又设有可怕到恐怖占有优势一例如, 与人们认为可怕的,但并非不能战胜的敌人进行战争。老 练的演说家希最激起好战的情感时,他会使他的听众产生 两层信念:在表层,夸大敌人的力量,以证明极大的勇气是 必须的,在深层,有必胜的信念。这两层信念在“公理将占 胜强权”这一类口号中有所体现。 演说家所希望的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少思考而 言于情籍,他们充满恐惧和随之而来的仇根,他们对于迟缓 而渐进的方法到不耐烦,而且立刻会被激怒,但艾满怀希 望。演说家如果不是彻底的愤世嫉俗者,他会得到一套可 为他的行动辩护的理论。他会认为,情遮是比强智更靠得住 的向导,我们的见解应当用血而不是用脑形成:人类生活中 最美好的成分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如果他能控制教 疗,他会使教育由调练和集体麻醉组成,而将知识和判断留 给无人性科学的冷卧信徒。 然而,爱好权力的人并非全属于演说家这一类型。还 有一些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们的权力嗜好是由控制机械 培养起来的。现以布魯诺·墨素里尼对阿比西尼亚战役中 他的空中业绩的描述为例: “我们必须使长有树木的山丘,田野和小村庄燃起 烈火…这是极有趣味的事情。……炸弹刚-一接触地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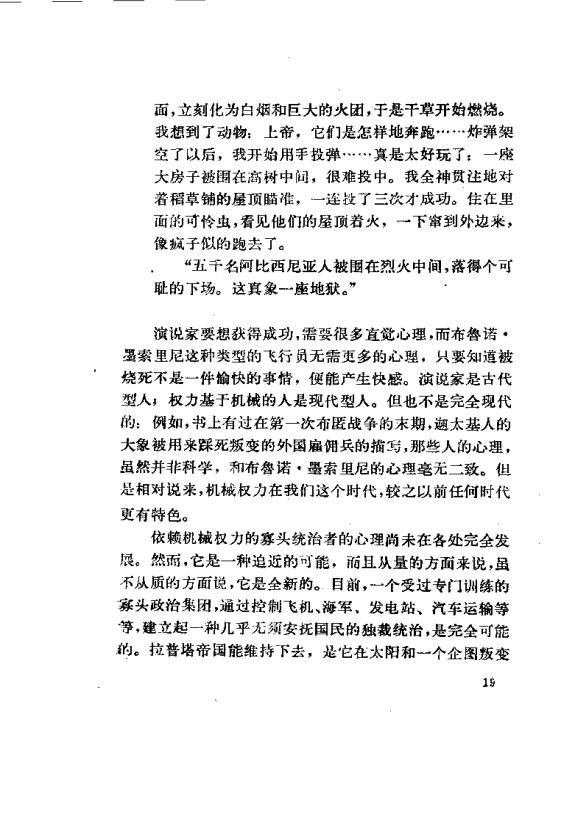
面,立刻化为白烟和巨大的火团,于是千草开始燃烧。 我想到了动物:上帝,它们是怎样地奔跑…炸弹架 空了以后,我开始用手投弹…真是太好玩了:一座 大房子被围在高树中间,很雅投中。我全神贯注地对 若稻草铺的屋顶瞄准,一连投了三次才成功。住在里 面的可怜虫,看见他们的屋顶着火,一下窜到外边来, 像抗子似的跑去了。 “五千名阿比西尼亚人被围在烈火中间,落得个可 耻的下场。这真象-一座地狱。” 演说家要想获得成功,需要很多直觉心理,而布魯诺· 墨絷里尼这种类型的飞行员无需更多的心理,只要知道被 烧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便能产生快感。演说家是古代 型人,权力基于机械的人是现代型人。但也不是完全现代 的:例如,书上有过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末期,趣太基人的 大象被用来踩死叛变的外国扁佣兵的指写,那些人的心理, 虽然并非科学,和布魯诺·墨索里尼的心理毫无二致。但 是相对说来,机械权力在我们这个时代,较之以前任何时代 更有特色。 依赖机械权力的寡头统治者的心理尚未在各处完全发 展。然而,它是一种迫近的可能,而且从量的方面来说,虽 不从质的方面说,它是全新的。目前,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 寡头政治集团,通过控制飞机、海军、发电站、汽车运输等 等,建立起一种几平无须安抚国民的独裁统治,是完全可能 的。拉普塔帝国能维持下去,是它在太阳和一个企图叛变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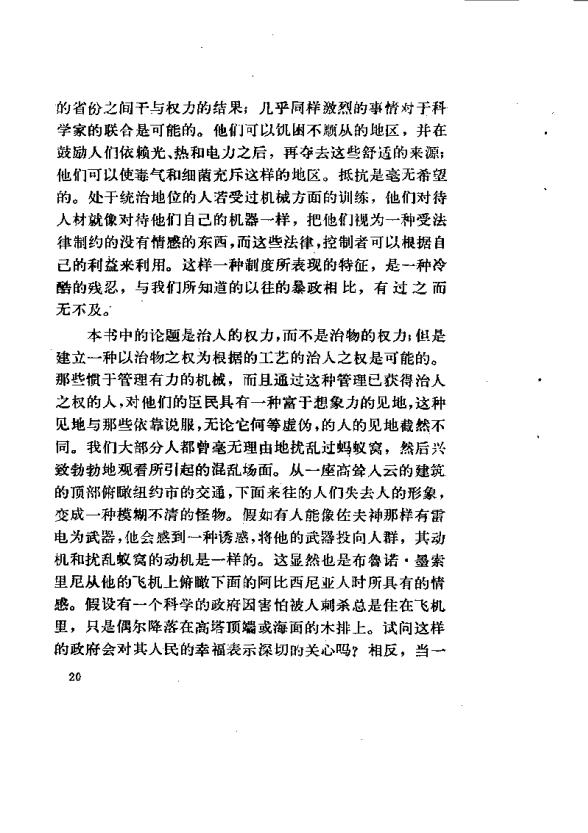
的省份之间千与权力的结果:几乎同样激烈的事撞对于科 学家的联合是可能的。他们可以机因不颛从的地区,并在 鼓励人们依赖光、热和电力之后,再夺去这些舒适的来源: 他们可以使毒气和细菌充斥这样的地区。抵抗是毫无希望 的。处于统治地位的人若受过机械方面的训练,他们对待 人材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机器一样,把他套]视为一种受法 律制约的没有情感的东西,而这些法律,控制者可以根据自 己的利益来利用。这样一种制度所表现的特征,是一种冷 酷的残忍,与我们所知道的以往的暴政相比,有过之而 无不及。 本书中的论题是治人的权力,而不是治物的权力:但是 建立一种以治物之权为根据的工艺的治人之权是可能的。 那些惯于管理有力的机诚,而且通过这种管理已类得治人 之权的人,对他们的臣民具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见地,这种 见地与那些依靠说服,无论它何等虚伪,的人的见地截然不 同。我们大部分人都曾毫无理由地扰乱过蚂蚁窝,然后兴 致勃勃地观看所引起的混乱场面。从一座高耸人云的建筑 的顶部俯瞰纽约市的交通,下面来往的人们失去人的形象, 变成一种模糊不清的怪物。假如有人能像佐夫神那样有雷 电为武器,他会感到一种诱盛,将他的武器投向人群,其动 机和扰乱蚁窝的动机是一样的。这显然也是布魯诺·盈索 里尼从他的飞机上俯瞰下面的阿比西尼亚人时所具有的情 惑。假设有一个科学的政府因害怕被人刺杀总是住在飞机 里,只是偶尔降落在高塔顶端或海面的木排上。试问这样 的政府会对其人民的幸福表示深切的关心吗?相反,当一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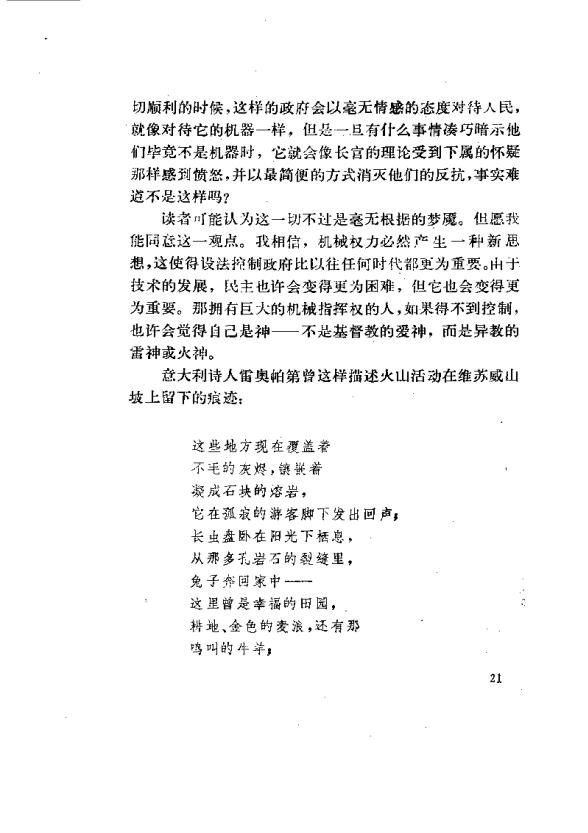
切颛利的时候,这样的政府会以毫无情盛的态度对待人民, 就像对待它的机器一样,但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凑巧暗示他 们毕竞不是机器时,它就会像长宫的理论受到下属的怀疑 那样感到愤怒,并以最简便的方式消灭他们的反抗,事实难 道不是这样吗? 读者可能认为这一切不过是毫无根据的梦魔。但愿我 能同途这一观点。我相信,机械权力必然产生一种新思 想,这使得设法控制政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出于 技术的发展,民主也许会变得更为困难,但它也会变得更 为重要。那拥有巨大的机械指挥权的人,知果得不到控制, 也许会觉得自己是神一不是基督教的爱神,而是异教的 雷神或火神。 慈大利诗人笛奥帕第曾这样描述火山活动在维苏威山 坡上留下的狼迹: 这些地方现在覆盖老 不毛的灰烬,镶献着 凝成石块的熔岩, 它在孤寂的游客脚下发出回声, 长虫盘卧在阳光下栖息, 从那多岩石的烈缝里, 免子舟回家中一 这里曾是幸福的田园, 耕地、金色的麦浪,还有那 鸣叫的件并,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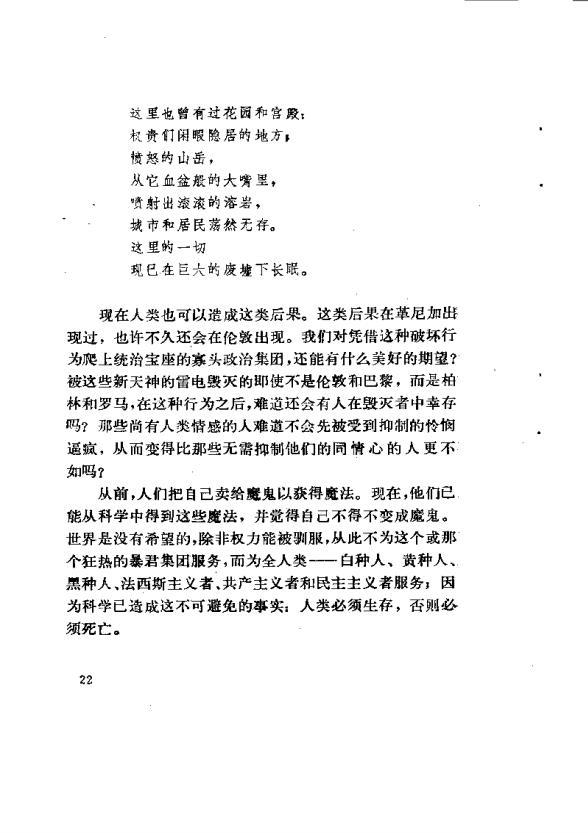
这里也曾有过花园和宫段: 权资们闲暇隐居的地方, 棱怒的山岳, 从它血盆般的大嘴里, 喷射出滚滚的溶岩, 城市和居民茜然无存。 这里的一切 现巳在巨大的废墟下长眠。 现在人类也可以造成这类后果。这类后果在革尼加出 现过,也许不久还会在伦敦出现。我们对凭借这种破坏行 为爬上统治宝座的寡头改治巢团,还能有什么美好的期望? 被这些新天神的雷电毁灭的即使不是伦教和巴黎,而是柏 林和罗马,在这种行为之后,难道还会有人在毁灭者中幸存 吗?那些尚有人类情盛的人难道不会先被受到抑制的怜悯 逼疯,从而变得比那些无稽抑制他们的同情心的人更不 如吗? 从前,人们把自己卖给魔鬼以获得魔法。现在,他们已 能从科学中得到这些魔法,并觉得自己不得不变成魔鬼。 世界是没有希望的,除非权力能被别服,从此不为这个或那 个狂热的暴君集团服务,而为全人类一一白种人、黄种人、 黑种人、法西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服务,因 为科学已造成这不可避免的事实:人类必须生存,否则必 须死亡。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