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外,新的政治经济学与系统分析方法亦非冰雪火炭。后者明确 提供了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面且还进一步认为、人们不 仅应该虑及经济系统,而且应该计及其他重要的社会系统。换言之, 如果我不揣冒味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过分专注于研究任何单独的一 系列社会变量一比如经济变量,其所得到的看法并不如系统分析所 具有的眼光周全成熟。系统分析并不臆断政治系统的环境中有什久 单独的系统(如经济系统)是具有首要的支配性,还是如同一些人所认 为的那样,具有最终的决定性。系统分析认为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一种 正确的眼光和衡度方法,椎有一般理论方法才会有承认这一点的逻辑 动机。由此使我们想到,比如,卓先我们曾锻造了联系心理学和人类 学的链条,其结果,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称谓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 学等边缘学科。而且系统分析在其概念化的过程中,备下了与其他社 会的、生物的及生态的系统的联系纽带,生物政治学即是一例。有些 东西流行一时,而且也未必有什么错误缺失之处,壁如政治经济学即 是如此。可是,我们不应认为这些东西就是确定科学总体发展中什么 是最终唯一必要的标尺。 进而言之,在八十年代,人们以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名义,如此强烈 地吁求“使国家回到”政治分析中来①而对于系统分析来说,这种吁 求几平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系统分析概念化伊始,所谓“国家”便担任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鉴于系统整局设计的着眼点,国家未曾成 为这样一种中心范畴,而是被分成了其几个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即是 “政治当局”。举凡熟谙系统分析的人都知道“政治当局”这一概念是 ①见P.B.埃文斯(P.B.Evans)、D.鲁谢迈耶(D.Rueschemeyer)及T,斯科遮波 (T.Sk0cpol)所著《使国家回门)-·B,尤见第一章,纽约坎布里奇人学出版社,··九 八年版。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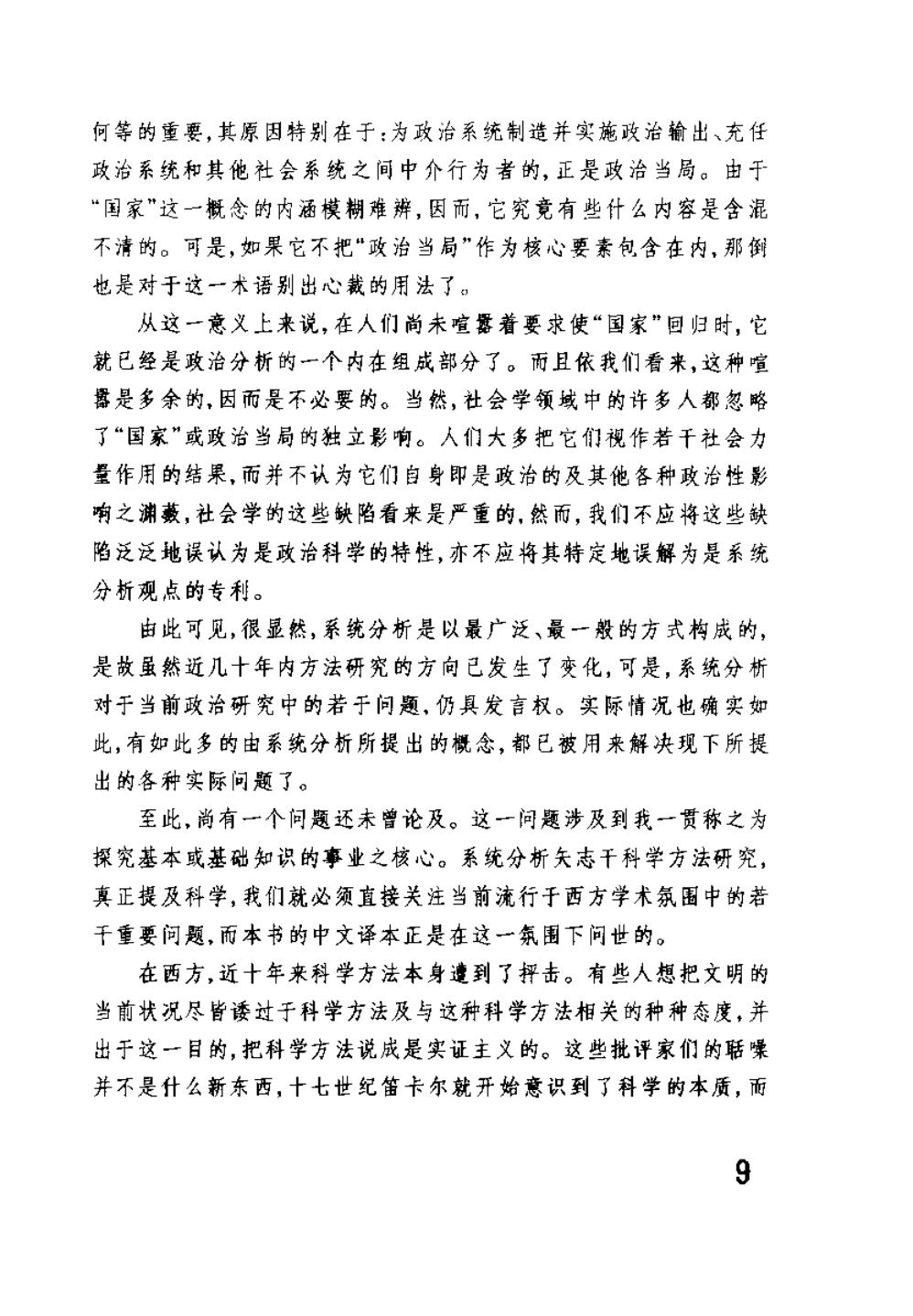
何等的重要,其原因特别在于:为政治系统制造并实施政治输出、充任 政治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中介行为者的,正是政治当局。由于 “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模糊难辨,因而,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是含混 不清的。可是,如果它不把“政治当局”作为核心要素包含在内,那倒 也是对于这一术语别出心裁的用法了。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人们尚未喧露着要求使“国家”回归时,它 就已经是政治分析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了。而且依我们看来,这种喧 露是多余的,因而是不必要的。当然,社会学领域中的许多人都忽略 了“国家”或政治当局的独立影响。人们大多把它们视作若干社会力 量作用的结果,而并不认为它们自身即是政治的及其他各种政治性影 南之渊薮,社会学的这些缺陷看来是严重的,然而,我们不应将这些缺 陷泛泛地误认为是政治科学的特性,亦不应将其特定地误解为是系统 分析观点的专利。 由此可见,很显然,系统分析是以最广泛、最一般的方式构成的, 是故虽然近儿十年内方法研究的方向已发生了变化,可是,系统分析 对于当前政治研究中的若于问题,仍具发言权。实际情况也确实如 此,有如此多的由系统分析所提出的概念,都已被用来解决现下所提 出的各种实际问题了。 至此,尚有一个问题还未曾论及。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一贯称之为 探究基本或基础知识的事业之核心。系统分析矢志干科学方法研究, 真正提及科学,我们就必须直接关注当前流行于西方学术氛围中的若 干重要问题,而本书的中文译本正是在这一氛围下问世的。 在西方,近十年来科学方法本身遭到了抨击。有些人想把文明的 当前状况尽皆诿过于科学方法及与这种科学方法相关的种种态度,并 出于这一目的,把科学方法说成是实证主义的。这些批评家们的聒噪 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十七世纪笛卡尔就开始意识到了科学的本质,而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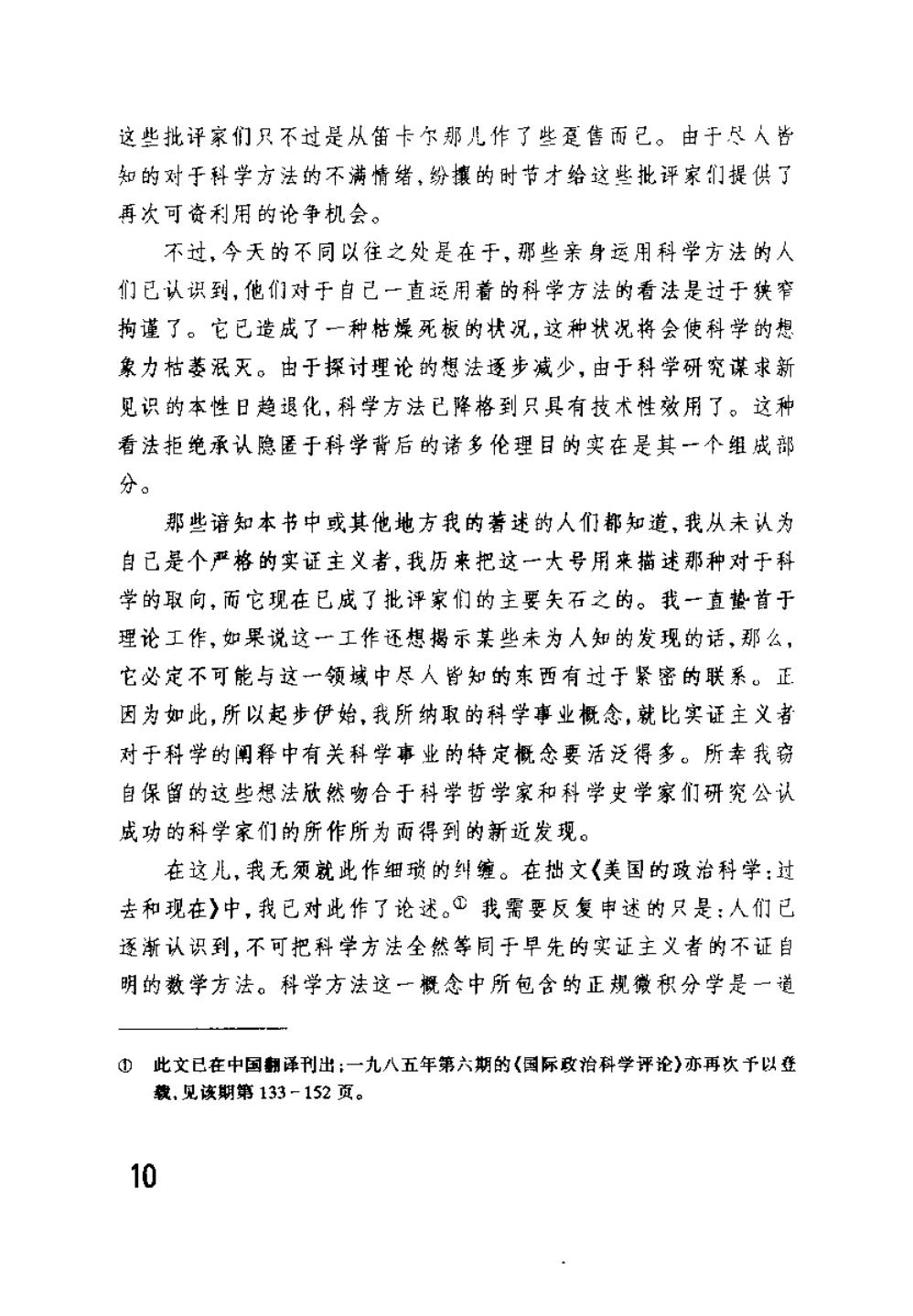
这些批评家们只不过是从笛卡尔那是作了些趸售而已。由于尺人皆 知的对于科学方法的不满情绪,纷攘的时节才给这些批评家]提供了 再次可资利用的论争机会。 不过,今天的不同以往之处是在于,那些亲身运用科学方法的人 们已以识到,他们对于自己一直运用着的科学方法的看法是过于狭窄 拘谨了。它已造成了一种枯燥死板的状况,这种状况将会使科学的想 象力枯萎泯灭。由于探讨理论的想法逐步减少,由于科学研究谋求新 见识的本性日趋退化,科学方法已降格到只具有技术性效用了。这种 看法拒绝承认隐匿于科学背后的诸多伦理目的实在是其一个组战部 分。 那些谙知本节中或其他地方我的著述的人们都知道,我从未认为 自己是个严格的实证主义者,我历来把这一大号用来描述那种对于科 学的取向,而它现在已成了批评家们的主要矢石之的。我一直蛰首于 理论工作,如果说这一工作还想揭示某些未为人知的发现的话,那么, 它必定不可能与这一领域中尽人皆知的东西有过于紧密的联系。正 因为如此,所以起步伊始,我所纳取的科学事业概念,就比实证主义者 对于科学的闲释中有关科学事业的特定概念要活泛得多。所幸我窃 自保留的这些想法欣然吻合于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们研究公认 成功的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而得到的新近发现。 在这儿,我无须就此作细琐的纠缠。在拙文〈美国的政治科学:过 去和现在》中,我已对此作了论述。①我需要反复申述的只是:人们已 逐渐认识到,不可把科学方法全然等同于早先的实证主义者的不证自 明的数学方法。科学方法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正规微积分学是一道 ①此文已在中国翻译刊出: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的《国际改治科学评论)亦再次予以登 载,见该期第133-152页。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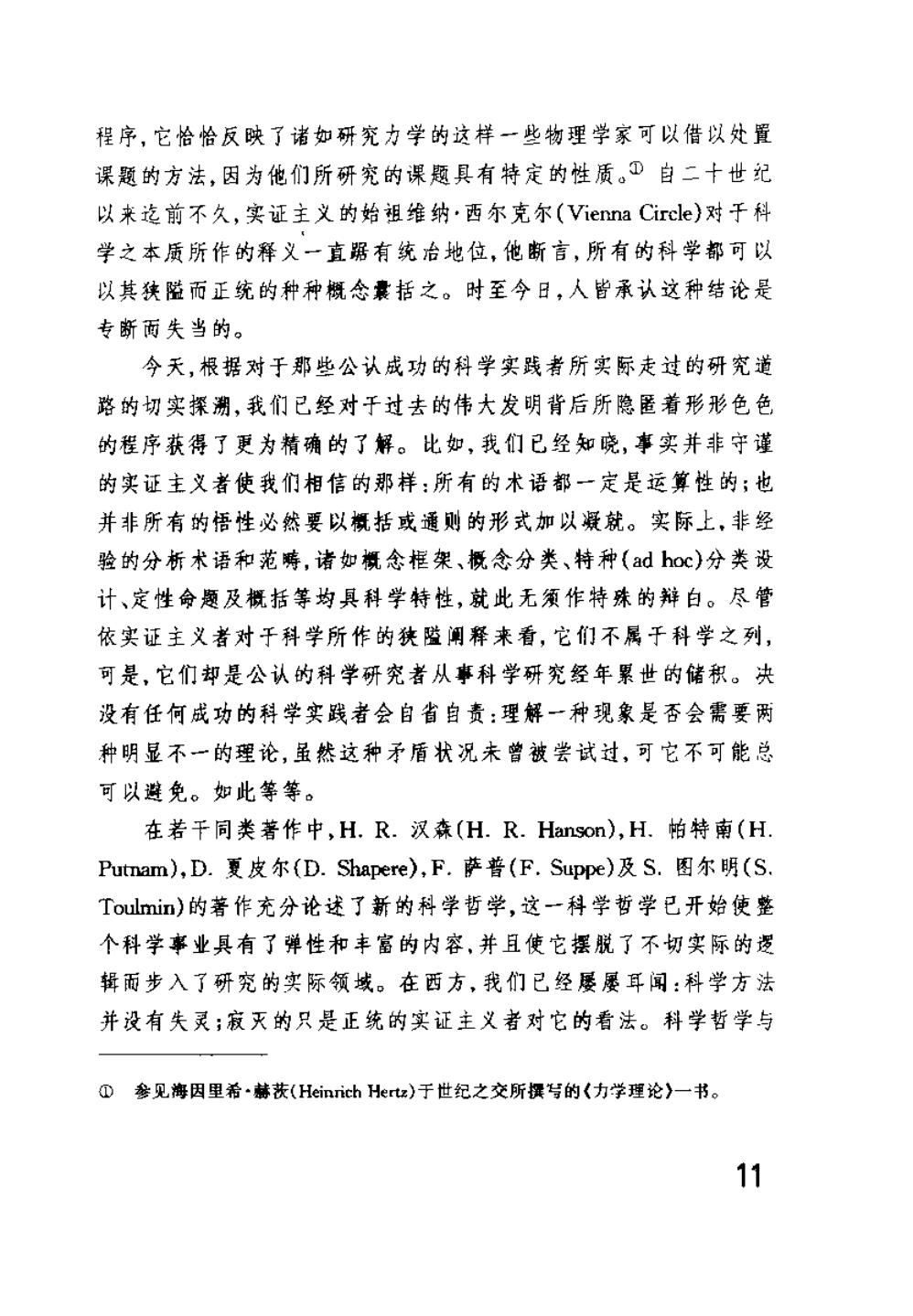
程序,它恰恰反映了诸如研究力学的这样一些物理学家可以借以处置 课题的方法,因为他们所研究的课题具有特定的性质。①自二十世纪 以来迄前不久,实证主义的始祖维纳,西尔克尔(Vienna Circle)对于科 学之本质所作的释义一直踞有统治地位,他断言,所有的科学都可以 以其狭隘而正统的种种概念囊括之。时至今日,人皆承认这种结论是 专断而失当的。 今天,根据对于那些公认成功的科学实践者所实际走过的研究道 路的切实探湖,我们已经对于过去的伟大发明背后所隐匿着形形色色 的程序获得了更为精确的了解。比如,我们已经知晓,事实并非守谨 的实证主义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所有的术语都一定是运算性的;也 并非所有的梧性必然要以概括或通则的形式加以凝就。实际上,非经 验的分析术语和范畴,诸如概念框架、概念分类、特种(ad hoc)分类设 计、定性命题及概括等均具科学特性,就此无须作特殊的辩白。尽管 依实证主义者对于科学所作的狭磁阐释来看,它们不属于科学之列, 可是,它们却是公认的科学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经年票世的储积。决 设有任何成功的科学实践者会自省自责:理解一种现象是否会需要两 种明显不一的理论,虽然这种矛盾状况未曾被尝试过,可它不可能总 可以避免。如此等等。 在若千同类著作中,H.R.汉森(H.R.Hanson),H.帕特南(H. Putnam),D.夏皮尔(D.Shapere)),F.萨普(F.Suppe)及S.图尔明(S. Toulmin)的著作充分论述了新的科学哲学,这一科学哲学已开始使整 个科学事业具有了弹性和丰富的内容,并且使它摆脱了不切实际的逻 辑面步入了研究的实际领域。在西方,我们已经屡屡耳闻:科学方法 并没有失灵;寂灭的只是正统的实证主义者对它的看法。科学哲学与 ①参见海因里希·赫获(Heinrich Hertz)于世纪之交所撰号的《力学理论》一书。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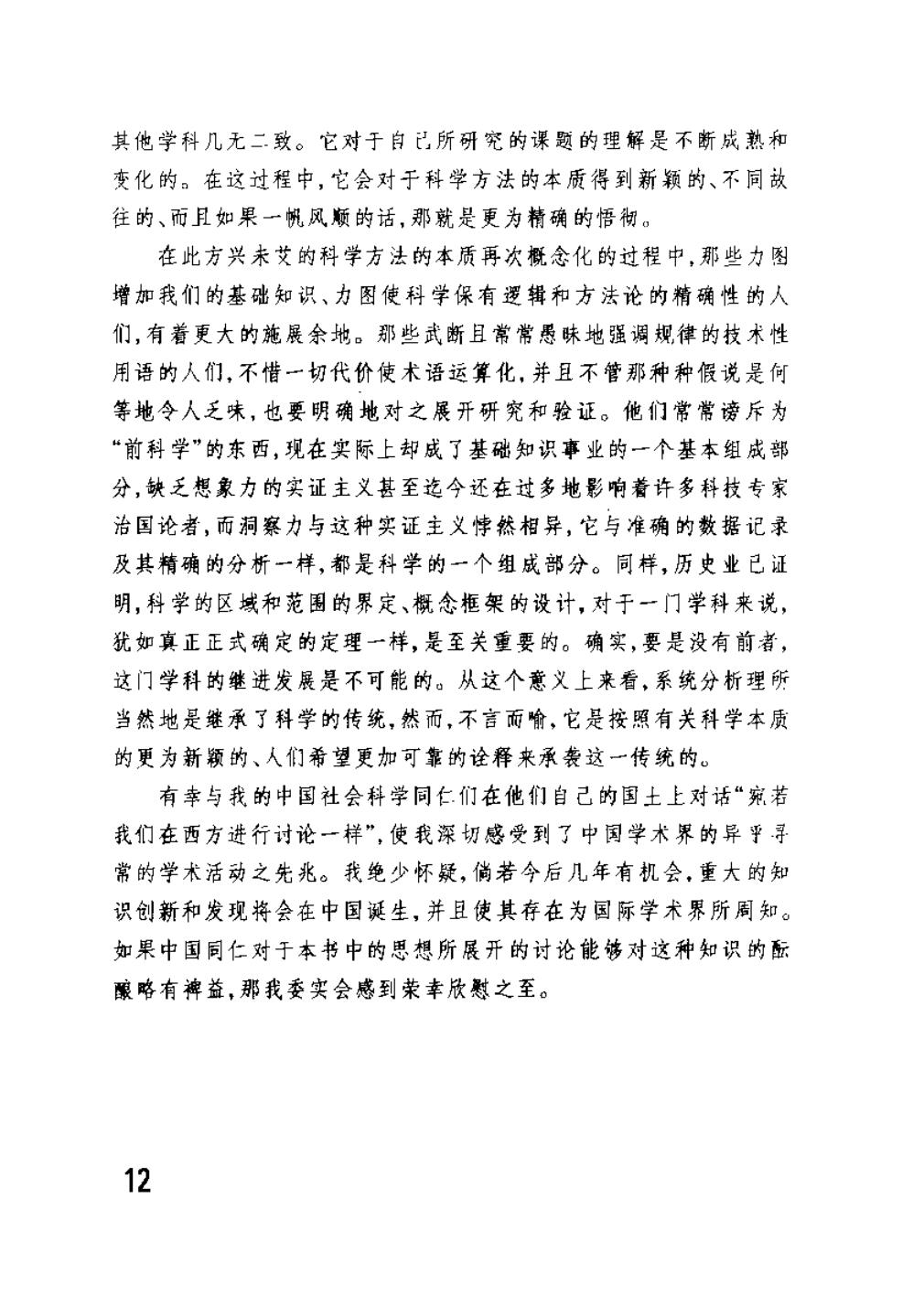
其他学科几无二致。它对于白已所研究的课题的理解是不断成熟和 变化的。在这过程中,它会对于科学方法的本质得到新颖的、不同故 往的、而月如果一帆风顺的话,那就是更为精确的悟彻。 在此方兴未艾的科学方法的本质再次概念化的过程中,那些力图 增加我们的基础知识、力图使科学保有逻辑和方法论的精确性的人 们,有着更大的施展余地。那些武断且常常愚味地强调规律的技术性 用语的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使术语运算化,并且不管那种种假说是何 等地令人乏味,也要明确地对之展开研究和验证。他们常常谤斥为 “前科学”的东西,现在实际上却成了基础知识事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 分,缺乏想象力的实证主义甚至迄今还在过多地影响着许多科技专家 治国论者,而洞察力与这种实证主义悖然相异,它与准确的数据记录 及其精确的分析一样,都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历史业已证 明,科学的区域和范围的界定、概念框架的设计,对于一门学科来说, 犹如真正正式确定的定理一样,是至关重要的。确实,要是没有前者, 这门学科的继进发展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系统分析理所 当然地是继承了科学的传统,然而,不言而喻,它是按照有关科学本质 的更为新颖的、人们希望更加可靠的诠释来承袭这一传统的。 有幸与我的中国社会科学同仁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对话“宛若 我们在西方进行讨论一样”,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异乎寻 常的学术活动之先兆。我绝少怀疑,倘若今后儿年有机会,重大的知 识创新和发现将会在中国诞生,并且使其存在为国际学术界所周知。 如果中国同仁对于本书中的思想所展开的讨论能够对这种知识的酝 酿略有裨益,那我委实会感到荣幸欣慰之至。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