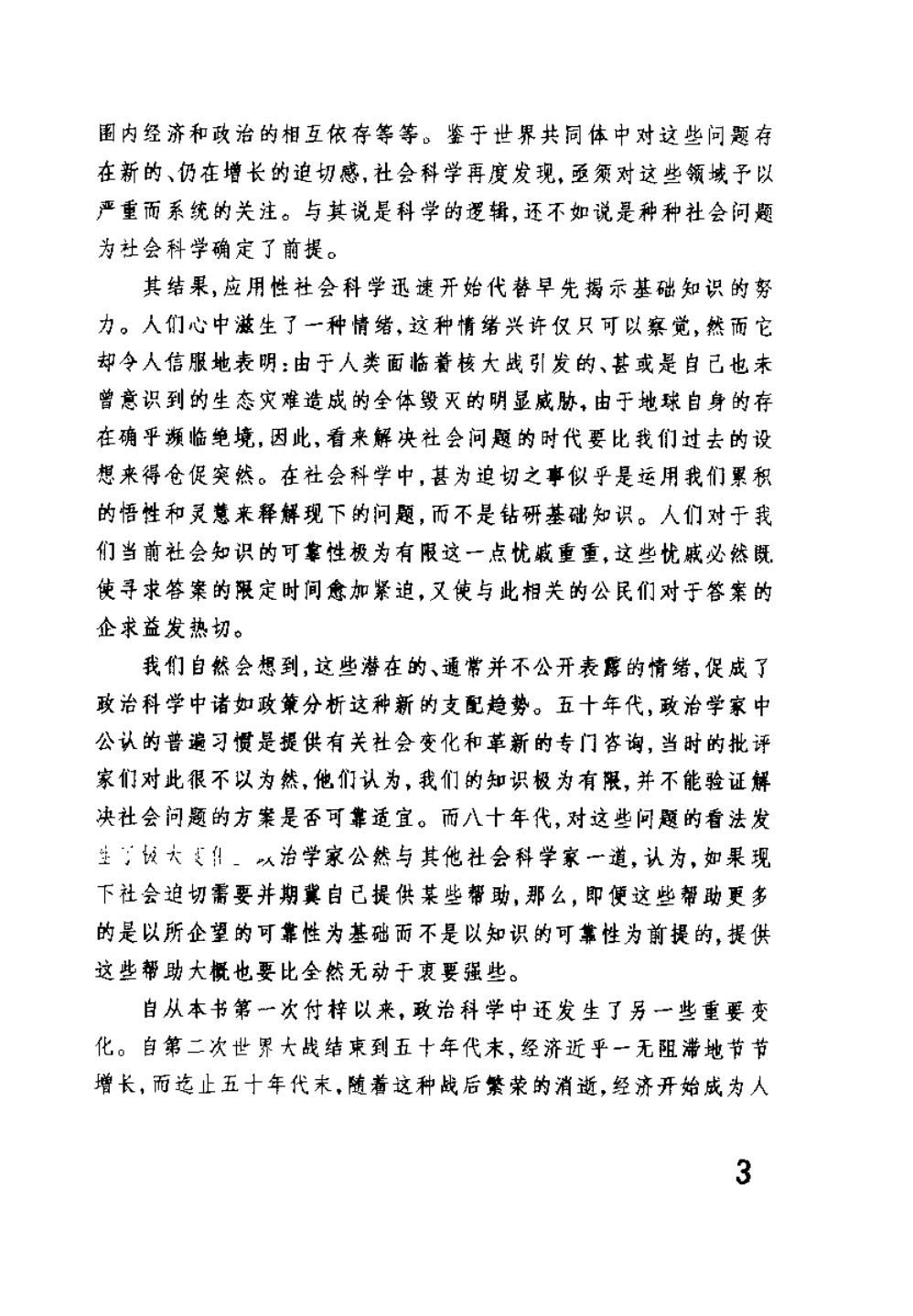
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鉴于世界共同体中对这些问题存 在新的、仍在增长的迫切感,社会科学再度发现,亟须对这些领域予以 严重而系统的关注。与其说是科学的逻辑,还不如说是种种社会问题 为社会科学确定了前提。 其结果,应用性社会科学迅速开始代替早先揭示基础知识的努 力。人们心中滋生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兴许仅只可以察觉,然而它 却令人信服地表明:由于人类面临着核大战引发的、甚或是自己也未 曾意识到的生态灾难造成的全体毁灭的明显威胁,由于地球自身的存 在确乎颜临绝境,因此,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要比我们过去的设 想来得仓促突然。在社会科学中,甚为追切之事似乎是运用我们累积 的悟性和灵惹来释解现下的问题,而不是钻研基础知识。人们对于我 们当前社会知识的可睾性极为有限这一点忧戚重重,这些忧戚必然既 使寻求答案的根定时间意加紧迫,又使与此相关的公民们对于答案的 企求益发热切。 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潜在的、通常并不公开表露的情绪,促成了 政治科学中诸如政策分析这种新的支配趋势。五十年代,政治学家中 公认的普递习惯是提供有关社会变化和革新的专门咨询,当时的批评 家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们的知识极为有根,并不能验证解 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否可靠适宜。而八十年代,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发 主设大和。以治学家公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一道,认为,如果现 下社会迫切需要并期冀自己提供某些帮助,那么,即使这些帮助更多 的是以所企望的可靠性为基础而不是以知识的可靠性为前提的,提供 这些帮助大概也要比全然无动于衷要强些。 自从本书第一次付梓以来,政治科学中还发生了另一些重要变 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五十年代末,经济近平一无阻滞地节节 增长,而迄止五十年代末,随着这种战后繁荣的消逝,经济开始成为人 3

所关注的中心领域。美国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一系列经济萧条给表面 持久繁荣的岁月投下了阴影。人们不禁回想起了三十年代大萧条的 境况。基于其对于社会变化的感受,社会科学各学科迅捷开始反映这 种再度兴起的对于经济的兴趣。 在政治科学中,这一点也拟若干方式得到了体现。首先,在三十 年代大萧条时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 性,此时,人们再度承认了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 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攻治经济学,它再 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 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 其次,再度兴起的对于经济的研究兴趣部分是由政治科学引起 的,为此,政治科学中的一个旧式术语“国家”(State)再度成为研究的 热点。在五十年代,随着行为主义的变革,作为一个概念的“国家”被 认为不合乎要求,未久就为一个涵义更加丰富的术语“政治系统”所代 替了。“国家”这一概念之所以会被政治学首先摒弃,是因为它早先是 含糊不清的。虽然现今照我看来,它丝毫也不明晰可鉴,但它却又成 了分析的术语。其原因,我在《国家重围之下的政治系统》①一文中 已作了剖析。除此之外,这一概念复苏的原因,一定程度上还确实在 于我所说的美国社会科学受到的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的冲击。第一次 冲击自然是在马克思在世期间,第二次冲击則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期 间,那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渗入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今天,在 其第三次冲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尼科斯·普兰札斯(Nic然 Poulantzas)的著作中所阑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社会 科学的方向和某些理论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新生的马克思主义 ① (政治理论》-九八五年第九期第303一325页。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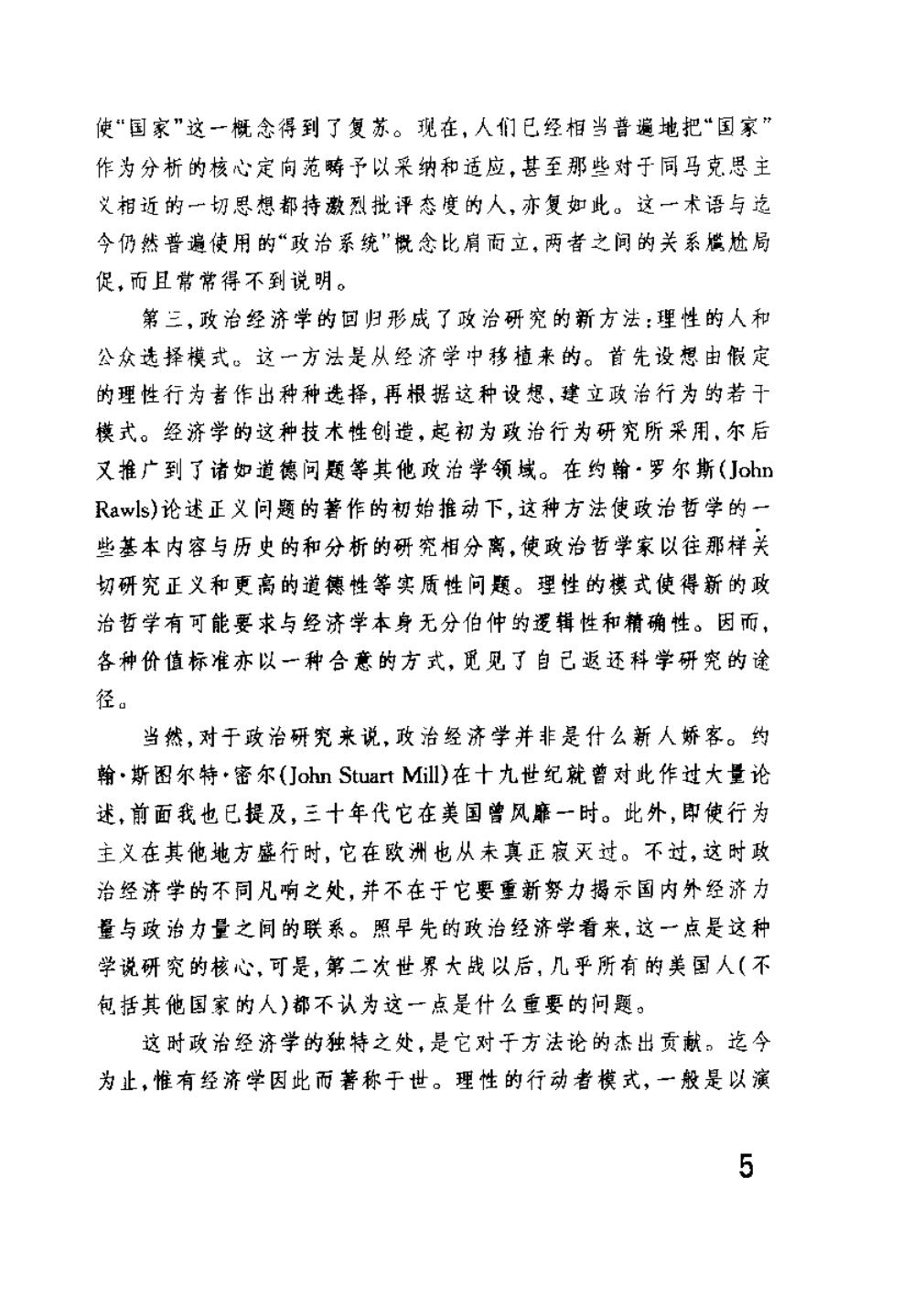
使“国家”这一概念得到了复苏。现在,人们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国家” 作为分析的核心定向范畴予以采纳和适应,甚至那些对于同马克思主 义相近的一切思想都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亦复如此。这一术语与迄 今仍然普遍使用的“政治系统”概念比肩而立,两者之间的关系档尬局 促,而且常常得不到说明。 第三,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理性的人和 公众选择模式。这一方法是从经济学中移植来的。首先设想由假定 的理性行为者作出种种选择,再根据这种设想,建立政治行为的若于 模式。经济学的这种技术性创造,起初为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 又推广到了诸如道德问題等其他政治学领域。在约翰·罗尔斯(Jon Rawls)论述正义问题的著作的初始推动下,这种方法使政治哲学的一 些基本内容与历史的和分析的研究相分离,使政治哲学家以往那样关 切研究正义和更高的道德性等实质性问題。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 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 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 径。 当然,对于政治研究来说,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什么新人娇客。约 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十九世纪就曾对此作过大量论 述,前面我也已提及,三十年代它在美国曾风靡一时。此外,即使行为 主义在其他地方盛行时,它在欧洲也从未真正寂灭过。不过,这时政 治经济学的不同凡响之处,并不在于它要重新努力揭示国内外经济力 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照早先的政治经济学着来,这一点是这种 学说研究的核心,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不 包括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认为这一点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 为业,椎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 5

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 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一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 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移易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 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 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 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也确实因为蜘此,许多经济学家才主张实行 这种“大帝国主义”。 热衷于这一模式的历史性初次狂潮现在正开始消退。经由政治 研究的各个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此模式的多次试验,人们正 在作出旱已料及的批评性反应。尽管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理性模 式一开始所具有的魅力要素尚不会消耗殆尽。 论及《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首次问世以来政治科学研究方 向和方法上的所有这些变化,我又回到了开始这番议论之初所提出的 问题上:随着本书被译成中文,今天,系统分析的位置何在呢? 首先,系统分析现在仍然是研究一般理论的唯一通览全局的方法 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竞争对手。我之所以 要谓之日“不幸”,是因为众所周知,只有某种理论方法不断为其他理 论方法所替代,科学方能够获致进步。以理性的设想为基础的模式并 不是系统分析的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并没有声称将适用于政治研究的 一切重要领域。 一方面,因为这些模式具有简化主义的特性,所以它们恐难适用 于政治研究的一切重要领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些模式用作分 析单独的行为或分析被看作一个个独立单位的团体行动者,是适宜 的。而且事实证明,当这些单独行为处于竞争状况而不是合作状况 时,这些模式更加有用。它们既不能被成功地运用于政治研究各重要 的规定领域、亦不能圆满地研究那些可能限假制、而且有时甚至支配单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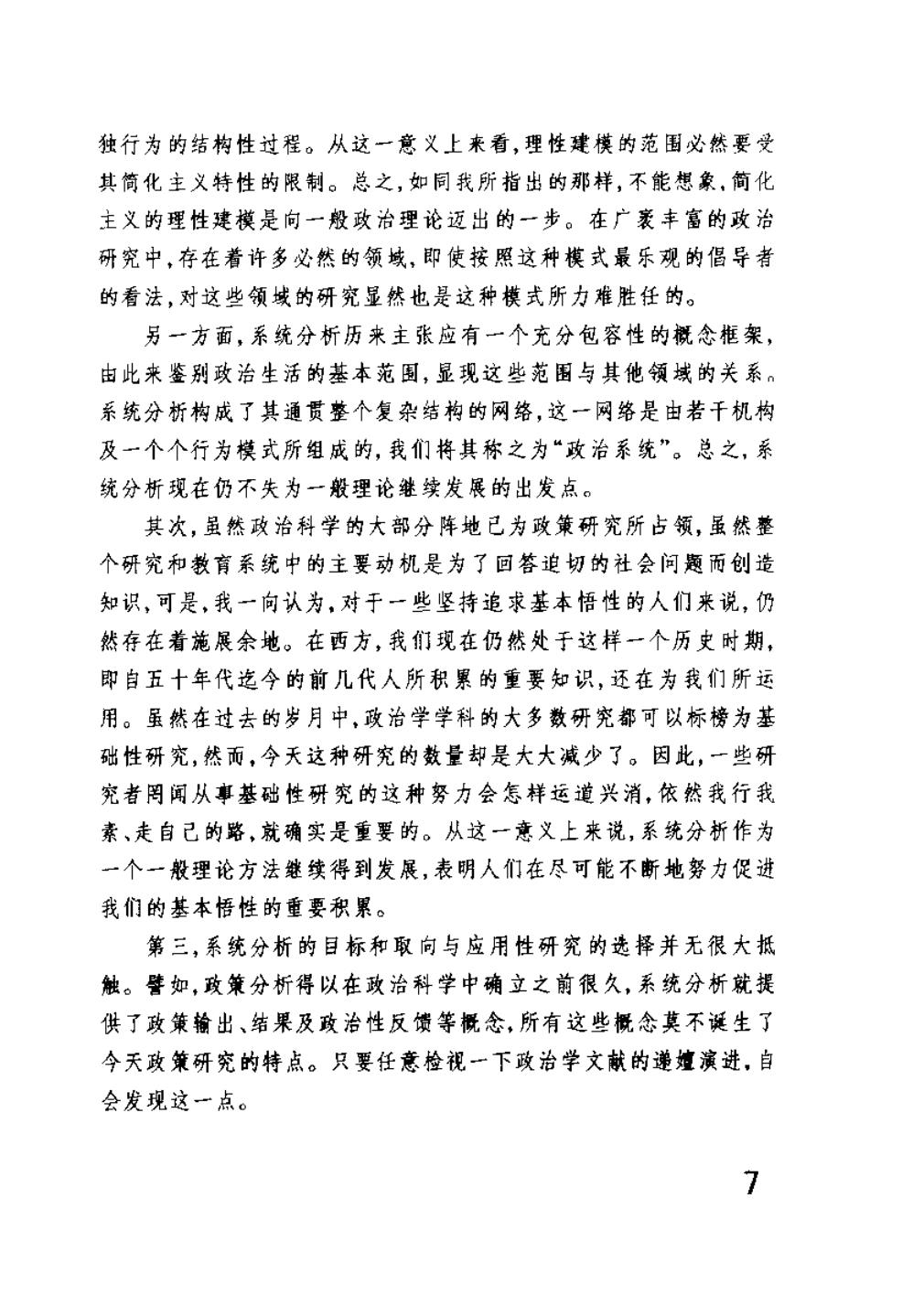
独行为的结构性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理性建模的范围必然要受 其简化主义特性的限制。总之,如同我所指出的那样,不能想象,简化 主义的理性建摸是向一般政治理论迈出的一步。在广袤丰富的攻治 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必然的领域,即使按照这种模式最乐观的倡导者 的看法,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显然也是这种模式所力难胜任的。 另一方面,系统分析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 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 系统分析构成了其通贯整个复杂结构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千机构 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攻治系统”。总之,系 统分析现在仍不失为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 其次,虽然政治科学的大部分阵地已为政策研究所古领,虽然整 个研究和教育系统中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回答追切的社会问题而创造 知识,可是,我一向认为,对于一些坚持追求基本悟性的人们来说,仍 然存在着施展余地。在西方,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即自五十年代迄今的前几代人所积累的重要知识,还在为我们所运 用。虽然在过去的岁月中,政治学学科的大多数研究都可以标榜为基 础性研究,然而,今天这种研究的数量却是大大减少了。因此,一些研 究者罔闻从事基础性研究的这种努力会怎样运道兴消,依然我行我 素、走自己的路,就确实是重要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系统分析作为 一个一般理论方法继续得到发展,表明人们在尽可能不断地努力促进 我们的基本悟性的重要积累。 第三,系统分析的目标和取向与应用性研究的选择并无很大抵 触。譬如,政策分析得以在政治科学中确立之前很久,系统分析就提 供了政策输出、结果及政治性反馈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莫不诞生了 今天政策研究的特点。只要任意检视一下政治学文献的递嬗演进,自 会发现这一点。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