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察尚公请 长路 戰爭與革命中的 西南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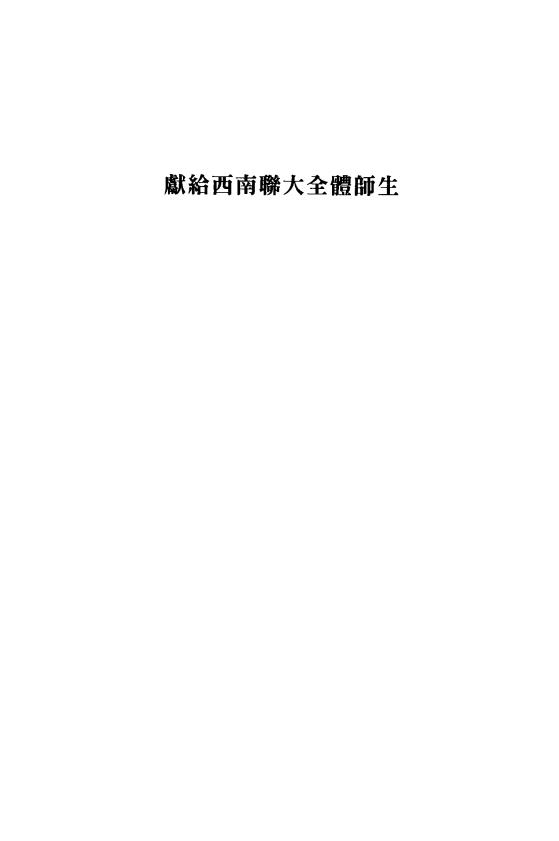
獻給西南聯大全體師生

序 戰爭、西南聯大與歷史遺產 一一讀易社強教授著《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 大》 呂芳上 如果把大學校史寫成一部革命史,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失 敗;要是把充滿活力的校史,寫成光有組織、只有制度,看 不到靈魂,看不到「人」的歷史,也同樣不會討好。大學本來 就是活生生的一群人,聚在一塊,共同耕耘、切磋知職學問的 學術樂圜。戰爭時期或許外在環境險惡,但教師埋頭著逃丶勤 快解惑,學生好像永速有填不滿的求知慾笔,師生交流綿密, 知識火花熱鬧迸放,如響斯應,此所謂「弦歌不輟」,既是浩 劫,也是風雲際會,更是因緣凑合。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作, 天津南開一一國人最早的私立大學,首遭戰爭摧折,接著國立 北大·清華,難逃劫運。三校先約會於湖南長沙臨大·糍又被 迫流徙雲南昆明。一九三八年昆明建起了一個臨時聯合學府, 來了一批又一批流亡的讀書人。九年之後,南渡之人,各自北 返,「神京復,還燕碣」,西南聯大幾與抗戰相始終,此確屬 一代盛事,百世難遇。這樣一所特殊大學的精彩校史,最後賴 一位孜孜讫吃的洋學者,奮力以成;中文本則在英文本成書十

載後方得面世,其中作者的用心與堅持,或許只有由三校流離 遷移之苦的主張和歷史中體會才能獲得。 西 南 二 大 《聯大》(Li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戰事 Revolution)這本書的作者是出身哈佛,後在維吉尼亞大學執 教多年的易社強(John W.Israel)教授,執著又認真的謙賺君 命 子。他一生的研究聚焦於二十世紀中國教育、政治與學運的歷 中國 史,他知名的主要著作,先是談抗戰前中國「學生民族主義」 (Student Nationalism)(1966),十年後討論了「一二·九運 動(1976),再二十年後的1999年出版這本《西南聯大》, 慢工細活,上乘作品,學界公認。 顧名思義,「聯合大學」是「混福」而非「化合」·因此 北大、清華、南開各自擁有的特色,南開活絡、北大自由、清 華嚴謹,依然保留。所謂「同無妨異、異不害同」,「八音合 奏,終和且平」。雖是一部校史,卻是三個學府精神所寄。昆 明雖號稱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常春之草,在三、四十年代仍 只是個「邊城」,戰火引燃後沒多久,突然有大批中原學者湧 入。當地人(少數民族為多)與外來者有如雨個世界不同世紀 人的聚合,難怪在政治上是民族主義者·在思想上又是世界主 義者的社會菁英,此時竟被視為「上海騙子」。其實,被迫漂 泊者與本地人糅合過程不易,這樣的歷史日後也一再複製。易 社強教授認為聯大九年的歷史是政治的、文化的又是知識的歷 史·得由跨文化中去理解·誠哉斯言。 西南聯大極盛時有教授一百七十餘人,學生二千多位· 風雲際會,把一批學界名人匯聚一地,頂尖學生群集一處。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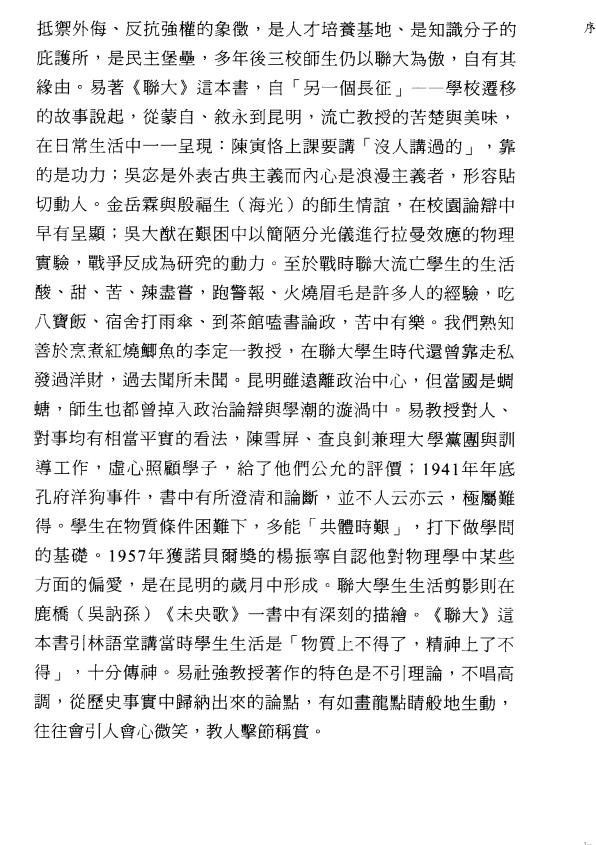
抵禦外侮、反抗強權的象徵,是人才培養基地、是知識分子的 序 庇護所,是民主堡壘,多年後三校師生仍以聯大為傲,自有其 緣由。易著《聯大》這本書,自「另一個長征」一一學校遷移 的故事說起,從蒙自、敘永到昆明,流亡教授的苦楚與美味, 在日常生活中一一呈現:陳寅恪上課要講「沒人講過的」,靠 的是功力;吳宓是外表古典主義而内心是浪漫主義者,形容贴 切動人。金岳霖與殷福生(海光)的師生情誼·在校園論辯中 早有呈顯:吳大猷在艱困中以簡陋分光儀進行拉曼效應的物理 實驗,戰爭反成為研究的動力。至於戰時聯大流亡學生的生活 酸、甜、苦、辣盡嘗,跑警報、火燒眉毛是許多人的經驗,吃 八寶饭、宿舍打雨傘·到茶館嗑書論政·苦中有樂。我們熟知 善於烹煮紅燒鲫魚的李定一教授,在聯大學生時代還曾靠走私 發過洋財,過去聞所未聞。昆明雖遠離政治中心,但當國是蜩 螗,師生也都曾掉入政治論辯與學潮的漩渦中。易教授對人、 對事均有相當平實的看法,陳雪屏、查良釗兼理大學黨團與副 導工作,虛心照顧學子·給了他們公允的評價:1941年年底 孔府洋狗事件,書中有所澄清和論斷,並不人云亦云,極屬難 得。學生在物質條件困難下,多能「共體時艱」,打下做學間 的基礎。1957年獲諾貝爾獎的楊振寧自認他對物理學中某些 方面的偏愛,是在昆明的歲月中形成。聯大學生生活剪影則在 鹿橋(吳訥孫)《未央歌》一書中有深刻的描箱。《聯大》這 本書引林語堂講當時學生生活是「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 得」,十分傅神。易社強教授著作的特色是不引理論,不唱高 調,從歷史事實中歸納出來的論點,有如畫龍點睛般地生動, 往往會引人會心微笑,教人擊節稱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