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丽塔母 第一部 1 洛丽塔,照亮我生命的光,点燃我情欲的火。我的罪恶,我 的灵魂。洛一丽一塔:舌尖顶到上男做一次三段旅行。洛。丽。 塔。 早晨叫她洛,就简单一个宇。当她只穿一只袜子出现在我面 前的时候。穿便服时,我叫她洛拉。学校里,人们叫她多丽,表 格的虚线上填的是多洛雷斯。可是在我的怀抱里,她永远叫洛丽 塔。 她之前还有过先来者吗?有的,确实有过。实际上,要不是 那年夏天,我爱上了一个稚气未脱的小丫头,也许压根儿就不会 有什么洛丽塔。那事发生在海边的一片小小的王国。哦,是什么 时候来着?那年夏天我的年龄正好是洛丽塔出生之前的那么多 年。可不是吗,要编神话,你尽管可以指望一个杀人犯。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证据第一号便可以使那个六翼天 使,那个总是稀里糊涂,传错消息,生着一双高贵翅膀的六翼天 使大为嫉妒。瞧瞧这团乱麻吧。女士们。先生们。 1

大师名作系列 2 我1910年生于巴黎。我父亲天性温和,无优无虑,“是像一 盘用不同人种基因做成的沙拉:瑞士公民,法兰西人和奥地利人 的后代,血管里奔腾著多瑙河的水。等会儿我要给你们看一些印 刷精美、闪着蓝光的明信片。我父亲在里维埃拉①拥有一座表 华的旅馆。祖父和两位曾祖父曾分别贩卖过酒、珠宝和丝绸。30 岁时,父亲娶了一位英国姑娘,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两 位多塞特郡教区牧师的孙女。这两位牧师老祖宗分别是古儿科学 和风奏琴专家→真让人弄不明白。我那位很上镜头的母亲死于 一场天灾(野餐时被闪电击中),那年我才3岁。在对遥远过去 的回忆中,在脑子里那些空空洞洞和沟沟坎坎里,母亲只给我留 下一口袋温暖。这回忆,假如你还能忍受我的文风的话(我是在 被监视的情祝下写作的),曾被我直年的太阳照亮。当然喽,那 逝去的风月给人留下的芳香记忆,你一定全都了如指掌。那花朵 盛开的绿篱上飞着的小虫呀,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呀,夏天黄昏 时的山谷呀,还有那让人受不了的热浪,那金龟子。 我母亲的姐姐叫塞比尔。父亲的一位表哥娶了她,但后来又 甩了她。塞比尔待候我们二家,就像一位不拿钱的家庭女救师或 管家婆。后来有人告诉我,她曾经爱过我父亲。某一个下雨天, 父亲很随便地占有了她,而雨停之后,他就把这事忘了。我很喜 欢这位姨妈,尽管她的有些规矩十分严厉—一严厉得要命。说不 ①里维埃拉。地中海边的旅游度粮胜地。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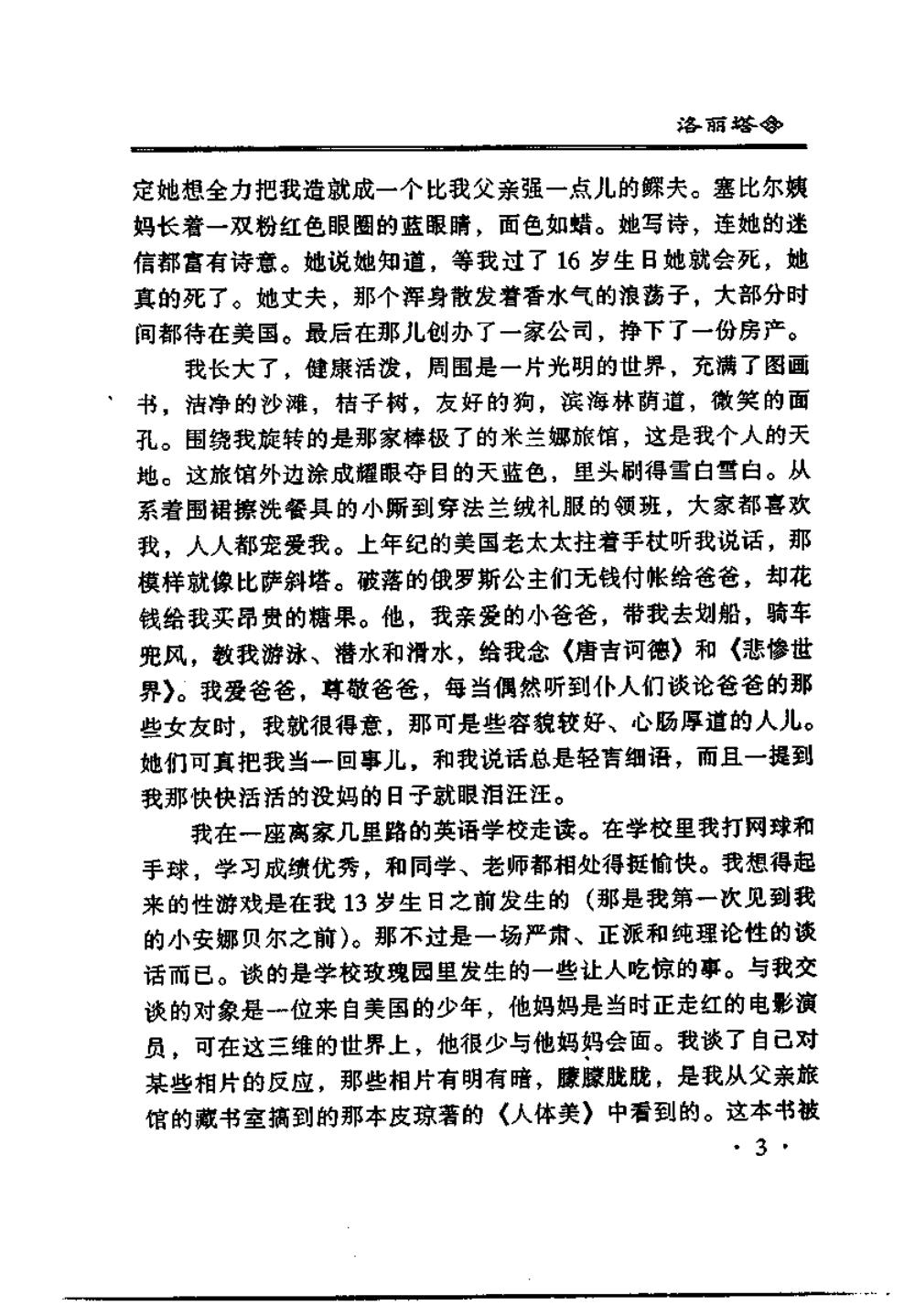
洛丽塔 定她想全力把我造就成一个比我父亲强一点儿的鳏夫。塞比尔姨 妈长着一双粉红色眼圈的蓝跟睛,面色如蜡。她写诗,连她的迷 信都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等我过了16岁生日她就会死,她 真的死了。她丈夫,那个浑身散发着香水气的浪荡子,大部分时 间都待在美国。最后在那儿创办了一家公司,挣下了一份房产。 我长大了,健康活泼,周围是一片光明的世界,充满了图画 ·书,法净的沙滩,桔子树,友好的狗,滨海林荫道,微笑的面 孔。围绕我旋转的是那家棒极了的米兰娜旅馆,这是我个人的天 地。这旅馆外边涂成耀眼夺目的天蓝色,里头刷得雪白雪白。从 系着围裙擦洗餐具的小厮到穿法兰绒礼服的领班,大家都喜欢 我,人人都宠没我。上年纪的美国老太太拄着手杖听我说话,那 模样就像比萨斜塔。破落的俄罗斯公主们无钱付帐给爸爸,却花 钱给我买昂贵的糖果。他,我亲爱的小爸爸,带我去划船,骑车 兜风,教我游泳、潜水和滑水,给我念《唐吉河德》和《悲惨世 界》。我爱爸爸,尊敬爸爸,每当偶然听到仆人们谈论爸爸的那 些女友时,我就很得意,那可是些容貌较好、心肠厚道的人儿。 她们可真把我当一回事儿,和我说话总是轻指细语,而且一提到 我那快快活活的没妈的日子就眼泪汪汪。 我在一座离家几里路的英语学校走读。在学校里我打网球和 手球,学习成绩优秀,和同学、老师都相处得挺偷快。我想得起 来的性游戏是在我13岁生日之前发生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 的小安娜贝尔之前)。那不过是一场严肃、正派和纯理论性的谈 话而已。谈的是学校玫瑰园里发生的一些让人吃惊的事。与我交 谈的对象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少年,他妈妈是当时正走红的电影演 员,可在这三维的世界上,他很少与他妈妈会面。我谈了自己对 某些相片的反应,那些相片有明有暗,朦朦胧胧,是我从父亲旅 馆的戴书室搞到的那本皮琼著的《人体美)》中看到的。这本书被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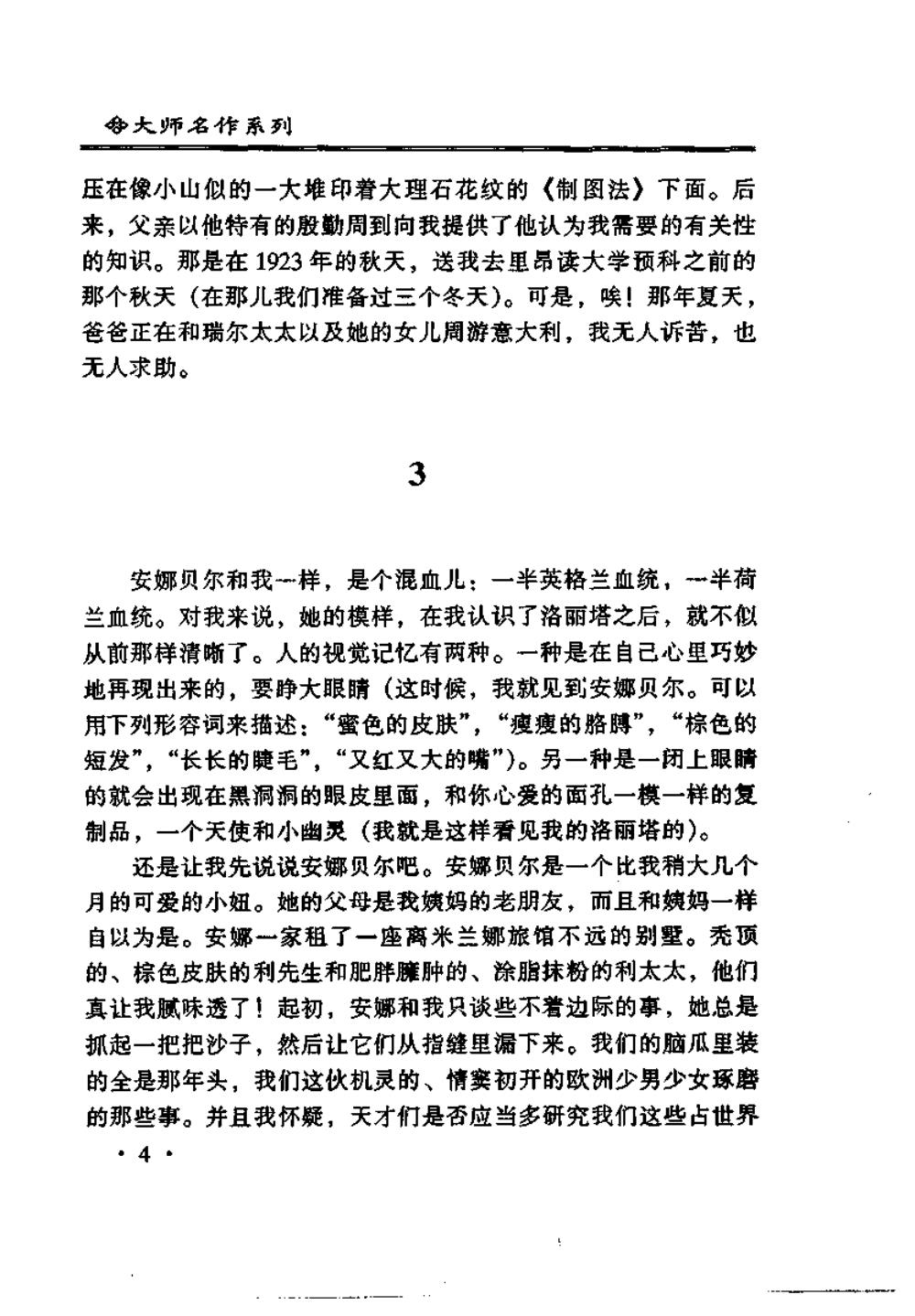
每大师名作系列 压在像小山似的一大堆印着大理石花纹的《制图法》下面。后 来,父亲以他特有的殷勤周到向我提供了他认为我需要的有关性 的知识。那是在123年的秋天,送我去里品读大学预科之前的 那个秋天(在那儿我们准备过三个冬天)。可是,唉!那年夏天, 爸爸正在和瑞尔太太以及她的女儿周游意大利,我无人诉苦,也 无人求助。 3 安娜贝尔和我样,是个混血儿:一半英格兰血统,…半荷 兰血统。对我来说,她的模样,在我认识了洛丽塔之后,就不似 从前那样清晰了。人的视觉记忆有两种。一种是在自已心里巧妙 地再现出来的,要睁大眼睛(这时候,我就见到安娜贝尔。可以 用下列形容词来描述:“蛮色的皮肤”,“瘦瘦的胳膊”,“棕色的 短发”,“长长的睫毛”,“又红又大的嘴”)。另一种是一闭上眼睛 的就会出现在黑洞洞的眼皮里面,和你心爱的面孔一模一样的复 制品,一个天使和小幽灵(我就是这样看见我的洛丽塔的)。 还是让我先说说安螂贝尔吧。安娜贝尔是一个此我稍大几个 月的可爱的小妞。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老朋友,而且和姨妈一样 自以为是。安娜一家租了一座离米兰娜旅馆不远的别墅。秃顶 的、棕色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臁肿的、涂脂抹粉的利太太,他们 真让我腻味透了!起初,安娜和我只谈些不着边际的事,她总是 抓起一把把沙子,然后让它们从指缝里漏下来。我们的脑瓜里装 的全是那年头,我们这伙机灵的、情窦初开的欧洲少男少女琢磨 的那些事。并且我怀疑,天才们是否应当多研究我们这些占世界 ·4

洛丽塔 人口大多数的人感兴趣的东西。诸如网球大赛啊,世界的无穷 啊,唯我论啊,等等。还有幼小动物的温柔与脆弱给我们带来相 同的痛苦。她打算将来到哪个挨饿的亚洲国家当一名护士,而我 则一心要做一名大侦探。 我们同时陷人情网,笨手笨脚,不知羞耻,痛苦面发狂地互 相爱恋,并且是毫无希望地爱恋。我得加上一句,因为那种需要 互相占有的狂热欲望,事实上只能通过相互间灵魂和肉体的完全 合一才能平息。可是,我们这一对可怜虫,甚至不能像贫民窟的 孩子们那样轻而易举地找到机会来满足我们的饥渴。一次晚上在 性急地做了到她家花园相会的尝试之后,我们唯一被准许的私下 接触只限于走到听不清喊叫那么远,但又不得越出海滨最稠密居 住区人们的视线。在那儿,趴在柔软的沙滩上,离大人仅几英尺 远,整个上午我们都处于一种被阵阵欲望折磨得发僵的状态,充 分利用一切空间和时间赐给我们的突然机会来相互触摸。她的 手,一半藏在沙子里,会悄销地向我伸过来,那伸长的棕色手指 梦游一般越来越近。然后,她的乳白色的膝盖就开始了一场小心 翼翼的长途旅行。有时,比我们还小的孩子们会给我们造成突如 其来的好时机,使我们能在足够隐蔽的情况下互相摩擦对方咸味 的嘴唇。这种不深入的接触使我们健康而毫无经验的年轻身体处 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以致在清凉的蓝色海水底下,紧紧地拥 抱也无法使我们得救。 在我成年之后,在那些四处流浪的日子里,我失去了许多宝 贵的东西。其中有一张姨妈拍的快照,照片上有安娜贝尔,她的 双亲,以及那位上年纪的、稳重的玻足绅士库柏医生。这个老头 那年夏天曾向我姨妈大献殷勤。这一群人在路旁一家咖啡店里围 桌而坐。安娜贝尔照得不好,照的恰巧是她低头吃冰镇巧克力那 一瞬间。我认出她来得凭着她那瘦削的光肩膀和头发中间的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