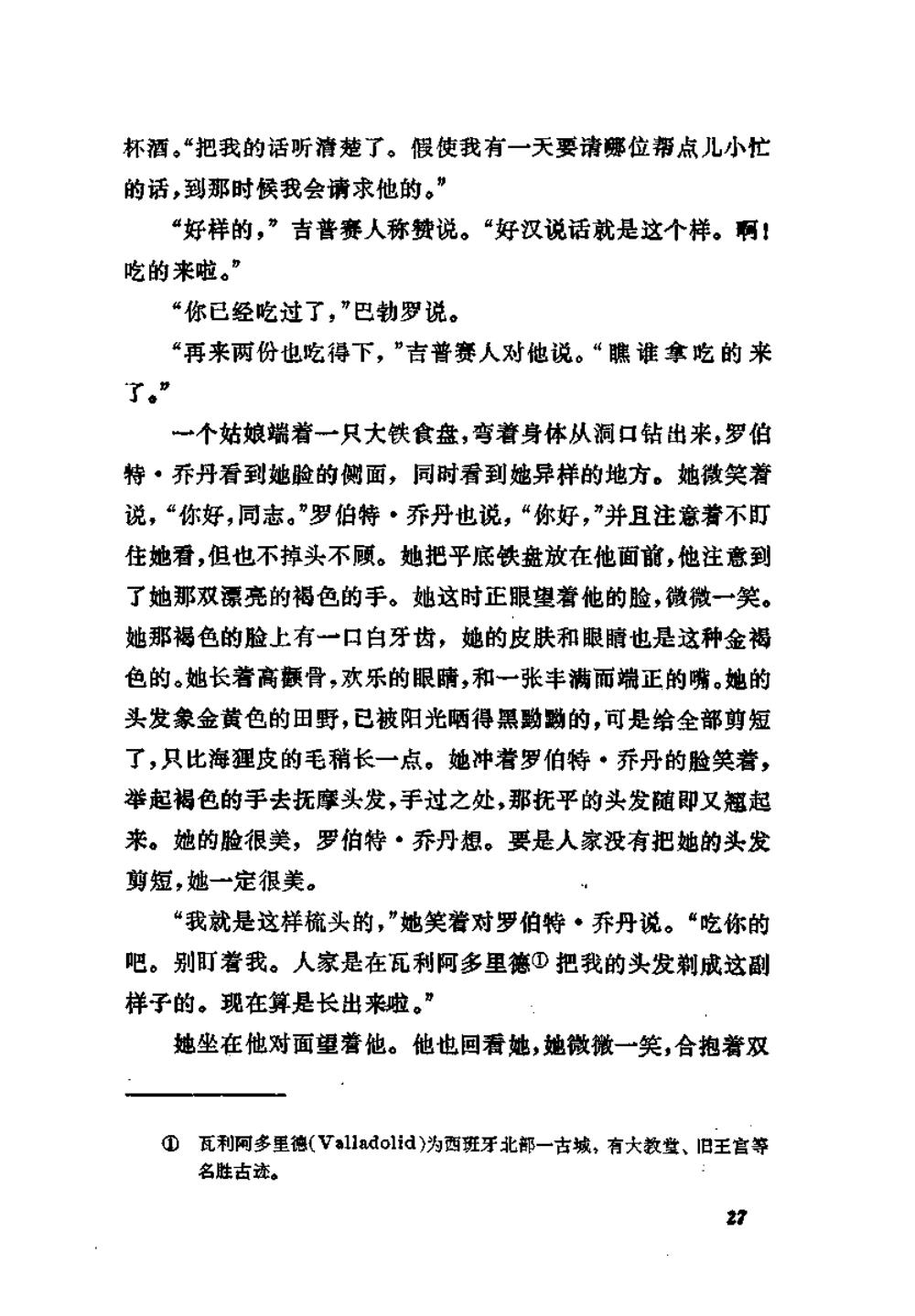
杯酒。“把我的话听清楚了。假使我有一天要请哪位帮点儿小忙 的话,到那时候我会请求他的。” “好样的,”吉普赛人称赞说。“好汉说话就是这个样。啊! 吃的来啦。” “你已经吃过了,”巴勃罗说。 “再来两份也吃得下,”吉普赛人对他说。“瞧谁拿吃的来 了。” 个姑娘端着一只大铁食盘,弯着身体从洞口钻出来,罗伯 特·乔丹看到她脸的侧面,同时看到她异样的地方。她微笑着 说,“你好,同志。”罗伯特·乔丹也说,“你好,”并且注意着不盯 住她看,但也不掉头不顾。她把平底铁盘放在他面前,他注意到 了她那双漂亮的褐色的手。她这时正眼望着他的脸,微微一笑。 她那褐色的脸上有一口白牙齿,她的皮肤和眼睛也是这种金褐 色的。她长着高鞭骨,欢乐的眼睛,和一张羊满面端正的嘴。她的 头发象金黄色的田野,已被阳光晒得黑黝黝的,可是给全部剪短 了,只比海狸皮的毛稍长一点。她冲着罗伯特·乔丹的脸笑着, 举起褐色的手去抚摩头发,手过之处,那抚平的头发随即又翘起 来。她的脸很美,罗伯特·乔丹想。要是人家没有把她的头发 剪短,她一定很美。 “我就是这样梳头的,”她笑着对罗伯特·乔丹说。“吃你的 吧。别盯着我。人家是在瓦利阿多里德①把我的头发剃成这副 样子的。现在算是长出来啦。” 她坐在他对面望着他。他也回看她,她微徵一笑,合抱着双 ①瓦利阿多里德(Vl1 adolid)为西班牙北部一古城,有大教堂、旧王官等 名胜古迹。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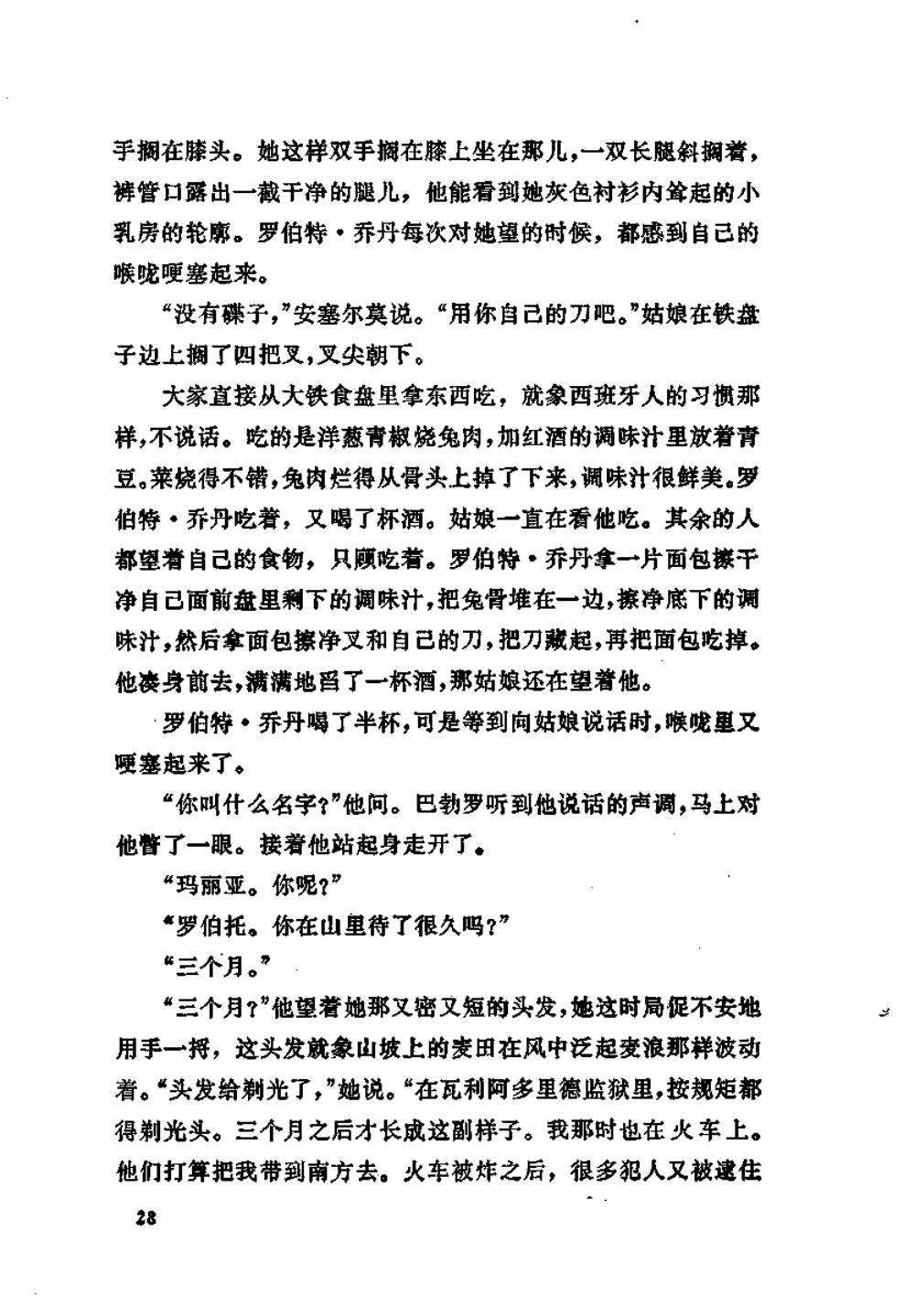
手搁在膝头。她这样双手搁在膝上坐在那儿,一双长腿斜搁营, 裤管口露出一截干净的腿儿,他能看到她灰色衬衫内耸起的小 乳房的轮廓。罗伯特·乔丹每次对她望的时候,都感到自己的 喉咙哽塞起来。 “没有碟子,”安塞尔莫说。“用你自己的刀吧。”姑娘在铁盘 子边上搁了四把叉,叉尖朝下。 大家直接从大铁食盘里拿东西吃,就象西斑牙人的习橱那 样,不说话。吃的是洋葱青椒烧兔肉,加红酒的调味汁里放着青 草,莱烧得不错,免肉烂得从骨头上掉了下来,调味汁很鲜美。罗 伯特·乔丹吃着,又喝了杯酒。姑娘一直在看他吃。其余的人 都望着自己的食物,只顾吃着。罗伯特·乔丹拿→片面包嶽干 净自己面前盘里利下的调味汁,把兔骨堆在一边,擦净底下的调 味汁,然后拿面包擦净叉和自已的刀,把刀裁起,再把面包吃掉。 他凑身前去,满满地舀了一杯酒,那姑娘还在望着他。 罗伯特·乔丹喝了半杯,可是等到向姑娘说话时,喉咙里又 哽塞起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巴勃罗听到他说话的声调,马上对 他瞥了一眼。接着他站起身走开了。 “玛丽亚。你呢?” 罗伯托。你在山里待了很久吗?” “三个月。” “三个月?”他望着她那又密又短的头发,她这时局促不安地 用手一捋,这头发就象山坡上的炭田在风中泛起竞浪那样波动 着。“头发给剃光了,”她说。“在瓦利阿多里德监狱里,按规矩都 得剃光头。三个月之后才长成这副样子。我那时也在火车上。 他们打算把我带到南方去。火车被炸之后,很多犯人又被逮住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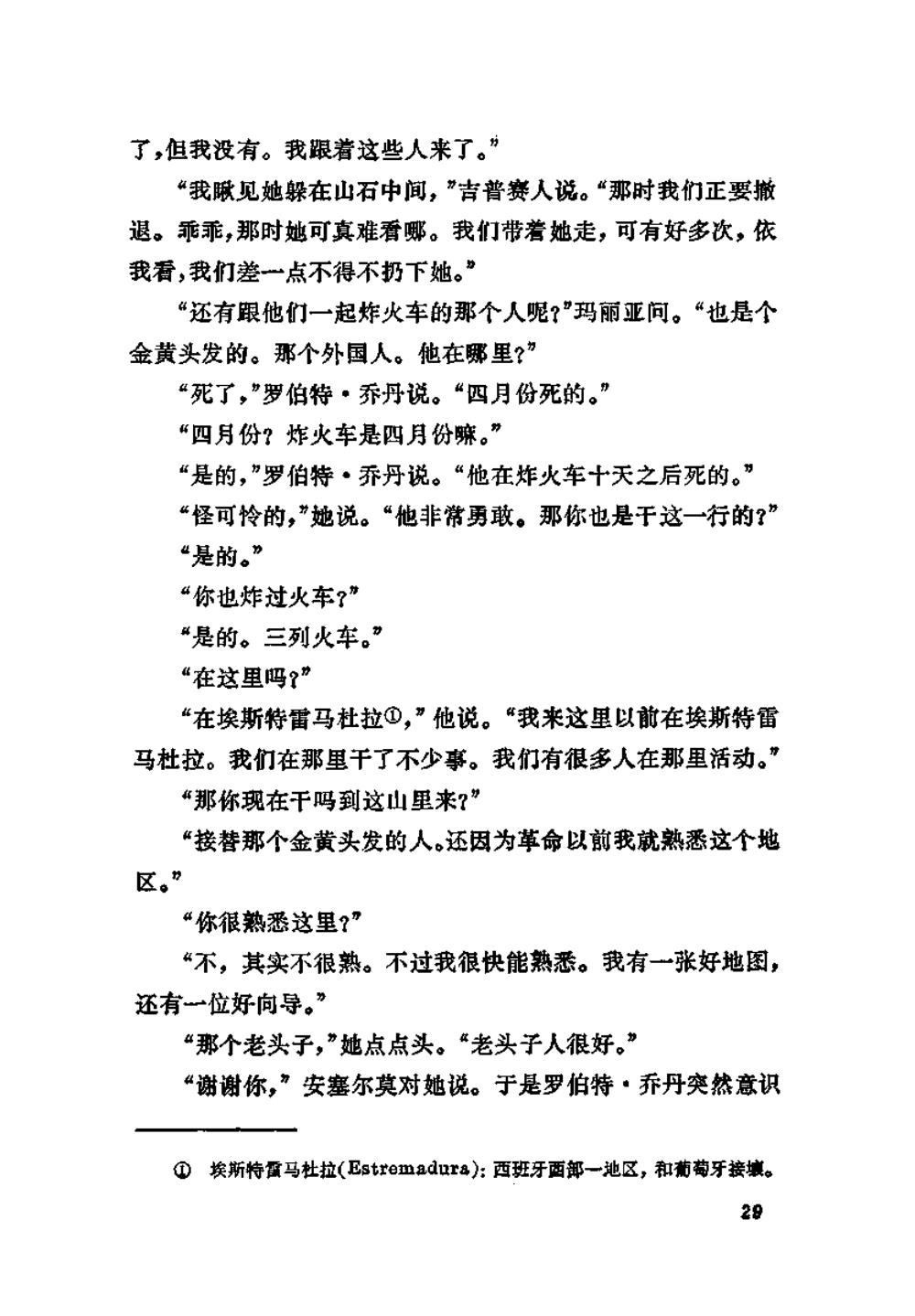
了,但我没有。我跟着这些人来了。” “我瞅见她躲在山石中间,”吉普赛人说。“那时我们正要撒 退。乖乖,那时她可真难看哪。我们带着她走,可有好多次,依 我看,我们差一点不得不扔下她。” “还有跟他们一起炸火车的那个人呢?”玛丽亚问。“也是个 金黄头发的。那个外国人。他在哪里?” “死了,”罗伯特·乔丹说。“四月份死的。” “四月份?炸火车是四月份嘛。”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他在炸火车十天之后死的。” “怪可怜的,”她说。“他非常勇敢。那你也是干这一行的?” “是的。” “你也炸过火车?” “是的。三列火车。” “在这里吗?” “在埃斯特雷马杜拉①,”他说。“我米这里以前在埃斯特雷 马杜拉。我们在那里千了不少事。我们有很多人在那里活动。” “那你现在干吗到这山里来?” 接替那个金黄头发的人。还因为革命以前我就熟悉这个地 区。” “你很熟悉这里?” “不,其实不很熟。不过我很快能熟悉。我有一张好地图, 还有一位好向导。” “那个老头子,”她点点头。“老头子人很好。” “谢谢你,”安塞尔莫对她说。于是罗伯特·乔丹突然意识 ①埃斯特瓶马杜拉(Estremadura):西班牙西部一地区,和葡萄牙接城。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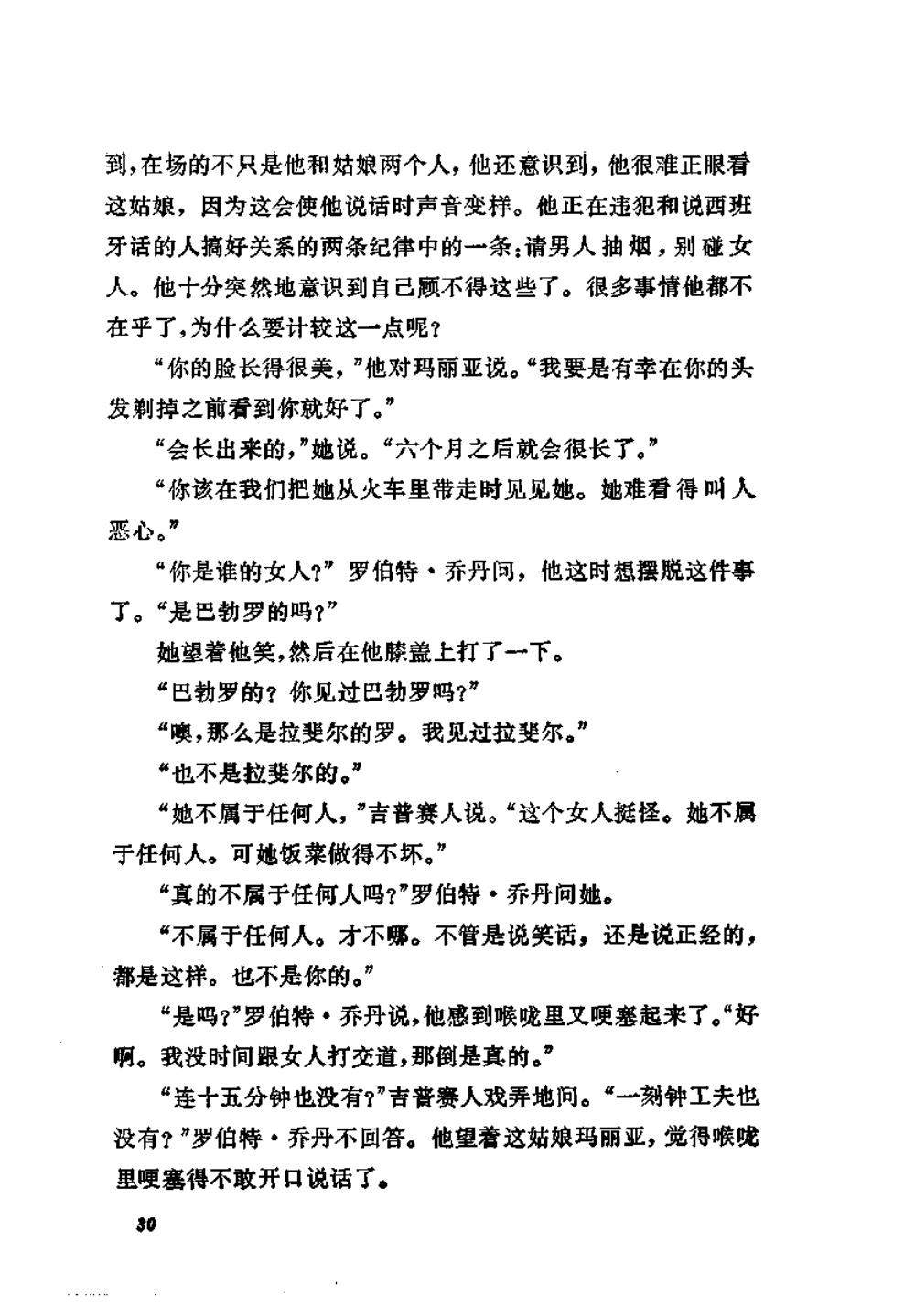
到,在场的不只是他和姑娘两个人,他还意识到,他很难正眼看 这姑娘,因为这会使他说话时声音变样。他正在违犯和说西班 牙话的人搞好关系的两条纪律中的一条:请男人抽烟,别碰女 人。他十分突然地意识到自己顾不得这些了。很多事情他都不 在乎了,为什么要计较这一点呢? “你的脸长得很美,”他对玛丽亚说。“我要是有幸在你的头 发剃掉之前看到你就好了。” “会长出来的,”她说。“六个月之后就会很长了,” “你该在我们把她从火车里带走时见见她。她难看得叫人 恶心。” “你是谁的女人?”罗伯特·乔丹问,他这时想摆脱这件事 了。“是巴勃罗的吗?” 她望着他笑,然后在他膝盖土打了一下。 “巴勃罗的?你见过巴勃罗吗?” “噢,那么是拉斐尔的罗。我见过拉斐尔。” “也不是拉斐尔的。” “她不属于任何人,”吉普赛人说。“这个女人挺怪。她不属 于任何人。可她饭菜做得不坏。” “真的不属于任何人吗?”罗伯特·乔丹问她。 “不属于任何人。才不哪。不管是说笑话,还是说正经的, 都是这样。也不是你的。” “是吗?”罗伯特·乔丹说,他感到喉咙里又哽塞起来了。“好 啊。我没时间跟女人打交道,那倒是真的。” “连十五分钟也没有?”吉普赛人戏手地问。“一刻钟工夫也 没有?”罗伯特·乔丹不回答。他望着这姑娘玛丽亚,觉得喉咙 里哽塞得不敢开口说话了。 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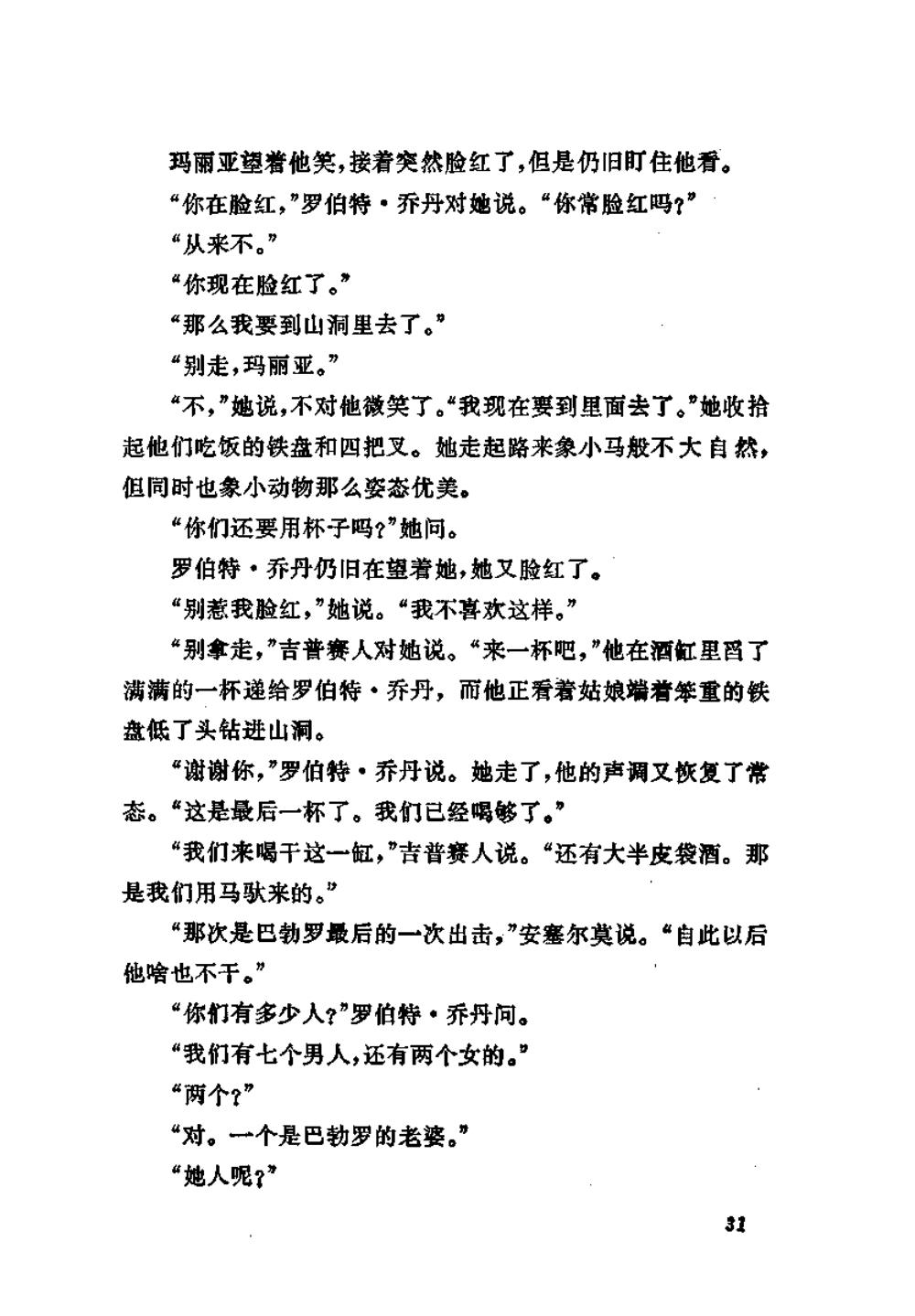
玛丽亚望着他笑,接着突然脸红了,但是仍引旧盯住他看。 “你在脸红,”罗伯特·乔丹对她说。“你常脸红吗?” “从来不。” “你现在脸红了。” “那么我要到山洞里去了。” “别走,玛丽亚。” “不,”她说,不对他微笑了。“我现在要到里面去了。”她收拾 起他们吃饭的铁盘和四把丈。她走起路来象小马般不大自然, 但同时也象小动物那么姿态优美。 “你们还要用杯子吗?”她问。 罗伯特·乔丹仍旧在望着她,她又脸红了。 “别惹我脸红,”她说。“我不喜欢这样。” “别拿走,”吉普赛人对她说。“来一杯吧,”他在酒缸里舀了 满满的一杯递给罗伯特·乔丹,而他正看着姑娘端着笨重的铁 盘低了头钻进山洞。 “谢谢你,”罗伯特·乔丹说。她走了,他的声调又恢复了常 态。“这是最后一杯了。我们已经喝够了。” “我们来喝干这一缸,”吉普赛人说。“还有大半皮袋酒。那 是我们用马欧来的。” “那次是巴勃罗最后的一次出击,”安塞尔莫说。“自此以后 他啥也不干。” “你们有多少人?”罗伯特·乔丹问。 “我们有七个男人,还有两个女的。” “两个?” “对。一个是巴勃罗的老婆。” “她人呢?”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