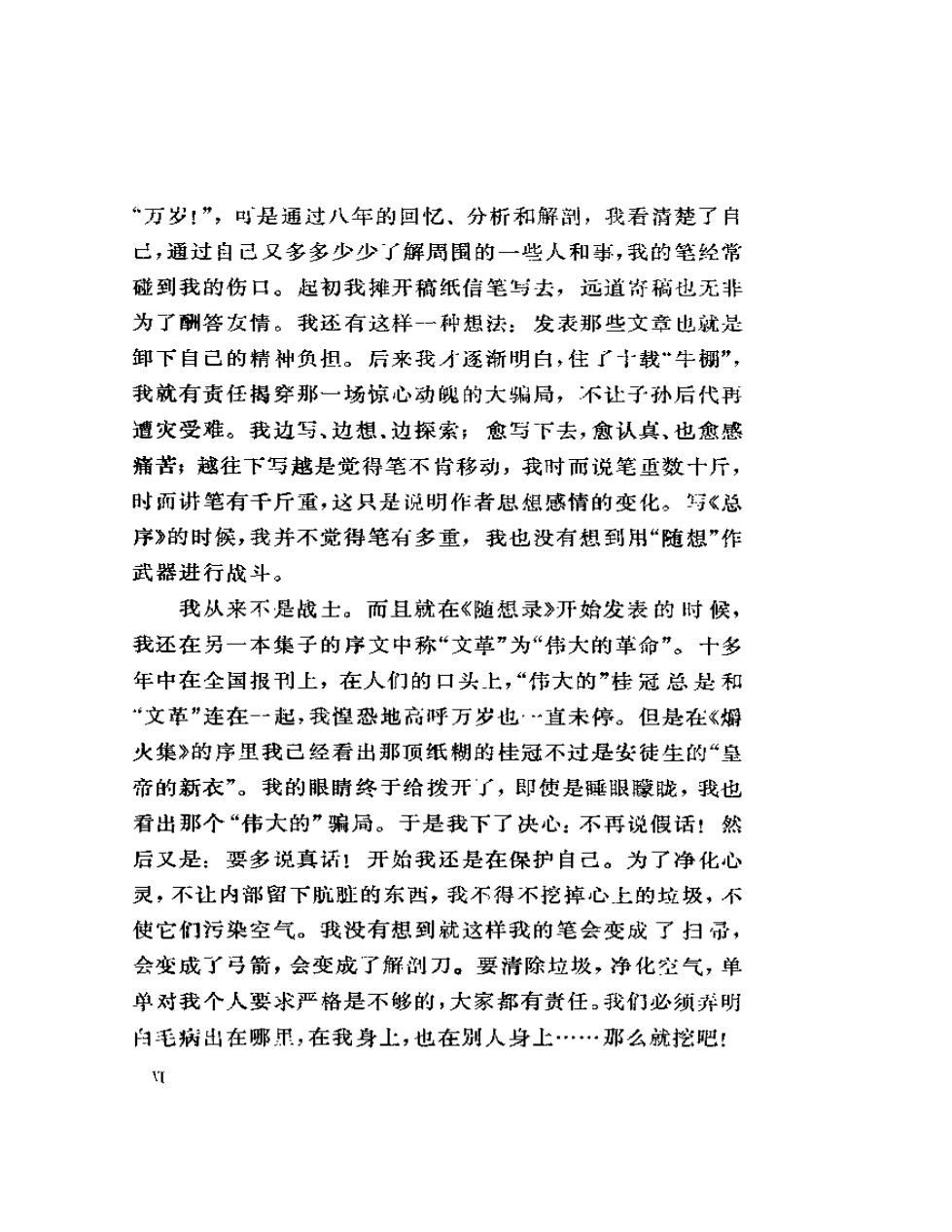
“万岁!”,是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请楚了月 已,通过自已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串,我的笔经常 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与去,远道寄稿也无非 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 卸下自己的精神负坦。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橱”, 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编局,不让子孙后代再 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 蒲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 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 序》的时候,我并不党得笔有多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作 武器进行战斗。 我从来不是战土。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 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佛大的革命”。十多 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 “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直未停。但是在《烟 火集》的序里我己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 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睡眼朦胧,我也 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 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 灵,不让内部留下航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 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 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腳刀。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 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弃明 白毛病出在哪罪,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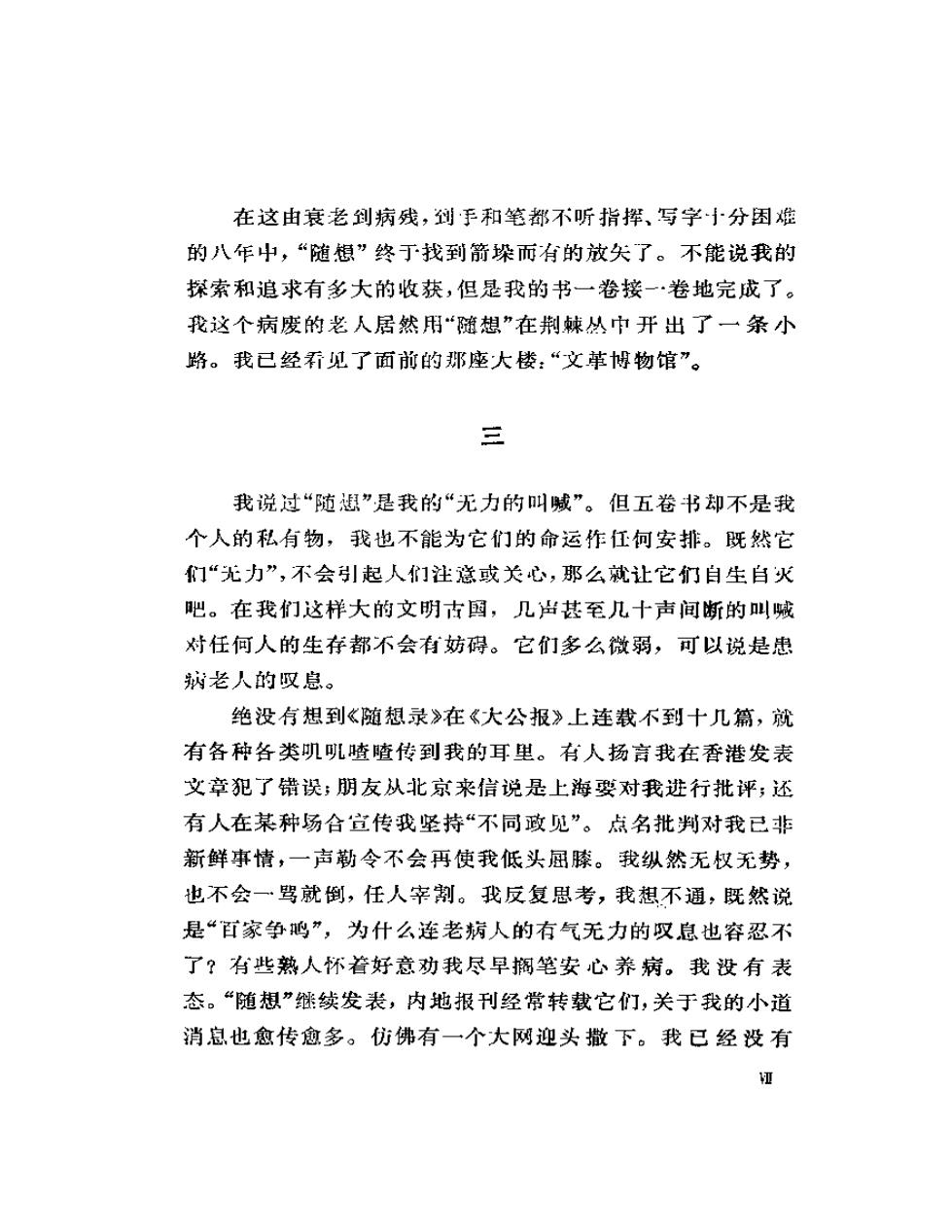
在这由衰老到病残,创乒和笔都不听指挥、写学分困強 的八作中,“随想”终丁找到箭垛而有的放矢了。不能说我的 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我的书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 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 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三 我说过“随思”是我的“无力的叫减”。但五卷书却不是我 个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为它们的命运作任钶安排。既然它 们“无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火 吧。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出基至儿十声间断的叫喊 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可以说是患 老人的叹息。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儿篇,就 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 义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 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 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 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说 是“百家争鸿”,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 了?有些熟人怀着好意劝我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我没有表 态。“随想”继续发表,内地报刊经常转载它们,关于我的小道 消息也愈传愈多。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 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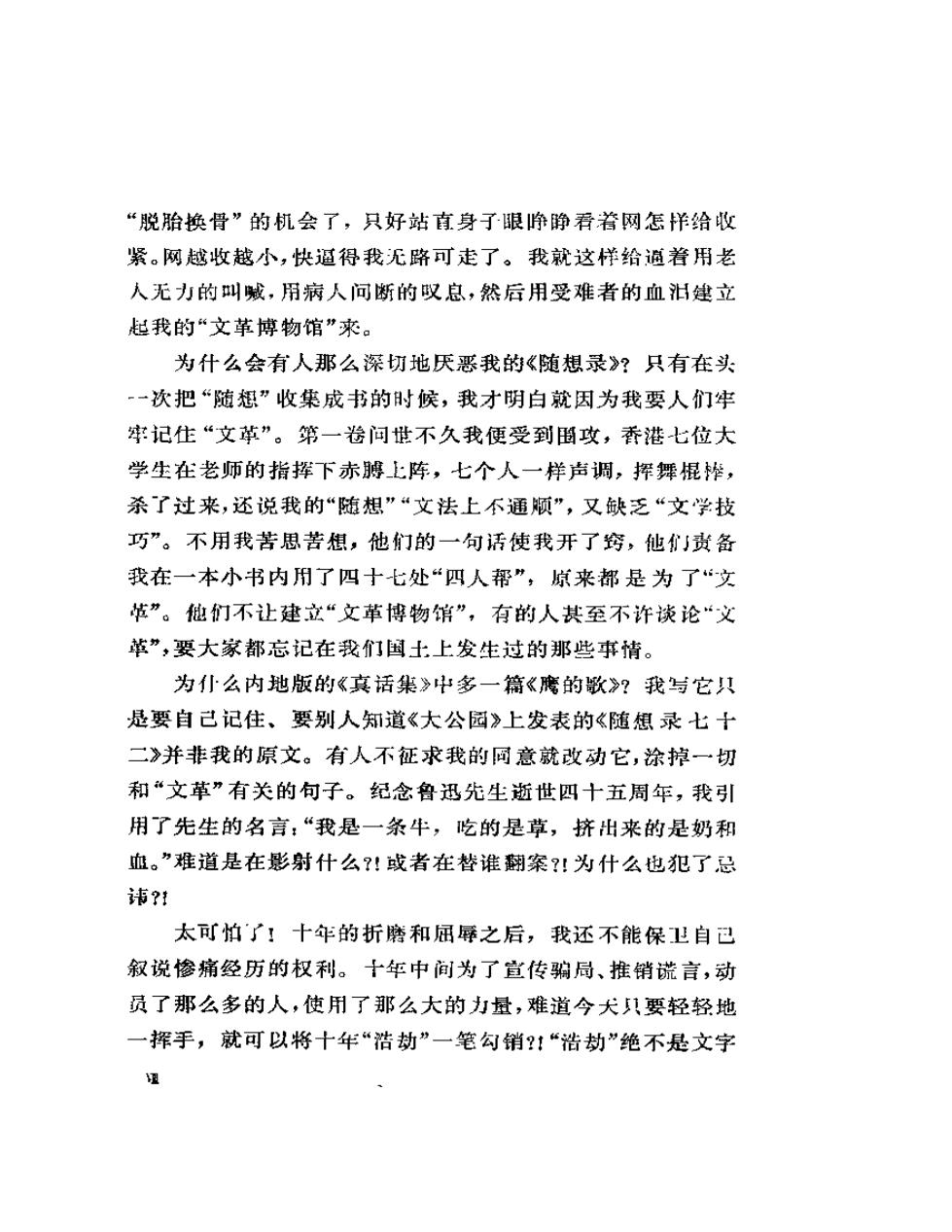
“脱胎换骨”的机会了,只好站直身了眼峥睁看着网怎样给收 紧。网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了。我就这样给遍着用老 天无力的叫贼,用病人问断的叹总,然后用受难者的血建立 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 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 牢记住“文革”。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固攻,香港七位大 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七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 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 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们的一句话使我开了窍,他贵备 我在一本小书内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惊来都是为了“文 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义 蜇”,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为升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贝 是要自已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 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 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 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 血。”难道是在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为什么也犯了忌 讳?1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已 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 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犬只要轻轻地 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绝不是文字 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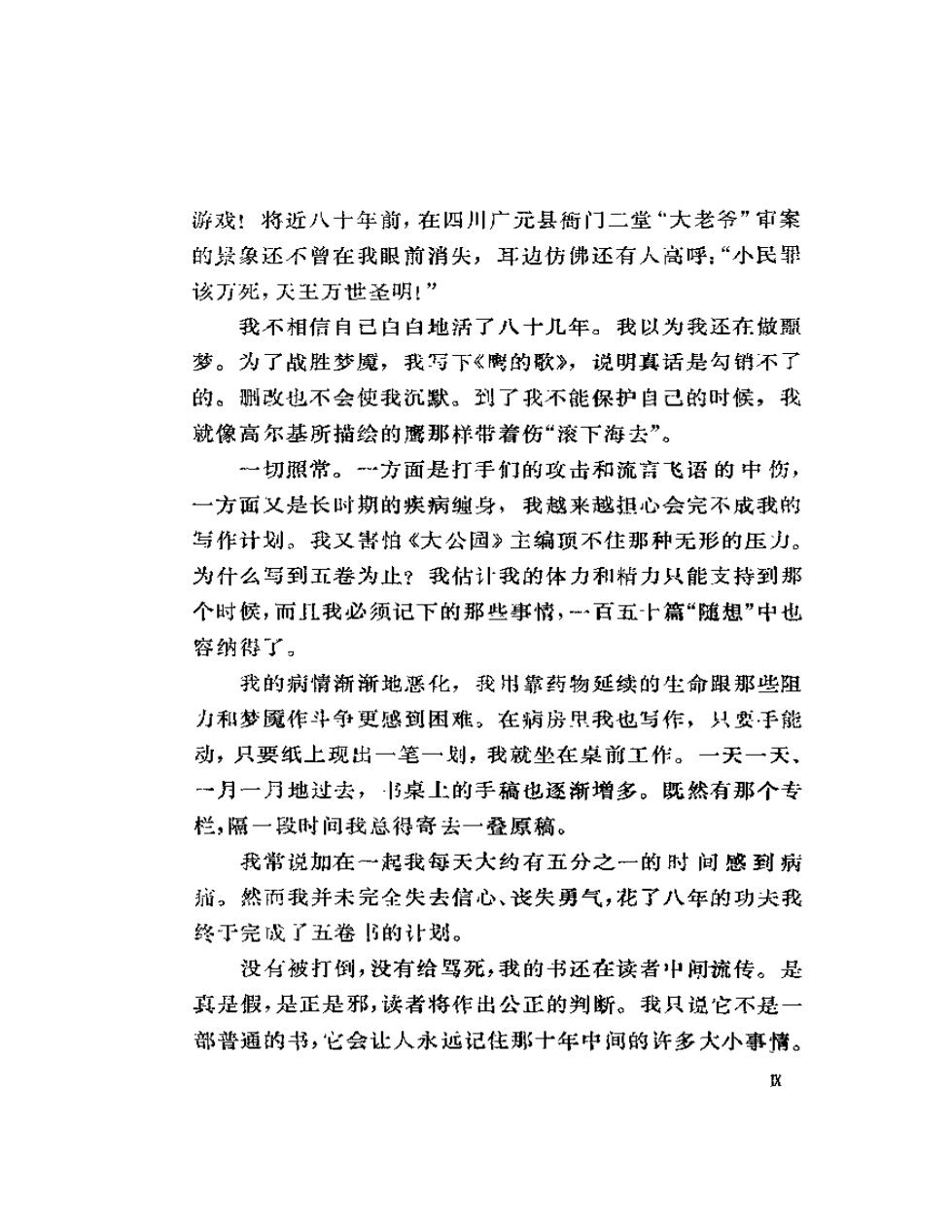
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 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尖,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 该万死,天王万世英明!” 我不相信自已白白地活了八十儿年。我以为我还在做 梦。为了战胜梦魇,我写下《牌的歌》,说明真话是勾销不了 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 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一切照常。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飞语的中伤, 一方面父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 与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 为什么写到五卷为止?我拈计我的体力刚精力只能支持到那 个时候,而几我必须记下的那些事情,一…百五上篇“随想”中也 容纳得了。 我的情渐渐地恶化,我州靠药物延续的生命跟那些阻 力和梦魇作半争更感到困难。在病房甲我也写作,只要手能 动,只要纸上现出一笔一划,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 一月一月地过去,桌上的手稿也逐渐增多。既然有那个专 栏,隔一段时间我总得寄去一叠原稿。 我常说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感到病 ⅷ。然而我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丧失勇气,北了八年的功夫我 终于完成了五卷的让划。 没有被打倒,没有给骂死,我的书还在读者中间流传。是 真是假,是正是邪,读者将作出公正的判断。我只说它不是一 部普通的书,它会让人永远记住那十年中间的许多大小事情。 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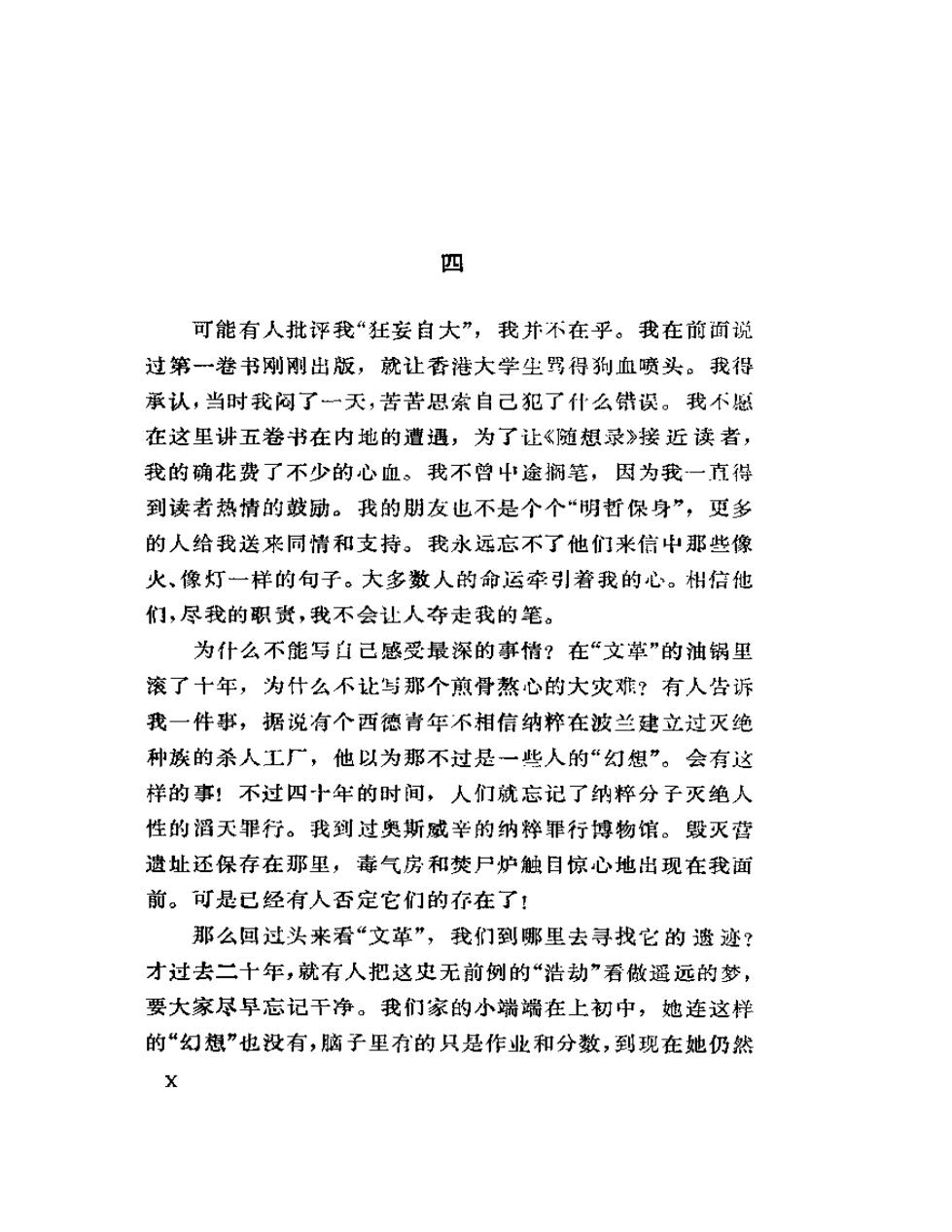
四 可能有人批评我“狂安自大”,我并不在乎。我在而面说 过第一卷书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我得 承认,当时我闷了一天,苦苦思索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不燃 在这里讲五卷书在内地的遭遇,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 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途搁笔,因为我一直得 到读者热情的鼓励。我的朋友也不是个个“明哲保身”,更多 的人给我送来同情和支持。我永远忘不了他来信中那些像 火、像灯一样的句子。大多数人的命运牵引着我的心。柑信他 们,尽我的职贵,我不会让人夺走我的笔。 为什么不能写白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 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 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 种族的杀人工,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 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 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 遗址还保存在那里,毒气房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 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1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 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 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 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