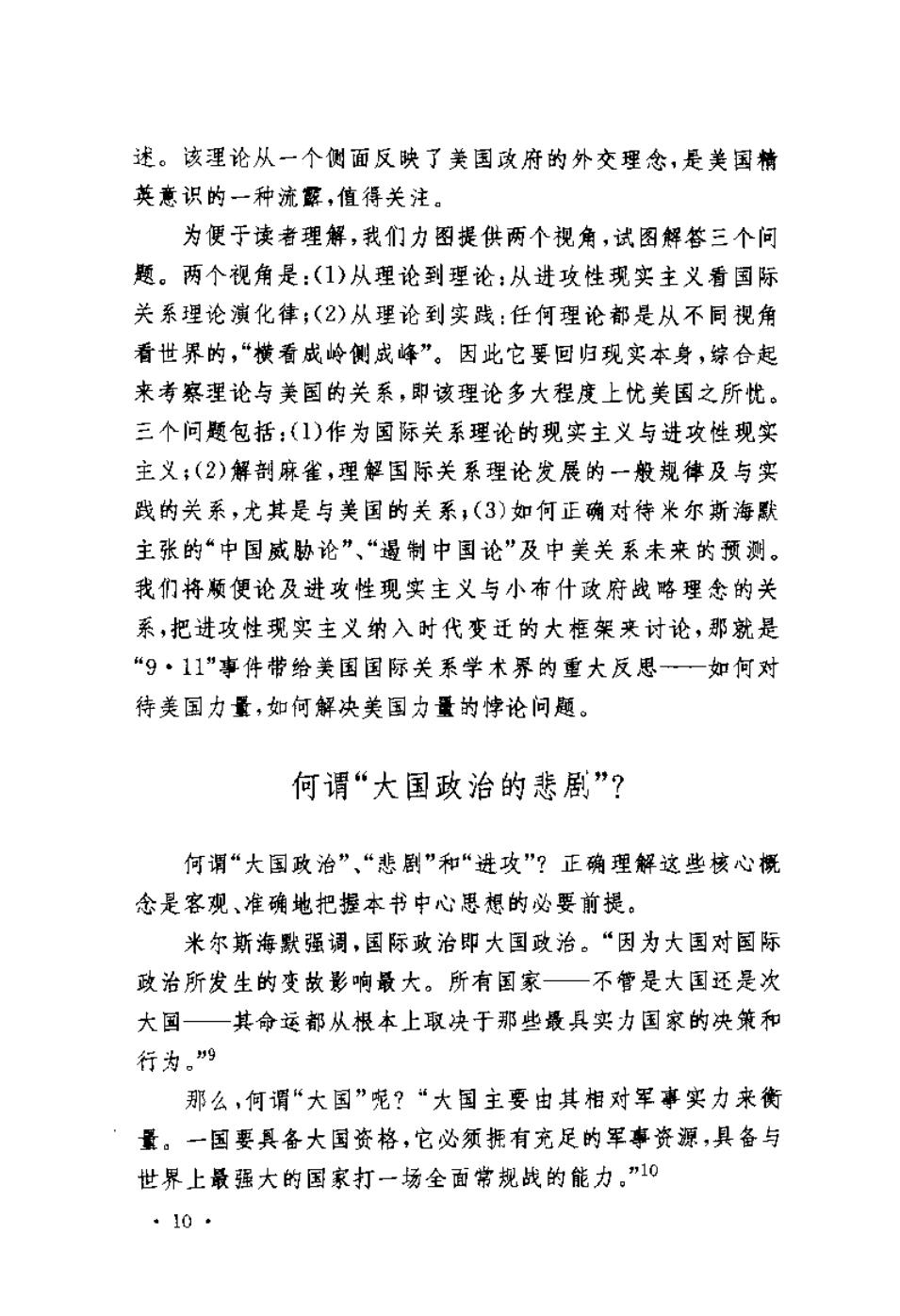
述。该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是美国精 英意识的一种流露,值得关注。 为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力图提供两个视角,试图解答三个问 题。两个视角是:(1)从理论到理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看国际 关系理论演化律;(2)从理论到实践:任何理论都是从不同视角 看世界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因此它要回归现实本身,综合起 来考察理论与美国的关系,即该理论多大程度上忧美国之所忧。 三个问题包括:(1)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 主义:(2)解剖麻雀,理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及与实 践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3)如何正确对待米尔斯海默 主张的“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及中美关系未来的预测。 我们将顺便论及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小布什政府战略理念的关 系,把进攻性现实主义纳入时代变迁的大框架夹讨论,那就是 “9·11”事件带给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重大反思一一如何对 待美国力量,如何解决美国力量的悖论问题。 何谓“大国政治的悲”? 何谓“大国政治”、“悲剧”和“进攻”?正确理解这些核心概 念是客观、准确地把握本书中心思想的必要前提。 米尔斯海默强调,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 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一不管是大国还是次 大国一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 行为。9 那么,何谓“大国”呢?“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 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瓶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10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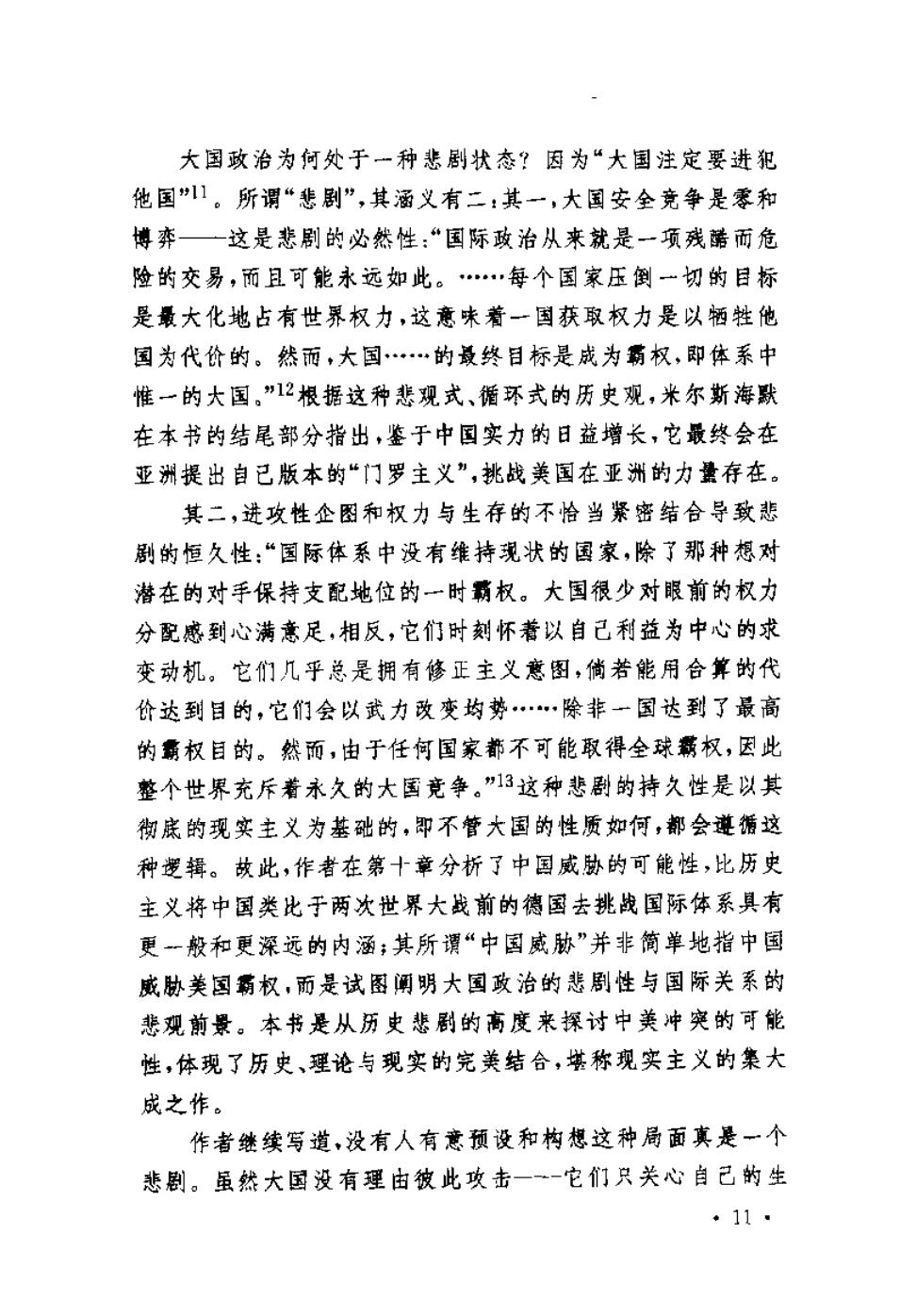
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 他国。所谓“悲剧”,其涵义有二:其一,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 博奔一这是悲剧的必然性:“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蒲而危 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 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 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即体系中 惟一的大国,”12根据这种悲观式、循环式的历史观,米尔斯海默 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指出,鉴于中国实力的日益增长,它最终会在 亚洲提出自已版本的“门罗主义”,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力囊存在。 其二,进攻性企图和权力与生存的不恰当紧密结合导致悲 剧的恒久性:“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 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精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 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 变动机。它们儿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 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 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薪权,因此 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13这种悲剧的持久性是以其 御底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即不管大国的性质如何,都会遵循这 种逻辑。故此,作者在第十章分析了中国威胁的可能性,比历史 主义将中国类比于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去挑战国际体系具有 更一般和更深远的内涵;其所谓“中国威胁”并非简单地指中国 威胁美国菊权,而是试图阐明大国政治的悲剧性与国际关系的 悲观前景。本书是从历史悲剧的高度来探讨中美冲突的可能 性,体现了历史、理论与现实的完美结合,基称现实主义的集大 成之作。 作者继续写道,没有人有意预设和构想这种局面真是一个 悲剧。虽然大国没有理由彼此攻击一一-它们只关心自己的生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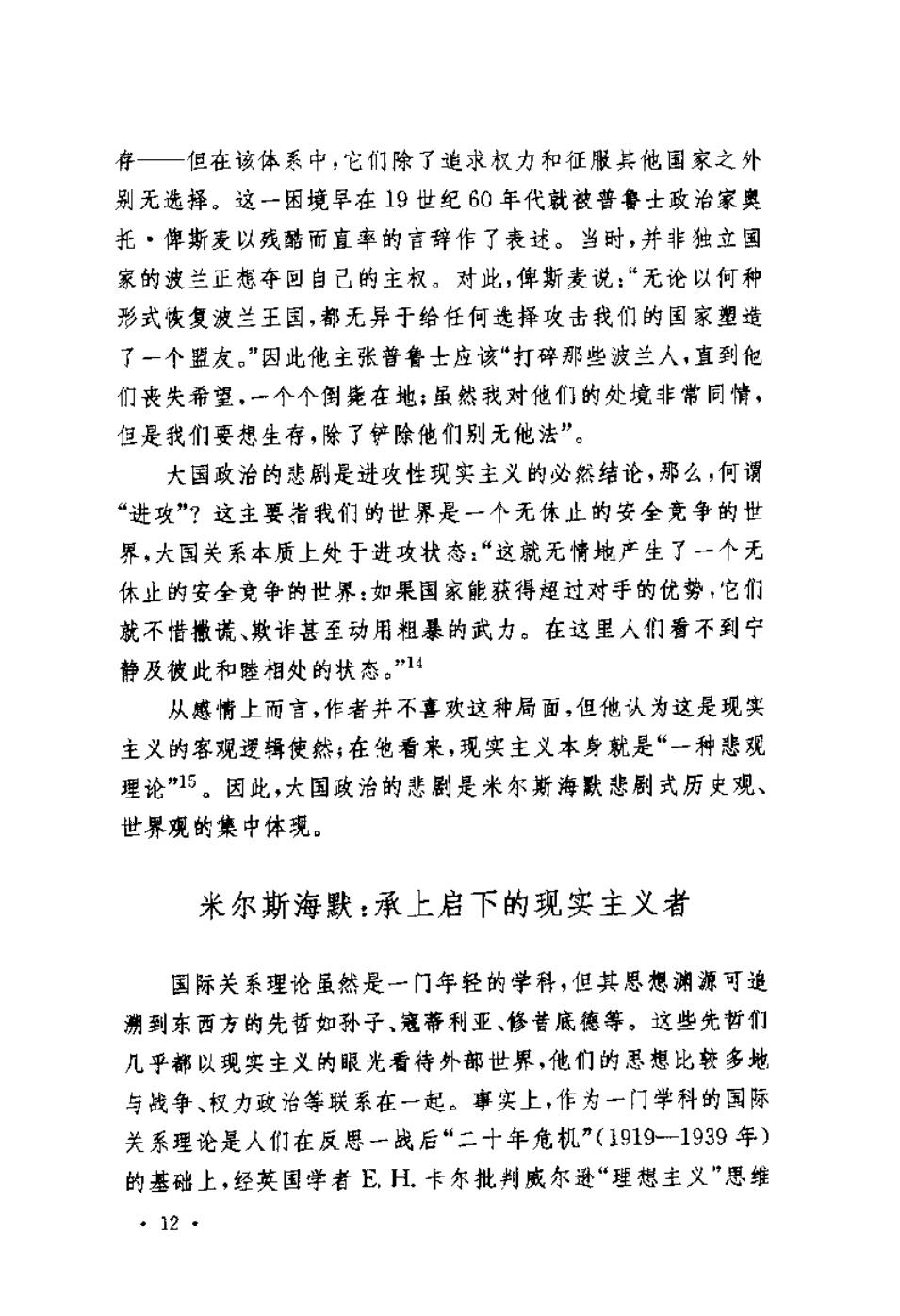
存一但在该体系中,它们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 别无选择。这一困境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被普鲁士政治家奥 托·俾斯麦以残酷而直率的言辞作了表述。当时,并非独立国 家的波兰正卷夺回自己的主权。对此,俾斯麦说:“无论以何种 形式恢复波兰王国,都无异于给任何选择攻击我们的国家塑造 了一个盟友。”因此他主张普鲁士应该“打碎那些波兰人,直到他 们丧失希望,一个个倒毙在地;虽然我对他们的处境非常同情, 但是我们要想生存,除了铲除他们别无他法”。 大国政治的悲剧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必然结论,那么,何谓 “进攻”?这主要指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无休止的安全竟争的世 界,大国关系本质上处于进攻状态:“这就无情地产生了一个无 休业的安全竟争的世界:如果国家能获得超过对手的优势,它们 就不惜撒谎、欺诈甚至动用粗暴的武力。在这里人们看不到宁 静及彼此和睦相处的状态。”14 从感情上而言,作者并不喜欢这种局面,但他认为这是现实 主义的客观逻辑使然;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悲观 理论15。因此,大国政治的悲剧是米尔斯海默悲剧式历史观、 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米尔斯海默:承上启下的现实主义者 国际关系理论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其思想渊源可追 湖到东西方的先哲如孙子、寇蒂利亚、修昔底德等。这些先哲们 几乎都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他们的思想比较多地 与战争、权力政治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 关系理论是人们在反思一战后“二十年危机”(1919-1939年) 的基础上,经英国学者E,H.卡尔批判威尔逊“理想主义”思维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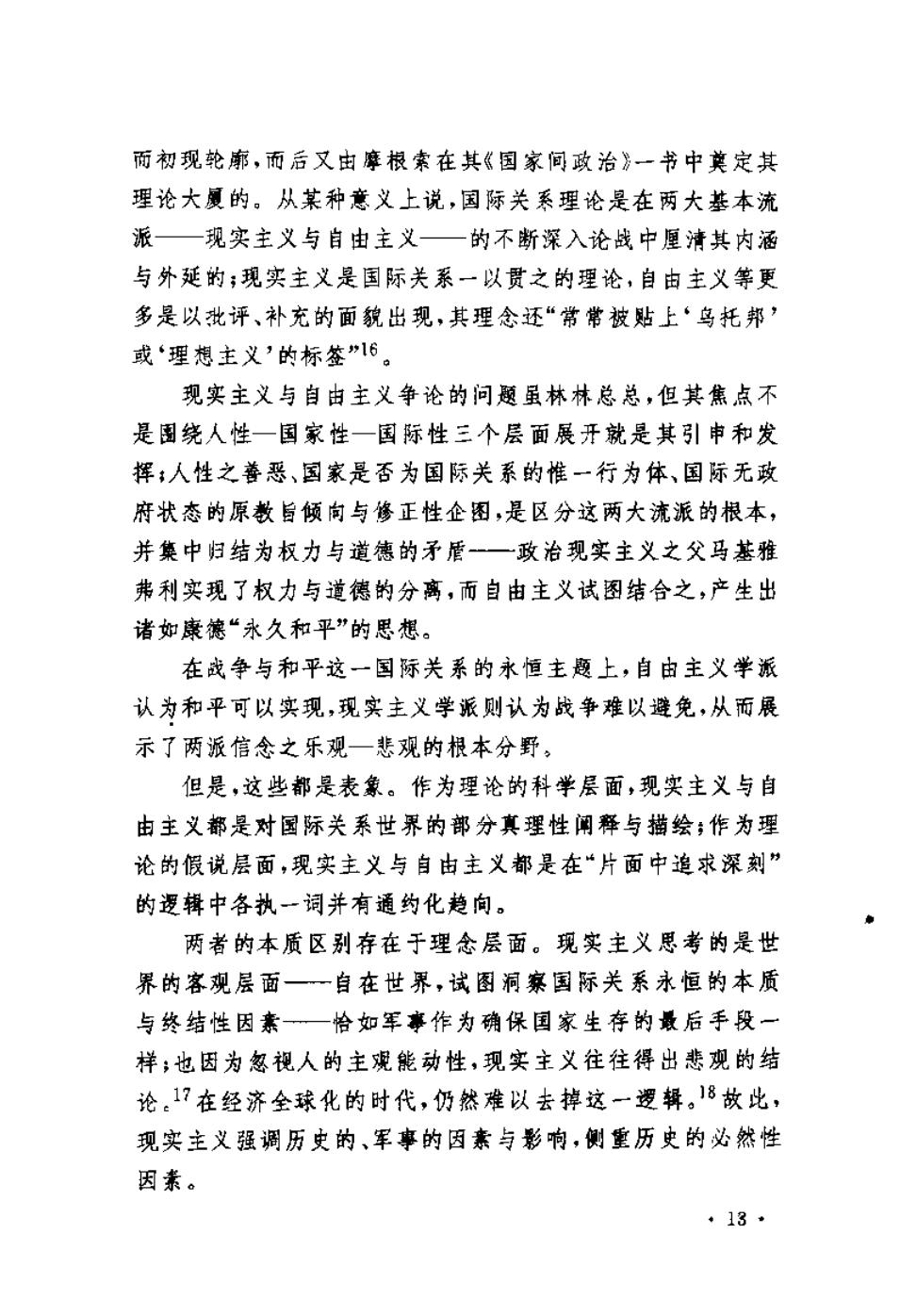
而初现轮廓,而后又由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奠定其 理论大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两大基本流 派—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一的不断深入论战中厘清其内涵 与外延的;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一以贯之的理论,自由主义等更 多是以批评、补充的面貌出现,其理念还“常常被贴上‘鸟托邦’ 或‘理想主义’的标签”16。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问题虽林林总总,但其焦点不 是围绕人性一国家性一国际性三个层面展开就是其引申和发 挥;人性之善恶、国家是否为国际关系的惟一行为体、国际无政 府状态的原教旨倾向与修正性企图,是区分这两大流派的根本, 并集中归结为权力与道德的矛唐一政治现实主义之父马基雅 弗利实现了权力与道德的分离,而自由主义试图结合之,产生出 诸如康德“永久和平”的思想。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上,自由主义学派 认为和平可以实现,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战争难以避免,从而展 示了两派信念之乐观一悲观的根本分野。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作为理论的科学层面,现实主义与自 由主义都是对国际关系世界的部分真理性阐释与描绘:作为理 论的假说层面,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在“片面中追求深刻” 的逻辑中各执一词并有通约化趋向。 两者的本质区别存在于理念层面。现实主义思考的是世 界的客观层面一一自在世界,试图洞察国际关系永恒的本质 与终结性因素一恰如军事作为确保国家生存的最后手段一 样;也因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现实主义往往得出悲观的结 论1?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仍然难以去掉这一逻辑。18故此, 现实主义强调历史的、军事的因素与影响,侧重历史的必然性 因素。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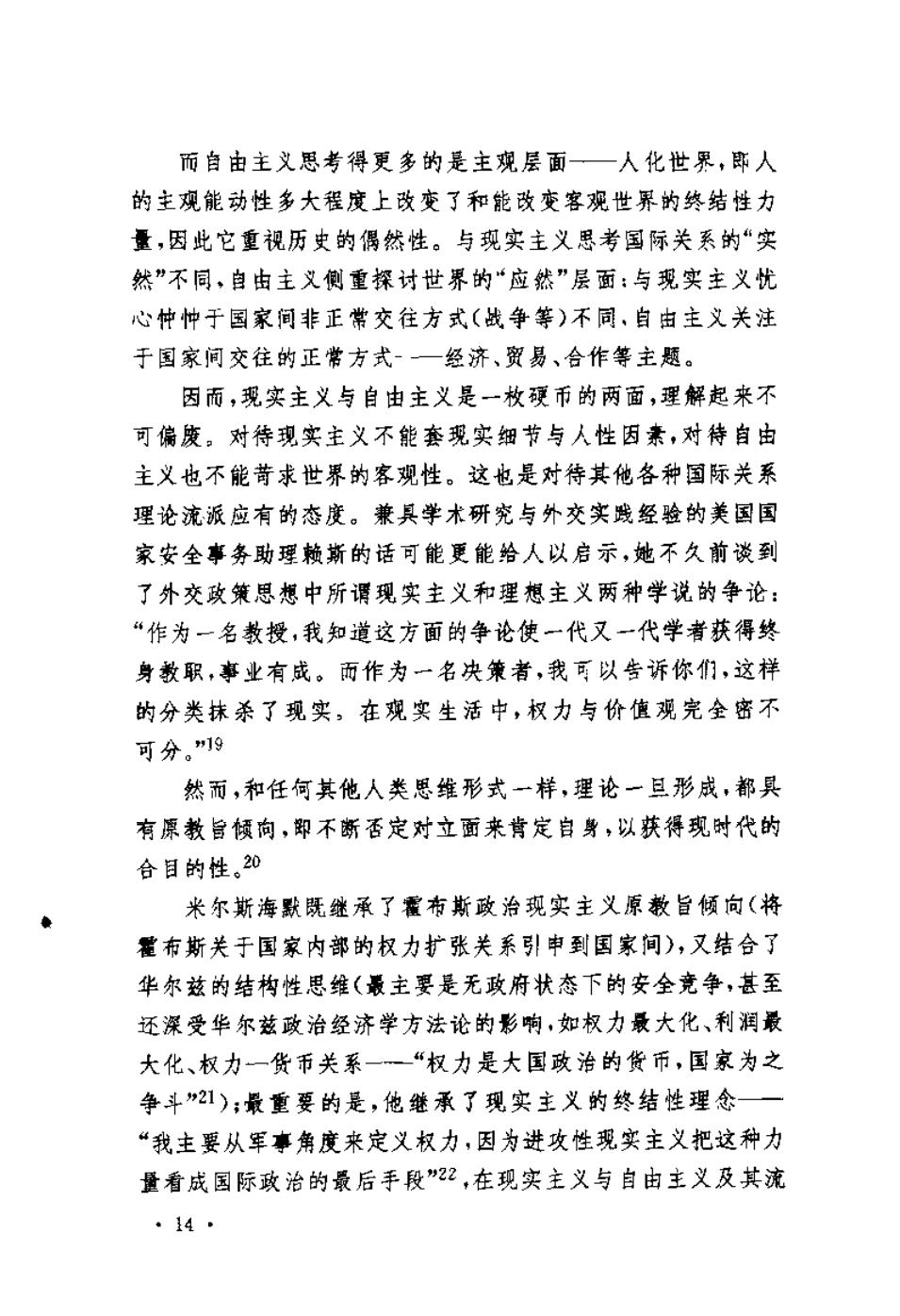
而自由主义思考得更多的是主观层面一人化世界,郎人 的主观能动性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和能改变客观世界的终结性力 量,因此它重视历史的偶然性。与现实主义思考国际关系的“实 然”不同,自由主义侧重探讨世界的“应然”层面:与现实主义忧 心忡忡于国家间非正常交往方式(战争等)不同、自由主义关注 于国家间交往的正常方式一经济、贸易、合作等主题。 因而,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理解起来不 可偏废。对待现实主义不能套现实细节与人性因素,对待自由 主义也不能苛求世界的客观性。这也是对待其他各种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应有的态度。兼具学术研究与外交实践经验的美国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的话可能更能给人以启示,她不久前谈到 了外交政策思想中所谓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学说的争论: “作为一名教授,我知道这方面的争论使一代又一代学者获得终 身教职,事业有成。而作为一名决策者,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 的分类抹杀了现实,在观实生活中,权力与价值观完全密不 可分。”]9 然而,和任何其他人类思维形式一样,理论一旦形成,都具 有原教言倾向,即不断否定对立面来肯定自身,以获得现时代的 合目的性。20 米尔斯海默既继承了霍市斯政治现实主义原教旨倾向(将 霍布斯关于国家内部的权力扩张关系引申到国家间),又结合了 华尔兹的结构性思维(最主要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竞争,甚至 还深受华尔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如权力最大化、利润最 大化、权力一货币关系一一“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京为之 争斗”21):最重要的是,他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终结性理念一一 “我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把这种力 量看成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22,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及其流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