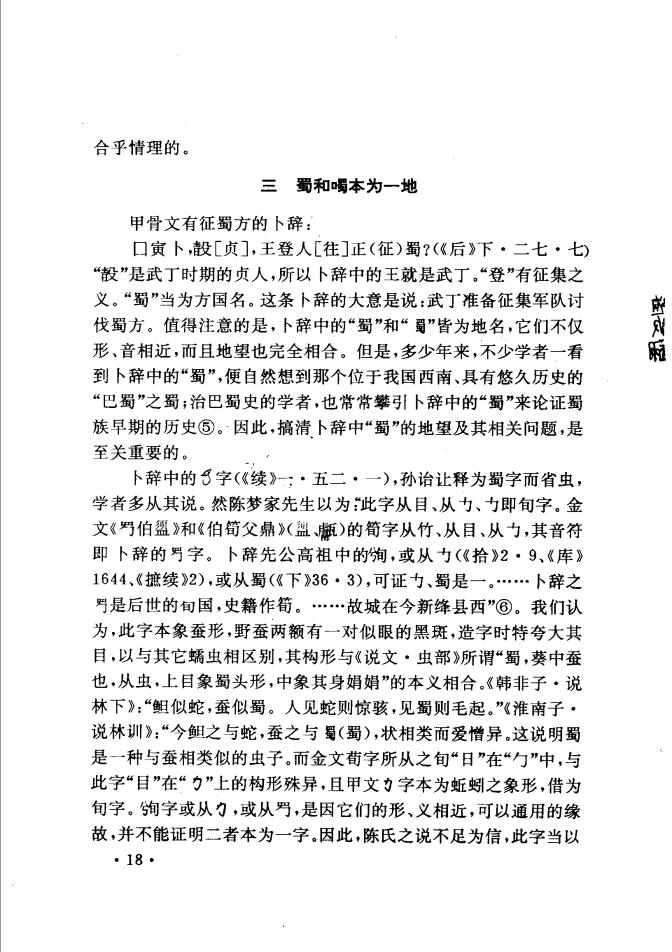
合乎情理的。 三 蜀和喝本为一地 甲骨文有征蜀方的卜辞: 口寅卜,轂[贞],王登人[往]正(征)蜀?(《后》下·二七·七) “設”是武丁时期的贞人,所以卜辞中的王就是武丁,“登”有征集之 义。“蜀”当为方国名。这条卜辞的大意是说:武丁准备征集军队讨 伐蜀方。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的“蜀”和“蜀”皆为地名,它们不仅 形、音相近,而且地望也完全相合。但是,多少年来,不少学者一看 到卜辞中的“蜀”,便自然想到那个位于我国西南、具有悠久历史的 “巴蜀”之蜀;治巴蜀史的学者,也常常攀引卜辞中的“蜀”来论证蜀 族早期的历史⑤。因此,搞清卜辞中“蜀”的地望及其相关问题,是 至关重要的。 卜辞中的8字(《续》:·五二·一),孙诒让释为蜀字而省虫, 学者多从其说。然陈梦家先生以为:此字从目、从力、力即旬字。金 文《男伯蕴》和《伯筍父鼎》(盟期)的筍字从竹、从目、从力,其音符 即辞的号字。卜辞先公高祖中的询,或从力(《拾》2·9、《库》 1644、《摭续》2),或从蜀(《下》36·3),可证力、蜀是一。…卜辞之 男是后世的旬国,史籍作筍。…故城在今新绛县西”⑥。我们认 为,此字本象蚕形,野蚕两额有一对似眼的黑斑,造字时特夸大其 目,以与其它蠕虫相区别,其构形与《说文·虫部》所谓“蜀,葵中蚕 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娟娟”的本义相合。《韩非子·说 林下》:“鲤似蛇,蚕似蜀。人见蛇则惊骇,见蜀则毛起。”《准南子· 说林训》:“今触之与蛇,蚕之与蜀(蜀),状相类而爱憎异,这说明蜀 是一种与蚕相类似的虫子。而金文荀字所从之旬“日”在“勹”中,与 此字“目”在“力”上的构形殊异,且甲文力字本为蚯蚓之象形,借为 旬字。询字或从力,或从男,是因它们的形、义相近,可以通用的缘 故,并不能证明二者本为一字,因此,陈氏之说不足为信,此字当以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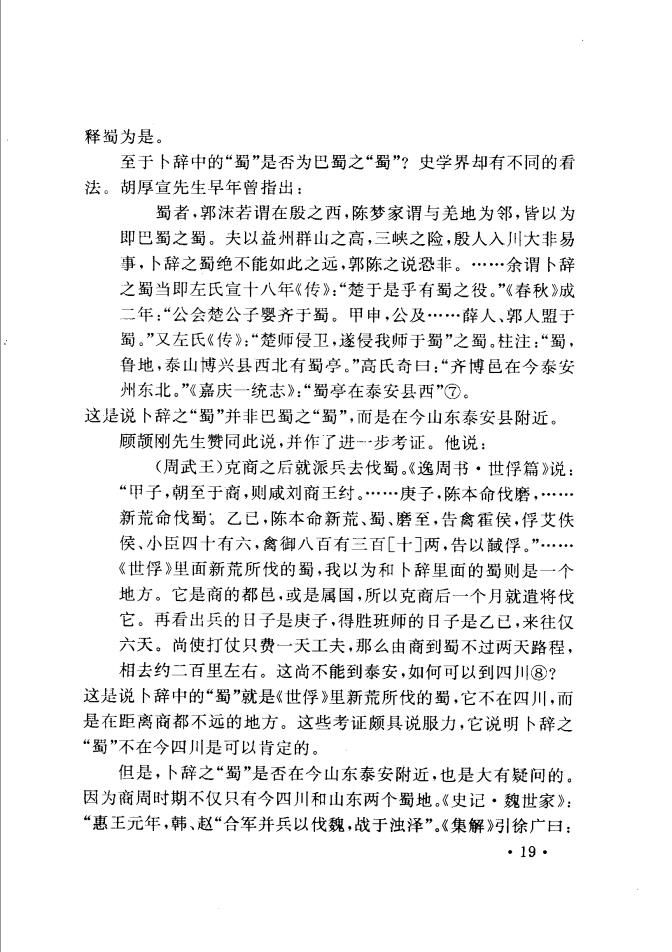
释蜀为是。 至于卜辞中的“蜀”是否为巴蜀之“蜀”?史学界却有不同的看 法。胡厚宣先生早年曾指出: 蜀者,郭沫若谓在殷之西,陈梦家谓与羌地为邻,皆以为 即巴蜀之蜀。夫以益州群山之高,三峡之险,殷人入川大非易 事,卜辞之蜀绝不能如此之远,郭陈之说恐非。…余谓卜辞 之蜀当即左氏宣十八年《传》:“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春秋》成 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甲申,公及…薛人、郭人盟于 蜀。”又左氏《传》:“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之蜀。柱注:“蜀, 鲁地,泰山博兴县西北有蜀亭。”高氏奇日:“齐博邑在今泰安 州东北。”《嘉庆一统志》:“蜀亭在泰安县西”⑦。 这是说卜辞之“蜀”并非巴蜀之“蜀”,而是在今山东泰安县附近。 顾颉刚先生赞同此说,并作了进-步考证。他说: (周武王)克商之后就派兵去伐蜀。《逸周书·世俘篇》说: “甲子,朝至于商,则咸刘商王纣。…庚子,陈本命伐磨,… 新荒命伐蜀。乙已,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 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十]两,告以馘俘。”… 《世俘》里面新荒所伐的蜀,我以为和卜辞里面的蜀则是一个 地方。它是商的都邑,或是属国,所以克商后一个月就遣将伐 它。再看出兵的日子是庚子,得胜班师的日子是乙已,来往仅 六天。尚使打仗只费一天工夫,那么由商到蜀不过两天路程, 相去约二百里左右。这尚不能到泰安,如何可以到四川⑧? 这是说卜辞中的“蜀”就是《世俘》里新荒所伐的蜀,它不在四川,而 是在距离商都不远的地方。这些考证颇具说服力,它说明卜辞之 “蜀”不在今四川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卜辞之“蜀”是否在今山东泰安附近,也是大有疑问的。 因为商周时期不仅只有今四川和山东两个蜀地,《史记·魏世家》: “惠王元年,韩、赵“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集解》引徐广日: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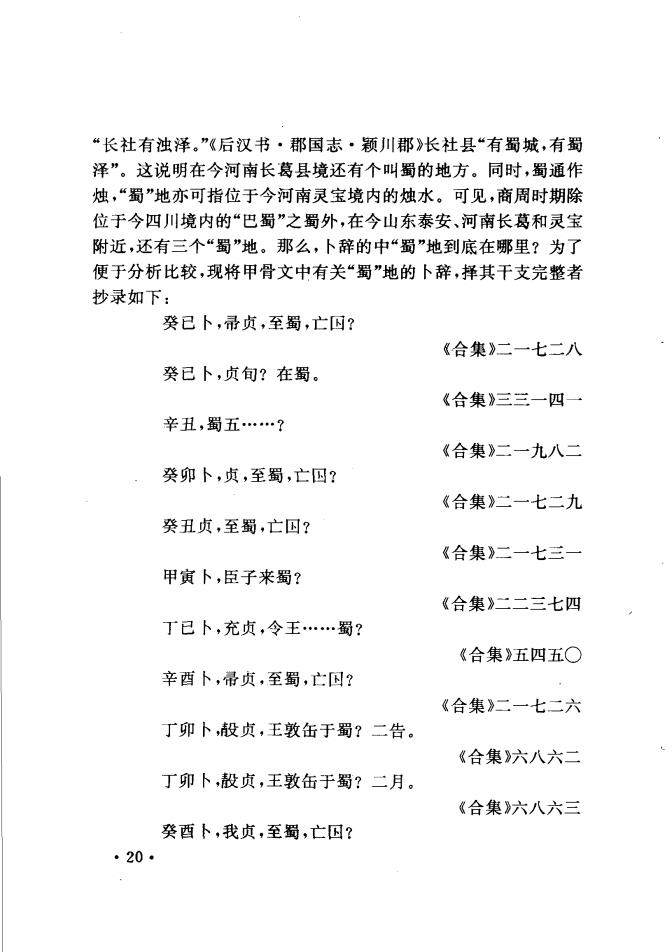
“长社有浊泽。”《后汉书·郡国志·颖川郡》长社县“有蜀城,有蜀 泽”。这说明在今河南长葛县境还有个叫蜀的地方。同时,蜀通作 烛,“蜀”地亦可指位于今河南灵宝境内的烛水。可见,商周时期除 位于今四川境内的“巴蜀”之蜀外,在今山东泰安、河南长葛和灵宝 附近,还有三个“蜀”地。那么,卜辞的中“蜀”地到底在哪里?为了 便于分析比较,现将甲骨文中有关“蜀”地的卜辞,择其干支完整者 抄录如下: 癸已卜,帚贞,至蜀,亡囚? 《合集》二一七二八 癸已卜,贞旬?在蜀。 《合集》三三一四一 辛丑,蜀五…? 《合集》二一九八二 癸卯卜,贞,至蜀,亡囚? 《合集》二一七二九 癸丑贞,至蜀,亡国? 《合集》二一七三一 甲寅卜,臣子来蜀? 《合集》二二三七四 丁已卜,充贞,令王…蜀? 《合集》五四五○ 辛酉卜,帚贞,至蜀,亡因? 《合集》二一七二六 丁卯卜,极贞,王敦缶于蜀?二告。 《合集》六八六二 丁卯卜,极贞,王敦缶于蜀?二月。 《合集》六八六三 癸酉卜,我贞,至蜀,亡囚?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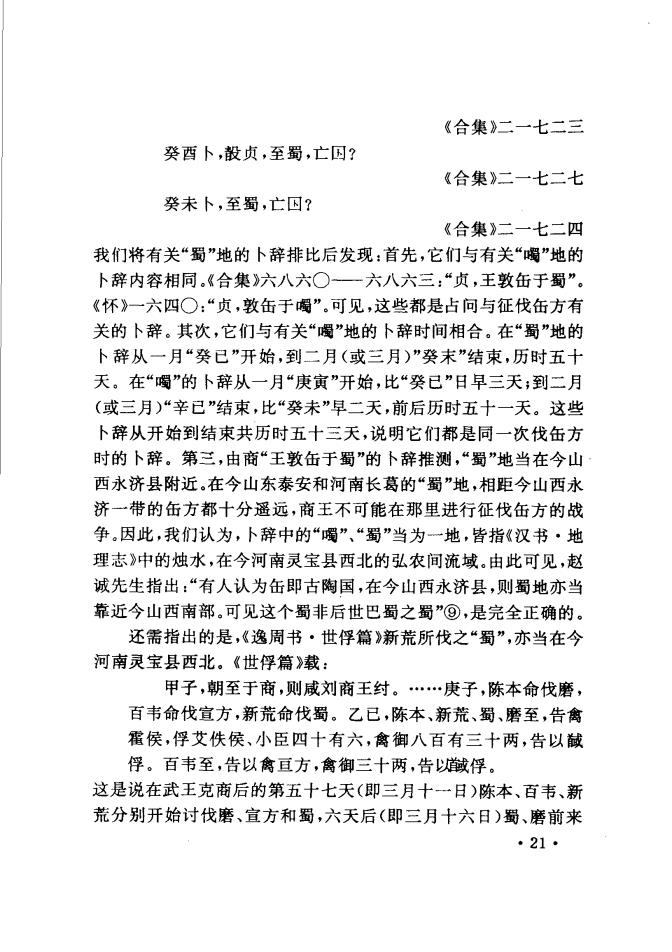
《合集》二一七二三 癸酉卜,設贞,至蜀,亡国? 《合集》二一七二七 癸未卜,至蜀,亡囚? 《合集》二一七二四 我们将有关“蜀”地的卜辞排比后发现:首先,它们与有关“嚼”地的 卜辞内容相同。《合集》六八六○一一六八六三:“贞,王敦缶于蜀”。 《怀》一六四○:“贞,敦缶于喝”。可见,这些都是占问与征伐缶方有 关的卜辞。其次,它们与有关“喝”地的卜辞时间相合。在“蜀”地的 卜辞从一月“癸已”开始,到二月(或三月)”癸末”结束,历时五十 天。在“喝”的卜辞从一月“庚寅”开始,比“癸已”日早三天;到二月 (或三月)“辛已”结束,比“癸未”早二天,前后历时五十一天。这些 卜辞从开始到结束共历时五十三天,说明它们都是同一次伐缶方 时的卜辞。第三,由商“王敦缶于蜀”的卜辞推测,“蜀”地当在今山 西永济县附近。在今山东泰安和河南长葛的“蜀”地,相距今山西永 济一带的缶方都十分遥远,商王不可能在那里进行征伐缶方的战 争。因此,我们认为,卜辞中的“嗳”、“蜀”当为一地,皆指《汉书·地 理志》中的烛水,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北的弘农间流域。由此可见,赵 诚先生指出:“有人认为缶即古陶国,在今山西永济县,则蜀地亦当 靠近今山西南部。可见这个蜀非后世巴蜀之蜀”⑨,是完全正确的。 还需指出的是,《逸周书·世俘篇》新荒所伐之“蜀”,亦当在今 河南灵宝县西北。《世俘篇》载: 甲子,朝至于商,则咸刘商王纣。…庚子,陈本命伐磨, 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已,陈本、新荒、蜀、磨至,告禽 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十两,告以馘 俘。百韦至,告以腐亘方,禽御三十两,告馘俘。 这是说在武王克商后的第五十七天(即三月十一日)陈本、百韦、新 荒分别开始讨伐磨、宣方和蜀,六天后(即三月十六日)蜀、磨前来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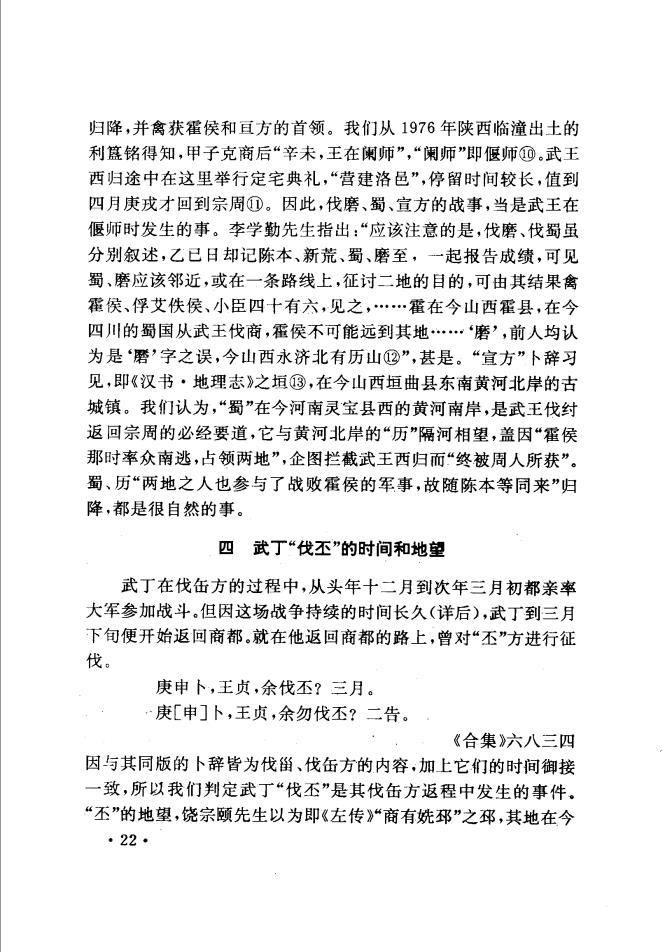
归降,并禽获霍侯和亘方的首领。我们从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 利簋铭得知,甲子克商后“辛未,王在阑师”,“阑师”即偃师©。武王 西归途中在这里举行定宅典礼,“营建洛邑”,停留时间较长,值到 四月庚戎才回到宗周①。因此,伐磨、蜀、宣方的战事,当是武王在 偃师时发生的事。李学勤先生指出:“应该注意的是,伐磨、伐蜀虽 分别叙述,乙已日却记陈本、新荒、蜀、磨至,一起报告成绩,可见 蜀、磨应该邻近,或在一条路线上,征讨二地的目的,可由其结果禽 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见之,…霍在今山西霍县,在今 四川的蜀国从武王伐商,霍侯不可能远到其地…‘磨’,前人均认 为是‘磨?字之误,今山西永济北有历山②”,甚是。“宣方”卜辞习 见,即《汉书·地理志》之垣③,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黄河北岸的古 城镇。我们认为,“蜀”在今河南灵宝县西的黄河南岸,是武王伐纣 返回宗周的必经要道,它与黄河北岸的“历”隔河相望,盖因“霍侯 那时率众南逃,占领两地”,企图拦截武王西归而“终被周人所获”。 蜀、历“两地之人也参与了战败霍侯的军事,故随陈本等同来”归 降,都是很自然的事。 四武丁“伐丕”的时间和地望 武丁在伐缶方的过程中,从头年十二月到次年三月初都亲率 大军参加战斗。但因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长久(详后),武丁到三月 下旬便开始返回商都。就在他返回商都的路上,曾对“不”方进行征 伐。 庚申卜,王贞,余伐丕?三月。 庚[申]卜,王贞,余勿伐丕?二告。 《合集》六八三四 因与其同版的卜辞皆为伐甾、伐缶方的内容,加上它们的时间御接 一致,所以我们判定武丁“伐不”是其伐缶方返程中发生的事件。 “丕”的地望,饶宗颐先生以为即《左传》“商有姚邳”之邳,其地在今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