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第一部分语言史的本质 必遭海淘汰。 本书旨在通过历史上的语言故事来展示世界语言史的典型特征。显然,生 活在一种语言中并不能完整地把握生命的哲学:有一些隐喻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有一些想法和态度,用某种语言更易于表达。我们使用什么语言,我们的祖先使 用什么语言,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语言帮助我们形成和分析自己的世界 观,使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早期的拉丁语诗泰斗恩尼乌斯会说拉丁语、希腊语 以及奥斯坎语三种语言,所以他曾这样说道:“我有三颗心。6 临数是 装@ PDG

成为世界语的条件,也许谁都无法回答 在过去的500年间,融合与征服两股势力曾使欧洲语言登上了世界20大语 言榜,而它却在20世纪末逐渐走向衰亡。 堂而皇之的帝国主义已站不住脚跟。结局也不再是可预期的,虽然21世纪 两次对外战争--一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说明了帝国主义仍是百足之虫,死 而不僵,要彻底放下帝国主义的大旗,恐怕也不能适得其所。同样,当时的大规 模移民也只得暂时作罢。在过去的200年里,欧洲国家的移民直接催生了包括 美洲、非洲、澳洲和新西兰地区英语和葡萄牙语的世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有 一批曾经是殖民地国家的移民,他们虽然规模较小,但代表的意义却很重大,他 们所创造的新的语言团体地处欧洲大陆腹地,与世隔绝 未来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仍不甚明了。现在,仍然有一群庞大的移民队伍 活跃在更为广泛的疆域,不仅仅局限于前殖民国家;然而这场运动却遇到了重重阻 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目标国家不愿接受移民进入他们的国土。在一些专家的 著作中,常常写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文化冲突”,矛头直指阿拉伯语国家和英语国 家,预言它们将势不两立,这个预言将通过强国的支持来证明其稳固的政治基础。 但世界语言的未来并不只是现在的问题,更不是新闻的分析研究。语言的 传播是长期的,可能要通过好几代人的传播,甚至可能是上百年、上千年。本书 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解答在什么情况下、因为怎样的动力,语言集体在历史长河 中究竟为何有些兴旺繁荣,有些却渐渐消退甚至绝迹。 研究一种语言为何兴旺发展的最直接途径,叫做“农耕法”(Farmer's Appo~ rach)。语言团体所需要做的就是团结在一起,同时发展其人口。这是一个有机 发展(Organic Growth),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语言都是典型的例子,在欧洲大陆 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欧洲东部地区。*取这样一个名字并不是哗众取宠 ¥该理论对于形成当今20大世界语言团体有着重要影响,也同本书所得出的结论十分相近。(参见 第十三章《今日二十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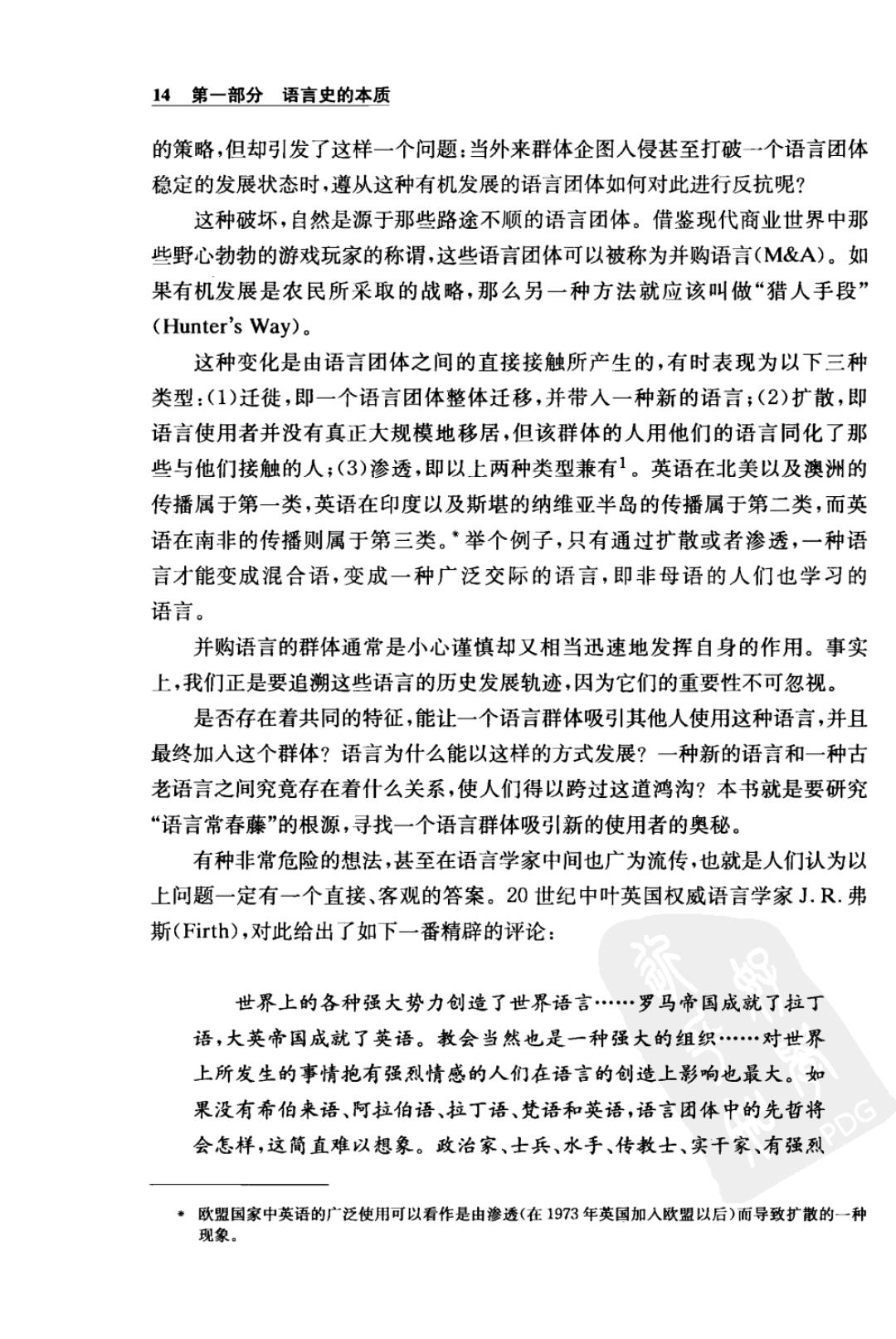
14第一部分语言史的本质 的策略,但却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外来群体企图人侵甚至打破一个语言团体 稳定的发展状态时,遵从这种有机发展的语言团体如何对此进行反抗呢? 这种破坏,自然是源于那些路途不顺的语言团体。借鉴现代商业世界中那 些野心勃勃的游戏玩家的称谓,这些语言团体可以被称为并购语言(M&A)。如 果有机发展是农民所采取的战略,那么另一种方法就应该叫做“猎人手段” (Hunter's Way). 这种变化是由语言团体之间的直接接触所产生的,有时表现为以下三种 类型:(1)迁徙,即一个语言团体整体迁移,并带入一种新的语言;(2)扩散,即 语言使用者并没有真正大规模地移居,但该群体的人用他们的语言同化了那 些与他们接触的人;(3)渗透,即以上两种类型兼有1。英语在北美以及澳洲的 传播属于第一类,英语在印度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传播属于第二类,而英 语在南非的传播则属于第三类。*举个例子,只有通过扩散或者渗透,一种语 言才能变成混合语,变成一种广泛交际的语言,即非母语的人们也学习的 语言。 并购语言的群体通常是小心谨慎却又相当迅速地发挥自身的作用。事实 上,我们正是要追溯这些语言的历史发展轨迹,因为它们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是否存在着共同的特征,能让一个语言群体吸引其他人使用这种语言,并且 最终加入这个群体?语言为什么能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一种新的语言和一种古 老语言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使人们得以跨过这道鸿沟?本书就是要研究 “语言常春藤”的根源,寻找一个语言群体吸引新的使用者的奥秘。 有种非常危险的想法,甚至在语言学家中间也广为流传,也就是人们认为以 上问题一定有一个直接、客观的答案。20世纪中叶英国权威语言学家J.R.弗 斯(irth),对此给出了如下一番精辟的评论: 世界上的各种强大势力创造了世界语言…罗马帝国成就了拉丁 语,大英帝国成就了英语。教会当然也是一种强大的组织…对世界 上所发生的事情抱有强烈情感的人们在语言的创造上影响也最大。如 果没有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梵语和英语,语言团体中的先哲将 会怎样,这简直难以想象。政治家、士兵、水手、传教士、实干家、有强烈 *欧盟国家中英语的广泛使用可以看作是由渗透(在1973年英国加入欧盟以后)而导致扩散的一种 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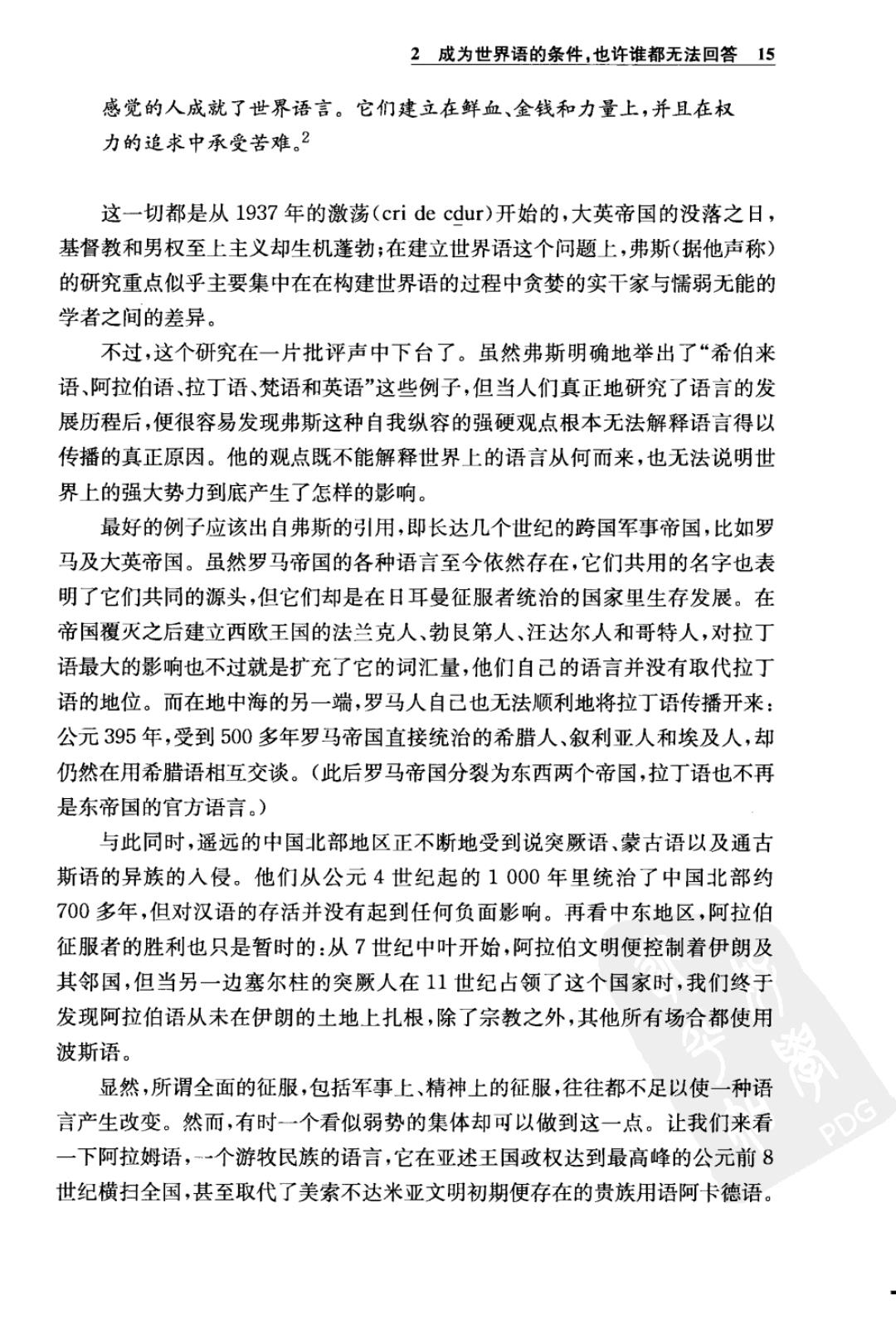
2成为世界语的条件,也许谁都无法回答15 感觉的人成就了世界语言。它们建立在鲜血、金钱和力量上,并且在权 力的追求中承受苦难。2 这一切都是从1937年的激荡(cri de cdur)开始的,大英帝国的没落之日, 基督教和男权至上主义却生机蓬勃;在建立世界语这个问题上,弗斯(据他声称) 的研究重点似乎主要集中在在构建世界语的过程中贪婪的实干家与懦弱无能的 学者之间的差异。 不过,这个研究在一片批评声中下台了。虽然弗斯明确地举出了“希伯来 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梵语和英语”这些例子,但当人们真正地研究了语言的发 展历程后,便很容易发现弗斯这种自我纵容的强硬观点根本无法解释语言得以 传播的真正原因。他的观点既不能解释世界上的语言从何而来,也无法说明世 界上的强大势力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最好的例子应该出自弗斯的引用,即长达几个世纪的跨国军事帝国,比如罗 马及大英帝国。虽然罗马帝国的各种语言至今依然存在,它们共用的名字也表 明了它们共同的源头,但它们却是在日耳曼征服者统治的国家里生存发展。在 帝国覆灭之后建立西欧王国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对拉丁 语最大的影响也不过就是扩充了它的词汇量,他们自己的语言并没有取代拉丁 语的地位。而在地中海的另一端,罗马人自己也无法顺利地将拉丁语传播开来: 公元395年,受到500多年罗马帝国直接统治的希腊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却 仍然在用希腊语相互交谈。(此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拉丁语也不再 是东帝国的官方语言。) 与此同时,遥远的中国北部地区正不断地受到说突厥语、蒙古语以及通古 斯语的异族的入侵。他们从公元4世纪起的1000年里统治了中国北部约 700多年,但对汉语的存活并没有起到任何负面影响。再看中东地区,阿拉伯 征服者的胜利也只是暂时的:从7世纪中叶开始,阿拉伯文明便控制着伊朗及 其邻国,但当另一边塞尔柱的突厥人在11世纪占领了这个国家时,我们终于 发现阿拉伯语从未在伊朗的土地上扎根,除了宗教之外,其他所有场合都使用 波斯语。 显然,所谓全面的征服,包括军事上、精神上的征服,往往都不足以使一种语 言产生改变。然而,有时一个看似弱势的集体却可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来看 PDG 一下阿拉姆语,一个游牧民族的语言,它在亚述王国政权达到最高峰的公元前8 世纪横扫全国,甚至取代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初期便存在的贵族用语阿卡德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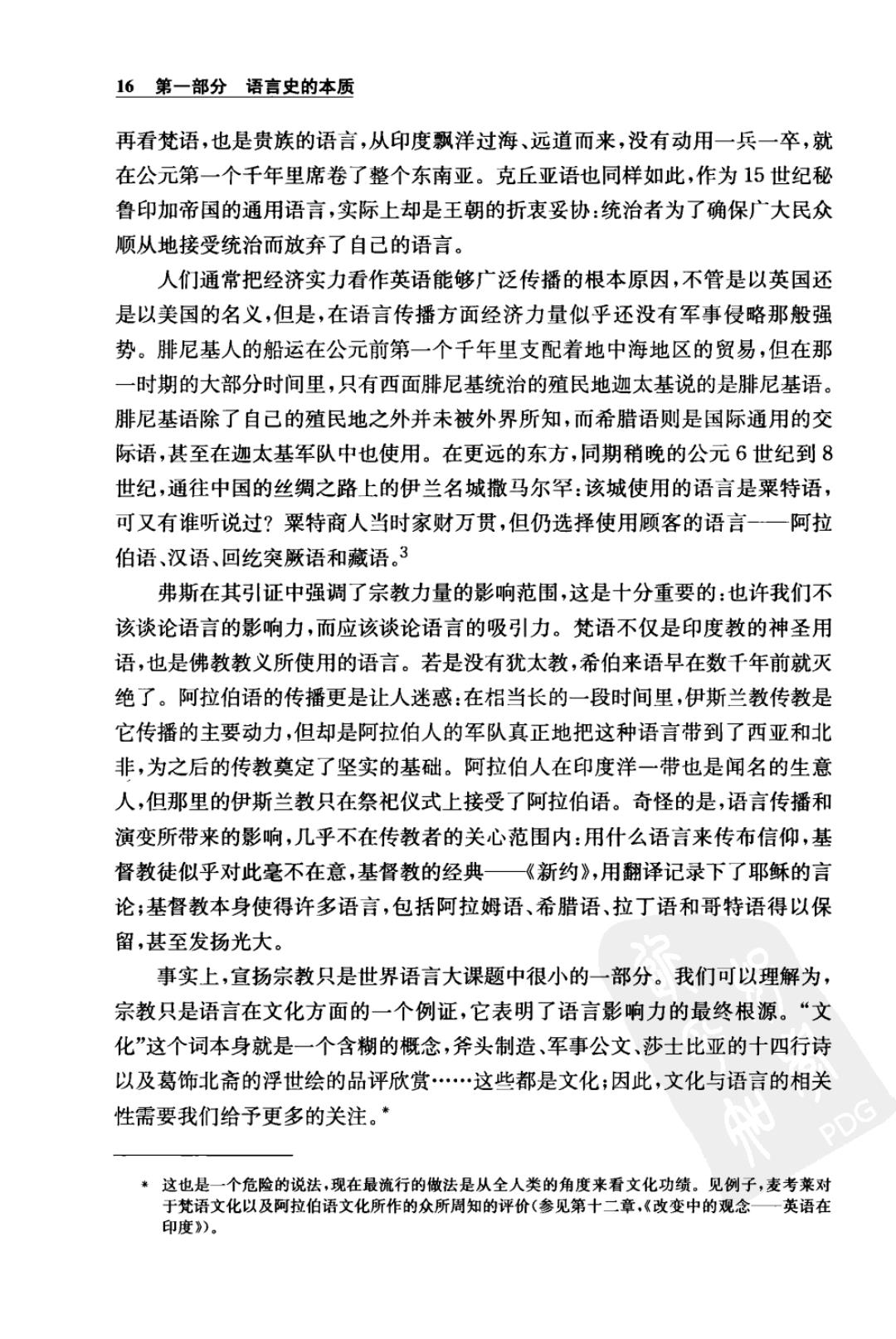
16第一部分语言史的本质 再看梵语,也是贵族的语言,从印度飘洋过海、远道而来,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就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里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克丘亚语也同样如此,作为15世纪秘 鲁印加帝国的通用语言,实际上却是王朝的折衷妥协:统治者为了确保广大民众 顺从地接受统治而放弃了自己的语言。 人们通常把经济实力看作英语能够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不管是以英国还 是以美国的名义,但是,在语言传播方面经济力量似乎还没有军事侵略那般强 势。腓尼基人的船运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里支配着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但在那 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西面腓尼基统治的殖民地迦太基说的是腓尼基语。 腓尼基语除了自己的殖民地之外并未被外界所知,而希腊语则是国际通用的交 际语,甚至在迦太基军队中也使用。在更远的东方,同期稍晚的公元6世纪到8 世纪,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上的伊兰名城撒马尔罕:该城使用的语言是粟特语, 可又有谁听说过?粟特商人当时家财万贯,但仍选择使用顾客的语言一阿拉 伯语、汉语、回纥突厥语和藏语。3 弗斯在其引证中强调了宗教力量的影响范围,这是十分重要的:也许我们不 该谈论语言的影响力,而应该谈论语言的吸引力。梵语不仅是印度教的神圣用 语,也是佛教教义所使用的语言。若是没有犹太教,希伯来语早在数千年前就灭 绝了。阿拉伯语的传播更是让人迷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伊斯兰教传教是 它传播的主要动力,但却是阿拉伯人的军队真正地把这种语言带到了西亚和北 非,为之后的传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一带也是闻名的生意 人,但那里的伊斯兰教只在祭祀仪式上接受了阿拉伯语。奇怪的是,语言传播和 演变所带来的影响,几乎不在传教者的关心范围内:用什么语言来传布信仰,基 督教徒似乎对此毫不在意,基督教的经典一《新约》,用翻译记录下了耶稣的言 论;基督教本身使得许多语言,包括阿拉姆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哥特语得以保 留,甚至发扬光大。 事实上,宣扬宗教只是世界语言大课题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理解为, 宗教只是语言在文化方面的一个例证,它表明了语言影响力的最终根源。“文 化”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斧头制造、军事公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以及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的品评欣赏…这些都是文化;因此,文化与语言的相关 性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这也是一个危险的说法,现在最流行的做法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文化功绩。见例子,麦考莱对 于梵语文化以及阿拉伯语文化所作的众所周知的评价(参见第十二章,《改变中的观念一英语在 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