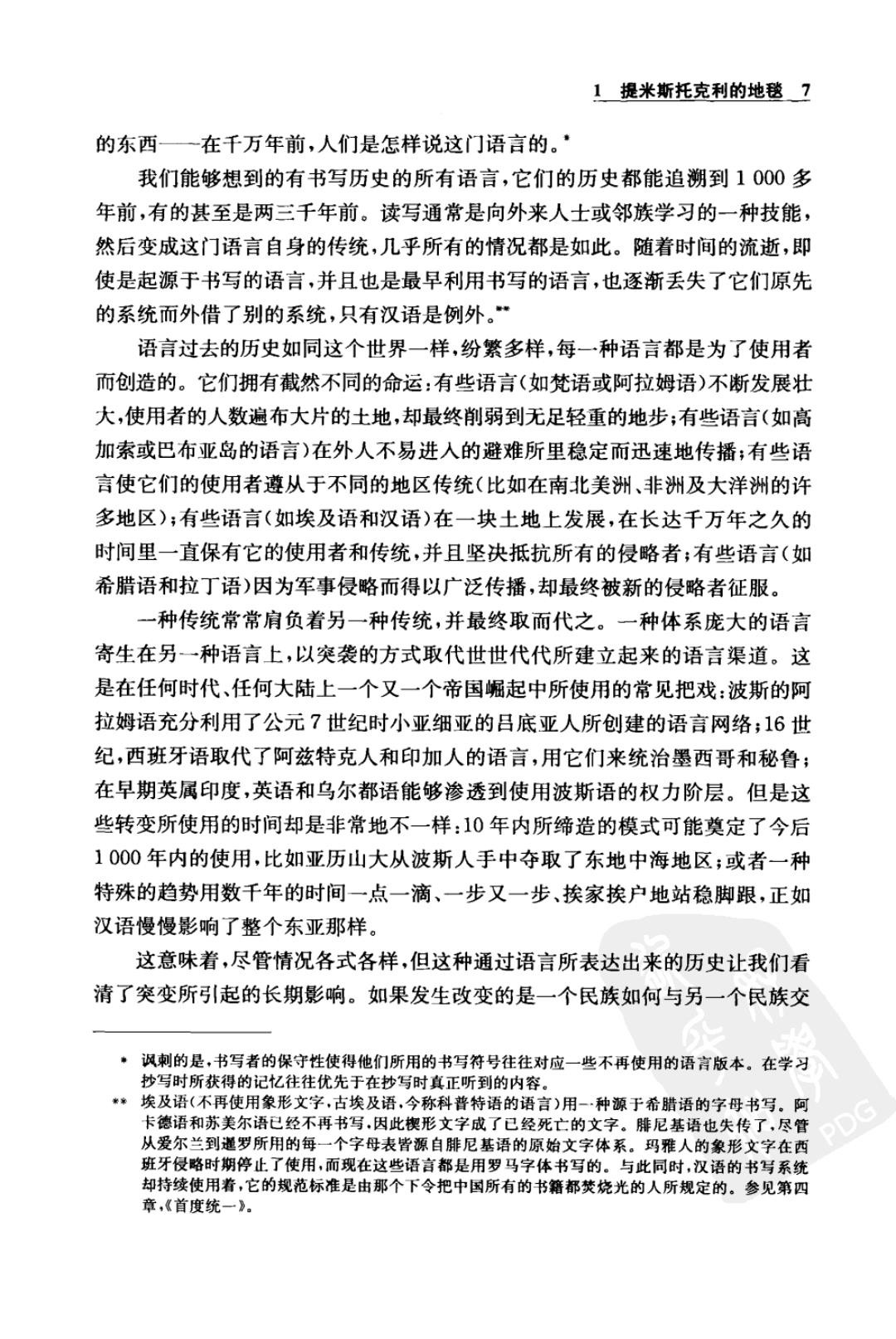
1提米斯托克利的地毯7 的东西一在千万年前,人们是怎样说这门语言的。 我们能够想到的有书写历史的所有语言,它们的历史都能追溯到1000多 年前,有的甚至是两三千年前。读写通常是向外来人士或邻族学习的一种技能, 然后变成这门语言自身的传统,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即 使是起源于书写的语言,并且也是最早利用书写的语言,也逐渐丢失了它们原先 的系统而外借了别的系统,只有汉语是例外。 语言过去的历史如同这个世界一样,纷繁多样,每一一种语言都是为了使用者 而创造的。它们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有些语言(如梵语或阿拉姆语)不断发展壮 大,使用者的人数遍布大片的土地,却最终削弱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有些语言(如高 加索或巴布亚岛的语言)在外人不易进人的避难所里稳定而迅速地传播;有些语 言使它们的使用者遵从于不同的地区传统(比如在南北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的许 多地区);有些语言(如埃及语和汉语)在一块土地上发展,在长达千万年之久的 时间里一直保有它的使用者和传统,并且坚决抵抗所有的侵略者;有些语言(如 希腊语和拉丁语)因为军事侵略而得以广泛传播,却最终被新的侵略者征服。 一种传统常常肩负着另一种传统,并最终取而代之。一种体系庞大的语言 寄生在另一种语言上,以突袭的方式取代世世代代所建立起来的语言渠道。这 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大陆上一个又一个帝国崛起中所使用的常见把戏:波斯的阿 拉姆语充分利用了公元7世纪时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所创建的语言网络;16世 纪,西班牙语取代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语言,用它们来统治墨西哥和秘鲁; 在早期英属印度,英语和乌尔都语能够渗透到使用波斯语的权力阶层。但是这 些转变所使用的时间却是非常地不一样:10年内所缔造的模式可能奠定了今后 1000年内的使用,比如亚历山大从波斯人手中夺取了东地中海地区;或者一种 特殊的趋势用数千年的时间一点一滴、一步又一步、挨家挨户地站稳脚跟,正如 汉语慢慢影响了整个东亚那样。 这意味着,尽管情况各式各样,但这种通过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历史让我们看 清了突变所引起的长期影响。如果发生改变的是一个民族如何与另一个民族交 ·讽刺的是,书写者的保守性使得他们所用的书写符号往往对应一些不再使用的语言版本。在学习 抄写时所获得的记忆往往优先于在抄写时真正听到的内容。 埃及语(不再使用象形文字,古埃及语,今称科普特语的语言)用-一种源于希腊语的字母书写。阿 卡德语和苏美尔语已经不再书写,因此楔形文字成了已经死亡的文字。腓尼基语也失传了,尽管 从爱尔兰到递罗所用的每一个字母表皆源自腓尼基语的原始文字体系。玛雅人的象形文字在西 班牙侵略时期停止了使用,而现在这些语言都是用罗马字体书写的。与此同时,汉语的书写系统 却持续使用着,它的规范标准是由那个下令把中国所有的书籍都焚烧光的人所规定的。参见第四 章,《首度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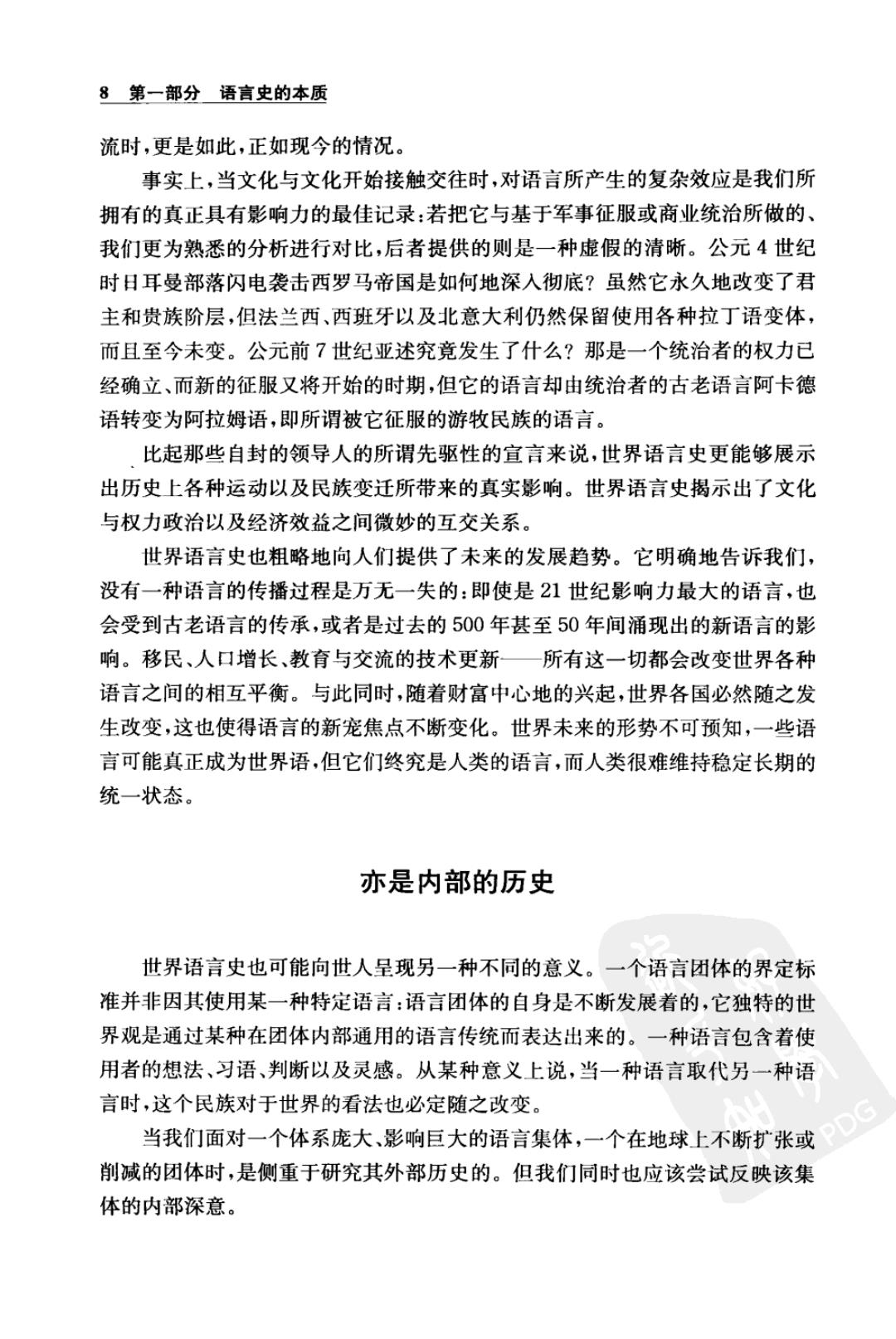
8第一部分语言史的本质 流时,更是如此,正如现今的情况。 事实上,当文化与文化开始接触交往时,对语言所产生的复杂效应是我们所 拥有的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最佳记录:若把它与基于军事征服或商业统治所做的、 我们更为熟悉的分析进行对比,后者提供的则是一种虚假的清晰。公元4世纪 时日耳曼部落闪电袭击西罗马帝国是如何地深入彻底?虽然它永久地改变了君 主和贵族阶层,但法兰西、西班牙以及北意大利仍然保留使用各种拉丁语变体, 而且至今未变。公元前7世纪亚述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是一个统治者的权力已 经确立、而新的征服又将开始的时期,但它的语言却由统治者的古老语言阿卡德 语转变为阿拉姆语,即所谓被它征服的游牧民族的语言。 比起那些自封的领导人的所谓先驱性的宣言来说,世界语言史更能够展示 出历史上各种运动以及民族变迁所带来的真实影响。世界语言史揭示出了文化 与权力政治以及经济效益之间微妙的互交关系。 世界语言史也粗略地向人们提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它明确地告诉我们, 没有一种语言的传播过程是万无一失的:即使是21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语言,也 会受到古老语言的传承,或者是过去的500年甚至50年间涌现出的新语言的影 响。移民、人口增长、教育与交流的技术更新—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世界各种 语言之间的相互平衡。与此同时,随着财富中心地的兴起,世界各国必然随之发 生改变,这也使得语言的新宠焦点不断变化。世界未来的形势不可预知,一些语 言可能真正成为世界语,但它们终究是人类的语言,而人类很难维持稳定长期的 统一状态。 亦是内部的历史 世界语言史也可能向世人呈现另一种不同的意义。一个语言团体的界定标 准并非因其使用某一种特定语言:语言团体的自身是不断发展着的,它独特的世 界观是通过某种在团体内部通用的语言传统而表达出来的。一种语言包含着使 用者的想法、习语、判断以及灵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 言时,这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必定随之改变。 当我们面对一个体系庞大、影响巨大的语言集体,一个在地球上不断扩张或 削减的团体时,是侧重于研究其外部历史的。但我们同时也应该尝试反映该集 体的内部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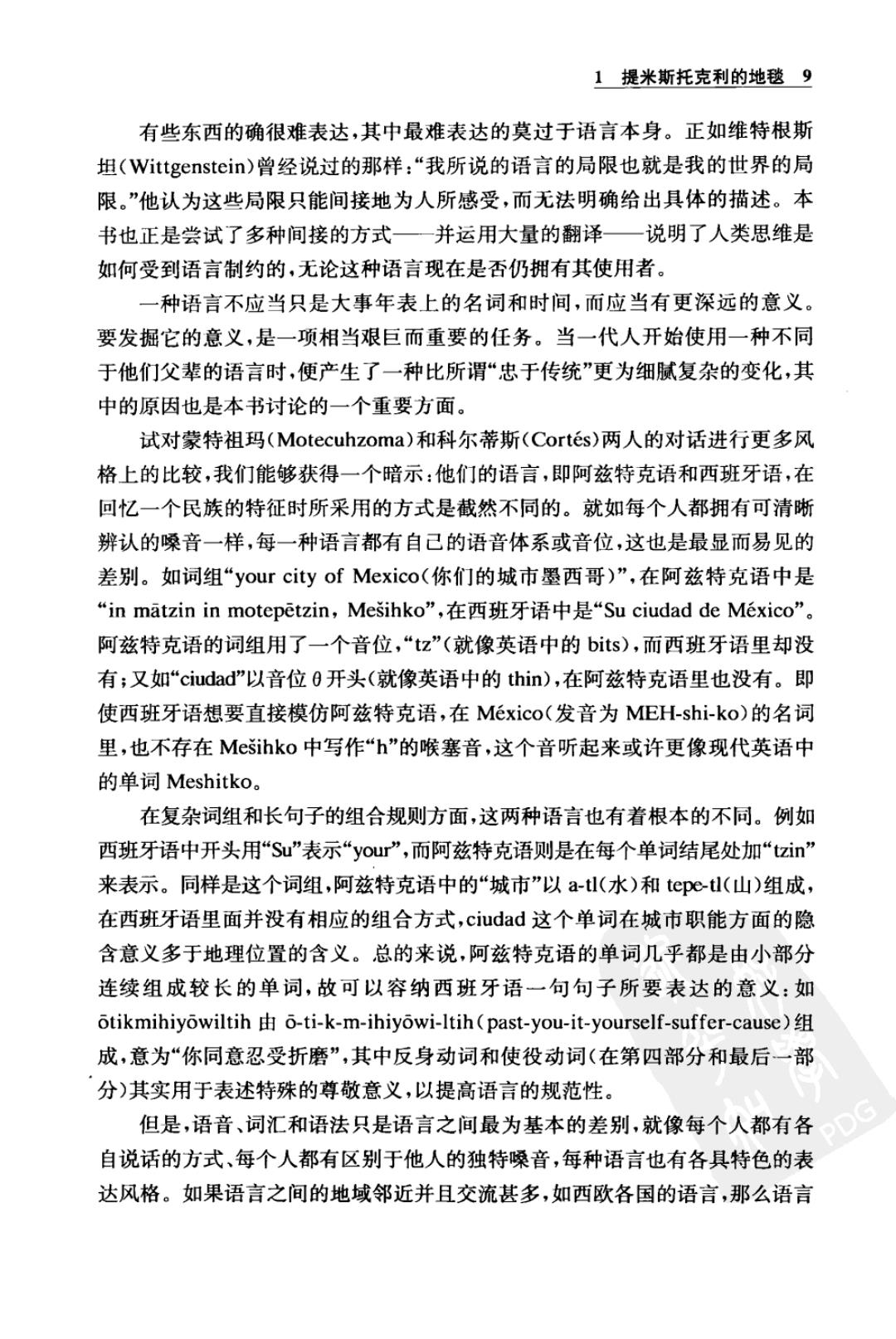
1提米斯托克利的地毯9 有些东西的确很难表达,其中最难表达的莫过于语言本身。正如维特根斯 坦(Wittgenstein)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所说的语言的局限也就是我的世界的局 限。”他认为这些局限只能间接地为人所感受,而无法明确给出具体的描述。本 书也正是尝试了多种间接的方式一一并运用大量的翻译一说明了人类思维是 如何受到语言制约的,无论这种语言现在是否仍拥有其使用者。 一种语言不应当只是大事年表上的名词和时间,而应当有更深远的意义。 要发掘它的意义,是一项相当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当一代人开始使用一种不同 于他们父辈的语言时,便产生了一种比所谓“忠于传统”更为细腻复杂的变化,其 中的原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试对蒙特祖玛(Motecuhzoma)和科尔蒂斯(Cortes)两人的对话进行更多风 格上的比较,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暗示:他们的语言,即阿兹特克语和西班牙语,在 回忆一个民族的特征时所采用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就如每个人都拥有可清晰 辨认的嗓音一样,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音体系或音位,这也是最显而易见的 差别。如词组“your city of Mexico(你们的城市墨西哥)”,在阿兹特克语中是 “in matzin in motepetzin,.Mesihko”,在西班牙语中是“Su ciudad de Mexico”。 阿兹特克语的词组用了一个音位,“tz”(就像英语中的bts),而西班牙语里却没 有;又如“ciudad”以音位0开头(就像英语中的thin),在阿兹特克语里也没有。即 使西班牙语想要直接模仿阿兹特克语,在México(发音为MEH-shi-ko)的名词 里,也不存在Mesihko中写作“h”的喉塞音,这个音听起来或许更像现代英语中 的单词Meshitko。 在复杂词组和长句子的组合规则方面,这两种语言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例如 西班牙语中开头用“Su”表示“your”,而阿兹特克语则是在每个单词结尾处加“tzin” 来表示。同样是这个词组,阿兹特克语中的“城市”以a-tl(水)和tepe-tl(山)组成, 在西班牙语里面并没有相应的组合方式,ciudad这个单词在城市职能方面的隐 含意义多于地理位置的含义。总的来说,阿兹特克语的单词几乎都是由小部分 连续组成较长的单词,故可以容纳西班牙语一句句子所要表达的意义:如 otikmihiyowiltih o-ti-k-m-ihiyowi-ltih (past-you-it-yourself-suffer-cause) 成,意为“你同意忍受折磨”,其中反身动词和使役动词(在第四部分和最后一部 分)其实用于表述特殊的尊敬意义,以提高语言的规范性。 但是,语音、词汇和语法只是语言之间最为基本的差别,就像每个人都有各 自说话的方式、每个人都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嗓音,每种语言也有各具特色的表 达风格。如果语言之间的地域邻近并且交流甚多,如西欧各国的语言,那么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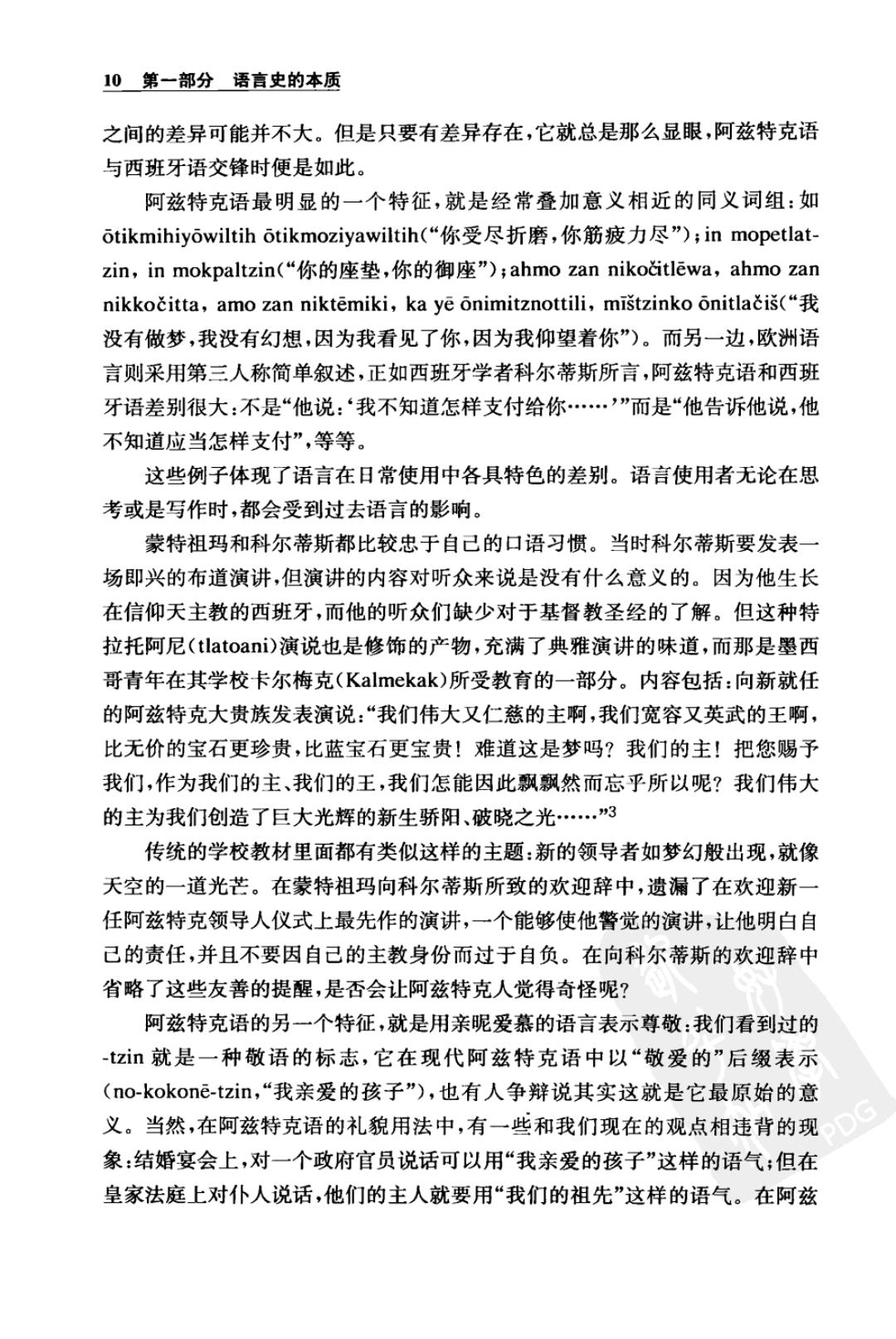
10第一部分语言史的本质 之间的差异可能并不大。但是只要有差异存在,它就总是那么显眼,阿兹特克语 与西班牙语交锋时便是如此。 阿兹特克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经常叠加意义相近的同义词组:如 δtikmihiyowiltih otikmoziyawiltih(“你受尽折磨,你筋疲力尽”);in mopetlat- zin,in mokpaltzin(“你的座垫,你的御座”);ahmo zan nikocitlewa,ahmo zan nikkocitta,amo zan niktemiki,ka ye onimitznottili,mistzinko onitlacis(" 没有做梦,我没有幻想,因为我看见了你,因为我仰望着你”)。而另一边,欧洲语 言则采用第三人称简单叙述,正如西班牙学者科尔蒂斯所言,阿兹特克语和西班 牙语差别很大:不是“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支付给你…’”而是“他告诉他说,他 不知道应当怎样支付”,等等。 这些例子体现了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各具特色的差别。语言使用者无论在思 考或是写作时,都会受到过去语言的影响。 蒙特祖玛和科尔蒂斯都比较忠于自己的口语习惯。当时科尔蒂斯要发表一 场即兴的布道演讲,但演讲的内容对听众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生长 在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而他的听众们缺少对于基督教圣经的了解。但这种特 拉托阿尼(tlatoani)演说也是修饰的产物,充满了典雅演讲的味道,而那是墨西 哥青年在其学校卡尔梅克(Kalmekak)所受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包括:向新就任 的阿兹特克大贵族发表演说:“我们伟大又仁慈的主啊,我们宽容又英武的王啊, 比无价的宝石更珍贵,比蓝宝石更宝贵!难道这是梦吗?我们的主!把您赐予 我们,作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怎能因此飘飘然而忘乎所以呢?我们伟大 的主为我们创造了巨大光辉的新生骄阳、破晓之光…3 传统的学校教材里面都有类似这样的主题:新的领导者如梦幻般出现,就像 天空的一道光芒。在蒙特祖玛向科尔蒂斯所致的欢迎辞中,遗漏了在欢迎新一 任阿兹特克领导人仪式上最先作的演讲,一个能够使他警觉的演讲,让他明白自 己的责任,并且不要因自己的主教身份而过于自负。在向科尔蒂斯的欢迎辞中 省略了这些友善的提醒,是否会让阿兹特克人觉得奇怪呢? 阿兹特克语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用亲呢爱慕的语言表示尊敬:我们看到过的 -tzi就是一种敬语的标志,它在现代阿兹特克语中以“敬爱的”后缀表示 (no-kokone-tzin,“我亲爱的孩子”),也有人争辩说其实这就是它最原始的意 义。当然,在阿兹特克语的礼貌用法中,有一些和我们现在的观点相违背的现 象:结婚宴会上,对一个政府官员说话可以用“我亲爱的孩子”这样的语气;但在 皇家法庭上对仆人说话,他们的主人就要用“我们的祖先”这样的语气。在阿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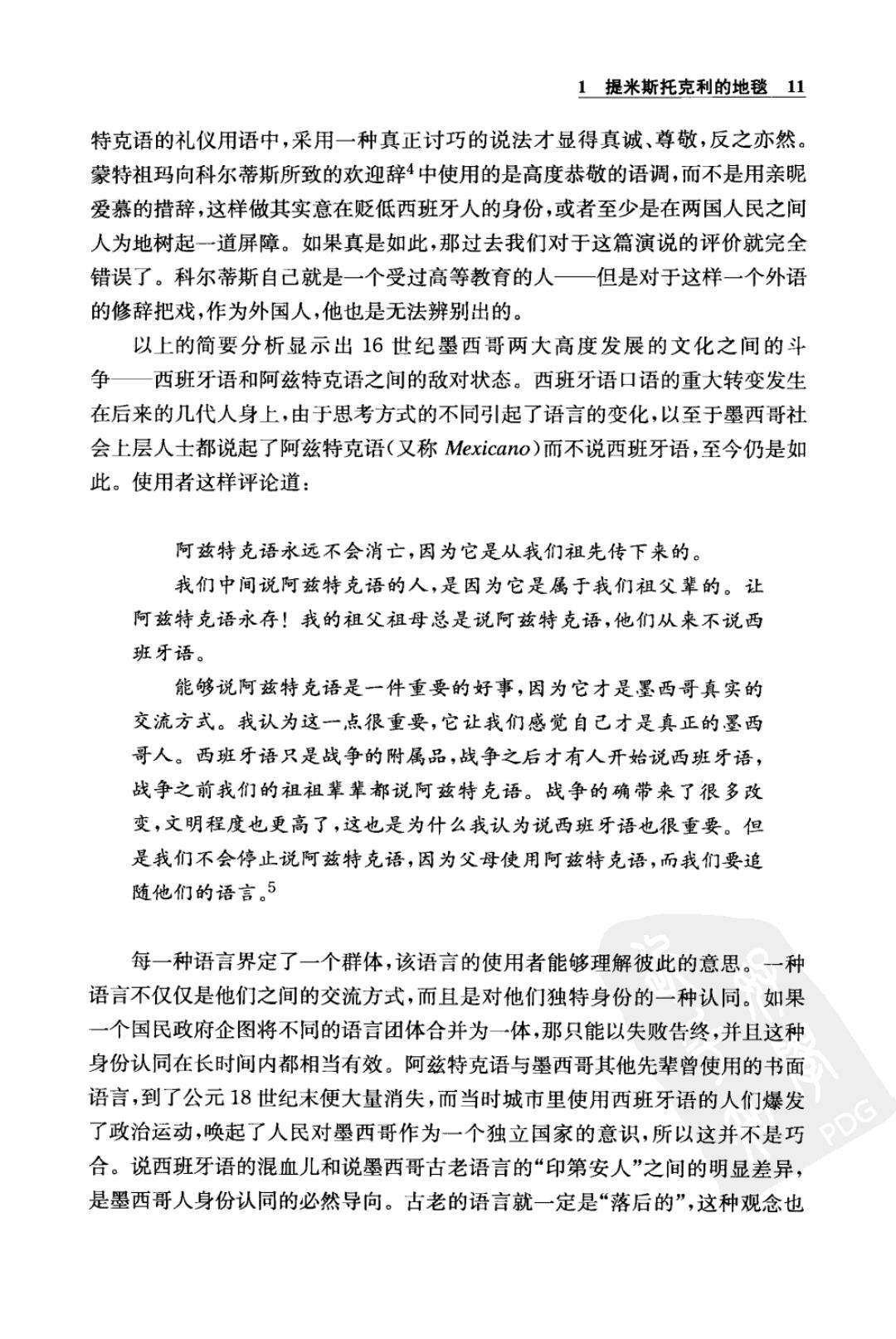
1提米斯托克利的地毯11 特克语的礼仪用语中,采用一种真正讨巧的说法才显得真诚、尊敬,反之亦然。 蒙特祖玛向科尔蒂斯所致的欢迎辞4中使用的是高度恭敬的语调,而不是用亲昵 爱慕的措辞,这样做其实意在贬低西班牙人的身份,或者至少是在两国人民之间 人为地树起一道屏障。如果真是如此,那过去我们对于这篇演说的评价就完全 错误了。科尔蒂斯自己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外语 的修辞把戏,作为外国人,他也是无法辨别出的。 以上的简要分析显示出16世纪墨西哥两大高度发展的文化之间的斗 争— 西班牙语和阿兹特克语之间的敌对状态。西班牙语口语的重大转变发生 在后来的几代人身上,由于思考方式的不同引起了语言的变化,以至于墨西哥社 会上层人士都说起了阿兹特克语(又称Mexicano)而不说西班牙语,至今仍是如 此。使用者这样评论道: 阿兹特克语永远不会消亡,因为它是从我们祖先传下来的。 我们中间说阿兹特克语的人,是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祖父辈的。让 阿兹特克语永存!我的祖父祖母总是说阿兹特克语,他们从来不说西 班牙语。 能够说阿兹特克语是一件重要的好事,因为它才是墨西哥真实的 交流方式。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它让我们感觉自己才是真正的墨西 哥人。西班牙语只是战争的附属品,战争之后才有人开始说西班牙语, 战争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说阿兹特克语。战争的确带来了很多改 变,文明程度也更高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说西班牙语也很重要。但 是我们不会停止说阿兹特克语,因为父母使用阿兹特克语,而我们要追 随他们的语言。5 每一种语言界定了一个群体,该语言的使用者能够理解彼此的意思。一种 语言不仅仅是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而且是对他们独特身份的一种认同。如果 一个国民政府企图将不同的语言团体合并为一体,那只能以失败告终,并且这种 身份认同在长时间内都相当有效。阿兹特克语与墨西哥其他先辈曾使用的书面 语言,到了公元18世纪末便大量消失,而当时城市里使用西班牙语的人们爆发 了政治运动,唤起了人民对墨西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意识,所以这并不是巧 合。说西班牙语的混血儿和说墨西哥古老语言的“印第安人”之间的明显差异, 是墨西哥人身份认同的必然导向。古老的语言就一定是“落后的”,这种观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