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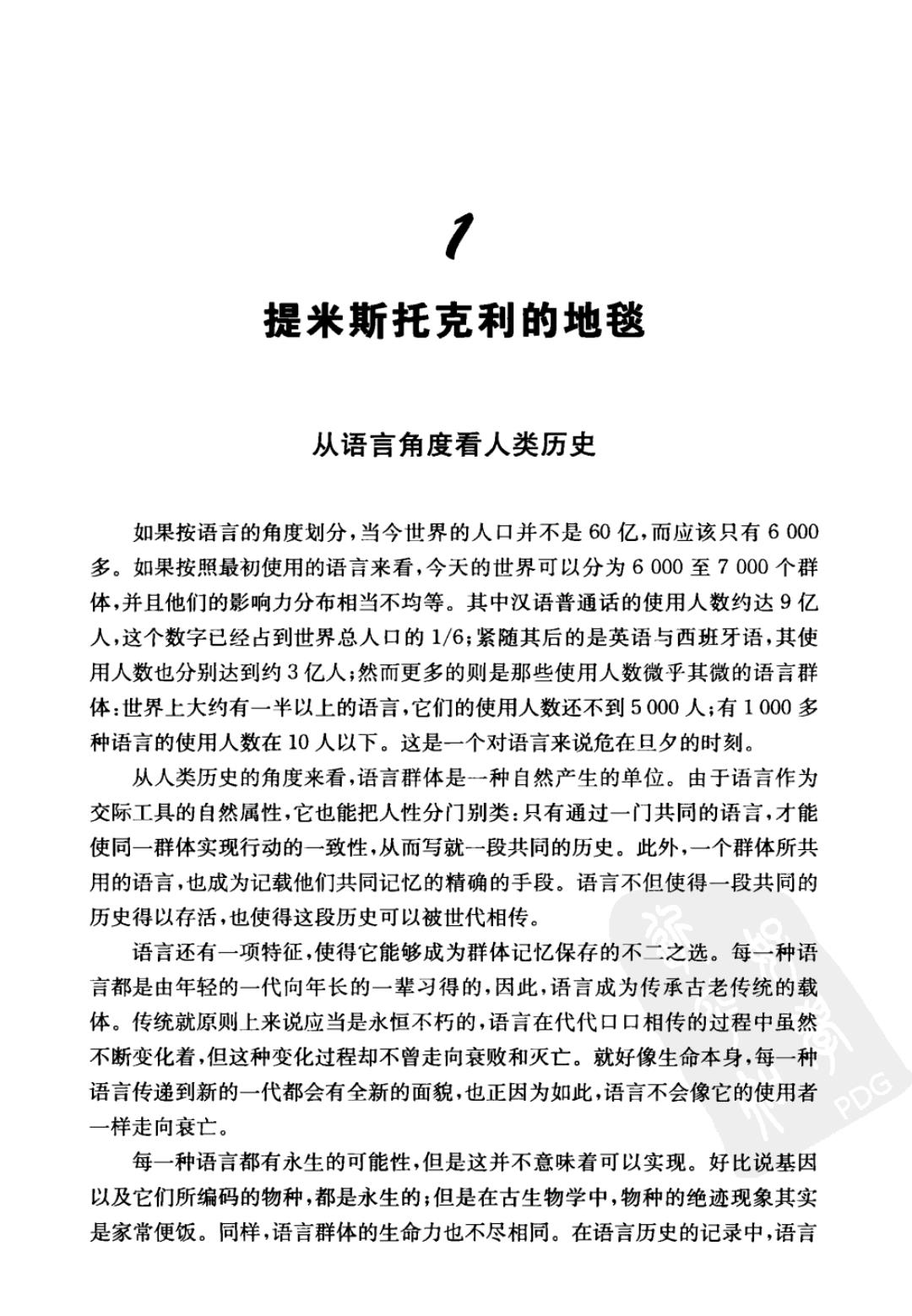
提米斯托克利的地毯 从语言角度看人类历史 如果按语言的角度划分,当今世界的人口并不是60亿,而应该只有6000 多。如果按照最初使用的语言来看,今天的世界可以分为6000至7000个群 体,并且他们的影响力分布相当不均等。其中汉语普通话的使用人数约达9亿 人,这个数字已经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6;紧随其后的是英语与西班牙语,其使 用人数也分别达到约3亿人;然而更多的则是那些使用人数微乎其微的语言群 体: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语言,它们的使用人数还不到5000人;有1000多 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在10人以下。这是一个对语言来说危在旦夕的时刻。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语言群体是一种自然产生的单位。由于语言作为 交际工具的自然属性,它也能把人性分门别类:只有通过一门共同的语言,才能 使同一群体实现行动的一致性,从而写就一段共同的历史。此外,一个群体所共 用的语言,也成为记载他们共同记忆的精确的手段。语言不但使得一段共同的 历史得以存活,也使得这段历史可以被世代相传。 语言还有一项特征,使得它能够成为群体记忆保存的不二之选。每一种语 言都是由年轻的一代向年长的一辈习得的,因此,语言成为传承古老传统的载 体。传统就原则上来说应当是永恒不朽的,语言在代代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虽然 不断变化着,但这种变化过程却不曾走向衰败和灭亡。就好像生命本身,每一种 语言传递到新的一代都会有全新的面貌,也正因为如此,语言不会像它的使用者 PDG 一样走向衰亡。 每一种语言都有永生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好比说基因 以及它们所编码的物种,都是永生的;但是在古生物学中,物种的绝迹现象其实 是家常便饭。同样,语言群体的生命力也不尽相同。在语言历史的记录中,语言

4第一部分语言史的本质 消亡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所承载的传统也灰飞烟灭,语言的使用者无迹可寻。 从语言学角度和基因角度看人类历史,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对于现在的我们观 照远古记忆产生着革命性的影响。一个语言群体的成员同一个生物种群,或是 一个母系宗谱的成员一样,有着非常明确的关系准则。当某一个体能够同某种 群的成员繁衍出后代,它便成为该种群的成员;当某一个体的母体属于某个母系 宗谱,那么它也被列为该母系宗谱的一员。同样,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只要 你掌握了某一语言群体的语言,你便成为该群体的一员。 这样一种从语言学角度定义的群体单位,优点就在于它给出了一个对于人 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群体概念。这种物种单位颇有意思,当我们区分我们的 远祖与其他亲属族群一如直立人和穴居人一的关系时,会发现,在智人崛起 后,这种划分方式不再有效,因为从物种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归为一类。血缘单位 同样有其价值,通过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我们可以化亿万年为一瞬,而且, 当某些在今天表现明显的血统特征在某个可能是其祖先的族群中却毫无踪迹 时,我们能通过血缘单位给出关于人类起源的有趣证据。因此我们推论出波利 尼西亚人并非来自南美洲,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出身要追溯到近东地区的农业发 源地,以及英国中部人群的先祖来自弗里斯兰1。但是,知道许多人的父母身份 不明并不会阻碍一个群体的完整性,这一点人类学和语言学不同。 人类学在仅仅依靠一系列固定特征划分的单位之间进行比照,例如种族,或 是如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那样凭借肤色、头部比例之类的肤浅表象,或是如 现代社会一般凭借血液、组织以及DNA序列。同样地,区分文化类别,比如民 族,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牵涉到对共同历史一或许还有共同语言一一这些 难以衡量的事物2。鉴于许多特征在不同年龄层的不同个体中处于零散状态,因 而怎样制定一套各种族或民族特有标准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但是对一种既 定语言的使用这一条是不可否认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毕竟这是每个已知 问题并不在于共同财富是无形虚构的(就好比纳粹曾经给犹太人定下的标准一样),也不因为这些 财富对于生存而言无足轻重。(举这样一个例子:镰状细胞贫血症与地中海贫血的基因获取,已经 被明确为遗传性疾病,而不属于疟疾的一类。)这个问题的根源与数据逻辑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 说拿一个人群作为考察对象,共有财富的一部分往往要从一个更大的子集中选取。共享一个财富 子集的群体未必共享其他群体的财富子集一(在考察开始前)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悠长的 历史进程中,谁有权力来界定所谓群体的概念呢?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发现,研究所选取的财富遗 产恰巧证实了研究者的种种猜想,也使得对于人类种群的基因与传统语言学分类方法成为了万众 瞩目的焦点。如此大胆建立的数据模型,也使得卡瓦利-斯福札(Luigi Luca Cavalli-Sforza,斯坦 福大学医学院遗传学荣誉教授,人类遗传学界泰斗,也是当前基因组多样性研究计划的主要发起 人)及其追随者的人类史前人口梯度理论的可信度正在发生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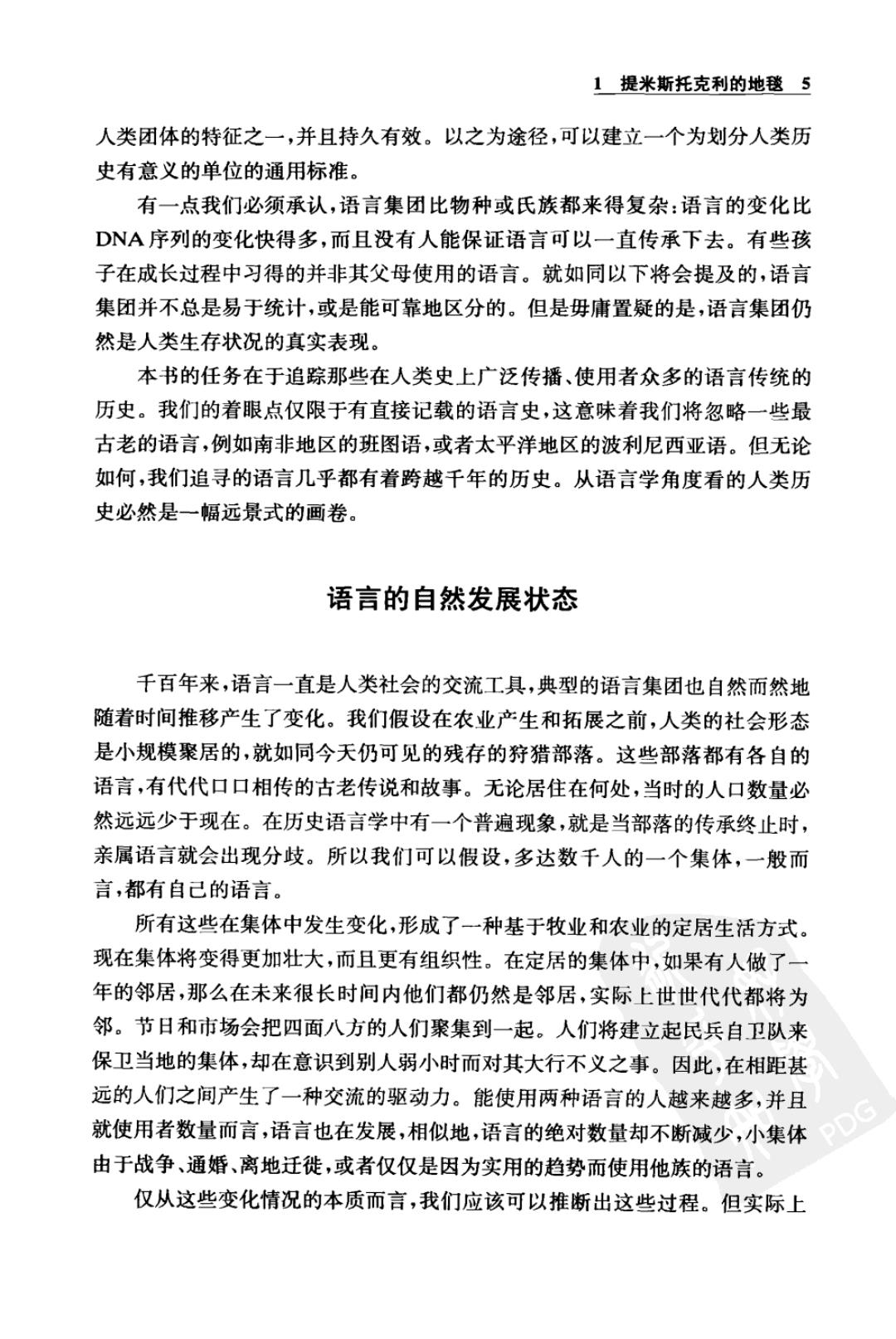
1提米斯托克利的地毯5 人类团体的特征之一,并且持久有效。以之为途径,可以建立一个为划分人类历 史有意义的单位的通用标准。 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语言集团比物种或氏族都来得复杂:语言的变化比 DNA序列的变化快得多,而且没有人能保证语言可以一直传承下去。有些孩 子在成长过程中习得的并非其父母使用的语言。就如同以下将会提及的,语言 集团并不总是易于统计,或是能可靠地区分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语言集团仍 然是人类生存状况的真实表现。 本书的任务在于追踪那些在人类史上广泛传播、使用者众多的语言传统的 历史。我们的着眼点仅限于有直接记载的语言史,这意味着我们将忽略一些最 古老的语言,例如南非地区的班图语,或者太平洋地区的波利尼西亚语。但无论 如何,我们追寻的语言几乎都有着跨越千年的历史。从语言学角度看的人类历 史必然是一幅远景式的画卷。 语言的自然发展状态 千百年来,语言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交流工具,典型的语言集团也自然而然地 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变化。我们假设在农业产生和拓展之前,人类的社会形态 是小规模聚居的,就如同今天仍可见的残存的狩猎部落。这些部落都有各自的 语言,有代代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和故事。无论居住在何处,当时的人口数量必 然远远少于现在。在历史语言学中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当部落的传承终止时, 亲属语言就会出现分歧。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多达数千人的一个集体,一般而 言,都有自己的语言。 所有这些在集体中发生变化,形成了一种基于牧业和农业的定居生活方式。 现在集体将变得更加壮大,而且更有组织性。在定居的集体中,如果有人做了一 年的邻居,那么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他们都仍然是邻居,实际上世世代代都将为 邻。节日和市场会把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到一起。人们将建立起民兵自卫队来 保卫当地的集体,却在意识到别人弱小时而对其大行不义之事。因此,在相距甚 远的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交流的驱动力。能使用两种语言的人越来越多,并且 就使用者数量而言,语言也在发展,相似地,语言的绝对数量却不断减少,小集体 由于战争、通婚、离地迁徙,或者仅仅是因为实用的趋势而使用他族的语言。 仅从这些变化情况的本质而言,我们应该可以推断出这些过程。但实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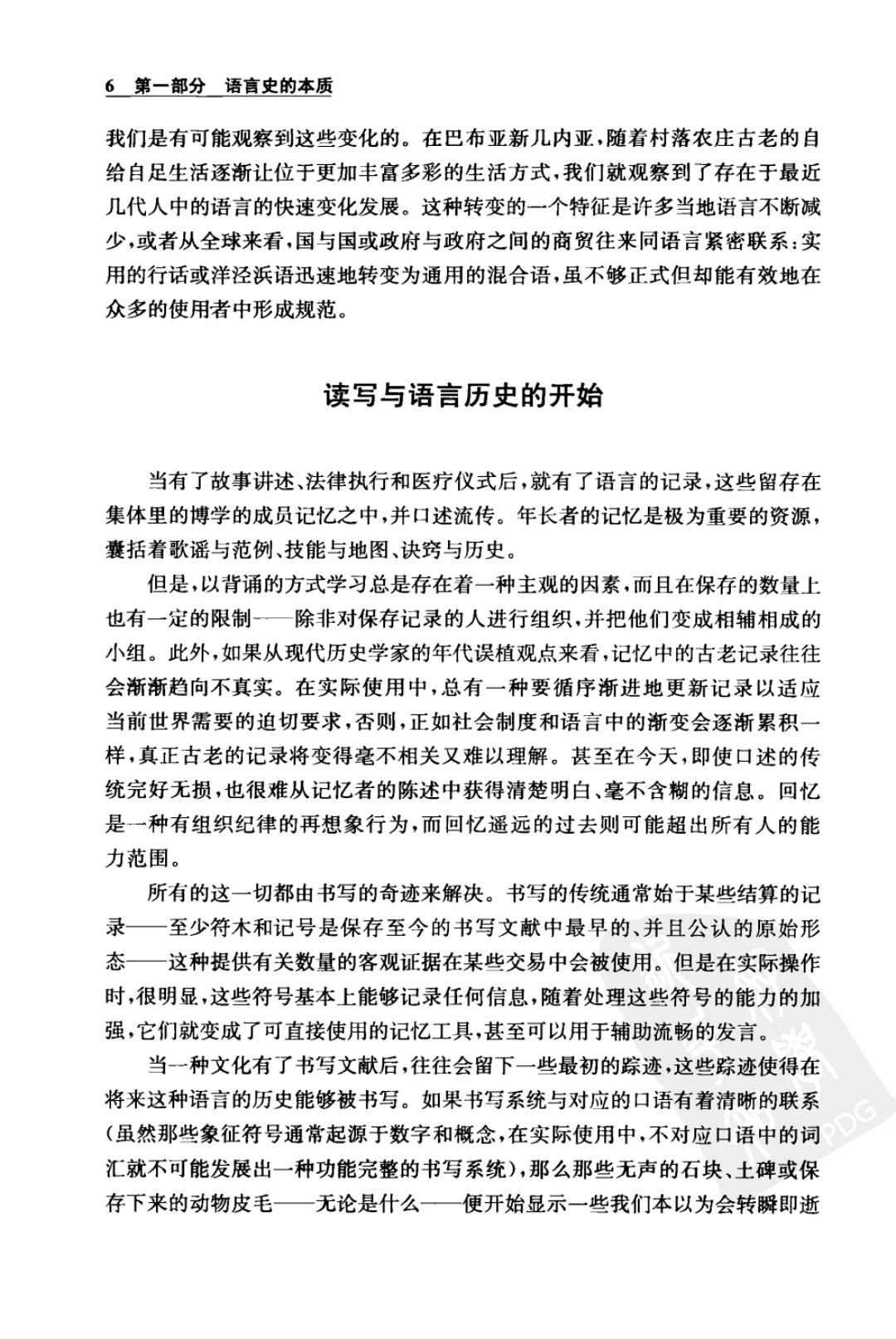
6第一部分语言史的本质 我们是有可能观察到这些变化的。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随着村落农庄古老的自 给自足生活逐渐让位于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我们就观察到了存在于最近 几代人中的语言的快速变化发展。这种转变的一个特征是许多当地语言不断减 少,或者从全球来看,国与国或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商贸往来同语言紧密联系:实 用的行话或洋泾浜语迅速地转变为通用的混合语,虽不够正式但却能有效地在 众多的使用者中形成规范。 读写与语言历史的开始 当有了故事讲述、法律执行和医疗仪式后,就有了语言的记录,这些留存在 集体里的博学的成员记忆之中,并口述流传。年长者的记忆是极为重要的资源, 囊括着歌谣与范例、技能与地图、诀窍与历史。 但是,以背诵的方式学习总是存在着一种主观的因素,而且在保存的数量上 也有一定的限制一除非对保存记录的人进行组织,并把他们变成相辅相成的 小组。此外,如果从现代历史学家的年代误植观点来看,记忆中的古老记录往往 会渐渐趋向不真实。在实际使用中,总有一种要循序渐进地更新记录以适应 当前世界需要的迫切要求,否则,正如社会制度和语言中的渐变会逐渐累积一 样,真正古老的记录将变得毫不相关又难以理解。甚至在今天,即使口述的传 统完好无损,也很难从记忆者的陈述中获得清楚明白、毫不含糊的信息。回忆 是一种有组织纪律的再想象行为,而回忆遥远的过去则可能超出所有人的能 力范围。 所有的这一切都由书写的奇迹来解决。书写的传统通常始于某些结算的记 录一至少符木和记号是保存至今的书写文献中最早的、并且公认的原始形 态一这种提供有关数量的客观证据在某些交易中会被使用。但是在实际操作 时,很明显,这些符号基本上能够记录任何信息,随着处理这些符号的能力的加 强,它们就变成了可直接使用的记忆工具,甚至可以用于辅助流畅的发言。 当一种文化有了书写文献后,往往会留下一些最初的踪迹,这些踪迹使得在 将来这种语言的历史能够被书写。如果书写系统与对应的口语有着清晰的联系 (虽然那些象征符号通常起源于数字和概念,在实际使用中,不对应口语中的词 汇就不可能发展出一种功能完整的书写系统),那么那些无声的石块、土碑或保 存下来的动物皮毛一无论是什么—便开始显示一些我们本以为会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