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群体研究 第一节个人与群体 如果要问什么是近代社会最重要的产物,我敢说那就是个人, 月从智人(homo sapiens)q在地球上出现,直至文艺复兴时期,人类 的视角总是“我们”(we或者us),也就是他们的群体或者家庭。人 们都受到来自群体和家庭的重大责任义务的约束。但是,一旦重 要的航行、贸易和科学分离了人类社会的单个原子一那些有思 想、有感情的单个生物一以后,人们活动的视角就变成了“我”(I 或者m)。这样的视角,在过去和现在都绝非轻松自如。我们相 信,一个名副其实的个人,其言行举止必定符合理智,判断人和事 物必定冷静客观,行动时必定胸有成竹,接受他人观点时,必定深 思熟虑,科学公正地反复考虑正反两方面的埋由,而不是屈从于权 ①智人,原为新人的分类名称。20世纪中期以来,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一般认 为古人和新人只有亚种的差别:因此,古人和新人同属智人。称古人为早期智人,称新 人为晚期樱人。晚期智人通常也称作现代人。也有人主张现代人的概念应局限于新石 器时代以后的人类

第·章群体研究 威或者大多数人的判断。我仁期望每个人都三思而行,期望他无 论作为单个人,还是与其伙伴同在时,都能受到理智及其利益的 指导。 但规察结果表明,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时不时地被 迫服从其主管利和上级的决定。他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其朋友,邻 居或者政党的观点。他还常常采纳周围人的态度、语言和品位格 调。更糟的是,一个人一旦加人一个群体,深陷于一群民众之中, 就可能变得过分暴躁、椋惶、热情或者残忍。他的行为举止与道德 良心相抵触,与其利益也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已完全变 成了另一个人。那就是不断困惑和惊扰我们的难解之谜。英国心 理学家巴特利特(Bartlett,F.)D在他的一部经典著作中引述一个 政治家的言论,对此作了清楚的表述:“社会行为是所有行为中最 大的奥秘。我为此不得不研究了一辈子。但我仍然不敢假装全部 都理解了。我可能对一个人已经了如指掌,但我仍然不敢说,他在 一个群体中首先会做些什么。”(巴特利特,1932:24) 这种不明确的原因何在呢?我们不可能说,一个朋友或者与 我们关系密切的人,他在专门会议上和政治集会上的举止,与他在 陪审团或者群体中的举止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对此,人们 总是说,在社会环境中,个人举止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道德良心, 或者表现出他们的最好方面。事实常常与此相反。他们的良好品 质趋于减少,逐渐败坏,而不是得到集中和升华。事实上,人类群 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 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因此,人们不能说,行为和思想 在这种情境下会趋向“平均值”。实际上,它们是最小的公分母的 平均值,也就是说,群体中的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 ①巴特利特(1886一1969),英国心理学家,以对记忆的研究而著名,强描述或个 案研究的方法,主要著作有《记忆:斌睑研究和社会心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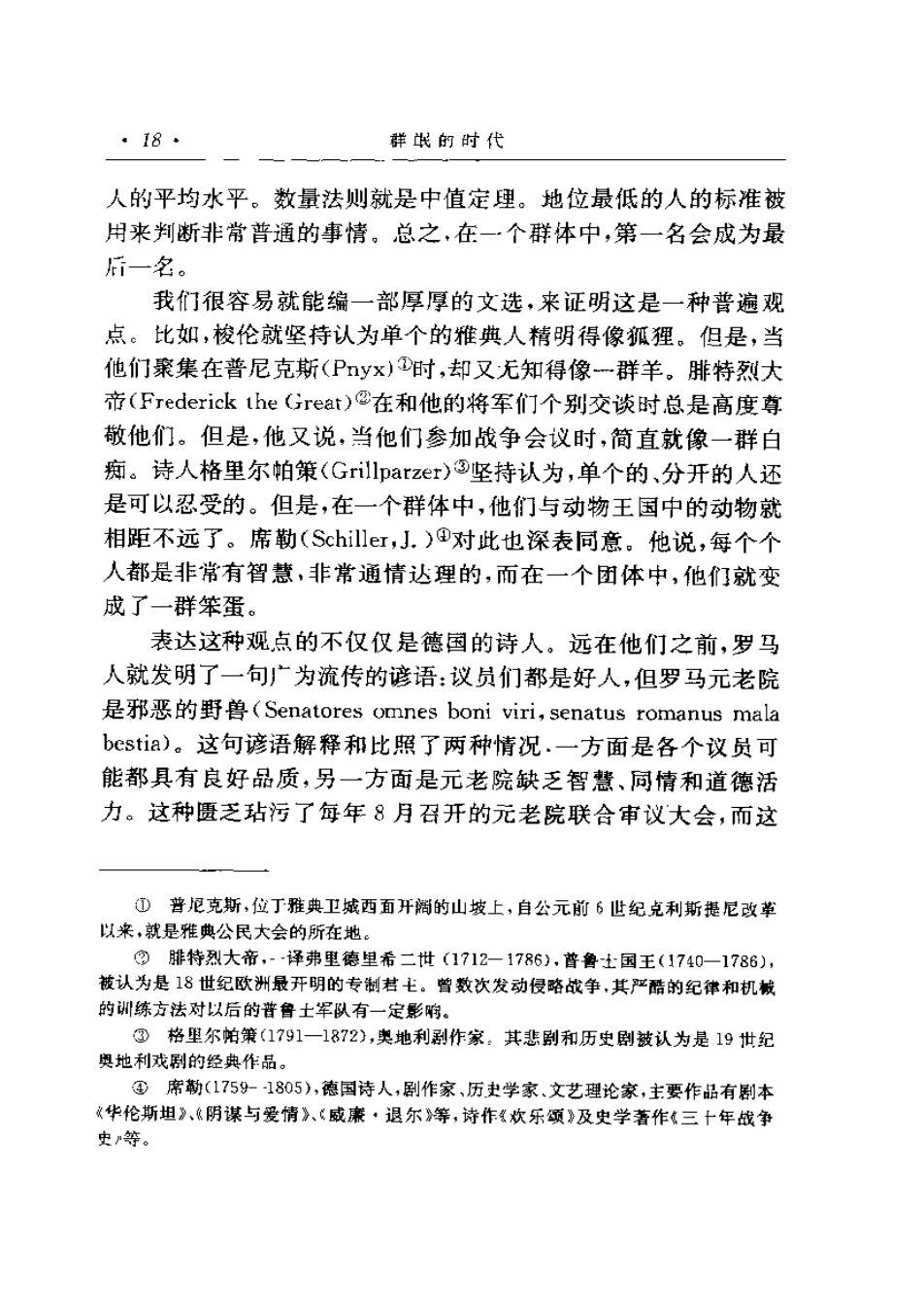
·18· 群氓的时代 人的平均水平。数量法则就是中值定理。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 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总之,在一·个群体中,第一名会成为最 后i一名。 我们很容易就能编一部厚厚的文选,来证明这是一种普遍观 点。比如,梭伦就坚持认为单个的雅典人精明得像狐狸。但是,当 他们聚集在普尼克斯(Pyx)③时,却又无知得像群羊。腓特烈大 帝(Frederick the(Great).②在和他的将军们个别交谈时,总是高度尊 敬他们。但是,他又说,当他们参加战争会议时,简直就像一群白 痴。诗人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③坚持认为,单个的、分开的人还 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在一个群体中,他们与动物王国中的动物就 相距不远了。席勒(Schiller,J.)④对此也深表同意。他说,每个个 人都是非常有智慧,非常通情达理的,而在一个团体中,他们就变 成了一群笨蛋。 表达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德国的诗人。远在他们之前,罗马 人就发明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议员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 是邪恶的野兽(Senatores omnes boni viri,senatus romanus mala bestia)。这句谚语解释和比照了两种情况.一方面是各个议员可 能都具有良好品质,另一方面是元老院缺乏智慧、同情和道德活 力。这种匮乏玷污了每年8月召开的元老院联合审议大会,而这 ①普厄克斯,位丁雅典卫城西面开搁的山坡上,自公元前6世纪克利斯提尼改草 以来,就是雅典公民大会的所在地。 ②腓特烈大帝,-译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一1786),普鲁土国王(1740一1786), 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最开明的专制君土。曾数次发动侵略战争,其严酷的纪律和机械 的训练方法对以后的普鲁土军队有一定影响。 ③格里尔帕策(1791一1872),奥地利别作家。其悲剧和历史剧被认为是19世纪 奥地利戏剧的经典作品。 ④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主要作品有剧本 《华伦斯坦》、《阴谋与爱情》、(威廉·退尔》等,诗作《炊乐颂》及史学著作《三十年战争 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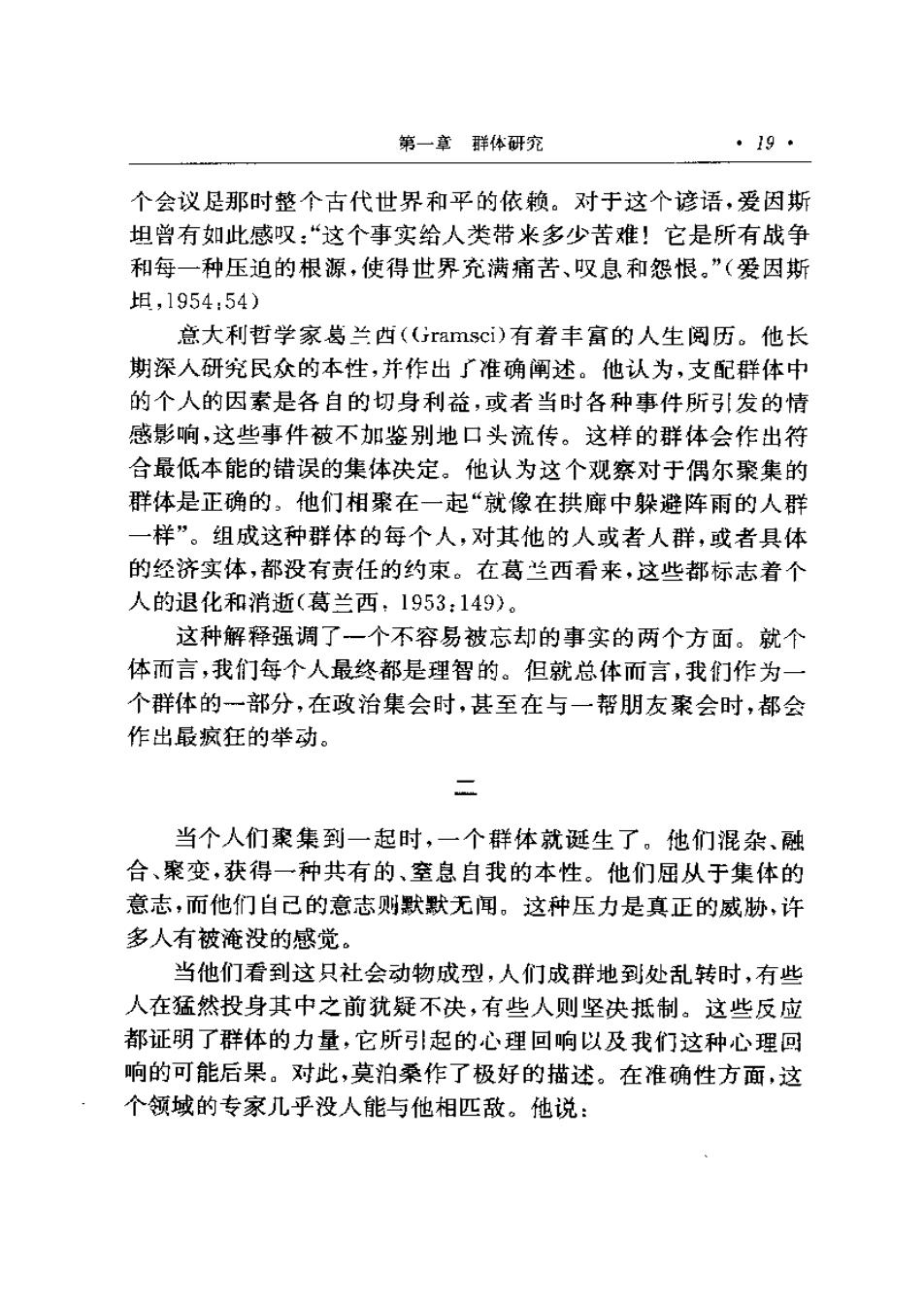
第一章群体研究 ·19 个会议是那时整个古代世界和平的依赖。对于这个谚语,爱因斯 坦曾有如此感叹:“这个事实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它是所有战争 和每一种压迫的根源,使得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怨恨。”(爱因斯 坦,1954:54) 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ramsci)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长 期深人研究民众的本性,并作出了准确阐述。他认为,支配群体中 的个人的因素是各自的切身利益,或者当时各种事件所引发的情 感影响,这些事件被不加鉴别地口头流传。这样的群体会作出符 合最低本能的错误的集体决定。他认为这个观察对于偶尔聚集的 群体是正确的。他们相聚在一起“就像在拱廊中躲避阵雨的人群 样”。组成这种群体的每个人,对其他的人或者人群,或者具体 的经济实体,都没有责任的约束。在葛兰西看来,这些都标志着个 人的退化和消逝(葛兰西,1953:149)。 这种解释强调了一个不容易被忘却的事实的两个方面。就个 体而言,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是理智的。但就总体而言,我们作为一 个群体的一部分,在政治集会时,甚至在与一帮朋友聚会时,都会 作出最疯在的举动。 当个人们聚集到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 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室息自我的本性。他们屈从于集体的 意志,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这种压力是真正的威胁,许 多人有被淹没的感觉。 当他们看到这只社会动物成型,人们成群地到处乱转时,有些 人在猛然投身其中之前犹疑不决,有些人则坚决抵制。这些反应 都证明了群体的力量,它所!起的心理回响以及我们这种心理回 响的可能后果。对此,莫泊桑作了极好的描述。在准确性方面,这 个领域的专家几乎没人能与他相匹敌。他说:

·20· 群氓的时代 此外,由于另一种理由,我对群体有一种恐惧。我不 能进电影院,或者观看公共集会。它们让我有一种奇怪 的无法忍受的不安全感、一种可怕的痛苦,似乎我在尽全 力搏击一种不可抵挡的神秘力量。其实我是在抵挡群本 的灵魂,它正在试图进入我的头脑。我多次注意到,当一 个人独处时,智慧就会增长,就会上升。而当一个人与其 他人混杂在一起时,智慧就减少并衰落。交生、广为传播 的思想、所有说出的话、被迫去听的话、听到并作出反应 的话,所有这些都会对一个人的思想产生影响。思想潮 起潮落,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 庭,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 个思想平面,也就是每一大群个人的平均智慧。每个人 都成了由他的伙伴组成的群氓的一部分。而这时,他自 身特有的素质一如智力的主动性、自由的意志、聪明的 反思,甚至还有洞察力一一都随之整个消失了。(莫泊 桑,1979:102) 莫泊桑对群体的偏见以及对个体的高度评价无疑都是些先人 之见。他对个人的评价也并不总是站得住脚。也许我应该罗列一 长串与他同时代和同阶层的人的观点。但无论如何,莫泊桑描述 了个人和集体(或者是艺术家和民众之间)交往的三个阶段,包括 本能恐惧、震惊和焦虑;随后是不可抗拒的被剥夺感,最后是反反 复复,可感党而不可见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必然都回响着真理 的声音。 莫泊桑的描写也显示了个人被人群淹没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那就是智力的平均化、创造力的停顿,以及群体灵魂对个体灵魂的 吞并。上述后果当然还不是全部,而只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那些内 容。莫泊桑的恐惧感帮助他认清了他焦虑的两个原因,一个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