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定会揭露出他扮演的是亲自动手直接指挥的角色,他曾共谋参与或批准赞同 “四人帮”犯下的大量罪行。毛泽东的名誉不容遭受污染:它对党的统治的 合法性来说至今仍然占据着心位置。 第二个原因不仅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而且涉及到整个国家。因为毛泽 东企望锻炼出新一代的革命者,他用“造反有理”口号鼓动青年并号召他们 “炮打司令部”。毛首先罢黜了那些试图约束青年的同僚,以此清扫了道 路,致使很多地方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即互相争斗人人自危的野蛮状 态),中学生和大学生实施暴力和恐怖整整两年,最先斗老师,然后斗党内 干部,最后自己互相斗。在文革刚结束时出现的“伤痕文学”和以后的一些 红卫兵回忆录,仅仅触及了事情的皮毛。假使作家巴金的建议一建立一个 文革博物馆一真能够实现的话,那么挖掘将会深刻得多。但是,真正的研 究可能形成对整个一代人的指控一那些文革的参与者和观看者。他们现在 正要掌握国家的领导权。 这样一种指控只应当由一个中国人来做。在其最有名的小说《苍蝇 王》中,英国作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姆·戈登暗示,如果没有父母和社 会的约束,任何地方的年轻人都可能行为残暴。然而,文革开始时,中国的 年轻人不单摆脱了管束,他们受到来自最高层的怂恿鼓动。而那些并非在中 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及其暴力文化中长大的人大概很难确定在红卫兵横冲直撞 的狂暴日子里他们是如何行事的。 王友琴是生于中国而现在美国从事在中国不能做成的文革研究的学者 之一。在这本书里,王教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着使中国人正视其近 期历史的方向。经过她的长期刻苦的努力,无疑还遇到过大量的挫折和阻 碍,她揭开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纱,特别是在她界定为文革中最残忍的两个时 期中的暴力。这两个时期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夏天,以及由“革命 委员会”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1968年冬天。在书中,她一个接一 个地详细描述了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希望以此种方式确保他们将不会被遗 忘。王友琴作为先锋开始了这种对红卫兵暴力以及随后的官方暴力的详尽透 彻的分析。但是,如果她的这种分析依然不能引导中国人重视确立各种制度 以防止这类暴行,至少要防止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暴行再次发生,这些受难 者还将会是白白死了。 (Roderick MacFarquhar是哈佛大学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现任政 府系系主任)■ 20 中因信息中心制作
前言 20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定会揭露出他扮演的是亲自动手直接指挥的角色,他曾共谋参与或批准赞同 “四人帮”犯下的大量罪行。毛泽东的名誉不容遭受污染;它对党的统治的 合法性来说至今仍然占据着心位置。 第二个原因不仅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而且涉及到整个国家。因为毛泽 东企望锻炼出新一代的革命者,他用“造反有理”口号鼓动青年并号召他们 “炮打司令部”。毛首先罢黜了那些试图约束青年的同僚,以此清扫了道 路,致使很多地方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即互相争斗人人自危的野蛮状 态),中学生和大学生实施暴力和恐怖整整两年,最先斗老师,然后斗党内 干部,最后自己互相斗。在文革刚结束时出现的“伤痕文学”和以后的一些 红卫兵回忆录,仅仅触及了事情的皮毛。假使作家巴金的建议——建立一个 文革博物馆——真能够实现的话,那么挖掘将会深刻得多。但是,真正的研 究可能形成对整个一代人的指控——那些文革的参与者和观看者。他们现在 正要掌握国家的领导权。 这样一种指控只应当由一个中国人来做。在其最有名的小说《苍蝇 王》中,英国作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姆·戈登暗示,如果没有父母和社 会的约束,任何地方的年轻人都可能行为残暴。然而,文革开始时,中国的 年轻人不单摆脱了管束,他们受到来自最高层的怂恿鼓动。而那些并非在中 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及其暴力文化中长大的人大概很难确定在红卫兵横冲直撞 的狂暴日子里他们是如何行事的。 王友琴是生于中国而现在美国从事在中国不能做成的文革研究的学者 之一。在这本书里,王教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着使中国人正视其近 期历史的方向。经过她的长期刻苦的努力,无疑还遇到过大量的挫折和阻 碍,她揭开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纱,特别是在她界定为文革中最残忍的两个时 期中的暴力。这两个时期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 1966 年夏天,以及由“革命 委员会”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 1968 年冬天。在书中,她一个接一 个地详细描述了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希望以此种方式确保他们将不会被遗 忘。王友琴作为先锋开始了这种对红卫兵暴力以及随后的官方暴力的详尽透 彻的分析。但是,如果她的这种分析依然不能引导中国人重视确立各种制度 以防止这类暴行,至少要防止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暴行再次发生,这些受难 者还将会是白白死了。 (Roderick MacFarquhar 是哈佛大学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现任政 府系系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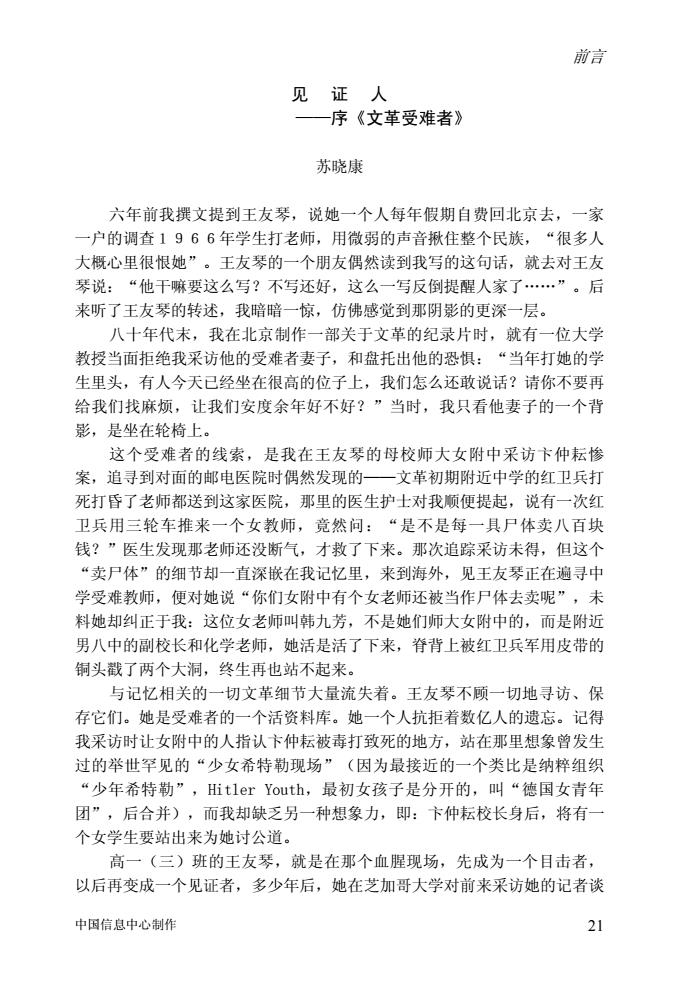
前言 见 证人 序《文革受难者》 苏晓康 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说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 一户的调查1966年学生打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很多人 大概心里很恨她”。王友琴的一个朋友偶然读到我写的这句话,就去对王友 琴说:“他干嘛要这么写?不写还好,这么一写反倒提醒人家了…”。后 来听了王友琴的转述,我暗暗一惊,仿佛感觉到那阴影的更深一层。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制作一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时,就有一位大学 教授当面拒绝我采访他的受难者妻子,和盘托出他的恐惧:“当年打她的学 生里头,有人今天已经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们怎么还敢说话?请你不要再 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安度余年好不好?”当时,我只看他妻子的一个背 影,是坐在轮椅上。 这个受难者的线索,是我在王友琴的母校师大女附中采访卞仲耘惨 案,追寻到对面的邮电医院时偶然发现的一文革初期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 死打昏了老师都送到这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顺便提起,说有一次红 卫兵用三轮车推来一个女教师,竟然问:“是不是每一具尸体卖八百块 钱?”医生发现那老师还没断气,才救了下来。那次追踪采访未得,但这个 “卖尸体”的细节却一直深嵌在我记忆里,来到海外,见王友琴正在遍寻中 学受难教师,便对她说“你们女附中有个女老师还被当作尸体去卖呢”,未 料她却纠正于我:这位女老师叫韩九芳,不是她们师大女附中的,而是附近 男八中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她活是活了下来,脊背上被红卫兵军用皮带的 铜头戳了两个大洞,终生再也站不起来。 与记忆相关的一切文革细节大量流失着。王友琴不顾一切地寻访、保 存它们。她是受难者的一个活资料库。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记得 我采访时让女附中的人指认卞仲耘被毒打致死的地方,站在那里想象曾发生 过的举世罕见的“少女希特勒现场”(因为最接近的一个类比是纳粹组织 “少年希特勒”,Hitler Youth,最初女孩子是分开的,叫“德国女青年 团”,后合并),而我却缺乏另一种想象力,即:卞仲耘校长身后,将有一 个女学生要站出来为她讨公道。 高一(三)班的王友琴,就是在那个血腥现场,先成为一个目击者, 以后再变成一个见证者,多少年后,她在芝加哥大学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谈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21
前言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21 见 证 人 ——序《文革受难者》 苏晓康 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说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 一户的调查1966年学生打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很多人 大概心里很恨她”。王友琴的一个朋友偶然读到我写的这句话,就去对王友 琴说:“他干嘛要这么写?不写还好,这么一写反倒提醒人家了……”。后 来听了王友琴的转述,我暗暗一惊,仿佛感觉到那阴影的更深一层。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制作一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时,就有一位大学 教授当面拒绝我采访他的受难者妻子,和盘托出他的恐惧:“当年打她的学 生里头,有人今天已经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们怎么还敢说话?请你不要再 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安度余年好不好?”当时,我只看他妻子的一个背 影,是坐在轮椅上。 这个受难者的线索,是我在王友琴的母校师大女附中采访卞仲耘惨 案,追寻到对面的邮电医院时偶然发现的——文革初期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 死打昏了老师都送到这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顺便提起,说有一次红 卫兵用三轮车推来一个女教师,竟然问:“是不是每一具尸体卖八百块 钱?”医生发现那老师还没断气,才救了下来。那次追踪采访未得,但这个 “卖尸体”的细节却一直深嵌在我记忆里,来到海外,见王友琴正在遍寻中 学受难教师,便对她说“你们女附中有个女老师还被当作尸体去卖呢”,未 料她却纠正于我:这位女老师叫韩九芳,不是她们师大女附中的,而是附近 男八中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她活是活了下来,脊背上被红卫兵军用皮带的 铜头戳了两个大洞,终生再也站不起来。 与记忆相关的一切文革细节大量流失着。王友琴不顾一切地寻访、保 存它们。她是受难者的一个活资料库。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记得 我采访时让女附中的人指认卞仲耘被毒打致死的地方,站在那里想象曾发生 过的举世罕见的“少女希特勒现场”(因为最接近的一个类比是纳粹组织 “少年希特勒”,Hitler Youth,最初女孩子是分开的,叫“德国女青年 团”,后合并),而我却缺乏另一种想象力,即:卞仲耘校长身后,将有一 个女学生要站出来为她讨公道。 高一(三)班的王友琴,就是在那个血腥现场,先成为一个目击者, 以后再变成一个见证者,多少年后,她在芝加哥大学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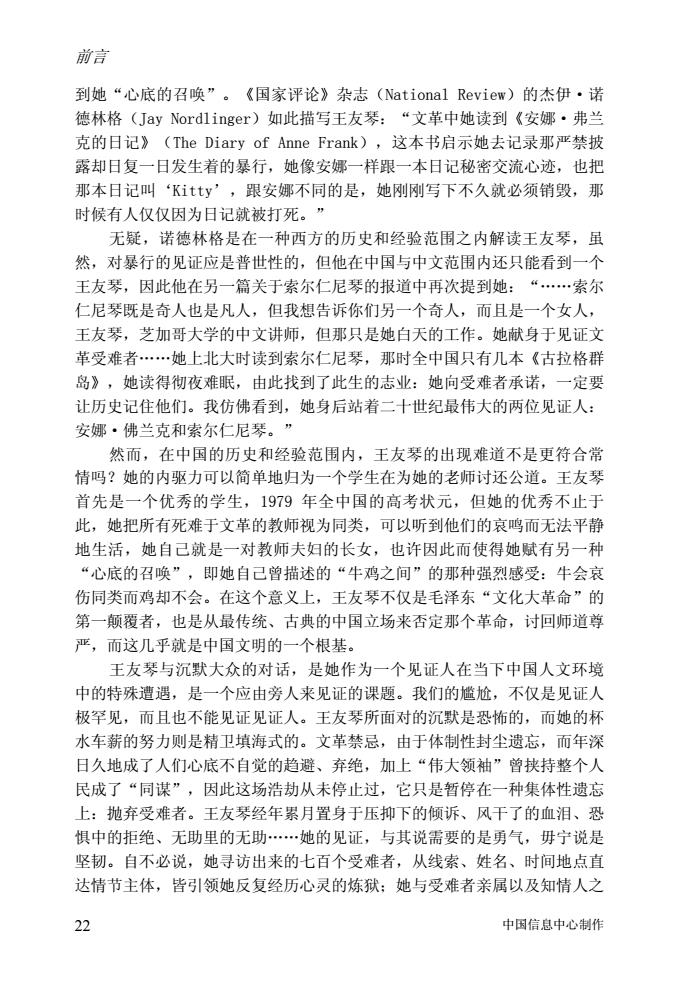
前言 到她“心底的召唤”。《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的杰伊·诺 德林格(Jay Nordlinger)如此描写王友琴:“文革中她读到《安娜·弗兰 克的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这本书启示她去记录那严禁披 露却日复一日发生着的暴行,她像安娜一样跟一本日记秘密交流心迹,也把 那本日记叫‘Ktty’,跟安娜不同的是,她刚刚写下不久就必须销毁,那 时候有人仅仅因为日记就被打死。” 无疑,诺德林格是在一种西方的历史和经验范围之内解读王友琴,虽 然,对暴行的见证应是普世性的,但他在中国与中文范围内还只能看到一个 王友琴,因此他在另一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报道中再次提到她:“…索尔 仁尼琴既是奇人也是凡人,但我想告诉你们另一个奇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王友琴,芝加哥大学的中文讲师,但那只是她白天的工作。她献身于见证文 革受难者…她上北大时读到索尔仁尼琴,那时全中国只有几本《古拉格群 岛》,她读得彻夜难眠,由此找到了此生的志业:她向受难者承诺,一定要 让历史记住他们。我仿佛看到,她身后站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见证人: 安娜·佛兰克和索尔仁尼琴。”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和经验范围内,王友琴的出现难道不是更符合常 情吗?她的内驱力可以简单地归为一个学生在为她的老师讨还公道。王友琴 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生,1979年全中国的高考状元,但她的优秀不止于 此,她把所有死难于文革的教师视为同类,可以听到他们的哀鸣而无法平静 地生活,她自己就是一对教师夫妇的长女,也许因此而使得她赋有另一种 “心底的召唤”,即她自己曾描述的“牛鸡之间”的那种强烈感受:牛会哀 伤同类而鸡却不会。在这个意义上,王友琴不仅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 第一颠覆者,也是从最传统、古典的中国立场来否定那个革命,讨回师道尊 严,而这几乎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根基。 王友琴与沉默大众的对话,是她作为一个见证人在当下中国人文环境 中的特殊遭遇,是一个应由旁人来见证的课题。我们的尴尬,不仅是见证人 极罕见,而且也不能见证见证人。王友琴所面对的沉默是恐怖的,而她的杯 水车薪的努力则是精卫填海式的。文革禁忌,由于体制性封尘遗忘,而年深 日久地成了人们心底不自觉的趋避、弃绝,加上“伟大领袖”曾挟持整个人 民成了“同谋”,因此这场浩劫从未停止过,它只是暂停在一种集体性遗忘 上:抛弃受难者。王友琴经年累月置身于压抑下的倾诉、风干了的血泪、恐 惧中的拒绝、无助里的无助…她的见证,与其说需要的是勇气,毋宁说是 坚韧。自不必说,她寻访出来的七百个受难者,从线索、姓名、时间地点直 达情节主体,皆引领她反复经历心灵的炼狱:她与受难者亲属以及知情人之 22 中因信息中心制作
前言 22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到她“心底的召唤”。《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的杰伊·诺 德林格(Jay Nordlinger)如此描写王友琴:“文革中她读到《安娜·弗兰 克的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这本书启示她去记录那严禁披 露却日复一日发生着的暴行,她像安娜一样跟一本日记秘密交流心迹,也把 那本日记叫‘Kitty’,跟安娜不同的是,她刚刚写下不久就必须销毁,那 时候有人仅仅因为日记就被打死。” 无疑,诺德林格是在一种西方的历史和经验范围之内解读王友琴,虽 然,对暴行的见证应是普世性的,但他在中国与中文范围内还只能看到一个 王友琴,因此他在另一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报道中再次提到她:“……索尔 仁尼琴既是奇人也是凡人,但我想告诉你们另一个奇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王友琴,芝加哥大学的中文讲师,但那只是她白天的工作。她献身于见证文 革受难者……她上北大时读到索尔仁尼琴,那时全中国只有几本《古拉格群 岛》,她读得彻夜难眠,由此找到了此生的志业:她向受难者承诺,一定要 让历史记住他们。我仿佛看到,她身后站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见证人: 安娜·佛兰克和索尔仁尼琴。”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和经验范围内,王友琴的出现难道不是更符合常 情吗?她的内驱力可以简单地归为一个学生在为她的老师讨还公道。王友琴 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生,1979 年全中国的高考状元,但她的优秀不止于 此,她把所有死难于文革的教师视为同类,可以听到他们的哀鸣而无法平静 地生活,她自己就是一对教师夫妇的长女,也许因此而使得她赋有另一种 “心底的召唤”,即她自己曾描述的“牛鸡之间”的那种强烈感受:牛会哀 伤同类而鸡却不会。在这个意义上,王友琴不仅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 第一颠覆者,也是从最传统、古典的中国立场来否定那个革命,讨回师道尊 严,而这几乎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根基。 王友琴与沉默大众的对话,是她作为一个见证人在当下中国人文环境 中的特殊遭遇,是一个应由旁人来见证的课题。我们的尴尬,不仅是见证人 极罕见,而且也不能见证见证人。王友琴所面对的沉默是恐怖的,而她的杯 水车薪的努力则是精卫填海式的。文革禁忌,由于体制性封尘遗忘,而年深 日久地成了人们心底不自觉的趋避、弃绝,加上“伟大领袖”曾挟持整个人 民成了“同谋”,因此这场浩劫从未停止过,它只是暂停在一种集体性遗忘 上:抛弃受难者。王友琴经年累月置身于压抑下的倾诉、风干了的血泪、恐 惧中的拒绝、无助里的无助……她的见证,与其说需要的是勇气,毋宁说是 坚韧。自不必说,她寻访出来的七百个受难者,从线索、姓名、时间地点直 达情节主体,皆引领她反复经历心灵的炼狱;她与受难者亲属以及知情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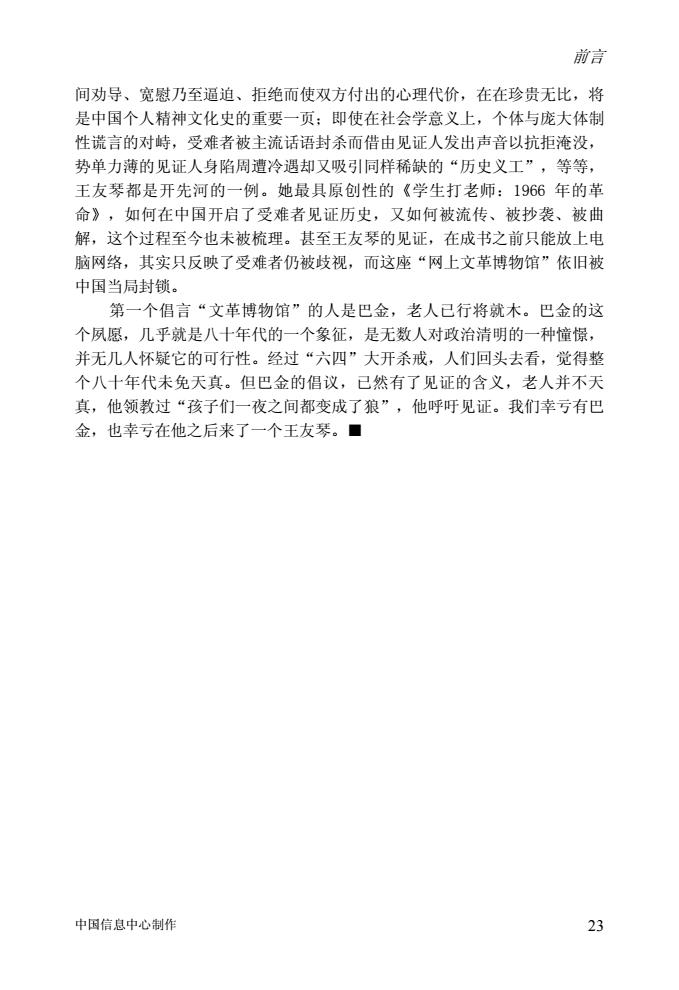
前言 间劝导、宽慰乃至逼迫、拒绝而使双方付出的心理代价,在在珍贵无比,将 是中国个人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一页:即使在社会学意义上,个体与庞大体制 性谎言的对峙,受难者被主流话语封杀而借由见证人发出声音以抗拒淹没, 势单力薄的见证人身陷周遭冷遇却又吸引同样稀缺的“历史义工”,等等, 王友琴都是开先河的一例。她最具原创性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 命》,如何在中国开启了受难者见证历史,又如何被流传、被抄袭、被曲 解,这个过程至今也未被梳理。甚至王友琴的见证,在成书之前只能放上电 脑网络,其实只反映了受难者仍被歧视,而这座“网上文革博物馆”依旧被 中国当局封锁。 第一个倡言“文革博物馆”的人是巴金,老人已行将就木。巴金的这 个夙愿,几乎就是八十年代的一个象征,是无数人对政治清明的一种憧憬, 并无几人怀疑它的可行性。经过“六四”大开杀戒,人们回头去看,觉得整 个八十年代未免天真。但巴金的倡议,已然有了见证的含义,老人并不天 真,他领教过“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他呼吁见证。我们幸亏有巴 金,也幸亏在他之后来了一个王友琴。■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23
前言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23 间劝导、宽慰乃至逼迫、拒绝而使双方付出的心理代价,在在珍贵无比,将 是中国个人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一页;即使在社会学意义上,个体与庞大体制 性谎言的对峙,受难者被主流话语封杀而借由见证人发出声音以抗拒淹没, 势单力薄的见证人身陷周遭冷遇却又吸引同样稀缺的“历史义工”,等等, 王友琴都是开先河的一例。她最具原创性的《学生打老师:1966 年的革 命》,如何在中国开启了受难者见证历史,又如何被流传、被抄袭、被曲 解,这个过程至今也未被梳理。甚至王友琴的见证,在成书之前只能放上电 脑网络,其实只反映了受难者仍被歧视,而这座“网上文革博物馆”依旧被 中国当局封锁。 第一个倡言“文革博物馆”的人是巴金,老人已行将就木。巴金的这 个夙愿,几乎就是八十年代的一个象征,是无数人对政治清明的一种憧憬, 并无几人怀疑它的可行性。经过“六四”大开杀戒,人们回头去看,觉得整 个八十年代未免天真。但巴金的倡议,已然有了见证的含义,老人并不天 真,他领教过“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他呼吁见证。我们幸亏有巴 金,也幸亏在他之后来了一个王友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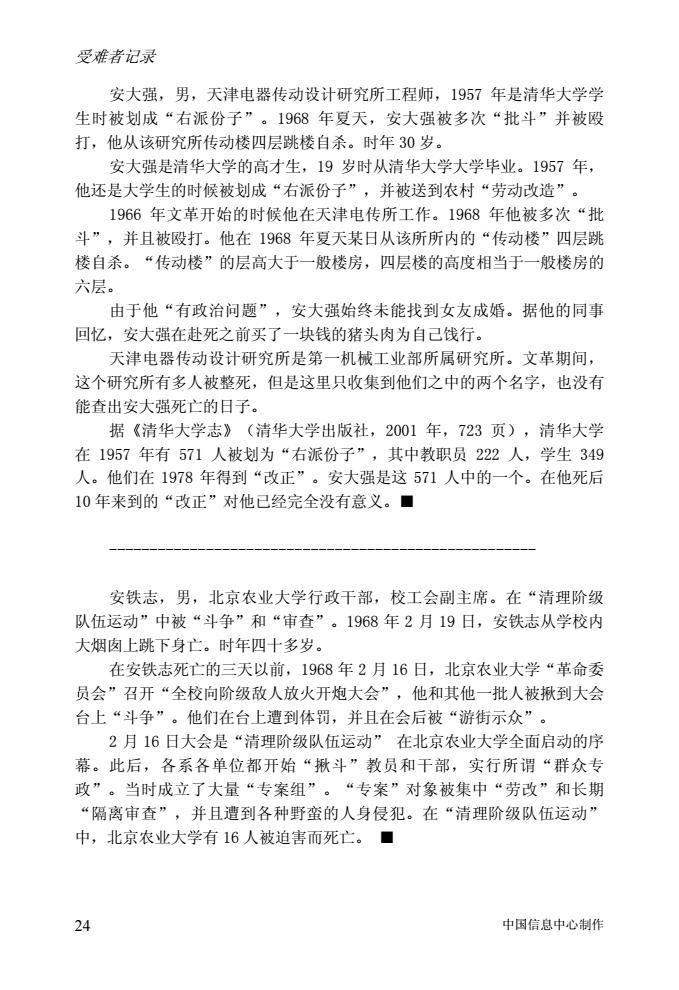
受谁者记录 安大强,男,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工程师,1957年是清华大学学 生时被划成“右派份子”。1968年夏天,安大强被多次“批斗”并被殴 打,他从该研究所传动楼四层跳楼自杀。时年30岁。 安大强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19岁时从清华大学大学毕业。1957年, 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在天津电传所工作。1968年他被多次“批 斗”,并且被殴打。他在1968年夏天某日从该所所内的“传动楼”四层跳 楼自杀。“传动楼”的层高大于一般楼房,四层楼的高度相当于一般楼房的 六层。 由于他“有政治问题”,安大强始终未能找到女友成婚。据他的同事 回忆,安大强在赴死之前买了一块钱的猪头肉为自己饯行。 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是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研究所。文革期间, 这个研究所有多人被整死,但是这里只收集到他们之中的两个名字,也没有 能查出安大强死亡的日子。 据《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723页),清华大学 在1957年有571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其中教职员222人,学生349 人。他们在1978年得到“改正”。安大强是这571人中的一个。在他死后 10年来到的“改正”对他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安铁志,男,北京农业大学行政干部,校工会副主席。在“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中被“斗争”和“审查”。1968年2月19日,安铁志从学校内 大烟囱上跳下身亡。时年四十多岁。 在安铁志死亡的三天以前,1968年2月16日,北京农业大学“革命委 员会”召开“全校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大会”,他和其他一批人被揪到大会 台上“斗争”。他们在台上遭到体罚,并且在会后被“游街示众”。 2月16日大会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北京农业大学全面启动的序 幕。此后,各系各单位都开始“揪斗”教员和干部,实行所谓“群众专 政”。当时成立了大量“专案组”。“专案”对象被集中“劳改”和长期 “隔离审查”,并且遭到各种野蛮的人身侵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北京农业大学有16人被迫害而死亡。■ 24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受难者记录 24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安大强,男,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工程师,1957 年是清华大学学 生时被划成“右派份子”。1968 年夏天,安大强被多次“批斗”并被殴 打,他从该研究所传动楼四层跳楼自杀。时年 30 岁。 安大强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19 岁时从清华大学大学毕业。1957 年, 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在天津电传所工作。1968 年他被多次“批 斗”,并且被殴打。他在 1968 年夏天某日从该所所内的“传动楼”四层跳 楼自杀。“传动楼”的层高大于一般楼房,四层楼的高度相当于一般楼房的 六层。 由于他“有政治问题”,安大强始终未能找到女友成婚。据他的同事 回忆,安大强在赴死之前买了一块钱的猪头肉为自己饯行。 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是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研究所。文革期间, 这个研究所有多人被整死,但是这里只收集到他们之中的两个名字,也没有 能查出安大强死亡的日子。 据《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723 页),清华大学 在 1957 年有 571 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其中教职员 222 人,学生 349 人。他们在 1978 年得到“改正”。安大强是这 571 人中的一个。在他死后 10 年来到的“改正”对他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 安铁志,男,北京农业大学行政干部,校工会副主席。在“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中被“斗争”和“审查”。1968 年 2 月 19 日,安铁志从学校内 大烟囱上跳下身亡。时年四十多岁。 在安铁志死亡的三天以前,1968 年 2 月 16 日,北京农业大学“革命委 员会”召开“全校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大会”,他和其他一批人被揪到大会 台上“斗争”。他们在台上遭到体罚,并且在会后被“游街示众”。 2 月 16 日大会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在北京农业大学全面启动的序 幕。此后,各系各单位都开始“揪斗”教员和干部,实行所谓“群众专 政”。当时成立了大量“专案组”。“专案”对象被集中“劳改”和长期 “隔离审查”,并且遭到各种野蛮的人身侵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北京农业大学有 16 人被迫害而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