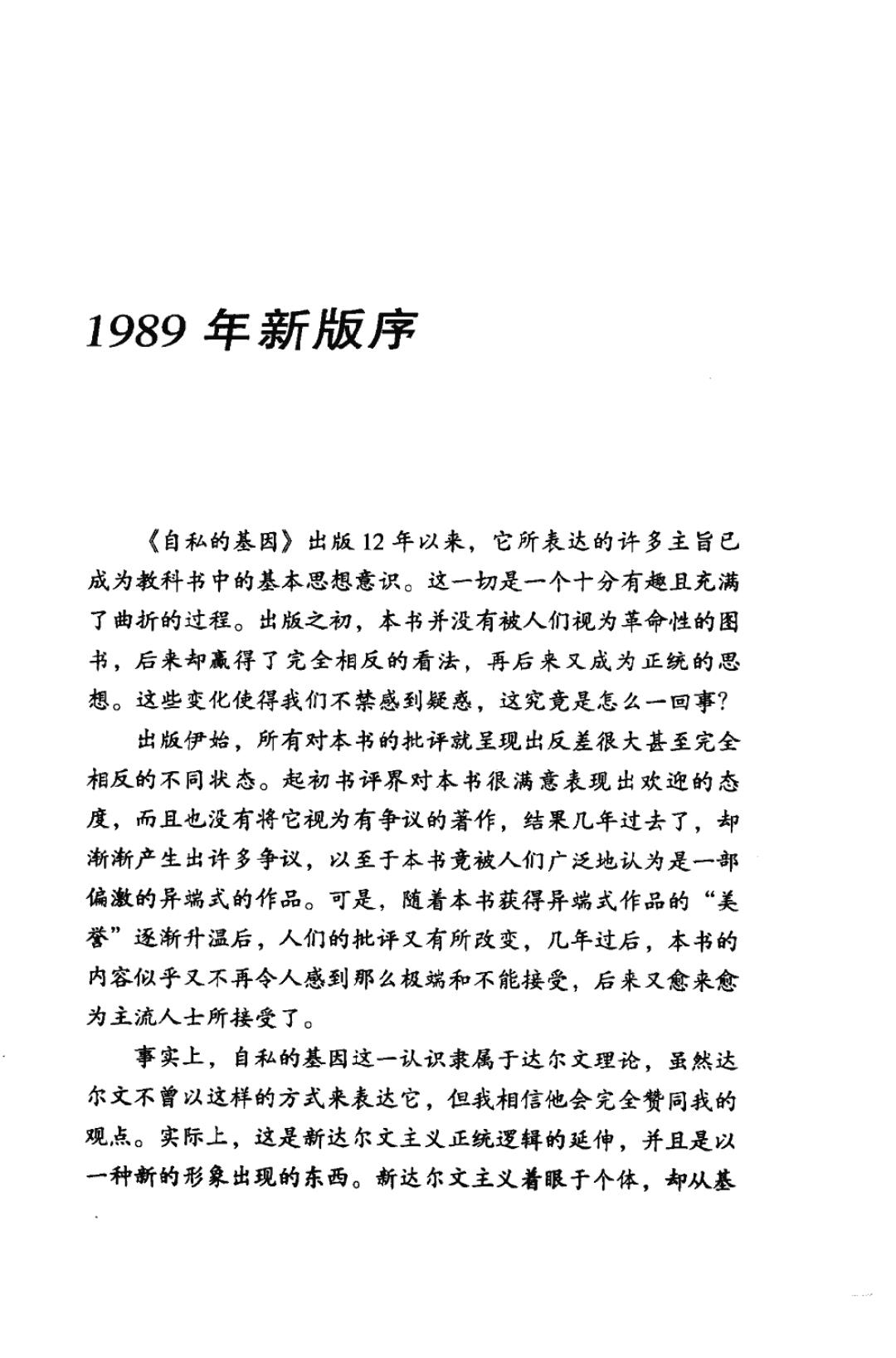
1989年新版序 《自私的基因》出版12年以来,它所表达的许多主旨已 成为教科书中的基本思想意识。这一切是一个十分有趣且充满 了曲折的过程。出版之初,本书并没有被人们视为革命性的图 书,后来却赢得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再后来又成为正统的思 想。这些变化使得我们不禁感到疑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出版伊始,所有对本书的批评就呈现出反差很大甚至完全 相反的不同状态。起初书评界对本书很满意表现出欢迎的态 度,而且也没有将它视为有争议的著作,结果几年过去了,却 渐渐产生出许多争议,以至于本书竟被人们广泛地认为是一部 偏激的异端式的作品。可是,随着本书获得异端式作品的“美 誉”逐渐升温后,人们的批评又有所改变,几年过后,本书的 内容似乎又不再令人感到那么极端和不能接受,后来又愈来愈 为主流人士所接受了。 事实上,自私的基因这一认识隶属于达尔文理论,虽然达 尔文不曾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它,但我相信他会完全赞同我的 观,点。实际上,这是新达尔文主义正统逻辑的延伸,并且是以 一种新的形象出现的东西。新达尔文主义着眼于个体,却从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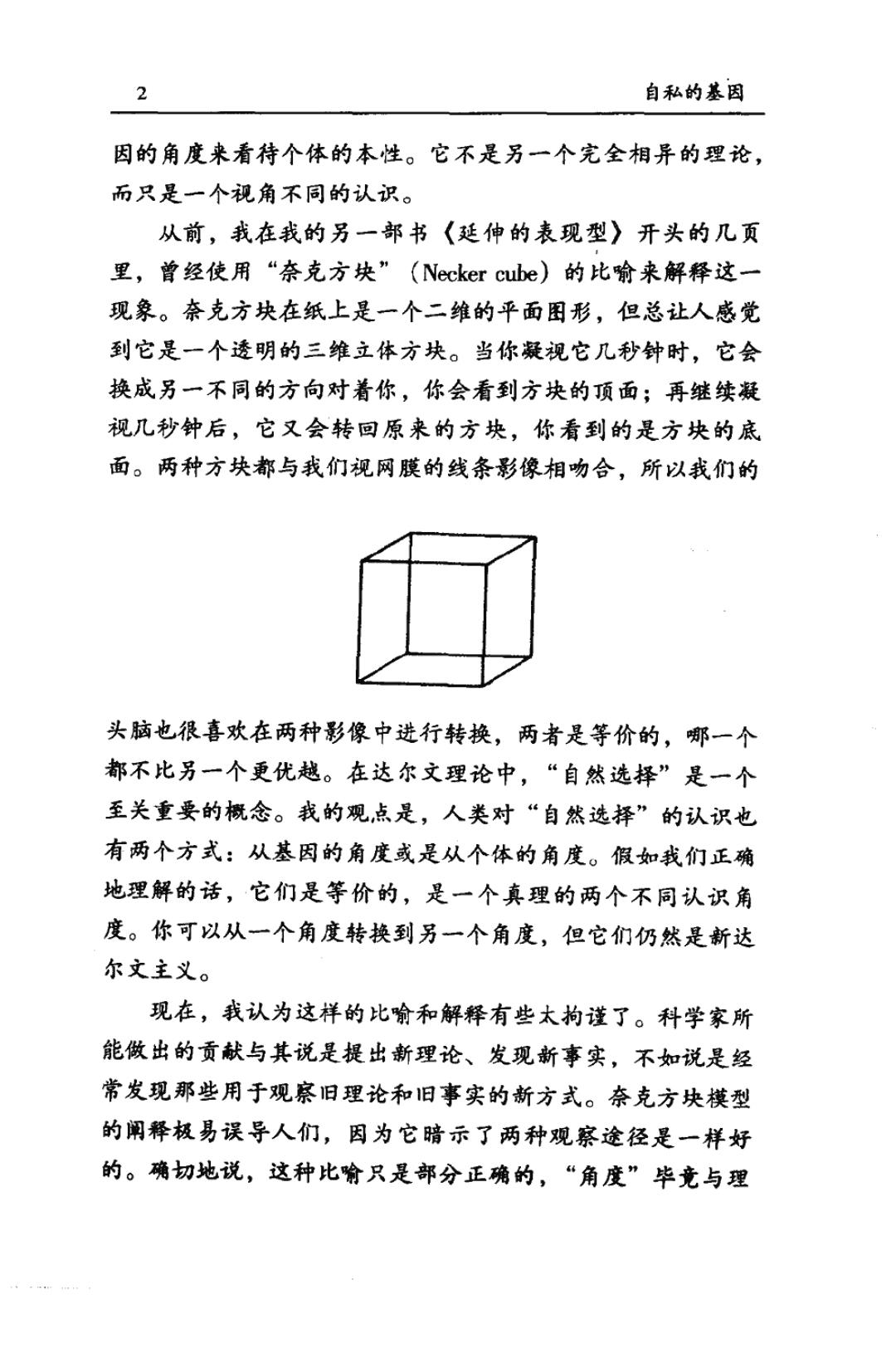
2 自私的基因 因的角度来看待个体的本性。它不是另一个完全相异的理论, 而只是一个视角不同的认识。 从前,我在我的另一部书《延伸的表现型》开头的几页 里,曾经使用“奈克方块”(Necker cube)的比喻来解释这一 现象。奈克方块在纸上是一个二维的平面图形,但总让人感觉 到它是一个透明的三维立体方块。当你凝视它几秒钟时,它会 换成另一不同的方向对着你,你会看到方块的顶面;再继续疑 视几秒钟后,它又会转回原来的方块,你看到的是方块的底 面。两种方块都与我们视网膜的线条影像相吻合,所以我们的 头脑也很喜欢在两种影像中进行转换,两者是等价的,哪一个 都不比另一个更优越。在达尔文理论中,“自然选择”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概念。我的观,点是,人类对“自然选择”的认识也 有两个方式:从基因的角度或是从个体的角度。假如我们正确 地理解的话,它们是等价的,是一个真理的两个不同认识角 度。你可以从一个角度转换到另一个角度,但它们仍然是新达 尔文主义。 现在,我认为这样的比喻和解释有些太拘谨了。科学家所 能做出的贡献与其说是提出新理论、发现新事实,不如说是经 常发现那些用于观察旧理论和旧事实的新方式。奈克方块模型 的阐释极易误导人们,因为它暗示了两种观察途径是一样好 的。确切地说,这种比喻只是部分正确的,“角度”毕竟与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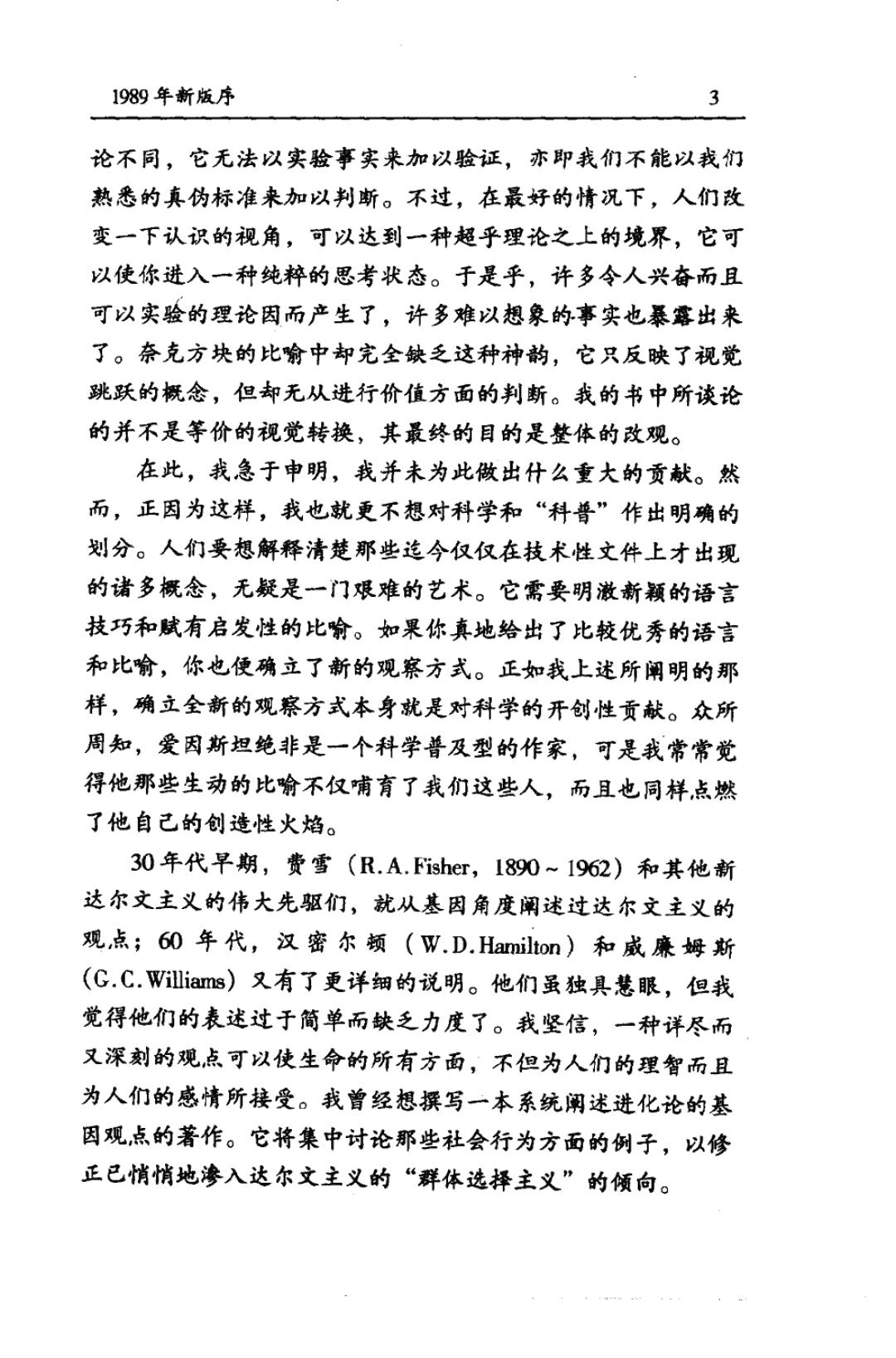
1989年新版序 论不同,它无法以实验事实来加以验证,亦即我们不能以我们 熟悉的真伪标准来加以判断。不过,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改 变一下认识的视角,可以达到一种超乎理论之上的境界,它可 以使你进入一种纯粹的思考状态。于是乎,许多令人兴奋而且 可以实验的理论因而产生了,许多难以想象的事实也暴露出来 了。奈克方块的比喻中却完全缺乏这种神韵,它只反映了视觉 跳跃的概念,但却无从进行价值方面的判断。我的书中所谈论 的并不是等价的视觉转换,其最终的目的是整体的改观。 在此,我急于申明,我并未为此做出什么重大的贡献。然 而,正因为这样,我也就更不想对科学和“科普”作出明确的 划分。人们要想解释清楚那些迄今仅仅在技术性文件上才出现 的诸多概念,无疑是一门艰难的艺术。它需要明澈新颖的语言 技巧和赋有启发性的比喻。如果你真地给出了比较优秀的语言 和比喻,你也便确立了新的观察方式。正如我上述所阐明的那 样,确立全新的观察方式本身就是对科学的开创性贡献。众所 周知,爱因斯坦绝非是一个科学普及型的作家,可是我常常觉 得他那些生动的比喻不仅甫育了我们这些人,而且也同样点燃 了他自己的创造性火焰。 30年代早期,费雪(R.A.Fisher,1890~1962)和其他新 达尔文主义的伟大先驱们,就从基因角度阐述过达尔文主义的 观,点;60年代,汉密尔顿(W.D.Hamilton)和成廉姆斯 (G.C.Williams)又有了更详细的说明。他们虽独具慧眼,但我 觉得他们的表述过于简单而缺乏力度了。我坚信,一种详尽而 又深刻的观,点可以使生命的所有方面,不但为人们的理智而且 为人们的感情所接受。我曾经想撰写一本系统阐述进化论的基 因观点的著作。它将集中讨论那些社会行为方面的例子,以修 正已悄悄地渗入达尔文主义的“群体选择主义”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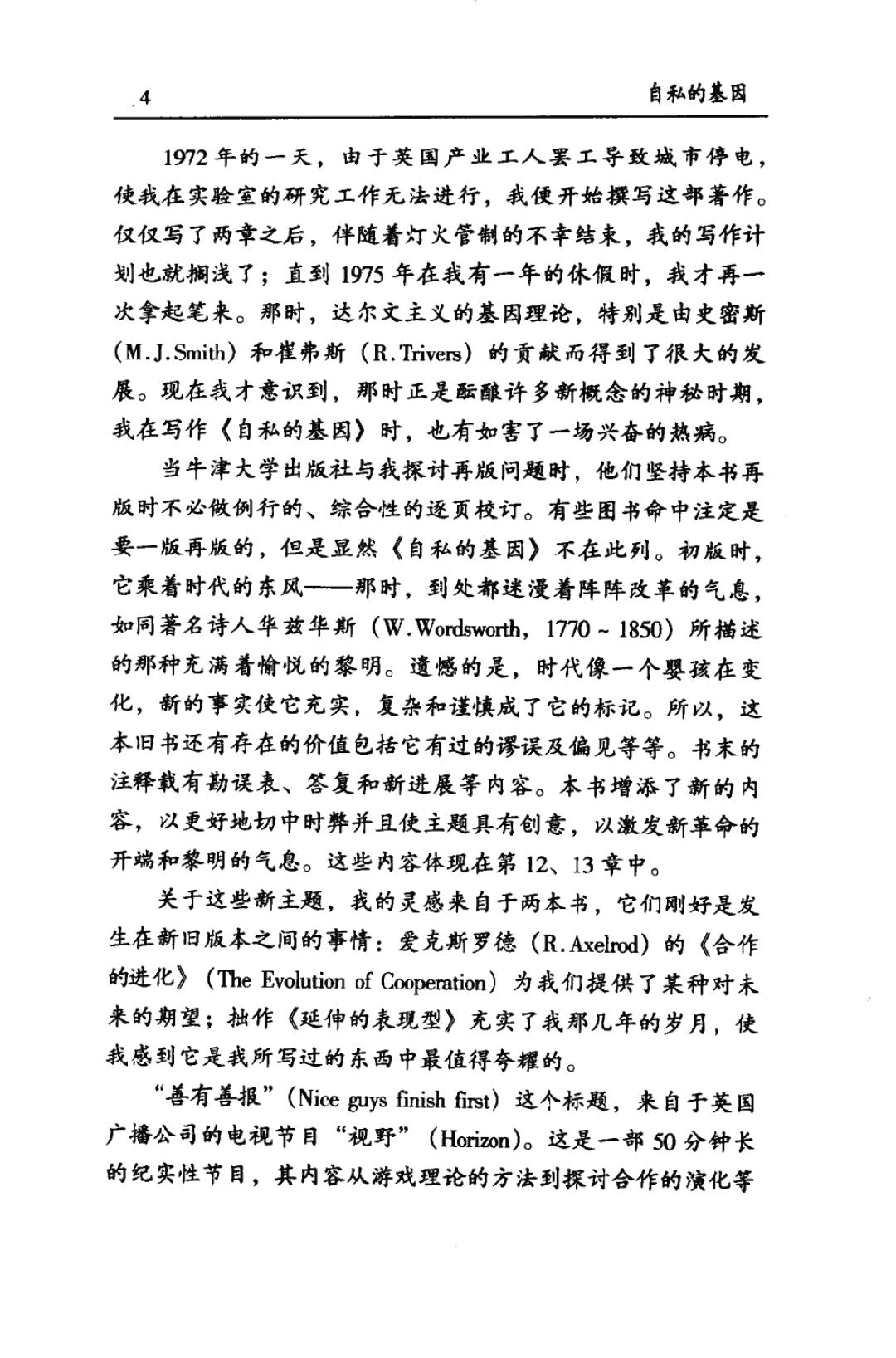
自私的基因 1972年的一天,由于荚国产业工人罢工导致城市停电, 使我在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我便开始撰写这部著作。 仅仅写了两章之后,伴随着灯火管制的不幸结束,我的写作计 划也就搁浅了;直到1975年在我有一年的休假时,我才再一 次拿起笔来。那时,达尔文主义的基因理论,特别是由史密斯 (M.J.Smith)和崔弗斯(R.Trivers)的贡献而得到了很大的发 展。现在我才意识到,那时正是酝酿许多新概念的神秘时期, 我在写作《自私的基因〉时,也有如害了一场兴奋的热病。 当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我探讨再版问题时,他们坚持本书再 版时不必做例行的、综合性的逐页校订。有些图书命中注定是 要一版再版的,但是显然《自私的基因》不在此列。初版时, 它乘着时代的东风一那时,到处都迷漫着阵阵改革的气息, 如同著名诗人华兹华斯(W.Wordsworth,1770~1850)所描述 的那种充满着愉悦的黎明。遗憾的是,时代像一个婴孩在变 化,新的事实使它充实,复杂和谨慎成了它的标记。所以,这 本旧书还有存在的价值包括它有过的谬误及偏见等等。书末的 注释载有勘误表、答复和新进展等内容。本书增添了新的内 容,以更好地切中时弊并且使主题具有创意,以激发新革命的 开端和黎明的气息。这些内容体现在第12、13章中。 关于这些新主题,我的灵感来自于两本书,它们刚好是发 生在新旧版本之间的事情:爱克斯罗德(R.Axelrod)的《合作 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对未 来的期望;拙作《延伸的表现型》充实了我那几年的岁月,使 我感到它是我所写过的东西中最值得夸耀的。 “善有善报”(Nice guys finish first)这个标题,来自于英国 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视野”(Horizon)。这是一部50分钟长 的纪实性节目,其内容从游戏理论的方法到探讨合作的演化等

1989年新版序 5 等。它和另一部电视节目“盲人钟表匠”(The Blind Watch- maker)一样,都是出自同一位制片人泰勒(J.Taylor)之手, 对泰勒的专业才能我表示崇高的敬意。从这一节目的处理和内 容中,我们可以看出“视野”的制作工作者们,已经转变成具 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家了。在美国,也可以经常看到这些节 目,不过它常常被在节目名称前冠之以“新”字。第12章的 功劳不仅是借用了“视野”节目的名字,而且它还让我与泰勒 及其同伴们一起分享了共同工作的乐趣和经验。 近来,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人们无法苟同的现象:一些 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乐于在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的作品上署名。 很显然,当一些资深的科学家为别人提供了实验室、研究经费 或校阅了手稿时,他们便声称自己有署名的权利。借此,他们 所有的科学声望可能就都是依靠学生和同事的工作堆垒而成 的。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阻止这种不伦不类的做法。遵此做 法,大概所有的期刊编辑们也都该有理由在每一位作者的成果 上署名了,那可是太方便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想作一个鲜明的对比。科 罗宁女士(H.Cronin)曾帮助我逐字逐句地修订过文稿,她应 该但是她坚决拒绝在本书的新版本上署名。我深深地感激她, 还怀有款疚之情。我的所有的谢意也仅仅如此。我还要感谢瑞 德利(Ridley),M.道金斯和格拉芬(A.Grafen)的忠告和对某 些段落的建设性批评,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韦伯斯特 (T.Webster)、马克格林(H.MeGlynn)及其他人对我唐突和拖 延的宽容。 里查德·道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