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4年秋瑾在她一部弹词(一种南方的表演形式)的手稿中,安排 了一幕士绅家庭中的场景,家中的父亲正与教他儿子读书的表哥谈话。他 的表哥首先表扬了他的学生的才智,然后建议让他学生的妹妹也接受同 样的教育:“因彼聪明且俊秀,玉汝不琢恨何如?”父亲反问道:“女子读 书何所用,难同男子耀门闾。纵使才高夸八斗,朝廷曾设女科无?”①这些 问题含蓄地证实了近来女性主义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阐明了清朝鼎盛时 期(1683一1839)的中国精英女性,是如何借助于一种可以追潮到唐朝的、 高度发达的女性写作传统,获得高水平的文化修养的。在这个意义上,“女 子无才便是德”的儒家教条,讽刺性地驳斥了任何所谓女性天生就缺乏知 性思考和写作能力的说法。②那位父亲的反对并不是建立在这种认为“女 性”天生有所欠缺的观念基础之上的。更准确地说,他指的是缺少这样的 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女性的学识才可能赢得社会的价值。③于是,有关女 性读书写作的问题,就是一个有关制度性承认、规范性报酬的社会机制安 排和社会价值分配的问题。 秋瑾就是那个时候涌现出来的一位女作家,一个革命的活动家,东京 ①秋瑾:《精卫石》,《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英译文选自(笔者有修正)“Scenes from Stones of the Jingwei Bird",Amy D.Dooling and Kristine M.Torgeson (eds.)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50. ②参见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形omen in China3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Dorothy Ko,Teachers of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China. I573-I77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又见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武汉: 湖北教有出版社,1993年。 ③尽管中国的封建王朝中不乏有学识的女性,但是女性的学习从来不是中国王朝历史制度的一部 分。隋代(581一618)以米的科举制度,作为某种组织原则和实行制度,在其存在的一千三百多 年中,一直都是一个男性专有的运作体系。 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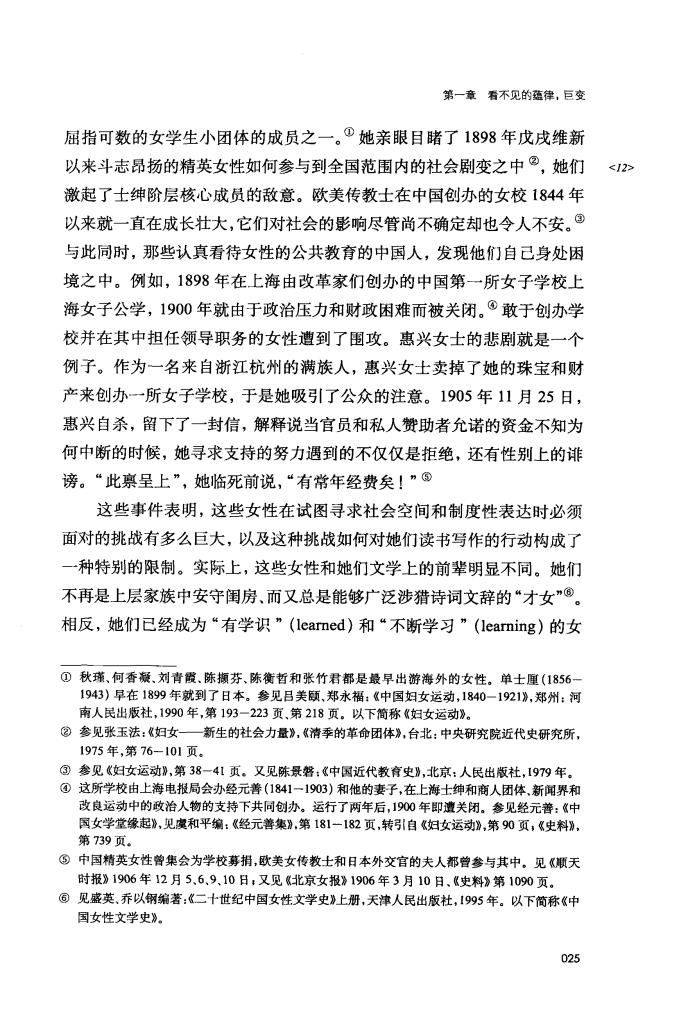
第一章看不见的蕴律,巨变 屈指可数的女学生小团体的成员之一。①她亲眼目睹了1898年戊戌维新 以来斗志昂扬的精英女性如何参与到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剧变之中③,她们 <12 激起了士绅阶层核心成员的敌意。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女校1844年 以来就一直在成长壮大,它们对社会的影响尽管尚不确定却也令人不安。③ 与此同时,那些认真看待女性的公共教育的中国人,发现他们自己身处因 境之中。例如,1898年在上海由改革家们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上 海女子公学,1900年就由于政治压力和财政困难而被关闭。①敢于创办学 校并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遭到了围攻。惠兴女士的悲剧就是一个 例子。作为一名来自浙江杭州的满族人,惠兴女士卖掉了她的珠宝和财 产来创办一所女子学校,于是她吸引了公众的注意。1905年11月25日, 惠兴自杀,留下了一封信,解释说当官员和私人赞助者允诺的资金不知为 何中断的时候,她寻求支持的努力遇到的不仅仅是拒绝,还有性别上的排 谤。“此禀呈上”,她临死前说,“有常年经费矣!”⑤ 这些事件表明,这些女性在试图寻求社会空间和制度性表达时必须 面对的挑战有多么巨大,以及这种挑战如何对她们读书写作的行动构成了 -一种特别的限制。实际上,这些女性和她们文学上的前辈明显不同。她们 不再是上层家族中安守闺房、而又总是能够广泛涉猎诗词文辞的“才女”⑥。 相反,她们已经成为“有学识”(learned)和“不断学习”(learning)的女 ①秋球、何香凝、刘青霞、陈撷芬、陈衡哲和张竹君都是最早出游海外的女性。单士厘(1856一 1943)早在1899年就到了日本。参见吕美颜,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一1921》,郑州:河 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3-223页.第218页。以下简称《妇女运动》。 ②参见张玉法:《妇女一新生的社会力量》,《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年,第76-101页。 ③叁见《妇女运动》,第38-一41页。又见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这所学校由上海电报局会办经元善(1841一1903)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士绅和商人团体,新闻界和 改良运动中的政治人物的支持下共同创办。运行了两年后,1900年即遭关闭。参见经元善:《中 国女学堂缘起》,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181一182页,转引自《妇女运动》,第90页,《史料》, 第739页。 ⑤中国精英女性曾集会为学校募捐,欧美女传教士和日本外交官的夫人都曾参与其中。见《顺天 时报》1906年12月5,6,9.10日,又见《北京女报》1906年3月10日、《史料》第1090页。 ⑥见盛英、乔以钢缩著:《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I995年。以下简称《中 国女性文学史》。 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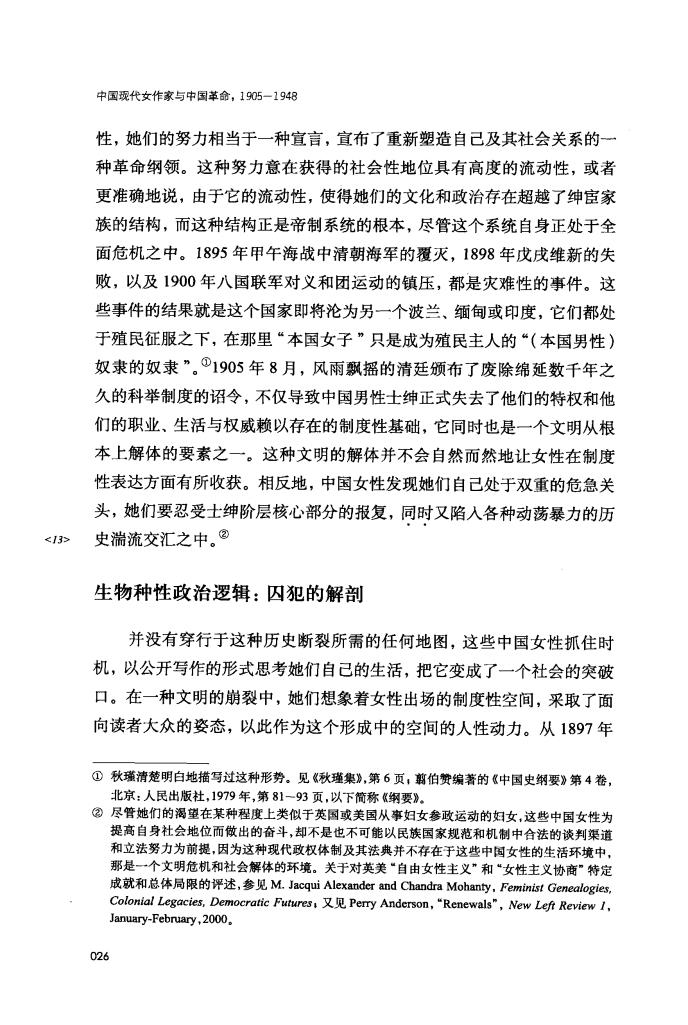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一1948 性,她们的努力相当于一种宣言,宣布了重新塑造自己及其社会关系的一 种革命纲领。这种努力意在获得的社会性地位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或者 更准确地说,由于它的流动性,使得她们的文化和政治存在超越了绅宦家 族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正是帝制系统的根本,尽管这个系统自身正处于全 面危机之中。1895年甲午海战中清朝海军的覆灭,1898年戊戌维新的失 败,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都是灾难性的事件。这 些事件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即将沦为另一个波兰、缅甸或印度,它们都处 于殖民征服之下,在那里“本国女子”只是成为殖民主人的“(本国男性) 奴隶的奴隶”。①1905年8月,风雨飘摇的清廷颁布了废除绵延数千年之 久的科举制度的诏令,不仅导致中国男性士绅正式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和他 们的职业、生活与权威赖以存在的制度性基础,它同时也是一个文明从根 本上解体的要素之一。这种文明的解体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让女性在制度 性表达方面有所收获。相反地,中国女性发现她们自己处于双重的危急关 头,她们要忍受士绅阶层核心部分的报复,同时又陷入各种动荡暴力的历 <13> 史湍流交汇之中。② 生物种性政治逻辑:囚犯的解剖 并没有穿行于这种历史断裂所需的任何地图,这些中国女性抓住时 机,以公开写作的形式思考她们自己的生活,把它变成了一个社会的突破 口。在一种文明的崩裂中,她们想象着女性出场的制度性空间,采取了面 向读者大众的姿态,以此作为这个形成中的空间的人性动力。从1897年 ①秋瑾清楚明白地描写过这种形势。见《秋瑾集》,第6页,翦伯赞编著的《中国史纲要》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1一93页,以下简称《纲要》。 ②尽管她们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英国或美国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妇女,这些中国女性为 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而做出的奋斗,却不是也不可能以民族国家规范和机制中合法的谈判渠道 和立法努力为前提,因为这种现代政权体制及其法典并不存在于这些中国女性的生活环境中, 那是一个文明危机和社会解体的环境。关于对英美“自由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协商”特定 成就和总体局限的评述,参见M.Jacqui Alexander and Chandra Mohanty,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Democratic FuturesPerry Anderson,"Renewals",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2000. 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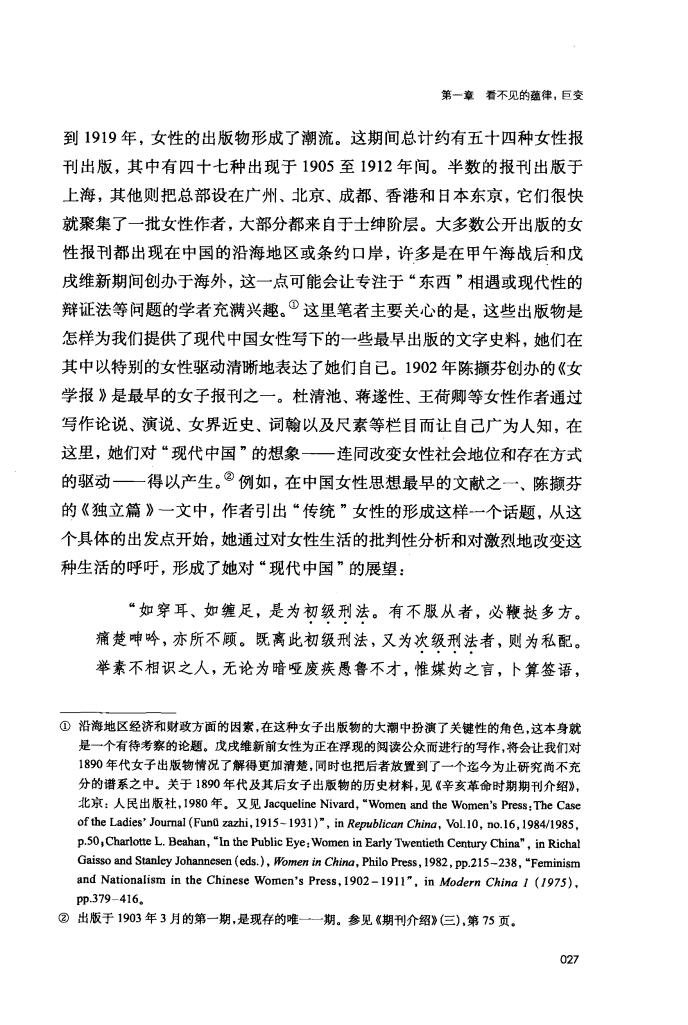
第一章看不见的蕴律,巨变 到1919年,女性的出版物形成了潮流。这期间总计约有五十四种女性报 刊出版,其中有四十七种出现于1905至1912年间。半数的报刊出版于 上海,其他则把总部设在广州、北京、成都、香港和日本东京,它们很快 就聚集了一批女性作者,大部分都来自于士绅阶层。大多数公开出版的女 性报刊都出现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或条约口岸,许多是在甲午海战后和戊 戌维新期间创办于海外,这一点可能会让专注于“东西”相遇或现代性的 辩证法等问题的学者充满兴趣。①这里笔者主要关心的是,这些出版物是 怎样为我们提供了现代中国女性写下的一些最早出版的文字史料,她们在 其中以特别的女性驱动清晰地表达了她们自己。1902年陈撷芬创办的《女 学报》是最早的女子报刊之一。杜清池、蒋遂性、王荷卿等女性作者通过 写作论说、演说、女界近史、词翰以及尺素等栏目而让自己广为人知,在 这里,她们对“现代中国”的想象一连同改变女性社会地位和存在方式 的驱动一得以产生。®例如,在中国女性思想最早的文献之一、陈撷芬 的《独立篇》一文中,作者引出“传统”女性的形成这样一个话题,从这 个具体的出发点开始,她通过对女性生活的批判性分析和对激烈地改变这 种生活的呼吁,形成了她对“现代中国”的展望: “如穿耳、如缠足,是为初级刑法。有不服从者,必鞭挞多方。 痛楚申吟,亦所不顾。既离此初级刑法,又为次级刑法者,则为私配。 举素不相识之人,无论为暗哑废疾愚鲁不才,惟媒妁之言,卜算签语, ①沿海地区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因紫,在这种女子出版物的大潮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本身就 是一个有待考察的论题。戊戌维新前女性为正在浮现的阅读公众而进行的写作,将会让我们对 1890年代女子出版物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同时也把后者放置到了一个迄今为止研究尚不充 分的谱系之中。关于1890年代及其后女子出版物的历史材料,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北京:人民出版杜,I980年。又见Jacqueline Nivard,“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The Case of the Ladies'Journal (Fundl zazhi,1915-1931)",in Republican China,Vol.10,no.16,1984/1985. p.50,Charlotte L.Beahan,"In the Public Eye:Wome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in Richal Gaisso and Stanley Johannesen (eds.),Women in China,Philo Press,1982,pp.215-238,"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1902-1911",in Modern China 1 (1975), pp.379-416。 ②出版于1903年3月的第一期,是现存的唯一一期。参见《期刊介绍》(三),第75页。 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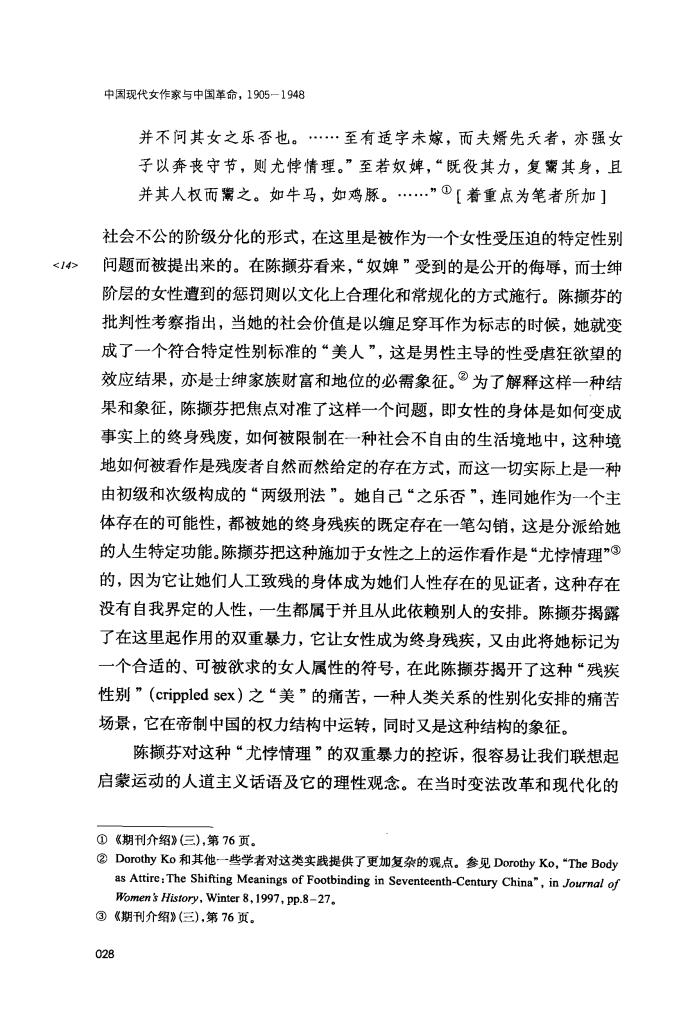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一1948 并不问其女之乐否也。…至有适字未嫁,而夫婿先天者,亦强女 子以奔丧守节,则尤悖情理。”至若奴婢,“既役其力,复鬻其身,且 并其人权而鬻之。如牛马,如鸡豚。”①〔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社会不公的阶级分化的形式,在这里是被作为一个女性受压迫的特定性别 <143 问题而被提出来的。在陈撷芬看来,“奴婢”受到的是公开的侮辱,而士绅 阶层的女性遭到的惩罚则以文化上合理化和常规化的方式施行。陈撷芬的 批判性考察指出,当她的社会价值是以缠足穿耳作为标志的时候,她就变 成了一个符合特定性别标准的“美人”,这是男性主导的性受虐狂欲望的 效应结果,亦是士绅家族财富和地位的必需象征。③为了解释这样一种结 果和象征,陈撷芬把焦点对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女性的身体是如何变成 事实上的终身残废,如何被限制在一种社会不自由的生活境地中,这种境 地如何被看作是残废者自然而然给定的存在方式,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 由初级和次级构成的“两级刑法”。她自己“之乐否”,连同她作为一个主 体存在的可能性,都被她的终身残疾的既定存在一笔勾销,这是分派给她 的人生特定功能。陈撷芬把这种施加于女性之上的运作看作是“尤悖情理”③ 的,因为它让她们人工致残的身体成为她们人性存在的见证者,这种存在 没有自我界定的人性,一生都属于并且从此依赖别人的安排。陈撷芬揭露 了在这里起作用的双重暴力,它让女性成为终身残疾,又由此将她标记为 一个合适的、可被欲求的女人属性的符号,在此陈撷芬揭开了这种“残疾 性别”(crippled sex)之“美”的痛苦,一种人类关系的性别化安排的痛苦 场景,它在帝制中国的权力结构中运转,同时又是这种结构的象征。 陈撷芬对这种“尤悖情理”的双重暴力的控诉,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 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话语及它的理性观念。在当时变法改革和现代化的 ①《期刊介绍》(三),第76页。 ②Dorothy Ko和其他一些学者对这类实践提供了更加复杂的观点。参见Dorothy Ko,“The Body as Attire: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in Journal of Women'3 History,Winter 8,1997,pp.8-27. ③《期刊介绍》(三),第76页。 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