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苹命,1905-1948 dynamics)。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种种人生历程,在这里以这些终有一 死的人们的想象性的构造表达而存在,这些想象构造是她们的虚构作品 的核心活力,而在这些人死后,这些作品仍会在实际的世界中以物质的形 式继续留存下去,呼唤着不同读者的变奏能量,在人们的重访中再现。这 些中国女作家虚构的、但将继续实际留存并进入21世纪的作品,她们当 时赋予作品以生命来源而现在已经都消逝到过去之中的血肉之躯①,在相 互联结或交汇中,孕育出一种非真的然而却不容否认的存在,它既生成了 这样-一个领域,又栖息于其中。就好像非真的蕴律(unreal rhythms)一样, 这种存在为笔者探求这些女性的写作与生活的特定方式,指示了聚焦的场 所:写作与人生在互为构成要素和转化过程中成形,从而充满想象力地产 <93 生出一种真实的人性。这样一种非真的蕴律,并不能完全通过话语中心 和文本主导的方式去探寻②。受到后现代理论的话语中心范式的限制一 或是追随这种范式一一系列关于中国女作家的当代研究也专注于历史 材料的话语维度,这种维度把这些女性及其写作着、生活着的身体(living bodies)边缘化了,从而无法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活跃的身体是如何实 现不同的社会性驱动,是如何使得某些文化传统的创造性方案和实践成 为可能的,这些方案和实践无法化约和通约为文本一话语材料证据,而 总是在文本一话语间悠远回荡,挥之不去。话语中心的范式对符号学自 身的强调就显示出了它的基本局限和内在极限,无论是其在宣称把体现 (embodiment)问题考虑在内的一些符号学版本中(semiotics),还是作为 在身体之上的领域运作的符号学的另一些变奏里(semiology),前者的批 判有效性的代价是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易于将活着的身体及其生命力边缘 化,后者则易于绕过生活着的身体。在本书研究的语境中,以语言学方法 为中心的思路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有局限性的。如果不把中国现代 ①冰心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她逝世于1999年2月28日。 ②这种方式是和西方形而上学及其许多有意识的“循环”式(revolving)的自我批判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对此局限进行分析的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工作,参见Satya Mohanty及他所主持的“Ethnic Minority Studies”"项目的近期成果。 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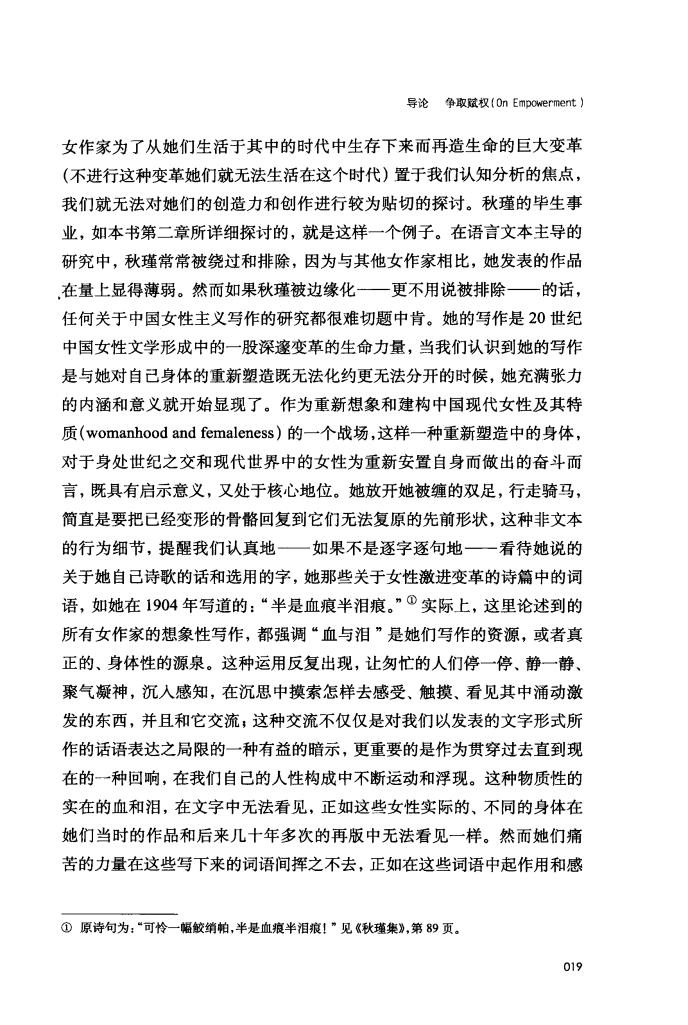
导论争取赋权(On Empowerment) 女作家为了从她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中生存下来而再造生命的巨大变革 (不进行这种变革她们就无法生活在这个时代)置于我们认知分析的焦点, 我们就无法对她们的创造力和创作进行较为贴切的探讨。秋瑾的毕生事 业,如本书第二章所详细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语言文本主导的 研究中,秋瑾常常被绕过和排除,因为与其他女作家相比,她发表的作品 在量上显得薄弱。然而如果秋瑾被边缘化一更不用说被排除一的话, 任何关于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研究都很难切题中肯。她的写作是20世纪 中国女性文学形成中的一股深邃变革的生命力量,当我们认识到她的写作 是与她对自已身体的重新塑造既无法化约更无法分开的时候,她充满张力 的内涵和意义就开始显现了。作为重新想象和建构中国现代女性及其特 质(womanhood and femaleness)的一个战场,这样一种重新塑造中的身体, 对于身处世纪之交和现代世界中的女性为重新安置自身而做出的奋斗而 言,既具有启示意义,又处于核心地位。她放开她被缠的双足,行走骑马, 简直是要把已经变形的骨骼回复到它们无法复原的先前形状,这种非文本 的行为细节,提醒我们认真地一如果不是逐字逐句地—一看待她说的 关于她自已诗歌的话和选用的字,她那些关于女性激进变革的诗篇中的词 语,如她在1904年写道的:“半是血痕半泪痕。”①实际上,这里论述到的 所有女作家的想象性写作,都强调“血与泪”是她们写作的资源,或者真 正的、身体性的源泉。这种运用反复出现,让匆忙的人们停一停、静一静、 聚气凝神,沉入感知,在沉思中摸索怎样去感受、触摸、看见其中涌动激 发的东西,并且和它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是对我们以发表的文字形式所 作的话语表达之局限的一种有益的暗示,更重要的是作为贯穿过去直到现 在的一种回响,在我们自己的人性构成中不断运动和浮现。这种物质性的 实在的血和泪,在文字中无法看见,正如这些女性实际的、不同的身体在 她们当时的作品和后来几十年多次的再版中无法看见一样。然而她们痛 苦的力量在这些写下来的词语间挥之不去,正如在这些词语中起作用和感 ①原诗句为:“可怜一幅皎绡帕,半是血痕半泪痕!”见《秋瑾集》,第89页。 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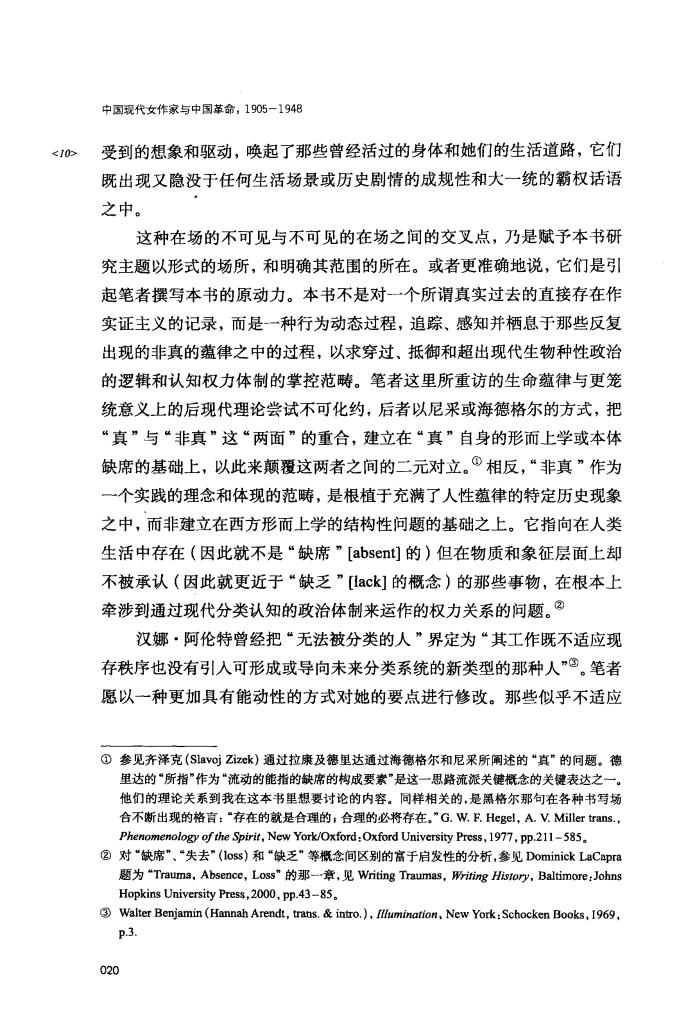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10> 受到的想象和驱动,唤起了那些曾经活过的身体和她们的生活道路,它们 既出现又隐没于任何生活场景或历史剧情的成规性和大一统的霸权话语 之中。 这种在场的不可见与不可见的在场之间的交叉点,乃是赋予本书研 究主题以形式的场所,和明确其范围的所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是引 起笔者撰写本书的原动力。本书不是对一个所谓真实过去的直接存在作 实证主义的记录,而是一种行为动态过程,追踪、感知并栖息于那些反复 出现的非真的蕴律之中的过程,以求穿过、抵御和超出现代生物种性政治 的逻辑和认知权力体制的掌控范畴。笔者这里所重访的生命蕴律与更笼 统意义上的后现代理论尝试不可化约,后者以尼采或海德格尔的方式,把 “真”与“非真”这“两面”的重合,建立在“真”自身的形而上学或本体 缺席的基础上,以此来颠覆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相反,“非真”作为 一个实践的理念和体现的范畴,是根植于充满了人性蕴律的特定历史现象 之中,而非建立在西方形而上学的结构性问题的基础之上。它指向在人类 生活中存在(因此就不是“缺席”[absent)的)但在物质和象征层面上却 不被承认(因此就更近于“缺乏”lack]的概念)的那些事物,在根本上 牵涉到通过现代分类认知的政治体制来运作的权力关系的问题。②@ 汉娜·阿伦特曾经把“无法被分类的人”界定为“其工作既不适应现 存秩序也没有引入可形成或导向未来分类系统的新类型的那种人”③。笔者 愿以一种更加具有能动性的方式对她的要点进行修改。那些似乎不适应 ①参见齐泽克(Slavoj Zizck)通过拉康及德里达通过海德格尔和尼采所阐述的“真”的问题。德 里达的“所指”作为“流动的能指的缺席的构成要素“是这一思路流派关键概念的关键表达之一。 他们的理论关系到我在这本书里想要讨论的内容。同样相关的,是黑格尔那句在各种书写场 合不断出现的格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必将存在。”G.W,F.Hegel,,A.V.Miller trans., 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211-585. @对“缺席"、“失去”(Ioss)和“峡乏”等概念间区别的富于启发性的分析,鑫见Dominick LaCapra 题为“Trauma,Absence,.Loss"的那-章,见Writing Traumas,Writing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43-85. Walter Benjamin (Hannah Arendt,trans.intro.),fllumination,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 p3. 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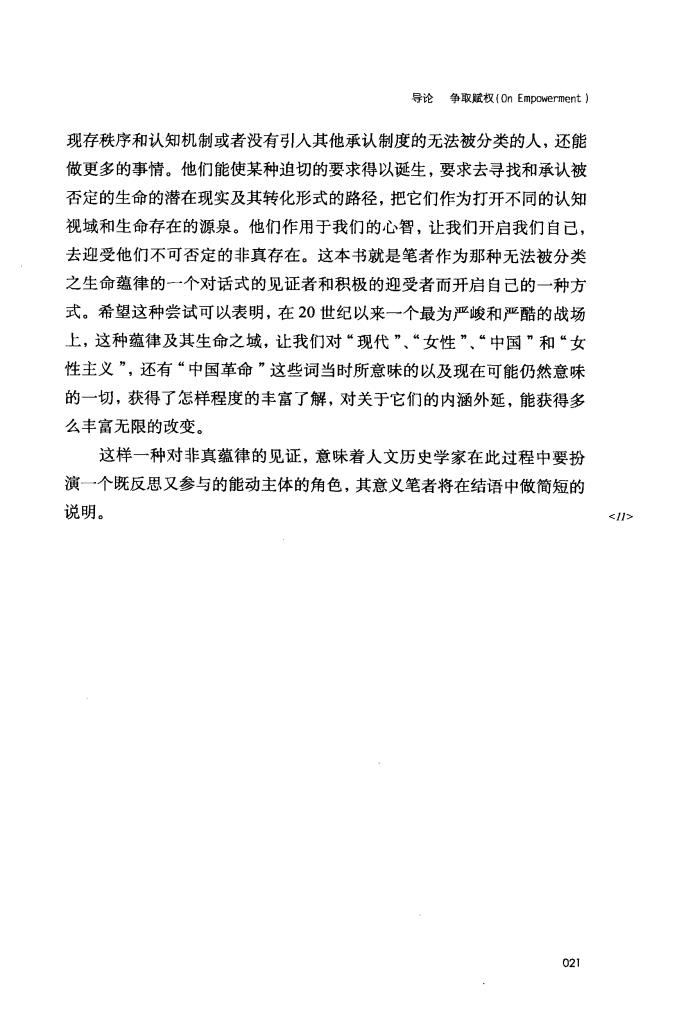
导论争取赋权{On Empowerment) 现存秩序和认知机制或者没有引入其他承认制度的无法被分类的人,还能 做更多的事情。他们能使某种迫切的要求得以诞生,要求去寻找和承认被 否定的生命的潜在现实及其转化形式的路径,把它们作为打开不同的认知 视域和生命存在的源泉。他们作用于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开启我们自己, 去迎受他们不可否定的非真存在。这本书就是笔者作为那种无法被分类 之生命蕴律的一个对话式的见证者和积极的迎受者而开启自己的一种方 式。希望这种尝试可以表明,在20世纪以来一个最为严峻和严酷的战场 上,这种蕴律及其生命之域,让我们对“现代”、“女性”、“中国”和“女 性主义”,还有“中国革命”这些词当时所意味的以及现在可能仍然意味 的一切,获得了怎样程度的丰富了解,对关于它们的内涵外延,能获得多 么丰富无限的改变。 这样一种对非真蕴律的见证,意味着人文历史学家在此过程中要扮 演一个既反思又参与的能动主体的角色,其意义笔者将在结语中做简短的 说明。 <11> 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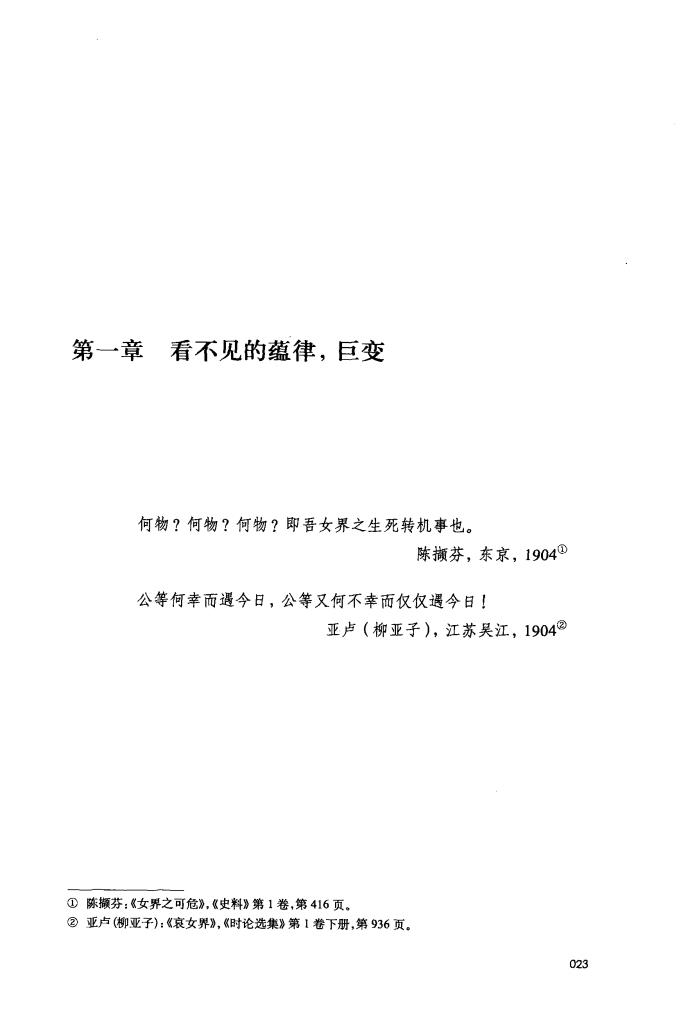
第一章看不见的蕴律,巨变 何物?何物?何物?即吾女界之生死转机事也。 陈撷芬,东京,19040 公等何幸而遇今日,公等又何不幸而仅仅遇今日! 亚卢(柳亚子),江苏吴江,1904② ①陈撷芬:《女界之可危》,《史料》第1卷,第416页。 ②亚卢(柳亚子):《哀女界》,《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36页。 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