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看不见的蕴律,巨变 领袖人物的著作中,这种援引是很常见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援引内 部存在着无法化约的差异。有一点尤其引人注月,那就是包括陈撷芬在内 的女性写下的大批文字中,都把“残疾性别”的身体遭遇置于突出的地位, 而大多数男性领袖的大量著作,却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残疾”的身体看 作“传统中国妇女”心智或认知状态的表征。“小脚女人”与“未开化者”、 “落后愚蠢”、“无知无用”互为社会隐喻,“无用”的中国女性“只知用力, 不知生力”。①这其中引入了一种对可辨认暨合理化的现代政体机制的预 示,按照这种体制,人性的价值根据给她指派和重新指派的功能而定,这 种功能被用于作为“放大了的家族”的“国家”对“财富”的获取.③女 性的身体曾经被塑型包装起来,用于男性中心的亲属谱系和传统等级秩序 的再生产,而这里引入的现代体制则转而将如此塑型的存在,作为她们无 法在功能上成为“现代”的证明,她们成为国家“麻烦的来源”和民族“落 后”的渊薮,这样的“落后”民族正处于被“由有竞争力的国家构成的现 代世界”“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而按照“现代世界”对人性常态的法 则规训,如此国运正是必然。@ 陈撷芬对女性身体遭受“刑法”之后果的解剂揭示,决绝地摆脱了古 代政权的性别规范,同时又抵御着现代化的性别话语,这种话语宣布中国 式“残疾性别”的身体本身是“无用人性”最新发现的例证。这种剖析在 诸多女性作者的书写中出现,它催化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声的焦虑。陈 <152 超在她著名的题为《呈梦坡先生并示撷芬吾友》中的诗篇写道: ①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几乎是直接地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参见康有为:《大同书》,沈阳:辽 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②严复(1854一1921),中国最早翻译西方一系列经济理论家著作的人,也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 富》(《国富论》),译本出版于1901年,在晚清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有关中倒现 代史上这一重要的文化和思想事件的最近讨论之一,见樅建诚:《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 与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③参见《女学堂章程》,《北京女报》1906年10月6.14,18日。又见Alison R.Drucker,“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Women on the Anti-footbinding Movement,1840-1911",in Richard W.Guisso and Stanley Johannesen (eds.),Women in China: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Youngstown:Philo Press,1981),pp.179-199:Hong Fan,Footbinding.Feminism,and Freedom: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Portland:Frank Cass,1997. 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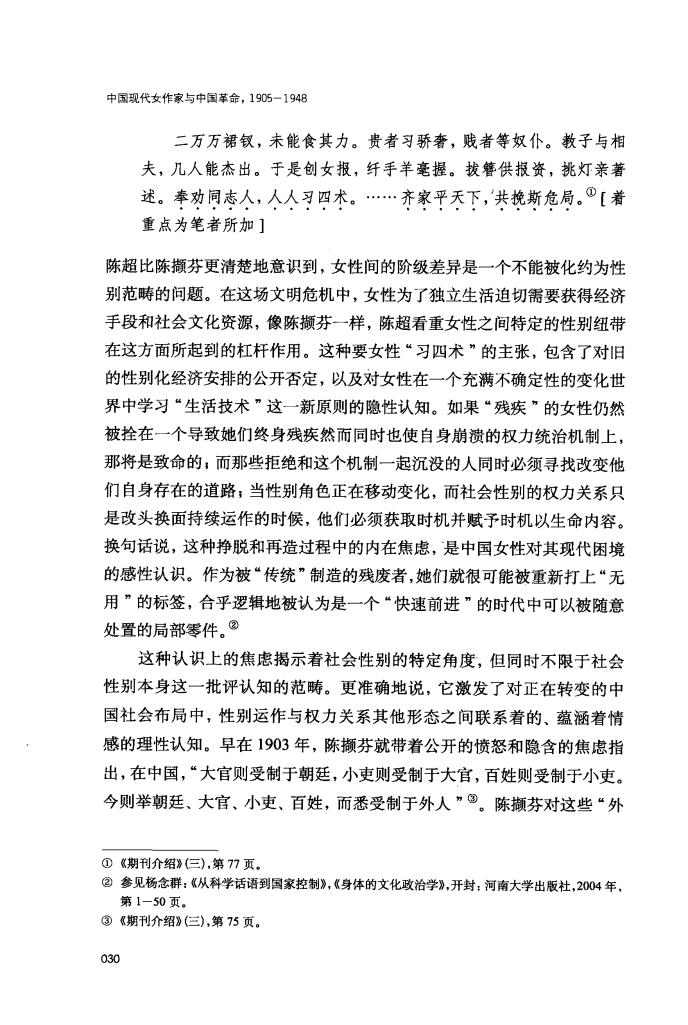
中团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一1948 二万万裙钗,未能食其力。贵者习骄奢,贱者等奴仆。教子与相 夫,几人能杰出。于是创女报,纤手羊毫握。拔簪供报资,挑灯亲著 述。奉劝同志人,人人习四术。…齐家平天下,共挽斯危局。①[着 重点为笔者所加] 陈超比陈撷芬更清楚地意识到,女性间的阶级差异是一个不能被化约为性 别范畴的问题。在这场文明危机中,女性为了独立生活迫切需要获得经济 手段和社会文化资源,像陈撷芬一样,陈超看重女性之间特定的性别纽带 在这方面所起到的杠杆作用。这种要女性“习四术”的主张,包含了对旧 的性别化经济安排的公开否定,以及对女性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世 界中学习“生活技术”这一新原则的隐性认知。如果“残疾”的女性仍然 被拴在一个导致她们终身残疾然而同时也使自身崩遗的权力统治机制上, 那将是致命的,而那些拒绝和这个机制一起沉没的人同时必须寻找改变他 们自身存在的道路,当性别角色正在移动变化,而社会性别的权力关系只 是改头换面持续运作的时候,他们必须获取时机并赋予时机以生命内容。 换句话说,这种挣脱和再造过程中的内在焦虑,是中国女性对其现代困境 的感性认识。作为被“传统”制造的残废者,她们就很可能被重新打上“无 用”的标签,合乎逻辑地被认为是一个“快速前进”的时代中可以被随意 处置的局部墨件。® 这种认识上的焦虑揭示着社会性别的特定角度,但同时不限于社会 性别本身这一批评认知的范畴。更准确地说,它激发了对正在转变的中 国社会布局中,性别运作与权力关系其他形态之间联系着的、蕴涵着情 感的理性认知。早在1903年,陈撷芬就带着公开的愤怒和隐含的焦虑指 出,在中国,“大官则受制于朝廷,小吏则受制于大官,百姓则受制于小吏。 今则举朝廷、大官、小吏、百姓,而悉受制于外人”③。陈撷芬对这些“外 ①《期刊介绍》(三),第77页。 ②参见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1-50页。 ③《期刊介绍》(三),第75页。 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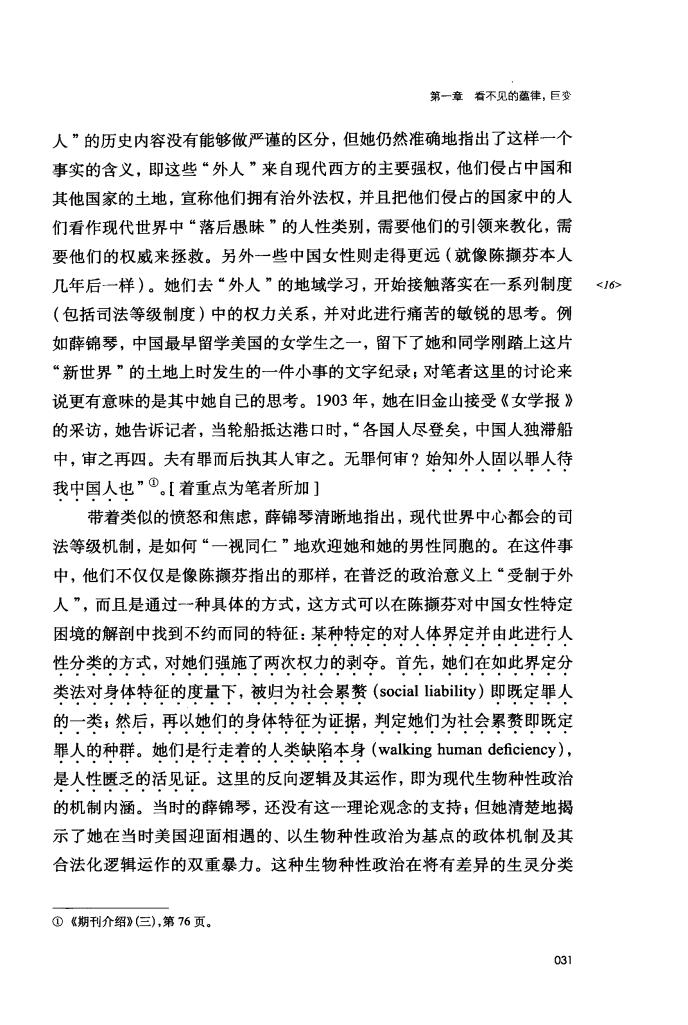
第一章看不见的蕴律,巨变 人”的历史内容没有能够做严谨的区分,但她仍然准确地指出了这样一个 事实的含义,即这些“外人”来自现代西方的主要强权,他们侵占中国和 其他国家的土地,宣称他们拥有治外法权,并且把他们侵占的国家中的人 们看作现代世界中“落后愚昧”的人性类别,需要他们的引领来教化,需 要他们的权威来拯救。另外一些中国女性则走得更远(就像陈撷芬本人 几年后一样)。她们去“外人”的地域学习,开始接触落实在一系列制度 <16 (包括司法等级制度)中的权力关系,并对此进行痛苦的敏锐的思考。例 如薛锦琴,中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学生之一,留下了她和同学刚踏上这片 “新世界”的土地上时发生的一件小事的文字纪录,对笔者这里的讨论来 说更有意味的是其中她自己的思考。1903年,她在旧金山接受《女学报》 的采访,她告诉记者,当轮船抵达港口时,“各国人尽登矣,中国人独滞船 中,审之再四。夫有罪而后执其人审之。无罪何审?始知外人固以罪人待 我中国人也”①。[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带着类似的愤怒和焦虑,薛锦琴清晰地指出,现代世界中心都会的司 法等级机制,是如何“一视同仁”地欢迎她和她的男性同胞的。在这件事 中,他们不仅仅是像陈撷芬指出的那样,在普泛的政治意义上“受制于外 人”,而且是通过一种具体的方式,这方式可以在陈撷芬对中国女性特定 困境的解剖中找到不约而同的特征:某种特定的对人体界定并由此进行人 性分类的方式,对她们强施了两次权力的剥夺。首先,她们在如此界定分 类法对身体特征的度量下,被归为社会累赘(social liability)即既定罪人 的一类,然后,再以她们的身体特征为证据,判定她们为社会累赘即既定 罪人的种群。她们是行走着的人类缺陷本身(walking human deficiency), 是人性匮乏的活见证。这里的反向逻辑及其运作,即为现代生物种性政治 的机制内涵。当时的薛锦琴,还没有这一一理论观念的支持,但她清楚地揭 示了她在当时美国迎面相遇的、以生物种性政治为基点的政体机制及其 合法化逻辑运作的双重暴力。这种生物种性政治在将有差异的生灵分类 ①《期刊介绍》(三),第76页。 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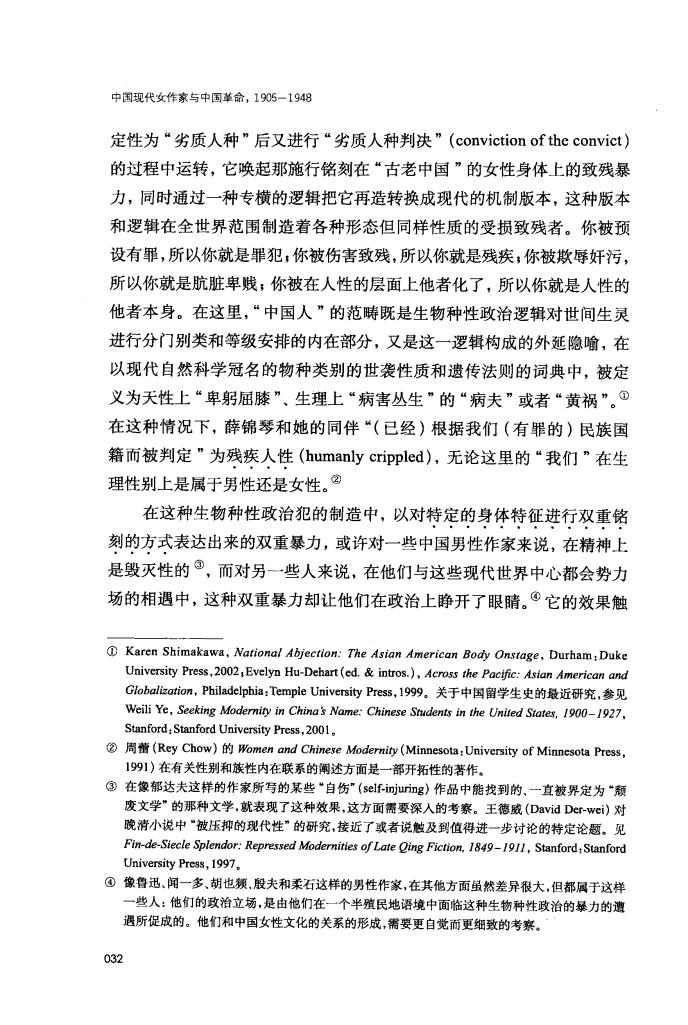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定性为“劣质人种”后又进行“劣质人种判决”(conviction of the convict) 的过程中运转,它唤起那施行铭刻在“古老中国”的女性身体上的致残暴 力,同时通过一种专横的逻辑把它再造转换成现代的机制版本,这种版本 和逻辑在全世界范围制造着各种形态但同样性质的受损致残者。你被预 设有罪,所以你就是罪犯,你被伤害致残,所以你就是残疾,你被欺辱奸污, 所以你就是肮脏卑贱;你被在人性的层面上他者化了,所以你就是人性的 他者本身。在这里,“中国人”的范畴既是生物种性政治逻辑对世间生灵 进行分门别类和等级安排的内在部分,又是这一逻辑构成的外延隐喻,在 以现代自然科学冠名的物种类别的世袭性质和遗传法则的词典中,被定 义为天性上“卑躬屈膝”、生理上“病害丛生”的“病夫”或者“黄祸”。@ 在这种情况下,薛锦琴和她的同伴“(已经)根据我们(有罪的)民族国 籍而被判定”为残疾人性(humanly crippled),无论这里的“我们”在生 理性别上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② 在这种生物种性政治犯的制造中,以对特定的身体特征进行双重铭 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双重暴力,或许对一些中国男性作家来说,在精神上 是毁灭性的③,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在他们与这些现代世界中心都会势力 场的相遇中,这种双重暴力却让他们在政治上睁开了眼睛。®它的效果触 D Karen Shimakawa,National Abjection:The Asian American Body Onstag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Evelyn Hu-Dehart (ed.intros.),Across the Pacific:Asian American and Globaliza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l999。关于中国留学生史的最近研究,参见 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②周t谐(Rey Chow)的W形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在有关性别和族性内在联系的阐述方面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③在像郁达夫这样的作家所写的某些“自伤”(sf-injuring)作品中能找到的、一直被界定为“颓 废文学”的那种文学,就表现了这种效果,这方面需要深人的考察。王德威(David Der-wci)对 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研究,接近了或者说触及到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特定论题。乳 Fin-de-Sie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④像鲁迅、闻一多、胡也领,殷夫和柔石这样的男性作家,在其他方面虽然差异很大,但都属于这样 一些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由他们在一个半殖民地语境中面临这种生物种性政治的暴力的遭 遇所促成的。他们和中国女性文化的关系的形成,需要更自觉而更细致的考察。 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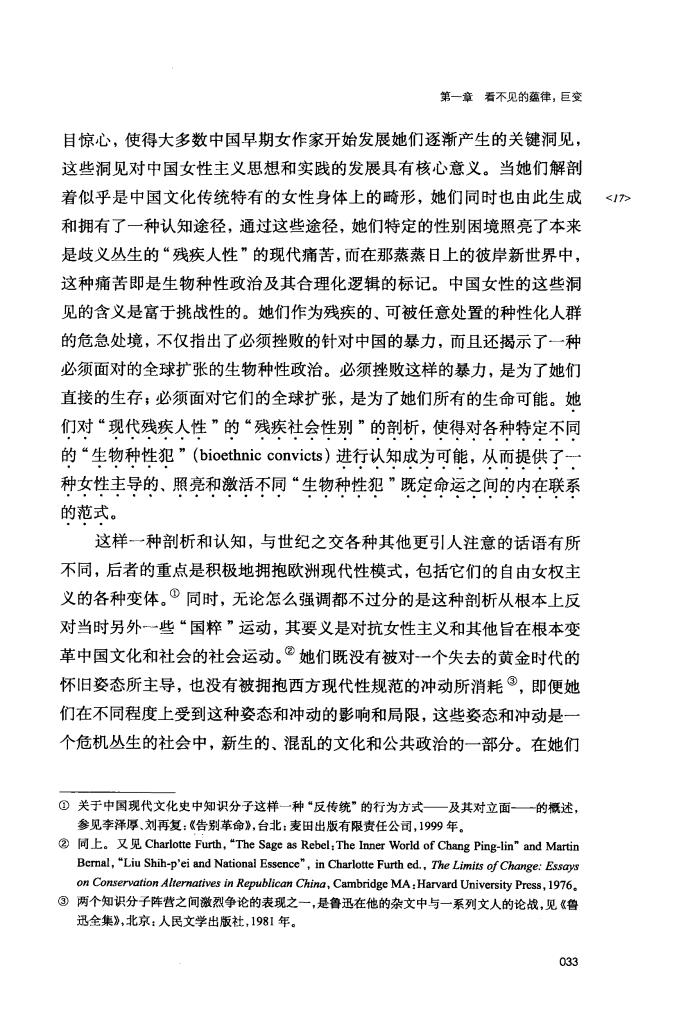
第一章看不见的蕴律,巨变 目惊心,使得大多数中国早期女作家开始发展她们逐渐产生的关键洞见, 这些洞见对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具有核心意义。当她们解剖 着似乎是中国文化传统特有的女性身体上的畸形,她们同时也由此生成 <17> 和拥有了一种认知途径,通过这些途径,她们特定的性别困境照亮了本来 是歧义丛生的“残疾人性”的现代痛苦,而在那蒸蒸日上的彼岸新世界中, 这种痛苦即是生物种性政治及其合理化逻辑的标记。中国女性的这些洞 见的含义是富于挑战性的。她们作为残疾的、可被任意处置的种性化人群 的危急处境,不仅指出了必须挫败的针对中国的暴力,而且还揭示了一种 必须面对的全球扩张的生物种性政治。必须挫败这样的暴力,是为了她们 直接的生存;必须面对它们的全球扩张,是为了她们所有的生命可能。她 们对“现代残疾人性”的“残疾社会性别”的剖析,使得对各种特定不同 的“生物种性犯”(bioethnic convicts)进行认知成为可能,从而提供了, 种女性主导的、照亮和激活不同“生物种性犯”既定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 的范式。 这样一种剖析和认知,与世纪之交各种其他更引人注意的话语有所 不同,后者的重点是积极地拥抱欧洲现代性模式,包括它们的自由女权主 义的各种变体。①同时,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是这种剖析从根本上反 对当时另外一些“国粹”运动,其要义是对抗女性主义和其他旨在根本变 革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社会运动。®她们既没有被对一个失去的黄金时代的 怀旧姿态所主导,也没有被拥抱西方现代性规范的冲动所消耗③,即便她 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姿态和冲动的影响和局限,这些姿态和冲动是一 个危机丛生的社会中,新生的、混乱的文化和公共政治的一部分。在她们 ①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知识分子这样一种“反传统”的行为方式一及其对立面一的概述, 参见李祥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台北:麦田出版有限贵任公司,1999年。 ②间上。又见Charlotte Furth,“The Sage as Rebel:The Inner World of Chang Ping-lin"and Martin Bernal,"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in Charlotte Furth ed..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on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③两个知识分子阵营之间激烈争论的表现之一,是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与一系列文人的论战,见《鲁 迅金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