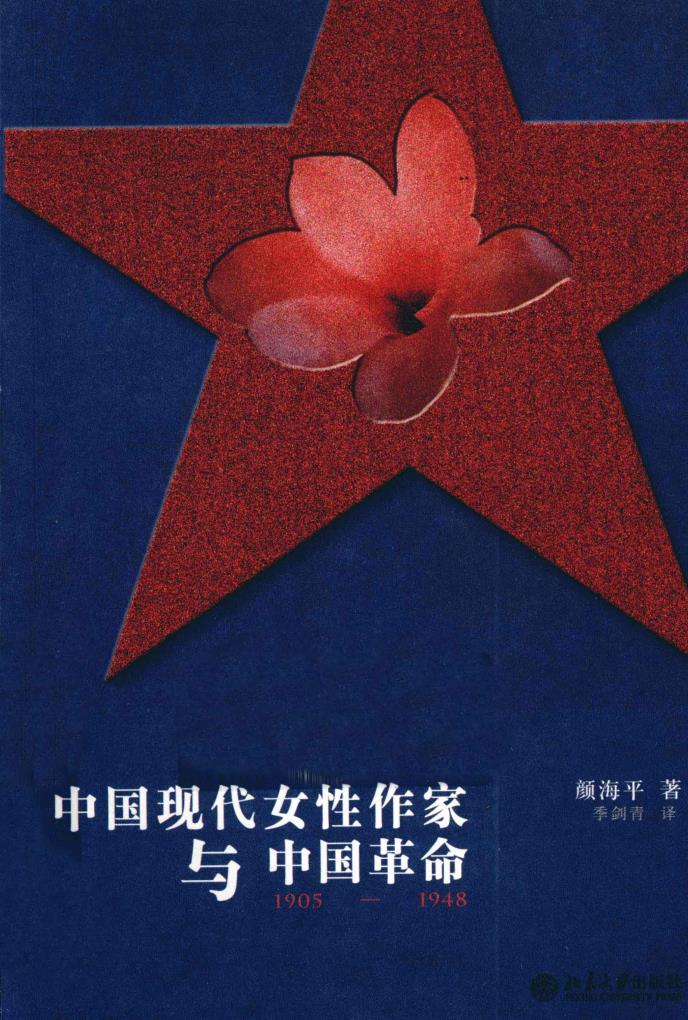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 颜海平著 季剑青译 与 中国革命 1905 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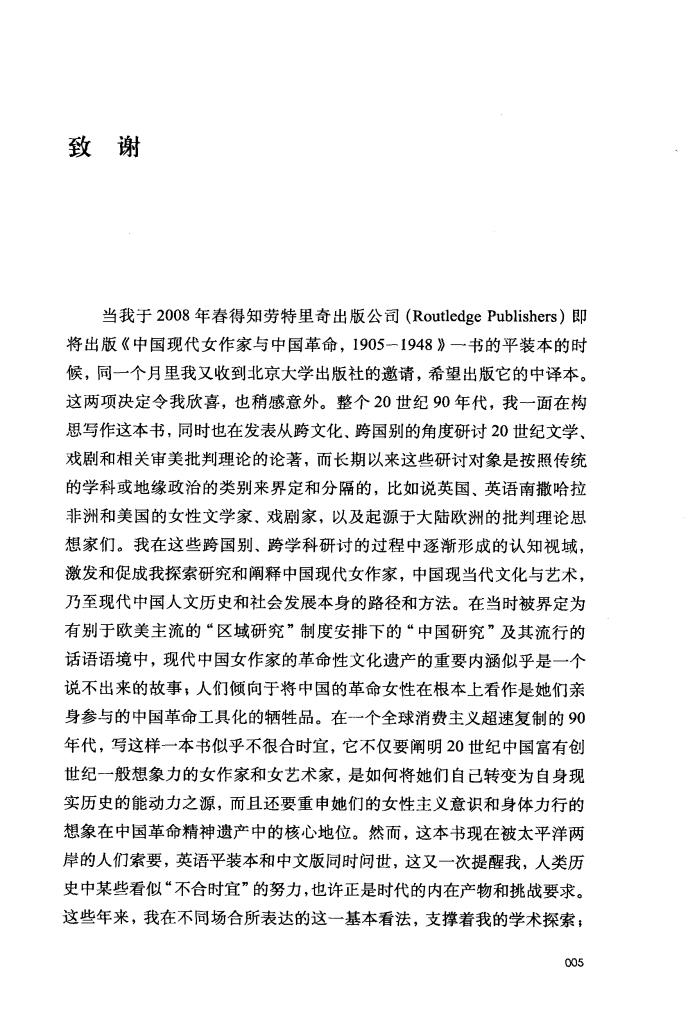
致谢 当我于2008年春得知劳特里奇出版公司(Routledge Publishers)即 将出版《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一1948》一书的平装本的时 候,同一个月里我又收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希望出版它的中译本。 这两项决定令我欣喜,也稍感意外。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一面在构 思写作这本书,同时也在发表从跨文化、跨国别的角度研讨20世纪文学、 戏剧和相关审美批判理论的论著,而长期以来这些研讨对象是按照传统 的学科或地缘政治的类别来界定和分隔的,比如说英国、英语南撒哈拉 非洲和美国的女性文学家、戏剧家,以及起源于大陆欧洲的批判理论思 想家们。我在这些跨国别、跨学科研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认知视域, 激发和促成我探索研究和阐释中国现代女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化与艺术, 乃至现代中国人文历史和社会发展本身的路径和方法。在当时被界定为 有别于欧美主流的“区域研究”制度安排下的“中国研究”及其流行的 话语语境中,现代中国女作家的革命性文化遗产的重要内涵似乎是一个 说不出来的故事,人们倾向于将中国的革命女性在根本上看作是她们亲 身参与的中国革命工具化的牺牲品。在一个全球消费主义超速复制的90 年代,写这样一本书似乎不很合时宜,它不仅要阐明20世纪中国富有创 世纪一般想象力的女作家和女艺术家,是如何将她们自己转变为自身现 实历史的能动力之源,而且还要重申她们的女性主义意识和身体力行的 想象在中国革命精神遗产中的核心地位。然而,这本书现在被太平洋两 岸的人们索要,英语平装本和中文版同时问世,这又一次提醒我,人类历 史中某些看似“不合时宜”的努力,也许正是时代的内在产物和挑战要求。 这些年来,我在不同场合所表达的这一基本看法,支撑着我的学术探索;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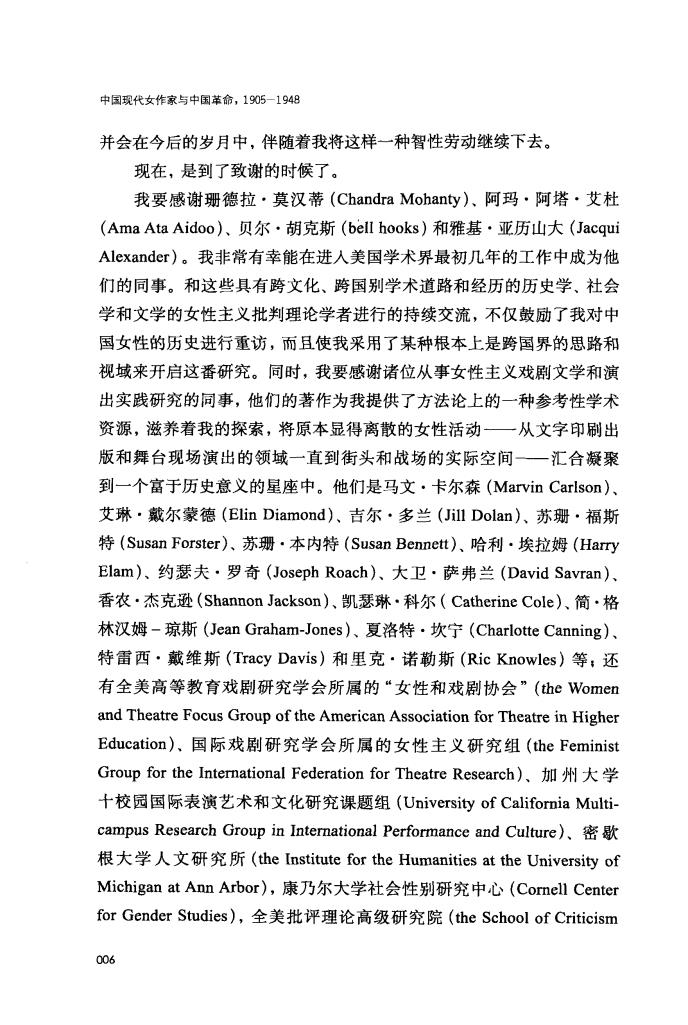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并会在今后的岁月中,伴随着我将这样一种智性劳动继续下去。 现在,是到了致谢的时候了。 我要感谢珊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阿玛·阿塔·艾杜 (Ama Ata Aidoo)、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和雅基·亚历山大(Jacqui Alexander)。我非常有幸能在进人美国学术界最初几年的工作中成为他 们的同事。和这些具有跨文化、跨国别学术道路和经历的历史学、社会 学和文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学者进行的持续交流,不仅鼓励了我对中 国女性的历史进行重访,而且使我采用了某种根本上是跨国界的思路和 视域来开启这番研究。同时,我要感谢诸位从事女性主义戏剧文学和演 出实践研究的同事,他们的著作为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一种参考性学术 资源,滋养着我的探索,将原本显得离散的女性活动一从文字印刷出 版和舞台现场演出的领域一直到街头和战场的实际空间一汇合凝聚 到一个富于历史意义的星座中。他们是马文·卡尔森(Marvin Carlson)、 艾琳·戴尔蒙德(Elin Diamond)、吉尔·多兰(Jill Dolan)、苏珊·福斯 特(Susan Forster)、苏珊·本内特(Susan Bennett)、哈利·埃拉姆(Harry Elam)、约瑟夫·罗奇(Joseph Roach)、大卫·萨弗兰(David Savran)、 香农·杰克逊(Shannon Jackson)、凯瑟琳·科尔(Catherine Cole)、简·格 林汉姆-琼斯(Jean Graham-Jones)、夏洛特·坎宁(Charlotte Canning)、 特雷西·戴维斯(Tracy Davis)和里克·诺勒斯(Ric Knowles)等,还 有全美高等教育戏剧研究学会所属的“女性和戏剧协会”(the Women and Theatre Focus Group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atre in Higher Education)、国际戏剧研究学会所属的女性主义研究组(the Feminist Group for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atre Research)、加州大学 十校园国际表演艺术和文化研究课题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ulti- campus Research Group in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and Culture) 根大学人文研究所(the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康乃尔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Cornell Center for Gender Studies),全美批评理论高级研究院(the School of Criticism 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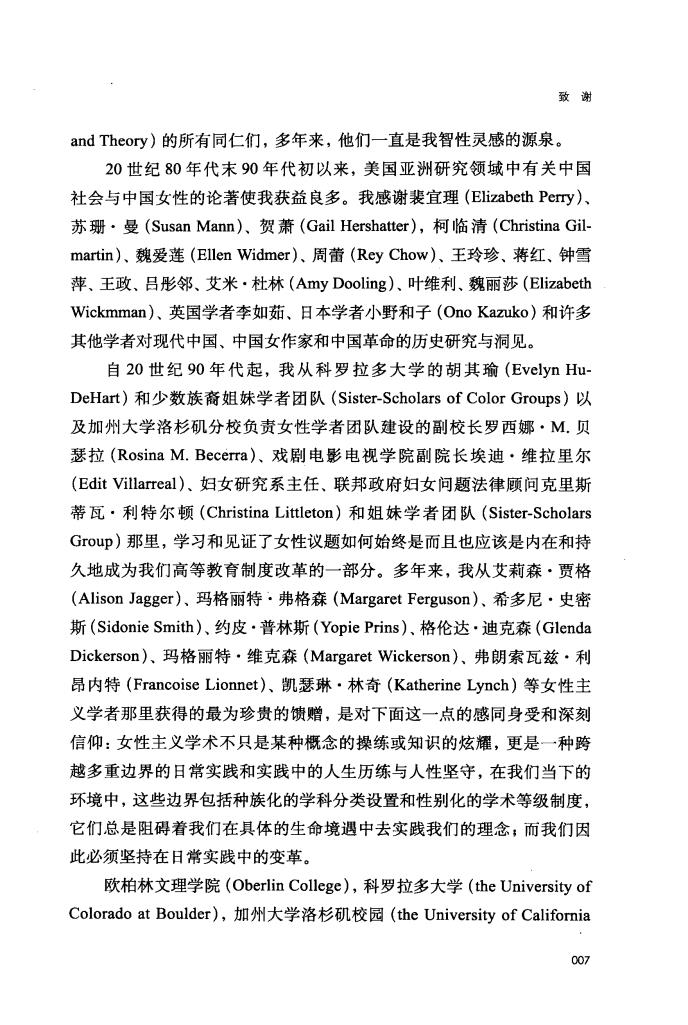
致谢 and Theory)的所有同仁们,多年来,他们一直是我智性灵感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亚洲研究领域中有关中国 社会与中国女性的论著使我获益良多。我感谢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苏珊·曼(Susan Mann)、贺萧(Gail Hershatter),柯临清(Christina Gil- martin)、魏爱莲(Ellen Widmer)、周蕾(Rey Chow)、王玲珍、蒋红、钟雪 萍、王政、吕彤邻、艾米·杜林(Amy Dooling)、叶维利、魏丽莎(Elizabeth Wickmman)、英国学者李如茹、日本学者小野和子(Ono Kazuko)和许多 其他学者对现代中国、中国女作家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与洞见。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从科罗拉多大学的胡其瑜(Evelyn Hu DeHart)和少数族裔姐妹学者团队(Sister-Scholars of Color Groups)以 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负责女性学者团队建设的副校长罗西娜·M. 瑟拉(Rosina M.Becerra)、戏剧电影电视学院副院长埃迪·维拉里尔 (Edit Villarreal)、妇女研究系主任、联邦政府妇女问题法律顾问克里斯 蒂瓦·利特尔顿(Christina Littleton)和姐妹学者团队(Sister-Scholars Goup)那里,学习和见证了女性议题如何始终是而且也应该是内在和持 久地成为我们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多年来,我从艾莉森·贾格 (Alison Jagger)、玛格丽特·弗格森(Margaret Ferguson)、希多尼·史密 斯(Sidonie Smith)、约皮·普林斯(Yopie Prins),格伦达·迪克森(Glenda Dickerson)、玛格丽特·维克森(Margaret Wickerson)、弗朗索瓦兹·利 昂内特(Francoise Lionnet)、凯瑟琳·林奇((Katherine Lynch)等女性主 义学者那里获得的最为珍贵的馈赠,是对下面这一点的感同身受和深刻 信仰:女性主义学术不只是某种概念的操练或知识的炫耀,更是一一种跨 越多重边界的日常实践和实践中的人生历练与人性坚守,在我们当下的 环境中,这些边界包括种族化的学科分类设置和性别化的学术等级制度, 它们总是阻碍着我们在具体的生命境遇中去实践我们的理念,而我们因 此必须坚持在日常实践中的变革。 欧柏林文理学院(Oberlin College),科罗拉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园(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007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at Los Angeles),密西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 的学生和友人,尤其是我在美国的求学之地,现应邀任教的康乃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的卓越的师友们,是我在英语世界里,尝试叙说这 “中国故事”最初因此亦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听众。 我要向女性主义研究的中国同行和女性学人致意,她们是北京大学 的乐黛云、戴锦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路爱国,清华大学的曹莉,北京外 国语大学的孙瑞珍,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玉、徐静华、姜进,上海文新集 团的汪澜,上海妇女联合会的孙小棋,上海文化界的王安忆、黄蜀芹、彭 小莲,母校复旦大学已故校长谢希德和所有杰出的前辈老师与同窗友人, 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贺美英和所有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爱护扶助我的 前辈和同仁,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与历史学者张济顺和所有多年诚挚 合作的学友同行,还有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其他许多从事人文社科研 究的朋友们,感谢她们在三十年巨变中,作为女性在智性前沿作出的卓 越成就,和对我始终如一的支持。 我要特别感谢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的迪莉娅·达文 (Delia Davin)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林春,这本书从最初的构思起,即得到了她们热 情慷慨、具体明确而富于洞见的评论和建议。 由美·塞尔登(Yumi Selden)一她自己就是一位优美的作家 对我为完成这本书而付出的十多年的努力而言,一直是一泓生命的源泉: 她的编辑协助工作一直都是无法估价的,就像这些年来我和她一以及 通过她和她的孩子们一进行的交流和讨论无法估价一样。 我要对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致以深切的感谢,作为“亚洲 的转变”(Asia's Transformations)系列丛书的总编,他那非同寻常的耐心 广博的知识和个人的热忱使得这本书付梓成为可能。和劳特里奇出版公 司的出色团队合作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这个团队是由斯蒂芬 妮·罗杰斯(Stephanie Rogers)领导的,包括索恩亚·范·里乌文(Sonia van Leeuwen)和所有其他同事。 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