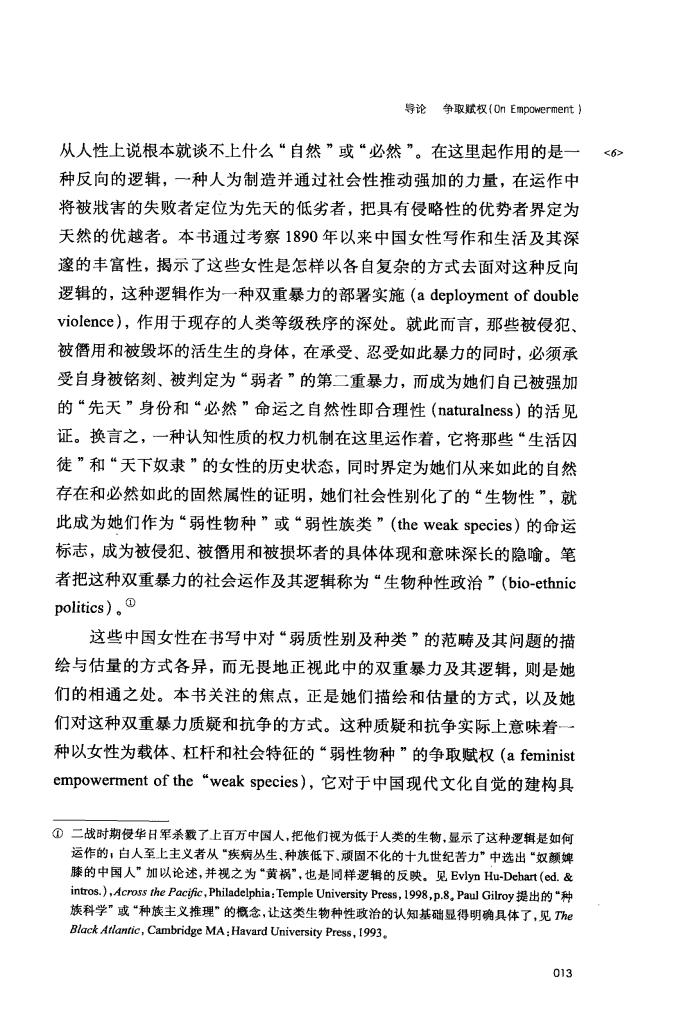
导论争取默权{On Empowerment) 从人性上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自然”或“必然”。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 <6> 种反向的逻辑,一种人为制造并通过社会性推动强加的力量,在运作中 将被戕害的失败者定位为先天的低劣者,把具有侵略性的优势者界定为 天然的优越者。本书通过考察1890年以来中国女性写作和生活及其深 邃的丰富性,揭示了这些女性是怎样以各自复杂的方式去面对这种反向 逻辑的,这种逻辑作为一种双重暴力的部署实施(a deployment of double violence),作用于现存的人类等级秩序的深处。就此而言,那些被侵犯、 被僭用和被毁坏的活生生的身体,在承受、忍受如此暴力的同时,必须承 受自身被铭刻、被判定为“弱者”的第二重暴力,而成为她们自己被强加 的“先天”身份和“必然”命运之自然性即合理性(naturalness)的活见 证。换言之,一种认知性质的权力机制在这里运作着,它将那些“生活囚 徒”和“天下奴隶”的女性的历史状态,同时界定为她们从来如此的自然 存在和必然如此的固然属性的证明,她们社会性别化了的“生物性”,就 此成为她们作为“弱性物种”或“弱性族类”(the weak species)的命运 标志,成为被侵犯、被僭用和被损坏者的具体体现和意味深长的隐喻。笔 者把这种双重暴力的社会运作及其逻辑称为“生物种性政治”(bio-ethnic politics)。@ 这些中国女性在书写中对“弱质性别及种类”的范畴及其问题的描 绘与估量的方式各异,而无畏地正视此中的双重暴力及其逻辑,则是她 们的相通之处。本书关注的焦点,正是她们描绘和估量的方式,以及她 们对这种双重暴力质疑和抗争的方式。这种质疑和抗争实际上意味着一 种以女性为载体、杠杆和社会特征的“弱性物种”的争取赋权(a feminist empowerment of the“weak species),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建构具 ①二战时期侵华日军杀裁了上百万中国人,把他们视为低于人类的生物,显示了这种逻辑是如何 运作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从“疾病丛生、种族低下、顽固不化的十九世纪苦力”中选出“奴颜蝉 藤的中国人"加以论述,并视之为“黄祸”,也是同样逻辑的反映。见Evlyn Hu-Dehart(ed.& intros.),Across the Pacific,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l998,p.8,Paul Gilroy提出的“种 族科学”或“种族主义推理”的概念,让这类生物种性政治的认知基础显得明确具体了,见Th Black Atlantic,Cambridge MA: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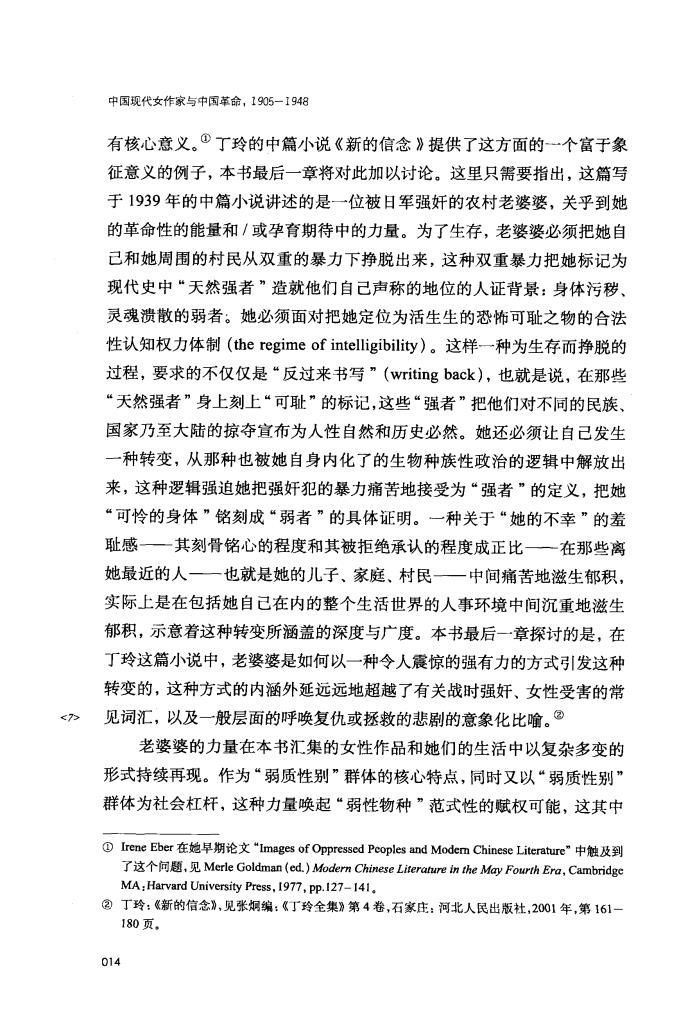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一1948 有核心意义。®丁玲的中篇小说《新的信念》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富于象 征意义的例子,本书最后一章将对此加以讨论。这里只需要指出,这篇写 于1939年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被日军强奸的农村老婆婆,关乎到她 的革命性的能量和/或孕育期待中的力量。为了生存,老婆婆必须把她自 己和她周围的村民从双重的暴力下挣脱出来,这种双重暴力把她标记为 现代史中“天然强者”造就他们自己声称的地位的人证背景:身体污秽、 灵魂溃散的弱者。她必须面对把她定位为活生生的恐怖可耻之物的合法 性认知权力体制(the regime of intelligibility)。这样一种为生存而挣脱的 过程,要求的不仅仅是“反过来书写”(writing back),也就是说,在那些 “天然强者”身上刻上“可耻”的标记,这些“强者”把他们对不同的民族、 国家乃至大陆的掠夺宣布为人性自然和历史必然。她还必须让自己发生 一种转变,从那种也被她自身内化了的生物种族性政治的逻辑中解放出 来,这种逻辑强迫她把强奸犯的暴力痛苦地接受为“强者”的定义,把她 “可怜的身体”铭刻成“弱者”的具体证明。一种关于“她的不幸”的羞 耻感一一其刻骨铭心的程度和其被拒绝承认的程度成正比一在那些离 她最近的人一一也就是她的儿子、家庭、村民一中间痛苦地滋生郁积, 实际上是在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整个生活世界的人事环境中间沉重地滋生 郁积,示意着这种转变所涵盖的深度与广度。本书最后一章探讨的是,在 丁玲这篇小说中,老婆婆是如何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强有力的方式引发这种 转变的,这种方式的内涵外延远远地超越了有关战时强奸、女性受害的常 <7 见词汇,以及一般层面的呼唤复仇或拯救的悲剧的意象化比喻。® 老婆婆的力量在本书汇集的女性作品和她们的生活中以复杂多变的 形式持续再现。作为“弱质性别”群体的核心特点,同时又以“弱质性别” 群体为社会杠杆,这种力量唤起“弱性物种”范式性的赋权可能,这其中 ①Irene Eber在她早期论文“Images of Oppressed Peoples and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中触及到 了这个问题,见Merle Goldman(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27-141. ②丁玲:《新的信念》,见张炯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1一 180页, 014

导论争取赋权(On Empowerment】 蕴含的悖论性的紧张,正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其想象的重心所在。0冰 心下面这句深刻的悖论式的警句,以持久敏锐的活力,似乎说的就是她们 的毕生事业:“我柔弱,所以我强韧。” 非真的蕴律:活遗产的场所和源泉 想象,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并不构成具体现实的活跃的能量。然而考 虑到人类生命离不开它,想象并不非得一实际上也不能—一和纯粹的 幻想混为一谈。毕竟虚构性的写作并不就是虚假性的产生。例如,丁玲的 虚构作品就让我们想起人类劫难和社会破环一特别是包括战争史上大 批被强暴的女性一的实际存在。想象,作为看得见的物质身体和看不 见的生命灵动的共同寓所,是这些女性成为潜在的能动力量的杠杆,使她 们可能成为转换性社会关系的场所和源泉。正如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所 注意到的,那些否则就是“天然”的被动无力者的这样一种对赋权的坚韧 争取一这些争取促进和推动了这种写作一在整个20世纪的不同时 刻反复地出现在女性实际的生活中,就像这本书研究的女作家们的生活道 路部分所见证的那样。本书下面的章节将逐一探讨这些女性是如何去面 对她们亲身所处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如何同时也是置身世界之中的中国的 结构转变的记录和呈现。她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拒绝把社会对于“弱质 性别”的规定和对“弱性物种”的设计作为她们的命运,努力从生物种性 政治运作的双重暴力的势力场中生存下来,在喧器甚至狂暴的社会和社会 运动中坚持和坚守着,杯着她们对时代的渴望而工作:在书案或者在街头, 在戏剧舞台和电影屏幕上,在大学的报告厅中,在公共的论坛或会议上, 同样也在监狱牢房、群众集会和武装暴动中。®作为社会性的个人和社会 ⊙这类主题出现在石评梅、陆晶清、陈学昭,沉樱、林数因、罗鸿、罗淑、冯悭及许多其他女作家的作 品中。限于篇幅,本书无法讨论这些作品。 Bobby Siu,Women of China:Imperialism and Women's Resistance 1900-1949,London:Zed Press, 1982.Ono Kazuko (Joshua A.Fogel,ed.),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Christine Gilmartin,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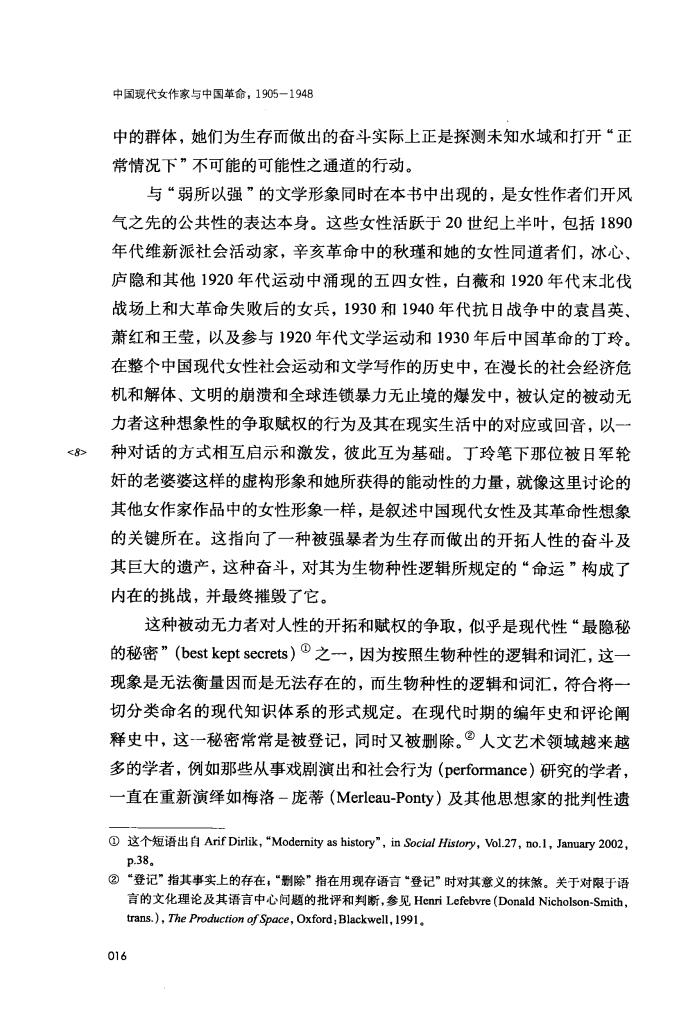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苹命,1905一1948 中的群体,她们为生存而做出的奋斗实际上正是探测未知水域和打开“正 常情况下”不可能的可能性之通道的行动。 与“弱所以强”的文学形象同时在本书中出现的,是女性作者们开风 气之先的公共性的表达本身。这些女性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包括1890 年代维新派社会活动家,辛亥革命中的秋瑾和她的女性同道者们,冰心、 庐隐和其他1920年代运动中涌现的五四女性,白薇和1920年代末北伐 战场上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女兵,1930和1940年代抗日战争中的袁昌英、 萧红和王莹,以及参与1920年代文学运动和1930年后中国革命的丁玲。 在整个中国现代女性社会运动和文学写作的历史中,在漫长的社会经济危 机和解体、文明的崩遗和全球连锁暴力无止境的爆发中,被认定的被动无 力者这种想象性的争取赋权的行为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对应或回音,以一 <8> 种对话的方式相互启示和激发,彼此互为基础。丁玲笔下那位被日军轮 奸的老婆婆这样的虚构形象和她所获得的能动性的力量,就像这里讨论的 其他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样,是叙述中国现代女性及其革命性想象 的关键所在。这指向了一种被强暴者为生存而做出的开拓人性的奋斗及 其巨大的遗产,这种奋斗,对其为生物种性逻辑所规定的“命运”构成了 内在的挑战,并最终摧毁了它。 这种被动无力者对人性的开拓和赋权的争取,似乎是现代性“最隐秘 的秘密”(best kept secrets)O之一,因为按照生物种性的逻辑和词汇,这一 现象是无法衡量因而是无法存在的,而生物种性的逻辑和词汇,符合将一 切分类命名的现代知识体系的形式规定。在现代时期的编年史和评论阐 释史中,这一秘密常常是被登记,同时又被删除。②人文艺术领域越来越 多的学者,例如那些从事戏剧演出和社会行为(performance)研究的学者, 一直在重新演绎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及其他思想家的批判性遗 ①这个短语出自Arif Dirlik,“Modernity as history”,in Social History,Vol.27,no.l,January2002, p.38。 ②“登记”指其事实上的存在,“别除”指在用现存语言“登记”时对其意义的抹煞。关于对限于语 言的文化理论及其语言中心问题的批评和判断,参见Henri Lefebvre(Donald Nicholson-Smit油, trans.),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1991. 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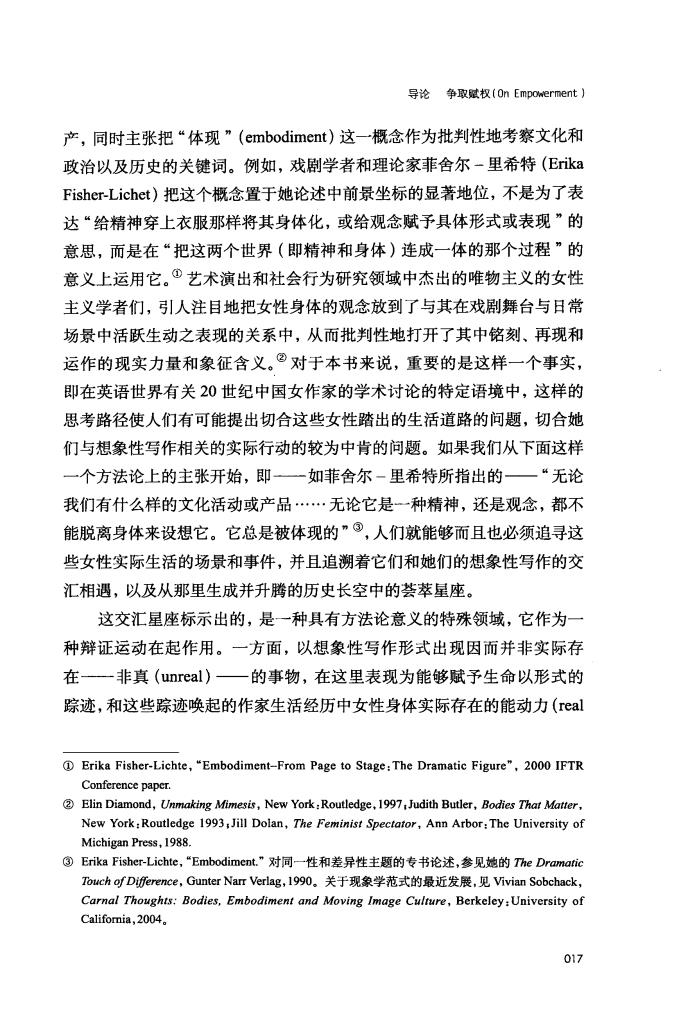
导论争取城权(On Empowerment】 产,同时主张把“体现”(embodiment)这一概念作为批判性地考察文化和 政治以及历史的关键词。例如,戏剧学者和理论家菲舍尔-里希特(Eika Fisher--Lichet)把这个概念置于她论述中前景坐标的显著地位,不是为了表 达“给精神穿上衣服那样将其身体化,或给观念赋予具体形式或表现”的 意思,而是在“把这两个世界(即精神和身体)连成一体的那个过程”的 意义上运用它。①艺术演出和社会行为研究领域中杰出的唯物主义的女性 主义学者们,引人注目地把女性身体的观念放到了与其在戏剧舞台与日常 场景中活跃生动之表现的关系中,从而批判性地打开了其中铭刻、再现和 运作的现实力量和象征含义。②对于本书来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英语世界有关20世纪中国女作家的学术讨论的特定语境中,这样的 思考路径使人们有可能提出切合这些女性踏出的生活道路的问题,切合她 们与想象性写作相关的实际行动的较为中肯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下面这样 一个方法论上的主张开始,即一如菲舍尔一里希特所指出的一“无论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活动或产品…无论它是一种精神,还是观念,都不 能脱离身体来设想它。它总是被体现的”③,人们就能够而且也必须追寻这 些女性实际生活的场景和事件,并且追溯着它们和她们的想象性写作的交 汇相遇,以及从那里生成并升腾的历史长空中的荟萃星座。 这交汇星座标示出的,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特殊领域,它作为一 种辩证运动在起作用。一方面,以想象性写作形式出现因而并非实际存 在一非真(unreal)一的事物,在这里表现为能够赋予生命以形式的 踪迹,和这些踪迹唤起的作家生活经历中女性身体实际存在的能动力(eal D Erika Fisher-Lichte,"Embodiment-From Page to Stage:The Dramatic Figure",2000 IFTR Conference paper. 2 Elin Diamond,Unmaking Mimesis,New York:Routledge,1997.Judith Butler,Bodies That Matter, New York:Routledge 1993:Jill Dolan,The Feminist Spectato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 ③Erika Fisher-Lichte,“Embodiment..”对同一性和差异性主题的专书论述,参见地的The Dramatic Touch of Difference,Gunter Narr Verlag,l990。关于现象学范式的最近发展,见Vivian Sobchack, Carnal Thoughts:Bodies,Embodiment and Moving Image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4. 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