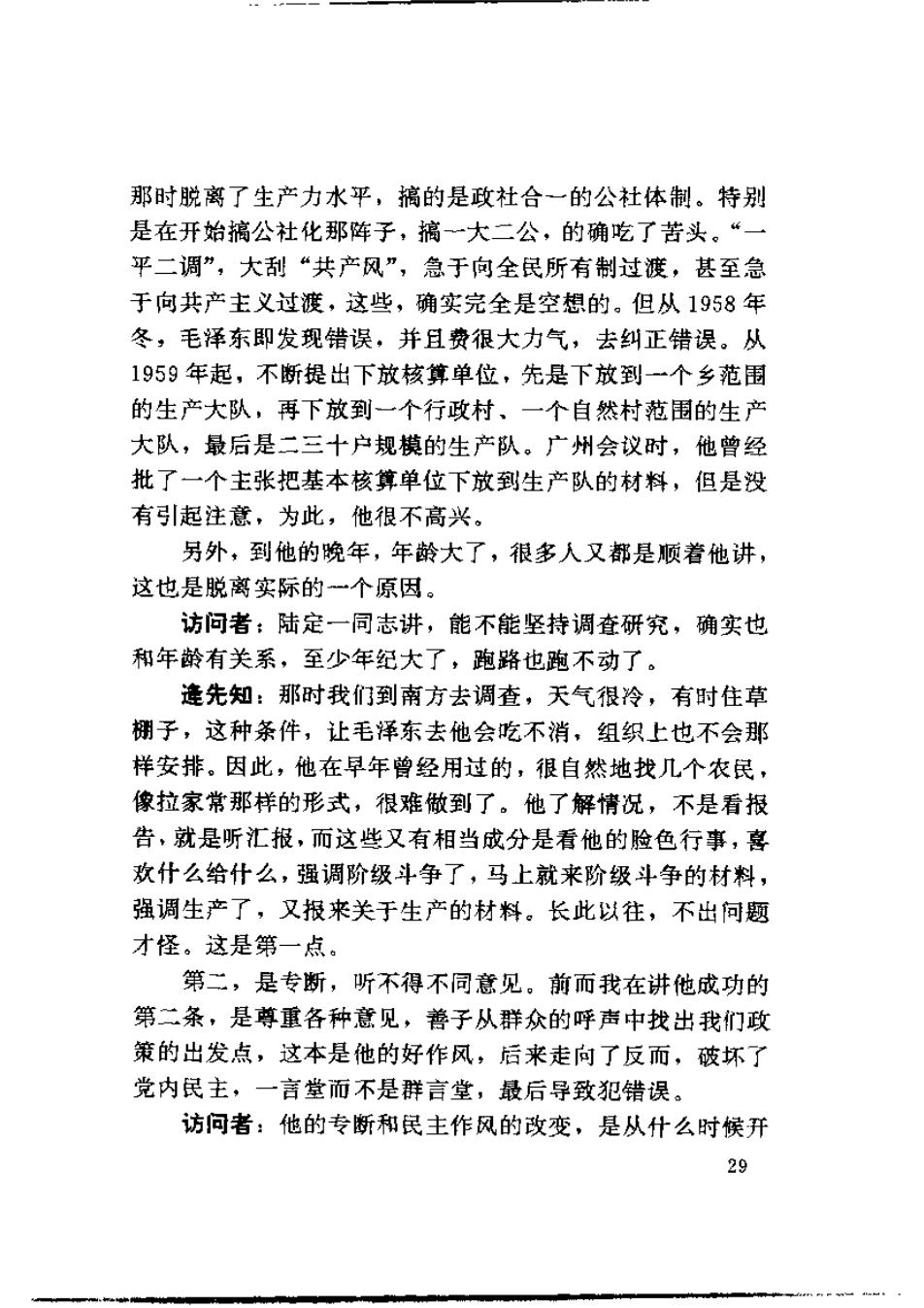
那时脱离了生产力水平,搞的是政社合一的公杜体制。特别 是在开始搞公社化那阵子,搞一大二公,的确吃了苦头。“一 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急 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确实完全是空想的。但从1958年 冬,毛泽东即发现错误,并且费很大力气,去纠正错误。从 1959年起,不断提出下放核算单位,先是下放到一个乡范围 的生产大队,再下放到一个行政村、一个自然村范围的生产 大队,最后是二三十户规模的生产队。广州会议时,他曾经 批了一个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材料,但是没 有引起注意,为此,他很不高兴。 另外,到他的晚年,年龄大了,很多人又都是顺着他讲, 这也是脱离实际的一个原因。 访问者:陆定一同志讲,能不能坚持调查研究,确实也 和年龄有关系,至少年纪大了,跑路也跑不动了。 逢先知:那时我们到南方去调查,天气很冷,有时住草 棚子,这种条件,让毛泽东去他会吃不消,组织上也不会那 样安排。因此,他在早年曾经用过的,很自然地找几个农民, 像拉家常那样的形式,很难做到了。他了解情况,不是看报 告,就是听汇报,而这些又有相当成分是看他的脸色行事,喜 欢什么给什么,强调阶级斗争了,马上就来阶级斗争的材料, 强调生产了,又报来关于生产的材料。长此以往,不出问题 才怪。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前而我在讲他成功的 第二条,是尊重各种意见,善子从群众的呼声中找出我们政 策的出发点,这本是他的好作风,后来走向了反而,破坏了 党内民主,一言堂而不是群言堂,最后导致犯错误。 访问者:他的专断和民主作风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 29

始的? 逢先知:按胡乔木同志讲,是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 评“反冒进”开始。但这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一个过程,1958 年南宁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3月的成都会议还算开得 生动活泼,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又来了一个升级,以后专断 就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他脱离实际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听 不得不同意见而导致专断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访问者:有人认为,庐山会议彭老总那种提意见的方式 也有不好的一而,如果换一种较为和缓的方式,后来的结果 可能不一样,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逢先知:过去乔木同志也讲过,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 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如果是当而的心平气和 地讲,不用赌气,情况也许不同一些。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当 然,这是问题的一而,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那时党内很多 人对“三面红旗”有意见,持不同意见的材料也陆续反映到 毛泽东那里,彭德怀只是一个代表,即使不是他出来讲,总 会有人出来讲,当然不至子出现那样尖锐的形式。另外,国 际上出现的赫鲁晓夫全而否定斯大林以及引起的一股反共恿 、潮,对毛泽东走向“左”的东面影响很大。在那种环境下,他 不能不想到我们党,不能不维护他提出的一套在他看来是正 确的东西,因此,出现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的那种结局 也是必然的了。 尽管如此,还要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是在一定 范围内偏离了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没有 一点正确的东西,那还不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搞垮了?特 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他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了 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的时机,打开了中美、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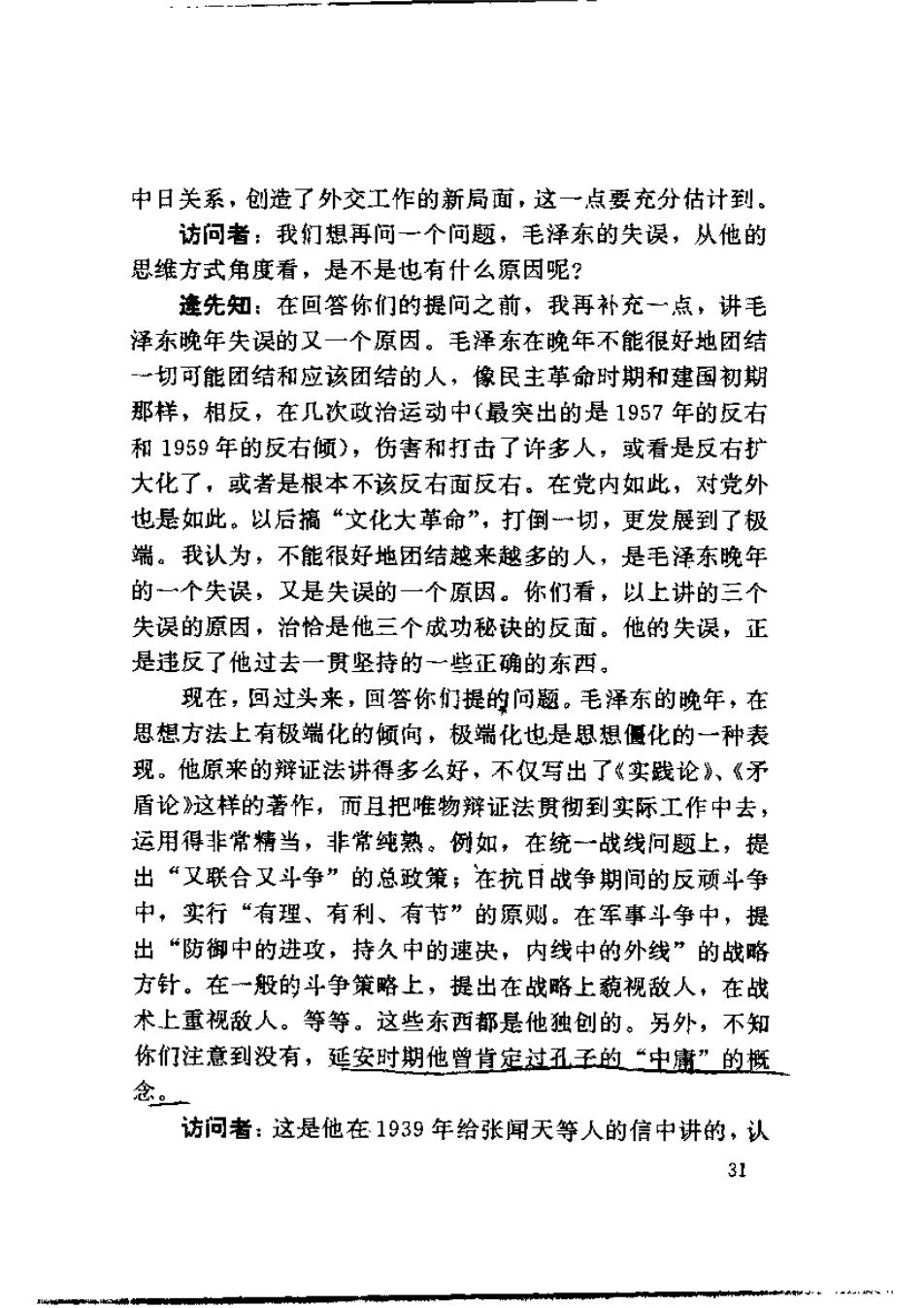
中日关系,创造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一点要充分估计到。 访问者: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毛泽东的失误,从他的 思维方式角度看,是不是也有什么原因呢? 逢先知:在回答你们的提问之前,我再补充一点,讲毛 泽东晚年失误的又一个原因。毛泽东在晚年不能很好地团结 一切可能团结和应该团结的人,像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 那样,相反,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的反右 和1959年的反右倾),伤害和打击了许多人,或看是反右扩 大化了,或者是根本不该反右面反右。在党内如此,对党外 也是如此。以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更发展到了极 端。我认为,不能很好地团结越来越多的人,是毛泽东晚年 的一个失误,又是失误的一个原因。你们看,以上讲的三个 失误的原因,治恰是他三个成功秘决的反面。他的失误,正 是违反了他过去一贯坚持的一些正确的东西。 现在,回过头来,回答你们提的问题。毛泽东的晚年,在 思想方法上有极端化的倾向,极端化也是思想偃化的一种表 现。他原来的辩证法讲得多么好,不仅写出了《实践论》、《矛 盾论》这样的著作,而且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运用得非常精当,非常纯熟。例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 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反顽斗争 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军事斗争中,提 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 方针。在一般的斗争策略上,提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 术上重视敌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独创的。另外,不知 你们注意到没有,延安时期他曾肯定过孔子的“中庸”的概 念。 访问者:这是他在1939年给张闻天等人的信中讲的,认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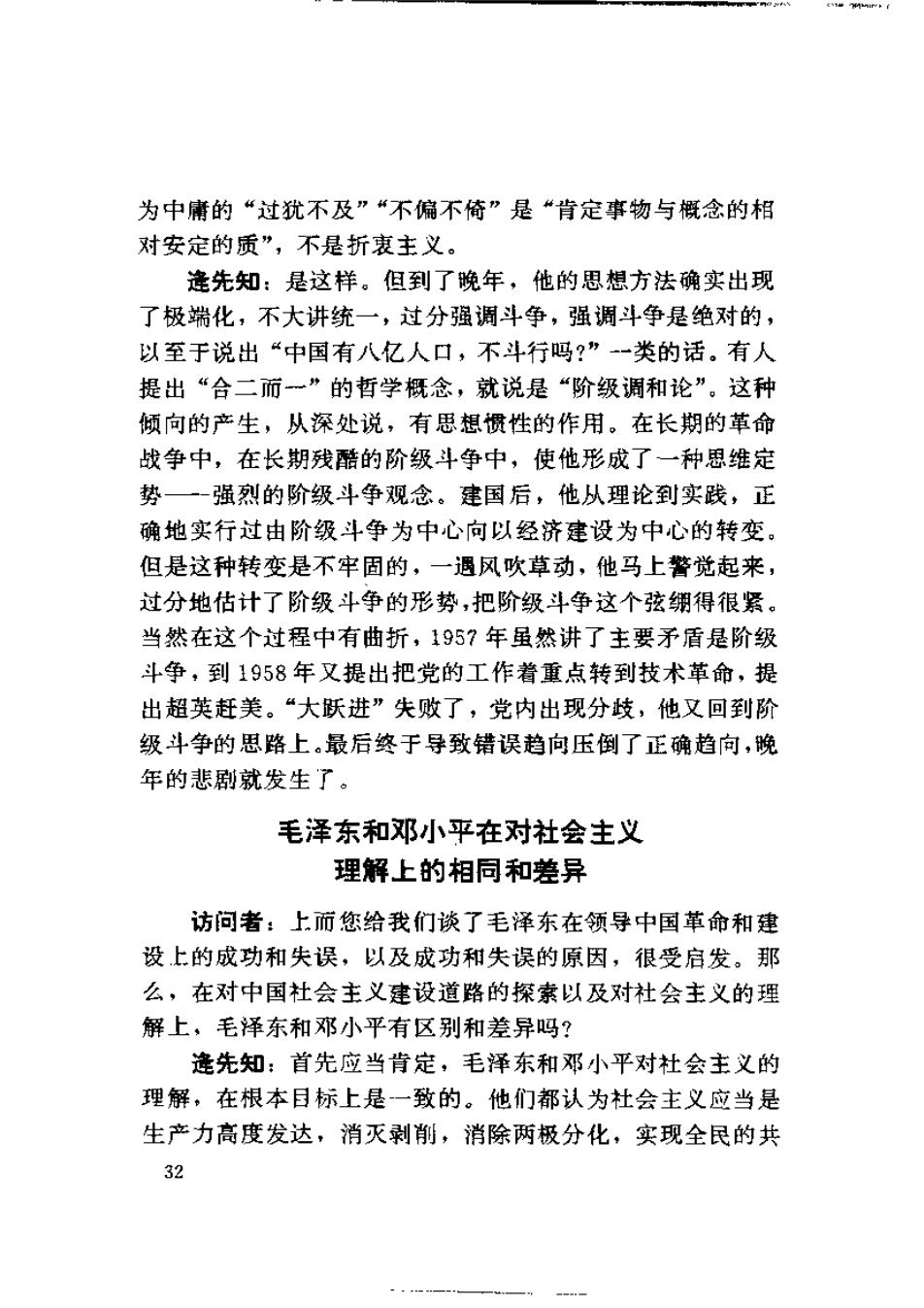
MIP 为中庸的“过犹不及”“不偏不倚”是“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 对安定的质”,不是折衷主义。 逢先知:是这样。但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方法确实出现 了极端化,不大讲统一,过分强调斗争,强调斗争是绝对的, 以至于说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一类的话。有人 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学概念,就说是“阶级调和论”。这种 倾向的产生,从深处说,有思想惯性的作用。在长期的革命 战争中,在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使他形成了一种思维定 势一-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建国后,他从理论到实践,正 确地实行过由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 但是这种转变是不牢固的,一遇风吹草动,他马上警觉起来, 过分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把阶级斗争这个弦绷得很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曲折,195?年虽然讲了主要矛盾是阶级 斗争,到1958年又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提 出超英赶美。“大跃进”失败了,党内出现分歧,他又回到阶 级斗争的思路上。最后终于导致错误趋向压倒了正确趋向,晚 年的悲剧就发生了。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 理解上的相同和差异 访问者:上而您给我们谈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 设上的成功和失误,以及成功和失误的原因,很受启发。那 么,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理 解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区别和差异吗? 逢先知:首先应当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杜会主义的 理解,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 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民的共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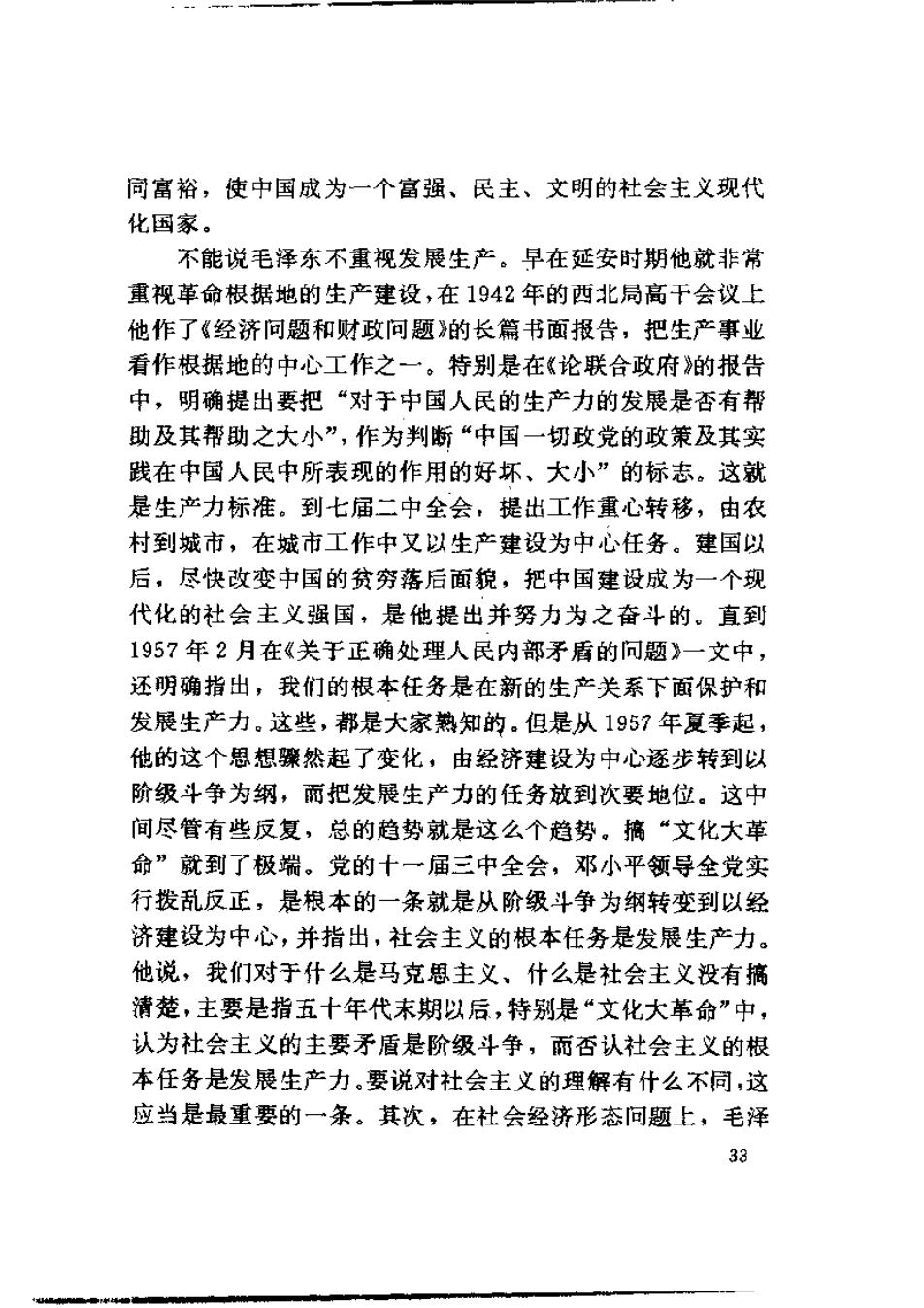
同富裕,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早在延安时期他就非常 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 他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把生产事业 看作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之一。特别是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中,明确提出要把“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 助及其帮助之大小”,作为判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 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的标志。这就 是生产力标准。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由农 村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又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建国以 后,尽快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 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他提出并努力为之奋斗的。直到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 还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 发展生产力。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从1957年夏季起, 他的这个思想骤然起了变化,由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到以 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放到次要地位。这中 间尽管有些反复,总的趋势就是这么个趋势。搞“文化大革 命”就到了极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领导全党实 行拨乱反正,是根本的一条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并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他说,我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 清楚,主要是指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 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而否认社会主义的根 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什么不同,这 应当是最重要的一条。其次,在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上,毛泽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