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茶水已经淡得跟白水差不多了,桌上的纸烟已经抽完,有人在 卷烟头了。罗队长正要宣布散会,曾工程师忽然提出个问题。他 把前胸紧靠着桌子,眼睛瞅着烟灰盒说: “指标,明年的各项指标,是不是都低了一点?” 一下子,会场的空气马上变了,仿佛甚么人一手推开了所有 这六面窗子。靠在椅背上打盹的,也伸直了腰。罗队长用眼晴 示意请曾刚说下去。 “这些数字,比咱们实际完成的还低一点,”曾刚手里捏着一 本计划,心里怪不好意思,所以把一点”说得特别清楚一些,以 缓和自已这个意见的锋芒。本来事先他已经在心里斗争了老半 天,可是这次会议和历次的会议的空气一向都那么温和,所以提 出这样的意见,事先都能预感到众人好奇的、责备的眼光会多么 难受:“我是说,应该把指标订高点。就说材料这一项,报上还批。 评过咱们,不想办法,明年超支要更严重。三分队的技术人员们 说,咱们队造两个桥就整整赔掉一个桥…” 罗立正心里好不自在。他鳅着曾刚的高而宽的前额,好象 在细心倾听别人的意见,心里可在想:哎一,怎么搞的,昨天在 下面都跟你谈了嘛:指标高点、低点有甚么关系?大家有多少劲 使多少劲嘛。“低点,超额容易点”一这个道理你还不懂?这 对国家也没有多少损失嘛! 经过周主任的解释,计划室主任又说了句“会后研究”,曾刚 这个问题没有引起甚么风波。可是这次事件却给罗立正一个警 号:曾刚这人在变! 从此,罗队长对三分队和曾工程师就多分了一份儿心。果 然,不出罗立正所料:从前,三分队新事儿也不少,一九五四年里 可有点特别。从前,罗立正觉得三分队出的事都和自已的意图 相吻合,比方说,打钢板桩不圆,是全队的大困难,三分队曾工程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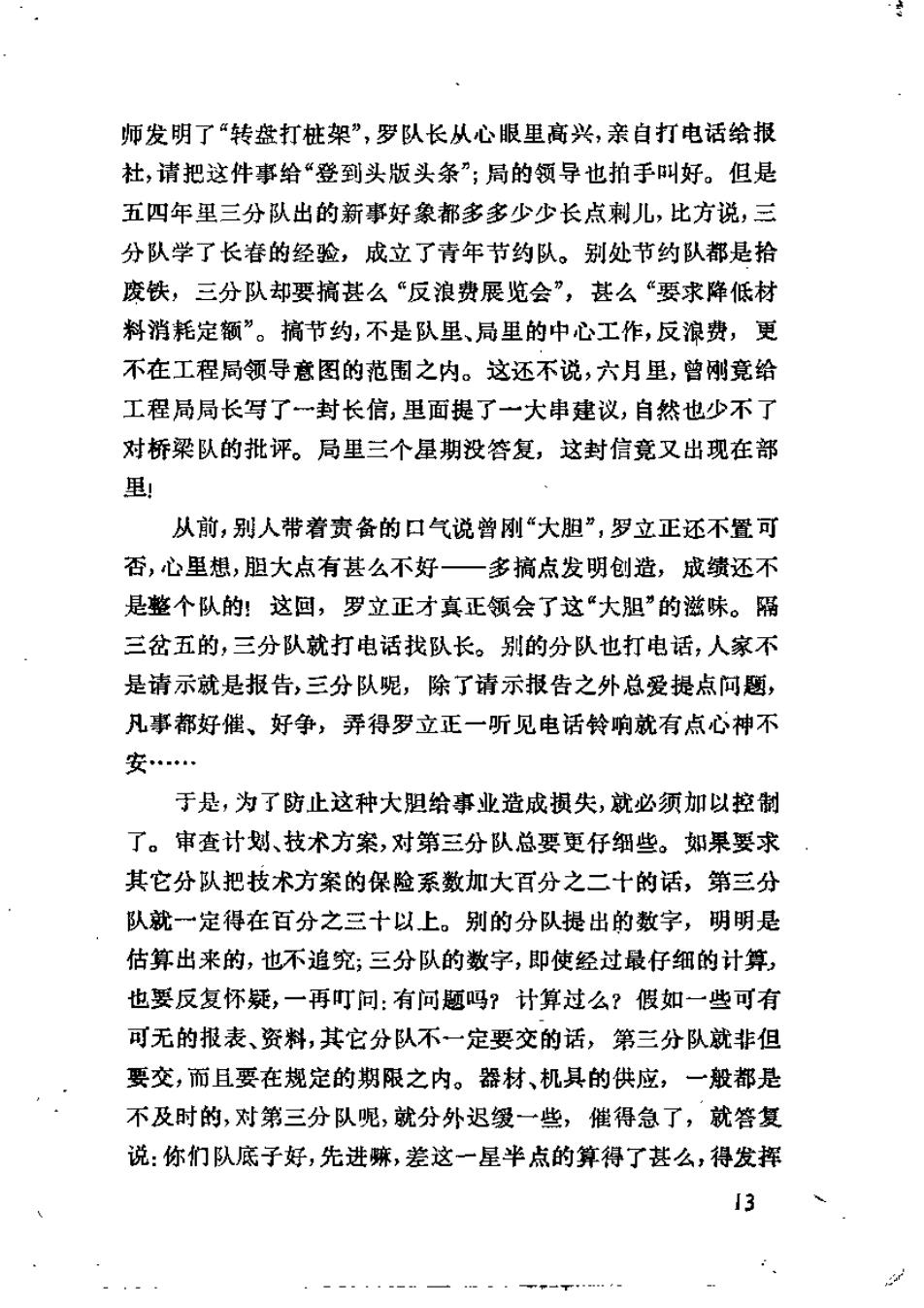
师发明了“转盘打桩架”,罗队长从心眼里高兴,亲自打电话给报 杜,请把这件事给“登到头版头条”;局的领导也拍手叫好。但是 五四年望三分队出的新事好象都多多少少长点刺儿,比方说,三 分队学了长春的经验,成立了青年节约队。别处节约队都是拾 废铁,三分队却要搞甚么“反浪费展览会”,甚么“要求降低材 料消耗定额”。搞节约,不是队里、局里的中心工作,反浪费,更 不在工程局领导意图的范围之内。这还不说,六月里,曾刚竟给 工程局局长写了一封长信,里面提了一大串建议,自然也少不了 对桥梁队的批评。局里三个星期没答复,这封信竟又出现在部 里! 从前,别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曾刚“大胆”,罗立正还不置可 否,心里想,胆大点有甚么不好一多搞点发明创造,成绩还不 是整个队的:这回,罗立正才真正领会了这“大胆”的滋味。隔 三岔五的,三分队就打电话我队长。别的分队也打电话,人家不 是请示就是报告,三分队呢,除了请示报告之外总爱提点问题, 凡事都好催、好争,弄得罗立正一听见电话铃响就有点心神不 安… 于是,为了防止这种大胆给事业造成损失,就必须加以控制 了。审查计划、技术方案,对第三分队总要更仔细些。如果要求 其它分队把技术方案的保险系数加大百分之二十的话,第三分 队就一定得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别的分队提出的数字,明明是 估算出来的,也不追究;三分队的数字,即使经过最仔细的计算, 也要反复怀疑,一再叮问:有问题吗?计算过么?假如一些可有 可无的报表、资料,其它分队不一定要交的话,第三分队就非但 要交,而且要在规定的期限之内。器材、机具的供应,一般都是 不及时的,对第三分队呢,就分外迟缓一些,催得急了,就答复 说:你们队底子好,先进嘛,差这一星半点的算得了甚么,得发挥 13 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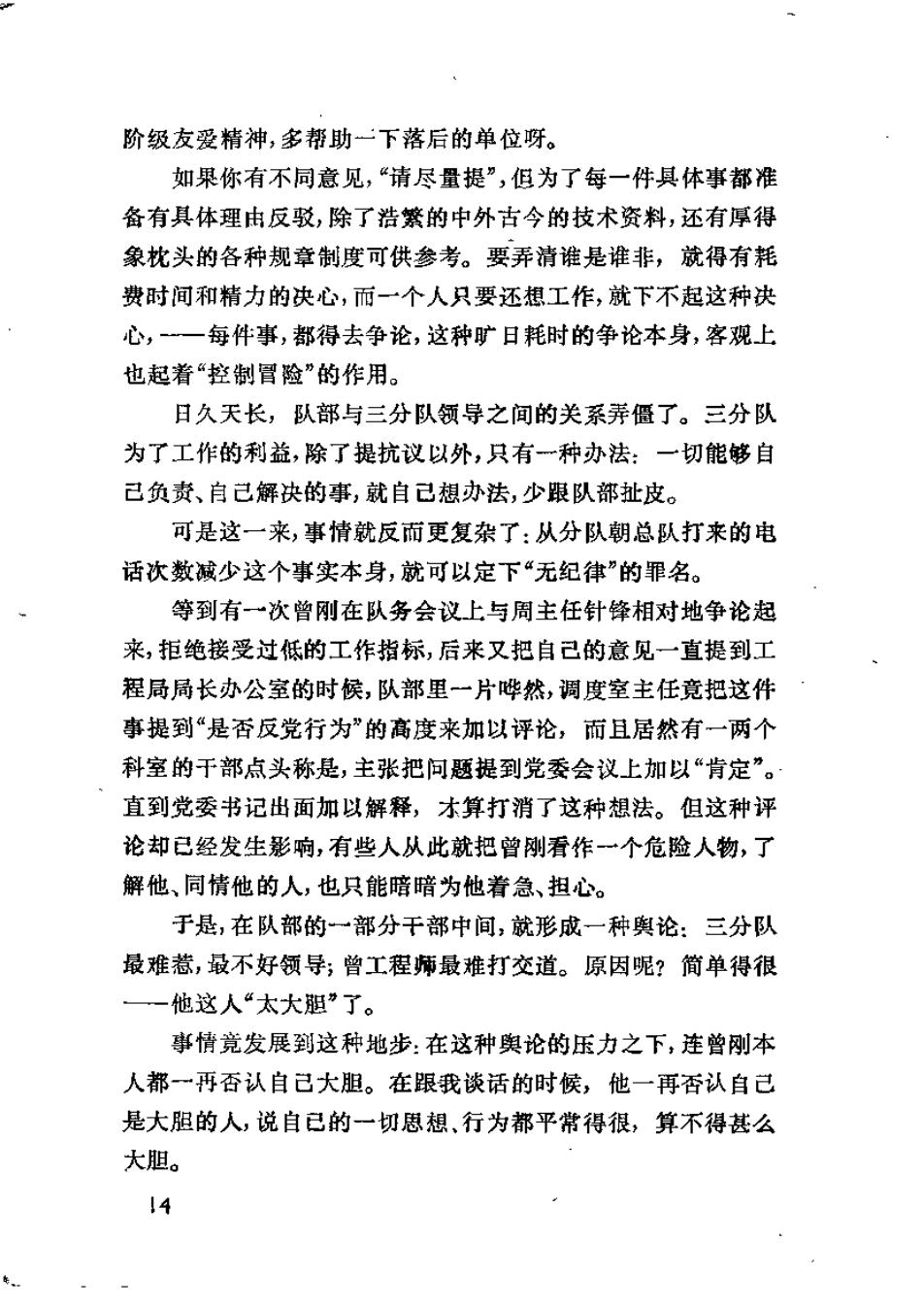
阶级友爱精神,多帮助一下落后的单位呀。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请尽量提”,但为了每一件具体事都准 备有具体理由反驳,除了浩繁的中外古今的技术资料,还有厚得 象枕头的各种规章制度可供参考。要弄清谁是谁非,就得有耗 费时间和精力的决心,而一个人只要还想工作,就下不起这种决 心,一一每件事,都得去争论,这种旷日耗时的争论本身,客观上 也起着“控制冒险”的作用。 日久天长,队部与三分队领导之间的关系弄僵了。三分队 为了工作的利益,除了提抗议以外,只有一种办法:一切能够自 已负责、自己解决的事,就自己想办法,少跟队部祉皮。 可是这一来,事情就反而更复杂了:从分队朝总队打来的电 话次数减少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定下“无纪律”的罪名。 等到有一次曾刚在队务会议上与周主任针锋相对地争论起 来,拒绝接受过低的工作指标,后来又把自己的意见一直提到工 程局局长办公室的时候,队部里一片哗然,调度室主任竟把这件 事提到“是否反党行为”的高度来加以评论,而且居然有一两个 科室的于部点头称是,主张把问题提到党委会议上加以“肯定”。 直到党委书记出面加以解释,才算打消了这种想法。但这种评 论却已经发生影响,有些人从此就把曾刚看作一个危险人物,了 解他、同情他的人,也只能暗暗为他着急、担心。 于是,在队部的一部分干部中间,就形成一种舆论:三分队 最难惹,最不好领导;曾工程师最推打交道。原因呢?简单得很 一一他这人“太大胆”了。 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在这种奥论的压力之下,连曾刚本 人都一再否认自己大胆。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他一再否认自己 是大胆的人,说自已的一切思想、行为都平常得很,算不得甚么 大胆。 14

后来才知道,在桥梁队,“大胆”这个字眼儿是“冒失”、“狂 安”、“鲁莽”以及“不负责任”等等东西的混合体,有时候“大胆” 和“冒险”又是一个意思。难怪连曾刚自己都害怕这个字眼儿了。 现在,再把话拉回来说。我从凌口大桥回来两天以后,罗队 长和曾工程师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开头是私人性质的, 结尾就变成纯粹工作性质一甚至可以说是政治性的谈话了。 许是因为很久没到罗队长家来过的缘故,曾刚一走进这个 房间,就觉得浑身紧张,好象小学生走进试场,‘又不能指望这次 考试顺利似的。 罗队长却和两年以前曾刚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一样,亲切而 自然地让曾刚坐在他自己的那把破转椅上,接着就去沏茶。 照例寒喧了一阵,照例闲扯扯队里的新闻以后,罗立正在不 知不觉中就把谈话引入了正题。 “不简单,不简单哪,”罗立正拖长声音说:“可是这几年咱们 祖国建设的成就,不能说不惊人哪。还记得咱们造木桥那时节 么?跟现在比比看。真是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一口气喝 下多半杯凉茶,又接着说:“当然,缺点也不是没有。有,有。就 拿你我说,以咱们这样水平负这样的责任,谁敢说没毛病?有, 有缺点…” 听他的语气,曾刚知道他这段话不过是引子,下面就该把这 些话否定掉了。先肯定后否定,一正一反,就分外有力量。果 然,罗立正的眼光更真挚感人了,语气也更师有力量: “可是,不管缺点怎么多,成绩还是最主要的。谁要是忽略 这一点,谁就得犯错误。就说造桥,就说咱们队上,有人批评说 我们浪费,成本超文,这都是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赔了 钱就是赔了钱。可是桥呢?桥还是造起来了!我们没来,这一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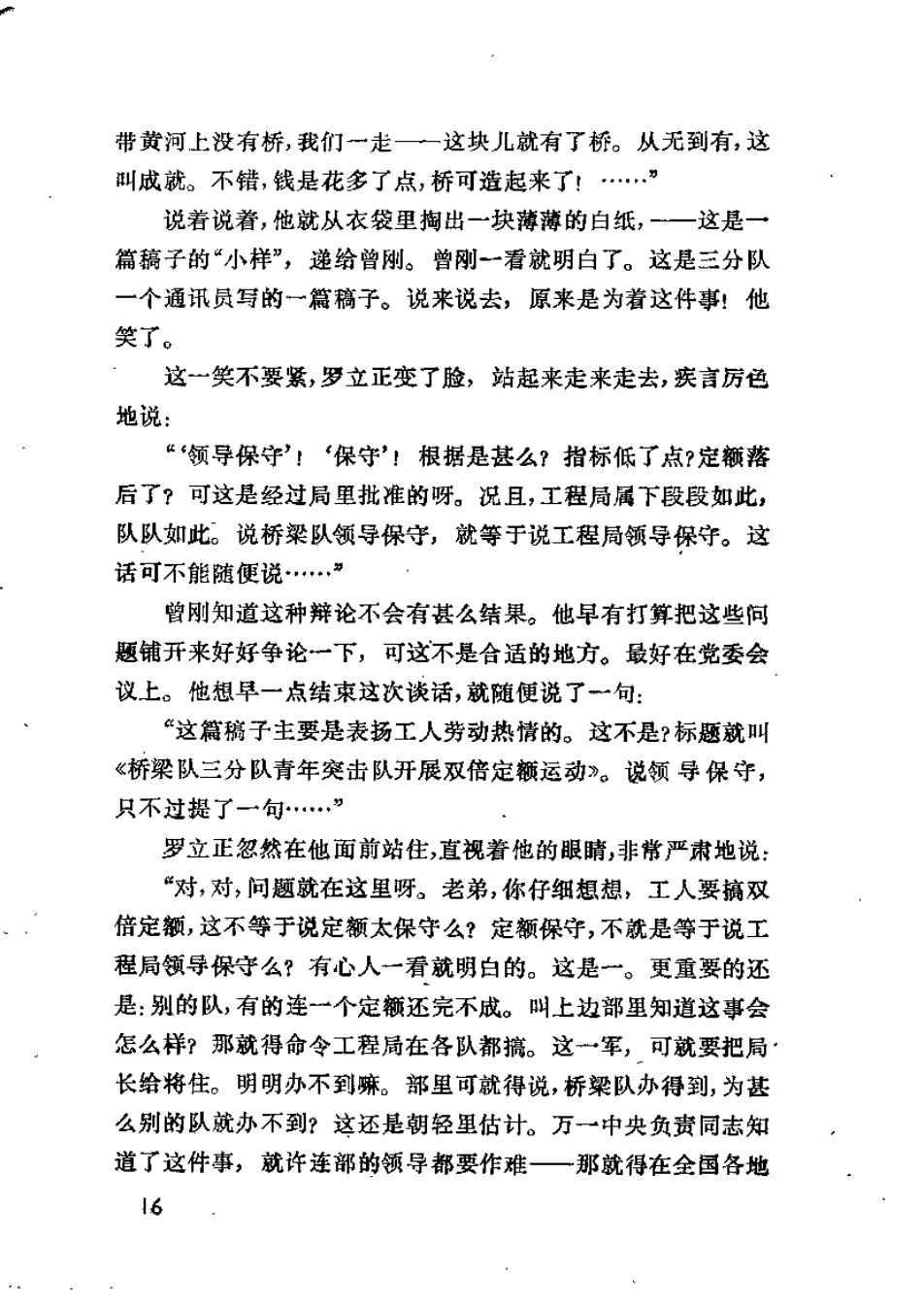
带黄河上没有桥,我们一走一这块儿就有了桥。从无到有,这 训成就。不错,钱是花多了点,桥可造起来了!” 说着说着,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薄薄的白纸,一这是一 篇稿子的“小样”,递给曾刚。曾刚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三分队 一个通讯员写的一篇稿子。说来说去,原来是为着这件事!他 笑了。 这一笑不要紧,罗立正变了脸,站起来走来走去,疾言厉色 地说: “领导保守’!‘保守!根据是甚么?指标低了点?定额落 后了?可这是经过局里批准的呀。况且,工程局属下段段如此, 队队如此。说桥梁队领导保守,就等于说工程局领导保守。这 话可不能随便说…” 曾刚知道这种辩论不会有甚么结果。他早有打算把这些问 题铺开来好好争论一下,可这不是合适的地方。最好在党委会 议上。他想早一点结束这次谈话,就随便说了一句: “这篇稿子主要是表扬工人劳动热情的。这不是?标题就叫 《桥梁队三分队青年突击队开展双倍定额运动》。说领导保守, 只不过提了一句…” 罗立正忽然在他面前站往,直视着他的眼晴,非常严肃地说: “对,对,问题就在这里呀。老弟,你仔细想想,工人要搞双 倍定额,这不等于说定额太保守么?定额保守,不就是等于说工 程局领导保守么?有心人一看就明白的。这是一。更重要的还 是:别的队,有的连一个定额还完不成。叫上边部里知道这事会 怎么样?那就得命令工程局在各以都搞。这一军,可就要把局· 长给将住。明明办不到嘛。部里可就得说,桥梁队办得到,为甚 么别的队就办不到?这还是朝轻里估计。万一中央负贵同志知 道了这件事,就许连部的领导都要作难一那就得在全国各地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