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相反。这几年采访中所见所闻,使我对于建筑工地的某些混 乱状态已经习以为常。而凌口大桥工地上,却是有条有理,秩序 并然。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闲人,地看不出一点忙乱。入,机 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看得出,甚至一个洗石子的地 方,一台混凝七搅拌机放在哪里,都是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才安 排下来的。一般工地上常见的恼入的“小搬运”,这里几乎没有。 我问过不少普通工人,都不仅知道自已今天、明天的任务是甚 么,而且了解本小组小队的任务和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在哪 里。所以,也就没有工地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我在哪儿?”的笑话 了。分队的计划,每月都超额完戒。 这一切,看来都那么稳当,和“冒险”是一点边儿也沾不上 的。而桥梁队的其它分队,精形却正好相反:经常是月初窝工, 月底加班加点,有的竟同时二者并存;每年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儿 拖到最后一个月完成,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从来无人说这种杂 乱无章、盲日赶工、大量发生人身、质量事故是冒险,反而觉得那 里一切都很正常,很稳当。 起初,我主要是从工作方法上去考虑了这种差别。我和曾 工程师一起一连坐了两个夜晚,研究和总结他的经验。他重视 计划工作,每次编计划都亲自动手。这样,每月、每句队里工作中 的各种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就都通过他一次脑筋,随时记得。一 切具体措施,都是在这个金盘考虑下作出的。和一般工程技术 人员不同,他亲自掌管全队的合理化建议工作,工人提出甚么意 见,他随时可以根据当前的和长远的需要及时作出结论,不必经 过繁复的登记、审查、批准等手续…如此等等。 但是谈了两个晚上,我忽然觉得这不是我需要了解的主要 之点。这儿年,速工组织上的经验总结得还算少么?但是在有 些人手下,再成功的经验也行不通。而一到把生产搞到一片混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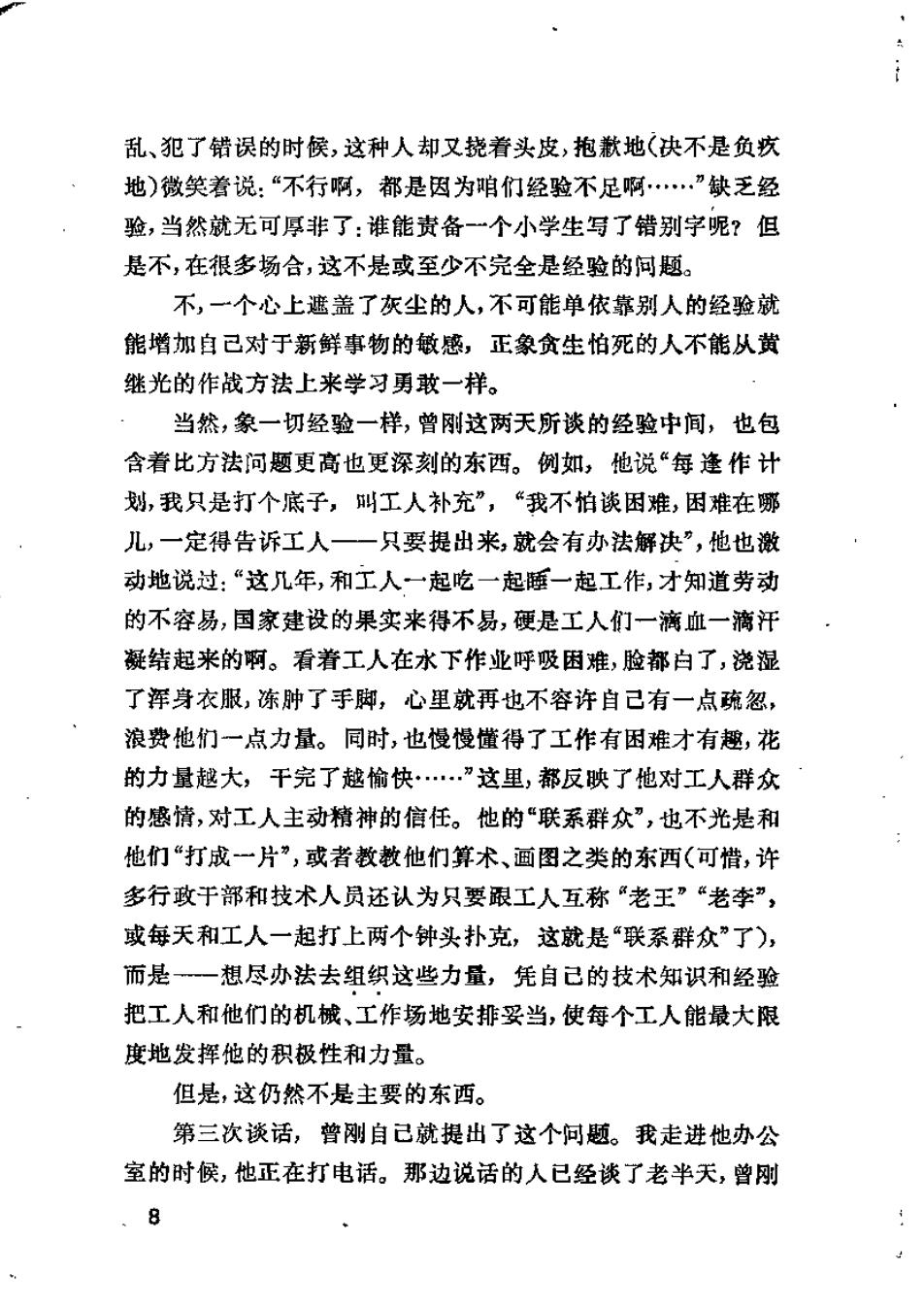
乱、犯了错误的时候,这种人却又挠着头皮,抱歉地(决不是负疚 地)微笑着说:“不行啊,都是因为咱们经验不足啊…”缺乏经 验,当然就无可厚非了:谁能责备一个小学生写了错别字呢?但 是不,在很多场合,这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经验的问题。 不,一“个心上遮盖了灰尘的人,不可能单依靠别人的经验就 能增加自已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正象贪生怕死的人不能从黄 继光的作战方法上来学习勇敢一样。 当然,象一切经验一样,曾刚这两天所谈的经验中间,也包 含着比方法问题更高也更深刻的东西。例如,他说“每逢作计 刘,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补充”,“我不怕谈困难,困难在哪 儿,一定得告诉工人一一只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解决”,他也激 动地说过:“这几年,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才知道劳动 的不容易,国家建设的果实来得不易,硬是工人们一滴血一滴汗 凝结起来的啊。看着工人在水下作业呼吸图难,脸都白了,浇湿 了浑身衣服,冻肿了手脚,心里就再也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疏忽, 浪费他们一点力量。同时,也慢慢懂得了工作有困推才有趣,花 的力量越大,干完了越愉快”这里,都反映了他对工人群众 的感情,对工人主动精神的信任。他的“联系群众”,也不光是和 他们“打成一片”,或者教教他们算术、画图之类的东西(可惜,许 多行政于部和技术人员还认为只要跟工人互称老王”“老李”, 或每天和工人一起打上两个钟头扑克,这就是“联系群众”了), 而是一想尽办法去组织这些力量,凭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 把工人和他们的机械、工作场地安排妥当,使每个工人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力量。 但是,这仍然不是主要的东西。 第三次谈话,普刚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走进他办公 室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那边说话的人已经谈了老半天,曾刚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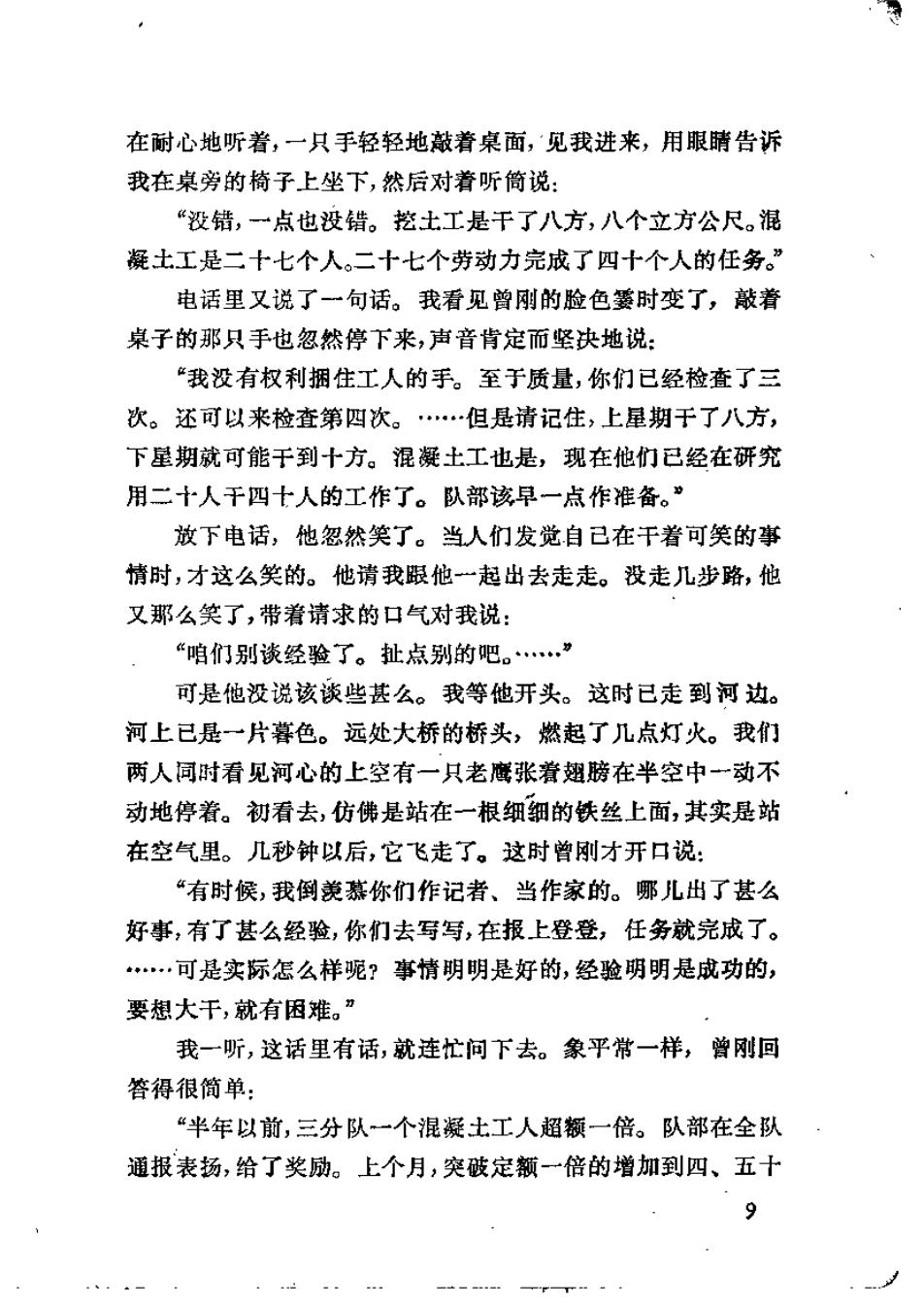
在耐心地听着,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面,‘见我进来,用眼睛告诉 我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对着听筒说: “没错,一点也没错。挖土工是干了八方,八个立方公尺。混 凝土工是二十七个人。二十七个劳动力完成了四十个人的任务。” 电话里又说了一句话。我看见曾刚的脸色霎时变了,敲着 桌子的那只手也忽然停下来,声音肯定而坚决地说: 我没有权利捆住工人的手。至于质量,你们已经检查了三 次。还可以来检查第四次。…但是请记住,上星期于了八方, 下星期就可能干到十方。混凝土工也是,现在他们已经在研究 用二十人干四十人的工作了。队部该早一点作准备。” 放下电话,他忽然笑了。当人们发觉自已在干着可笑的事 情时,才这么笑的。他请我跟他一起出去走走。没走几步路,他 又那么笑了,带着请求的口气对我说: “咱们别谈经验了。扯点别的吧。…” 可是他没说该谈些甚么。我等他开头。这时已走到河边。 河上已是一片暮色。远处大桥的桥头,燃起了几点灯火。我们 两人同时看见河心的上空有一只老鹰张着翅膀在半空中一动不 动地停着。初看去,仿佛是站在一根细细的铁丝上面,其实是站 在空气里。几秒钟以后,它飞走了。这时曾刚才开口说: “有时候,我倒美慕你们作记者、当作家的。哪儿出了甚么 好事,有了甚么经验,你们去写写,在报上登登,任务就完成了。 …可是实际怎么样呢?事情明明是好的,经验明明是成功的, 要想大干,就有困雄。” 我一听,这话里有话,就连忙问下去。象平常一样,曾刚回 答得很简单: “半年以前,三分队一个混凝土工人超额一倍。队部在全队 通报表扬,给了奖励。上个月,突破定额一倍的增加到四、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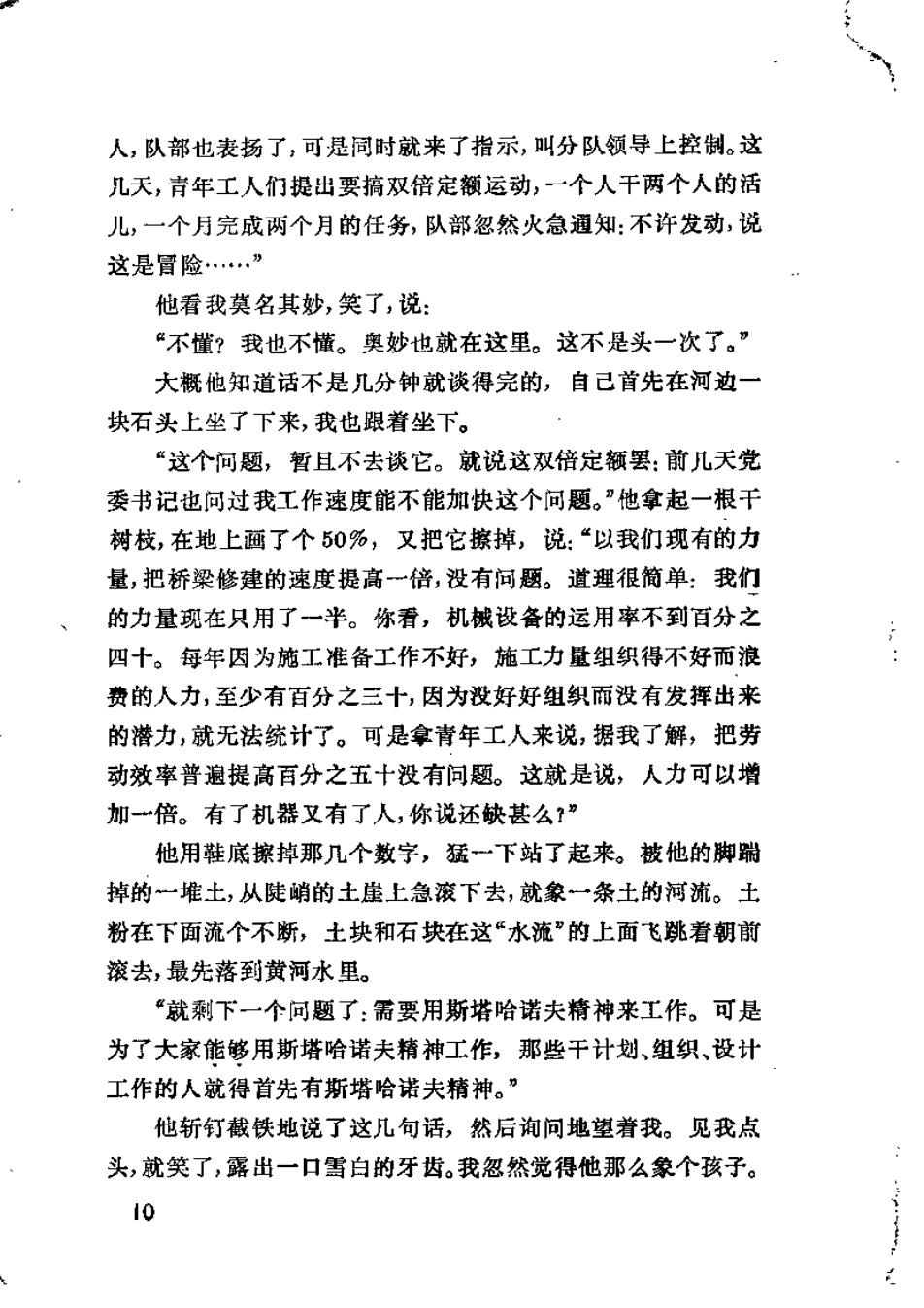
人,队部也表扬了,可是同时就来了指示,叫分队领导上控制。这 儿天,青年工人们提出要搞双倍定额运动,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儿,一个月完成两个月的任务,队部忽然火急通知:不许发动,说 这是冒险…” 他看我莫名其妙,笑了,说: “不懂?我也不懂。奥妙也就在这里。这不是头一次了。” 大概他知道话不是几分钟就谈得完的,自己首先在河边一 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也跟着坐下。 “这个问题,暂且不去谈它。就说这双倍定额罢:前儿天党 委书记也问过我工作速度能不能加快这个问题。”他拿起一根干 树枝,在地上画了个50%,又把它擦掉,说:“以我们现有的力 量,把桥梁修建的速度提高一倍,没有问题。道理很简单:我门 的力量现在只用了一半。你看,机械设备的运用率不到百分之 四十。每年因为施工准备工作不好,施工力量组织得不好而浪 费的人力,至少有百分之三十,因为没好好组织而没有发挥出来 的潜力,就无法统计了。可是拿青年工人来说,据我了解,把劳 动效率普遍提高百分之五十没有问题。这就是说,人力可以增 加-一倍。有了机器又有了人,你说还缺甚么?” 他用鞋底擦掉那几个数字,猛一下站了起来。被他的脚踹 掉的一堆土,从陡哨的土崖上急滚下去,就象一条土的河流。土 粉在下面流个不断,土块和石块在这“水流”的上面飞跳着朝前 滚去,最先落到黄河水里。 “就剩下一个问题了:需要用斯塔哈诺夫精神来工作。可是 为了大家能够用斯塔哈诺夫精神工作,那些干计划、组织、设计 工作的人就得首先有斯塔哈诺夫精神。” 他斩钉截铁地说了这几句话,然后询问地望着我。见我点 头,就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我忽然觉得他那么象个孩子。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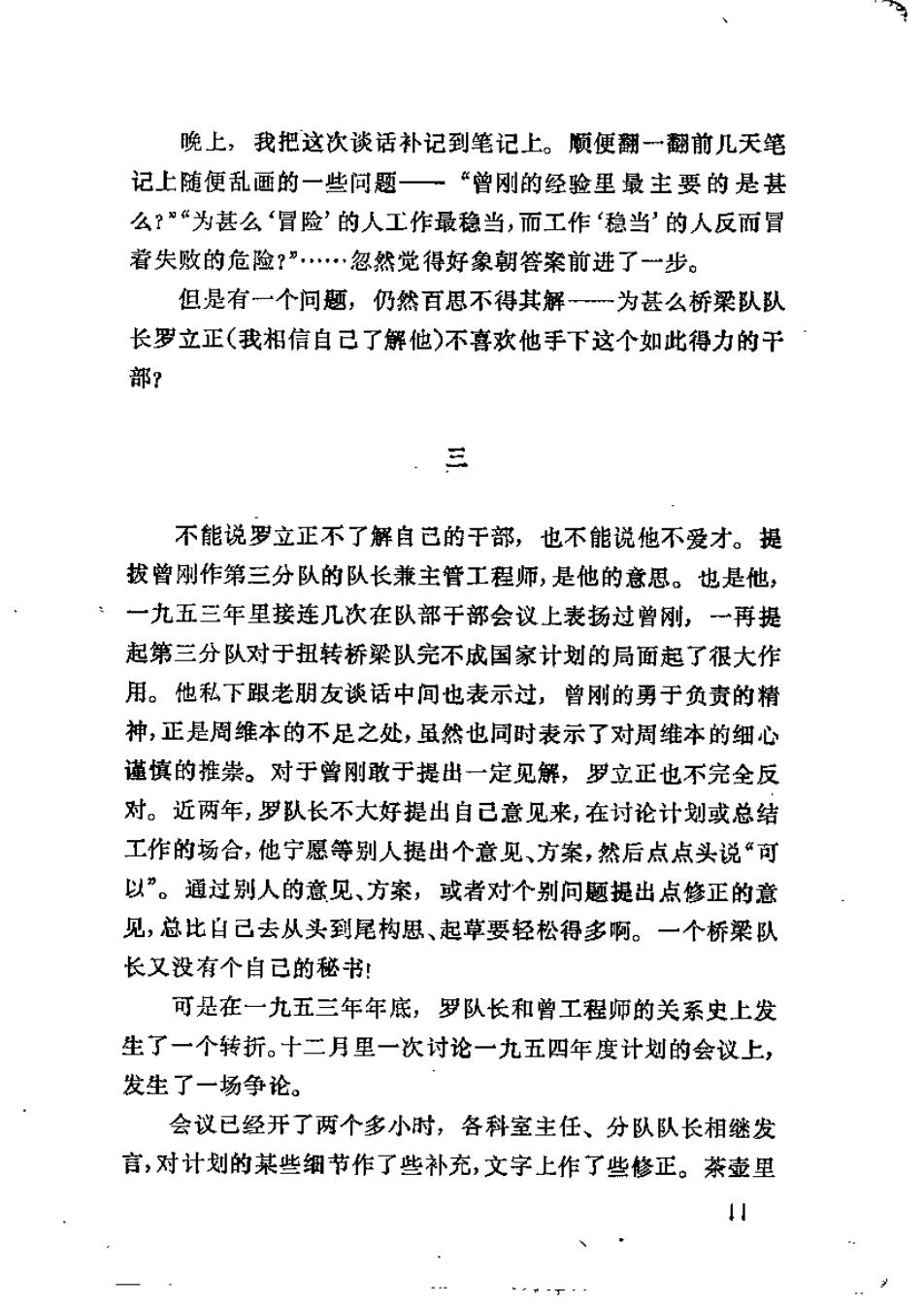
晚上,我把这次谈话补记到笔记上。顺便翻一翻前儿天笔 记上随便乱画的一些问题一“曾刚的经验里最主要的是甚 么?如“为甚么冒险’的人工作最稳当,而工作‘稳当'的人反而冒 着失败的危险?”…忽然觉得好象朝答案前进了一步。 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一为甚么桥梁队队 长罗立正(我相信自己了解他)不喜欢他手下这个如此得力的干 部? 三 不能说罗立正不了解自已的干部,也不能说他不爱才。提 拔曾刚作第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是他的意思。也是他, 一九五三年里接连几次在队部干部会议上表扬过曾刚,一再提 起第三分队对于扭转桥梁队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局面起了很大作 用。他私下跟老朋友谈话中间也表示过,曾刚的勇于负责的精 神,正是周维本的不足之处,虽然也同时表示了对周维本的细心 谨慎的推崇。对于曾刚敢于提出一定见解,罗立正也不完全反 对。近两年,罗队长不大好提出自已意见来,在讨论计划或总结 工作的场合,他宁愿等别人提出个意见、方案,然后点点头说“可 以”。通过别人的意见、方案,或者对个别问题提出点修正的意 见,总比自己去从头到尾构思、起草要轻松得多啊。一个桥梁队 长又没有个自己的秘书! 可是在一九五三年年底,罗队长和曾工程师的关系史上发 生了一个转折。十二月里一次讨论一九五四年度计划的会议上, 发生了一场争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各科室主任、分队队长相继发 言,对计划的某些细节作了些补充,文字上作了些修正。茶壶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