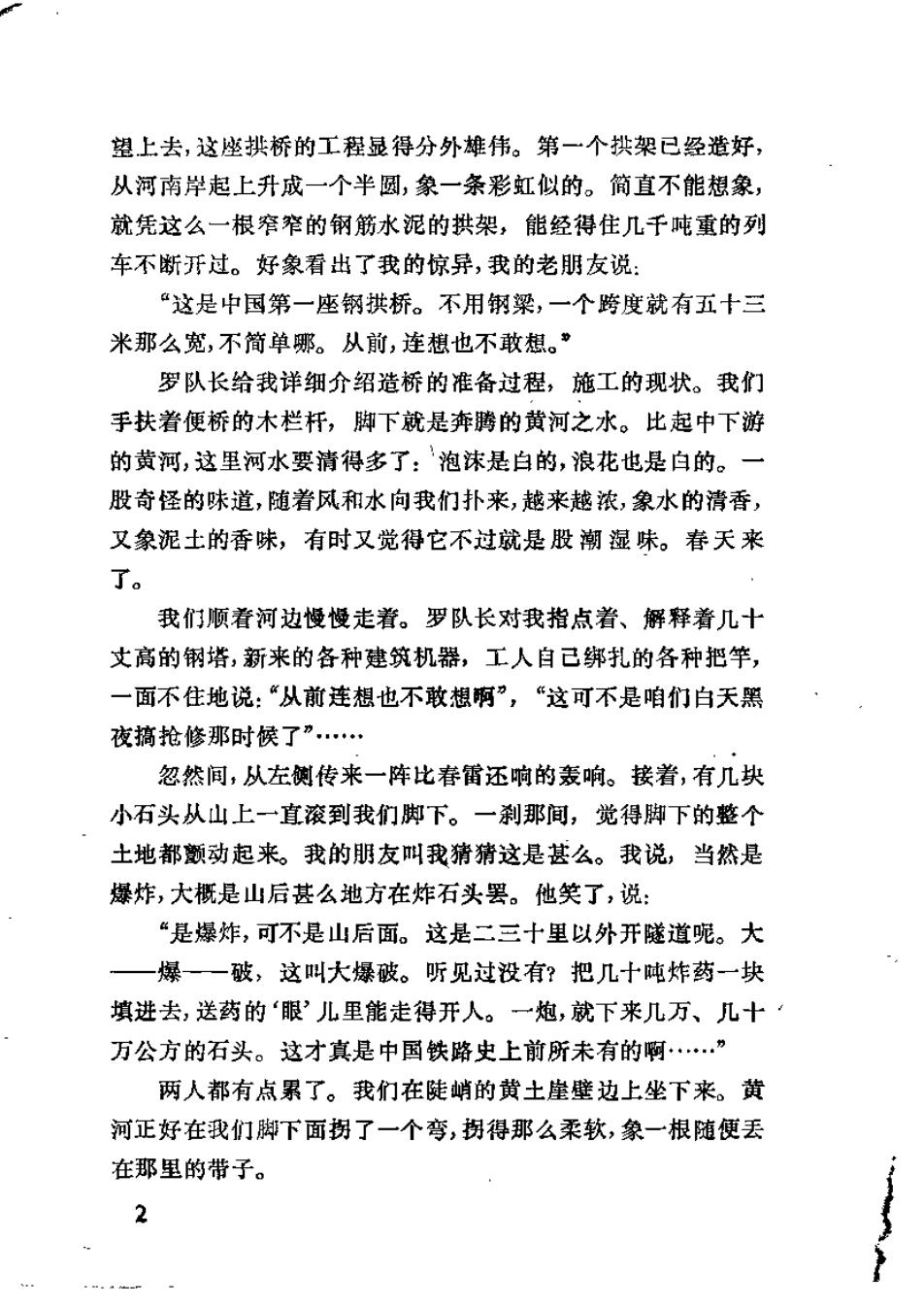
望上去,这座拱桥的工程显得分外雄伟。第一个拱架已经造好, 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圆,象一条彩虹似的。简直不能想象, 就凭这么一根窄窄的钢筋水泥的拱架,能经得住几千吨重的列 车不断开过。好象看出了我的惊异,我的老朋友说: “这是中国第一座钢拱桥。不用钢梁,一个跨度就有五十三 米那么宽,不简单哪。从前,连想也不敢想。” 罗队长给我详细介绍造桥的准备过程,施工的现状。我们 手扶着便桥的木栏杆,脚下就是奔腾的黄河之水。比起中下游 的黄河,这里河水要清得多了:'泡沫是白的,浪花也是白的。一 股奇怪的味道,随着风和水向我们扑来,越来越浓,象水的清香, 又象泥土的香味,有时又觉得它不过就是股潮湿味。春天来 了。 我们顺着河边慢慢走着。罗队长对我指点着、解释着几十 丈高的钢塔,新来的各种建筑机器,工人自己绑的各种把竿, 一面不住地说:“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响”,“这可不是咱们白天黑 夜搞抢修那时候了”… 忽然间,从左侧传来一阵比春雷还响的轰响。接着,有几块 小石头从山上一直滚到我们脚下。一刹那间,觉得脚下的整个 土地都颤动起来。我的朋友叫我猜猜这是甚么。我说,当然是 爆炸,大概是山后甚么地方在炸石头罢。他笑了,说: “是爆炸,可不是山后面。这是二三十里以外开隧道晚。大 一爆一一破,这叫大爆破。听见过没有?把几十吨炸药一块 填进去,送药的‘眼?儿里能走得开人。一炮,就下来几万、几十· 万公方的石头。这才真是中国铁路史上前所未有的啊…” 两人都有点累了。我们在陡峭的黄土崖壁边上坐下来。黄 河正好在我们脚下面拐了一个弯,拐得那么柔软,象一根随便丢 在那里的带子。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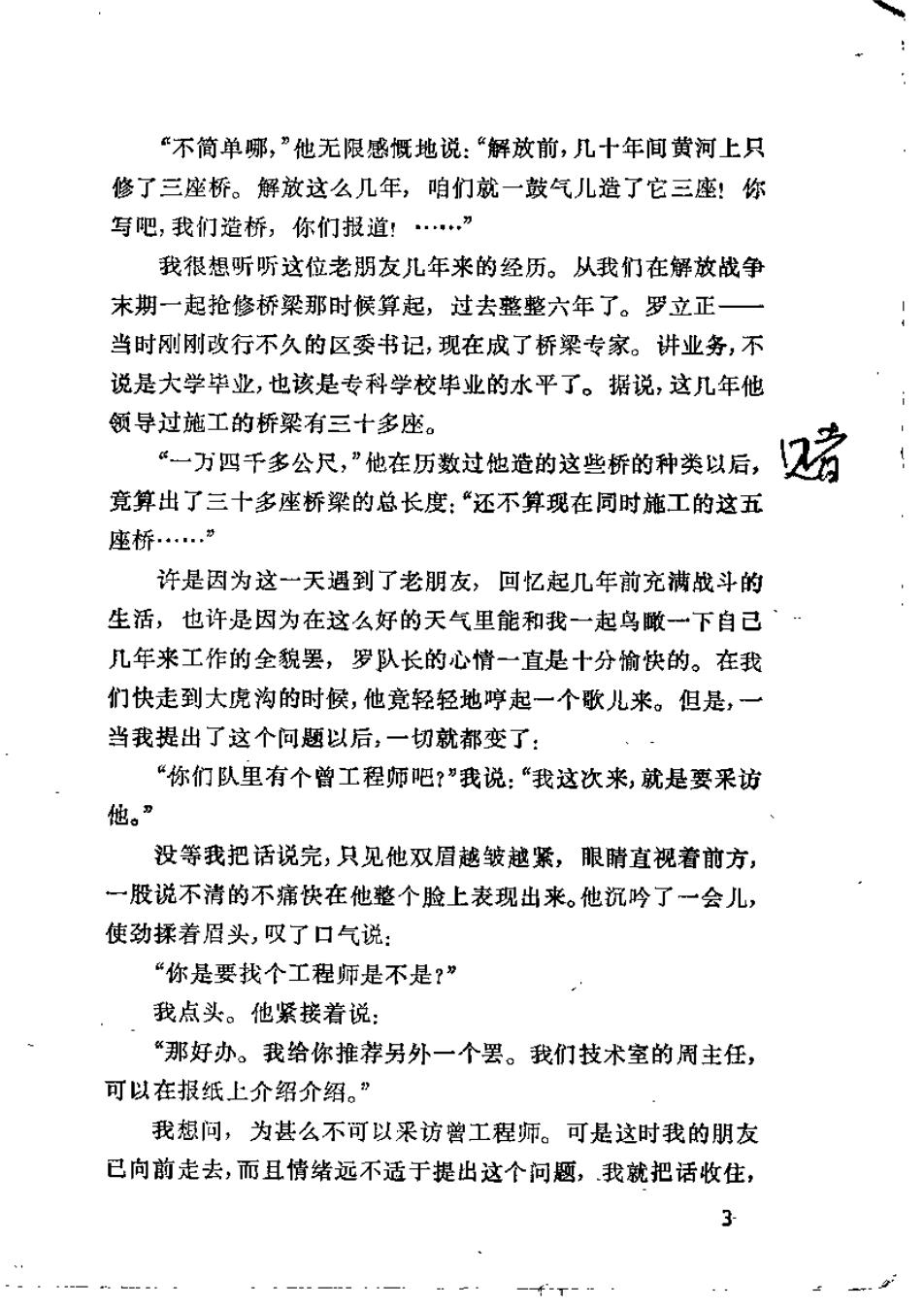
“不简单哪,”他无限感慨地说:“解放前,几十年间黄河上只 修了三座桥。解放这么几年,咱们就一鼓气儿造了它三座!你 写吧,我们造桥,你们报道!” 我很想听听这位老朋友儿年来的经历。从我们在解放战争 末期一起抢修桥梁那时候算起,过去整整六年了。罗立正一 当时刚刚改行不久的区委书记,现在成了桥梁专家。讲业务,不 说是大学毕业,也该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了。据说,这几年他 领导过施工的桥梁有三十多座。 “一万四千多公尺,”他在历数过他造的这些桥的种类以后, 竟算出了三十多座桥梁的总长度:“还不算现在同时施工的这五 座桥” 许是因为这一天遇到了老朋友,回忆起几年前充满战斗的 生活,也许是因为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能和我一起鸟瞰一下自已 、… 几年来工作的全貌罢,罗以长的心情一直是十分愉快的。在我 们快走到大虎沟的时候,他竟轻轻地哼起一个歌儿来。但是,一 当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一切就都变了: “你们队里有个曾工程师吧?”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采访 他。” 没等我把话说完,只见他双眉越皱越紧,限睛直视着前方, 一股说不清的不痛快在他整个脸上表现出来。他沉吟了一会儿, 使劲揉着眉头,叹了口气说: “你是要找个工程师是不是?” 我点头。他紧接着说: “那好办。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罢。我们技术室的周主任, 可以在报纸上介绍介绍。” 我想问,为甚么不可以采访曾工程师。可是这时我的朋友 已向前走去,而且情绪远不适于提出这个河题,我就把话收住,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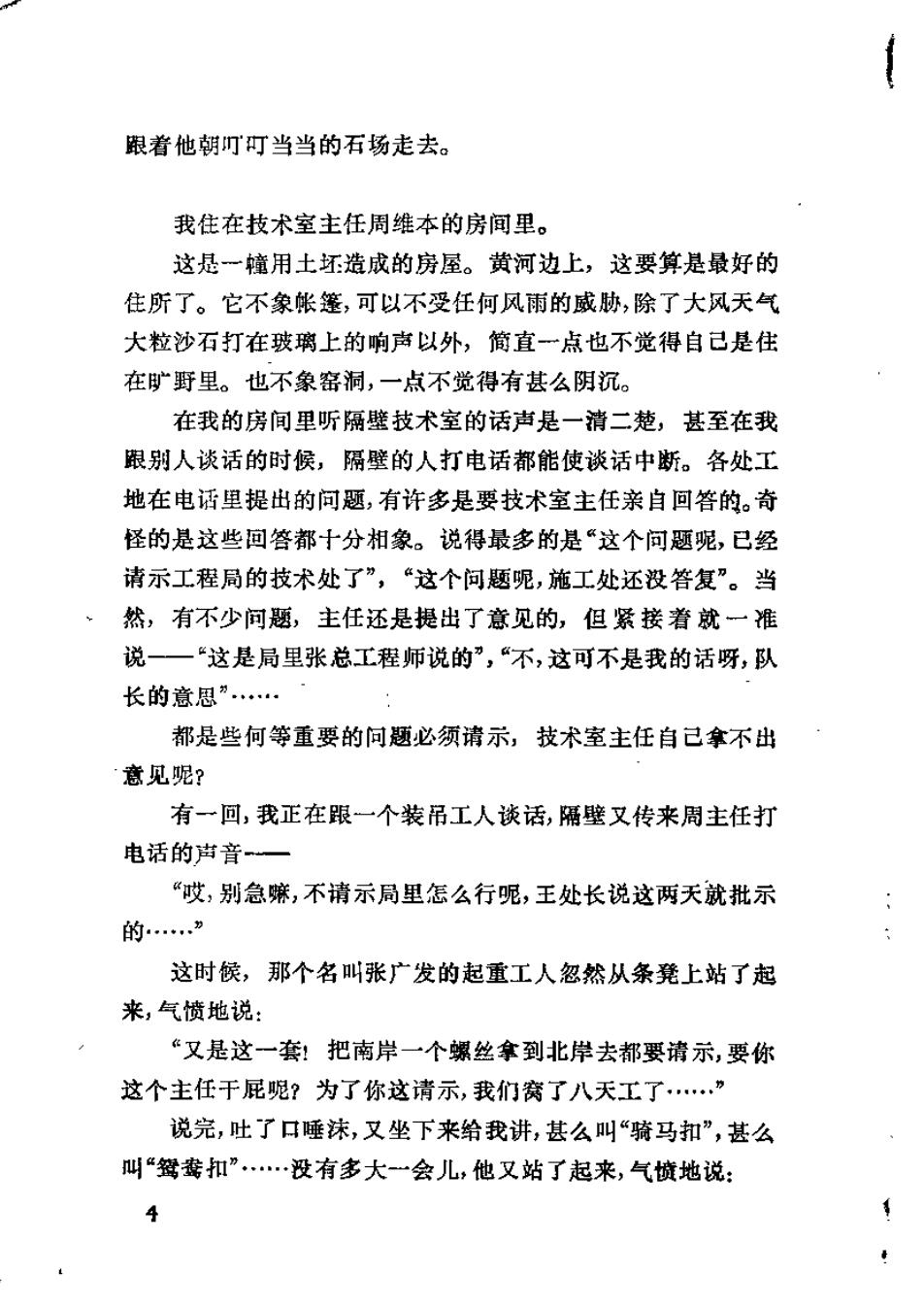
跟着他朝门灯当当的石场走去。 我住在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的房闻里。 这是一幢用土还造成的房屋。黄河边上,这要算是最好的 住所了。它不象帐篷,可以不受任何风雨的威胁,除了大风天气 大粒沙石打在玻璃上的响声以外,简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住 在旷野里。也不象窑洞,一点不党得有甚么阴沉。 在我的房间里听隔壁技术室的话声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 跟别人谈话的时候,隔壁的人打电话都能使谈话中断。各处工 地在电话望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要技术室主任亲自回答的。奇 怪的是这些回答都十分相象。说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呢,已经 请示工程局的技术处了”,“这个问题呢,施工处还没答复”。当 ·然,有不少问题,主任还是提出了意见的,但紧接着就一准 说一一“这是局里张总工程师说的”,“不,这可不是我的话呀,队 长的意思”… 都是些何等重要的问题必须请示,技术室主任自己拿不出 意见呢? 有一回,我正在跟一个装吊工人谈话,隔壁又传来周主任打 电话的声音一 “哎,别急嘛,不请示局里怎么行呢,王处长说这两天就批示 的” .: 这时候,那个名叫张广发的起重工人忽然从条凳上站了起 来,气愤地说: “又是这一套!把南岸一个螺丝拿到北岸去都要请示,要你 这个主任于屁呢?为了你这请示,我们窝了八天工了” 说完,吐了口唾沫,又坐下来给我讲,甚么叫“骑马扣”,甚么 叫“鸳鸯扣”…没有多大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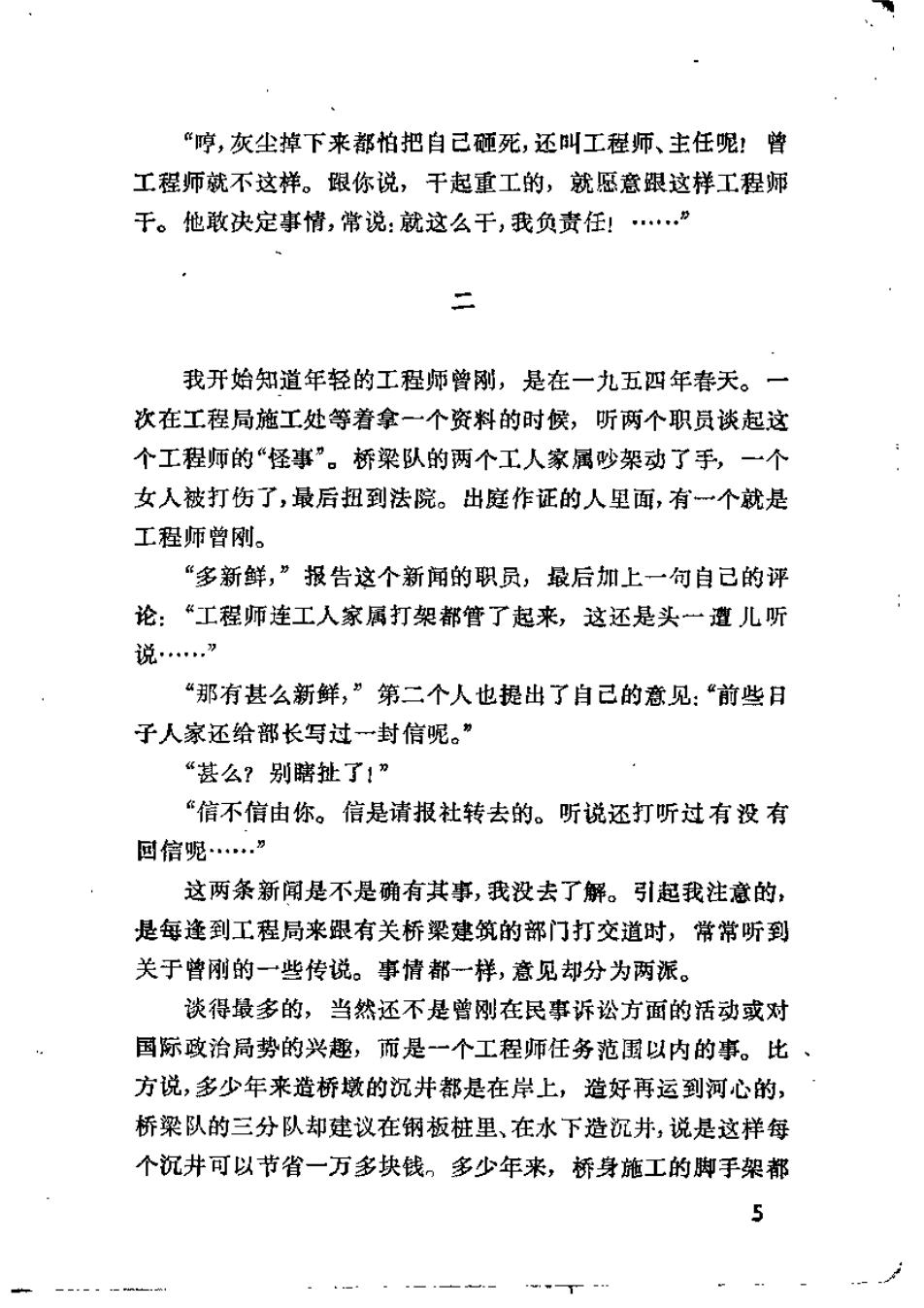
“哼,灰尘掉下来都怕把自己硬死,还训工程师、主任呢!曾 工程师就不这样。跟你说,干起重工的,就意跟这样工程师 于。他敢决定事情,常说:就这么干,我负责任!…” 我开始知道年轻的工程师曾刚,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一 次在工程局施工处等着拿一个资料的时候,听两个职员谈起这 个工程师的“怪事”。桥梁队的两个工人家属吵架动了手,一个 女人被打伤了,最后扭到法院。出庭作证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 工程师曾刚。 “多新鲜,”报告这个新闻的职员,最后加上一句自己的评 论:“工程师连工人家属打架都管了起来,这还是头一遭儿听 说….” “那有甚么新鲜,”第二个人也提出了自已的意见:“前些日 子人家还给部长写过一封信呢。” “甚么?别瞎批了1” “信不信由你。信是请报社转去的。听说还打听过有没有 回信呢.” 这两条新闻是不是确有其事,我没去了解。引起我注意的, 是每逢到工程局来跟有关桥梁建筑的部门打交道时,常常听到 关于曾刚的一些传说。事情都一样,意见却分为两派。 谈得最多的,当然还不是曾刚在民事诉讼方面的活动或对 国际政治局势的兴趣,而是一个工程师任务范围以内的事。比 、 方说,多少年来造桥墩的沉井都是在岸上,造好再运到河心的, 桥梁队的三分队却建议在钢板柱里、在水下造沉井,说是这样每 个沉井可以节省一万多块钱。多少年来,桥身施工的脚手架都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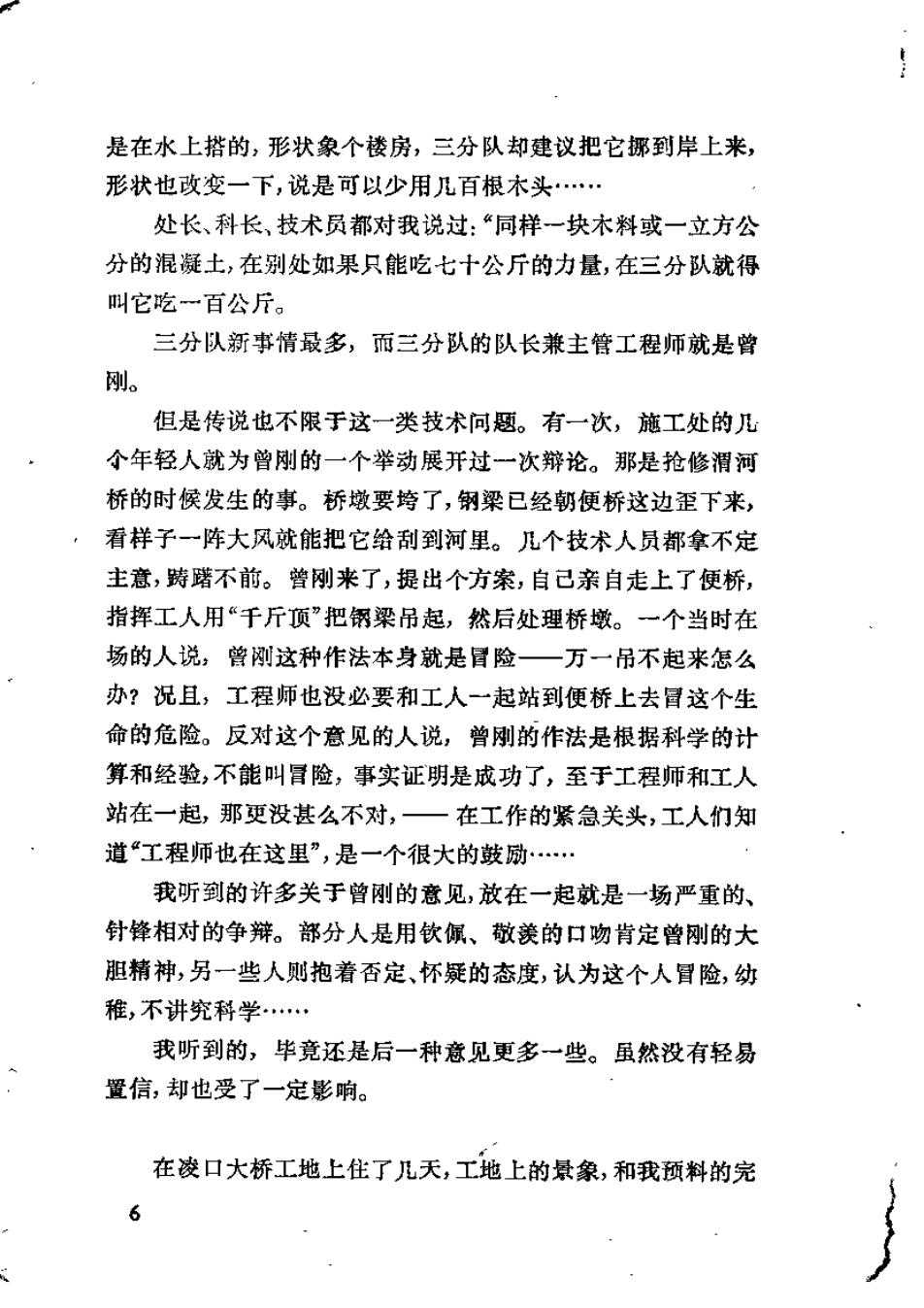
是在水上搭的,形状象个楼房,三分队却建议把它挪到岸上来, 形状也改变一下,说是可以少用几百根木头… 处长、科长、技术员都对我说过:“同样一块木料或一立方公 分的混凝土,在别处如果只能吃七十公厅的力量,在三分队就得 叫它吃一百公斤。 三分队新事情最多,而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就是曾 刚。 但是传说也不限于这一类技术问题。有一次,施工处的 个年轻人就为曾刚的一个举动展开过一次辩论。那是抢修渭河 桥的时候发生的事。桥嫩要垮了,钢梁已经朝便桥这边歪下来, t 看样子一阵大风就能把它给刮到河里。几个技术人员都拿不定 主意,踌躇不前。曾刚来了,提出个方案,自己亲自走上了便桥, 指挥工人用“千斤顶”把钢梁吊起,然后处理桥墩。一个当时在 场的人说,曾刚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冒险一万一吊不起来怎么 办?况且,工程师也没必要和工人一起站到便桥上去冒这个生 命的危险。反对这个意见的人说,曾刚的作法是根据科学的计 算和经验,不能叫冒险,事实证明是成功了,至于工程师和工人 站在一起,那更没甚么不对,一在工作的紧急关头,工人们知 道“工程师也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听到的许多关于曾刚的意见,放在一起就是一场严重的、 针锋相对的争辩。部分人是用钦佩、敬羡的口吻肯定曾刚的大 胆精神,另一些人则抱着否定、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个人冒险,幼 稚,不讲究科学… 我听到的,毕竟还是后一种意见更多一些。虽然没有轻易 置信,却也受了一定影响。 在凌口大桥工地上住了天,工地上的景象,和我预料的完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