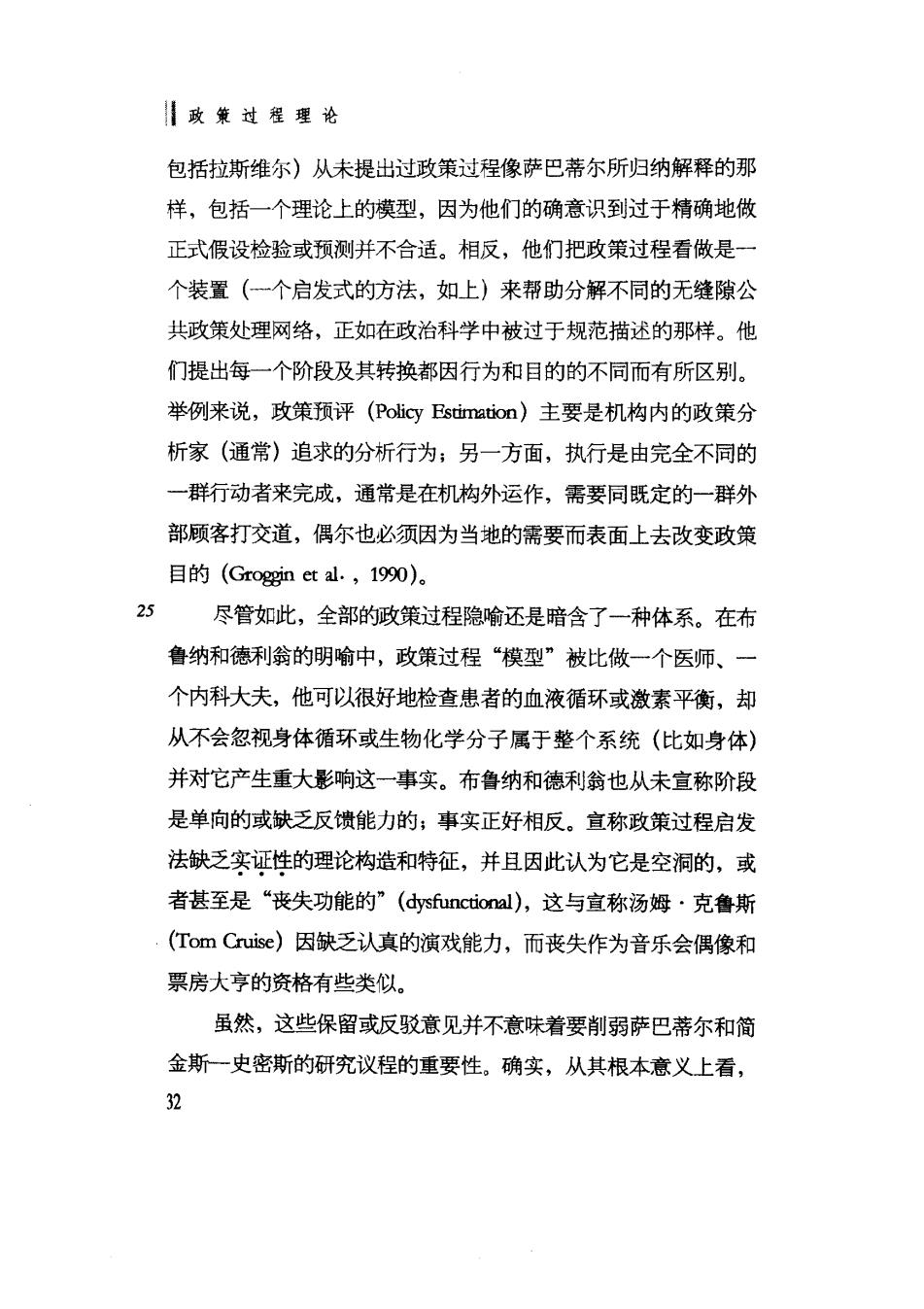
‖政策过程理论 包括拉斯维尔)从未提出过政策过程像萨巴蒂尔所归纳解释的那 样,包括一个理论上的模型,因为他们的确意识到过于精确地做 正式假设检验或预测并不合适。相反,他们把政策过程看做是一 个装置(一个启发式的方法,如上)来帮助分解不同的无缝隙公 共政策处理网络,正如在政治科学中被过于规范描述的那样。他 们提出每一个阶段及其转换都因行为和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举例来说,攻策预评(Policy Estimation)主要是机构内的政策分 析家(通常)追求的分析行为;另一方面,执行是由完全不同的 一群行动者来完成,通常是在机构外运作,需要同既定的一群外 部顾客打交道,偶尔也必须因为当地的需要而表面上去改变政策 目的(Groggin et al.,1990)。 25 尽管如此,全部的政策过程隐喻还是暗含了一种体系。在布 鲁纳和德利翁的明喻中,政策过程“模型”被比做一个医师、一 个内科大夫,他可以很好地检查患者的血液循环或激素平衡,却 从不会忽视身体循环或生物化学分子属于整个系统(比如身体) 并对它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实。布鲁纳和德利翁也从未宣称阶段 是单向的或缺乏反馈能力的;事实正好相反。宣称政策过程启发 法缺乏实证性的理论构造和特征,并且因此认为它是空洞的,或 者甚至是“丧失功能的”(dysfunctional),这与宣称汤姆·克鲁斯 (Tom Cruise)因缺乏认真的演戏能力,而丧失作为音乐会偶像和 票房大亨的资格有些类似。 虽然,这些保留或反驳意见并不意味着要削弱萨巴蒂尔和简 金斯一史密斯的研究议程的重要性。确实,从其根本意义上看,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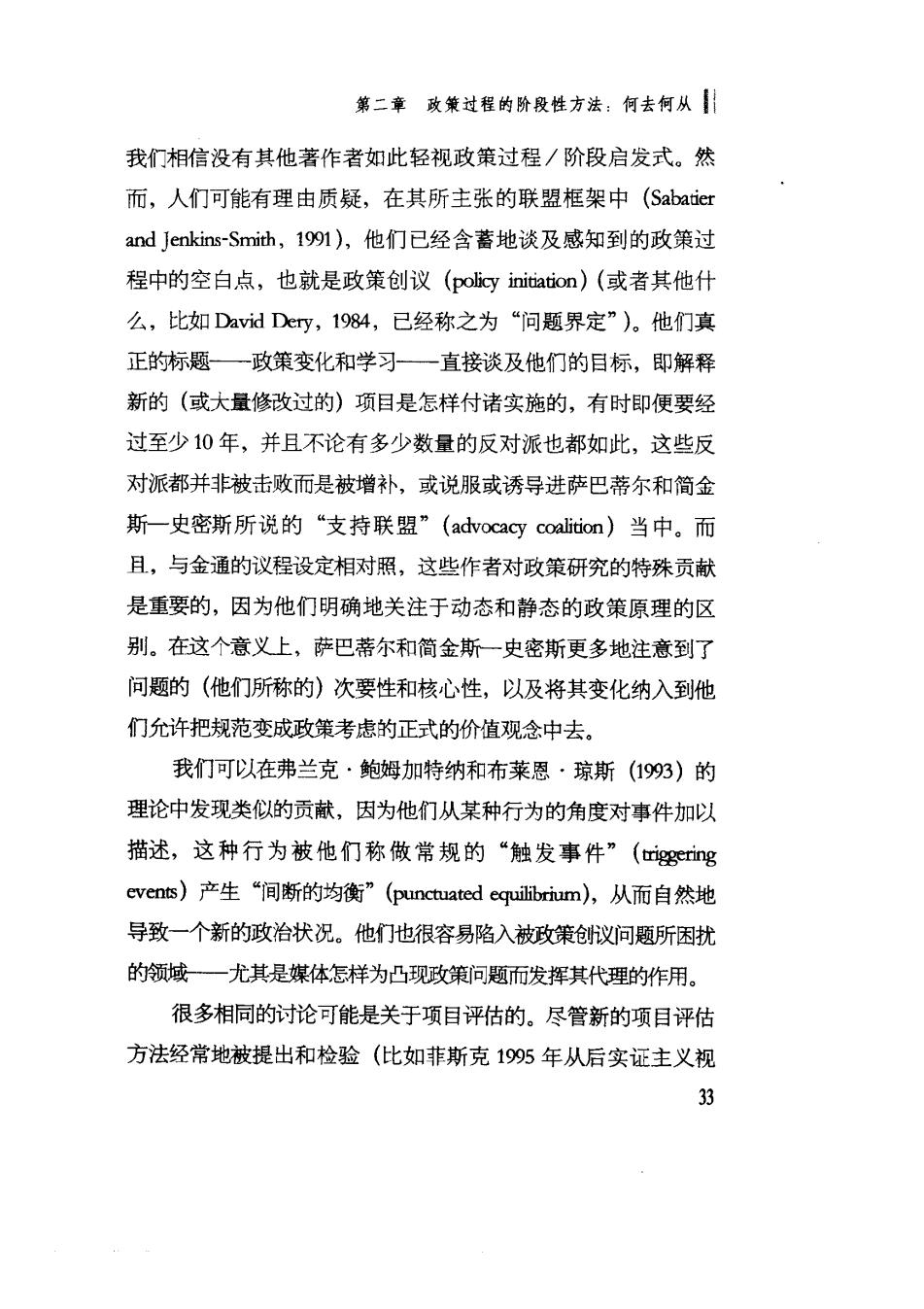
第二章政策过程的阶段性方法:何去何从【‖ 我们相信没有其他著作者如此轻视政策过程/阶段启发式。然 而,人们可能有理由质疑,在其所主张的联盟框架中(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1991),他们已经含蓄地谈及感知到的政策过 程中的空白点,也就是政策创议(policy initiation)(或者其他什 么,比如David Dery,1984,已经称之为“问题界定”)。他们真 正的标题—一政策变化和学习一直接谈及他们的目标,即解释 新的(或大量修改过的)项目是怎样付诸实施的,有时即便要经 过至少10年,并且不论有多少数量的反对派也都如此,这些反 对派都并非被击败而是被增补,或说服或诱导进萨巴蒂尔和简金 斯一史密斯所说的“支持联盟”(advocacy coalition)当中。而 且,与金通的议程设定相对照,这些作者对政策研究的特殊贡献 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明确地关注于动态和静态的政策原理的区 别。在这个意义上,萨巴蒂尔和简金斯一史密斯更多地注意到了 问题的(他们所称的)次要性和核心性,以及将其变化纳入到他 们允许把规范变成政策考虑的正式的价值观念中去。 我们可以在弗兰克·鲍姆加特纳和布莱恩·琼斯(13)的 理论中发现类似的贡献,因为他们从某种行为的角度对事件加以 描述,这种行为被他们称做常规的“触发事件”(triggering events)产生“间断的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从而自然地 导致一个新的政治状况。他们也很容易陷入被政策创议问题所困扰 的领域一尤其是媒体怎样为凸现政策问题而发挥其代理的作用。 很多相同的讨论可能是关于项目评估的。尽管新的项目评估 方法经常地被提出和检验(比如菲斯克1995年从后实证主义视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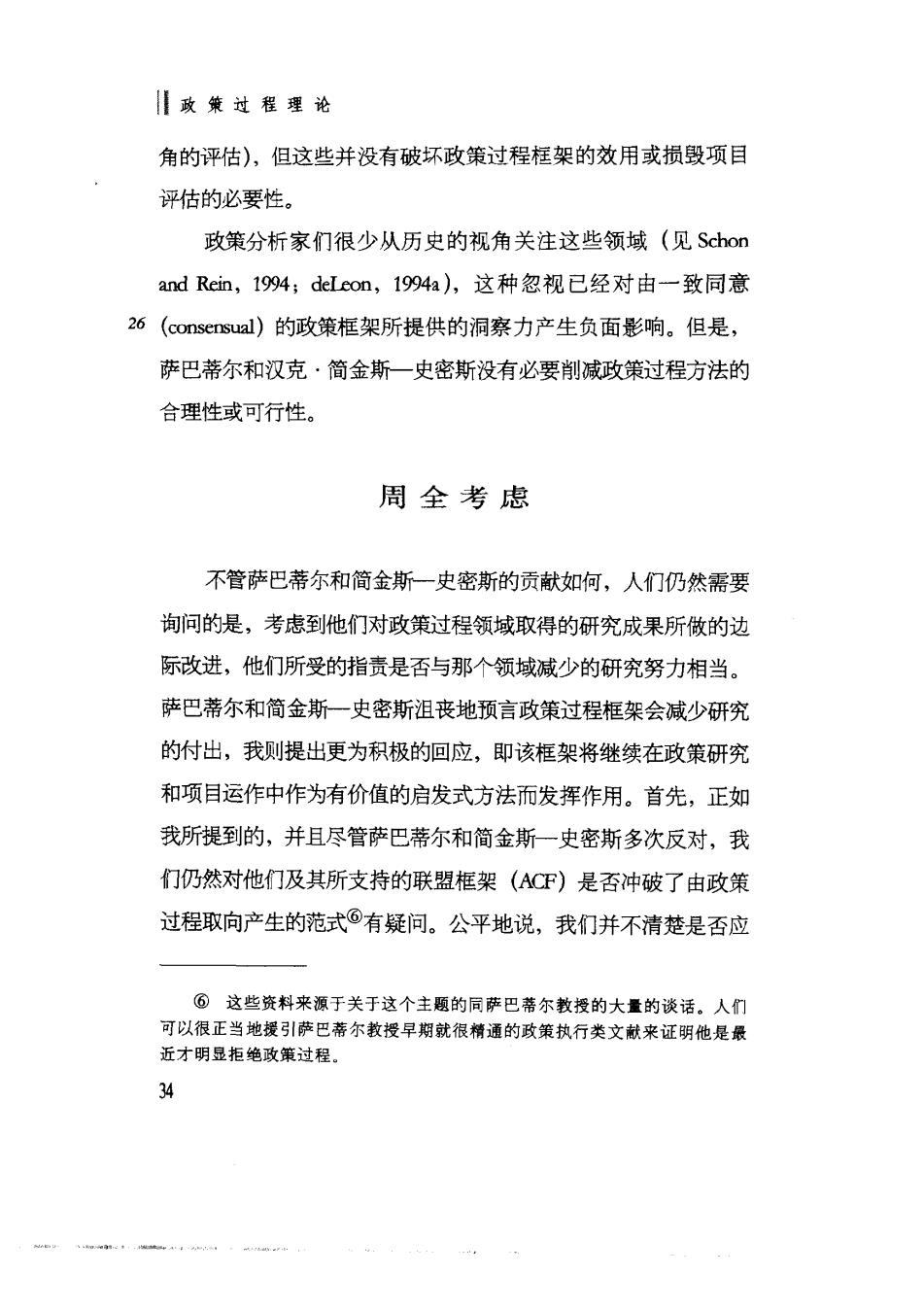
政策过程理论 角的评估),但这些并没有破坏政策过程框架的效用或损毁项目 评估的必要性。 政策分析家们很少从历史的视角关注这些领域(见Shon and Rein,1994:deLeon,1994a),这种忽视已经对由-致同意 26(consensual)的政策框架所提供的洞察力产生负面影响。但是, 萨巴蒂尔和汉克·简金斯一史密斯没有必要削减政策过程方法的 合理性或可行性。 周全考虑 不管萨巴蒂尔和简金斯一史密斯的贡献如何,人们仍然需要 询问的是,考虑到他们对政策过程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所做的边 际改进,他们所受的指责是否与那个领域减少的研究努力相当。 萨巴蒂尔和简金斯一史密斯沮丧地预言政策过程框架会减少研究 的付出,我则提出更为积极的回应,即该框架将继续在政策研究 和项目运作中作为有价值的启发式方法而发挥作用。首先,正如 我所提到的,并且尽管萨巴蒂尔和简金斯一史密斯多次反对,我 们仍然对他们及其所支持的联盟框架(ACF)是否冲破了由政策 过程取向产生的范式⑥有疑问。公平地说,我们并不清楚是否应 ⑥这些资料来源于关于这个主题的同萨巴蒂尔教授的大量的谈话。人们 可以很正当地援引萨巴蒂尔教授早期就很精通的政策执行类文献来证明他是最 近才明显拒绝政策过程。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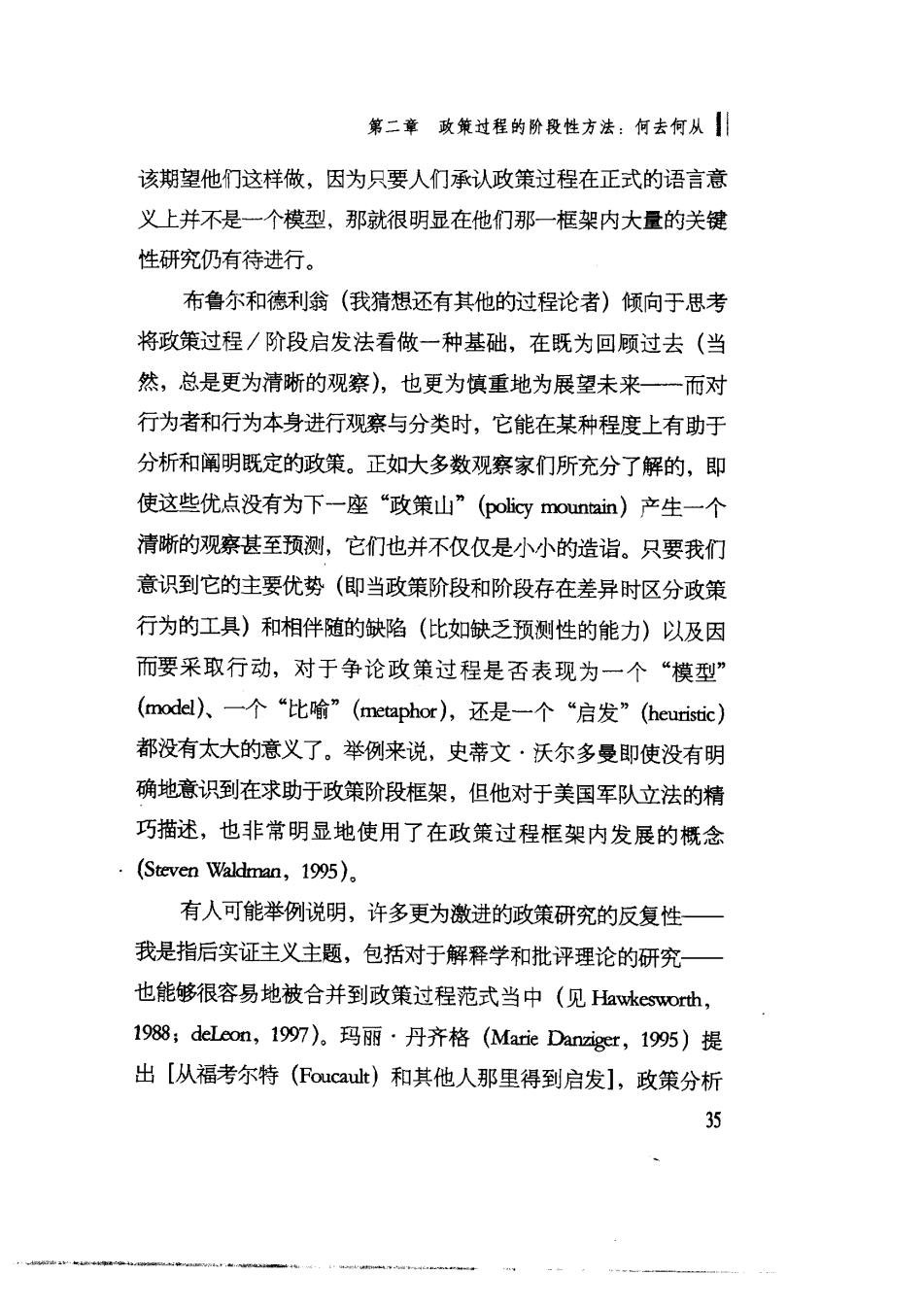
第二章政策过程的阶段性方法:何去何从‖ 该期望他们这样做,因为只要人们承认政策过程在正式的语言意 义上并不是一个模型,那就很明显在他们那一框架内大量的关键 性研究仍有待进行。 布鲁尔和德利翁(我猜想还有其他的过程论者)倾向于思考 将政策过程/阶段启发法看做一种基础,在既为回顾过去(当 然,总是更为清晰的观察),也更为慎重地为展望未来一一而对 行为者和行为本身进行观察与分类时,它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 分析和阐明既定的政策。正如大多数观察家们所充分了解的,即 使这些优点没有为下一座“政策山”(policy mountain)产生一个 清晰的观察甚至预测,它们也并不仅仅是小小的造诣。只要我们 意识到它的主要优势(即当政策阶段和阶段存在差异时区分政策 行为的工具)和相伴随的缺陷(比如缺乏预测性的能力)以及因 而要采取行动,对于争论政策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模型” (model)、一个“比喻”(metaphor),还是一个“启发”(heuristic) 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举例来说,史蒂文·沃尔多曼即使没有明 确地意识到在求助于政策阶段框架,但他对于美国军队立法的精 巧描述,也非常明显地使用了在政策过程框架内发展的概念 (Steven Waldman,1995). 有人可能举例说明,许多更为激进的政策研究的反复性 我是指后实证主义主题,包括对于解释学和批评理论的研究 也能够很容易地被合并到政策过程范式当中(见Hawkesworth, 1988;deLeon,1997)。玛丽·丹齐格(Marie Danziger,1995)提 出[从福考尔特(Foucault)和其他人那里得到启发],政策分析 35

情政策过程理论 的“客观”基础与主观判断差别不大,并且不能被当作似乎是科 学的“事实”来使用。举例来说,批评理论指出,“系统地歪曲 信息沟通”会威胁到好政策和社会合法性的根基,也就是说,根 据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说法就是“沟通的理 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Forester,1985,1993)。就改进了 27的问题界定来说,我们会很容易地实现从批评理论到描述一种包 含更大主观色彩或趋于更大沟通理性的运动的转变。拉斯维尔最 初称这个阶段为有“情报”功能的阶段,并且随后的学者们一 如布鲁尔和德利翁(1983)提到它时,称之为创议阶段。其他后 实证主义者比如费希尔和弗雷斯特(1993)也有此类似的说法。 像萨巴蒂尔和简金斯一史密斯的支持联盟框架那样仔细构建的一 个模型,可能无法包括这些更新的政策分析方法,诸如沟通理性 和后实证主义。 同样地,对政策研究的新贡献,比如人种学方法或调停谈判 学方法,也能被放入政策过程模型当中,从而对政策过程的有效 理解、运作,或更确切地说,对改善提供给政府信息的质量,不 但毫无损害一实际上,还会有所增强。当然,这最后一项任 务,是拉斯维尔原初和持久的指责之一。在上面的事例中,如果 我们认为可信度源自于引用的研究方法的话(并且我认为很少有 人能完全否认这一点),类似萨巴蒂尔这样的政策学者就可能被 认为会通过紧紧依靠实证主义思想和程序的问题原则来抑制政策 科学的进步。相反地,这些供选择的概念会很容易被政策过程框 架所获取。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