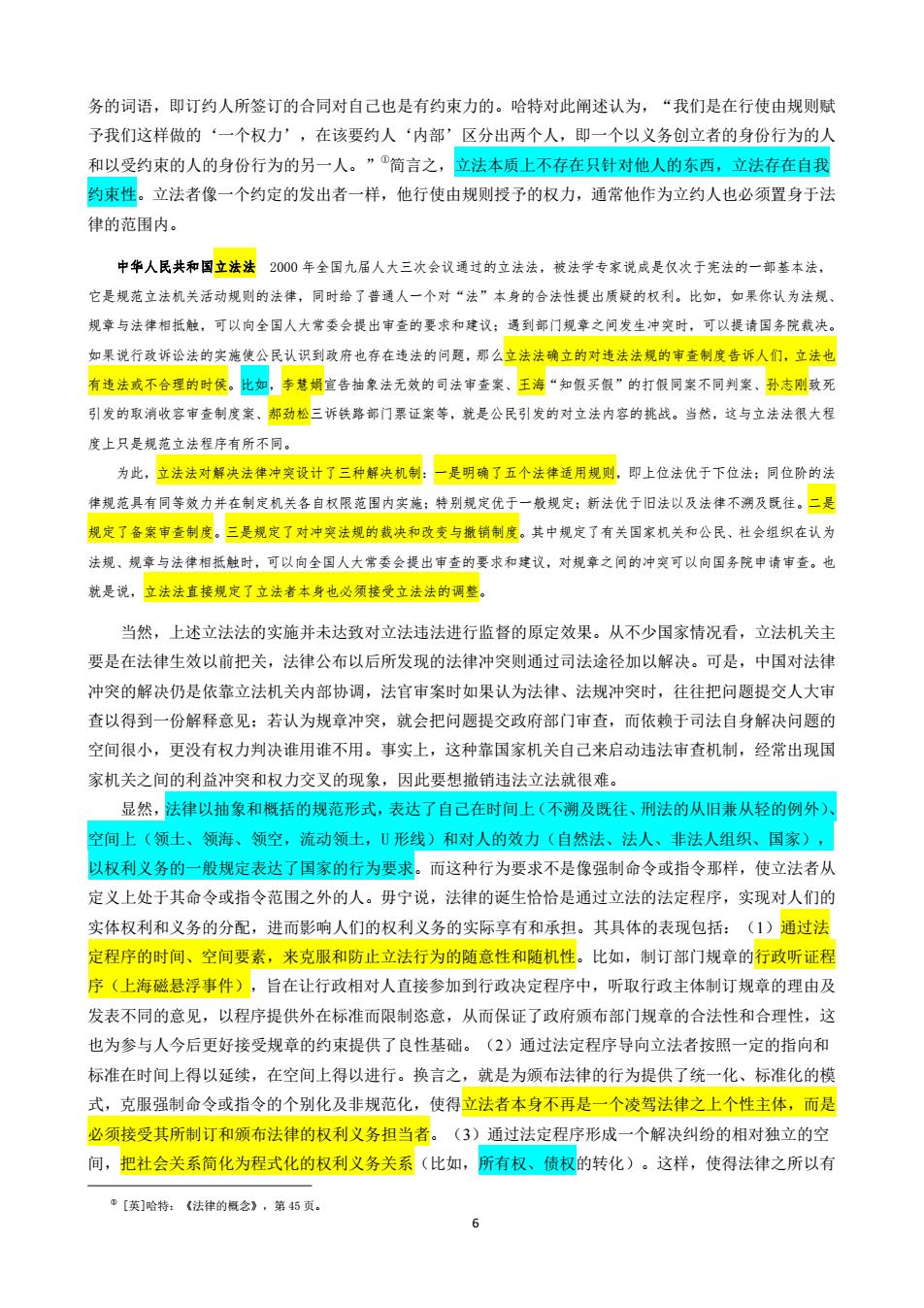
务的词语,即订约人所签订的合同对自己也是有约束力的。哈特对此阐述认为,“我们是在行使由规则赋 予我们这样做的‘一个权力’,在该要约人‘内部’区分出两个人,即一个以义务创立者的身份行为的人 和以受约束的人的身份行为的另一人。”①简言之,立法本质上不存在只针对他人的东西,立法存在自我 约束性。立法者像一个约定的发出者一样,他行使由规则授予的权力,通常他作为立约人也必须置身于法 律的范围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年全国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被法学专家说成是仅次于宪法的一部基本法, 它是规范立法机关活动规则的法律,同时给了普通人一个对“法”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权利。比如,如果你认为法规、 规章与法律相抵触,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要求和建议;遇到部门规章之间发生冲突时,可以提请国务院裁决。 如果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使公民认识到政府也存在违法的问题,那么立法法确立的对违法法规的审查制度告诉人们,立法也 有违法或不合理的时侯。比如,李慈娟宣告抽象法无效的司法审查案、王海“知假买假”的打假同案不同判案、孙志刚致死 引发的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案、郝劲松三诉铁路部门票证案等,就是公民引发的对立法内容的挑战。当然,这与立法法很大程 度上只是规范立法程序有所不同。 为此,立法法对解决法律冲突设计了三种解决机制: 是明确了五个法律适用规则,即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同位阶的法 律规范具有同等效力并在制定机关各自权限范围内实施;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法优于旧法以及法律不溯及既往。二是 规定了备案审查制度。三是规定了对冲突法规的裁决和改变与撤销制度。其中规定了有关国家机关和公民、社会组织在认为 法规、规章与法律相抵触时,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要求和建议,对规章之间的冲突可以向国务院申请审查。也 就是说,立法法直接规定了立法者本身也必须接受立法法的调整。 当然,上述立法法的实施并未达致对立法违法进行监督的原定效果。从不少国家情况看,立法机关主 要是在法律生效以前把关,法律公布以后所发现的法律冲突则通过司法途径加以解决。可是,中国对法律 冲突的解决仍是依靠立法机关内部协调,法官审案时如果认为法律、法规冲突时,往往把问题提交人大审 查以得到一份解释意见;若认为规章冲突,就会把问题提交政府部门审查,而依赖于司法自身解决问题的 空间很小,更没有权力判决谁用谁不用。事实上,这种靠国家机关自己来启动违法审查机制,经常出现国 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交叉的现象,因此要想撤销违法立法就很难。 显然,法律以抽象和概括的规范形式,表达了自己在时间上(不溯及既往、刑法的从旧兼从轻的例外) 空间上(领土、领海、领空,流动领士,U形线)和对人的效力(自然法、法人、非法人组织、国家), 以权利义务的一般规定表达了国家的行为要求。而这种行为要求不是像强制命令或指令那样,使立法者从 定义上处于其命令或指令范围之外的人。毋宁说,法律的诞生恰恰是通过立法的法定程序,实现对人们的 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进而影响人们的权利义务的实际享有和承担。其具体的表现包括:(1)通过法 定程序的时间、空间要素,来克服和防止立法行为的随意性和随机性。比如,制订部门规章的行政听证程 序(上海磁悬浮事件),旨在让行政相对人直接参加到行政决定程序中,听取行政主体制订规章的理由及 发表不同的意见,以程序提供外在标准而限制恣意,从而保证了政府颁布部门规章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 也为参与人今后更好接受规章的约束提供了良性基础。(2)通过法定程序导向立法者按照一定的指向和 标准在时间上得以延续,在空间上得以进行。换言之,就是为颁布法律的行为提供了统一化、标准化的模 式,克服强制命令或指令的个别化及非规范化,使得立法者本身不再是一个凌驾法律之上个性主体,而是 必须接受其所制订和颁布法律的权利义务担当者。(3)通过法定程序形成一个解决纠纷的相对独立的空 间,把社会关系简化为程式化的权利义务关系(比如,所有权、债权的转化)。这样,使得法律之所以有 ①[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45页。 6
6 务的词语,即订约人所签订的合同对自己也是有约束力的。哈特对此阐述认为,“我们是在行使由规则赋 予我们这样做的‘一个权力’,在该要约人‘内部’区分出两个人,即一个以义务创立者的身份行为的人 和以受约束的人的身份行为的另一人。” ①简言之,立法本质上不存在只针对他人的东西,立法存在自我 约束性。立法者像一个约定的发出者一样,他行使由规则授予的权力,通常他作为立约人也必须置身于法 律的范围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000 年全国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被法学专家说成是仅次于宪法的一部基本法, 它是规范立法机关活动规则的法律,同时给了普通人一个对“法”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权利。比如,如果你认为法规、 规章与法律相抵触,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要求和建议;遇到部门规章之间发生冲突时,可以提请国务院裁决。 如果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使公民认识到政府也存在违法的问题,那么立法法确立的对违法法规的审查制度告诉人们,立法也 有违法或不合理的时侯。比如,李慧娟宣告抽象法无效的司法审查案、王海“知假买假”的打假同案不同判案、孙志刚致死 引发的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案、郝劲松三诉铁路部门票证案等,就是公民引发的对立法内容的挑战。当然,这与立法法很大程 度上只是规范立法程序有所不同。 为此,立法法对解决法律冲突设计了三种解决机制:一是明确了五个法律适用规则,即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同位阶的法 律规范具有同等效力并在制定机关各自权限范围内实施;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法优于旧法以及法律不溯及既往。二是 规定了备案审查制度。三是规定了对冲突法规的裁决和改变与撤销制度。其中规定了有关国家机关和公民、社会组织在认为 法规、规章与法律相抵触时,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要求和建议,对规章之间的冲突可以向国务院申请审查。也 就是说,立法法直接规定了立法者本身也必须接受立法法的调整。 当然,上述立法法的实施并未达致对立法违法进行监督的原定效果。从不少国家情况看,立法机关主 要是在法律生效以前把关,法律公布以后所发现的法律冲突则通过司法途径加以解决。可是,中国对法律 冲突的解决仍是依靠立法机关内部协调,法官审案时如果认为法律、法规冲突时,往往把问题提交人大审 查以得到一份解释意见;若认为规章冲突,就会把问题提交政府部门审查,而依赖于司法自身解决问题的 空间很小,更没有权力判决谁用谁不用。事实上,这种靠国家机关自己来启动违法审查机制,经常出现国 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交叉的现象,因此要想撤销违法立法就很难。 显然,法律以抽象和概括的规范形式,表达了自己在时间上(不溯及既往、刑法的从旧兼从轻的例外)、 空间上(领土、领海、领空,流动领土,U 形线)和对人的效力(自然法、法人、非法人组织、国家), 以权利义务的一般规定表达了国家的行为要求。而这种行为要求不是像强制命令或指令那样,使立法者从 定义上处于其命令或指令范围之外的人。毋宁说,法律的诞生恰恰是通过立法的法定程序,实现对人们的 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进而影响人们的权利义务的实际享有和承担。其具体的表现包括:(1)通过法 定程序的时间、空间要素,来克服和防止立法行为的随意性和随机性。比如,制订部门规章的行政听证程 序(上海磁悬浮事件),旨在让行政相对人直接参加到行政决定程序中,听取行政主体制订规章的理由及 发表不同的意见,以程序提供外在标准而限制恣意,从而保证了政府颁布部门规章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 也为参与人今后更好接受规章的约束提供了良性基础。(2)通过法定程序导向立法者按照一定的指向和 标准在时间上得以延续,在空间上得以进行。换言之,就是为颁布法律的行为提供了统一化、标准化的模 式,克服强制命令或指令的个别化及非规范化,使得立法者本身不再是一个凌驾法律之上个性主体,而是 必须接受其所制订和颁布法律的权利义务担当者。(3)通过法定程序形成一个解决纠纷的相对独立的空 间,把社会关系简化为程式化的权利义务关系(比如,所有权、债权的转化)。这样,使得法律之所以有 ①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 4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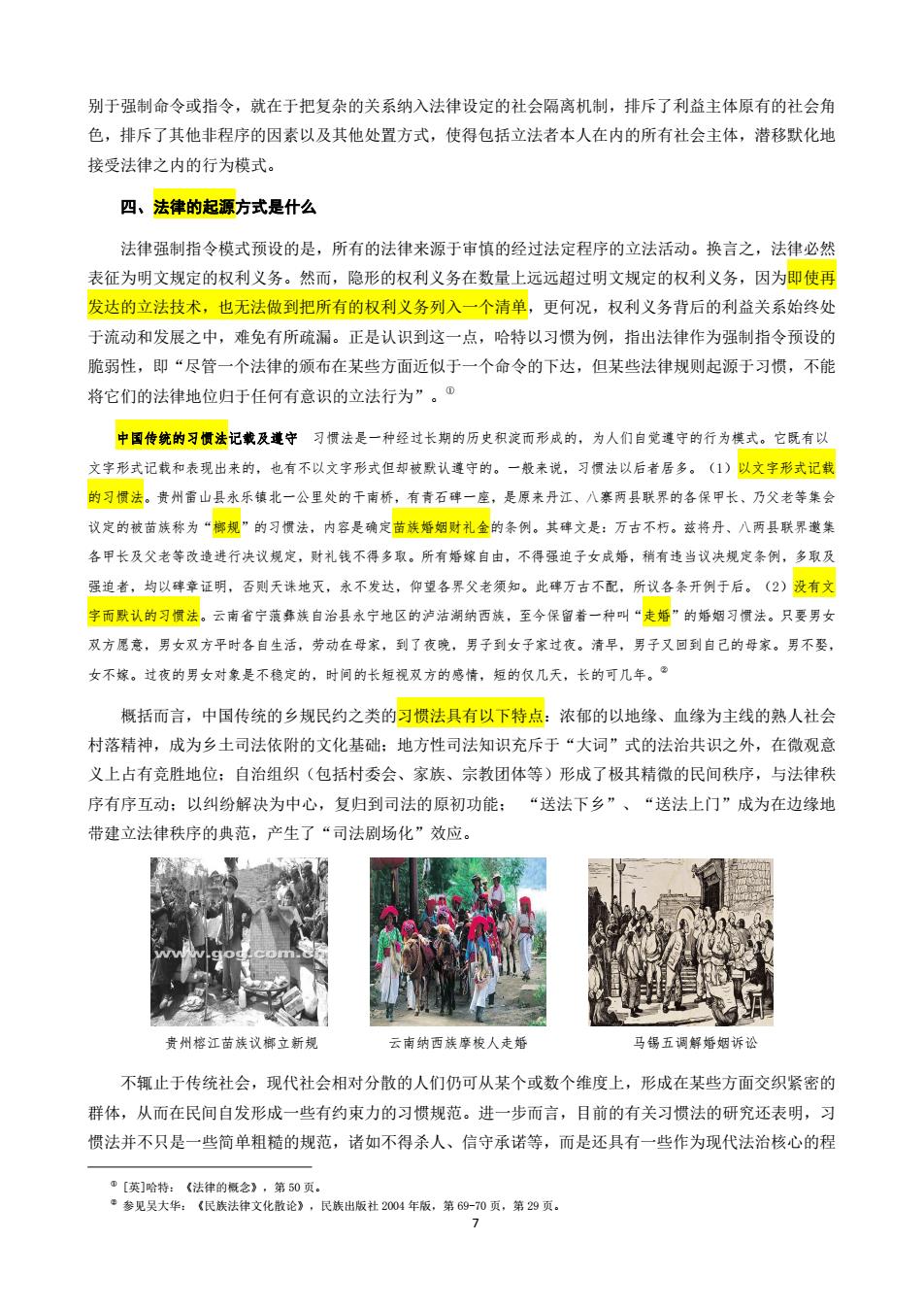
别于强制命令或指令,就在于把复杂的关系纳入法律设定的社会隔离机制,排斥了利益主体原有的社会角 色,排斥了其他非程序的因素以及其他处置方式,使得包括立法者本人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体,潜移默化地 接受法律之内的行为模式。 四、法律的起源方式是什么 法律强制指令模式预设的是,所有的法律来源于审慎的经过法定程序的立法活动。换言之,法律必然 表征为明文规定的权利义务。然而,隐形的权利义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明文规定的权利义务,因为即使再 发达的立法技术,也无法做到把所有的权利义务列入一个清单,更何况,权利义务背后的利益关系始终处 于流动和发展之中,难免有所疏漏。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哈特以习惯为例,指出法律作为强制指令预设的 脆弱性,即“尽管一个法律的颁布在某些方面近似于一个命令的下达,但某些法律规则起源于习惯,不能 将它们的法律地位归于任何有意识的立法行为”。① 中国传统的习惯法记载及遵守习惯法是一种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模式。它既有以 文字形式记载和表现出来的,也有不以文字形式但却被默认遵守的。一般来说,习惯法以后者居多。(1)以文字形式记载 的习惯法。贵州雷山县永乐镇北一公里处的干南桥,有青石碑一座,是原来丹江、八寨两县联界的各保甲长、乃父老等集会 议定的被苗族称为“榔规”的习惯法,内容是确定苗族婚姻财礼金的条例。其碑文是:万古不朽。兹将丹、八两县联界邀集 各甲长及父老等改造进行决议规定,财礼钱不得多取。所有婚嫁自由,不得强迫子女成婚,稍有违当议决规定条例,多取及 强迫者,均以碑章证明,否则天诛地灭,永不发达,仰望各界父老领须知。此碑万古不配,所议各条开例于后。(2)没有文 字而默认的习惯法。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地区的泸沽湖纳西族,至今保留着一种叫“走婚”的婚姻习惯法。只要男女 丸方愿意,男女双方平时各自生活,劳动在母家,到了夜晚,男子到女子家过夜。清早,男子又回到自己的母家。男不娶, 女不嫁。过夜的男女对象是不稳定的,时间的长短视双方的感情,短的仅几天,长的可几年。® 概括而言,中国传统的乡规民约之类的习惯法具有以下特点:浓郁的以地缘、血缘为主线的熟人社会 村落精神,成为乡土司法依附的文化基础:地方性司法知识充斥于“大词”式的法治共识之外,在微观意 义上占有竞胜地位:自治组织(包括村委会、家族、宗教团体等)形成了极其精微的民间秩序,与法律秩 序有序互动:以纠纷解决为中心,复归到司法的原初功能:“送法下乡”、“送法上门”成为在边缘地 带建立法律秩序的典范,产生了“司法剧场化”效应。 贵州榕江苗族议榔立新规 云南纳西族摩梭人走婚 马锡五调解婚姻诉讼 不辄止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相对分散的人们仍可从某个或数个维度上,形成在某些方面交织紧密的 群体,从而在民间自发形成一些有约束力的习惯规范。进一步而言,目前的有关习惯法的研究还表明,习 惯法并不只是一些简单粗糙的规范,诸如不得杀人、信守承诺等,而是还具有一些作为现代法治核心的程 ①[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50页。 ⑧参见吴大华:《民族法律文化散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69-70页,第29页。 7
7 别于强制命令或指令,就在于把复杂的关系纳入法律设定的社会隔离机制,排斥了利益主体原有的社会角 色,排斥了其他非程序的因素以及其他处置方式,使得包括立法者本人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体,潜移默化地 接受法律之内的行为模式。 四、法律的起源方式是什么 法律强制指令模式预设的是,所有的法律来源于审慎的经过法定程序的立法活动。换言之,法律必然 表征为明文规定的权利义务。然而,隐形的权利义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明文规定的权利义务,因为即使再 发达的立法技术,也无法做到把所有的权利义务列入一个清单,更何况,权利义务背后的利益关系始终处 于流动和发展之中,难免有所疏漏。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哈特以习惯为例,指出法律作为强制指令预设的 脆弱性,即“尽管一个法律的颁布在某些方面近似于一个命令的下达,但某些法律规则起源于习惯,不能 将它们的法律地位归于任何有意识的立法行为”。 ① 中国传统的习惯法记载及遵守 习惯法是一种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模式。它既有以 文字形式记载和表现出来的,也有不以文字形式但却被默认遵守的。一般来说,习惯法以后者居多。(1)以文字形式记载 的习惯法。贵州雷山县永乐镇北一公里处的干南桥,有青石碑一座,是原来丹江、八寨两县联界的各保甲长、乃父老等集会 议定的被苗族称为“榔规”的习惯法,内容是确定苗族婚姻财礼金的条例。其碑文是:万古不朽。兹将丹、八两县联界邀集 各甲长及父老等改造进行决议规定,财礼钱不得多取。所有婚嫁自由,不得强迫子女成婚,稍有违当议决规定条例,多取及 强迫者,均以碑章证明,否则天诛地灭,永不发达,仰望各界父老须知。此碑万古不配,所议各条开例于后。(2)没有文 字而默认的习惯法。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地区的泸沽湖纳西族,至今保留着一种叫“走婚”的婚姻习惯法。只要男女 双方愿意,男女双方平时各自生活,劳动在母家,到了夜晚,男子到女子家过夜。清早,男子又回到自己的母家。男不娶, 女不嫁。过夜的男女对象是不稳定的,时间的长短视双方的感情,短的仅几天,长的可几年。 ② 概括而言,中国传统的乡规民约之类的习惯法具有以下特点:浓郁的以地缘、血缘为主线的熟人社会 村落精神,成为乡土司法依附的文化基础;地方性司法知识充斥于“大词”式的法治共识之外,在微观意 义上占有竞胜地位;自治组织(包括村委会、家族、宗教团体等)形成了极其精微的民间秩序,与法律秩 序有序互动;以纠纷解决为中心,复归到司法的原初功能; “送法下乡”、“送法上门”成为在边缘地 带建立法律秩序的典范,产生了“司法剧场化”效应。 贵州榕江苗族议榔立新规 云南纳西族摩梭人走婚 马锡五调解婚姻诉讼 不辄止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相对分散的人们仍可从某个或数个维度上,形成在某些方面交织紧密的 群体,从而在民间自发形成一些有约束力的习惯规范。进一步而言,目前的有关习惯法的研究还表明,习 惯法并不只是一些简单粗糙的规范,诸如不得杀人、信守承诺等,而是还具有一些作为现代法治核心的程 ①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 50 页。 ② 参见吴大华:《民族法律文化散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9-70 页,第 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