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六七入日十月n+洗#日 法軍离莫斯科。 十月十二日十月出四日 馬洛·雅罗斯拉雜次的战役。 十月计一日十一月二日哥逵克兵在雜亞倚馬擄掠法 軍。 一入-二年(第四卷第三部) 丰月个想晋 十一月卒品鲁 法軍在斯摩陵斯克。 一入一二年(第四卷第四部) 十一月婴日晋十一月表在目 克拉斯諾的战役。 十一月九日 十一月廿一日 柰伊后衛到达奥尔沙。 十一月香 十一月#大鲁 渡柏來西那河。 十一月廿三日十二月五日 拿破命在斯摩尔高尼离弃軍 除。 十二月六日 十二月十入日 拿破命到达巴黎。 一八一三一一一入二O(尾声第一部) V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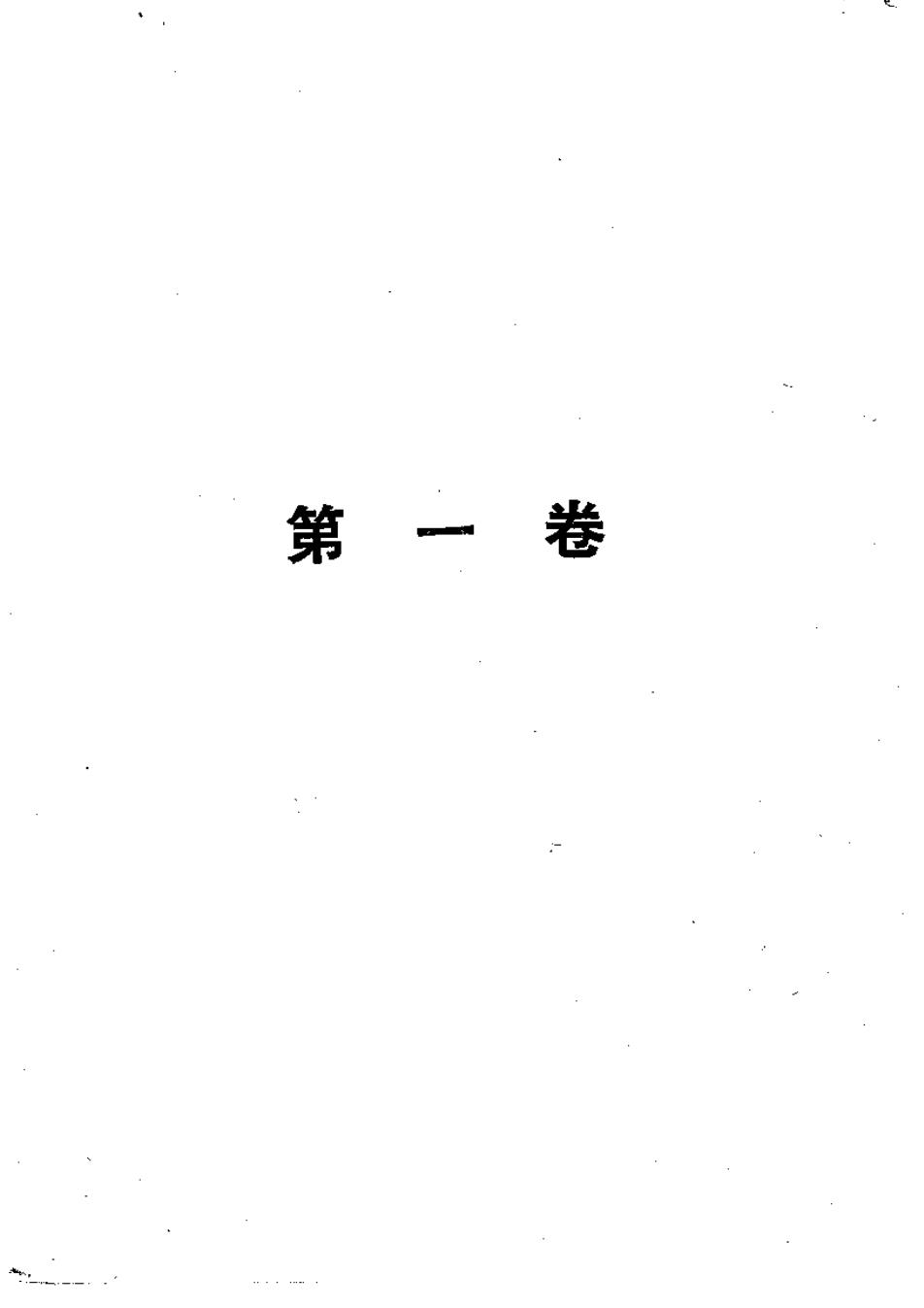
第 一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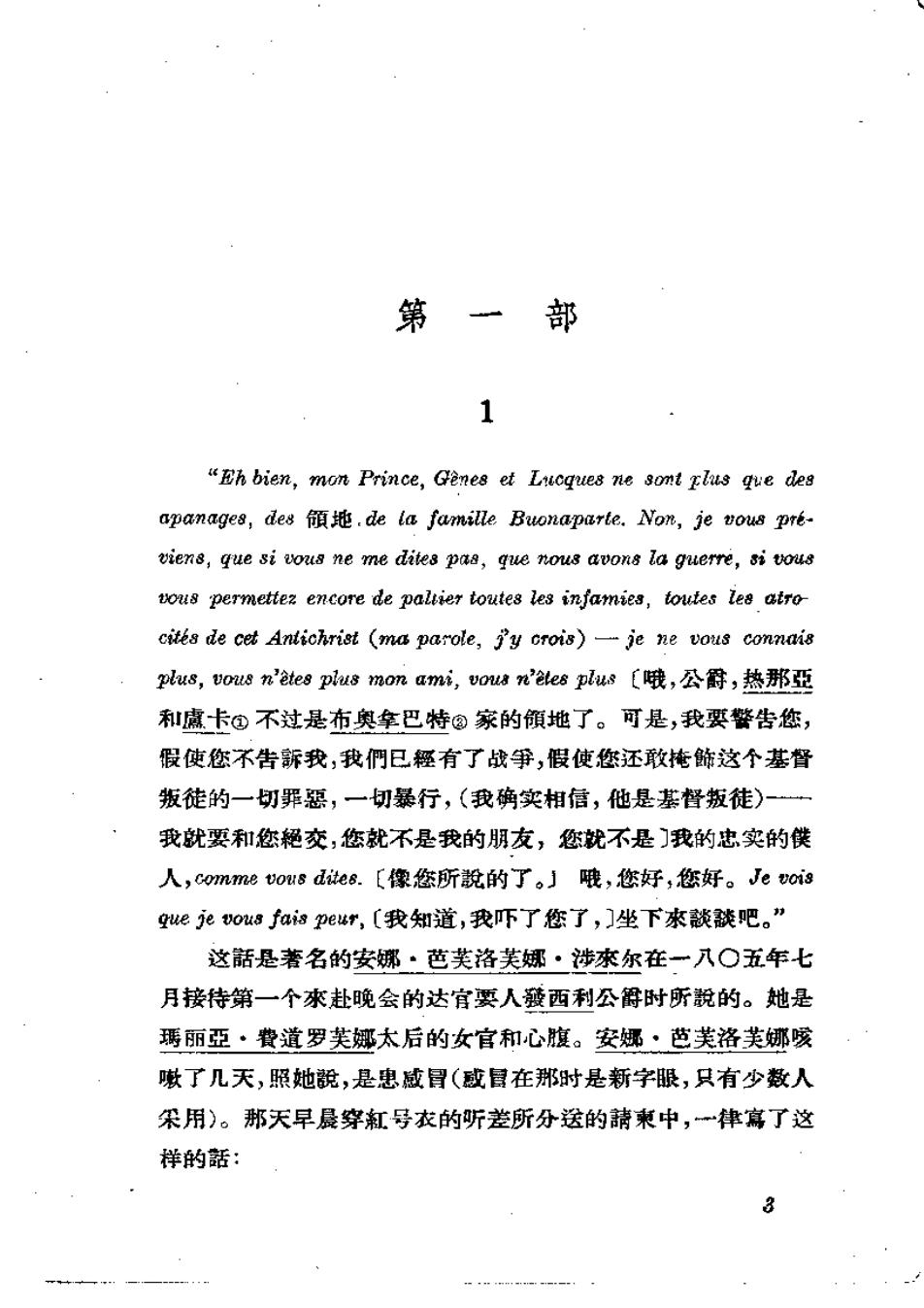
第 部 1 "Ph bien,mon Prince,Genes et Lucgues ne somt plus gue des apanages,des.de la famille Buonaparte.Non,je vous pre- viens,que si vous ne me dites pas,que nous avons la guerre,si vous vous permettez encore de paltier toutes les infamies,toutes les atro cites de cet Antichrist (ma parole,fy crois)-je ne vous comnais plus,vou8'tes plu8 mon ami,voua%'ee8pus〔哦,公爵,热那亞 和廬卡@不过是布奥拿巴特®家的頜地了。可是,我要警告您, 限使您不告訴我,我們已經有了战笋,假使您还敢掩飾这个基督 叛徒的一切罪惡,一切暴行,(我确实相信,他是基督叛徒)一 我就要和您絕交,您就不是我的朋友,您就不是〕我的忠实的濮 人,comme vous dite8.〔像您所說的了。j哦,您好,您好。Je vois ue je vou8 fais peut*,〔我知道,我吓了您了,]坐下來談談吧。” 这話是著名的安娜·芭芙洛芙娜·涉來尔在一入○五年七 月接待第一个來赴晚会的达宜要人發西利公爵时所說的。她是 瑪丽亞·費道罗芙娜太后的女官和心腹。安娜·芭芙洛美娜咳 嗽了几天,照她說,是患威冒(咸冒在那时是新字服,只有少数人 宋用)。那天早晨穿紅号衣的听差所分送的請束中,律篇了这 样的話: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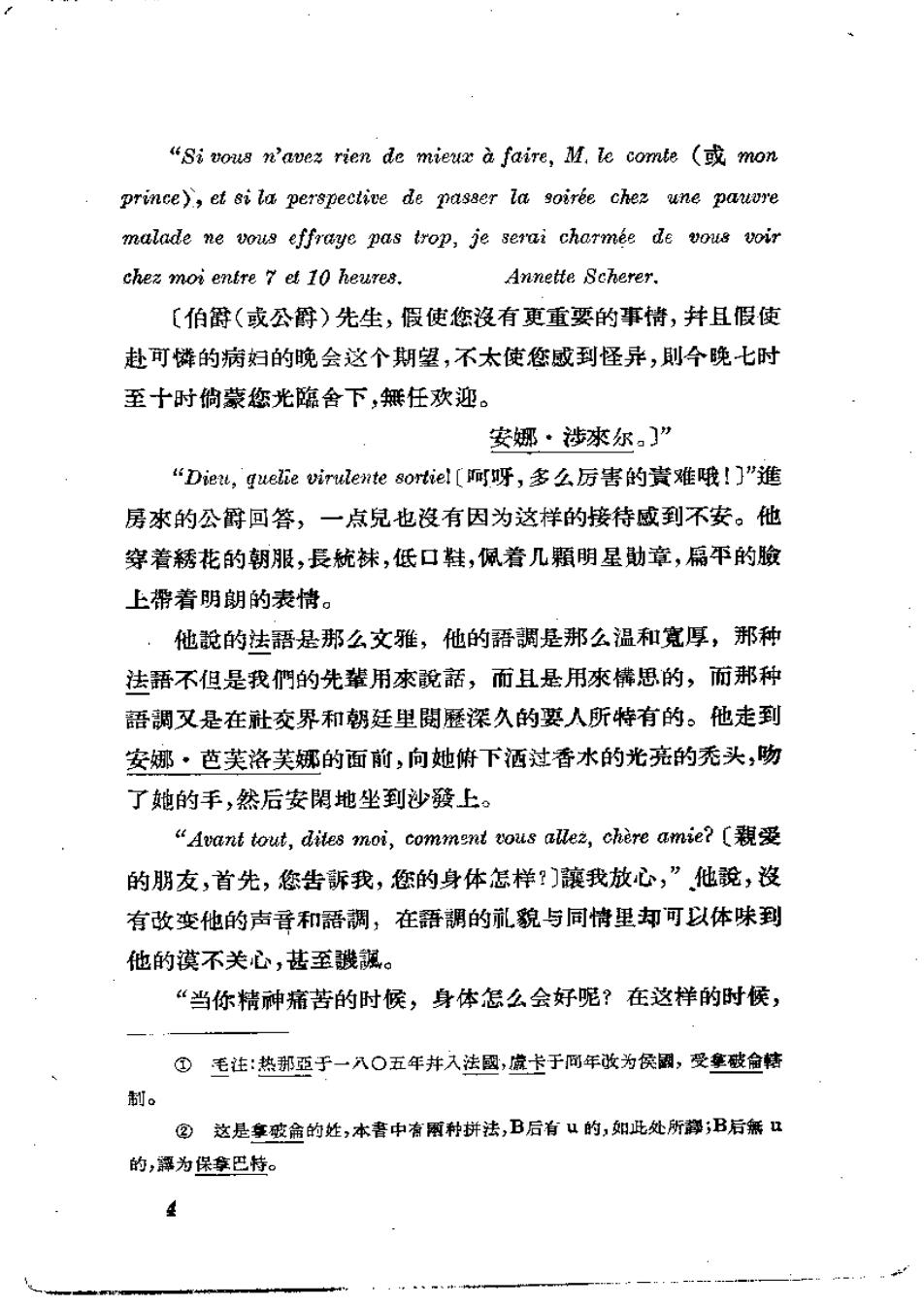
"Si vous n'avez rien de mieux a faire,M.le comte mon prince),et si la perspective de passer la soiree chez une pauure malade ne vous effraye pas trop,je serai charmee de vous voir chez moi entre 7 et 10 heures, Annette Scherer. 〔伯爵(或公爵)先生,假使您沒有更重要的事错,并且假使 赴可憐的病妇的晚会这个期望,不太使您威到怪异,則今晚七时 至十时徜蒙您光臨舍下,無任欢迎。 安娜·涉來尔。]” “Dieu,quelie virulente sortiel[m呵呀,多么厉害的黄难哦!]”進 房來的公爵回答,一点兒也沒有因为这样的接待威到不安。他 穿着锈花的朝服,長統袜,低口鞋,佩着几顆明星助章,隔平的臉 上帶着明朗的表情。 他說的法語是那么文雅,他的語調是那么温和寬厚,那种 法語不但是我們的先輩用來說話,而且是用來構思的,而那种 語調叉是在社交界和朝廷里閱歷深八的要人所特有的。他走到 安娜·芭芙洛芙挪的面前,向她俯下洒过香水的光亮的秃头,吻 了她的手,然后安閑地坐到沙發上。 “Avant tout,dites moi,,comment tous alle之,chere amie?〔親爱 的朋友,首先,您告新我,您的身体怎样?〕藤我放心,”他說,沒 有改变他的声音和語調,在語調的礼貌与同情里却可以体味到 他的漠不关心,甚至譏飄。 “当你精神痛苦的时候,身体怎么会好呢?在这样的时候, ⊙毛注:热那亞于一八O五年并入法國,成卡于阿年改为侯围,受拿酸侖精 制。 ② 这是拿破侖的姓,本書中有丽种拼法,B后有u的,如此处所都;B后無口 的,霹为保年巴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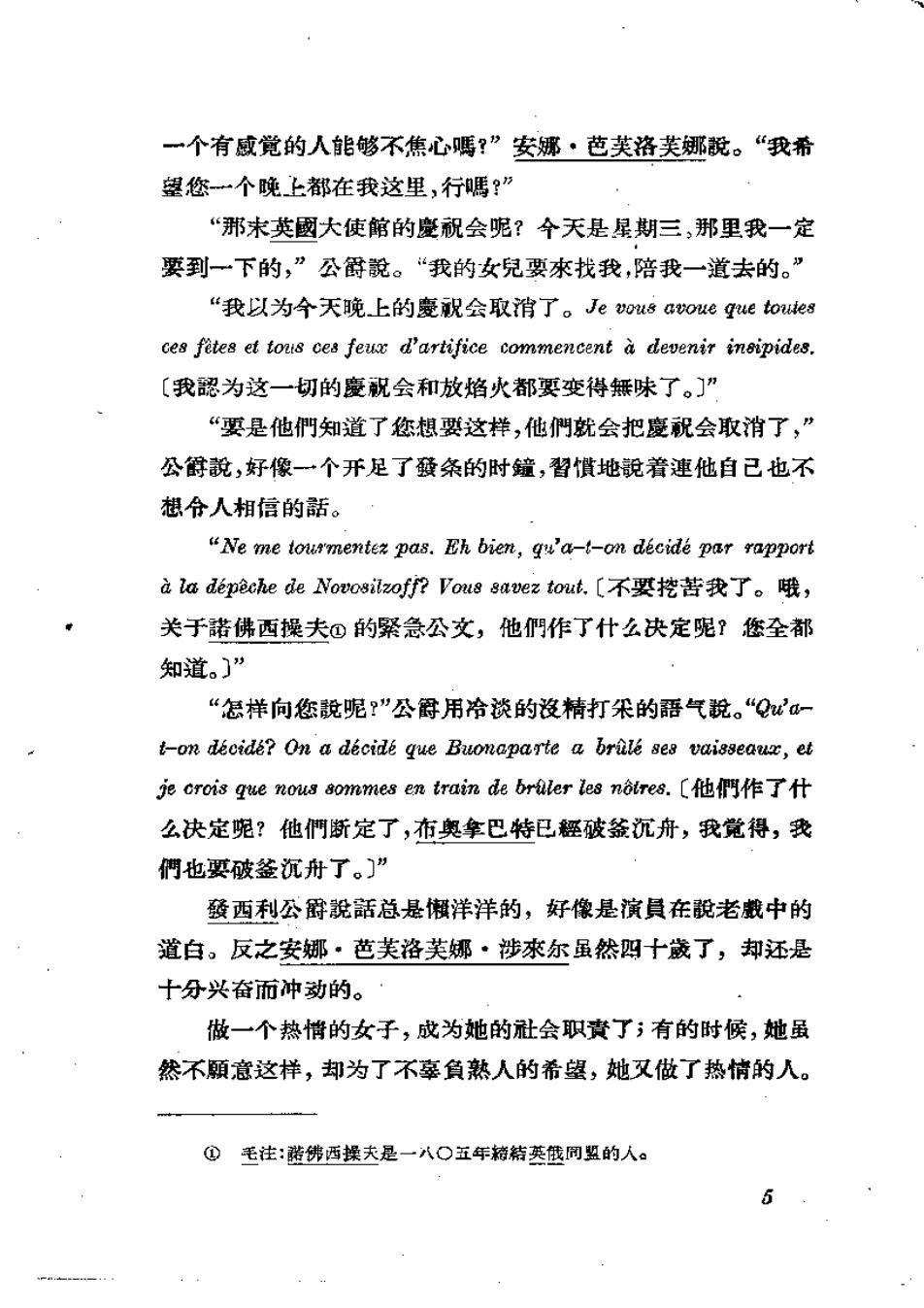
一个有威党的人能够不焦心嗎?”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我希 望您一个晚上都在我这里,行嗎?” “那未英國大使館的慶祝会呢?今天是星期三,邢里我一定 要到一下的,”公爵說。“我的女兒要來找我,陪我一道去的。” “我以为今天晚上的慶祝会取消了。Je vous avoue que toute8 ces fites et tous ces feux d'artifice commencent a devenir insipides. 〔我認为这一切的慶祝会和放焰火都要变得無味了。]” “要是他們知道了您想要这样,他們就会把慶祝会取消了,” 公僻說,好像一个开足了發条的时鐘,智慣地說着連他自已也不 想合人相信的話。· "Ne me tourmentex pas.Eh bien,qu'a-t-on decide par rapport a1ad论neche de Novositzoff护Vou88 ivez tout..〔不要挖苦我了。哦, 关于諾佛西操夫@的緊急公文,他們作了什么决定呢?您全都 知道。〕” “怎样向您說呢?”公爵用冷淡的沒精打朵的語气說。“t- t-on decide?On a deci记形que Buonaparte a briile ses vai&seaux,et je crois gue nou38 ommes e%train de braler ies n6tres.〔他們作了t 么决定呢?他們断定了,布奥拿巴特已經破签沉升,我党得,我 們也要破签沉升了。]” 發西利公爵說話总是潮洋洋的,好像是演員在說老戡中的 道白。反之安娜·芭芙洛芙娜·涉來尔虽然四十歲了,却还是 十分兴奋而冲动的。· 做一个热惜的女子,成为她的肚会职黄了;有的时候,她虽 然不願意这样,却为了不辜負熟人的希望,她父做了热梢的人。 ① 毛注:诺佛西操夫是一八○立年箱待英俄刷盟的人。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