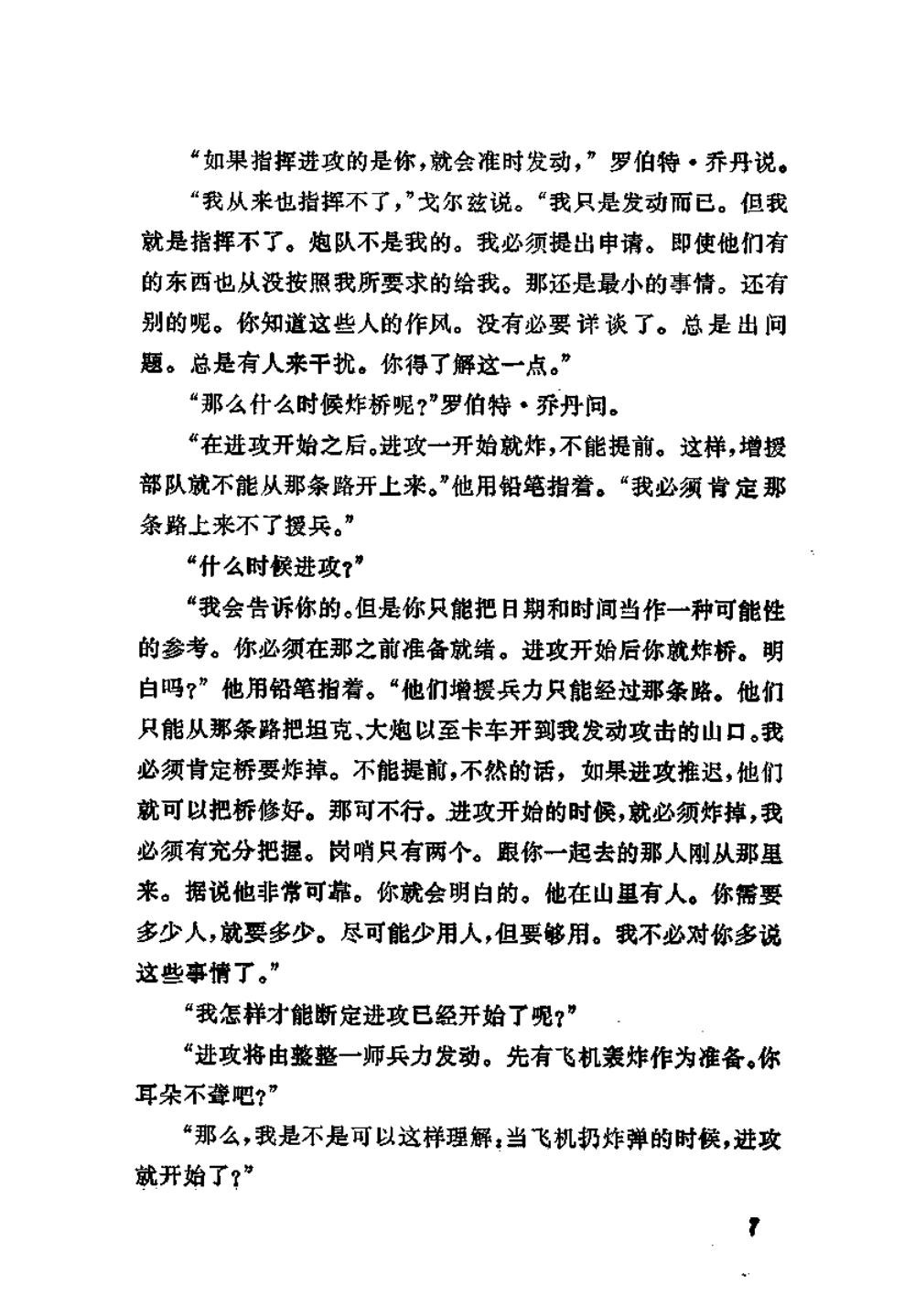
“如果指挥进攻的是你,就会准时发动,”罗伯特·乔丹说。 “我从来也指挥不了,”戈尔兹说。“我只是发动而已。但我 就是指挥不了。炮队不是我的。我必须提出申请。即使他们有 的东西也从没按照我所要求的给我。那还是最小的事情。还有 别的呢。你知道这些人的作风。没有必要详谈了。总是出问 题。总是有人来干扰。你得了解这一点。” “那么什么时候炸桥呢?”罗伯特·乔丹问。 “在进攻开始之后。进攻一开始就炸,不能提前。这样,增援 部队就不能从那条路开上来。”他用铅笔指着。“我必须肯定那 条路上来不了援兵。” “什么时侯进攻?”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你只能把日期和时间当作一种可能性 的参考。你必须在那之前准备就绪。进攻开始后你就炸桥。明 白吗?”他用铅笔指着。“他们增援兵力只能经过那条路。他们 只能从那条路把坦克、大炮以至卡车开到我发动攻击的山口。我 必须肯定桥要炸掉。不能提前,不然的话,如果进攻推迟,他们 就可以把桥修好。那可不行。进攻开始的时候,就必须炸掉,我 必须有充分把握。岗哨只有两个。跟你一起去的那人刚从那里 来。据说他非常可靠。你就会明白的。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 多少人,就要多少。尽可能少用人,但要够用。我不必对你多说 这些事情了。” “我怎样才能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呢?” “进攻将由整整一师兵力发动。先有飞机美炸作为推备。你 耳朵不聋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飞机扔炸弹的时侯,进攻 就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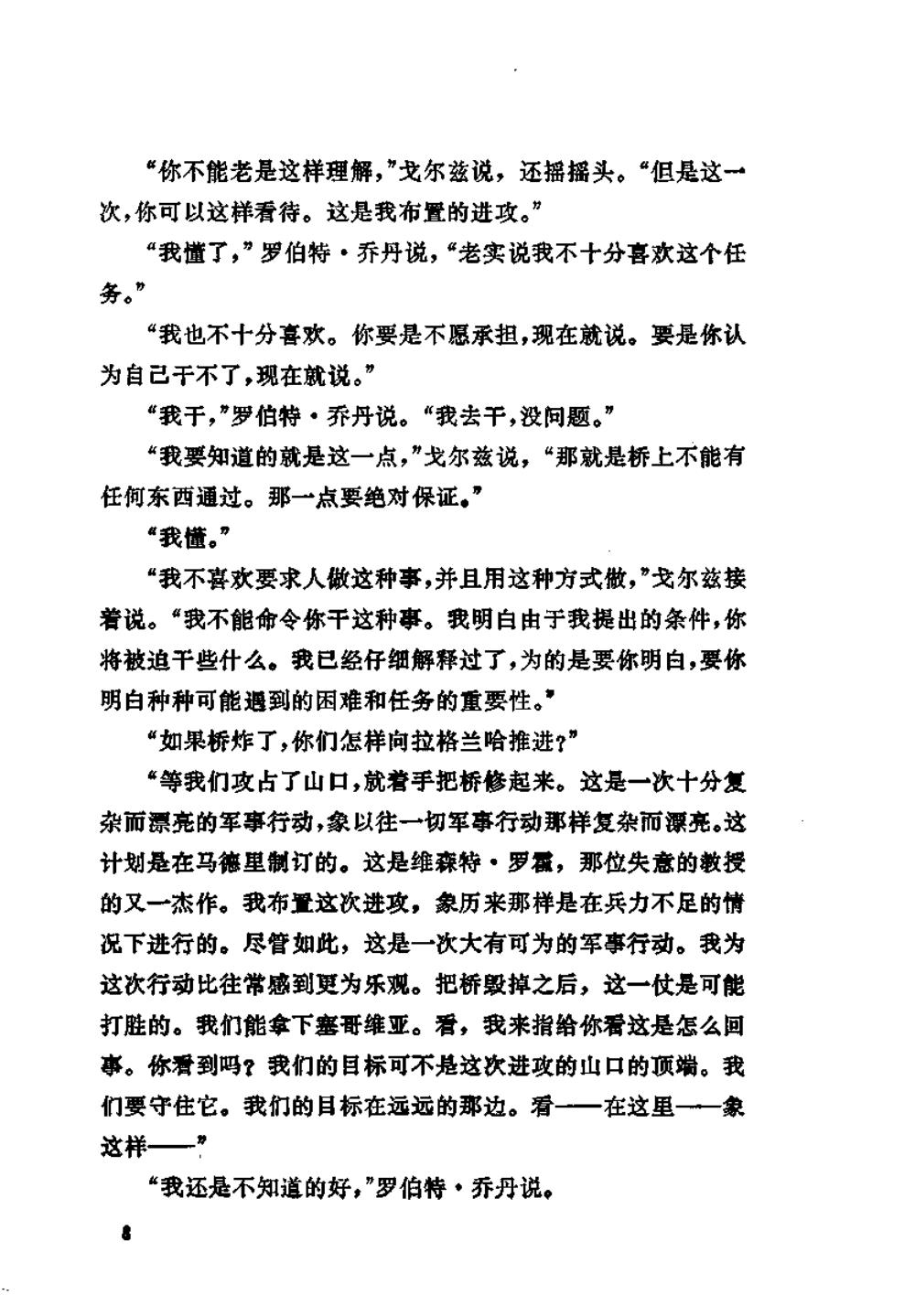
“你不能老是这样理解,”戈尔兹说,还摇摇头。“但是这一 次,你可以这样看待。这是我布置的进攻。” “我懂了,”罗伯特·乔丹说,“老实说我不十分喜欢这个任 务。” “我也不十分喜欢。你要是不愿承担,现在就说。要是你认 为自己于不了,现在就说。”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去干,没问题。” “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戈尔兹说,“那就是桥上不能有 任何东西通过。那一点要绝对保证,” “我懂。” “我不喜欢要求人做这种事,并且用这种方式做,”戈尔兹接 若说。“我不能命令你干这种事。我明白由于我提出的条种,你 将被迫干些什么。我已经仔细解释过了,为的是要你明白,要你 明白种种可能通到的困难和任务的重要性。 “如果桥炸了,你们怎样向拉格兰哈推进?” “等我们攻占了山口,就营手把桥修起来。这是一次十分复 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象以往一切军事行动那样复杂而漂亮。这 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这是维森特·罗,那位失意的散授 的又一杰作。我布置这次进攻,象历来那样是在兵力不足的情 况下进行的。尽管如此,这是一次大有可为的军事行动。我为 这次行动比往常感到更为乐观。把桥毁掉之后,这一仗是可能 打胜的。我们能拿下塞哥维亚。君,我来指给你看这是怎么回 事。你看到吗?我们的目标可不是这次进攻的山口的顶端。我 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在远远的那边。看一在这里一一象 这样一一”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罗伯特·乔丹说。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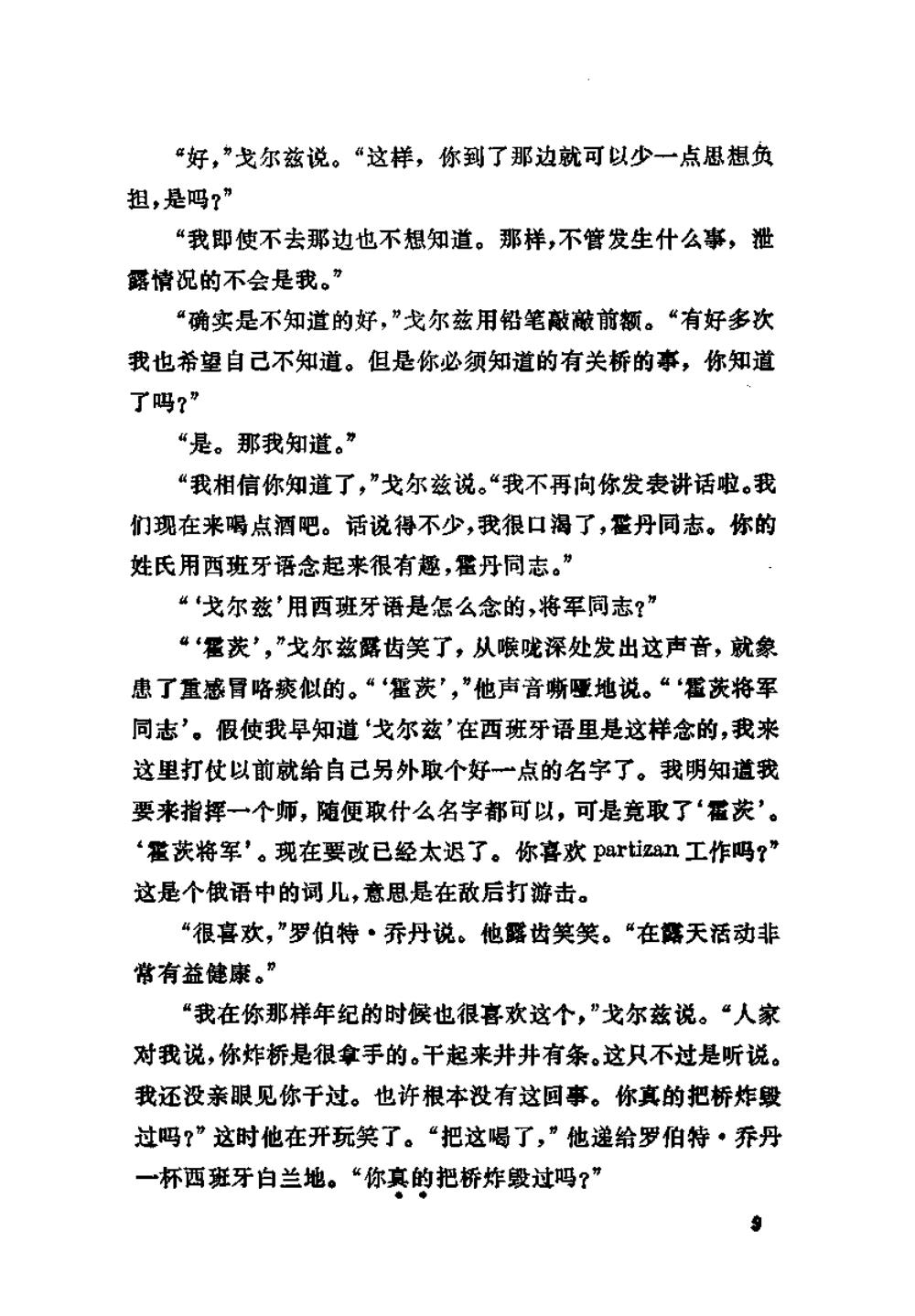
“好,”戈尔兹说。“这样,你到了那边就可以少一点思想负 担,是吗?” “我即使不去那边也不想知道。那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泄 露情况的不会是我。” “确实是不知道的好,”戈尔兹用铅笔敲敲前额。“有好多次 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桥的事,你知道 了吗?” “是。那我知道。” “我相信你知道了,”戈尔兹说。“我不再向你发表讲话啦。我 们现在来喝点酒吧。话说得不少,我很口渴了,丹同志。你的 姓氏用西班牙语念起来很有趣,猛丹同志。” “戈尔兹'用西班牙语是怎么念的,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兹露齿笑了,从喉咙深处发出这声音,就象 患了重感冒咯获似的。“‘瞿茨’,”他声音嘶哑地说。“‘霍茨将军 同志’。假使我早知道‘戈尔兹'在西班牙语里是这样念的,我来 这里打仗以前就给自己另外取个好一点的名字了。我明知道我 要来指挥一个师,随便取什么名字都可以,可是竞取了‘福茨’。 ‘猛茨将军'。现在要改已经太迟了。你喜欢partizan工作吗?” 这是个俄语中的词儿,意思是在敌后打游击。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露齿笑笑。“在露天活动非 常有益健康。” “我在你那样年纪的时候也很喜欢这个,”戈尔兹说。“人家 对我说,你炸桥是很拿手的。干起来井井有条。这只不过是听说。 我还没亲眼见你千过。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你真的把桥炸毁 过吗?”这时他在开玩笑了。“把这喝了,”他递给罗伯特·乔丹 一杯西斑牙白兰地。“你真的把桥炸毁过吗?”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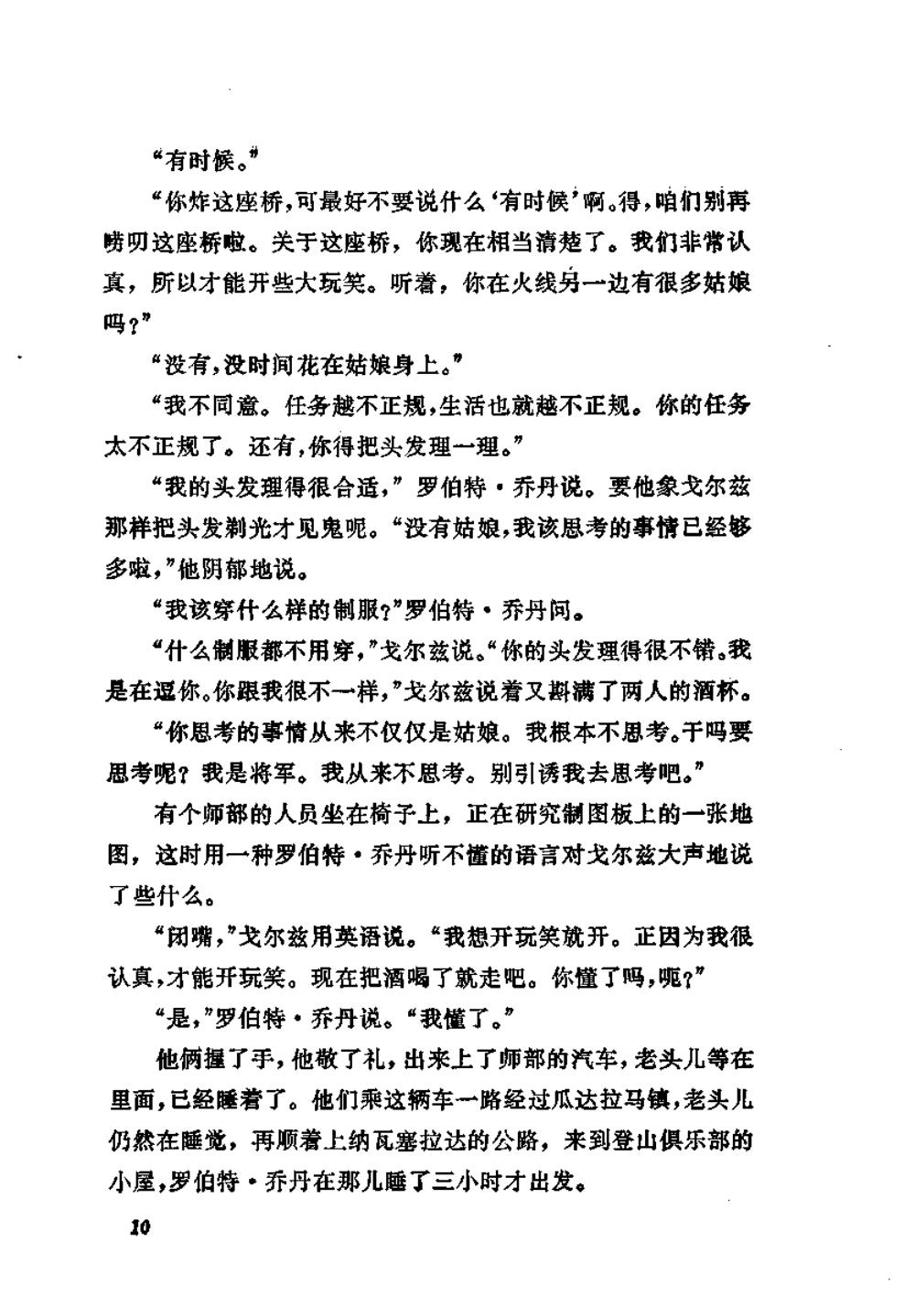
“有时候。# “你炸这座桥,可最好不要说什么‘有时候’啊。得,咱们别再 崂叨这座桥啦。关于这座桥,你现在相当清楚了。我们非常认 真,所以才能开些大玩笑。听着,你在火线另一边有很多姑娘 吗?” “没有,没时间花在姑娘身上。” “我不同意。任务越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你的任务 太不正规了。还有,你得把头发理一理。” “我的头发理得很合适,”罗伯特·乔丹说。要他象戈尔兹 那样把头发剃光才见鬼呢。“没有姑娘,我该思考的事情已经够 多啦,”他阴郁地说。 “我该穿什么样的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制服都不用穿,”戈尔兹说。“你的头发理得很不错,我 是在逗你。你跟我很不一样,”戈尔兹说着又斟满了两人的酒杯。 “你思考的事情从来不仅仅是姑娘。我根本不思考。于吗要 思考呢?我是将军。我从来不思考。别引诱我去思考吧。” 有个师部的人员坐在椅子上,正在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 图,这时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对戈尔兹大声地说 了些什么。 “闭嘴,”戈尔兹用英语说。“我想开玩笑就开。正因为我很 认真,才能开玩笑。现在把酒喝了就走吧。你懂了吗,呃?” “是,”罗伯特·乔丹说。“我懂了。” 他俩握了手,他散了礼,出来上了师部的汽车,老头儿等在 里面,已经睡着了。他们乘这辆车一路经过瓜达拉马镇,老头儿 仍然在睡觉,再顺着上纳瓦塞拉达的公路,来到登山俱乐部的 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儿睡了三小时才出发。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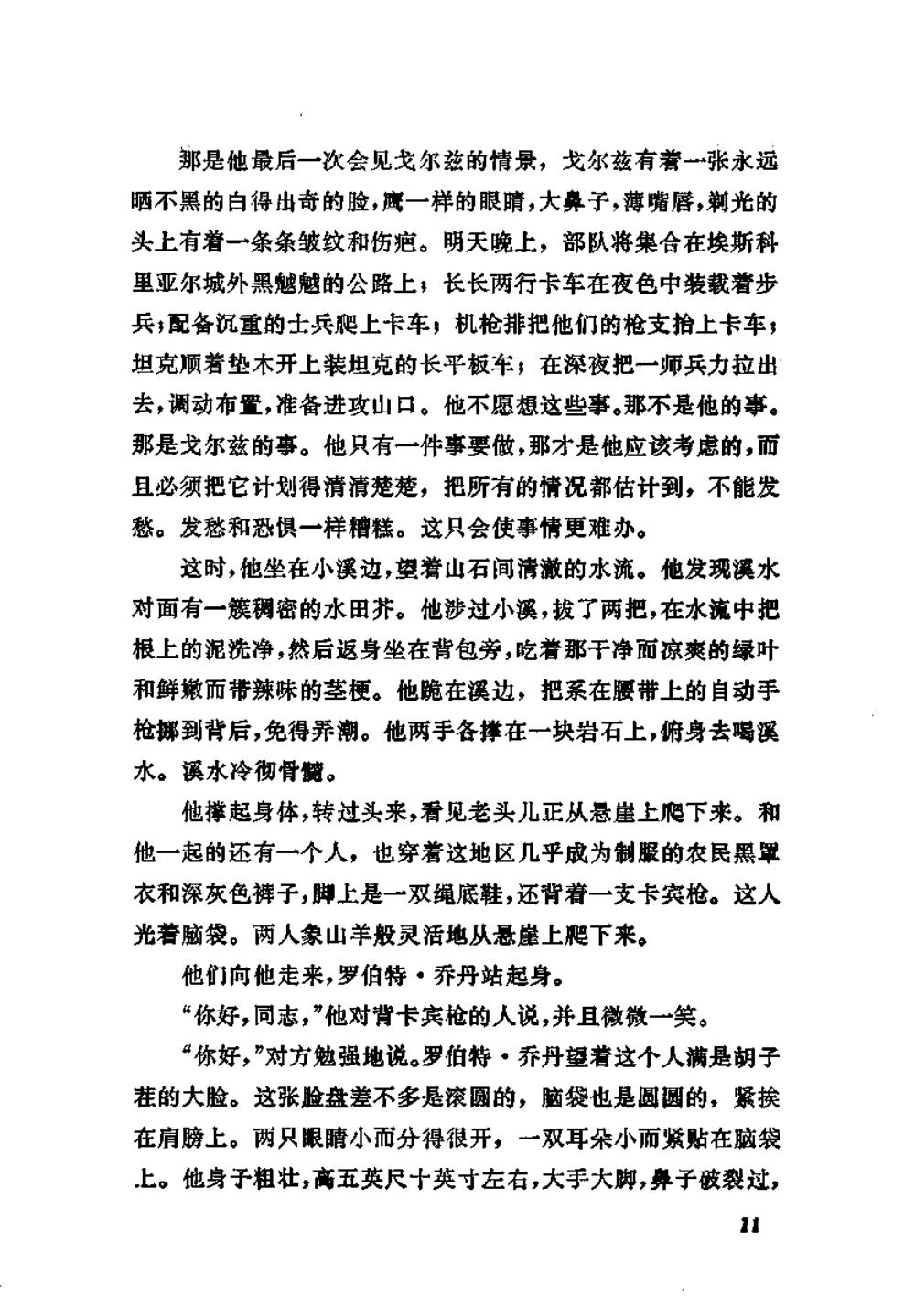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兹的情景,戈尔兹有着张永远 晒不黑的白得出奇的脸,鹰一样的眼睛,大鼻子,薄嘴唇,荆光的 头上有着一条条皱纹和伤疤。明天晚上,部队将集合在埃斯科 里亚尔城外黑魆触的公路上,长长两行卡车在夜色中装载着步 兵配备沉重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把他们的枪支抬上卡车, 坦克顺着垫木开上装坦克的长平板车;在深夜把一师兵力拉出 去,调动布置,准备进攻山口。他不愿想这些事。那不是他的事。 那是戈尔兹的事。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而 且必须把它计划得清清楚楚,把所有的情况都估计到,不能发 愁。发愁和恐惧一样糟糕。这只会使事情更难办。 这时,他坐在小溪边,望着山石间清澈的水流。他发现溪水 对面有一簇稠密的水田芥。他涉过小溪,拔了两把,在水流中把 根上的泥洗净,然后返身坐在背包劳,吃着那干净而凉爽的绿叶 和鲜嫩而带辣味的茎梗。他跪在溪边,把系在腰带上的自动手 枪娜到背后,免得手潮。他两手各撑在一块岩石上,俯身去喝溪 水。溪水拎彻骨魈。 他撑起身体,转过头来,看见老头儿正从悬崖上爬下来。和 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这地区几乎成为制服的农民黑罩 衣和深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还背着一支卡宾枪。这人 光若脑袋。两人象山羊般灵活地从悬崖上爬下来。 他们向他走来,罗伯特·乔丹站起身。 “你好,同志,”他对背卡宾枪的人说,并且微微一笑。 “你好,”对方勉强地说。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个人满是胡子 茬的大脸。这张脸盘差不多是滚圆的,脑袋也是圆圆的,紧挨 在肩膀上。两只眼睛小而分得很开,一双耳朵小而紧贴在脑袋 上。他身子粗壮,高五英尺十英寸左右,大手大脚,鼻子破裂过,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