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8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 “清奇”,他描绘道: 可人如玉,步屧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 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可人”对着悠悠的碧空出神,那冷冷如秋月 般的眼神,是内心孤寂的说明。论“高古”,他描绘道: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宜然空踪。月出东斗,好 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 一个身历人间浩劫的人,在清风明月之夜,呆在太华之巅,默然地 听着远处传来的山寺钟声,其清冷孤寂之情,可以料知。论“典雅”, 他说: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如此良辰美景,而淡泊如菊之人竟典雅到面对落花默默无言。其 心灰意冷的神态,也可以想见。此外: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旷达》) 语不涉难,已不堪忧。(《含蓄》) 百岁如流,富贵冷灰。(《悲慨》) 人生苦多乐少,富贵化为冷灰,这是逃避现实的超人的伤心处。 司空图逃避到王官谷中,他的生活境界正是这样的。 总之,逃避现实,游心于道,这是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所表现 出来的基本思想。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他认为构成一切风格本源的 就是“道”。这就不仅使他把各种风格说得那么玄虚、神秘,诱惑诗人 走向逃避现实的泥坑,而且也割断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血缘关系,使 文学成为与人民群众绝缘的东西。这种理论,就其根本之点说,对当

绪论029 时与现在,都是有害的。 (二)《二十四诗品》的表现方法 诗的风格不是什么抽象的、虚无缥渺的东西。作为社会意识形态 的诗,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诗人头脑中的反映。诗人所创造的形象, 乃是现实生活所孳育的果实。所谓诗的风格,必然关系着一定社会生 活的内容、诗人的思想感情、艺术修养、性格倾向等等方面。如果我们 割断了诗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不从产生诗的本源上来探索诗学上的一 切问题,那么,一切诗的现象都将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把一切诗的现 象问题只归之于作家的主观思想问题,那就必然要凭着神的意旨去说 话了。 司空图论风格,由于他以玄学思想为指导,是抽掉诗的社会现实 生活内容来谈问题的。这一来,便使人对他所谈的问题难于把握了。 它要求诗写得有“道气”,玄远超然,而他所处的时代呢,是农民起义摧 毁唐王朝统治的时代。以这样有火、有血、有饥寒、有斗争的时代生活 内容入诗,在他看来,是很不超然的。于是,不得已,他只好从心造的 幻影出发,一面描绘幻觉中的自然,一面描绘幻觉中的畸人、幽人、高 人之类的行径,来表达他论诗的玄学思想。他既要“超以象外”,而又 不能太上无情,还要写《二十四诗品》,那就只好谈什么“落花无言,人 淡如菊”,“幽人空山,过水采巅”,“晴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 客听琴”,“太华夜碧,人闻清钟”,等等。超脱确是超脱了,只是他的诗 的风格论也就变成了诗的玄学论。不管是雄浑、冲淡的风格也好,还 是绮丽、纤秾的风格也好,在他看来,这都是道的“离形得似”,与现实 无关。而道又是“超超神明,返返冥无”的东西。显然,照他的说法,诗 人要描绘什么样的意境,要具有什么样的风格,就只能听凭上帝的恩 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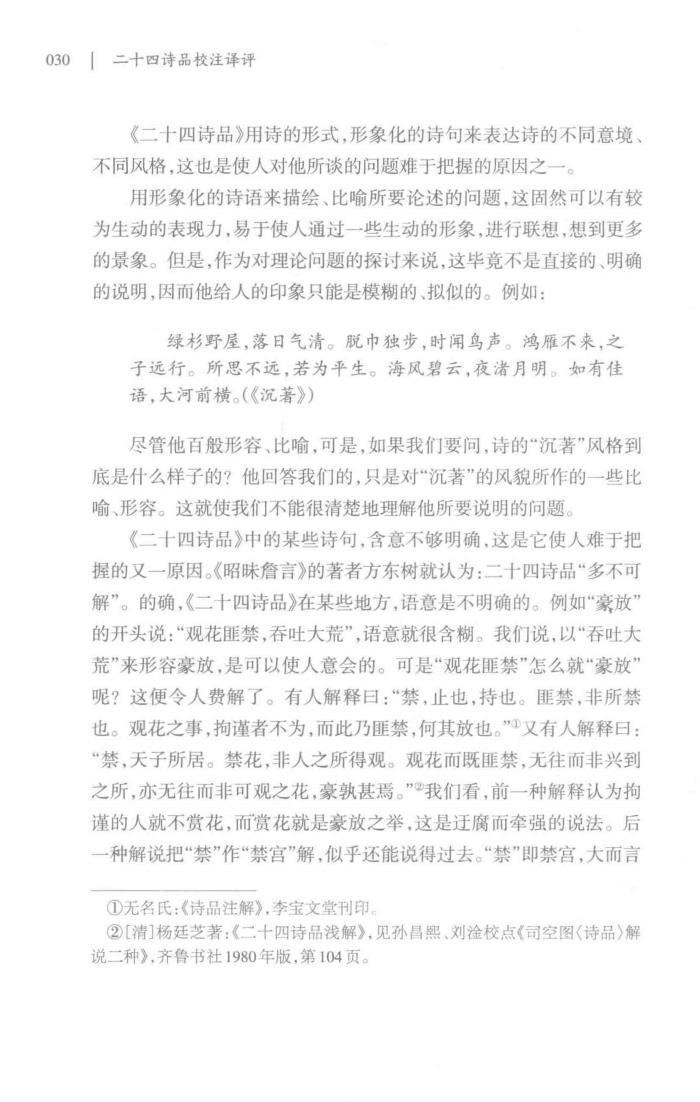
030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 《二十四诗品》用诗的形式,形象化的诗句来表达诗的不同意境、 不同风格,这也是使人对他所谈的问题难于把握的原因之一。 用形象化的诗语来描绘、比喻所要论述的问题,这固然可以有较 为生动的表现力,易于使人通过一些生动的形象,进行联想,想到更多 的景象。但是,作为对理论问题的探讨来说,这毕竟不是直接的、明确 的说明,因而他给人的印象只能是模糊的、拟似的。例如: 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 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 语,大河前横。(《沉著》)】 尽管他百般形容、比喻,可是,如果我们要问,诗的“沉著”风格到 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回答我们的,只是对“沉著”的风貌所作的一些比 喻、形容。这就使我们不能很清楚地理解他所要说明的问题 《二十四诗品》中的某些诗句,含意不够明确,这是它使人难于把 握的又一原因。《昭昧詹言》的著者方东树就认为:二十四诗品“多不可 解”。的确,《二十四诗品》在某些地方,语意是不明确的。例如“豪放” 的开头说:“观花匪禁,吞吐大荒”,语意就很含糊。我们说,以“吞吐大 荒”来形容豪放,是可以使人意会的。可是“观花匪禁”怎么就“豪放” 呢?这便令人费解了。有人解释日:“禁,止也,持也。匪禁,非所禁 也。观花之事,拘谨者不为,而此乃匪禁,何其放也。”①又有人解释日: “禁,天子所居。禁花,非人之所得观。观花而既匪禁,无往而非兴到 之所,亦无往而非可观之花,豪孰甚焉。”我们看,前一种解释认为拘 谨的人就不赏花,而赏花就是豪放之举,这是迂腐而牵强的说法。后 种解说把“禁”作“禁宫”解,似乎还能说得过去。“禁”即禁宫,大而言 ①无名氏:《诗品注解》,李宝文堂刊印 ②[清]杨廷芝著:《二十四诗品浅解》,见孙昌熙、刘淦校点《司空图(诗品)解 说二种》,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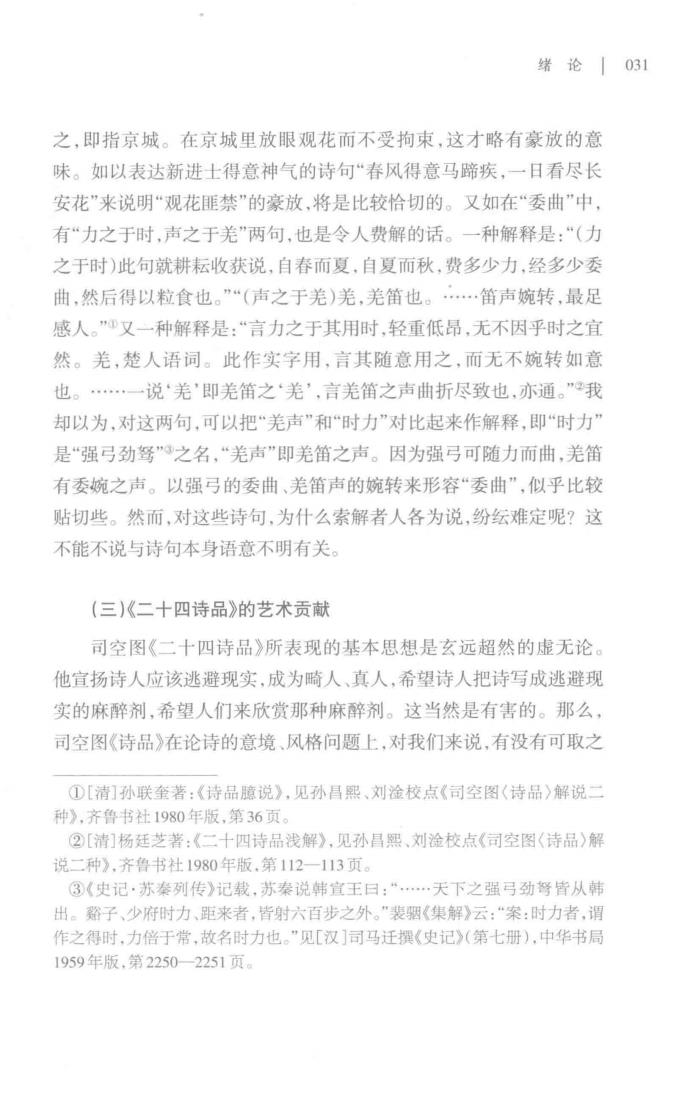
绪论「 031 之,即指京城。在京城里放眼观花而不受拘束,这才略有豪放的意 味。如以表达新进士得意神气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 安花”来说明“观花匪禁”的豪放,将是比较恰切的。又如在“委曲”中, 有“力之于时,声之于羌”两句,也是令人费解的话。一种解释是:“(力 之于时)此句就耕耘收获说,自春而夏,自夏而秋,费多少力,经多少委 曲,然后得以粒食也。”“(声之于羌)羌,羌笛也。…笛声婉转,最足 感人。”心又一种解释是:“言力之于其用时,轻重低昂,无不因乎时之宜 然。羌,楚人语词。此作实字用,言其随意用之,而无不婉转如意 也。…一说羌'即羌笛之羌’,言羌笛之声曲折尽致也,亦通。”我 却以为,对这两句,可以把“羌声”和“时力”对比起来作解释,即“时力” 是“强弓劲驽”之名,“羌声”即羌笛之声。因为强弓可随力而曲,羌笛 有委婉之声。以强弓的委曲、羌笛声的婉转来形容“委曲”,似乎比较 贴切些。然而,对这些诗句,为什么索解者人各为说,纷纭难定呢?这 不能不说与诗句本身语意不明有关。 (三)《二十四诗品》的艺术贡献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表现的基本思想是玄远超然的虚无论。 他宣扬诗人应该逃避现实,成为畸人、真人,希望诗人把诗写成逃避现 实的麻醉剂,希望人们来欣赏那种麻醉剂。这当然是有害的。那么, 司空图《诗品》在论诗的意境、风格问题上,对我们来说,有没有可取之 ①[清]孙联奎著:《诗品臆说》,见孙昌熙、刘淦校点《司空图(诗品〉解说二 种》,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6页。 ②[清]杨廷芝著:《二十四诗品浅解》,见孙昌熙、刘淦校点《司空图〈诗品)解 说二种》,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12一113页。 ③《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说韩宣王曰:“…天下之强马劲弩皆从韩 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裴驷《集解》云:“案:时力者,谓 作之得时,力倍于常,故名时力也。”见[汉]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中华书局 1959年版,第2250一22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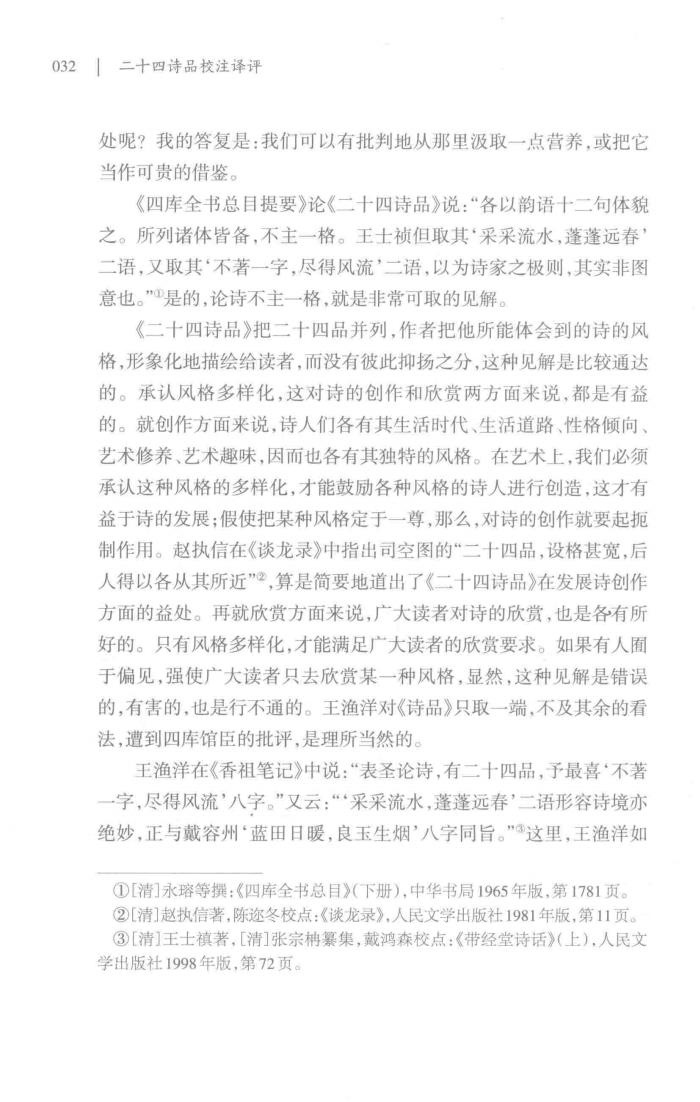
032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 处呢?我的答复是:我们可以有批判地从那里汲取一点营养,或把它 当作可贵的借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二十四诗品》说:“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 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王士祯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远春 二语,又取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语,以为诗家之极则,其实非图 意也。”是的,论诗不主一格,就是非常可取的见解。 《二十四诗品》把二十四品并列,作者把他所能体会到的诗的风 格,形象化地描绘给读者,而没有彼此抑扬之分,这种见解是比较通达 的。承认风格多样化,这对诗的创作和欣赏两方面来说,都是有益 的。就创作方面来说,诗人们各有其生活时代、生活道路、性格倾向 艺术修养、艺术趣味,因而也各有其独特的风格。在艺术上,我们必须 承认这种风格的多样化,才能鼓励各种风格的诗人进行创造,这才有 益于诗的发展;假使把某种风格定于一尊,那么,对诗的创作就要起扼 制作用。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指出司空图的“二十四品,设格甚宽,后 人得以各从其所近”2,算是简要地道出了《二十四诗品》在发展诗创作 方面的益处。再就欣赏方面来说,广大读者对诗的欣赏,也是各有所 好的。只有风格多样化,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欣赏要求。如果有人囿 于偏见,强使广大读者只去欣赏某一种风格,显然,这种见解是错误 的,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王渔洋对《诗品》只取一端,不及其余的看 法,遭到四库馆臣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王渔洋在《香祖笔记》中说:“表圣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 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境亦 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这里,王渔洋如 ①[清]永溶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81页。 ②[清]赵执信著,陈迩冬校点:《谈龙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③[清]王士稹著,[清]张宗神纂集,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上),人民文 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