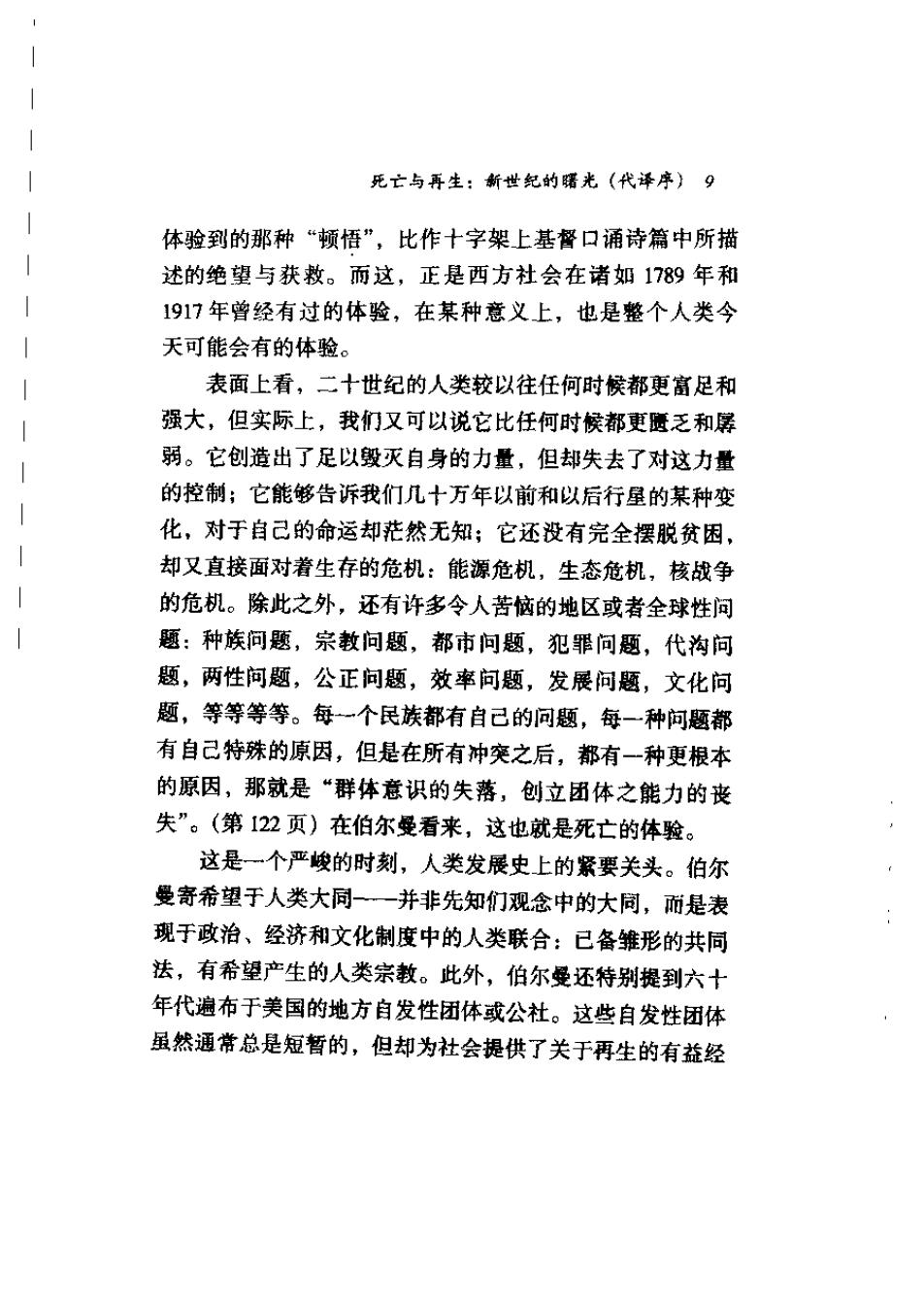
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代译序)9 体验到的那种“顿悟”,比作十字架上基督口诵诗篇中所描 述的绝望与获救。而这,正是西方社会在诸如1789年和 1917年曾经有过的体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人类今 天可能会有的体验。 表面上看,二十世纪的人类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足和 强大,但实际上,我们又可以说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匮乏和孱 弱。它创造出了足以毁灭自身的力量,但却失去了对这力量 的控制;它能够告诉我们几十万年以前和以后行星的某种变 化,对于自己的命运却茫然无知;它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 却又直接面对着生存的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核战争 的危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令人苦恼的地区或者全球性问 题:种族问题,宗教问题,都市问题,犯罪问题,代沟问 题,两性问题,公正问题,效率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 题,等等等等。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一种问题都 有自己特殊的原因,但是在所有冲突之后,都有-一种更根本 的原因,那就是“群体意识的失落,创立团体之能力的丧 失”。(第122页)在伯尔曼看来,这也就是死亡的体验。 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人类发展史上的紧要关头。伯尔 曼寄希望于人类大同一一并非先知们观念中的大同,而是表 现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中的人类联合:已备维形的共同 法,有希望产生的人类宗教。此外,伯尔曼还待别提到六十 年代遍布于美国的地方自发性团体或公社。这些自发性团体 虽然通常总是短暂的,但却为社会提供了关于再生的有益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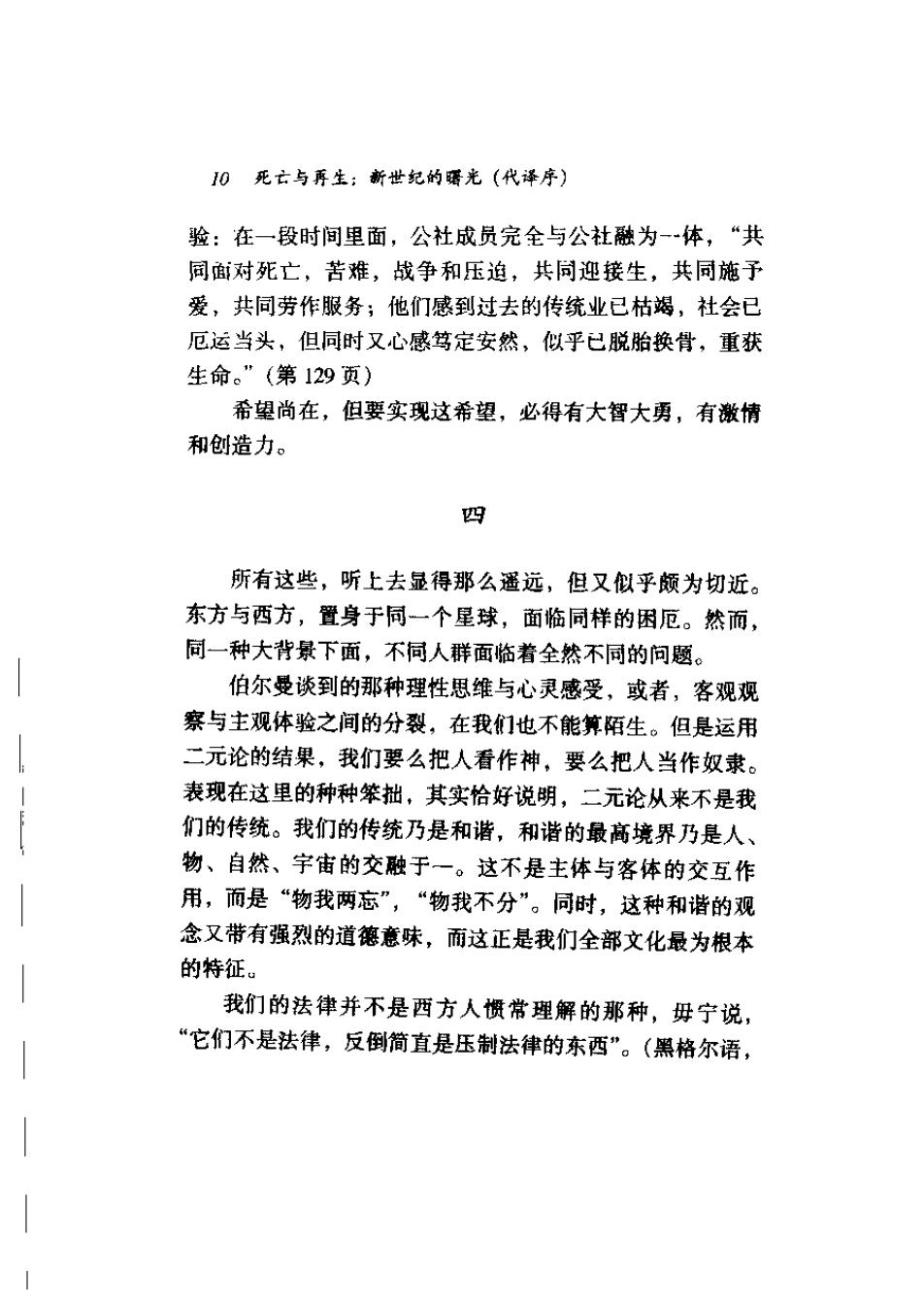
0死亡与再生;斯新世纪的婚光(代译序) 验:在一段时间里面,公社成员完全与公社融为-一体,“共 同面对死亡,苦摊,战争和压迫,共同迎接生,共同施予 爱,共同劳作服务;他们感到过去的传统业已枯竭,社会已 厄运当头,但同时又心感笃定安然,似乎已脱胎换骨,重获 生命。”(第129页) 希望尚在,但要实现这希望,必得有大智大勇,有激情 和创造力。 所有这些,听上去显得那么遥远,但又似乎领为切近。 东方与西方,置身于同一个星球,面临同样的困厄。然而, 同一种大背景下面,不同人群面临着全然不同的问题。 伯尔曼谈到的那种理性思维与心灵感受,或者,客观观 察与主观体验之间的分裂,在我们也不能算陌生。但是运用 二元论的结果,我们要么把人看作神,要么把人当作奴隶。 表现在这里的种种笨拙,其实恰好说明,二元论从来不是我 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乃是和谐,和谐的最高境界乃是人、 物、自然、字宙的交融于一。这不是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 用,而是“物我两忘”,“物我不分”。同时,这种和谐的观 念又带有强烈的道德意味,而这正是我们全部文化最为根本 的特征。 我们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那种,毋宁说, “它们不是法律,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东西”。(黑格尔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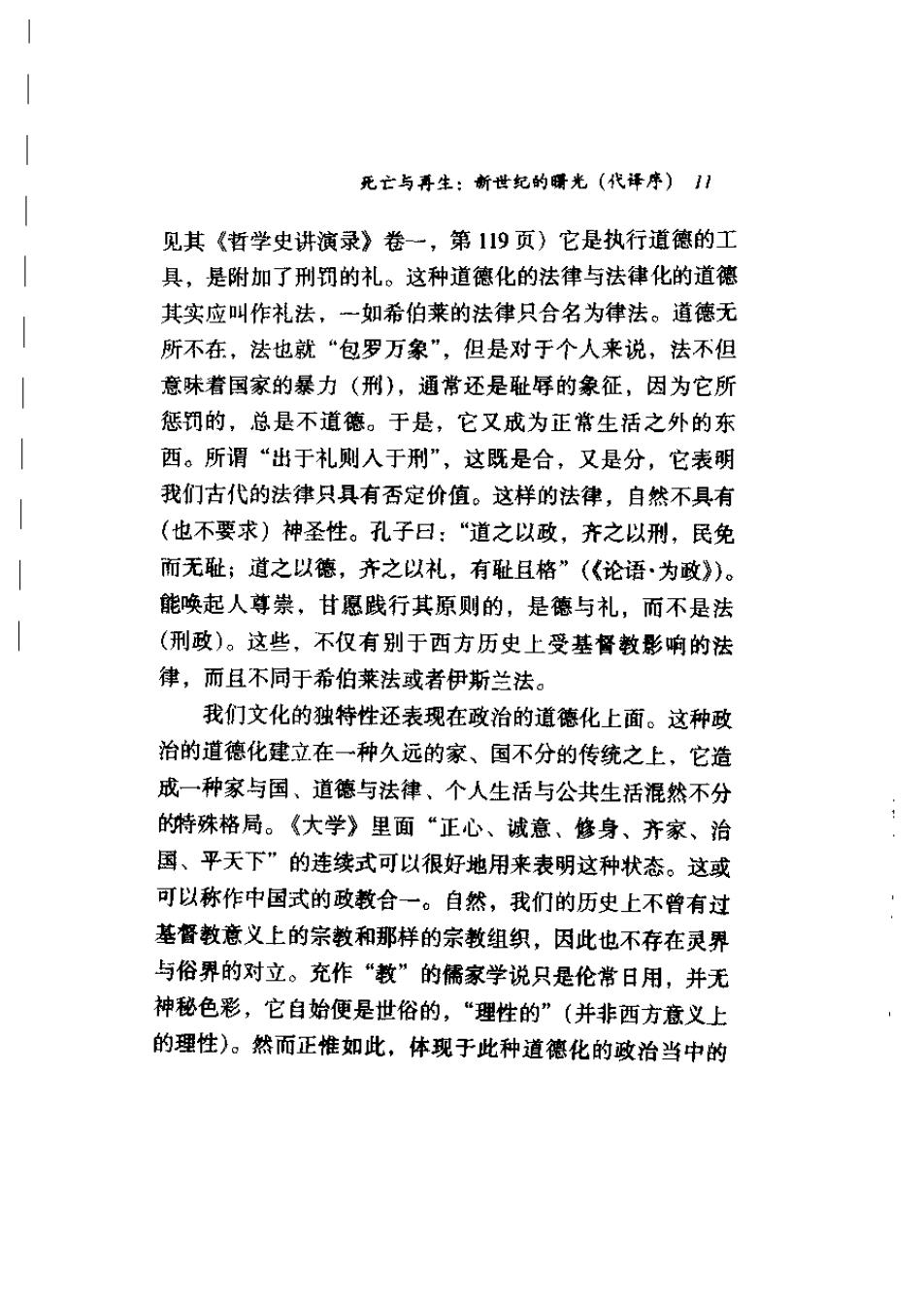
死亡与荐生:新世纪的嚼光(代译序)1? 见其《哲学史讲演录》卷一,第119页)它是执行道德的工 具,是附加了刑罚的礼。这种道德化的法律与法律化的道德 其实应叫作礼法,一如希伯莱的法律只合名为律法。道德无 所不在,法也就“包罗万象”,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法不但 意味着国家的暴力(刑),通常还是耻辱的象征,因为它所 惩罚的,总是不道德。于是,它又成为正常生活之外的东 西。所谓“出于礼则入于刑”,这既是合,又是分,它表明 我们古代的法律只具有否定价值。这样的法律,自然不具有 (也不要求)神圣性。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 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能唤起人尊崇,甘愿践行其原则的,是德与礼,而不是法 (刑政)。这些,不仅有别于西方历史上受基督教影响的法 律,而且不同于希伯莱法或者伊斯兰法。 我们文化的独特性还表现在政治的道德化上面。这种政 治的道德化建立在一种久远的家、国不分的传统之上,它造 成一种家与国、道德与法律、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混然不分 的特殊格局。《大学》里面“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连续式可以很好地用来表明这种状态。这或 可以称作中国式的政救合一。自然,我们的历史上不管有过 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和那样的宗教组织,因此也不存在灵界 与俗界的对立。充作“教”的儒家学说只是伦常日用,并无 神秘色彩,它自始便是世俗的,“理性的”(并非西方意义上 的理性)。然而正椎如此,体现于此种道德化的政治当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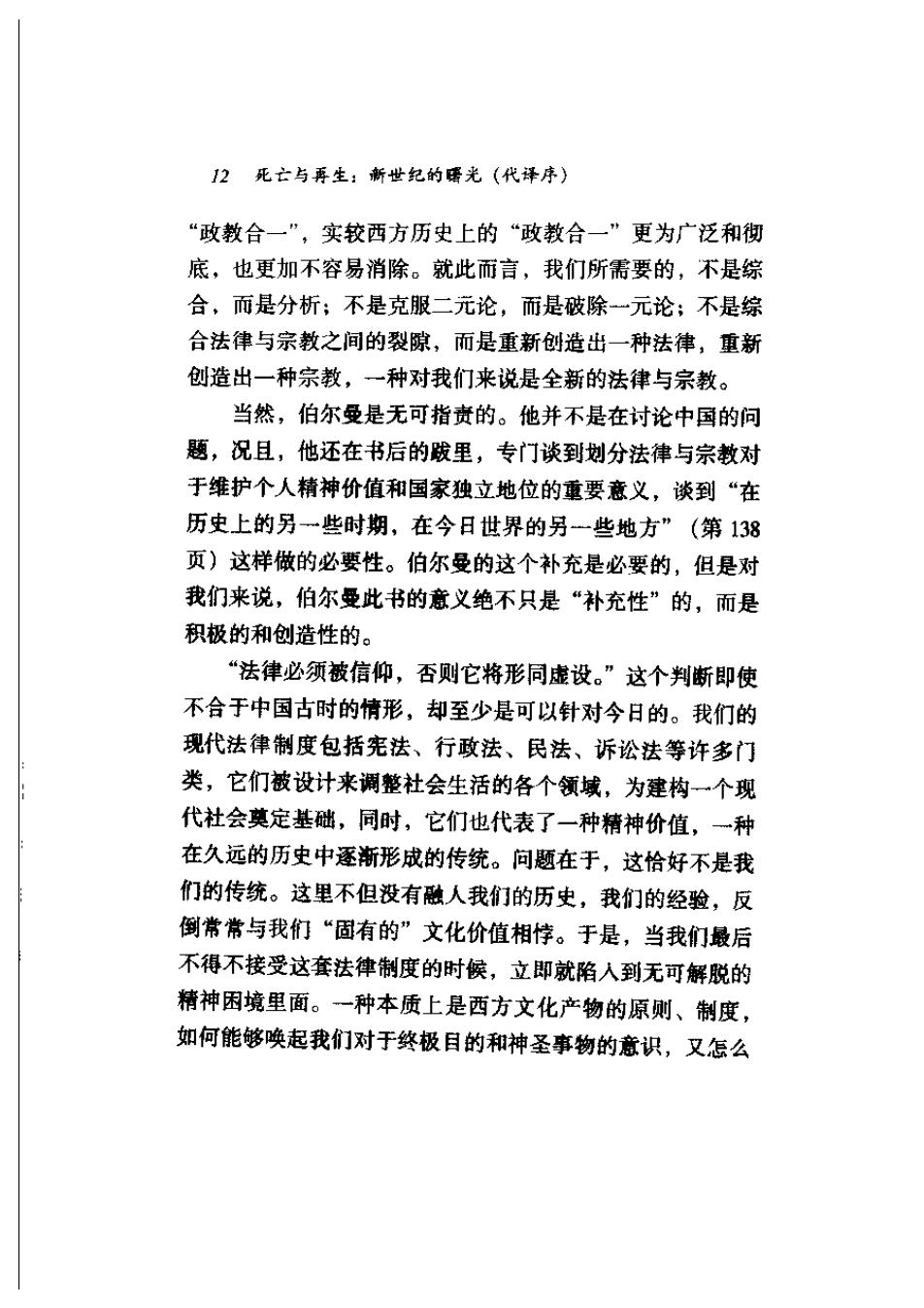
12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代评序】 “政教合一”,实较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更为广泛和彻 底,也更加不容易消除。就此而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综 合,而是分析;不是克服二元论,而是破除一元论;不是综 合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裂隙,而是重新创造出一种法律,重新 创造出一种宗教,一种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法律与宗教。 当然,伯尔曼是无可指责的。他并不是在讨论中国的问 题,况且,他还在书后的跋里,专门谈到划分法律与宗教对 于维护个人精神价值和国家独立地位的重要意义,谈到“在 历史上的另一些时期,在今日世界的另一些地方”(第138 页)这样做的必要性。伯尔曼的这个补充是必要的,但是对 我们来说,伯尔曼此书的意义绝不只是“补充性”的,而是 积极的和创造性的。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个判断即使 不合于中国古时的情形,却至少是可以针对今日的。我们的 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 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 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 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 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 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 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 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 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

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代译序)13 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 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 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尊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 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人。这样的困境不是比西方人面临 的危机更难以摆脱吗?这也是一种死亡的征兆,其真实性与 严重性绝不在后者之下。 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侵人,我们历史的进程 改变了。我们被迫接受西方的事物,从生产技术,一直到西 方人的基本价值。在这种强有力的挑战面前,传统的文化格 局分崩离析,这是较伯尔曼书中所谓法律与宗教之间纽带的 断裂更为严重的事件,也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 震荡。生存的问题被提出来了,有时是以物质的方式,有时 是以精神的方式。前者表现在诸如甲午海战一败所引发的举 国震惊,或者日寇人侵带来的亡国亡种的危机里面,后者表 现在五·四以来的历次文化大论战当中。我们应当这样来认 识近代以来的文化论战,因为所谓文化传统不仅代表着一个 民族的过去,而且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核心。文化 的解体意味着死亡,文化的抗争实即是生存的抗争。这正是 一种死亡的体验,而我们至今仍未脱此死亡之境。这即是八 十年代提出新的现代化方案(“保留球籍”问题)和重开文 化讨论(改造和保存文化)的根本缘由。 社会也象个人一样具有求生的本能,但是处在今天这样 的特殊情境里面,仅仅依靠本能是不够的。历史不曾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