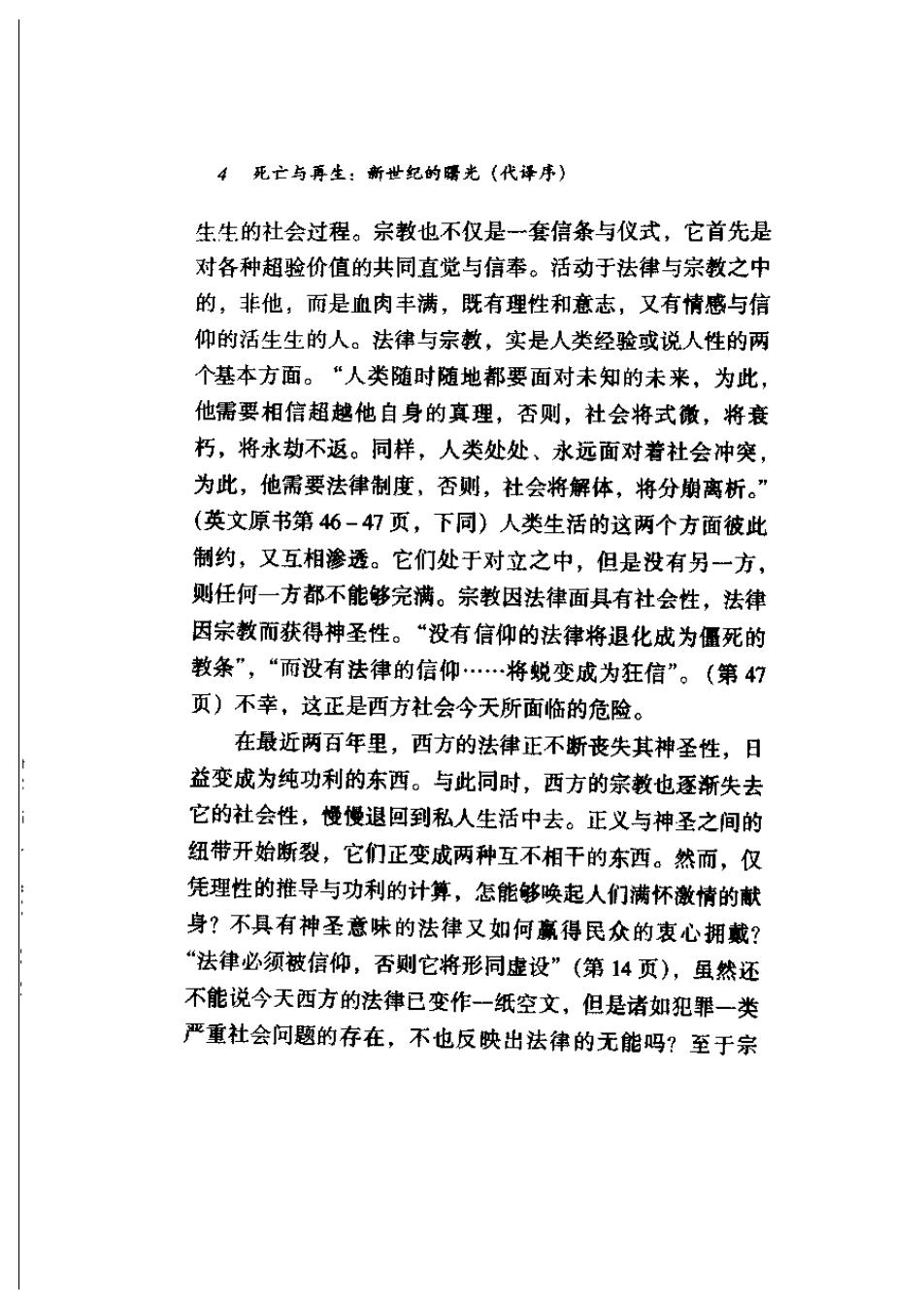
4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质光(代译序) 生生的杜会过程。宗教也不仅是-一套信条与仪式,它首先是 对各种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与信奉。活动于法律与宗教之中 的,非他,而是血肉丰满,既有理性和意志,又有情感与信 仰的活生生的人。法律与宗教,实是人类经验或说人性的两 个基本方面。“人类随时随地都要面对未知的未来,为此, 他需要相信超越他自身的真理,否则,社会将式徽,将衰 朽,将永劫不返。同样,人类处处、永远面对着社会冲突, 为此,他需要法律制度,否则,社会将解体,将分崩离析。” (英文原书第46-47页,下同)人类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彼此 制约,又互相渗透。它们处于对立之中,但是没有另一方, 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完满。宗教因法律面具有社会性,法律 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循死的 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第47 页)不幸,这正是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危险。 在最近两百年里,西方的法律正不断丧失其神圣性,日 益变成为纯功利的东西。与此同时,西方的宗教也逐渐失去 它的社会性,慢慢退回到私人生活中去。正义与神圣之间的 纽带开始断裂,它们正变成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然而,仅 凭理性的推导与功利的计算,怎能够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 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如何赢得民众的衷心拥戴?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第14页),虽然还 不能说今天西方的法律已变作一纸空文,但是诸如罪一类 严重社会问题的存在,不也反映出法律的无能吗?至于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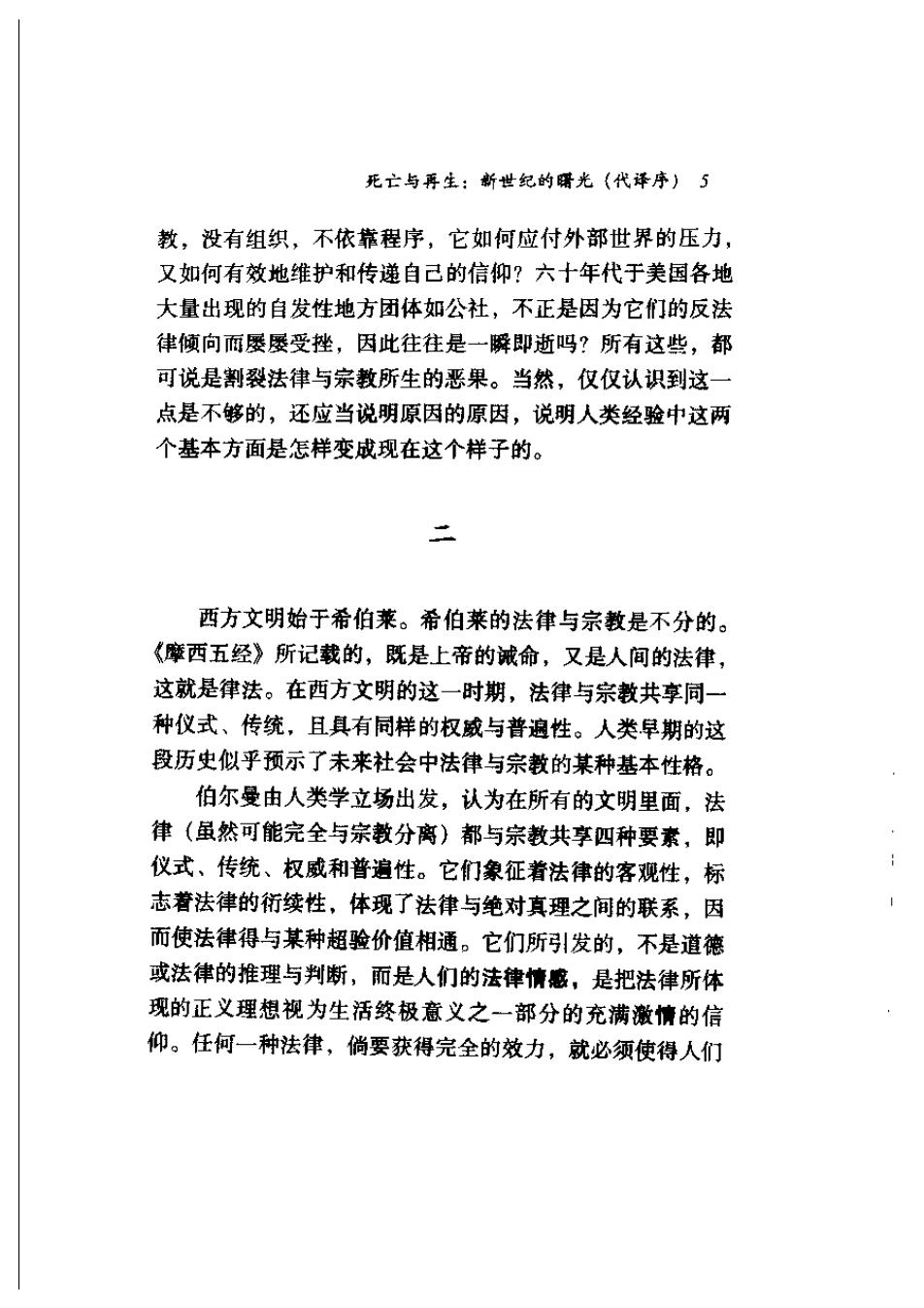
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代译序)5 教,没有组织,不依靠程序,它如何应付外部世界的压力, 又如何有效地维护和传递自己的信抑?六十年代于美国各地 大量出现的自发性地方团体如公社,不正是因为它们的反法 律倾向而屡屡受挫,因此往往是一瞬即逝吗?所有这些,都 可说是割裂法律与宗教所生的恶果。当然,仅仅认识到这一 点是不够的,还应当说明原因的原因,说明人类经验中这两 个基本方面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二 西方文明始于希伯莱。希伯莱的法律与宗教是不分的。 《摩西五经》所记载的,既是上帝的诫命,又是人间的法律, 这就是律法。在西方文明的这一时期,法律与宗教共享同一 种仪式、传统,且具有同样的权威与普遍性。人类早期的这 段历史似乎预示了未来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某种基本性格。 伯尔曼由人类学立场出发,认为在所有的文明里面,法 律(虽然可能完全与宗教分离)都与宗教共享四种要素,即 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它们象征着法律的客观性,标 志着法律的衍续性,体现了法律与绝对真理之间的联系,因 而使法律得与某种超验价值相通。它们所引发的,不是道德 或法律的推理与判断,而是人们的法律情感,是把法律所体 现的正义理想视为生活终极意义之一部分的充满激情的信 仰。任何一种法律,徜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得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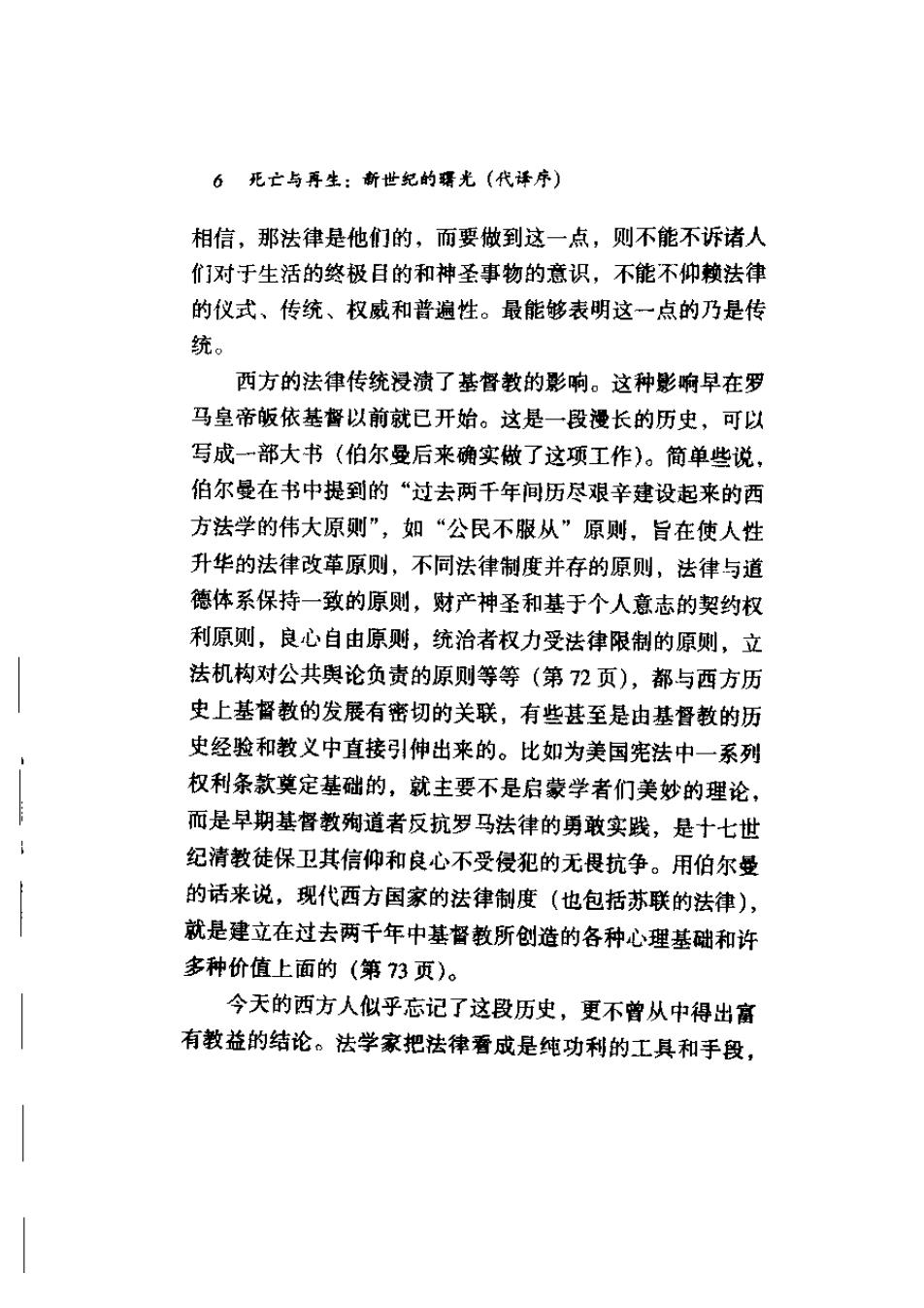
6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籍光(代语序) 相信,那法律是他们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则不能不诉诸人 ]对于生活的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不能不仰赖法律 的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最能够表明这一点的乃是传 统。 西方的法律传统浸渍了基督教的影响。这种影响早在罗 马皇帝皈依基督以前就已开始。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可以 写成一部大书(伯尔曼后来确实做了这项工作)。简单些说, 伯尔曼在书中提到的“过去两千年间历尽艰辛建设起来的西 方法学的伟大原测”,如“公民不服从”原则,旨在使人性 升华的法律改革原则,不同法律制度并存的原则,法律与道 德体系保持一致的原则,财产神圣和基于个人意志的契约权 利原则,良心自由原则,统治者权力受法律限制的原则,立 法机构对公共舆论负责的原则等等(第72页),都与西方历 史上基督教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有些甚至是由基督教的历 史经验和教义中直接引伸出来的。比如为美国宪法中一系列 权利条款奠定基础的,就主要不是启蒙学者们美妙的理论 而是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反抗罗马法律的勇敢实践,是十七世 纪清教徒保卫其信仰和良心不受侵犯的无畏抗争。用伯尔曼 的话来说,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包括苏联的法律), 就是建立在过去两千年中基督教所创造的各种心理基础和许 多种价值上面的(第3页)。 今天的西方人似乎忘记了这段历史,更不曾从中得出富 有教益的结论。法学家把法律看成是纯功利的工具和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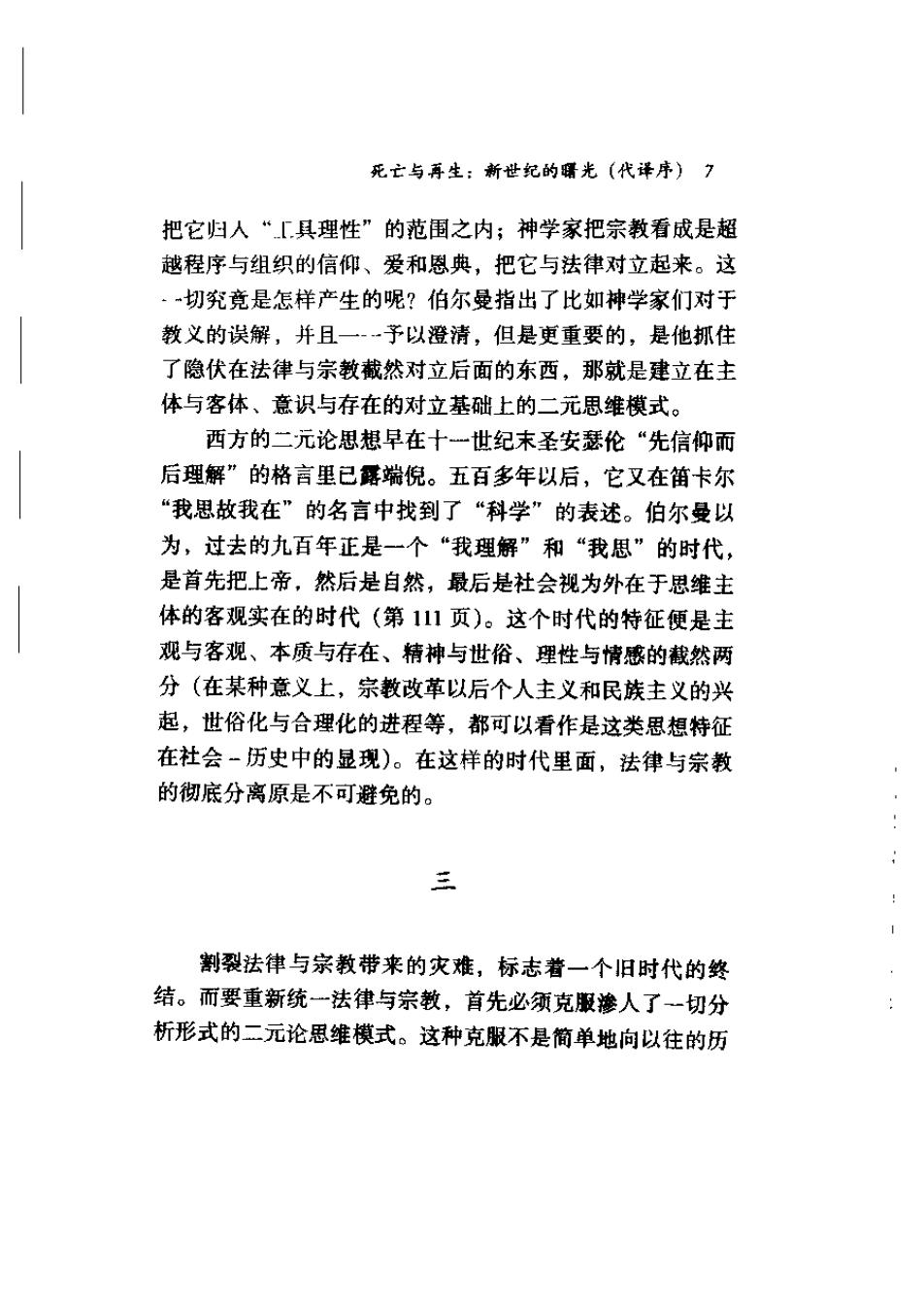
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光(代译序)7 把它归人“[具理性”的范围之内;神学家把宗教看成是超 越程序与组织的信仰、爱和恩典,把它与法律对立起来。这 ·一切究竞是怎样产生的呢?伯尔曼指出了比如神学家们对于 教义的误解,并且一予以澄清,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抓住 了隐伏在法律与宗教截然对立后面的东西,那就是建立在主 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的对立基础上的二元思维模式。 西方的二元论思想早在十一世纪末圣安瑟伦“先信仰而 后理解”的格言里已露端倪。五百多年以后,它又在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名言中找到了“科学”的表述。伯尔曼以 为,过去的九百年正是一个“我理解”和“我思”的时代, 是首先把上帝,然后是自然,最后是社会视为外在于思维主 体的客观实在的时代(第111页)。这个时代的特征便是主 观与客观、本质与存在、精神与世俗、理性与情感的截然两 分(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改革以后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 起,世俗化与合理化的进程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类思想特征 在社会一历史中的显现)。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法律与宗教 的彻底分离原是不可避免的。 割裂法律与宗教带来的灾摊,标志著一个旧时代的终 结。而要重新统一法律与宗教,首先必须克服滲人了一切分 析形式的二元论思维模式。这种克服不是简单地向以往的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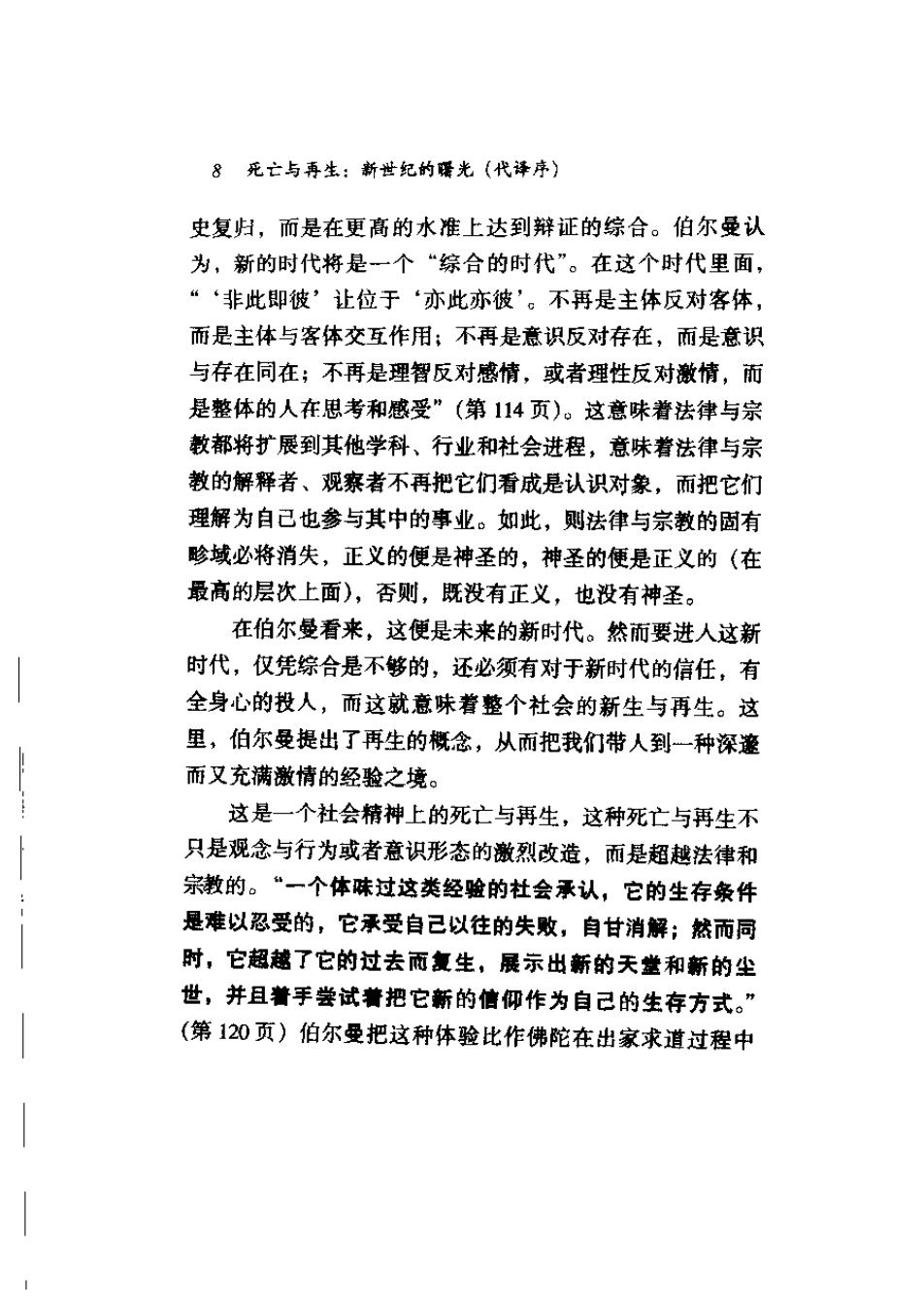
8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腰光(代译序】 史复归,而是在更高的水准上达到辩证的综合。伯尔曼认 为,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 “‘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 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 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感情,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 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受”(第114页)。这意味着法律与宗 教都将扩展到其他学科、行业和社会进程,意味着法律与宗 教的解释者、观寮者不再把它们看成是认识对象,而把它们 理解为自己也参与其中的事业。如此,则法律与宗教的固有 畛域必将消失,正义的便是神圣的,神圣的便是正义的(在 最高的层次上面),否则,既没有正义,也没有神圣。 在伯尔曼看来,这便是未来的新时代。然而要进人这新 时代,仅凭综合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于新时代的信任,有 全身心的投人,而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新生与再生。这 里,伯尔曼提出了再生的概念,从而把我们带人到一种深邃 而又充满激情的经验之境。 这是一个社会精神上的死亡与再生,这种死亡与再生不 只是观念与行为或者意识形态的激烈改造,而是超越法律和 宗教的。“一个体味过这类经验的杜会承认,它的生存条件 是难以忍受的,它承受自己以往的失败,自甘消解;然而同 时,它超越了它的过去而复生,展示出新的天堂和新的尘 世,并且着手尝试普把它新的信仰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 (第120页)伯尔曼把这种体验比作佛陀在出家求道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