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订版评者前言11 者的角色,而把这些问题留与后人思考和解答。作为一个历 史的预言者,他在展现我们过去的同时,更把眼光投向未 来。他将希望寄托于来者。 现在要说到有关译稿修订的事情。 本书的翻译完成于187年,现在对照原文仔细再读十 六年前的译文,不禁为其中的错误汗颜。于是据英文原书逐 字逐句校改,结果几乎将原稿重译。现在的译稿虽不敢保证 无一疵,总算差强人意。 本书增订的完成得益于多方的慷慨相助。首先要感谢原 书作者伯尔曼教授。十六年前,他手书数札,用一种原始但 富人情味的沟通方式回答一个年轻译者的无知问题,其耐心 与慷慨令我至今不能忘怀。这次他一如既往,慷慨答允有关 版权授权的请求,并应所请推荐增订文章一篇并惠寄原书, 使眼下的这个新版成为可能。 当年,还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陈维钢教授曾帮助我解决了 不少翻译中的问题,因而改善了译文质量。这一次,香港大 学哲学系的慈继伟教授校读了本书第一章,指出了其中的若 干错误,予我帮助良多。当然,也像当初一样,译文中所有 错讹与不当,仍由我个人负责。此外,香港大学法学院的陈 弘毅教授为我提供了Faith and Order一书;《二十一世纪》 编辑部慷慨地允许我将刊登于该刊1999年4月号的对伯尔 曼教授的专访收人本书附录。谨此致谢

12增订版译者前言 我还要提到来自母亲的意想不到的帮助,她因为勒读 《圣经》,所以毫不费力就帮我找出了新增译文中两处经文的 出处。对她来说,我相信,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报偿。 最后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他们在这样 本小书上花费的精力多半超出读者们的想象,而他们的敬业 和效率总是令我印象深刻。 梁治平 2003年6月3日于北京万寿寺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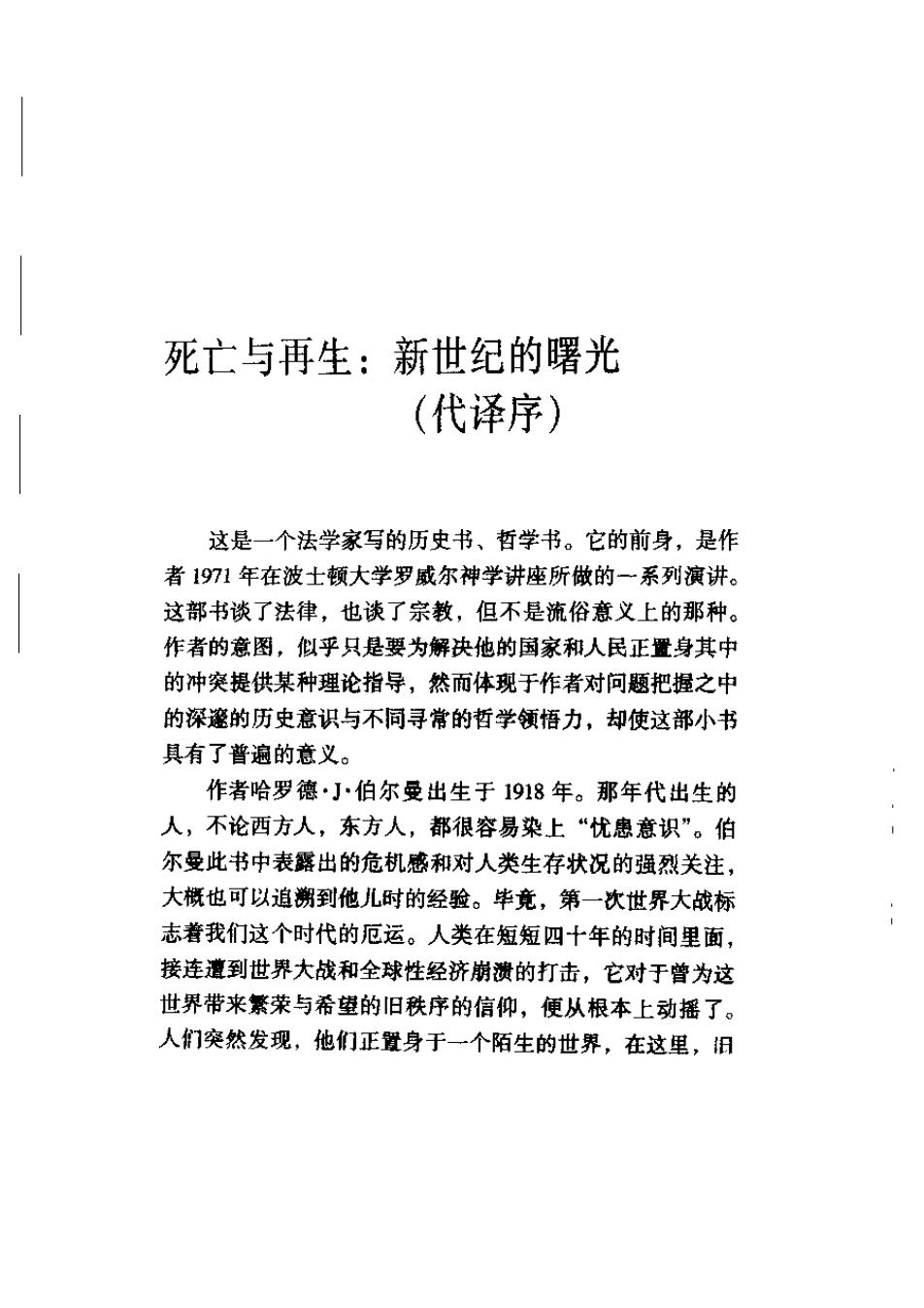
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 (代译序) 这是一个法学家写的历史书、哲学书。它的前身,是作 者1971年在波士顿大学罗威尔神学讲座所做的一系列演讲。 这部书谈了法律,也谈了宗教,但不是流俗意义上的那种。 作者的意图,似乎只是要为解决他的国家和人民正置身其中 的冲突提供某种理论指导,然而体现于作者对问题把握之中 的深邃的历史意识与不同寻常的哲学领悟力,却使这部小书 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作者哈罗德J小伯尔曼出生于1918年。那年代出生的 人,不论西方人,东方人,都很容易染上“忧患意识”。伯 尔曼此书中表露出的危机感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通烈关注, 大概也可以追潮到他儿时的经验。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标 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厄运。人类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面, 接连遭到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经济崩遗的打击,它对于曾为这 世界带来繁荣与希望的旧秩序的信仰,便从根本上动摇了。 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正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里,阳

2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代译序) 日里熟知的信念意义尽失,即便理性本身也已变得可疑,不 足信赖。未来变得不可捉摸,当下也同样推以理解。从这 里,产生出现代人的失落、荒谬感与焦虑,产生出五、六十 年代西方世界的一系列文化思潮与社会运动。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探索的时代,其间充满 了冲突,但也不乏有益的试验和真知灼见闪烁其中的预言 书。HJ·伯尔曼这部《法律与宗教》便是其中极富洞见的 一本。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生活的意义何在?我们正去向何 方?这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宗教问题。西方人所面临的危机 正源自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困闲惑。在伯尔曼看来,这预示了 西方文化行将崩遗的暗淡前景。而它的一个主要征兆,便是 整个社会对于法律与宗教的信仲严重地丧失。这里,法律被 看成是用以解决纷争以及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创造合作纽 带的程序,宗教则被界定为对于生活之终极意义和目的的集 体关切和献身。它们代表了人类生活中两个基本的方面,法 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 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明 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伯尔曼所说西方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 信任危机竞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代译序)3 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伯尔曼指出了其中 的一种,即在流俗见解当中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对立。这回, 伯尔曼再次表现了他观察问题的敏锐与独到。 通常认为,现代法律纯是世俗的、合理的,是用以贯彻 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工具,而与生活终极意义一类 观念无涉。在有实用主义传统的美国,这种观念尤其盛行。 比如,有人把法院的判决看成是解决问题所作的试验,甚至 把法看成是“对法院实际上将做什么的预测”。当然这只是 极端一派的理论。但就是强调法律中绝对价值的哲理一派, 它在解释法律诸基本原则的时候,也只限于提供诸如人道主 义哲学一类的说明,全不谈人的情感、信念和终极关切。在 另一方面,现代许多宗教思想派别,无论是把爱看作是对基 督徒椎一约束的“爱之神学”,还是认为基督徒应当依靠信 仰而非法律来生活的所谓“信仰神学”,或是强调神恩的唯 信仰论的一派,都表现出排斥法律的倾向。它们把法律与 爱、信仰和神恩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互相排斥。同样的立场 也反映在一些世俗的社会运动如美国的青年文化或反主流文 化集团里面。它们强调爱、自发性和激情,轻视乃至拒斥法 律一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程序与结构。 上面两种情形实际是同一种谬误的两个方面。给法律与 宗教一个过于狭隘的定义,面将它们截然对立起来,不仅大 谬不然,而且注定要摧抑人们对于法律与宗教的信任。因为 事实上,法律并不只是一套规则,它还是一种程序,一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