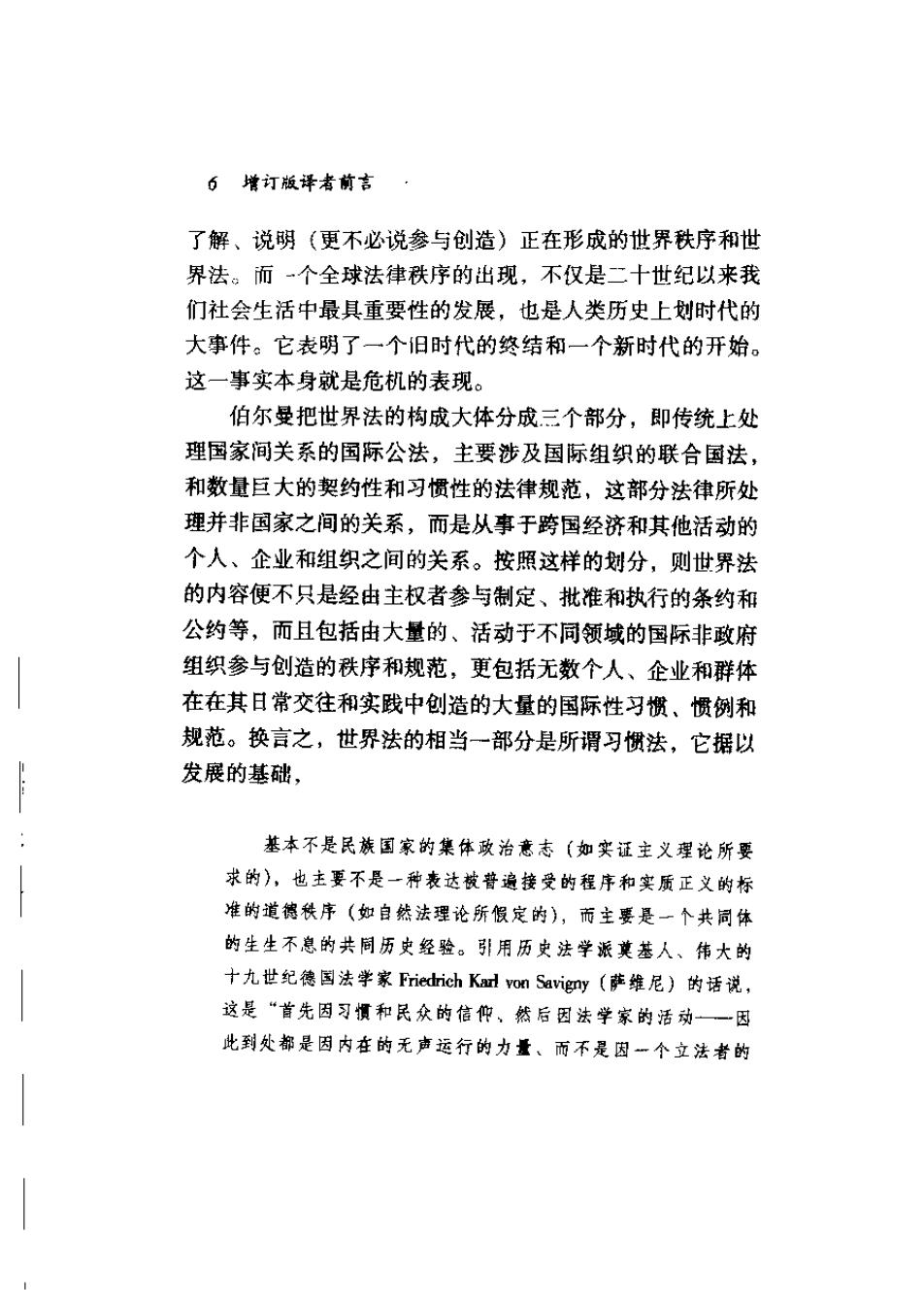
6增订版译者前言 了解、说明(更不必说参与创造)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和世 界法。而一个全球法律秩序的出现,不仅是二十世纪以来我 们社会生活中最具重要性的发展,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 大事件。它表明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危机的表现。 伯尔曼把世界法的构成大体分成三个部分,即传统上处 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公法,主要涉及国际组织的联合国法, 和数量巨大的契约性和习惯性的法律规范,这部分法律所处 理并非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事于跨国经济和其他活动的 个人、企业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按照这样的划分,则世界法 的内容便不只是经由主权者参与制定、批准和执行的条约和 公约等,而且包括由大量的、活动于不同领域的国际非政府 组织参与创造的秩序和规范,更包括无数个人、企业和群体 在在其日常交往和实践中创造的大量的国际性习惯、惯例和 规范。换言之,世界法的相当一部分是所谓习惯法,它据以 发展的基础, 基本不是民族国家的集体攻治意志(如实证主义理论所要 求的)),也主要不是一种表达被普遍接受的程序和实质正义的标 准的道德秩序(如自然法理论所假定的),而主要是一个共同体 的生生不急的共同历史经验。引用历史法学派莫叁人、伟大的 十九世纪德国法学家Friedrich K von Savigny(萨维尼)的话说. 这是“首先因习惯和民众的信仲、然后因法学家的活动一因 此到处都是因内在的无声运行的力量、而不是因一个立法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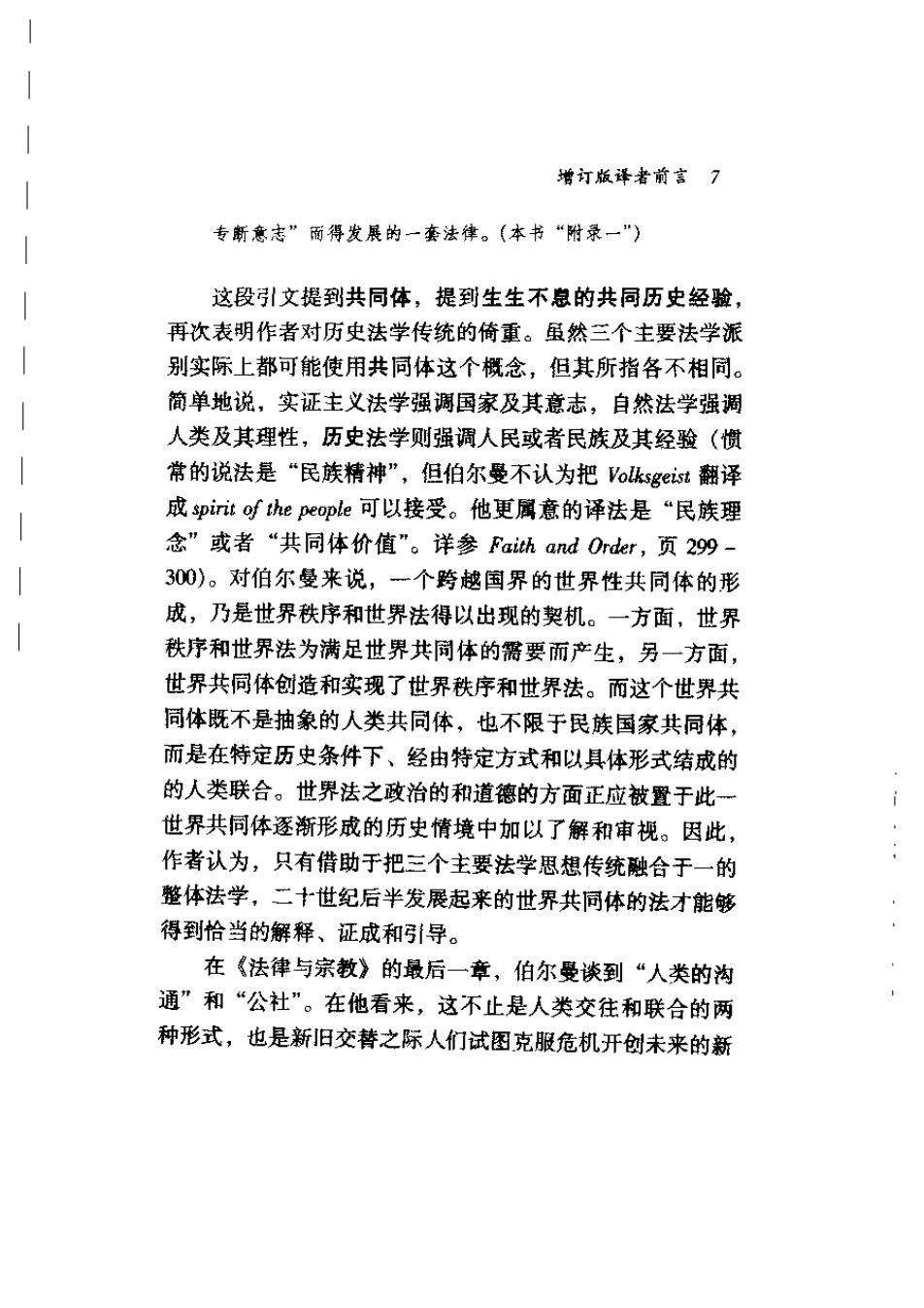
增订版译者前言7 专新意志”面得发展的一套法律。(本书“附录一”) 这段引文提到共同体,提到生生不总的共同历史经验」 再次表明作者对历史法学传统的倚重。虽然三个主要法学派 别实际上都可能使用共同体这个概念,但其所指各不相同。 简单地说,实证主义法学强调国家及其意志,自然法学强涸 人类及其理性,历史法学则强调人民或者民族及其经验(惯 常的说法是“民族精神”,但伯尔曼不认为把Volksgeist翻译 成spirit of the people可以接受。他更属意的译法是“民族理 念”或者“共同体价值”。详参Faith and Order,页29- 00)。对伯尔曼来说,一个跨越国界的世界性共同体的形 成,乃是世界秩序和世界法得以出现的契机。一方面,世界 秩序和世界法为满足世界共同体的需要而产生,另一方面, 世界共同体创造和实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法。而这个世界共 同体既不是抽象的人类共同体,也不限于民族国家共同体 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由特定方式和以具体形式结成的 的人类联合。世界法之政治的和道德的方面正应被置于此 世界共同体逐渐形戒的历史情境中加以了解和审视。因此, 作者认为,只有借助于把三个主要法学思想传统融合于一的 整体法学,二十世纪后半发展起来的世界共同体的法才能够 得到恰当的解释、证成和引导。 在《法律与宗教》的最后一章,伯尔曼谈到“人类的沟 通”和“公社”。在他看来,这不止是人类交往和联合的两 种形式,也是新旧交替之际人们试图克服危机开创未来的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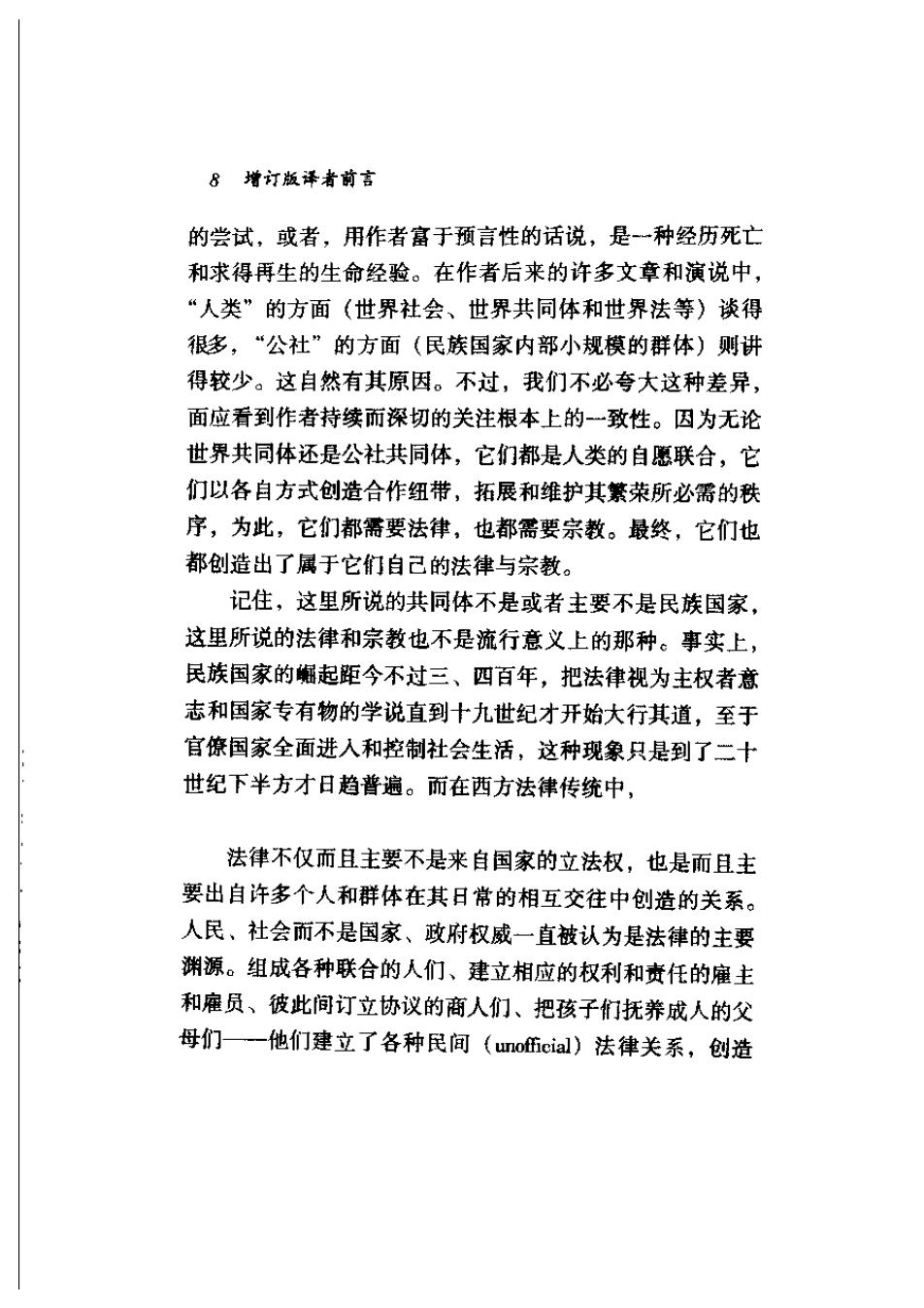
8增订版译者前言 的尝试,或者,用作者富于预言性的话说,是一种经历死亡 和求得再生的生命经验。在作者后来的许多文章和演说中, “人类”的方面(世界社会、世界共同体和世界法等)谈得 很多,“公社”的方面(民族国家内部小规模的群体)则讲 得较少。这自然有其原因。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种差异 面应看到作者持续而深切的关注根本上的一致性。因为无论 世界共同体还是公社共同体,它们都是人类的自愿联合,它 们以各自方式创造合作纽带,拓展和维护其繁荣所必需的秩 序,为此,它们都需要法律,也都需要宗教。最终,它们也 都创造出了属于它们自己的法律与宗教。 记住,这里所说的共同体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民族国家, 这里所说的法律和宗教也不是流行意义上的那种。事实上, 民族国家的崛起距今不过三、四百年,把法律视为主权者意 志和国家专有物的学说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大行其道,至于 官僚国家全面进入和控制社会生活,这种现象只是到了二十 世纪下半方才日趋普遍。而在西方法律传统中, 法律不仅而且主要不是来自国家的立法权,也是而且主 要出自许多个人和群体在其日常的相互交往中创造的关系。 人民、社会而不是国家、政府权威一直被认为是法律的主要 渊源。组成各种联合的人们、建立相应的权利和责任的雇主 和雇员、彼此间订立协议的商人们、把孩子们抚养成人的父 母们一一他们建立了各种民间(umo压cial)法律关系,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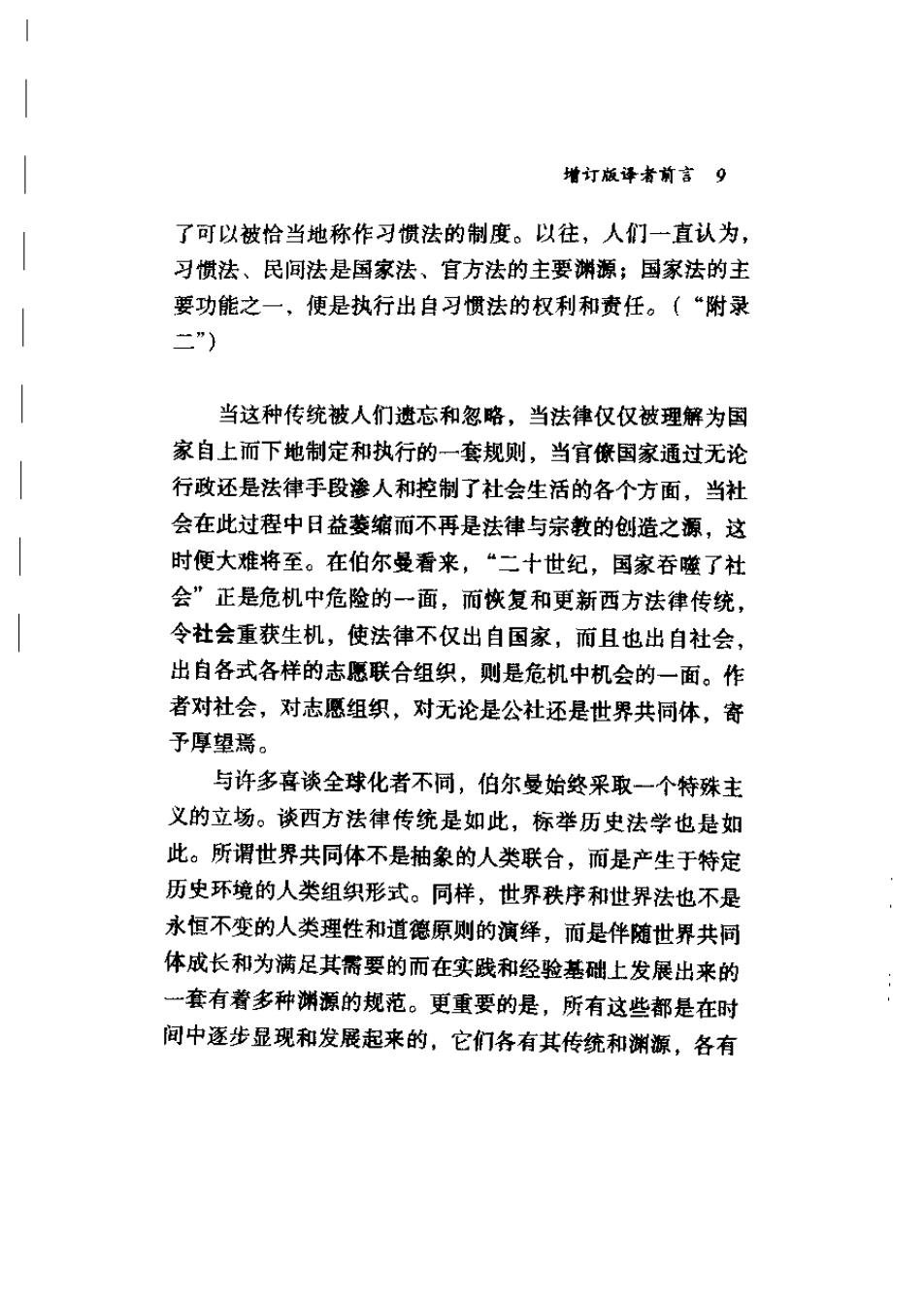
增订版译者前言9 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作习惯法的制度。以往,人们一直认为, 习惯法、民间法是国家法、官方法的主要渊源;国家法的主 要功能之一,便是执行出自习惯法的权利和责任。(“附录 二”) 当这种传统被人们遗忘和忽略,当法律仅仅被理解为国 家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执行的一套规则,当官僚国家通过无论 行政还是法律手段渗人和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社 会在此过程中日益菱缩而不再是法律与宗教的创造之源,这 时便大难将至。在伯尔曼看来,“二十世纪,国家吞噬了社 会”正是危机中危险的一面,而恢复和更新西方法律传统, 令社会重获生机,使法律不仅出自国家,而且也出自社会, 出自各式各样的志愿联合组织,则是危机中机会的一面。作 者对社会,对志愿组织,对无论是公社还是世界共同体,寄 予厚望焉。 与许多喜谈全球化者不同,伯尔曼始终采取一个特殊主 义的立场。谈西方法律传统是如此,标举历史法学也是如 此。所谓世界共同体不是抽象的人类联合,而是产生于特定 历史环境的人类组织形式。同样,世界秩序和世界法也不是 永恒不变的人类理性和道德原则的演锋,而是伴随世界共同 体成长和为满足其需要的而在实践和经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一套有着多种渊源的规范。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在时 间中逐步显现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各有其传统和渊源,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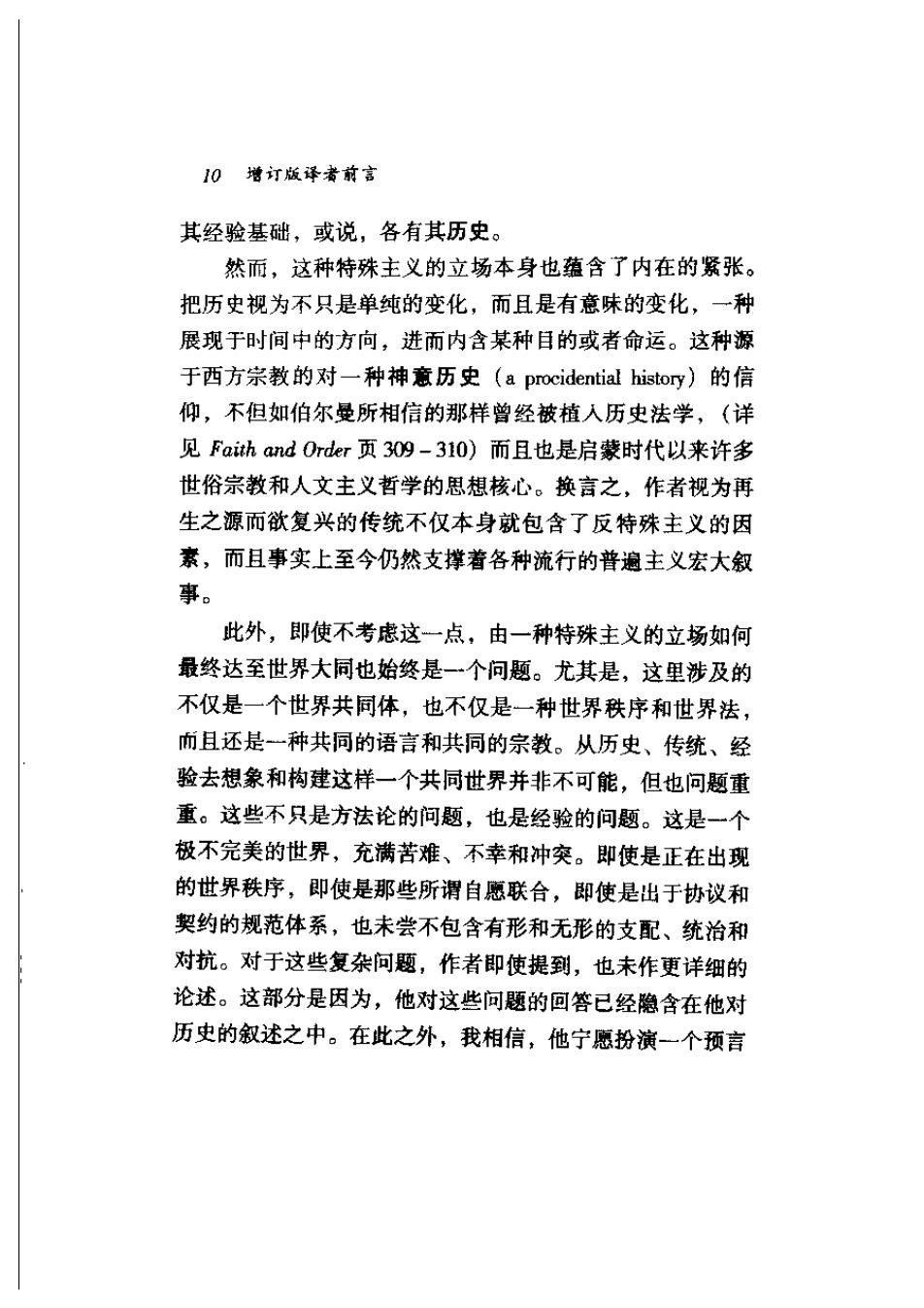
10增订版译者前言 其经验基础,或说,各有其历史。 然而,这种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也蕴含了内在的紧张。 把历史视为不只是单纯的变化,而且是有意味的变化,一种 展现于时间中的方向,进而内含某种目的或者命运。这种源 于西方宗教的对一种神意历史(a procidential history)的信 仰,不但如伯尔曼所相信的那样曾经被植入历史法学,(详 见Faith and Order页309-310)而且也是启蒙时代以来许多 世俗宗教和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核心。换言之,作者视为再 生之源而欲复兴的传统不仅本身就包含了反特殊主义的因 素,而且事实上至今仍然支撑着各种流行的普遍主义宏大叙 。 此外,即使不考意这一点,由一种特殊主义的立场如何 最终达至世界大同也始终是一个问题。尤其是,这里涉及的 不仅是一个世界共同体,也不仅是一种世界秩序和世界法, 而且还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宗教。从历史、传统、经 验去想象和构建这样一个共同世界并非不可能,但也问题重 重。这些不只是方法论的问题,也是经验的问题。这是一个 极不完美的世界,充满苦难、不幸和冲突。即使是正在出现 的世界秩序,即使是那些所谓自愿联合,即使是出于协议和 契约的规范体系,也未尝不包含有形和无形的支配、统治和 对抗。对于这些复杂问题,作者即使提到,也未作更详细的 论述。这部分是因为,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隐含在他对 历史的叙述之中。在此之外,我相信,他宁愿扮演一个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