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订版译者前言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自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以来,这句引文在法律学者和学生们笔下和口中如此 流行,以至引用者常常省略了这个引语所由出的那本小书 一《法律与宗教》一和它的作者—哈罗德J.伯尔 曼。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的法律译著当中,《法律与宗教》 可能是读者最众和被引用最多的一种。不过,本书自1991 年出版,当时印行6000册,之后没有重印,其数量无法满 足读者的需要,也是可以想见的。我猜想,有些《法律与宗 教》的引用者可能并未读到原书,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上段说 到的那种情形。无论如何,这次有机会将本书再版,是一件 令人高兴的事情。 着手再版,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改正初版翻译和印刷中的 各种错误。另一件事是考虑能否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以令读 者更好地了解作者和作者在这本小书里表达的思想。先说后 一件事。 《法律与宗教》的英文原书出版于1974年,这个中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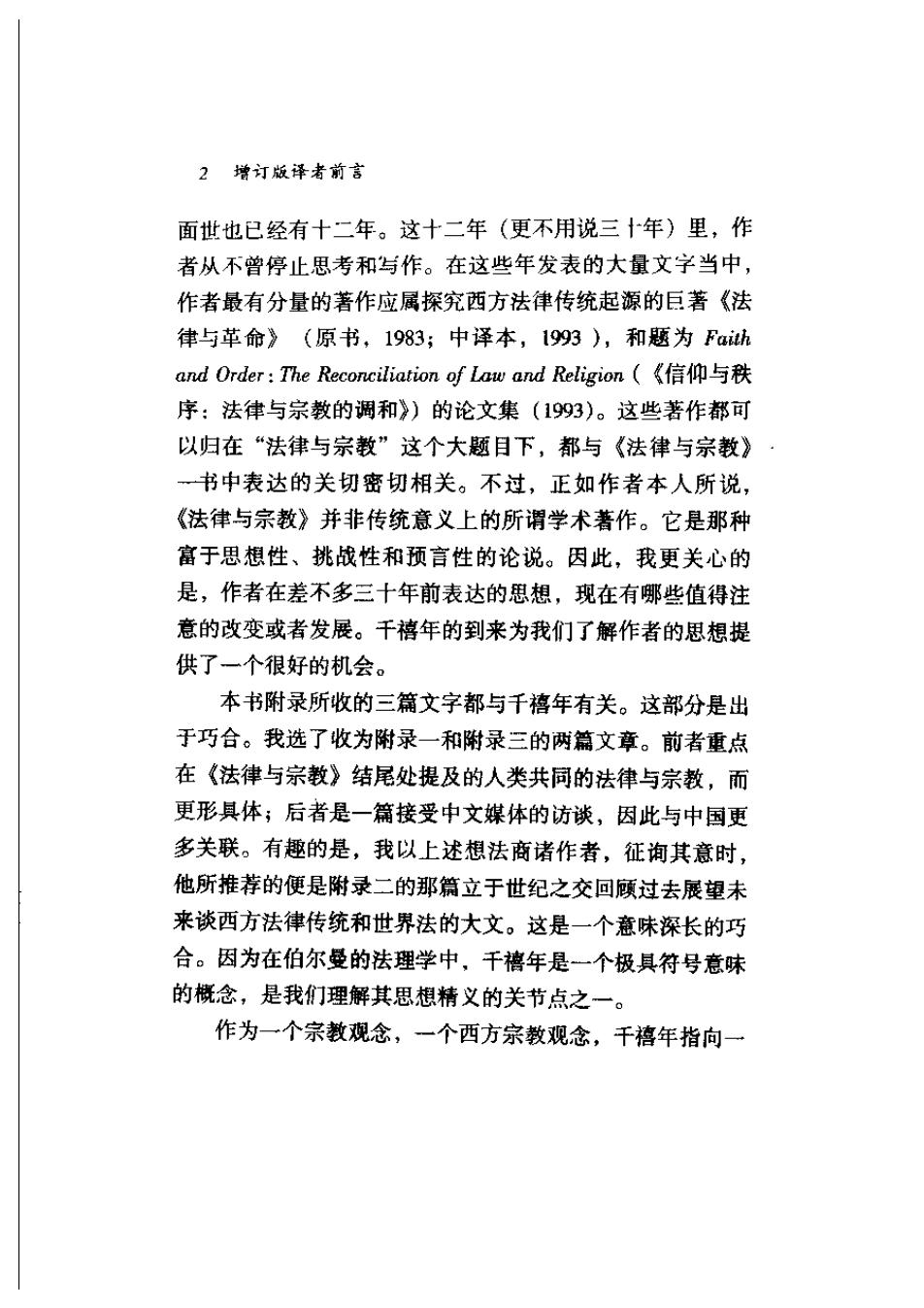
2城订版译者前言 面世也已经有十二年。这十二年(更不用说三年)里,作 者从不曾停止思考和与作。在这些年发表的大量文学当中, 作者最有分量的著作应属探究西方法律传统起源的巨著《法 律与革命》(原书,1983;中译本,1993),和题为Fah and Order:The Reconciliation of Law and Religion(《信仰与秩 序:法律与宗教的调和》)的论文集(1993)。这些著作都可 以归在“法律与宗教”这个大题目下,都与《法律与宗教》 书中表达的关切密切相关。不过,正如作者本人所说, 《法律与宗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学术著作。它是那种 富于思想性、挑战性和预言性的论说。因此,我更关心的 是,作者在差不多三十年前表达的思想,现在有哪些值得注 意的改变或者发展。千禧年的到来为我们了解作者的思想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本书附录所收的三篇文字都与千禧年有关。这部分是出 于巧合。我选了收为附录一和附录三的两篇文章。前者重点 在《法律与宗教》结尾处提及的人类共同的法律与宗教,而 更形具体;后者是一篇接受中文媒体的访谈,因此与中国更 多关联。有趣的是,我以上述想法商诸作者,征询其意时, 他所推荐的便是附录二的那篇立于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 来谈西方法律传统和世界法的大文。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巧 合。因为在伯尔曼的法理学中,千槽年是一个极具符号意味 的概念,是我们理解其思想精义的关节点之一。 作为一个宗教观念,一个西方宗教观念,千禧年指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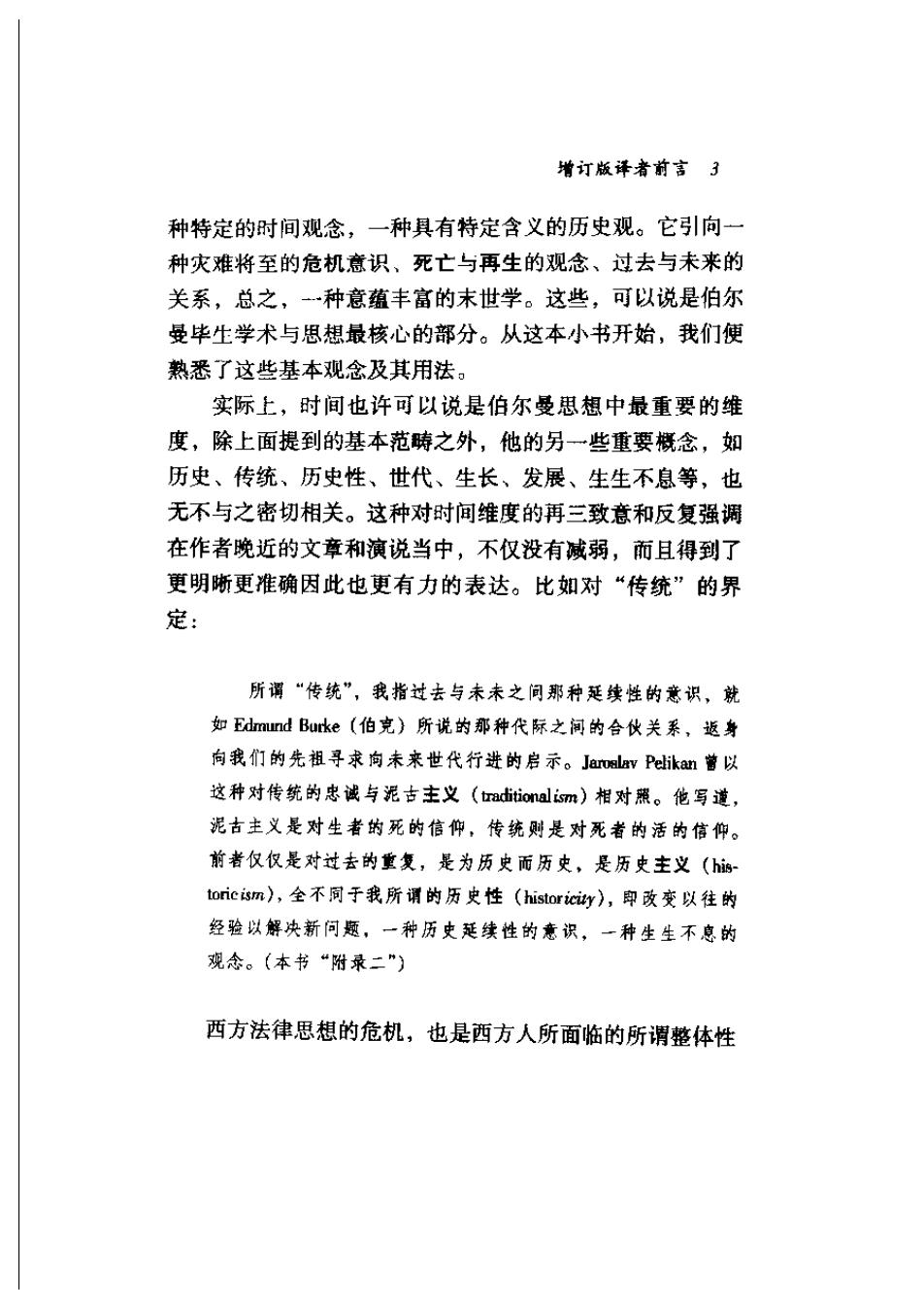
增订版译者前言3 种特定的时间观念,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历史观。它引向一 种灾难将至的危机意识、死亡与再生的观念、过去与未来的 关系,总之,一一种意蕴丰富的末世学。这些,可以说是伯尔 曼毕生学术与思想最核心的部分。从这本小书开始,我们便 熟悉了这些基本观念及其用法 实际上,时间也许可以说是伯尔曼思想中最重要的维 度,除上面提到的基本范畴之外,他的另一些重要概念,如 历史、传统、历史性、世代、生长、发展、生生不息等,也 无不与之密切相关。这种对时间维度的再三致意和反复强调 在作者晚近的文章和演说当中,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得到了 更明晰更准确因此也更有力的表达。比如对“传统”的界 所谓“传统”,我指过去与未未之间那种延续性的意识,就 如Edmund Burke(伯克)所说的那种代际之间的合伙关系,返身 向我们的先祖寻求向未来世代行进的启示。Jaroelay Pelikan首以 这种对传统的忠浅与泥古主义(ditionism)相对黑。他写道 泥古主义是对生者的死的信仲,传统则是对死者的活的信仰。 前者仅仅是对过去的重复,是为历史而历史,是历史主义(h, toricism),全不同于我所谓的历史性(historiciy),即改变以往的 经验以解央新问题,一种历史延续性的意识,一种生生不息的 观念。(本书“附录二”) 西方法律思想的危机,也是西方人所面临的所谓整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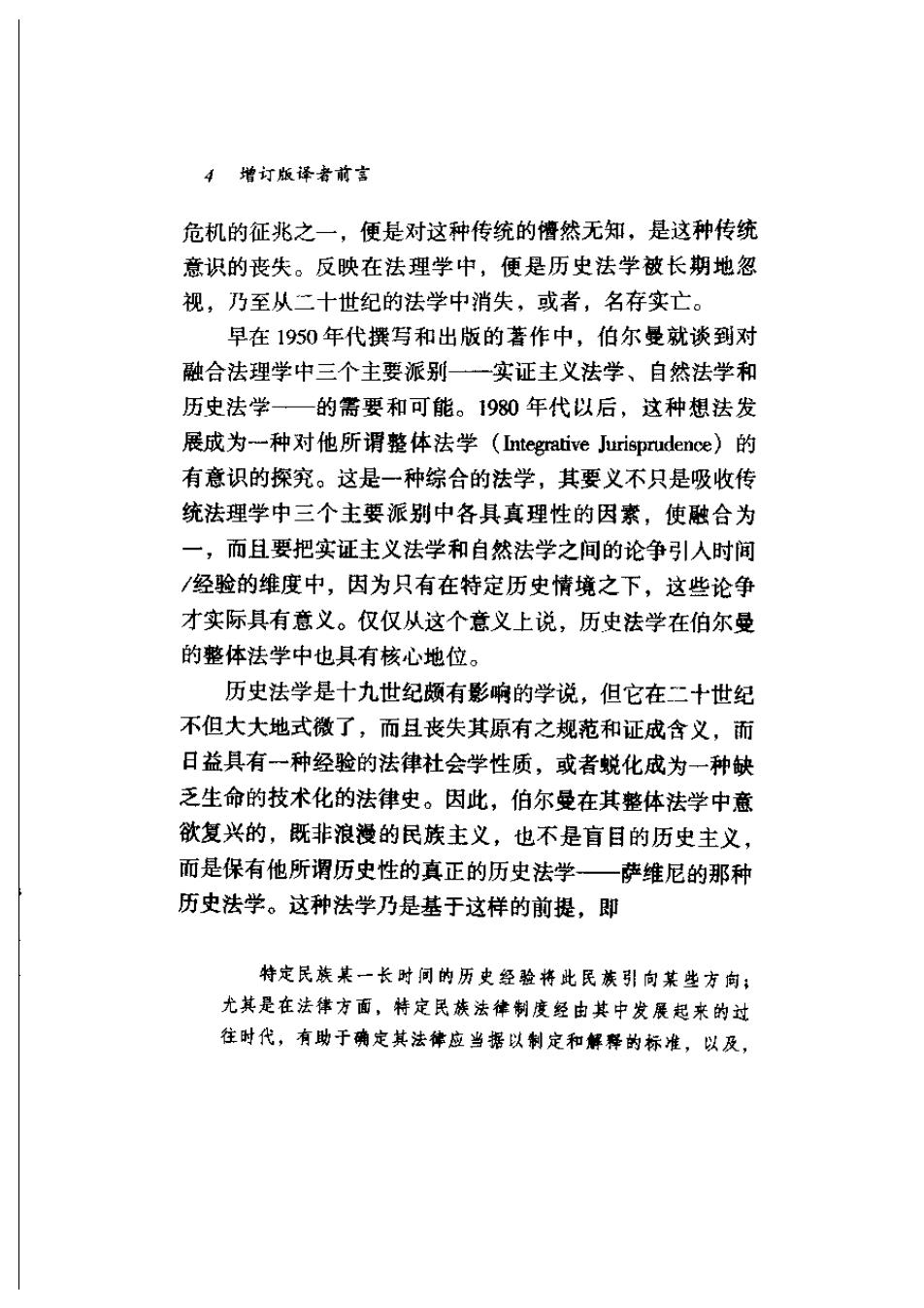
4增订版译者前言 危机的征兆之一,便是对这种传统的懵然无知,是这种传统 意识的丧失。反映在法理学中,便是历史法学被长期地忽 视,乃至从二十世纪的法学中消失,或者,名存实亡。 早在1950年代撰写和出版的著作中,伯尔曼就谈到对 融合法理学中三个主要派别一一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学和 历史法学一的需要和可能。980年代以后,这种想法发 展成为一种对他所谓整体法学(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的 有意识的探究。这是一种综合的法学,其要义不只是吸收传 统法理学中三个主要派别中各具真理性的因素,使融合为 一,而且要把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之间的论争引人时间 /经验的维度中,因为只有在特定历史情境之下,这些论争 才实际具有意义。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法学在伯尔曼 的整体法学中也具有核心地位。 历史法学是十九世纪颇有影响的学说,但它在二十世纪 不但大大地式微了,而且丧失其原有之规范和证成含义,而 日益具有一种经验的法律社会学性质,或者蜕化成为一种缺 乏生命的技术化的法律史。因此,伯尔曼在其整体法学中意 欲复兴的,既非浪漫的民族主义,也不是盲目的历史主义, 而是保有他所谓历史性的真正的历史法学一萨维尼的那种 历史法学。这种法学乃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即 特定民族某一长时同的历史经验将此民族引向某些方向: 尤其是在法律方面,特定民族法律制度经由其中发展起来的过 往时代,有助于确定其法体应当据以制定和解释的标准,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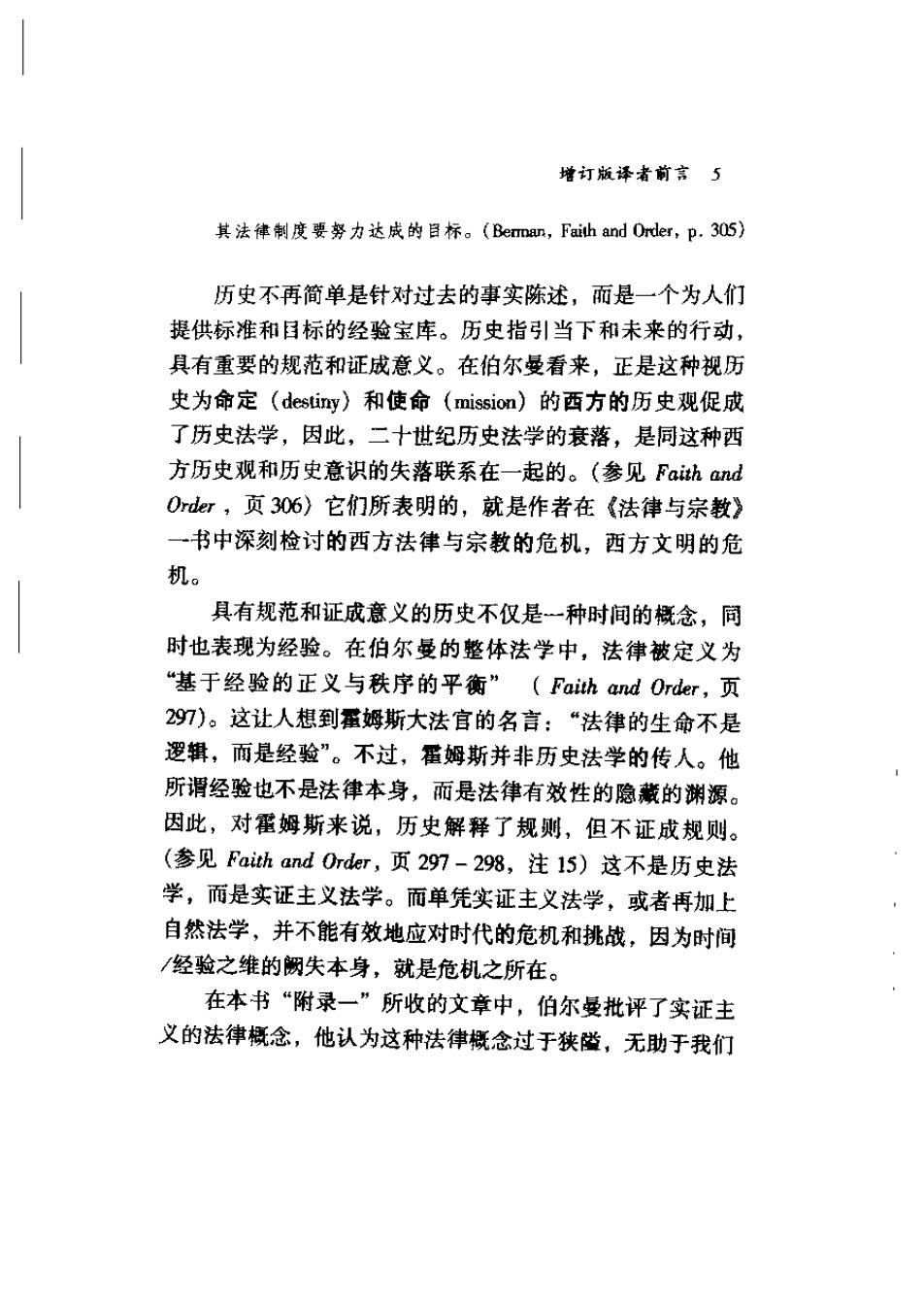
增订版译者前言5 其法律制度要努力达成的旨标。(Beran,Faith and0rer,p.30S) 历史不再简单是针对过去的事实陈述,而是一个为人们 提供标准和目标的经验宝库。历史指引当下和未来的行动, 具有重要的规范和证成意义。在伯尔曼看来,正是这种视历 史为命定(destiny》和使命(mission)的西方的历史观促成 了历史法学,因此,二十世纪历史法学的衰落,是同这种西 方历史观和历史意识的失落联系在一起的。(参见Faith and 0dr,页306)它们所表明的,就是作者在《法律与宗教》 一书中深刻检讨的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危机,西方文明的危 机。 具有规范和证成意义的历史不仅是一种时间的概念,同 时也表现为经验。在伯尔曼的整体法学中,法律被定义为 “基于经验的正义与秩序的平衡”(Faith and Order,页 297)。这让人想到猫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 逻辑,而是经验”。不过,霍姆斯并非历史法学的传人。他 所谓经验也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有效性的隐戴的渊源。 因此,对霍姆斯来说,历史解释了规则,但不证成规则。 (参见Faith and0rder,页297-298,注15)这不是历史法 学,而是实证主义法学。而单凭实证主义法学,或者再加上 自然法学,并不能有效地应对时代的危机和挑战,因为时间 /经验之维的阙失本身,就是危机之所在。 在本书“附录一”所收的文章中,伯尔曼批评了实证主 义的法律概念,他认为这种法律概念过于狭隘,无助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