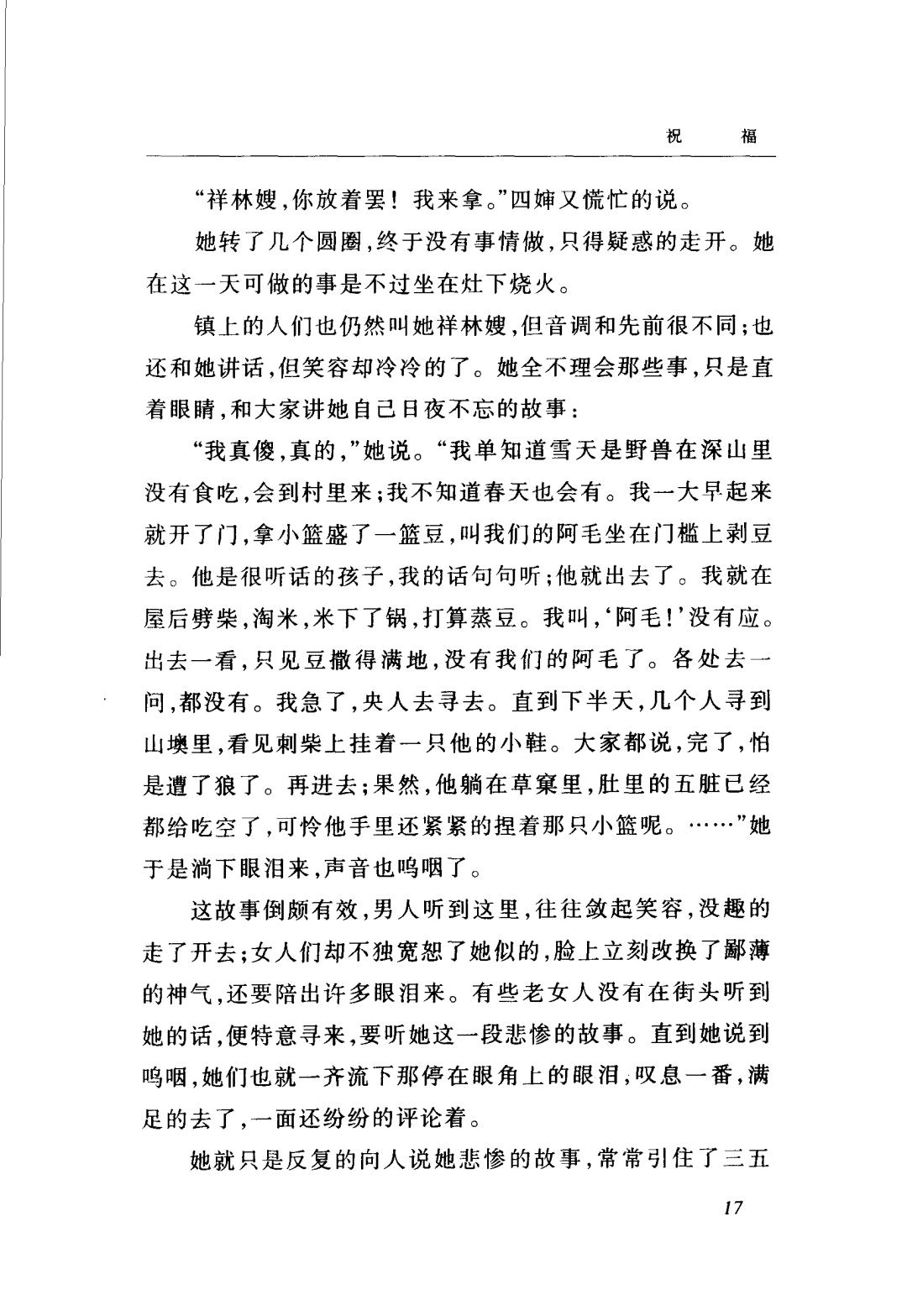
祝 福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她 在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 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 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 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 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 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 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 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 问,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 山墺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 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 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 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鸣咽了。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 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 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 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 鸣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 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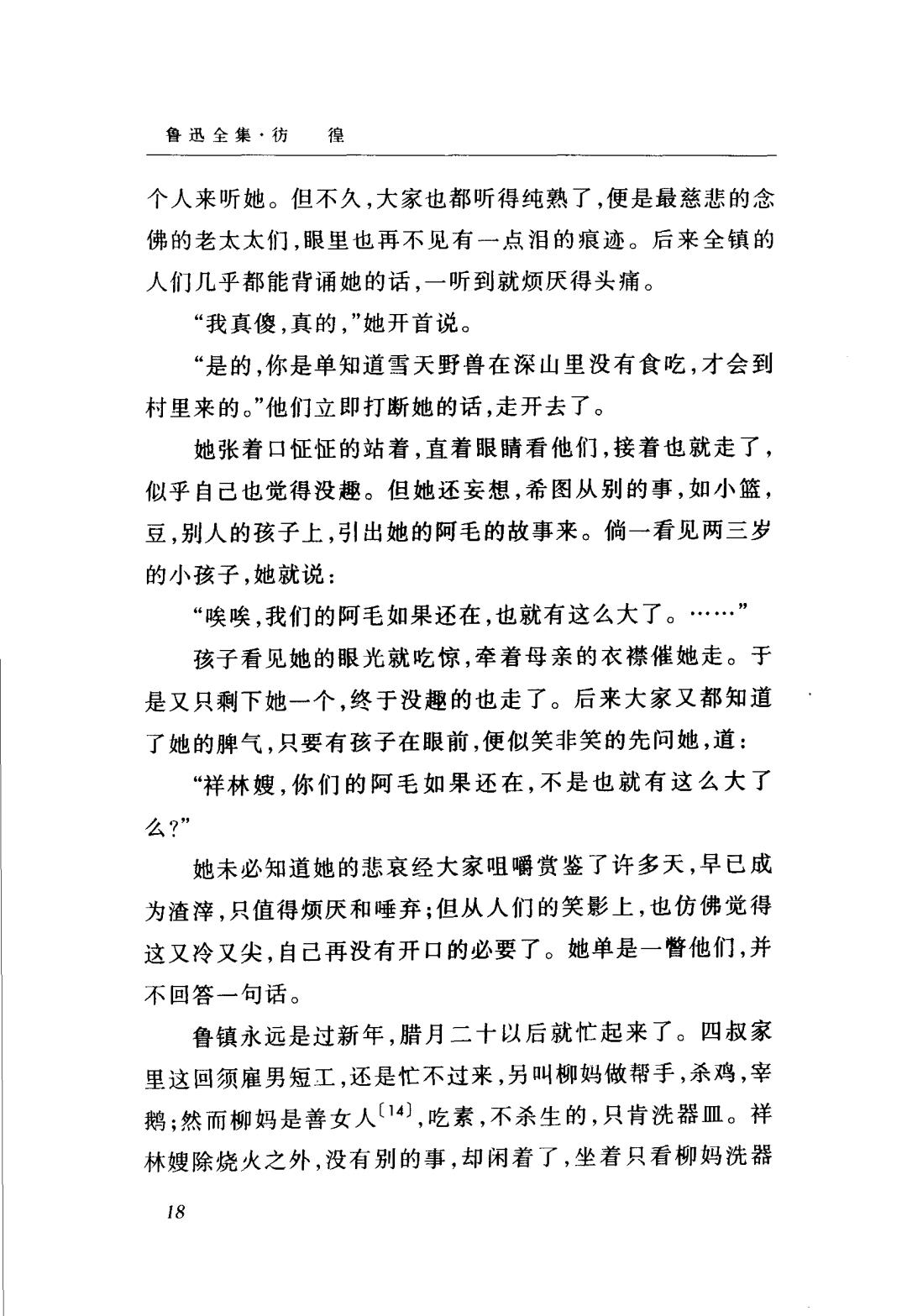
鲁迅全集·彷 徨 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 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 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 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她张着口征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 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但她还妄想,希图从别的事,如小篮, 豆,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倘一看见两三岁 的小孩子,她就说: “唉唉,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也就有这么大了。…” 孩子看见她的眼光就吃惊,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于 是又只剩下她一个,终于没趣的也走了。后来大家又都知道 了她的脾气,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问她,道: “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 么?”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 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 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 不回答一句话。 鲁镇永远是过新年,腊月二十以后就忙起来了。四叔家 里这回须雇男短工,还是忙不过来,另叫柳妈做帮手,杀鸡, 鹅;然而柳妈是善女人14),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祥 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了,坐着只看柳妈洗器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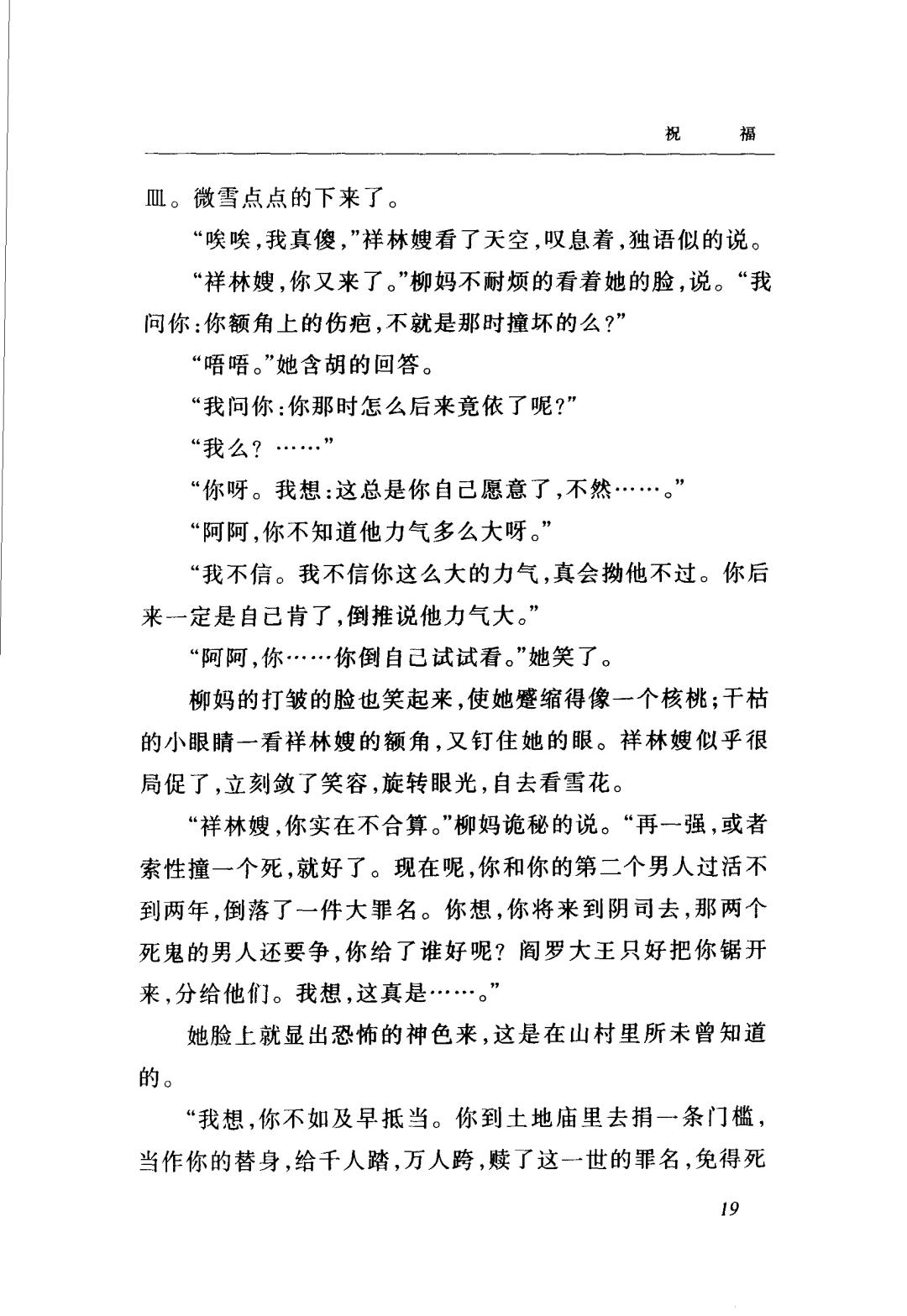
祝 福 皿。微雪点点的下来了。 “唉唉,我真傻,”样林嫂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 “样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 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疤,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 “唔唔。”她含胡的回答。 “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竞依了呢?” “我么?…” “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 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她笑了。 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 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 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 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 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 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 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 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 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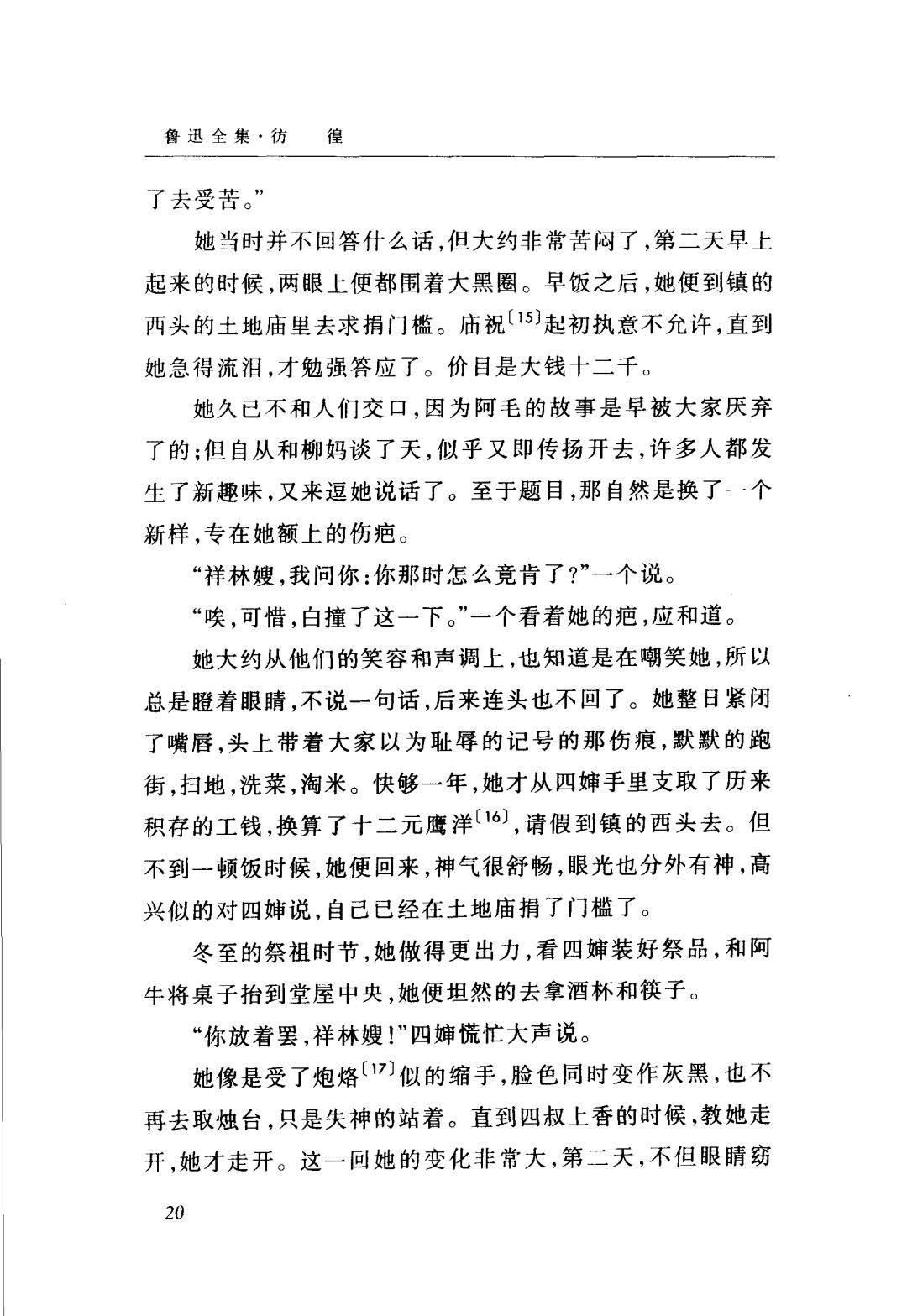
鲁迅全集·彷 徨 了去受苦。” 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 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 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15)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 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干。 她久已不和人们交口,因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厌弃 了的;但自从和柳妈谈了天,似乎又即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 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 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 “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一个说。 “唉,可惜,白撞了这一下。”一个看着她的疤,应和道。 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 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 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 街,扫地,洗菜,淘米。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 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16),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 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 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 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1)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 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 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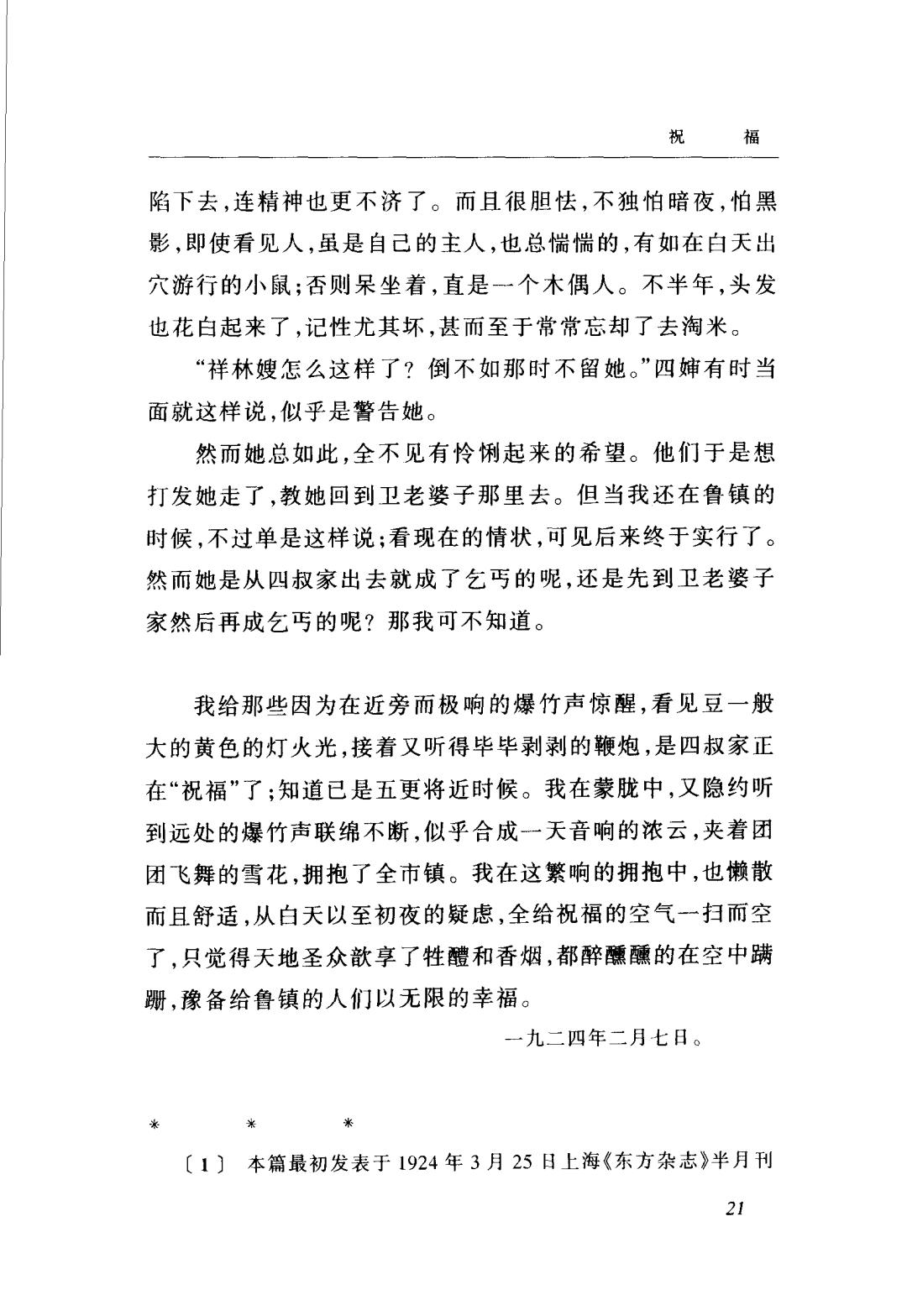
祝 福 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 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 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 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样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她。”四婶有时当 面就这样说,似乎是警告她。 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怜俐起来的希望。他们于是想 打发她走了,教她回到卫老婆子那里去。但当我还在鲁镇的 时候,不过单是这样说:看现在的情状,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 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 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 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 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 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 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 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 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 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米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