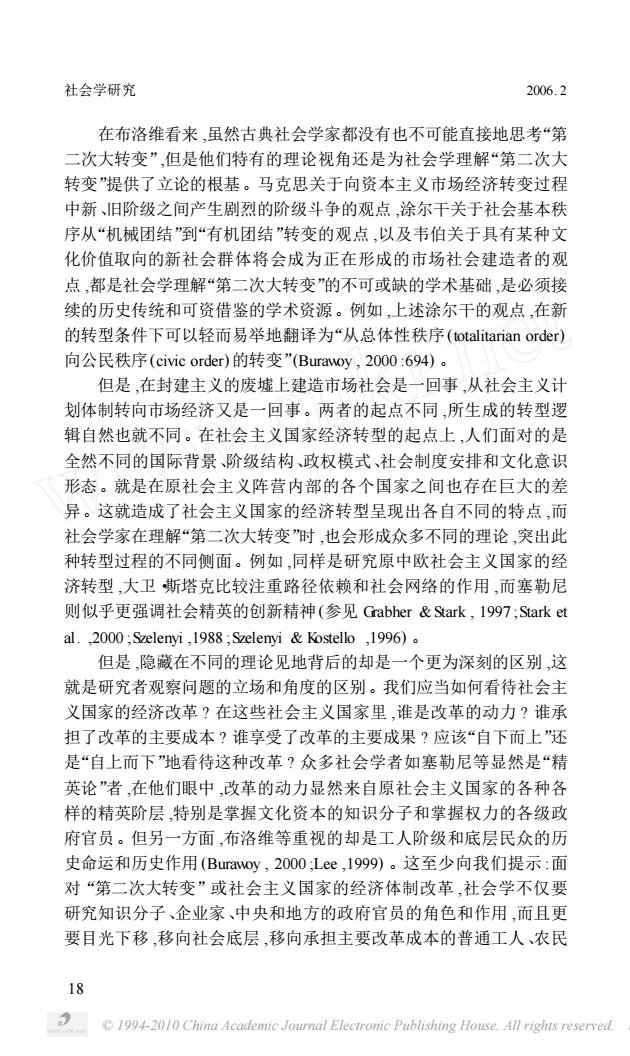
社会学研究 2006.2 在布洛维看来,虽然古典社会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地思考“第 二次大转变”,但是他们特有的理论视角还是为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 转变”提供了立论的根基。马克思关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 中新、旧阶级之间产生剧烈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涂尔干关于社会基本秩 序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转变的观点,以及韦伯关于具有某种文 化价值取向的新社会群体将会成为正在形成的市场社会建造者的观 点,都是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的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是必须接 续的历史传统和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例如,上述涂尔干的观点,在新 的转型条件下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译为“从总体性秩序(totalitarian order) 向公民秩序(civic order)的转变”(Burawoy,2000:694)。 但是,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造市场社会是一回事,从社会主义计 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又是一回事。两者的起点不同,所生成的转型逻 辑自然也就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起点上,人们面对的是 全然不同的国际背景、阶级结构、政权模式、社会制度安排和文化意识 形态。就是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 异。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而 社会学家在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时,也会形成众多不同的理论,突出此 种转型过程的不同侧面。例如,同样是研究原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济转型,大卫斯塔克比较注重路径依赖和社会网络的作用,而塞勒尼 则似乎更强调社会精英的创新精神(参见Grabher&Sark,1997:Stark et al.,2000 Szelenyi,1988 Szelenyi Kostello,1996) 但是,隐藏在不同的理论见地背后的却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区别,这 就是研究者观察问题的立场和角度的区别。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 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谁是改革的动力?谁承 担了改革的主要成本?谁享受了改革的主要成果?应该“自下而上”还 是“自上而下”地看待这种改革?众多社会学者如塞勒尼等显然是“精 英论”者,在他们眼中,改革的动力显然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 样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和掌握权力的各级政 府官员。但另一方面,布洛维等重视的却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历 史命运和历史作用(Burawoy,2000;Lee,1999)。这至少向我们提示:面 对“第二次大转变”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学不仅要 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的角色和作用,而且更 要目光下移,移向社会底层,移向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 18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布洛维看来 ,虽然古典社会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地思考“第 二次大转变”,但是他们特有的理论视角还是为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 转变”提供了立论的根基。马克思关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 中新、旧阶级之间产生剧烈的阶级斗争的观点 ,涂尔干关于社会基本秩 序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转变的观点 ,以及韦伯关于具有某种文 化价值取向的新社会群体将会成为正在形成的市场社会建造者的观 点 ,都是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的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是必须接 续的历史传统和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例如 ,上述涂尔干的观点 ,在新 的转型条件下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译为“从总体性秩序(totalitarian order) 向公民秩序(civic order) 的转变”(Burawoy , 2000 :694) 。 但是 ,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造市场社会是一回事 ,从社会主义计 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又是一回事。两者的起点不同 ,所生成的转型逻 辑自然也就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起点上 ,人们面对的是 全然不同的国际背景、阶级结构、政权模式、社会制度安排和文化意识 形态。就是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 异。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而 社会学家在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时 ,也会形成众多不同的理论 ,突出此 种转型过程的不同侧面。例如 ,同样是研究原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济转型 ,大卫·斯塔克比较注重路径依赖和社会网络的作用 ,而塞勒尼 则似乎更强调社会精英的创新精神(参见 Grabher &Stark , 1997 ;Stark et al. ,2000 ;Szelenyi ,1988 ;Szelenyi & Kostello ,1996) 。 但是 ,隐藏在不同的理论见地背后的却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区别 ,这 就是研究者观察问题的立场和角度的区别。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 义国家的经济改革 ? 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 ,谁是改革的动力 ? 谁承 担了改革的主要成本 ? 谁享受了改革的主要成果 ? 应该“自下而上”还 是“自上而下”地看待这种改革 ? 众多社会学者如塞勒尼等显然是“精 英论”者 ,在他们眼中 ,改革的动力显然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 样的精英阶层 ,特别是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和掌握权力的各级政 府官员。但另一方面 ,布洛维等重视的却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历 史命运和历史作用(Burawoy , 2000 ;Lee ,1999) 。这至少向我们提示 :面 对“第二次大转变”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学不仅要 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的角色和作用 ,而且更 要目光下移 ,移向社会底层 ,移向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 18 社会学研究 200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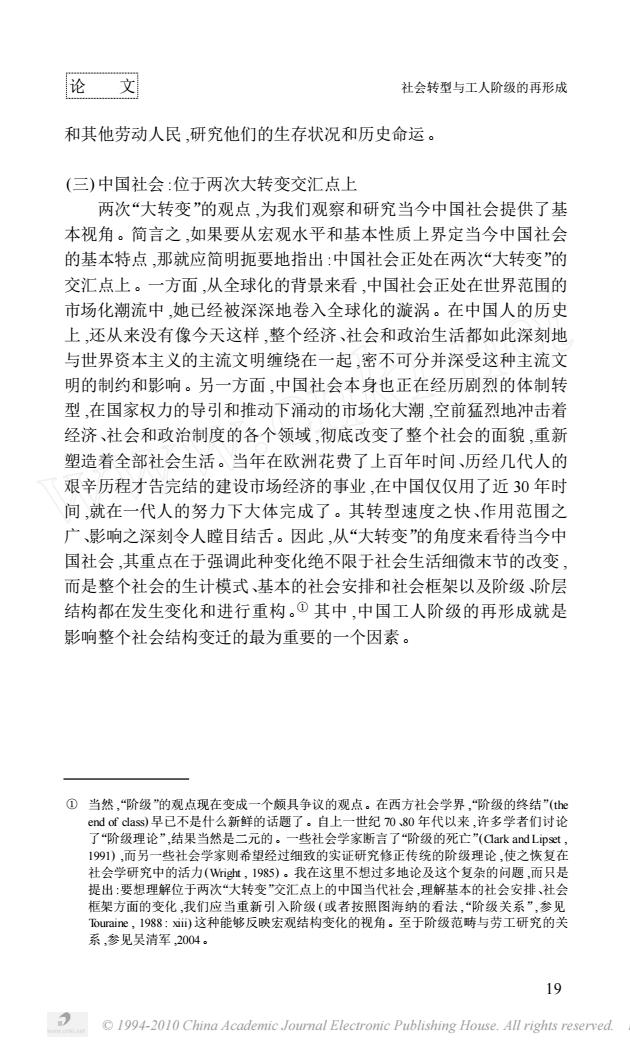
论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和其他劳动人民,研究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 (三)中国社会:位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 两次“大转变”的观点,为我们观察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提供了基 本视角。简言之,如果要从宏观水平和基本性质上界定当今中国社会 的基本特点,那就应简明扼要地指出:中国社会正处在两次“大转变”的 交汇点上。一方面,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世界范围的 市场化潮流中,她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全球化的漩涡。在中国人的历史 上,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深刻地 与世界资本主义的主流文明缠绕在一起,密不可分并深受这种主流文 明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本身也正在经历剧烈的体制转 型,在国家权力的导引和推动下涌动的市场化大潮,空前猛烈地冲击着 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各个领域,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重新 塑造着全部社会生活。当年在欧洲花费了上百年时间、历经几代人的 艰辛历程才告完结的建设市场经济的事业,在中国仅仅用了近30年时 间,就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大体完成了。其转型速度之快、作用范围之 广、影响之深刻令人膛目结舌。因此,从“大转变”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中 国社会,其重点在于强调此种变化绝不限于社会生活细微末节的改变, 而是整个社会的生计模式、基本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 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和进行重构。①其中,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就是 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①当然,“阶级”的观点现在变成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在西方社会学界,“阶级的终结”(te end of class)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自上一世纪70、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们讨论 了“阶级理论”,结果当然是二元的。一些社会学家断言了“阶级的死亡”(Clark and Lipset, 1991),而另一些社会学家则希望经过细致的实证研究修正传统的阶级理论,使之恢复在 社会学研究中的活力(Wg,1985)。我在这里不想过多地论及这个复杂的问题,而只是 提出:要想理解位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的中国当代社会,理解基本的社会安排、社会 框架方面的变化,我们应当重新引入阶级(或者按照图海纳的看法,“阶级关系”,参见 Touraine,1988:ii)这种能够反映宏观结构变化的视角。至于阶级范畴与劳工研究的关 系,参见吴清军,2004。 19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其他劳动人民 ,研究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 (三) 中国社会 :位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 两次“大转变”的观点 ,为我们观察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提供了基 本视角。简言之 ,如果要从宏观水平和基本性质上界定当今中国社会 的基本特点 ,那就应简明扼要地指出 :中国社会正处在两次“大转变”的 交汇点上。一方面 ,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 ,中国社会正处在世界范围的 市场化潮流中 ,她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全球化的漩涡。在中国人的历史 上 ,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深刻地 与世界资本主义的主流文明缠绕在一起 ,密不可分并深受这种主流文 明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 ,中国社会本身也正在经历剧烈的体制转 型 ,在国家权力的导引和推动下涌动的市场化大潮 ,空前猛烈地冲击着 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各个领域 ,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 ,重新 塑造着全部社会生活。当年在欧洲花费了上百年时间、历经几代人的 艰辛历程才告完结的建设市场经济的事业 ,在中国仅仅用了近 30 年时 间 ,就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大体完成了。其转型速度之快、作用范围之 广、影响之深刻令人瞠目结舌。因此 ,从“大转变”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中 国社会 ,其重点在于强调此种变化绝不限于社会生活细微末节的改变 , 而是整个社会的生计模式、基本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 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和进行重构。① 其中 ,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就是 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19 论 文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① 当然“, 阶级”的观点现在变成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在西方社会学界“, 阶级的终结”(the end of class)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自上一世纪 70、80 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们讨论 了“阶级理论”,结果当然是二元的。一些社会学家断言了“阶级的死亡”(Clark and Lipset , 1991) ,而另一些社会学家则希望经过细致的实证研究修正传统的阶级理论 ,使之恢复在 社会学研究中的活力(Wright , 1985) 。我在这里不想过多地论及这个复杂的问题 ,而只是 提出 :要想理解位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的中国当代社会 ,理解基本的社会安排、社会 框架方面的变化 ,我们应当重新引入阶级 (或者按照图海纳的看法 “, 阶级关系”,参见 Touraine , 1988 : xiii) 这种能够反映宏观结构变化的视角。至于阶级范畴与劳工研究的关 系 ,参见吴清军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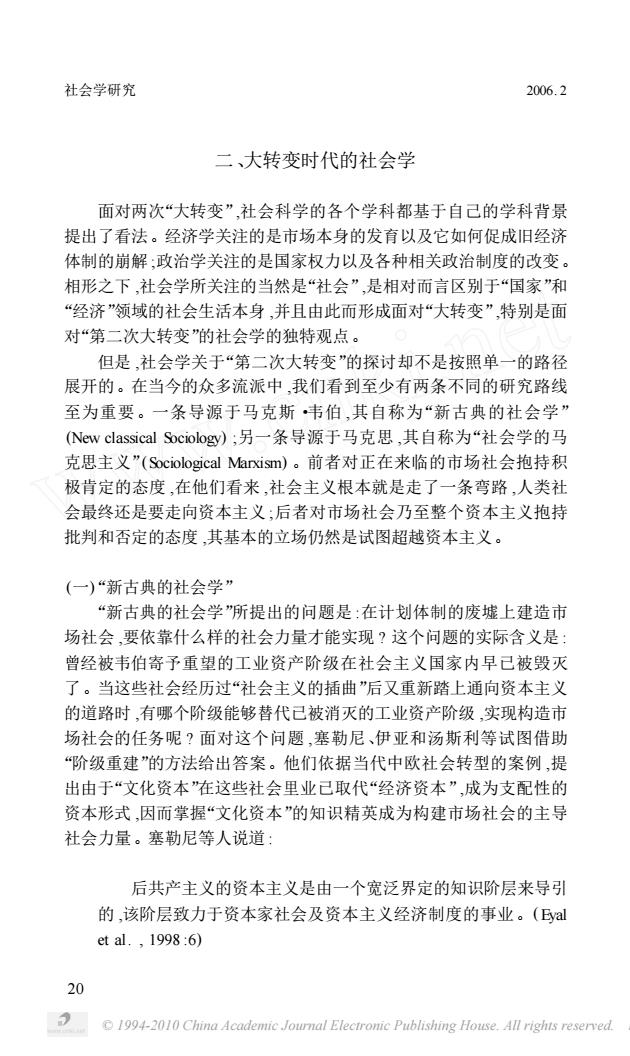
社会学研究 2006.2 二、大转变时代的社会学 面对两次“大转变”,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 提出了看法。经济学关注的是市场本身的发育以及它如何促成旧经济 体制的崩解:政治学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以及各种相关政治制度的改变。 相形之下,社会学所关注的当然是“社会”,是相对而言区别于“国家”和 “经济”领域的社会生活本身,并且由此而形成面对“大转变”特别是面 对“第二次大转变”的社会学的独特观点。 但是,社会学关于“第二次大转变”的探讨却不是按照单一的路径 展开的。在当今的众多流派中,我们看到至少有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 至为重要。一条导源于马克斯韦伯,其自称为“新古典的社会学” (New classical Sociology);另一条导源于马克思,其自称为“社会学的马 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 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根本就是走了一条弯路,人类社 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后者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 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基本的立场仍然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 (一)“新古典的社会学” “新古典的社会学”所提出的问题是:在计划体制的废墟上建造市 场社会,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是: 曾经被韦伯寄予重望的工业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早已被毁灭 了。当这些社会经历过“社会主义的插曲”后又重新踏上通向资本主义 的道路时,有哪个阶级能够替代已被消灭的工业资产阶级,实现构造市 场社会的任务呢?面对这个问题,塞勒尼、伊亚和汤斯利等试图借助 “阶级重建”的方法给出答案。他们依据当代中欧社会转型的案例,提 出由于“文化资本”在这些社会里业己取代“经济资本”,成为支配性的 资本形式,因而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成为构建市场社会的主导 社会力量。塞勒尼等人说道: 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宽泛界定的知识阶层来导引 的,该阶层致力于资本家社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事业。(El etal.,1998:6) 20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大转变时代的社会学 面对两次“大转变”,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 提出了看法。经济学关注的是市场本身的发育以及它如何促成旧经济 体制的崩解 ;政治学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以及各种相关政治制度的改变。 相形之下 ,社会学所关注的当然是“社会”,是相对而言区别于“国家”和 “经济”领域的社会生活本身 ,并且由此而形成面对“大转变”,特别是面 对“第二次大转变”的社会学的独特观点。 但是 ,社会学关于“第二次大转变”的探讨却不是按照单一的路径 展开的。在当今的众多流派中 ,我们看到至少有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 至为重要。一条导源于马克斯·韦伯 ,其自称为“新古典的社会学” (New classical Sociology) ;另一条导源于马克思 ,其自称为“社会学的马 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 。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 极肯定的态度 ,在他们看来 ,社会主义根本就是走了一条弯路 ,人类社 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 ;后者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 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其基本的立场仍然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 (一)“新古典的社会学” “新古典的社会学”所提出的问题是 :在计划体制的废墟上建造市 场社会 ,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 ? 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是 : 曾经被韦伯寄予重望的工业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早已被毁灭 了。当这些社会经历过“社会主义的插曲”后又重新踏上通向资本主义 的道路时 ,有哪个阶级能够替代已被消灭的工业资产阶级 ,实现构造市 场社会的任务呢 ? 面对这个问题 ,塞勒尼、伊亚和汤斯利等试图借助 “阶级重建”的方法给出答案。他们依据当代中欧社会转型的案例 ,提 出由于“文化资本”在这些社会里业已取代“经济资本”,成为支配性的 资本形式 ,因而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成为构建市场社会的主导 社会力量。塞勒尼等人说道 : 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宽泛界定的知识阶层来导引 的 ,该阶层致力于资本家社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事业。( Eyal et al. , 1998 :6) 20 社会学研究 2006. 2

论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塞勒尼将他们的这一套理论称为“新古典的社会学”,其意即在与 第一次“大转变”中产生的“古典社会学”即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社 会学理论相比照: 共产主义的衰落可以被理解成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以重访 马克思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所研讨过的那些旧的研究基 点。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 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议程,即为新古典社会学设定了研究议 程。(Eyal et al.,1998:3) (二)“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 导源于马克思的研究路线即“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似乎要更为 复杂一些。按照布洛维的概括,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本人的 社会理论之后,其在发展过程中分化成两条支流,但最后殊途同归,共 同走向一个终点。其中,第一条支流以列宁为中介而以葛兰西为终点, 第二条支流以卢卡奇为中介而以波兰尼为终点。就是说,葛兰西和波 兰尼分别代表了发展途程的两个端项,两者最后汇合为“社会学的马克 思主义”(Burawoy,2003)。 所谓“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自然是彰显“社会”本身的研 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虽说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关于“社 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论述。葛兰西和波兰尼都以区别于国 家和市场的“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但是两者的角度又各有不同。葛 兰西所强调的是“公民社会”,这种“公民社会”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得 到界定的:波兰尼强调的则是“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这种“能动社 会”是在与市场的搏斗中成长起来的。布洛维评论道: 葛兰西的“公民社会”结合了国家以吸纳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挑 战。因此葛兰西描述了资本主义内部从政治专政到政治霸权的过 渡…波兰尼的“能动社会”反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 在这里是从市场专制到市场调节的过渡…(Burawoy,2003:220) 但是,正如布洛维指出的,虽然葛兰西和波兰尼都突出了“社会”本 21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塞勒尼将他们的这一套理论称为“新古典的社会学”,其意即在与 第一次“大转变”中产生的“古典社会学”即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社 会学理论相比照 : 共产主义的衰落可以被理解成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 ,以重访 马克思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所研讨过的那些旧的研究基 点。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 ,共产主 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议程 ,即为新古典社会学设定了研究议 程。(Eyal et al. , 1998 :3) (二)“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 导源于马克思的研究路线即“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似乎要更为 复杂一些。按照布洛维的概括 ,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本人的 社会理论之后 ,其在发展过程中分化成两条支流 ,但最后殊途同归 ,共 同走向一个终点。其中 ,第一条支流以列宁为中介而以葛兰西为终点 , 第二条支流以卢卡奇为中介而以波兰尼为终点。就是说 ,葛兰西和波 兰尼分别代表了发展途程的两个端项 ,两者最后汇合为“社会学的马克 思主义”(Burawoy , 2003) 。 所谓“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自然是彰显“社会”本身的研 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虽说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 ,关于“社 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论述。葛兰西和波兰尼都以区别于国 家和市场的“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 ,但是两者的角度又各有不同。葛 兰西所强调的是“公民社会”,这种“公民社会”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得 到界定的 ;波兰尼强调的则是“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 ,这种“能动社 会”是在与市场的搏斗中成长起来的。布洛维评论道 : 葛兰西的“公民社会”结合了国家以吸纳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挑 战。因此葛兰西描述了资本主义内部从政治专政到政治霸权的过 渡 ……波兰尼的“能动社会”反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 在这里是从市场专制到市场调节的过渡 ……(Burawoy , 2003 :220) 但是 ,正如布洛维指出的 ,虽然葛兰西和波兰尼都突出了“社会”本 21 论 文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