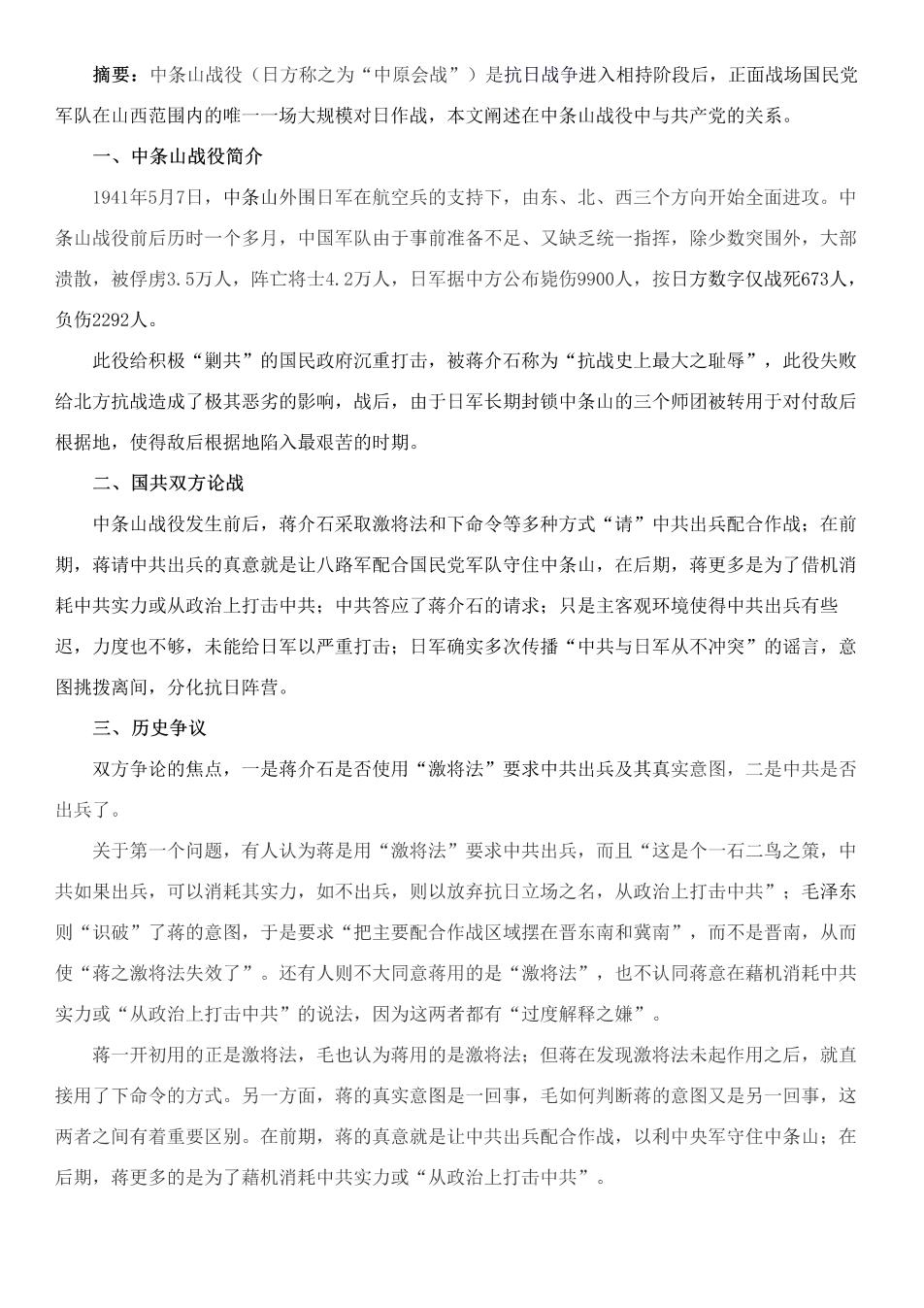
摘要: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 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本文阐述在中条山战役中与共产党的关系。 一、中条山战役简介 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中 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 溃散,被俘虏3.5万人,阵亡将士4.2万人,日军据中方公布毙伤9900人,按日方数字仅战死673人, 负伤2292人. 此役给积极“剿共”的国民政府沉重打击,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此役失败 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战后,由于日军长期封锁中条山的三个师团被转用于对付敌后 根据地,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 二、国共双方论战 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在前 期,蒋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是为了借机消 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 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确实多次传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 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 三、历史争议 双方争论的焦点,一是蒋介石是否使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及其真实意图,二是中共是否 出兵了。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蒋是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而且“这是个一石二鸟之策,中 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毛泽东 则“识破”了蒋的意图,于是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而不是晋南,从而 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还有人则不大同意蒋用的是“激将法”,也不认同蒋意在藉机消耗中共 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说法,因为这两者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蒋一开初用的正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但蒋在发现激将法未起作用之后,就直 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另一方面,蒋的真实意图是一回事,毛如何判断蒋的意图又是另一回事,这 两者之间有着重要区别。在前期,蒋的真意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 后期,蒋更多的是为了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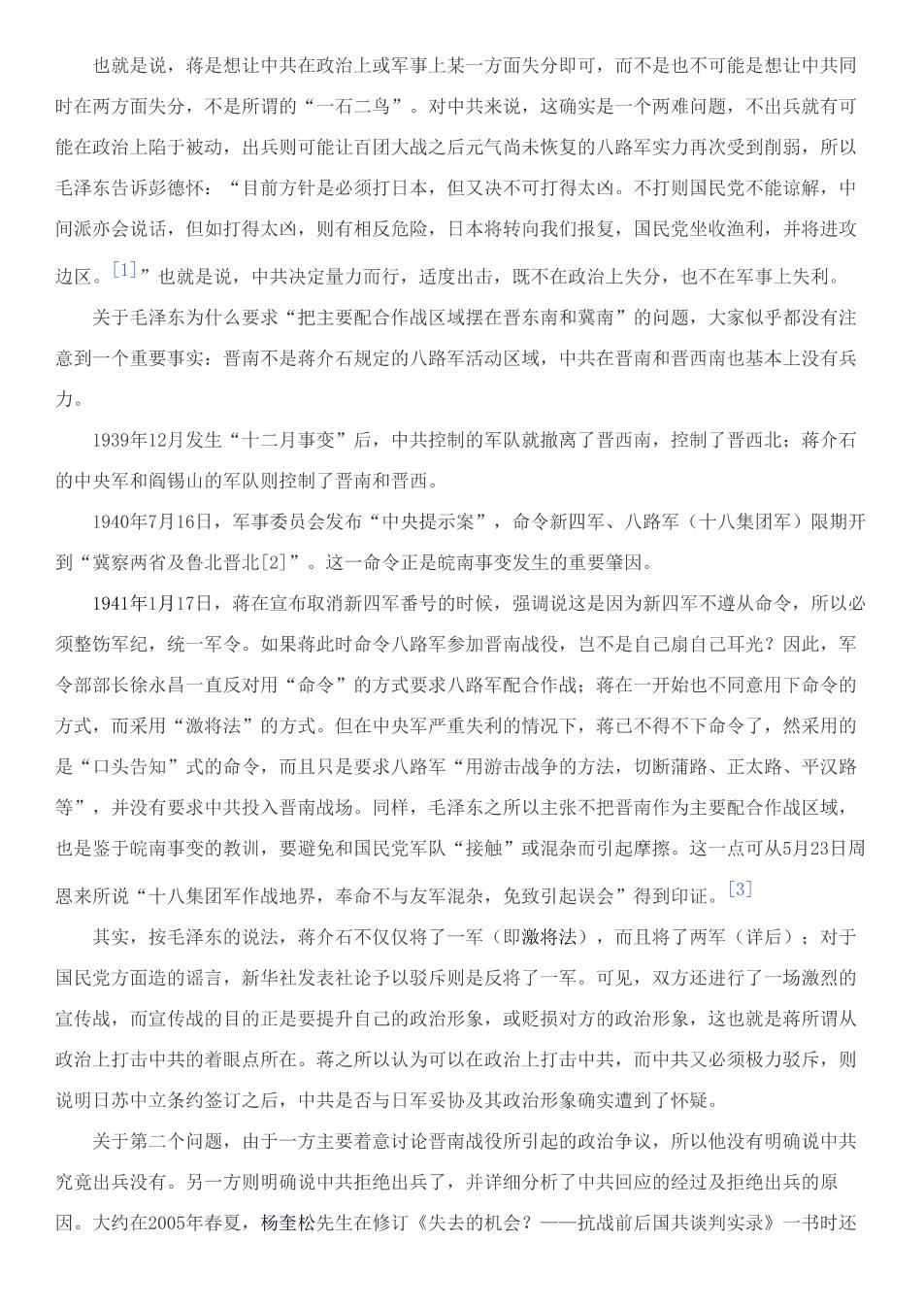
也就是说,蒋是想让中共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某一方面失分即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想让中共同 时在两方面失分,不是所谓的“一石二鸟”。对中共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不出兵就有可 能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出兵则可能让百团大战之后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次受到削弱,所以 毛泽东告诉彭德怀:“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 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 边区。[]”也就是说,中共决定量力而行,适度出击,既不在政治上失分,也不在军事上失利。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的问题,大家似乎都没有注 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晋南不是蒋介石规定的八路军活动区域,中共在晋南和晋西南也基本上没有兵 力。 1939年12月发生“十二月事变”后,中共控制的军队就撤离了晋西南,控制了晋西北:蒋介石 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则控制了晋南和晋西。 1940年7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十八集团军)限期开 到“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2]”。这一命令正是皖南事变发生的重要肇因。 1941年1月17日,蒋在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时候,强调说这是因为新四军不遵从命令,所以必 须整饬军纪,统一军令。如果蒋此时命令八路军参加晋南战役,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因此,军 令部部长徐永昌一直反对用“命令”的方式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蒋在一开始也不同意用下命令的 方式,而采用“激将法”的方式。但在中央军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蒋己不得不下命令了,然采用的 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且只是要求八路军“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蒲路、正太路、平汉路 等”,并没有要求中共投入晋南战场。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主张不把晋南作为主要配合作战区域, 也是鉴于皖南事变的教训,要避免和国民党军队“接触”或混杂而引起摩擦。这一点可从5月23日周 恩来所说“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得到印证。[3] 其实,按毛泽东的说法,蒋介石不仅仅将了一军(即激将法),而且将了两军(详后);对于 国民党方面造的谣言,新华社发表社论予以驳斥则是反将了一军。可见,双方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 宣传战,而宣传战的目的正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或贬损对方的政治形象,这也就是蒋所谓从 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蒋之所以认为可以在政治上打击中共,而中共又必须极力驳斥,则 说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中共是否与日军妥协及其政治形象确实遭到了怀疑。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一方主要着意讨论晋南战役所引起的政治争议,所以他没有明确说中共 究竞出兵没有。另一方则明确说中共拒绝出兵了,并详细分析了中共回应的经过及拒绝出兵的原 因。大约在2005年春夏,杨奎松先生在修订《失去的机会?一一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一书时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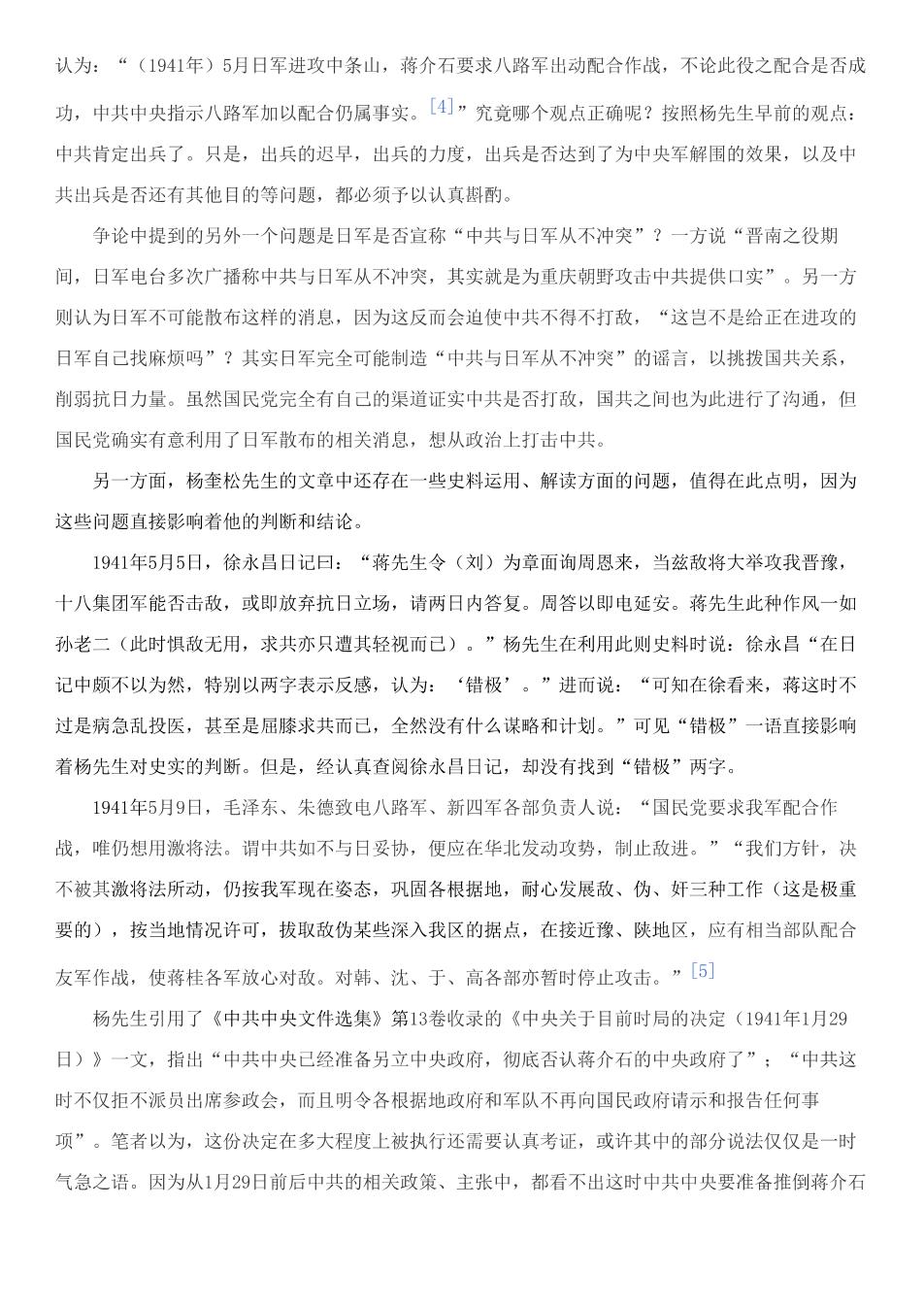
认为:“(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此役之配合是否成 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4]”究竞哪个观点正确呢?按照杨先生早前的观点: 中共肯定出兵了。只是,出兵的迟早,出兵的力度,出兵是否达到了为中央军解围的效果,以及中 共出兵是否还有其他目的等问题,都必须予以认真斟酌。 争论中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日军是否宣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一方说“晋南之役期 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另一方 则认为日军不可能散布这样的消息,因为这反而会迫使中共不得不打敌,“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 日军自己找麻烦吗”?其实日军完全可能制造“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以挑拨国共关系, 削弱抗日力量。虽然国民党完全有自己的渠道证实中共是否打敌,国共之间也为此进行了沟通,但 国民党确实有意利用了日军散布的相关消息,想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另一方面,杨奎松先生的文章中还存在一些史料运用、解读方面的问题,值得在此点明,因为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判断和结论。 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记曰:“蒋先生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 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 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杨先生在利用此则史料时说:徐永昌“在日 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进而说:“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 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己,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可见“错极”一语直接影响 着杨先生对史实的判断。但是,经认真查阅徐永昌日记,却没有找到“错极”两字。 1941年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说:“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 战,唯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 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 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 友军作战,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5] 杨先生引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收录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 日)》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中共这 时不仅拒不派员出席参政会,而且明令各根据地政府和军队不再向国民政府请示和报告任何事 项”。笔者以为,这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还需要认真考证,或许其中的部分说法仅仅是一时 气急之语。因为从1月29日前后中共的相关政策、主张中,都看不出这时中共中央要准备推倒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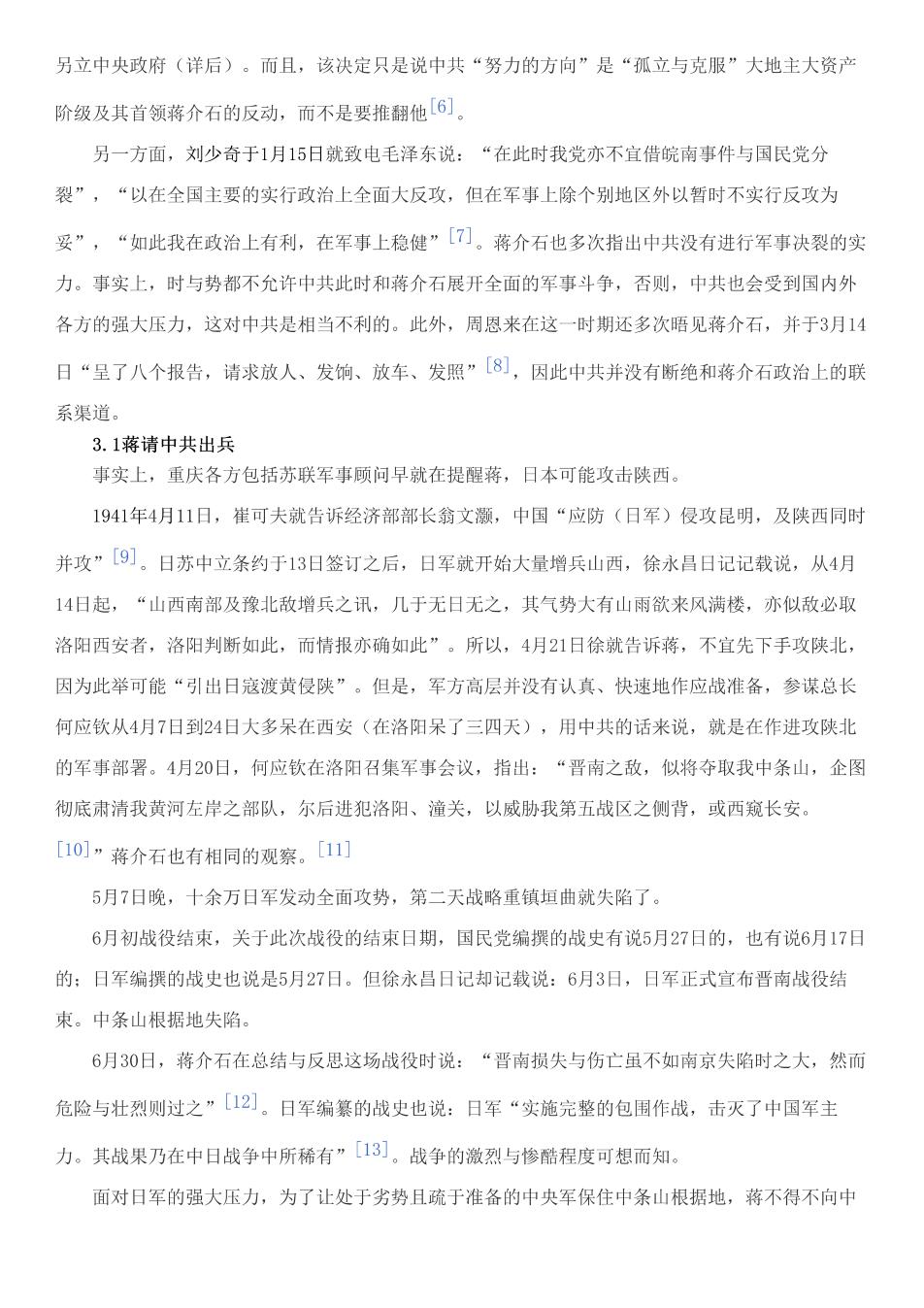
另立中央政府(详后)。而且,该决定只是说中共“努力的方向”是“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而不是要推翻他[6]。 另一方面,刘少奇于1月15日就致电毛泽东说:“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 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 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7门。蒋介石也多次指出中共没有进行军事决裂的实 力。事实上,时与势都不允许中共此时和蒋介石展开全面的军事斗争,否则,中共也会受到国内外 各方的强大压力,这对中共是相当不利的。此外,周恩来在这一时期还多次晤见蒋介石,并于3月14 日“呈了八个报告,请求放人、发饷、放车、发照”[8],因此中共并没有断绝和蒋介石政治上的联 系渠道。 3.1蒋请中共出兵 事实上,重庆各方包括苏联军事顾问早就在提醒蒋,日本可能攻击陕西。 1941年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诉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中国“应防(日军)侵攻昆明,及陕西同时 并攻”[9]。日苏中立条约于13日签订之后,日军就开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记记载说,从4月 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之讯,几于无日无之,其气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亦似敌必取 洛阳西安者,洛阳判断如此,而情报亦确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诉蒋,不宜先下手攻陕北, 因为此举可能“引出日寇渡黄侵陕”。但是,军方高层并没有认真、快速地作应战准备,参谋总长 何应钦从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阳呆了三四天),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在作进攻陕北 的军事部署。4月20日,何应钦在洛阳召集军事会议,指出:“晋南之敌,似将夺取我中条山,企图 彻底肃清我黄河左岸之部队,尔后进犯洛阳、潼关,以威胁我第五战区之侧背,或西窥长安。 [10]”蒋介石也有相同的观察。[1 5月7日晚,十余万日军发动全面攻势,第二天战略重镇垣曲就失陷了。 6月初战役结束,关于此次战役的结束日期,国民党编撰的战史有说5月27日的,也有说6月17日 的:日军编撰的战史也说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记却记载说:6月3日,日军正式宣布晋南战役结 束。中条山根据地失陷。 6月30日,蒋介石在总结与反思这场战役时说:“晋南损失与伤亡虽不如南京失陷时之大,然而 危险与壮烈则过之”12]。日军编纂的战史也说:日军“实施完整的包围作战,击灭了中国军主 力。其战果乃在中日战争中所稀有”[13]。战争的激烈与惨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为了让处于劣势且疏于准备的中央军保住中条山根据地,蒋不得不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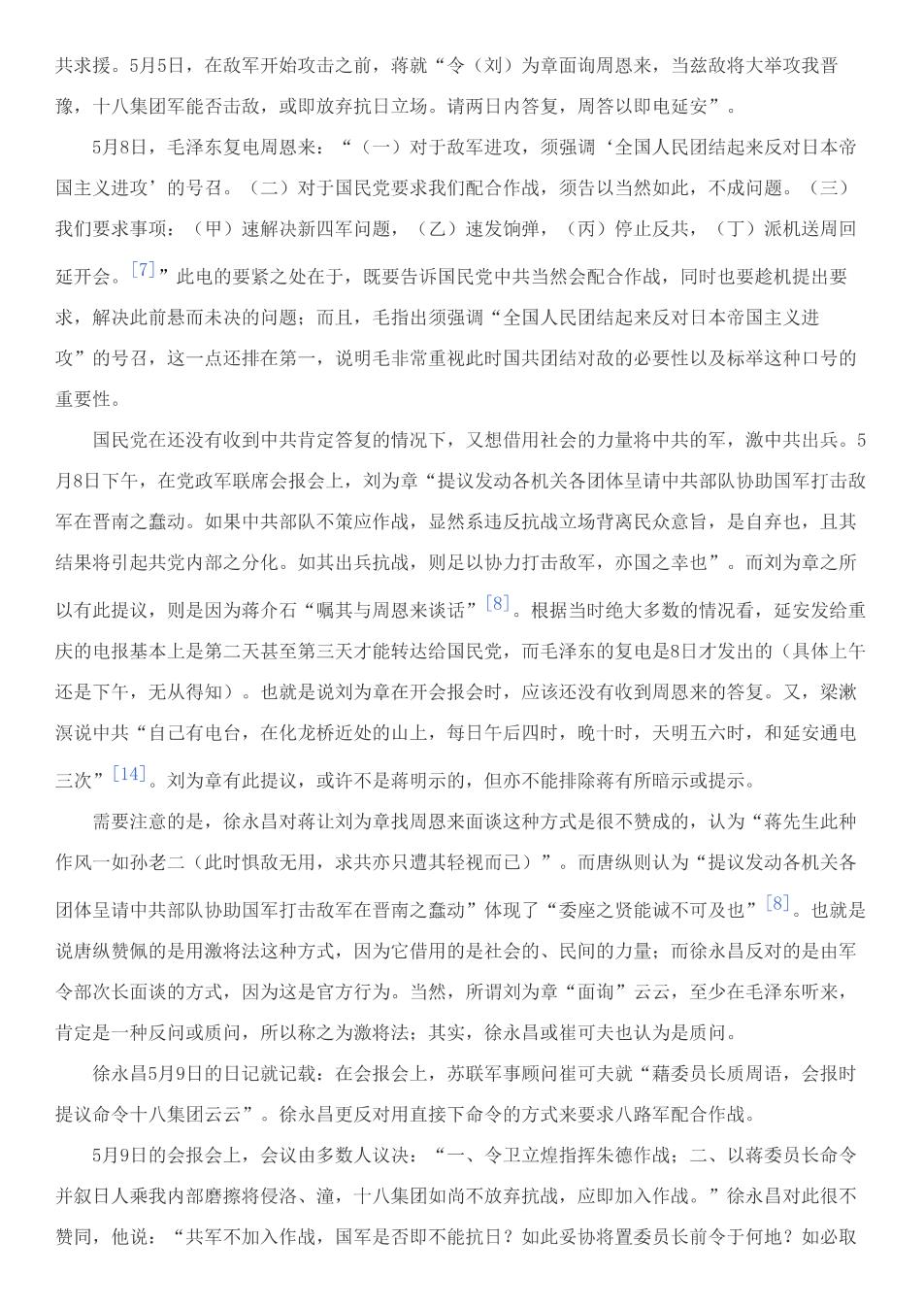
共求援。5月5日,在敌军开始攻击之前,蒋就“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 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 5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 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 延开会。[门”此电的要紧之处在于,既要告诉国民党中共当然会配合作战,同时也要趁机提出要 求,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毛指出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 攻”的号召,这一点还排在第一,说明毛非常重视此时国共团结对敌的必要性以及标举这种口号的 重要性。 国民党在还没有收到中共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又想借用社会的力量将中共的军,激中共出兵。5 月8日下午,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 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 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而刘为章之所 以有此提议,则是因为蒋介石“嘱其与周恩来谈话”[8]。根据当时绝大多数的情况看,延安发给重 庆的电报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转达给国民党,而毛泽东的复电是8日才发出的(具体上午 还是下午,无从得知)。也就是说刘为章在开会报会时,应该还没有收到周恩来的答复。又,梁漱 溟说中共“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 三次”[14]。刘为章有此提议,或许不是蒋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蒋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对蒋让刘为章找周恩来面谈这种方式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蒋先生此种 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而唐纵则认为“提议发动各机关各 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体现了“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8]。也就是 说唐纵赞佩的是用激将法这种方式,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的、民间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对的是由军 令部次长面谈的方式,因为这是官方行为。当然,所谓刘为章“面询”云云,至少在毛泽东听来, 肯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所以称之为激将法:其实,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认为是质问。 徐永昌5月9日的日记就记载:在会报会上,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就“藉委员长质周语,会报时 提议命令十八集团云云”。徐永昌更反对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5月9日的会报会上,会议由多数人议决:“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命令 并叙日人乘我内部磨擦将侵洛、潼,十八集团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对此很不 赞同,他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