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不久,地狱巢打架咬脖子的现象明显减少。有权有势的都廂 了律师代理:没钱的每人发一本《阁罗六法》于册,计他们请律 师打官可维护灵魂权利。阎王爷还下诮小达学院培训判官宣传法 治,接下米还准备延骋专家起草宪法。 一开始,人间禁止报道地狱改,凡捉造、散或听信谣 言若一律收容审查,知情不举者追究责任。然血不出仁月,还是 透露出一点风声。一说网上可以查到;万联网接通地狱,是中央 情报局的阴谋。一说阁王爷出了大价钱,要挖人问的法律人才小。总 之,现在明里不说,但圈内人十已经在传:一旦地狱建成法治,下 不下地狱便尢所谓了。 二00三年六月 从前没有律师9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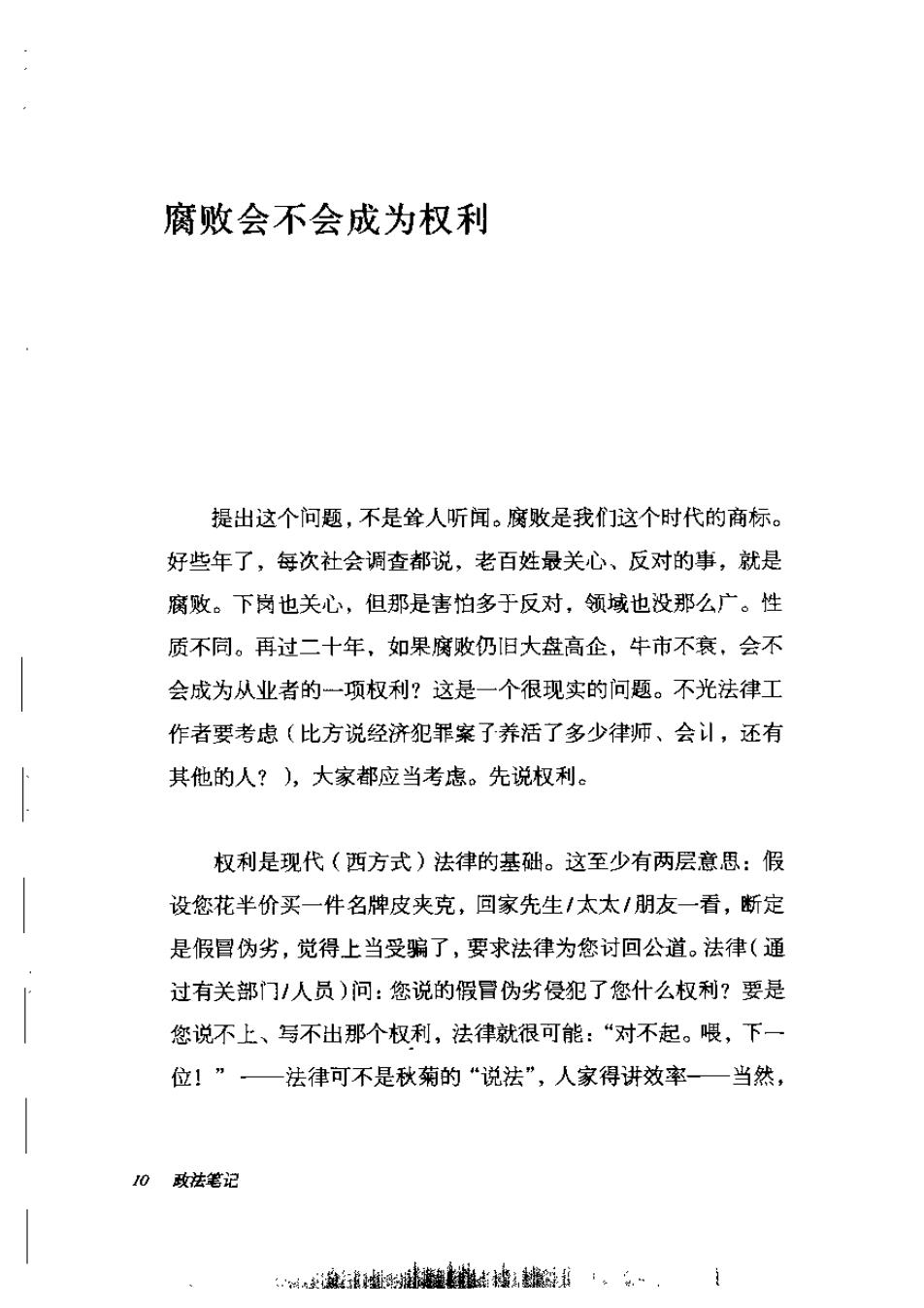
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耸人听闻。腐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商标。 好些年了,每次社会调查都说,老百姓最关心、反对的事,就是 腐败。下岗也关心,但那是害怕多于反对,领域也没那么广。性 质不同。再过二十年,如果腐败仍旧大盘高企,牛市不衰,会不 会成为从业者的一项权利?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光法律工 作者要考虑(比方说经济犯罪案了养活了多少律师、会川,还有 其他的人?),大家都应当考虑。先说权利。 权利是现代(西方式)法律的基础。这至少有两层意思:假 设您花半价买一件名牌皮夹克,回家先生/太太/朋友一看,断定 是假冒伪劣,觉得上当受骗了,要求法律为您讨回公道。法律(通 过有关部门/人员)问:您说的假冒伪劣侵犯了您什么权利?要是 您说不上、写不出那个权利,法律就很可能:“对不起。喂,下一 位!”—法律可不是秋菊的“说法”,人家得讲效率-一当然, 0政法笔记 时盈:逢描菲·、。-

受贿徇情枉法的不算。原来,权利是一种资格、能力、特许、豁 免,有了它(再加上其他必要的条件,例如金钱、知识、时间), 才能劳法律的大驾,保护或促进以权利命名的各种利益。这是第 一层意思。第二层,假设您说出了自己主张的权利,法律却仍不 能还您公道。例如您要求像“王海打假”那样,按照《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双倍赔偿,法律却不承认您是“消费者”,因为据调查 您是“知假头假”。这条理由,背后的那通理论、那场辩论、那杆 标准,偏偏就有某项据说跟您冲突、比您重要的权利作依据。宣 传出去,很多人都同意:法律没错,为索赔而“消费”,动机不纯, 哪能鼓励呀?这么看,权利还是用来解释、宜传、生产和消灭(上 述第-一层意思的)权利的那一套套理由、理论、辩论和标准的总 归宿。通俗地说,就是意识形态。特指马克思批判过的那部掩盖 着矛盾的和倒置的现实的法权神话:“那座人入的固有权利的伊甸 园,那个大写的自由、平等、物权同边沁(Bentham)的唯一领地” (《资本论》卷一章六)。注:边沁(1748一1832)是英国法学家, 神章(四岁通拉丁语),善改革,创功利派哲学及“全视”无死角 环形监狱(panopticon)。死后遵其嘱附,遗体(蜡头肉身玻璃棺) 存伦敦大学学院 举一个有名的案例说明: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倪培璐和王颖到北京国贸中心 下属的惠康超级市场购物。在糖果柜台前看了一会,然后到另 脑敏会不会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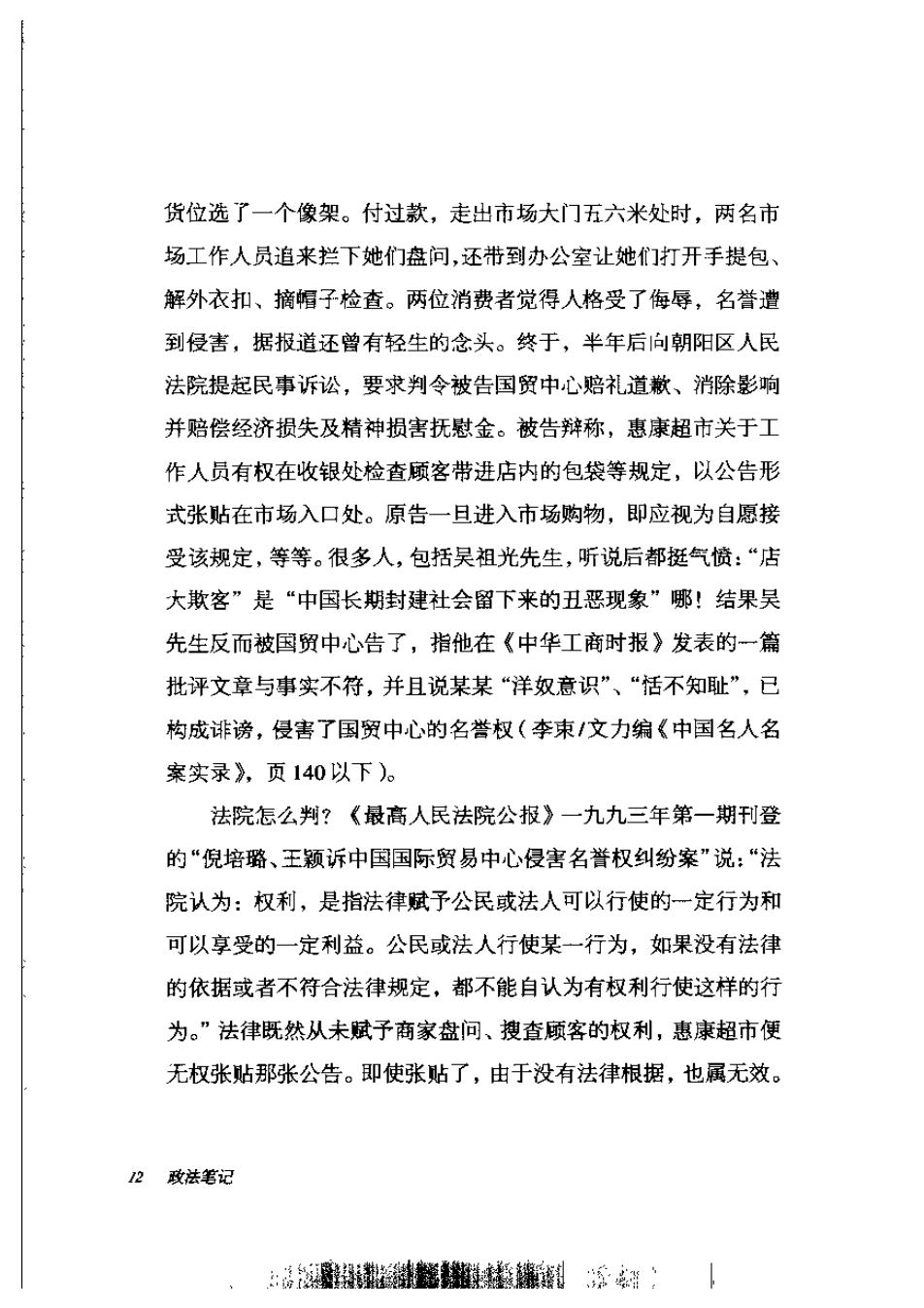
货位选了一个像架。付过款,走出市场大门五六米处时,两名市 场工作人员追来拦下她们盘问,还带到办公室让她们打开手提包、 解外衣扣、摘帽子检查。两位消费者觉得人格受了侮辱,名誉遭 到侵害,据报道还曾有轻生的念头。终于,半年后问朝阳区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国贸中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辩称,惠康超市关于工 作人员有权在收银处检查顾客带进店内的包袋等规定,以公告形 式张贴在市场入口处。原告一旦进入市场购物,即应视为自愿接 受该规定,等等。很多人,包括吴祖光先生,听说后都挺气愤:“店 大欺客”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留下来的丑恶现象”哪!结果吴 先生反而被国贸中心告了,指他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的一篇 批评文章与事实不符,并且说某某“洋奴意识”、“活不知耻”,已 构成诽谤,侵害了国贸中心的名誉权(李束1文力编《中国名人名 案实录》,页140以下)。 法院怎么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刊登 的“倪培路、王颗诉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侵害名誉权纠纷案”说:“法 院认为:权利,是指法律赋予公民或法人可以行使的一定行为和 可以享受的一定利益。公民或法人行使某一行为,如果没有法律 的依据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都不能自认为有权利行使这样的行 为。”法律既然从未赋子商家盘问、搜查倾客的权利,惠康超市便 无权张贴那张公告。即使张贴了,由于没有法律根据,也属无效。 2政法笔记 魔能维鲜罐茶:

超市和(推定看了公告,接受其规定)进入超市购物的硕客之间, 形成不了契约关系。没有契约上的权利,仅仅因为怀疑(而无确 凿证据)原告偷拿货物,就盘问、搜查,便是严重侵害原告“依 法享有”的名誉权。最后,经法院“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被告 表示愿向原告道歉并各付一干元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补偿,请求 原告撤诉。原告接受了“补偿费”,同意自行和解。法院裁定,准 予澈诉。 表面上,“法院认为”一段似乎主张权利法定,调过头米以法 律为权利的基础,拒绝契约自由的原则。实际上这里有-个宪法 性约束或难题,就是人民法院无权解释《宪法》:本来可能直接适 用本案的《宪法》条款,如“禁止.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 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七条),在审判中 不许引用、讨论。法院只好借口权利法定,将“找法作业”推给 被告,绕开这个难题(刘连泰《我国宪法规范》,页17)。说不出 法律“赋予”即无权利张贴公告,这样的推论,当然是现实的倒 置:大写的权利(意识形态)对权利的否定,或权利话语的无穷 循环。 然而“法院认为”作为司法文件公开发表,和被告请求和解 -样,也是法院“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结果,即以事实(问 题)和是非(价值)为出发点界定权利、解释法律。所以此案同 时表明,权利的界定在司法实践(和实际生活)中可以是“机会 腐做会不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