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可以得到的。但是,着来我们不得不接受它内在的变幻无常, 特别是当我们着眼于它的比较强烈的形式时。高峰体验不会持 续,也无法持续很久。强烈的幸福是偶发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 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对统治我们达3千年之久的幸福理 论进行修正,这种理论决定着我们的各种概念,如天国、伊甸园、美 满生活、美好社会、完善的人等等概念。我们传统的爱情故事结尾 时总是说“他们打那以后直幸福的生活着”。我们的杜会改良和 社会革命理论也是从来如此。种种喋喋不休的宣传,例如对我们 社会中虽然极其有限但是确有其事的改良的宜传,我们也早就听 够了,因而也就倍感失望。为了工联主义,为了妇女选举权,为了 直接选举参议员,为了按收入缴纳所得税,为了许多已被我们写进 宪法修正案的改良所进行的喋喋不休的宣传,我们也早就听够了。 每一种改良都说是能带来黄金时代,带来永久的幸福,带来所有问 题的最终解决。结果则往往是碰了事实之壁后的幻灭。但是幻灭 意味着曾经有过幻想。这一点似乎可以明明白白地讲清楚:我们 期待着改良,这完全合情合理;但我们如果还期待着什么十全十 美,什么永久的幸福,那就再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 1 有一个事实尽管现在看来已经十分明显,但却几乎是被普遗 地忽略了。对此,我也必须唤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我们已经得到 的好处,慢慢地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会被忘记,会从意识中消 失,最后甚至会不再被珍惜一至少在它们没有被割夺前是这祥 (可以参见483)。例如,当我于1970年1月写这篇前言时,美国文化 的典型特征便是:在150年间所一直为之奋斗并最终获得的无可 置疑的进展和改良,却被许多没有头脑的浅薄之辈轻蔑地抛到一 边,认为全都是虚假和毫无价值的,不值得为之一战,不值得捍卫, 不值得珍惜。而这,只不过是因为社会尚未十全十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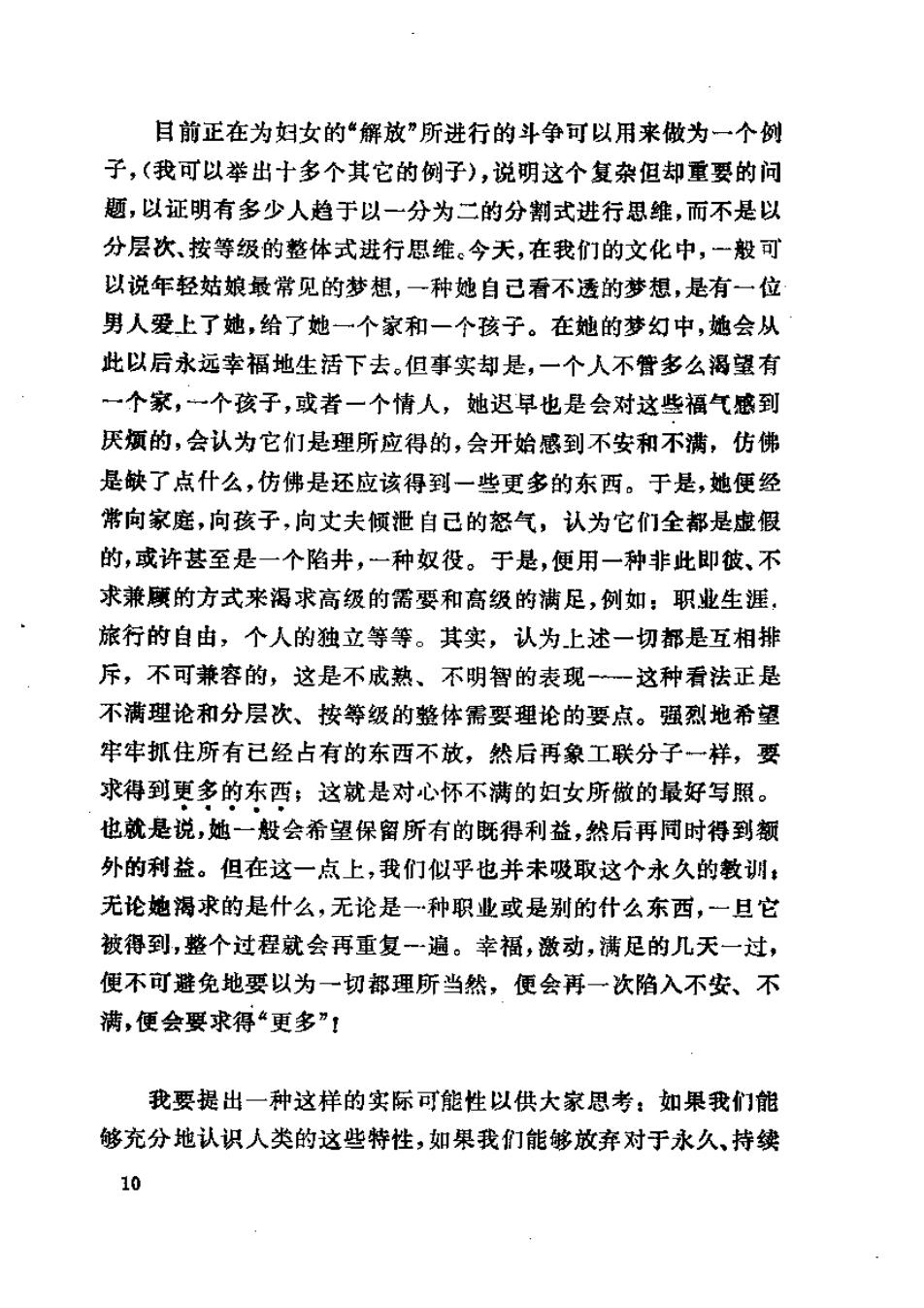
目前正在为妇女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可以用来做为一个例 子,(我可以举出十多个其它的例子),说明这个复杂但却重要的问 题,以证明有多少人趋于以一分为二的分割式进行思雏,而不是以 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式进行思维。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毅可 以说年轻姑娘最常见的梦想,一种她自已看不透的梦想,是有一位 男人爱上了她,给了她一个家和一个孩子。在她的梦幻中,她会从 此以后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事实却是,一个人不管多么褐望有 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情人,她迟早也是会对这些福气感到 厌须的,会认为它们是理所应得的,会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仿佛 是缺了点什么,仿佛是还应该得到一些更多的东西。于是,她便经 常向家庭,向孩子,向丈夫倾泄自己的怒气,认为它们全都是虚假 的,或许甚至是一个陷井,一种奴役。于是,便用一种非此即彼、不 求兼膜的方式来渴求高级的需要和高级的满足,例如:职业生涯, 旅行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等等。其实,认为上述一切都是互相排 斥,不可兼容的,这是不成熟、不明智的表现一一这种看法正是 不满理论和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需要理论的要点。强烈地希望 牢牢抓住所有已经占有的东西不放,然后再象工联分子一样,要 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对心怀不满的妇女所做的最好写照。 也就是说,她一般会希望保留所有的既得利益,然后再同时得到额 外的利益。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也并未吸取这个永久的教训: 无论她褐求的是什么,无论是一一种职业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一且它 被得到,整个过程就会再重复-遍。幸福,激动,满足的儿天一过, 便不可避免地要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便会再一次陷入不安、不 满,便会要求得“更多”! 我要提出一种这样的实际可能性以供大家思考:如果我们能 够充分地认识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对于永久、持续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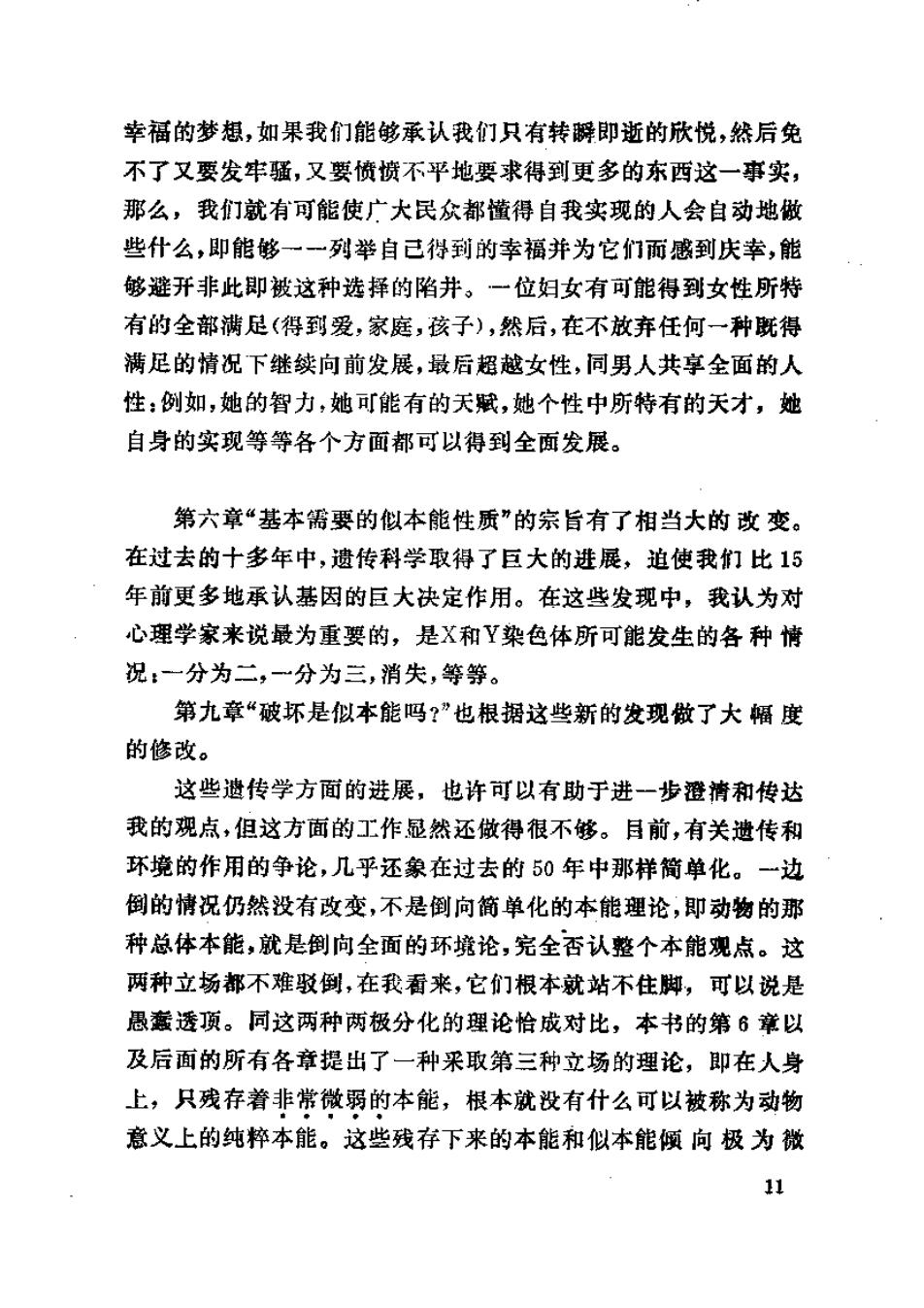
幸福的梦想,如果我们能够承认我们只有转解即逝的欣悦,然后免 不了又要发牢骚,又要愤愤不平地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一事实,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广大民众都懂得自我实现的人会自动地做 些什么,即能够一一列举自己得到的幸福并为它们而感到庆幸,能 够避开非此即被这种选择的陷井。一位妇女有可能得到女性所特 有的全部满足(得到爱,家庭,孩子),然后,在不放弃任何一种既得 满足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最后超越女性,同男人共享全面的人 性:例如,她的智力,她可能有的天赋,她个性中所特有的天才,她 自身的实现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 第六章“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的宗旨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遗传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迫使我们比15 年前更多地承认基因的巨大决定作用。在这些发现中,我认为对 心理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X和Y染色体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 况: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消失,等等。 第九章“破坏是似本能吗?”也根韬这些新的发现做了大幅度 的修改。 这些遗传学方面的进展,也许可以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传达 我的观点,但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做得很不够。目前,有关遗传和 环境的作用的争论,几平还象在过去的50年中那样简单化。一边 倒的情祝仍然没有改变,不是倒向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动物的那 种总体本能,就是倒向全面的环境论,完全否认整个本能观点。这 两种立场都不难驳倒,在我看来,它们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以说是 愚藏透顶。同这两种两极分化的理论恰成对比,本书的第6章以 及后面的所有各章提出了一种采取第三种立场的理论,即在人身 上,只残存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动物 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下来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极为微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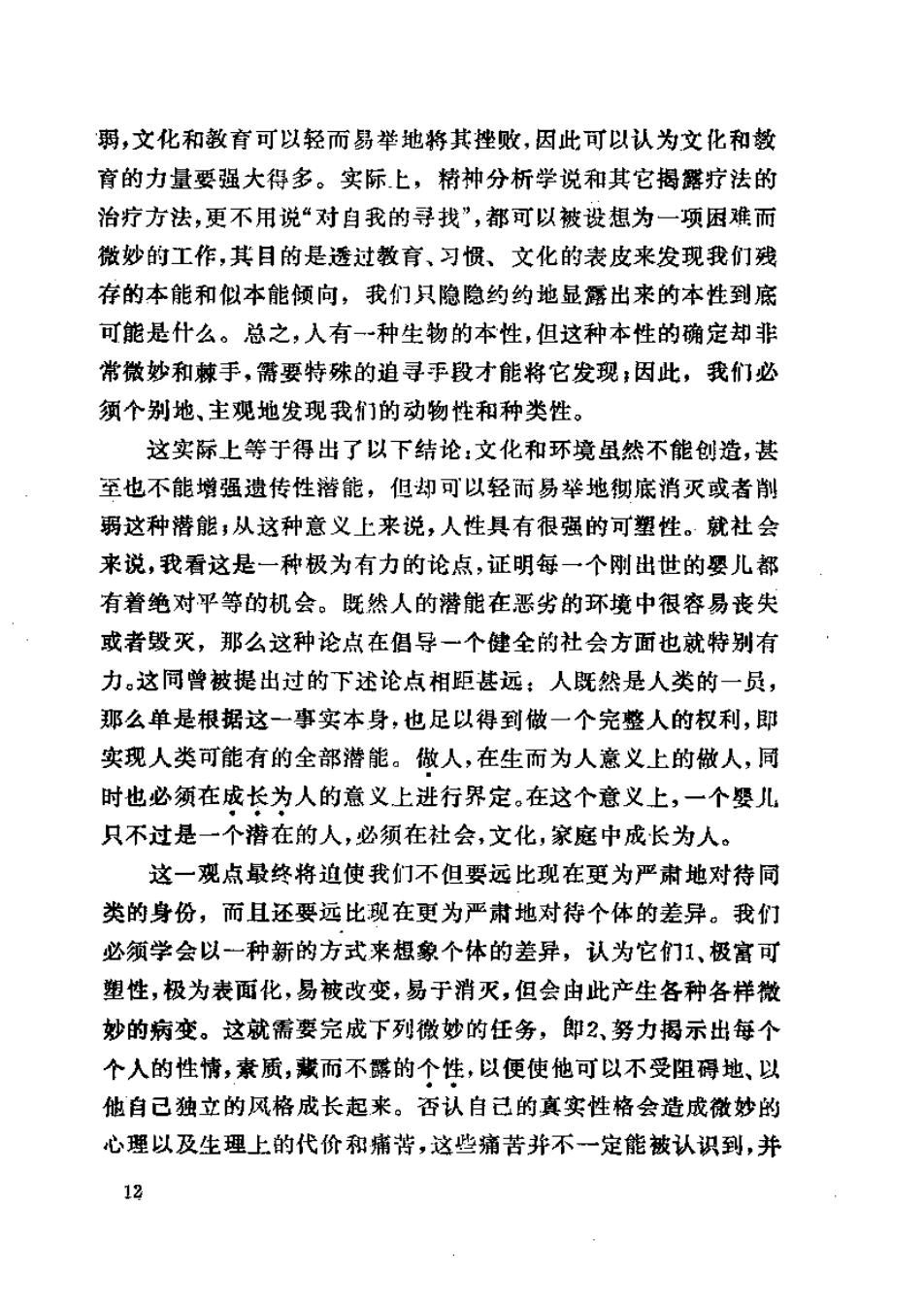
弱,文化和教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挫败,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和教 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精神分析学说和其它揭露疗法的 治疗方法,更不用说“对自我的寻找”,都可以被设想为一项困难而 微妙的工作,其目的是透过教育、习惯、文化的表皮来发现我们残 存的本能和似本能领向,我们只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的本性到底 可能是什么。总之,入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这种本性的确定却非 常微妙和棘手,箫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它发现:因此,我们必 须个别地、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种类性。 这实际上等于得出了以下结论: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 至也不能增强遗传性濬能,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或者削 弱这种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就杜会 来说,我看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论点,证明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都 有着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人的潜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丧失 或者毁灭,那么这种论点在倡导一个健全的社会方面也就特别有 力。这同曾被提出过的下述论点相距甚远: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员 那么单是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也足以得到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即 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意义上的做人,同 时也必须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婴儿 只不过是一个潜在的人,必须在社会,文化,家庭中成长为人。 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不但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同 类的身份,而且还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个体的差异。我们 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想象个体的差异,认为它们1、极富可 塑性,极为表面化,易被改变,易于消灭,但会由此产生各种各样微 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下列微妙的任务,即2、努力揭示出每个 个入的性情,素质,裁而不露的个性,以便使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以 他自己独立的风格成长起来。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造成微妙的 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能被认识到,并 12

不容易从外表看出,但上述态度却要求心理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极 大关注来对待这种代价和痛苦。这转过来又意味着要对每一个年 龄阶段上的“健康成长”的实用意义给予更为细心的关注。 最后,我必须指出,如果放东社会的不平等这个借口,就会产 生令人战栗的后果;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准备好应付这种后果。我 们越是不断地消灭社会的不平等,就越是能发觉它会被“生物的不 平等”取而代之,因为婴儿一生到世上就有着不同的遗传潜能。如 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能向每一个婴儿的优势潜能提供充分机会的程 度,那就意味着我们同时也要接受他们的劣势潜能。如果一个婴 儿出生时心胜就有毛病,或者肾的功能就不健全,或者神经系统就 有缺陷,那我们又该怪谁呢?如果只能怪造物,那么对这位受到了 造物本身“虐待”的人的自尊,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一章里,同时也在其:它一些论文中,我首创了“主观生物 学”这一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弥合主观与 客观以及现象与行为之间的鸿沟。我发现,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内 省地和主观地研究自身的生物学;我希望这一发现对别人也会有 所神益,特别是对于生物学家。 论述破坏性的第九章得到了全面的修订。我把它归到了范围 更广的邪恶心理学类下,希望通过详细论述邪恶的一个方面,来证 明整个问题在经验上和科学上是可以解决的。将它置于经验科学 的管辖范围之内,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我 们的了解会有稳步的增长,而这总是意味着有可能就此采取某些 措施了。 我们已经知道,进攻性是受遗传和文化两个方面决定的。而 且我还认为,键康的和不健康的进攻性之间的区别是极端重要的。 正如进攻性既不能完全归绺于社会,也不能完全均咎于内在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