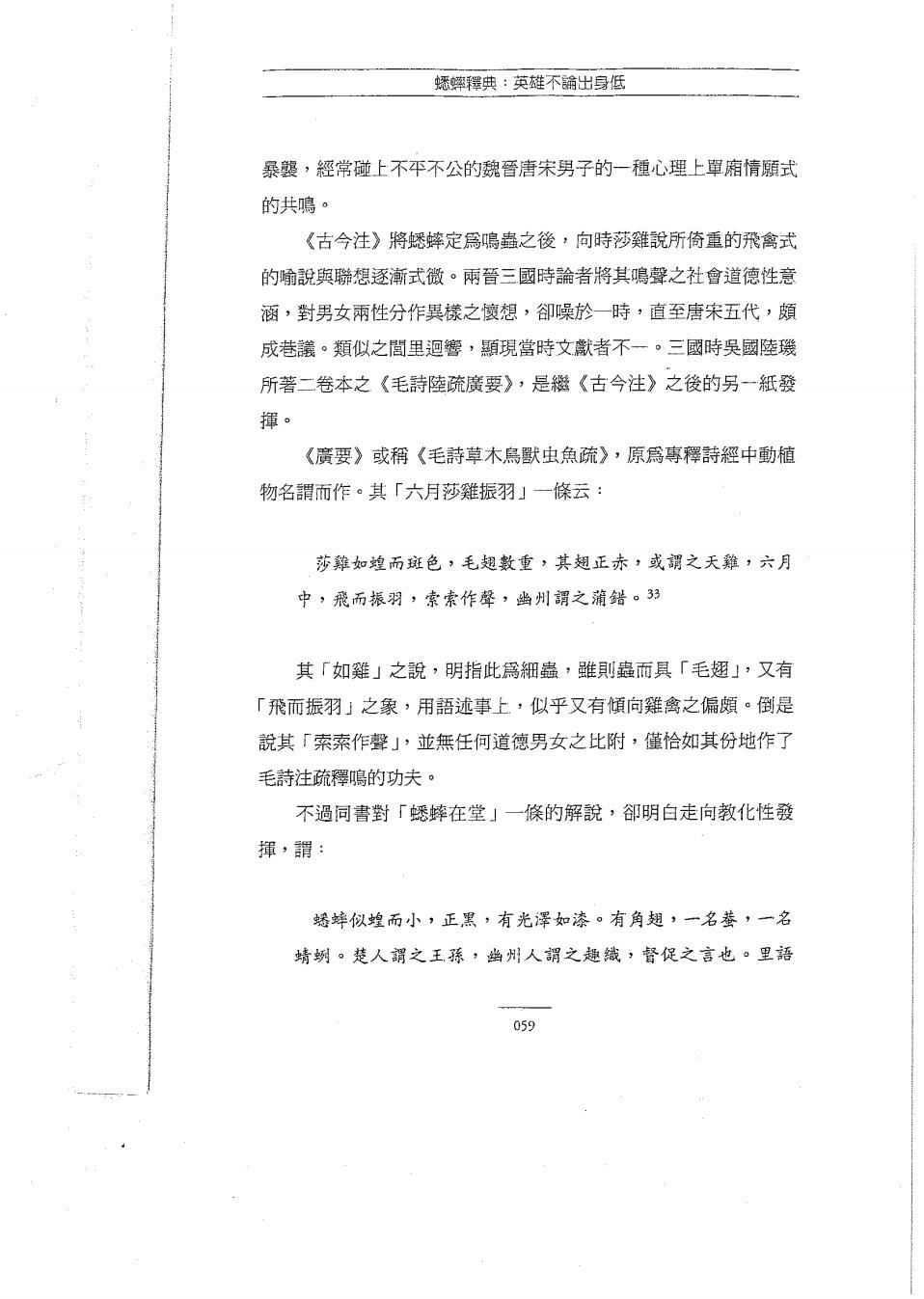
蟋蟀釋典:英雄不論出身低 暴襲,經常碰上不平不公的魏晉唐宋男子的一種心理上單廂情願式 的共鳴。 《古今注》將蟋蟀定篇鳴蟲之後’向時莎雞說所倚重的飛禽式 的喻說與聯想逐漸式微。兩晉三國時論者將其鳴聲之社會道德性意 涵,對男女雨性分作異樣之懷想,卻噪於一時,直至唐宋五代,頗 成巷議。類似之閭里迴響,顯現當時文獻者不一。三國時吳國陸璣 所著二卷本之《毛詩陸疏廣要》,是繼《古今注》之後的另一紙發 揮。 《廣要》或稱《毛詩草木鳥獸虫魚疏》,原爲專釋詩經中動植 物名謂而作·其「六月莎雞振羽」一條云: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 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33 其「如雞」之說,明指此爲細蟲·雖則蟲面具「毛翅」,又有 「飛而振羽」之象,用語述事上,似乎又有傾向雞禽之偏頗。倒是 說其「索索作聲」,並無任何道德男女之比附,僅恰如其份地作了 毛詩注疏釋鳴的功夫。 不過同書對「蟋蟀在堂」一倏的解說,卻明白走向教化性發 揮,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荟,一名 蜻蜊。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 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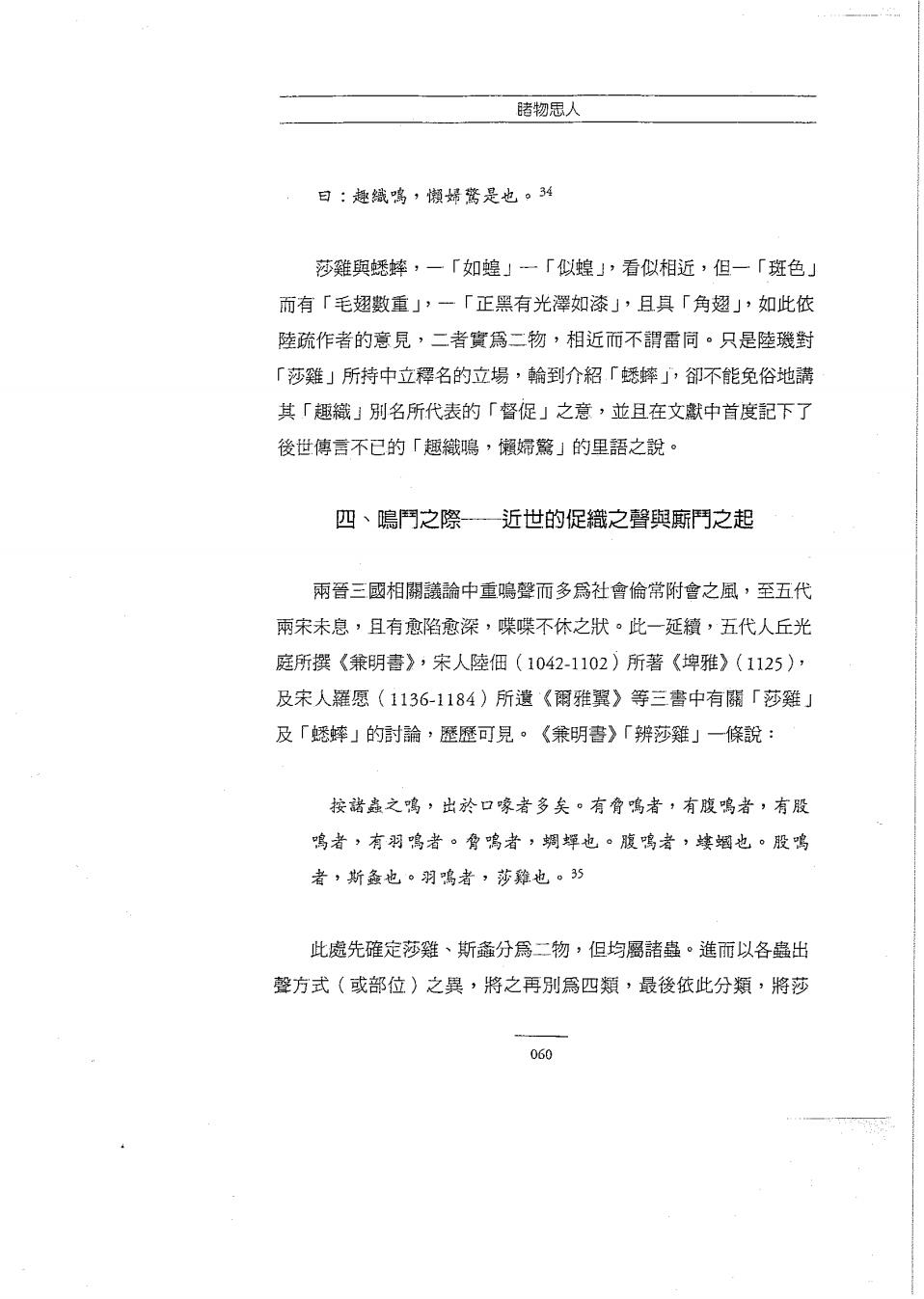
睹物思人 曰:趣織鳴,懶婦驚是也。34 莎雞與蟋蟀,一「如蝗」一「似蝗」,看似相近,但一「斑色」 而有「毛翅數重」,一「正黑有光澤如漆」·且具「角翅」,如此依 陸疏作者的意見,二者實爲二物,相近而不謂雷同。只是陸璣對 「莎雞」所持中立釋名的立場,輪到介紹「蟋蟀」,卻不能免俗地講 其「趣織」别名所代表的「督促」之意,並且在文默中首度記下了 後世傳言不已的「趣織鳴,懶婦驚」的里語之說。 四、偏鬥之際一近世的促織之謦與廝鬥之起 兩晉三國相關議論中重鳴警而多爲社會倫常附會之風,至五代 雨宋未急,且有愈陷愈深,喋喋不休之狀·此一延續,五代人丘光 庭所撰《兼明書》;宋人陸佃(1042-1102)所著《埤雅》(1125), 及宋人羅愿(1136-1184)所遺《爾雅翼》等三書中有關「莎雞」 及「蟋蟀」的討論,歷歷可見。《策明書》「辨莎雞」一條說: 按諾蟲之鳴,出於口喙者多矣。有會鳴者;有腹鳴者,有股 鳴者,有羽鳴者。骨鳴者,蜩蟬也。腹鳴者,蝼蟈也。股鳴 者,斯螽也。羽嗚者,莎雞也。5 此處先確定莎雞、斯螽分爲二物,但均屬諸蟲。進而以各蟲出 聲方式(或部位)之異,將之再別爲四類,最後依此分類,將莎 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