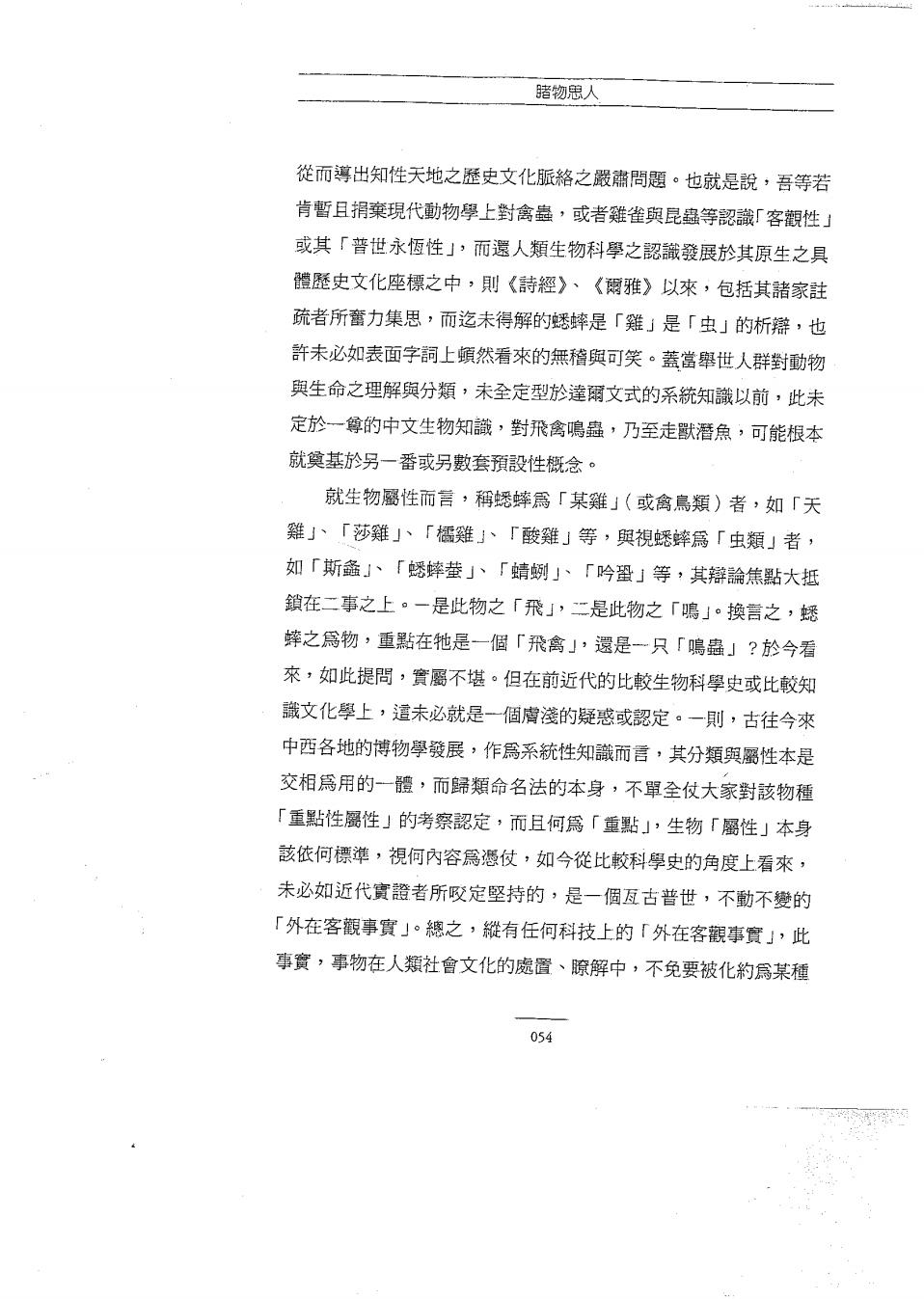
睹物思人 從而導出知性天地之歷史文化脈絡之嚴肅間題。也就是說,吾等若 肯暫且捐棄現代動物學上對禽蟲,或者雞雀與昆蟲等認藏「客觀性」 或其「普世永恆性」,而還人類生物科學之認識發展於其原生之具 體歷史文化座標之中,則《詩經》、《爾雅》以來,包括其諸家註 疏者所奮力集思,而迄未得解的蟋蟀是「雞」是「虫」的析辯,也 許未必如表面字詞上顫然看來的無稽與可笑·蓋當舉世人群對動物 與生命之理解與分類,未全定型於達爾文式的系統知藏以前,此未 定於一算的中文生物知藏,對飛禽鳴蟲,乃至走默潛魚,可能根本 就莫基於另一番或另敷套預設性概念。 就生物屬性而言,稱蟋蟀爲「某雞」(或禽鳥類)者,如「天 雞」~「莎雞」、「櫺雞」、「酸雞」等,與視蟋蟀爲「虫麵」者, 如「斯螽」、「蟋蟀蛬」、「靖蛚」、「吟蛩」等,其辯論焦點大抵 鎖在二事之上。一是此物之「飛」,二是此物之「鳴」·换言之,蟋 蟀之爲物,重點在牠是一個「飛禽」,還是一只「鳴蟲」?於今看 來,如此提間,寶屬不堪。但在前近代的比較生物科學史或比較知 藏文化學上,這未必就是一個膚淺的疑惑或認定。一則,古往今來 中西各地的博物學發展,作爲系統性知識而言,其分類與屬性本是 交相爲用的一醴,而歸類命名法的本身,不單全仗大家對該物種 「重點性屬性」的考察認定,而且何爲「重點」,生物「屬性」本身 蔽依何標準,視何內容篇憑仗,如今從比較科學史的角度上看來, 未必如近代實證者所咬定堅持的,是一個亙古普世,不動不變的 「外在客觀事實」總之,縱有任何科技上的「外在客觀事寶」,此 事竇,事物在人類社會文化的處置、瞭解中,不免要被化約爲某種 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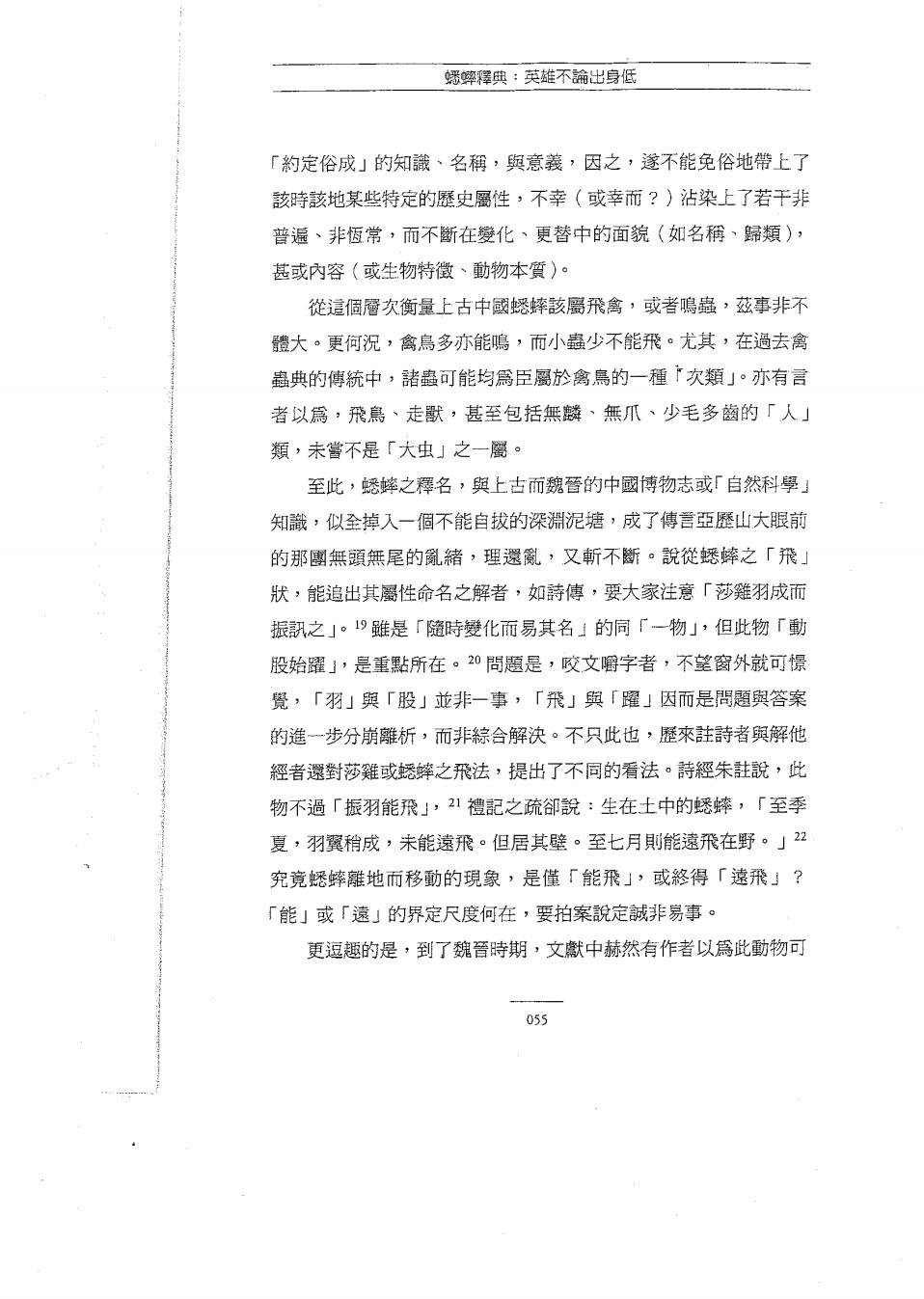
蟋弊釋典:英雄不論出身低 「約定俗成」的知識、名稱,與意義,因之,遂不能免俗地帶上了 該時該地某些特定的歷史屬性,不幸(或幸而?)沾染上了若干非 普遍、非恆常,而不斷在變化、更替中的面貌(如名稱、歸類), 基或内容(或生物特徵~動物本質)。 從這個層次衡量上古中國蟋蟀骸屬飛禽,或者鳴蟲,茲事非不 體大。更何况,禽鳥多亦能鳴,而小蟲少不能飛。尤其,在過去禽 蟲典的傅統中,諸蟲可能均篇臣屬於禽鳥的一種”次類」·亦有言 者以爲,飛鳥、走獸,甚至包括無麟,無爪、少毛多齒的「人」 類,未嘗不是「大虫」之一屬。 至此,蟋蟀之釋名,與上古而魏晉的中國博物志或「自然科學」 知藏,似全掉入一個不能自拔的深淵泥塘,成了傅言亞歷山大眼前 的那團無頭無尾的亂緒,理還亂,又斬不斷。說從蟋蟀之「飛」 狀,能追出其屬性命名之解者,如詩傳,要大家注意「莎雞羽成而 振訊之」。19雖是「隨時變化而易其名」的同「一物」,但此物「動 股始耀」,是重點所在。20問題是,咬文嚼字者,不望窗外就可憬 覺,「形」與「股」並非一事,「飛」與「」因而是問題與答案 的進一步分崩離析,而非綜合解决。不只此也,歷來註詩者與解他 經者還對莎雞或蟋蟀之飛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詩經朱註說,此 物不過「振羽能飛」,1禮記之疏卻說:生在土中的蟋蟀,「至季 夏,羽羹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2 究竟蟋蟀離地而移動的現象,是僅「能飛」,或怒得「速飛」? 「能」或「遠」的界定尺度何在,要拍案說定誠非易事。 更逗趣的是·到了魏晉時期,文獻中赫然有作者以爲此動物可 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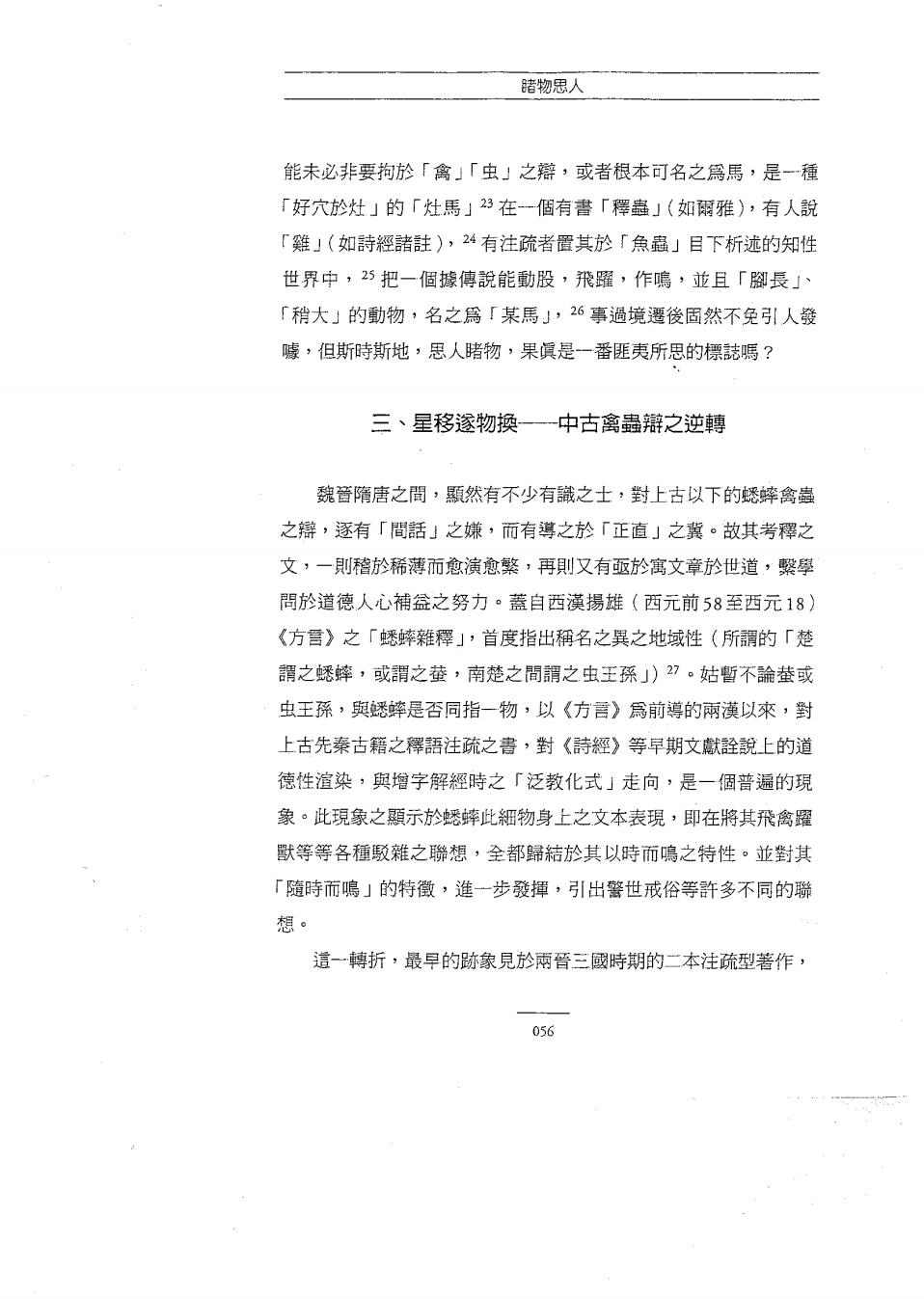
睹物思人 能未必非要拘於「禽」「虫」之幕,或者根本可名之篇馬,是種 「好穴於灶」的「灶馬」23在一個有書「釋蟲」(如爾雅),有人說 「雞」(如詩經藷註),24有注疏者置其於「魚蟲」目下析远的知性 世界中,25把一個據傳說能動股,飛躍,作鳴,並且「腳長」、 「稍大」的動物,名之爲「某馬」,26事過境遷後固然不免引人發 噱,但斯時斯地,思人睹物,果眞是一番匪夷所思的標誌嗎? 三、星移逐物换—中古禽蟲辩之逆轉 魏晉隋唐之間,顯然有不少有識之士·對上古以下的蟋蟀禽蟲 之辯,逐有「間話」之嫌,而有導之於「正直」之冀。故其考釋之 文,一則稽於稀薄而愈演愈繁,再則又有亟於寓文章於世道,繫學 間於道德人心補盒之努力。蓋自西漢揚雄(西元前58至西元18) 《方鲁》之「蟋蟀雜釋」,首度指出稱名之異之地域性(所謂的「楚 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間謂之虫王孫」)27。姑暫不論蛬或 虫王孫,與蟋蟀是否同指一物,以《方言》爲前導的两漢以來,對 上古先秦古籍之釋語注疏之書,對《詩經》等早期文獻詮說上的道 德性渲染,與增字解經時之「泛教化式」走向,是一個普遍的現 象·此現象之顯示於蟋蟀此細物身上之文本表現,即在將其飛禽躍 獸等等各種駁雜之聯想,全都歸結於其以時而鳴之特性。並對其 「隨時而鳴」的特徵,進一步發揮,引出警世戒俗等許多不同的聯 想。 這一轉折,最早的胁象見於雨晉三國時期的二本注疏型著作, 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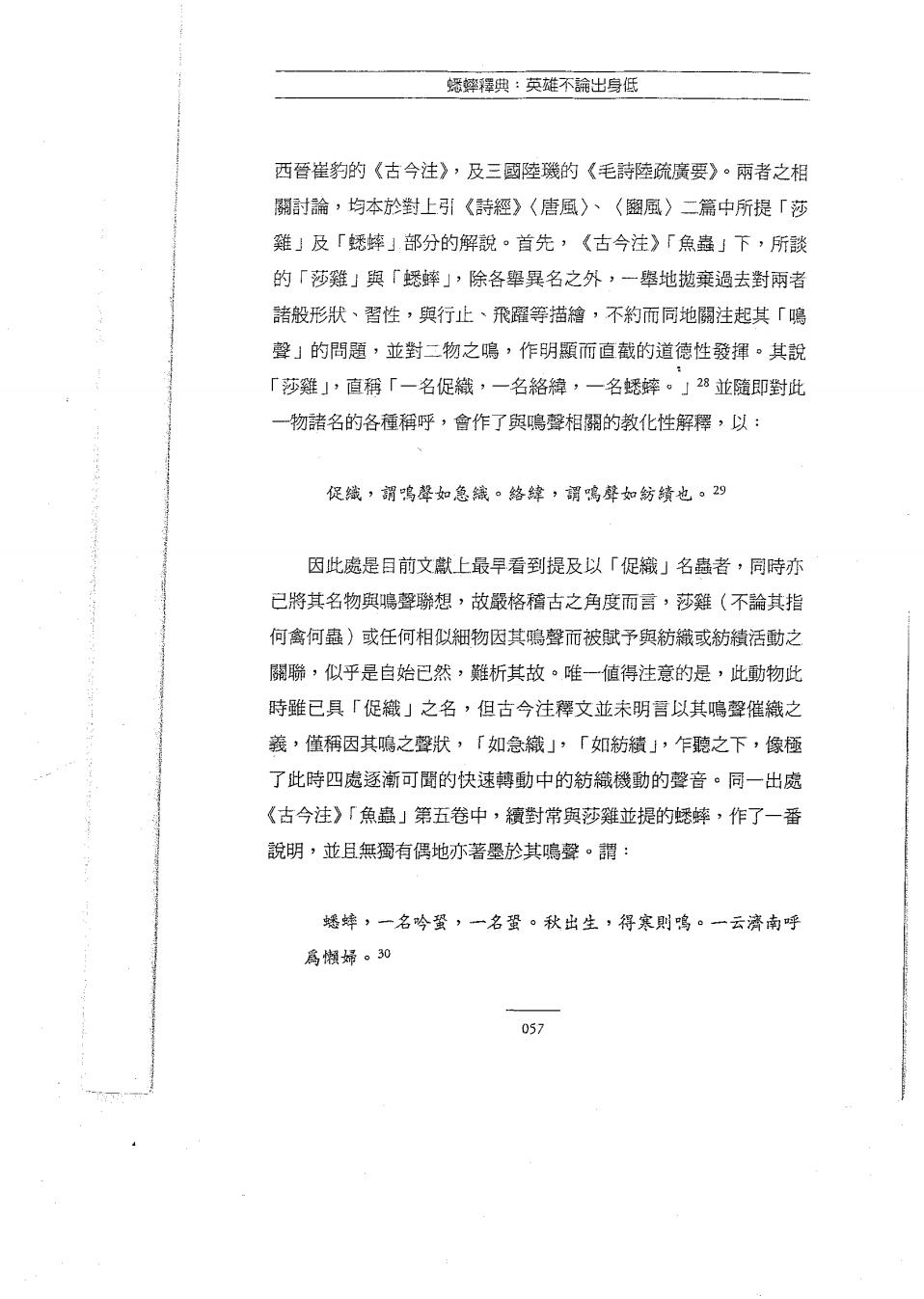
蟋蟀釋典:英雄不論出身低 西管崔豹的《古今注》,及三國陸璣的《毛詩陸疏廣要》。兩者之相 關討論,均本於對上引《詩經》〈唐風〉、〈盥風〉二篇中所提「莎 雞」及「蟋蟀」部分的解說。首先,《古今注》「魚蟲」下,所談 的「莎雞」與「蟋蟀」,除各舉異名之外,一舉地拋棄過去對兩者 者般形状、習性,與行止丶飛躍等描繪,不約而同地關注起其「鳴 聲」的問題,並對二物之鳴,作明顯而直截的道德性發揮·其說 「莎雞」,直稱「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28並隨即對此 一物諸名的各種稱呼,會作了與鳴馨相關的教化性解釋,以: 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鳴聲如紡績也。29 因此處是目前文默上最早看到提及以「促織」名蟲者,同時亦 已將其名物與鳴聲聯想,故嚴格稽古之角度而言,莎雞(不論其指 何禽何蟲)或任何相似細物因其鳴聲而被赋予與紡織或紡績活動之 關聯,似乎是自始已然,難析其故·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此動物此 時雖已具「促織」之名,但古今注釋文並未明言以其鳴聲催織之 義·僅稱因其鳴之馨状,「如急織」,「如紡績」,乍聽之下,像極 了此時四處逐渐可聞的快速轉動中的紡織機動的聲音。同一出處 《古今注》「魚蟲」第五卷中,續對常與莎雞並提的蟋蟀,作了一番 說明,並且無獨有偶地亦著墨於其鳴聲。謂: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出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 爲懶婦。30 0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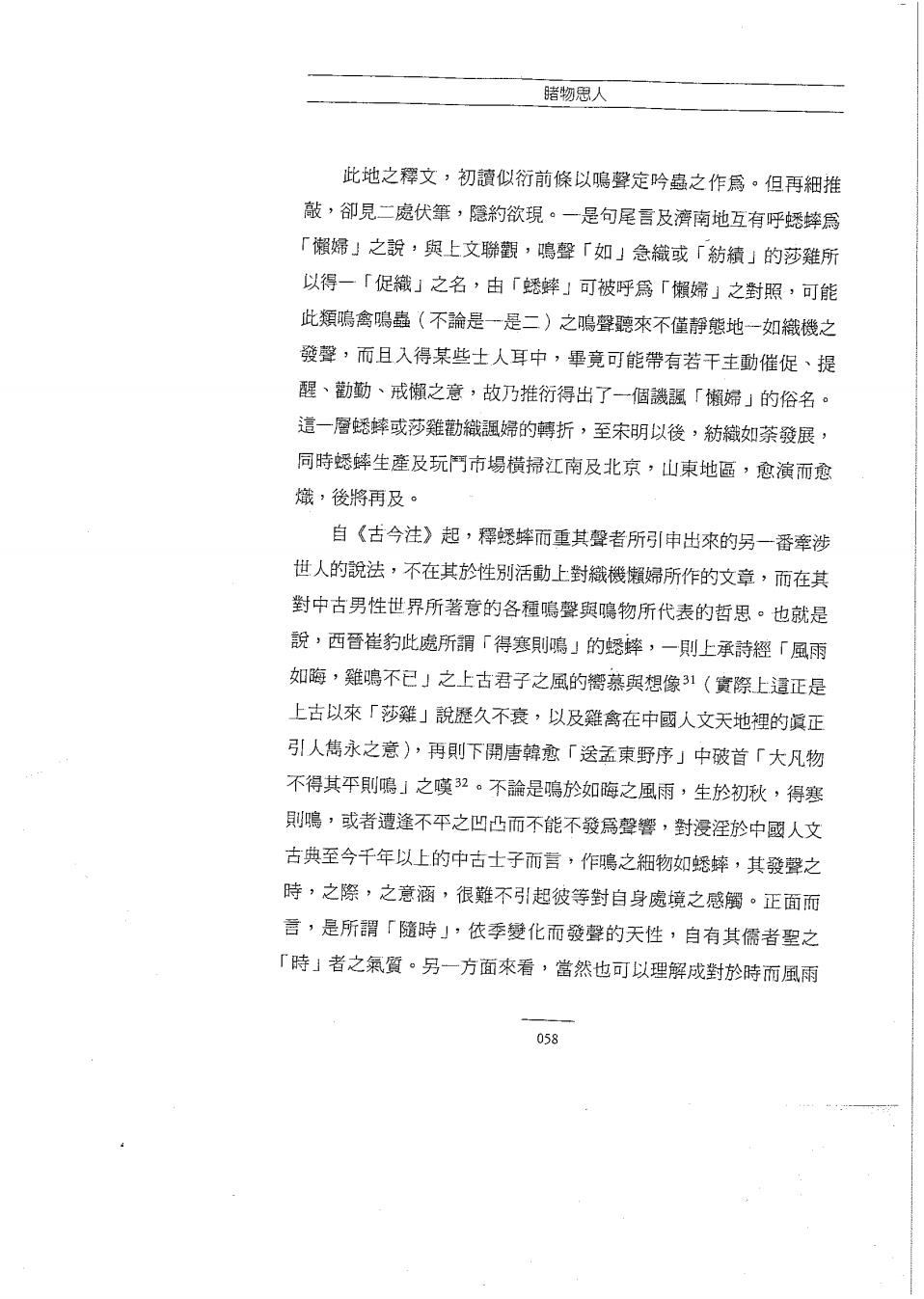
睹物思人 此地之釋文,初讀似衍前條以鳴馨定吟蟲之作爲。但再細推 敲,卻見二處伏筆,隱約欲現。一是句尾言及濟南地互有呼蟋蟀爲 「懶婦」之說,與上文聯觀,鳴聲「如」急織或「紡績」的莎雞所 以得一「促織」之名,由「蟋蟀」可被呼爲「懶婦」之對照,可能 此類鴨禽鳴蟲(不論是一是二)之鳴聲聽來不僅静態地一如織機之 發聲,而且入得某些士人耳中,畢竟可能帶有若干主動催促、提 醒、勸勤、戒懶之意,故乃推衍得出了一個譏飄「懶婦」的俗名· 這一層蟋蟀或莎雞勸織飄婦的轉折,至宋明以後,紡織如茶發展, 同時蟋蟀生產及玩鬥市場横掃江南及北京,山東地區,愈演而愈 熾,後將再及。 自《古今注》起,釋蟋蟀而重其聲者所引申出來的另一番率涉 世人的說法,不在其於性别活動上對織機瀨婦所作的文章,而在其 對中古男性世界所著意的各種鳴聲與鳴物所代表的哲思。也就是 說,西晉崔豹此處所謂「得寒則鳴」的蟋蟀,一則上承詩經「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之上古君子之風的嚮慕與想像31(實際上這正是 上古以來「莎雞」說歷久不衰,以及雞禽在中國人文天地裡的頒正 引人雋永之意),再則下開唐韓愈「送孟東野序」中破首「大凡物 不得其下则鳴」之嘆2。不論是鳴於如晦之風雨,生於初秋,得寒 則鳴,或者遭逢不不之凹凸而不能不發爲聲響,對浸淫於中國人文 古典至今千年以上的中古士子而言,作鳴之細物如蟋蟀,其發馨之 時,之際,之意涵,很難不引起彼等對自身處境之感觸。正面而 言,是所謂「隨時」,依季變化而發聲的天性,自有其儒者聖之 「時」者之氣質。另一方面來看,當然也可以理解成對於時而風雨 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