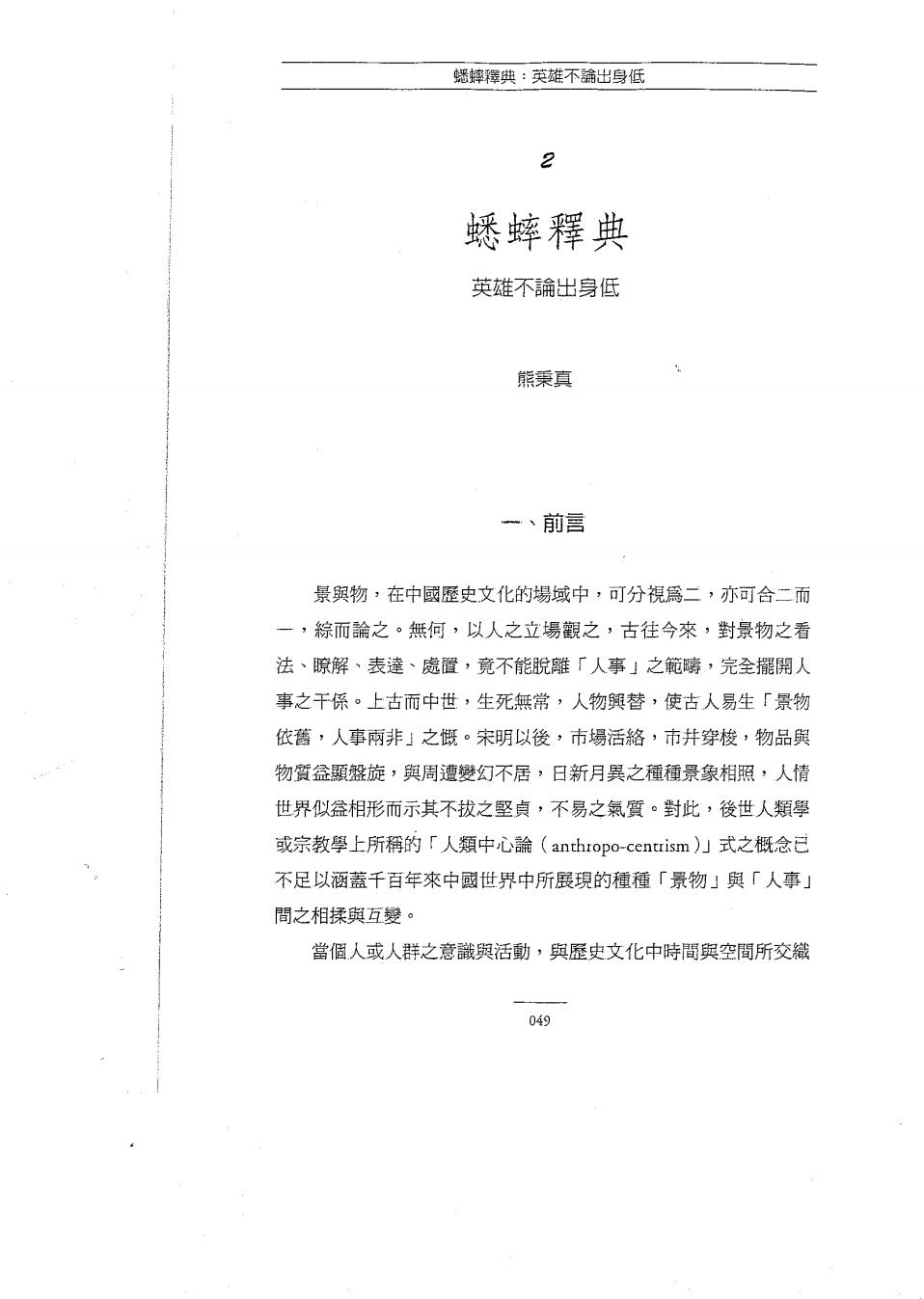
蟋蟀攀典:英雄不論出身低 2 蟋蟀釋典 英雄不論出身低 熊秉真 一、前言 景與物,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場域中,可分視爲二,亦可合二而 一,粽而論之。無何,以人之立場觀之,古往今來,對景物之看 法、暸解、表達丶處置,竟不能脫離「人事」之範疇,完全擺開人 事之干係。上古而中世,生死無常,人物興替,使古人易生「景物 依舊,人事兩非」之慨。宋明以後,市場活絡,市井穿梭,物品與 物質盒顯盤旋,與周遭變幻不居,日新月異之種種景象相照,人情 世界似盒相形而示其不拔之堅貞,不易之氣質。對此,後世人類學 或宗教學上所的「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sm)」式之概念已 不足以涵蓄千百年來中國世界中所展現的種種「景物」與「人事」 間之相揉與互變。 當個人或人群之意識與活動,與雁史文化中時間與空間所交織 049

睹物思人 成的系譜相逢,景·物,或景物·逐一則成篇歷史文化意藏與活動 的内容或主體,同時與文字、圖像等其他「證據」併列,成爲個人 或人群意藏與活動所運用的器皿、工具,乃至此類意藏與活動所留 下的諸般歷史痕跡、文化遺產之一種面目·某種素材。由此角度出 發,數千年來中國民間傳講與娛樂文化中的「蟋蟀」,由上古之 「莎雞」說,經中世之「鳴蟲」,終至近世翻轉爲士庶老小懷中手上 之「猛將」。此綿延而曲折之變化,本非一脈相承之思縷能盡,細 索起來,卻不能不篇千百年來,南北東西,仕女頑童,浪人雅士喜 樂哀愁之共繫此物,怒而交集某景,而爲奇誕之嘆。如今追蹤此細 物殊景之婉蜓、發展,其思其情,固可穿鑿遠古近世之時空,對其 間中國社會人群耳目排遣世界,作一葉知秋之窺,同時由鳴「禽」 而鬥「蟲」,此生物在中國歷史文化,社會生活中之際遇,亦頗是 見微而知著,透露宏觀人群世界中若干演化訊息之關键,以爲比較 文化史上「景物」與「人事」交相更替之一範例。 二、睹物與思人一上古莎雞說之起源 宋而明清,土子之間鬥弄蟋蟀日盒成風以後,文獻掌故亦有溯 古之求。相關之用力,不論類書或專輯,最後於上古源流之稽,嘗 得《詩經》、《禮記》、《爾雅》、《汲周書》、《准南子》等五典· 五倏資料,.言簡意賅,大抵均繞其居息,行止,及稱謂(即「釋名」 問題)三方面重點著墨· 詩經相關資料者二條,一爲唐風「蟋蟀」,文日:-「蟋蟀在 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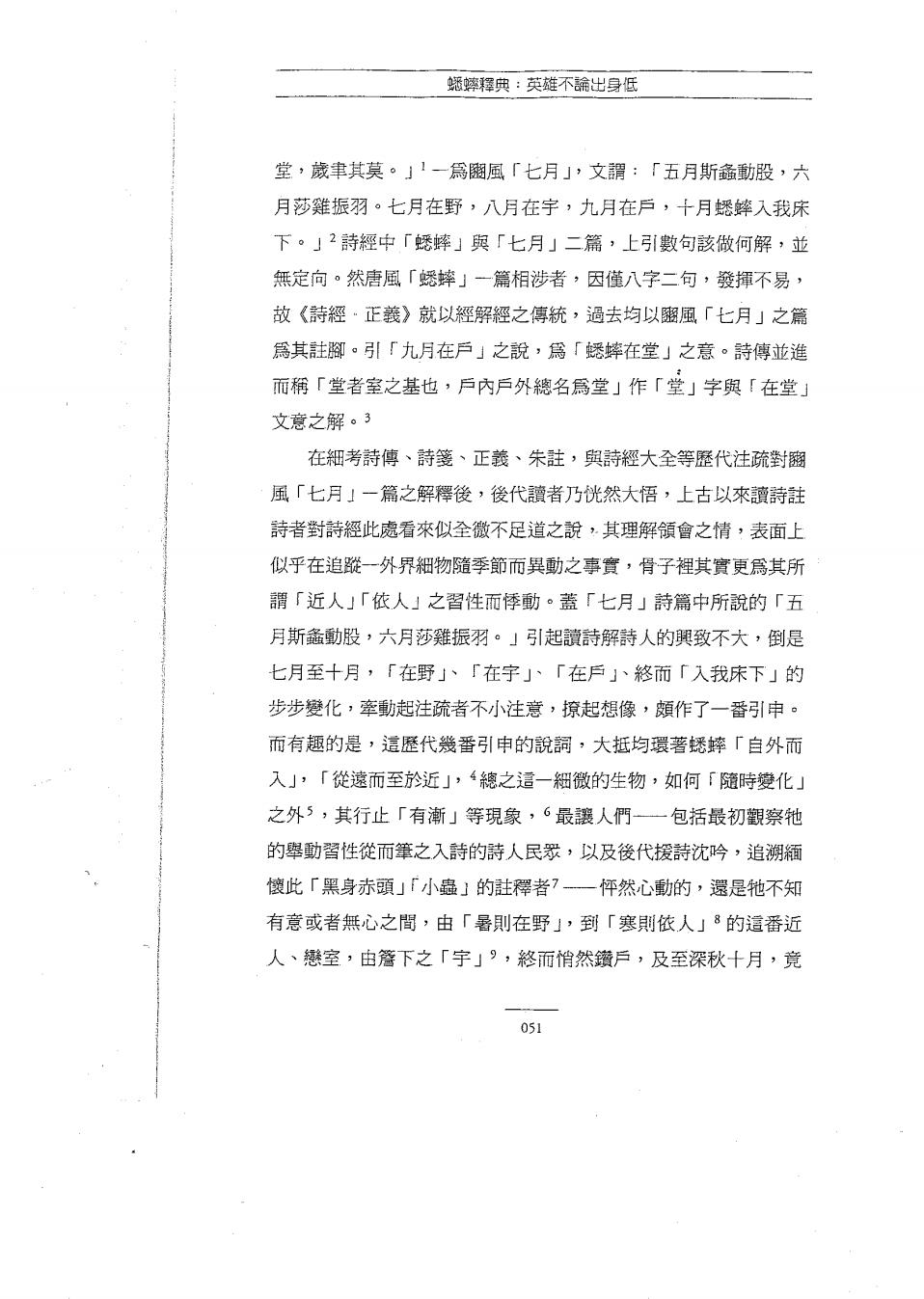
蟋蟀釋典:英雄不論出身低 堂,歲聿其莫。」1一爲豳風「七月」,文謂:「五月斯螽動股,六 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 下。」2詩經中「蟋蟀」與「七月」二篇,上引數句骸做何解,並 無定向。然唐風「蟋蟀」一篇相涉者,因僅八字二句,發揮不易, 故《詩經·正義》就以經解經之傳統,過去均以豳風「七月」之篇 篇其註腳。引「九月在戶」之說,爲「蟋蟀在堂」之意。詩傳並進 而稱「堂者室之基也,戶内戶外德名爲堂」作「堂」字與「在堂」 文意之解。3 在細考詩傅、詩箋、正義、朱註,與詩經大全等歷代注疏對豳 風「七月」一篇之解釋後,後代讀者乃祧然大悟,上古以來讀詩註 詩者對詩經此處看來似全微不足道之說,其理解頜會之情,表面上 似乎在追蹤一外界細物隨季節而異動之事寶,骨子裡其實更爲其所 蕭「近人」「依人」之習性而悸動。蓋「七月」詩篇中所說的「五 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引起讀詩解詩人的興致不大,倒是 七月至十月,「在野」、「在宇」、「在戶」~怒而「入我床下」的 步步變化,牵動起注疏者不小注意,撩起想像,頗作了一番引申。 而有趣的是,這歷代幾番引申的說詞,大抵均環著蟋蟀「自外而 入」,「從遠而至於近」,4總之這一細微的生物,如何「隨時變化」 之外5,其行止「有渐」等現象,6最諼人們一包括最初觀察牠 的舉動習性從而筆之入詩的詩人民眾,以及後代援詩沈吟,追溯緬 懷此「黑身赤頭」「小蟲」的註釋者7一悴然心動的,還是牠不知 有意或者無心之間,由「暑則在野」,到「寒則依人」8的這番近 人、戀室,由簷下之「宇」9,終而悄然鑽戶,及至深秋十月,竟 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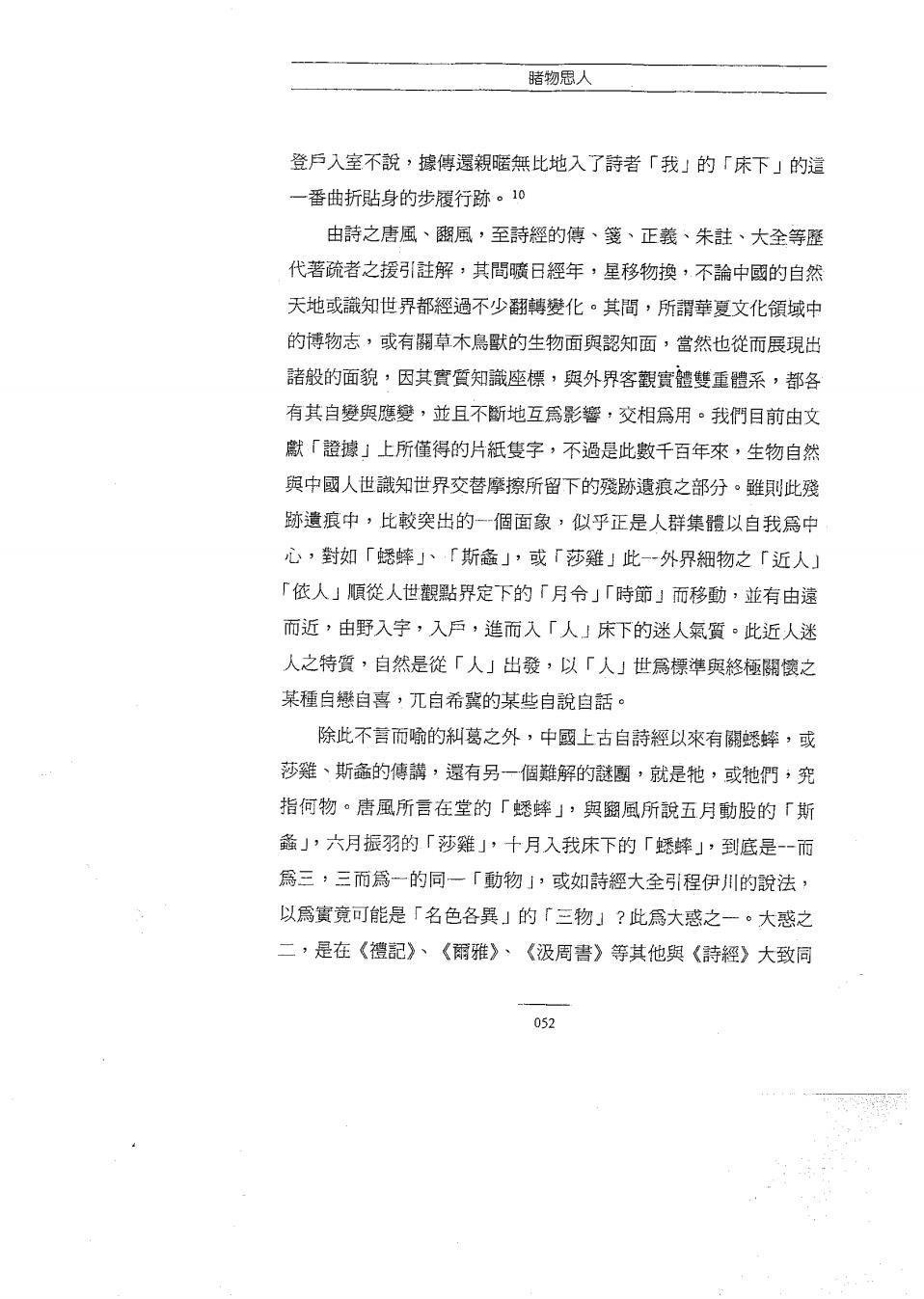
睹物思人 登戶入室不說,據傳還親暱無比地入了詩者「我」的「床下」的道 一番曲折贴身的步履行跡。10 由詩之唐風、豳風·至詩經的傳、箋、正義、朱註、大全等歷 代著疏者之援引註解,其間曠日經年,星移物换,不論中國的自然 天地或識知世界都經過不少翻轉變化·其間,所謂華夏文化頜域中 的博物志,或有翻草木鳥獸的生物面與認知面,當然也從而展現出 諸般的面貌,因其寶質知識座標,與外界客觀實體雙重體系,都各 有其自變與應變,並且不斷地互爲影響,交相爲用。我們目前由文 獻「證據」上所僅得的片紙隻字,不過是此數千百年來,生物自然 與中國人世藏知世界交替摩擦所留下的殘胁遗痕之部分。雖則此殘 跡遺痕中,比較突出的-個面象,似乎正是人群集體以自我爲中 心,對如「蟋蟀」、「斯螽」,或「莎雞」此-外界細物之「近人」 「依人」順從人世觀點界定下的「月令」「時節」而移動,並有由遠 而近,由野入宇,入戶,進而入「人」床下的迷人氣質·此近人迷 人之特質,自然是從「人」出發,以「人」世爲標準與終極關懷之 某種自懋自喜,兀自希冀的某些自說自話。 除此不言而喻的糾葛之外,中國上古自詩經以來有關蟋蟀,或 莎雞、斯螽的傳麟,還有另一個難解的謎團,就是牠,或牠們·究 指何物。唐風所言在堂的「蟋蟀」,與翻風所說五月動股的「斯 螽」,六月振羽的「莎雞」,十月入我床下的「蟋蟀」,到底是-而 爲三·三而爲一的同一「動物」,或如詩經大全引程伊川的說法, 以爲實竟可能是「名色各異」的「三物」?此震大惑之一。大惑之 二,是在《禮記》、《爾雅》、《汲周書》等其他與《詩經》大致同 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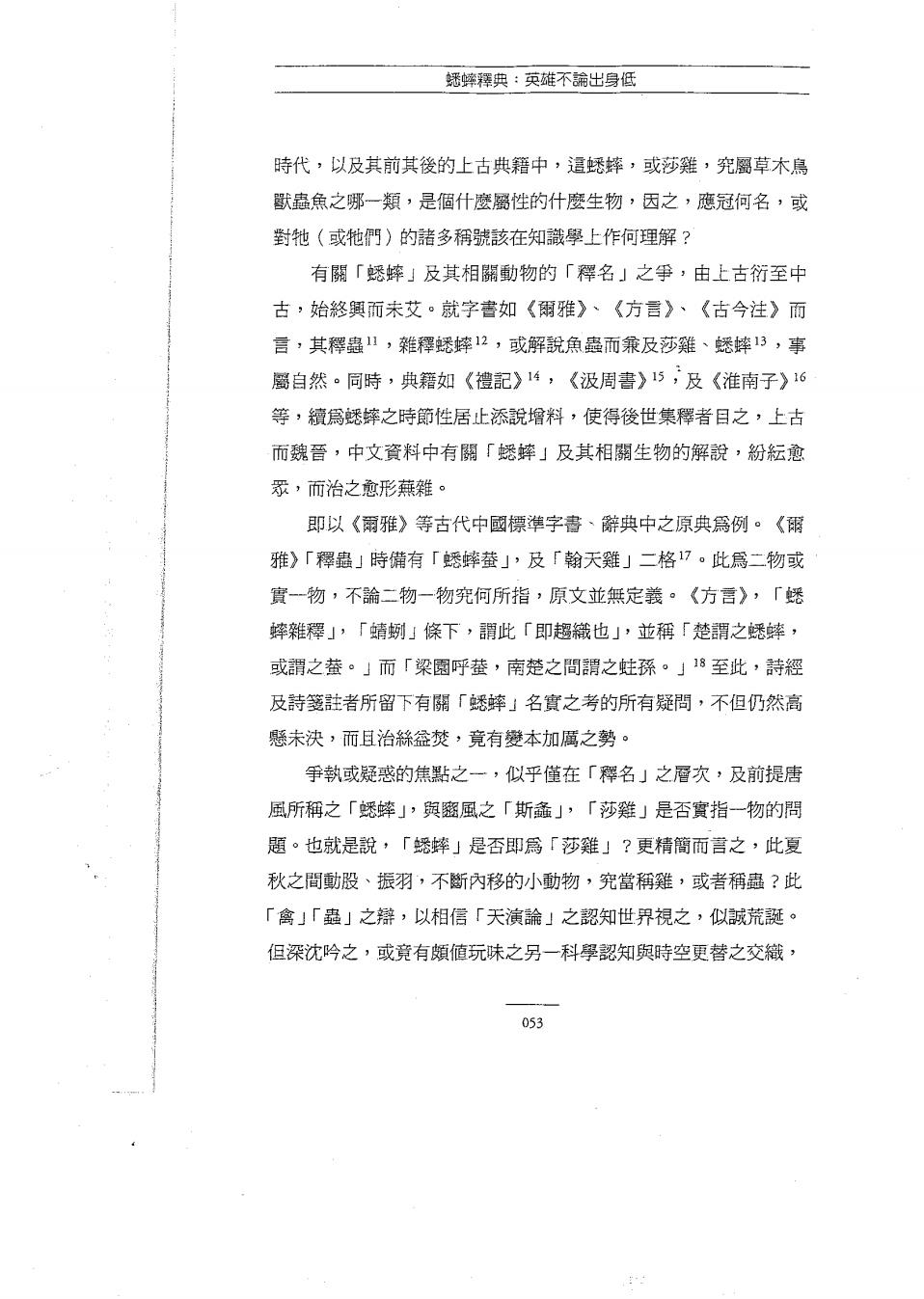
蟋蟀釋典:英雄不論出身低 時代,以及其前其後的上古典籍中,逼蟋蟀,或莎雞,究屬草木鳥 默蟲魚之哪一類,是個什夔屬性的什麼生物,因之,應冠何名,或 對牠(或他們門)的諸多稱號骸在知識學上作何理解? 有關「蟋蟀」及其相關動物的「釋名」之争,由上古衍至中 古,始終興而未艾。就字書如《爾雅》、《方言》、《古今注》而 言,其釋蟲Ⅱ,雜釋蟋蟀12,或解說魚蟲而兼及莎雞丶蟋蟀13,事 屬自然。同時,典籍如《禮記》1,《汲周書》15,及《淮南子》6 等,續爲蟋蟀之時節性居止添說增料,使得後世集釋者目之,上古 而魏晉,中文資料中有關「蟋蟀」及其相關生物的解說,紛紜愈 爱,而治之愈形蕪雜。 即以《爾雅》等古代中國標準字書~等典中之原典爲例。《爾 雅》「釋蟲」時備有「蟋蟀蛬」,及「翰天雞」二格17。此爲二物或 實-一物,不論二物一物究何所指,原文並無定義。《方言》,「蟋 蟀雜釋」,「靖蜊」條下,謂此「即趨織也」,並稱「楚謂之蟋蟀, 或謂之蛬。」而「梁園呼蛬,南楚之間謂之蛀孫。」18至此,詩經 及詩箋註者所留下有關「蟋蟀」名實之考的所有凝問,不但仍然高 懸未决,而且治絲金焚,竟有變本加厲之勢· 争執或凝惑的焦點之一,似乎僅在「釋名」之層次,及前提唐 風所稱之「蟋蟀」,與魑風之「斯螽」,「莎雞」是否寳指一物的問 題。也就是說,「蟋蟀」是否即爲「莎雞」?更精簡而言之,此夏 秋之間動股、振羽,不斷內移的小動物,究當稱雞,或者稱蟲?此 「禽」「蟲」之辯,以相信「天演論」之認知世界視之,似賦荒誕。 但深沈吟之,或竟有頗値玩昧之另一科學認知與時空更替之交織, 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