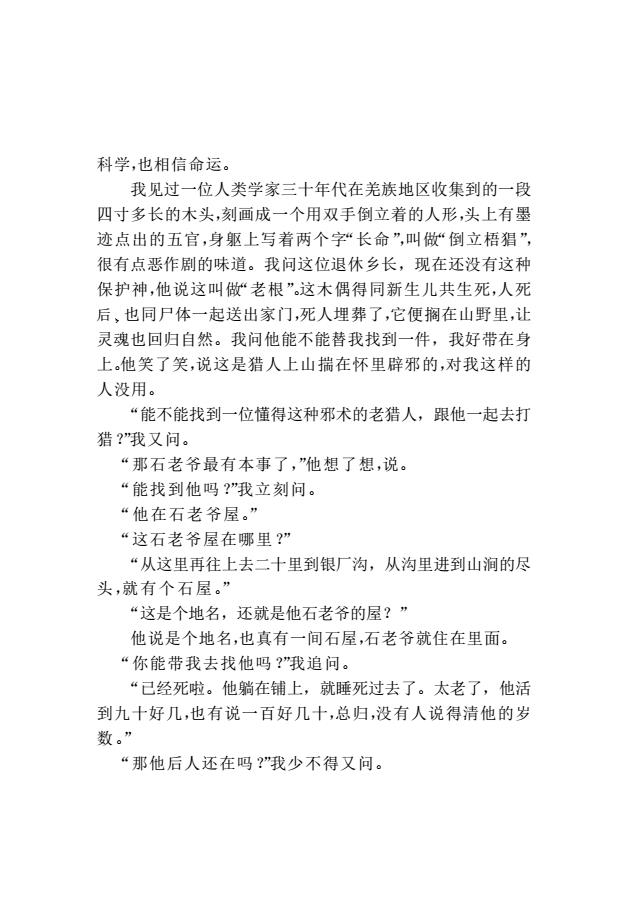
科学,也相信命运。 我见过一位人类学家三十年代在羌族地区收集到的一段 四寸多长的木头,刻画成一个用双手倒立着的人形,头上有墨 迹点出的五官,身躯上写着两个字“长命”,叫做“倒立梧猖”, 很有点恶作剧的味道。我问这位退休乡长,现在还没有这种 保护神,他说这叫做“老根”这木偶得同新生儿共生死,人死 后,也同尸体一起送出家门,死人埋葬了,它便搁在山野里,让 灵魂也回归自然。我问他能不能替我找到一件,我好带在身 上。他笑了笑,说这是猎人上山揣在怀里辟邪的,对我这样的 人没用。 “能不能找到一位懂得这种邪术的老猎人,跟他一起去打 猎?”我又问。 “那石老爷最有本事了,”他想了想,说。 “能找到他吗?”我立刻问。 “他在石老爷屋。” “这石老爷屋在哪里?” “从这里再往上去二十里到银厂沟,从沟里进到山涧的尽 头,就有个石屋。” “这是个地名,还就是他石老爷的屋?” 他说是个地名,也真有一间石屋,石老爷就住在里面。 “你能带我去找他吗?”我追问。 “已经死啦。他躺在铺上,就睡死过去了。太老了,他活 到九十好几,也有说一百好几十,总归,没有人说得清他的岁 数。” “那他后人还在吗?”我少不得又问
后 科学,也相信命运。 我见过一位人类学家三十年代在羌族地区收集到的一段 四寸多长的木头,刻画成一个用双手倒立着的人形,头上有墨 迹点出的五官,身躯上写着两个字“长命”,叫做“倒立梧猖”, 很有点恶作剧的味道。我问这位退休乡长,现在还没有这种 保护神,他说这叫做“老根”。这木偶得同新生儿共生死,人死 也同尸体一起送出家门,死人埋葬了,它便搁在山野里,让 灵魂也回归自然。我问他能不能替我找到一件,我好带在身 上。他笑了笑,说这是猎人上山揣在怀里辟邪的,对我这样的 人没用。 “能不能找到一位懂得这种邪术的老猎人,跟他一起去打 猎?”我又问。 “那石老爷最有本事了,”他想了想,说。 “能找到他吗 ?”我立刻问。 “他在石老爷屋。” “这石老爷屋在哪里?” “从这里再往上去二十里到银厂沟,从沟里进到山涧的尽 头,就有个石屋。” “这是个地名,还就是他石老爷的屋?” 他说是个地名,也真有一间石屋,石老爷就住在里面。 “你能带我去找他吗?”我追问。 “已经死啦。他躺在铺上,就睡死过去了。太老了,他活 到九十好几,也有说一百好几十,总归,没有人说得清他的岁 数。” “那他后人还在吗?”我少不得又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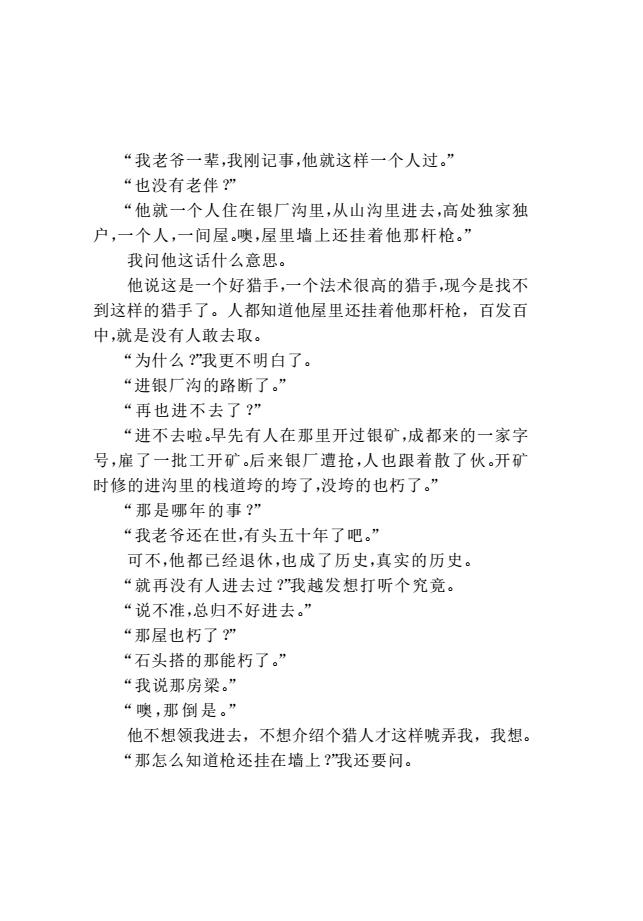
“我老爷一辈,我刚记事,他就这样一个人过。” “也没有老伴?” “他就一个人住在银厂沟里,从山沟里进去,高处独家独 户,一个人,一间屋。噢,屋里墙上还挂着他那杆枪。” 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 他说这是一个好猎手,一个法术很高的猎手,现今是找不 到这样的猎手了。人都知道他屋里还挂着他那杆枪,百发百 中,就是没有人敢去取。 “为什么?”我更不明白了。 “进银厂沟的路断了。” “再也进不去了?” “进不去啦。早先有人在那里开过银矿,成都来的一家字 号,雇了一批工开矿。后来银厂遭抢,人也跟着散了伙。开矿 时修的进沟里的栈道垮的垮了,没垮的也朽了。” “那是哪年的事?” “我老爷还在世,有头五十年了吧。” 可不,他都已经退休,也成了历史,真实的历史。 “就再没有人进去过?”我越发想打听个究竞。 “说不准,总归不好进去。” “那屋也朽了?” “石头搭的那能朽了。” “我说那房梁。” “噢,那倒是。” 他不想领我进去,不想介绍个猎人才这样唬弄我,我想。 “那怎么知道枪还挂在墙上?”我还要问
“我老爷一辈,我刚记事,他就这样一个人过。” “也没有老伴?” “他就一个人住在银厂沟里,从山沟里进去,高处独家独 户,一个人,一间屋。噢,屋里墙上还挂着他那杆枪。” 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 他说这是一个好猎手,一个法术很高的猎手,现今是找不 到这样的猎手了。人都知道他屋里还挂着他那杆枪,百发百 中,就是没有人敢去取。 “为什么?”我更不明白了。 “进银厂沟的路断了。” “再也进不去了 ?” “进不去啦。早先有人在那里开过银矿,成都来的一家字 号,雇了一批工开矿。后来银厂遭抢,人也跟着散了伙。开矿 时修的进沟里的栈道垮的垮了,没垮的也朽了。” “那是哪年的事 ?” “我老爷还在世,有头五十年了吧。” 可不,他都已经退休,也成了历史,真实的历史。 “就再没有人进去过?”我越发想打听个究竟。 “说不准,总归不好进去。” “那屋也朽了?” “石头搭的那能朽了。” “我说那房梁。” “噢,那 倒是。” 他不想领我进去,不想介绍个猎人才这样唬弄我,我想。 “那怎么知道枪还挂在墙上?”我还要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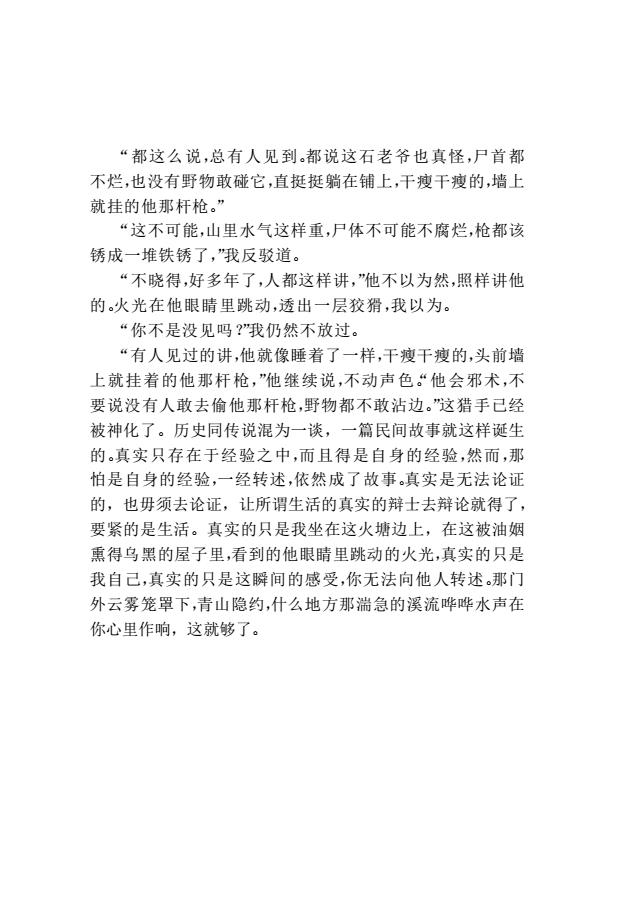
“都这么说,总有人见到。都说这石老爷也真怪,尸首都 不烂,也没有野物敢碰它,直挺挺躺在铺上,干瘦干瘦的,墙上 就挂的他那杆枪。” “这不可能,山里水气这样重,尸体不可能不腐烂,枪都该 锈成一堆铁锈了,"”我反驳道。 “不晓得,好多年了,人都这样讲,”他不以为然,照样讲他 的。火光在他眼睛里跳动,透出一层狡猾,我以为。 “你不是没见吗?”我仍然不放过。 “有人见过的讲,他就像睡着了一样,干瘦干瘦的,头前墙 上就挂着的他那杆枪,”他继续说,不动声色。“他会邪术,不 要说没有人敢去偷他那杆枪,野物都不敢沾边。"这猎手己经 被神化了。历史同传说混为一谈,一篇民间故事就这样诞生 的。真实只存在于经验之中,而且得是自身的经验,然而,那 怕是自身的经验,一经转述,依然成了故事。真实是无法论证 的,也毋须去论证,让所谓生活的真实的辩士去辩论就得了, 要紧的是生活。真实的只是我坐在这火塘边上,在这被油姻 熏得乌黑的屋子里,看到的他眼睛里跳动的火光,真实的只是 我自己,真实的只是这瞬间的感受,你无法向他人转述。那门 外云雾笼罩下,青山隐约,什么地方那湍急的溪流哗哗水声在 你心里作响,这就够了
“都这么说,总有人见到。都说这石老爷也真怪,尸首都 不烂,也没有野物敢碰它,直挺挺躺在铺上,干瘦干瘦的,墙上 就挂的他那杆枪。” “这不可能,山里水气这样重,尸体不可能不腐烂,枪都该 锈成一堆铁锈了,”我反驳道。 “不晓得,好多年了,人都这样讲,”他不以为然,照样讲他 的。火光在他眼睛里跳动,透出一层狡猾,我以为。 “你不是没见吗?”我仍然不放过。 “有人见过的讲,他就像睡着了一样,干瘦干瘦的,头前墙 上就挂着的他那杆枪,”他继续说,不动声色“。他会邪术,不 要说没有人敢去偷他那杆枪,野物都不敢沾边。”这猎手已经 被神化了。历史同传说混为一谈,一篇民间故事就这样诞生 的。真实只存在于经验之中,而且得是自身的经验,然而,那 怕是自身的经验,一经转述,依然成了故事。真实是无法论证 的,也毋须去论证,让所谓生活的真实的辩士去辩论就得了, 要紧的是生活。真实的只是我坐在这火塘边上,在这被油姻 熏得乌黑的屋子里,看到的他眼睛里跳动的火光,真实的只是 我自己,真实的只是这瞬间的感受,你无法向他人转述。那门 外云雾笼罩下,青山隐约,什么地方那湍急的溪流哗哗水声在 你心里作响,这就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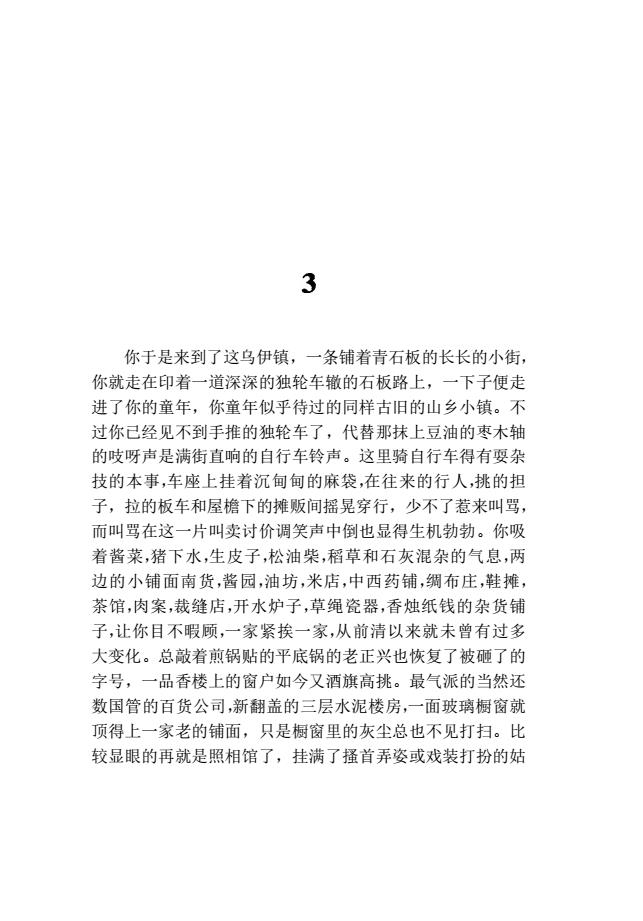
3 你于是来到了这乌伊镇,一条铺着青石板的长长的小街, 你就走在印着一道深深的独轮车辙的石板路上,一下子便走 进了你的童年,你童年似乎待过的同样古旧的山乡小镇。不 过你已经见不到手推的独轮车了,代替那抹上豆油的枣木轴 的吱呀声是满街直响的自行车铃声。这里骑自行车得有耍杂 技的本事,车座上挂着沉甸甸的麻袋,在往来的行人,挑的担 子,拉的板车和屋檐下的摊贩间摇晃穿行,少不了惹来叫骂, 而叫骂在这一片叫卖讨价调笑声中倒也显得生机勃勃。你吸 着酱菜,猪下水,生皮子,松油柴,稻草和石灰混杂的气息,两 边的小铺面南货,酱园,油坊,米店,中西药铺,绸布庄,鞋摊, 茶馆,肉案,裁缝店,开水炉子,草绳瓷器,香烛纸钱的杂货铺 子,让你目不暇顾,一家紧挨一家,从前清以来就未曾有过多 大变化。总敲着煎锅贴的平底锅的老正兴也恢复了被砸了的 字号,一品香楼上的窗户如今又酒旗高挑。最气派的当然还 数国管的百货公司,新翻盖的三层水泥楼房,一面玻璃橱窗就 顶得上一家老的铺面,只是橱窗里的灰尘总也不见打扫。比 较显眼的再就是照相馆了,挂满了搔首弄姿或戏装打扮的姑
你于是来到了这乌伊镇,一条铺着青石板的长长的小街, 你就走在印着一道深深的独轮车辙的石板路上,一下子便走 进了你的童年,你童年似乎待过的同样古旧的山乡小镇。不 过你已经见不到手推的独轮车了,代替那抹上豆油的枣木轴 的吱呀声是满街直响的自行车铃声。这里骑自行车得有耍杂 技的本事,车座上挂着沉甸甸的麻袋,在往来的行人,挑的担 子,拉的板车和屋檐下的摊贩间摇晃穿行,少不了惹来叫骂, 而叫骂在这一片叫卖讨价调笑声中倒也显得生机勃勃。你吸 着酱菜,猪下水,生皮子,松油柴,稻草和石灰混杂的气息,两 边的小铺面南货,酱园,油坊,米店,中西药铺,绸布庄,鞋摊, 茶馆,肉案,裁缝店,开水炉子,草绳瓷器,香烛纸钱的杂货铺 子,让你目不暇顾,一家紧挨一家,从前清以来就未曾有过多 大变化。总敲着煎锅贴的平底锅的老正兴也恢复了被砸了的 字号,一品香楼上的窗户如今又酒旗高挑。最气派的当然还 数国管的百货公司,新翻盖的三层水泥楼房,一面玻璃橱窗就 顶得上一家老的铺面,只是橱窗里的灰尘总也不见打扫。比 较显眼的再就是照相馆了,挂满了搔首弄姿或戏装打扮的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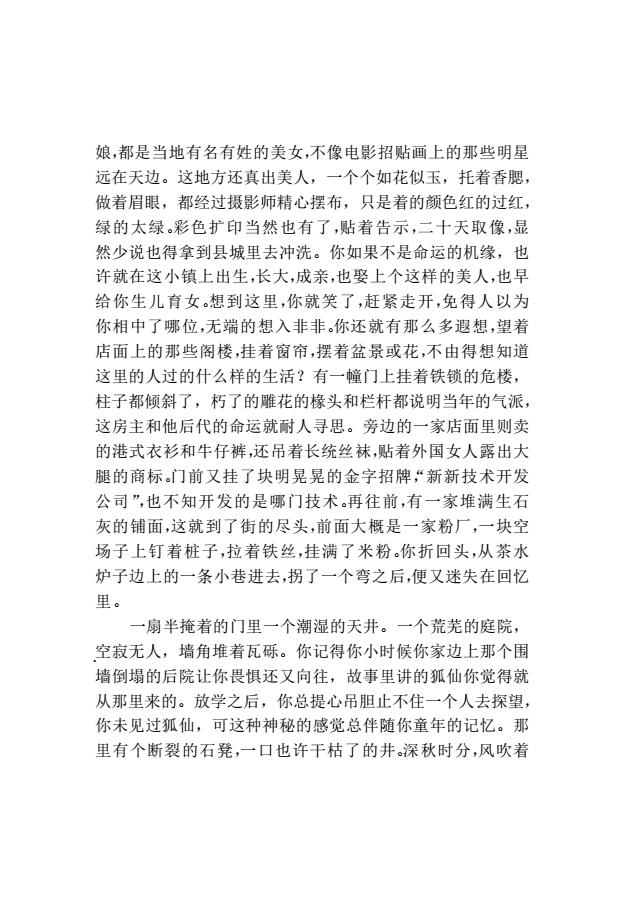
娘,都是当地有名有姓的美女,不像电影招贴画上的那些明星 远在天边。这地方还真出美人,一个个如花似玉,托着香腮, 做着眉眼,都经过摄影师精心摆布,只是着的颜色红的过红, 绿的太绿。彩色扩印当然也有了,贴着告示,二十天取像,显 然少说也得拿到县城里去冲洗。你如果不是命运的机缘,也 许就在这小镇上出生,长大,成亲,也娶上个这样的美人,也早 给你生儿育女。想到这里,你就笑了,赶紧走开,免得人以为 你相中了哪位,无端的想入非非。你还就有那么多遐想,望着 店面上的那些阁楼,挂着窗帘,摆着盆景或花,不由得想知道 这里的人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有一幢门上挂着铁锁的危楼, 柱子都倾斜了,朽了的雕花的椽头和栏杆都说明当年的气派, 这房主和他后代的命运就耐人寻思。旁边的一家店面里则卖 的港式衣衫和牛仔裤,还吊着长统丝袜,贴着外国女人露出大 腿的商标。门前又挂了块明晃晃的金字招牌,“新新技术开发 公司”,也不知开发的是哪门技术。再往前,有一家堆满生石 灰的铺面,这就到了街的尽头,前面大概是一家粉厂,一块空 场子上钉着桩子,拉着铁丝,挂满了米粉。你折回头,从茶水 炉子边上的一条小巷进去,拐了一个弯之后,便又迷失在回忆 里。 一扇半掩着的门里一个潮湿的天井。一个荒芜的庭院, 空寂无人,墙角堆着瓦砾。你记得你小时候你家边上那个围 墙倒塌的后院让你畏惧还又向往,故事里讲的狐仙你觉得就 从那里来的。放学之后,你总提心吊胆止不住一个人去探望, 你未见过狐仙,可这种神秘的感觉总伴随你童年的记忆。那 里有个断裂的石凳,一口也许干枯了的井。深秋时分,风吹着
娘,都是当地有名有姓的美女,不像电影招贴画上的那些明星 远在天边。这地方还真出美人,一个个如花似玉,托着香腮, 做着眉眼,都经过摄影师精心摆布,只是着的颜色红的过红, 绿的太绿。彩色扩印当然也有了,贴着告示,二十天取像,显 然少说也得拿到县城里去冲洗。你如果不是命运的机缘,也 许就在这小镇上出生,长大,成亲,也娶上个这样的美人,也早 给你生儿育女。想到这里,你就笑了,赶紧走开,免得人以为 你相中了哪位,无端的想入非非。你还就有那么多遐想,望着 店面上的那些阁楼,挂着窗帘,摆着盆景或花,不由得想知道 这里的人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有一幢门上挂着铁锁的危楼, 柱子都倾斜了,朽了的雕花的椽头和栏杆都说明当年的气派, 这房主和他后代的命运就耐人寻思。旁边的一家店面里则卖 的港式衣衫和牛仔裤,还吊着长统丝袜,贴着外国女人露出大 腿的商标。门前又挂了块明晃晃的金字招牌“,新新技术开发 公司”,也不知开发的是哪门技术。再往前,有一家堆满生石 灰的铺面,这就到了街的尽头,前面大概是一家粉厂,一块空 场子上钉着桩子,拉着铁丝,挂满了米粉。你折回头,从茶水 炉子边上的一条小巷进去,拐了一个弯之后,便又迷失在回忆 里。 一扇半掩着的门里一个潮湿的天井。一个荒芜的庭院, 空寂无人,墙角堆着瓦砾。你记得你小时候你家边上那个围 墙倒塌的后院让你畏惧还又向往,故事里讲的狐仙你觉得就 从那里来的。放学之后,你总提心吊胆止不住一个人去探望, 你未见过狐仙,可这种神秘的感觉总伴随你童年的记忆。那 里有个断裂的石凳,一口也许干枯了的井。深秋时分,风吹着